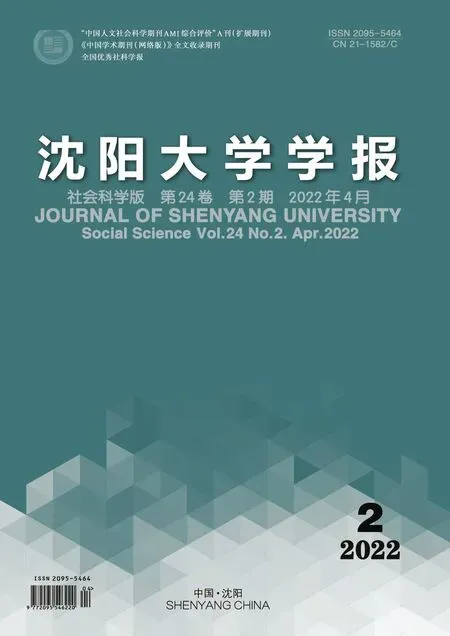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对立和纠结及划界问题再议
车 飞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2.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1)
近年来, 对类成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川方言中, 以任志萍[1]、殷志佳[2]为代表。 此外, 白云飞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为语料基础对其中359个四字格类成语进行分析, 并涉及类成语与惯用语、歇后语的区分问题[3]。 将类成语与俗成语两者划界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始于刘燕[4]。 截至目前, 尚未见其他更深度讨论此论题的新文献。 以上文献对类成语与俗成语的讨论, 还存在3个方面问题: 一是概念划分不明晰; 二是语料归属有争议; 三是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区分标准比较模糊。
本文把“类成语”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5]、方言成语放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进行比较, 重新探讨类成语的界域。 拟从俗语与成语的分野, 俗成语与雅成语、方言成语的空间分布, 类成语的空间归属, 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可能划界标准及其分歧实质等角度展开讨论。
一、 俗语与成语:划界纠葛与源头回溯
想要探明俗成语与类成语的界限,还需回溯到俗语与成语的关系上面。
1. 典型俗语:通俗定型、广泛流行、简练形象
“俗语”定义较为丰富,徐宗才[6]列举了11种观点和9种辞书解释,认为定义比较恰当并得到多数认同的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也叫俗话。”[7]
2. 典型成语:典范雅正、四字定位、二二相成
成语定义有宽严之分。宽式定义为广义理解,可包括二字成语(如“推敲”)、三字成语(如“口头禅”)、四字成语(如“忧心忡忡”)、五字以上的短句及复句成语(如“水至清则无鱼”“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不过这种广义成语归类,不利于划清成语与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语类的界限。
严式定位为狭义定义, 即四言定位, 是人们心目中的典型成语。成语词典中收录的基本上为四字形式, 也比较符合汉语使用者语感。 以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为例, 四字格形式成语占比达到95.58%, 新版《中国成语大辞典》(2020)收录的成语则全都为四字格[8]。 温端政为持狭义理解代表, 以“二二相承”四字格结构为标志, 表述语中除去谚语的剩余部分及描述语中除去惯用语的剩余部分都为成语[9]。 补充条件有3条: 一是对于“不A不B”“七A八B”“可A可B”式四字格, 应根据其结构的相对固定性来划归, 尊重不断变化的惯用性和个人语感, 允许“过渡性”的不同处理意见, 这类短语还有“类固定短语”[10]、 “定式镶嵌四字格”[11]、“框式结构”[12]等称谓, 但范围大了许多, 近些年已经延伸到“X你个头”类新兴类结构; 二是对于新生的、结构尚不十分定型的四字格归属, 允许有个“考察期”, 静观其变, 暂不下结论; 三是对于“AABB”式四字格的归属, 用是否为语法范畴上的重迭、是否具有惯用性这两条标准来检验。
3. 纠葛部分与游离状态:四字格
俗语与成语的区别客观来说较为明显,形式上成语多是四言体,俗语多是五言以上的杂言体;语体风格上,成语典雅庄重倾向于书面语,俗语则通俗活泼偏向于口语风格。例如:
甲组: 笨鸟先飞、财大气粗、树大招风、僧多粥少、事不过三、鸡飞蛋打、水涨船高;
乙组: 南辕北辙、无济于事、分道扬镳、巧夺天工、两全其美、一箭双雕、随心所欲;
从语言风格(庄与谐、雅与俗)和语义完整性上看,容易辨认出甲组是俗语、乙组是成语。
但这类四字格正是俗语和成语的纠葛部分, 俗成语即为纠葛产物。 对于甲组类四字俗语, 刘玉凯、乔云霞作“俗成语”处理, 在他们编注的《中国俗成语》(1991年)里达到了8 000条, 认为“俗成语”是“通俗成语”, 是历代人民群众集体口头创造的成语, 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13]。 对这种处理方式, 徐宗才持肯定意见, 说明这些俗语与成语非常接近[6]11-36。 王勤则持否定意见, 认为这种做法不足取, 破坏了成语整体统一的风格。 从属性上说, 所谓“俗成语”实际就是四音节俗语, 其风格特性与所表达的内容特点同杂言体俗语性质一样[14]。
在成语中离析出“俗成语”这一概念,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促进研究的进一步细化、深化、明确化,忧的是这种处理又带来模糊度较高、区分度较低的问题。
二、 代表性分歧意见及简评
1. 定义不一,表述模糊
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定义有两种代表性意见,见表1。

表1 对类成语与俗成语的不同定义
上述两种定义,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共同点是:口语色彩浓厚,语义直白、结构稳定的四字格形式。但白云飞侧重于时间与空间的框定[3]8-16,刘燕侧重于同其他相似语类作比较[4]112-114,在不同点上区分不够明显,尚未触及到两者的差异根源。
2. 微观比对,不易辨别
再看两种观点对类成语特点的具体描述,以及刘燕对俗成语特点的具体描述,见表2。
从表2可看出, 两文对类成语的表述中, 第②③条正好相反。 白云飞中“类成语”看起来与刘燕所说的“俗成语”更为相似。 假设用表2中刘燕的5条界定原则来验证“类成语”特点, 语料采用白云飞统计的359条类成语, 发现以上5条界定原则中①③④这3条不符合类成语的实际情况[15]。 一是结构上一般可以增减、替换、颠倒、分拆, 除了刘燕文中列举的4个类成语(鸵鸟政策、你争我夺、畅通无阻、流血牺牲)可以改换外, 白云飞文中还有以下6个类成语可以改换: 装疯卖傻→卖傻装疯、只言片语→片语只言、宝刀不老→宝刀未老、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胜利果实→胜利的果实、鳄鱼眼泪→鳄鱼的眼泪, 占全部类成语的比例仅约为1.67%, 看来“一般”应为“少数”。 二是意义往往是构成成分意义的体现, 通过对这359条类成语进行逐一查对, 具有比喻义、引申义的类成语如“狗急跳墙、帽子戏法、鸵鸟政策、卸磨杀驴、小肚鸡肠、鳄鱼眼泪”等共计77条, 占比约为21.45%, 剩下的为构成成分意义的体现, 这一点比白云飞有进步。 三是意义可以含义文雅, 也不一定通俗易懂, 类成语多数通俗易懂, 含义晦涩难懂的仅为少数, 如“大轰大嗡”(形容不注重实际, 只在形式上轰轰烈烈)。 四是具有书面或通用语色彩, 使用语域不受限制, 也不符合类成语实际, 口语色彩浓厚、语义直白才是类成语的特点。

表2 对类成语、俗成语性质的不同描述
3. 缺乏参照,差异难显
白云飞直接定名为类成语,把类成语理解为“类似成语”之意,回避了与俗成语的比较,重在观察、描写与解释这些类成语的语言学特点,所归纳的各项语法特征相对来说更经得住推敲。刘燕初衷很好,认为类成语是介于成语与自由短语之间的具有半熟语性质的短语,希望能在两者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遗憾的是“半熟语性质”是一个较模糊、宽泛的概念,试图通过界定俗成语来否定白云飞概括的类成语这些语法特征,得出的结论相对片面,把两类语言形式的关系弄得稍显混沌[16]。
假设都承认白文对类成语的界定和刘文对俗成语的界定,两者除了顶层语法性质有差异外,具体语法特征几乎相同,区别性特征也不很明显。这种无参照标准的界定反倒模糊了两者的差异,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 俗成语、雅成语、方言成语的空间分布差异
1. “俗成语”“雅成语”属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方言成语属于方言系统
温端政认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成语有雅俗之分,成语里除了雅成语外,还有俗成语[9]1-15,两者在来源、构成成分、通行范围等3方面存在差异。
再把范围扩大到方言成语,李小平对俗成语、雅成语和方言成语三者作了区分,认为所谓的俗成语不能指代方言成语……方言内部本质上并不存在雅俗之别的问题……在方言内部的成语,也就没有所谓的雅成语和俗成语的分别[17]。也就是说地方方言并不等同于俗语,方言成语不能指代俗成语,方言内部亦无雅俗之别。
因此,不管是俗成语还是雅成语,都属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只不过俗成语的口语色彩更浓,雅成语的书面语色彩更浓。而俗成语与方言成语也不能混同,俗成语属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方言成语属于方言系统。为更清楚观察它们的不同,见图1。

图1 俗成语、雅成语、方言成语的空间分布
图1未将俗成语、雅成语、方言成语三者的上位层次进一步框定,因为从语汇层面看,除了成语还有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不宜再扩大图示辖域。所示范围可作如下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包括俗成语和雅成语两个部分,方言成语相对于游离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之外,只有一小部分最终进入到俗成语类别。而俗成语很多条目均来自俗语,两者重合部分较多。
2. “俗成语”的3个层次及新定义
白云飞指出成语含有古朴、典雅之意,而“俗”意为通俗、直白,用“俗+成语”自相矛盾,这种完全排斥俗成语的提法值得商榷[3]7-8。刘燕将“俗成语”定义为是介于成语和俗语之间的较为惯用的熟语[4]112,看清楚了俗成语属于俗语与成语的交迭部分,不过又忽略了那些结构凝固、通用性较强的方言成语语源。此外,将俗成语的属性限定在熟语上,标准有些过于宽松,因为熟语范围很广,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俗语5大部分,不利于对俗成语的性质作进一步确认。
从图1可以看出,俗成语应该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四字格词语先为成语,然后演变为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俗成语部分。第二个层次:先是非四字格俗语,之后浓缩为四字格形式,并向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俗成语靠拢,最后被吸收,形成俗语与成语的交迭部分----俗成语。如成语“敝帚自珍”脱胎于俗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第三个层次:隶属于方言系统中的方言成语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具备通用语的性质,趋近于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俗成语部分。例如“一头雾水”最初流传于广州地区,但它具有成为共同语成语的特点,逐渐为广大受众所接受,成为了俗成语。
因此,可将俗成语定义修正如下:俗成语是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历代口头创作、口头运用的口语色彩较浓的“二二相承”的表述语或描述语,介于成语与俗语、方言成语之间,一部分俗语、方言成语结构凝固化、通用化之后可能演变为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俗成语。
3. 部分语料需重新归类
再反观刘玉凯、乔云霞编注的《中国俗成语》(1991)中收录的俗成语条目,应剔除纯方言成语或是俚语部分。比如京津地区的“没罪扛枷”、四川地区的“四棱吊肚”等40余条所谓俗成语,它们多流行于地方口语中,还不具备全民通用性,具有方言色彩,列为方言成语或俚语更妥当。
同样, 开篇提到的任志萍《四川方言中的类成语短语分析》和殷志佳《四川方言中的类成语短语分析》中列举的“类成语”形式, 把它们当作“方言成语”似乎更妥, 有些甚至只能算作“方言四字格”。 白云飞所列的359条类成语, 也应剔除里面的一些纯方言成语, 如“阿猫阿狗、吹灯拔蜡、归里包堆、门里出身、食亲财黑、死气白赖、一溜歪斜、奓着胆子”。
四、 类成语空间归属及可能划界标准
1. 游离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之外
应该说类成语与俗成语并不在同一词汇系统,在口语色彩上整体强于俗成语,尚游离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之外,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小部分类成语结构相对不固定,向类固定短语靠拢,沦为自由短语;二是结构逐渐凝固、口语色彩较浓厚、为大众所惯用的类成语,会逐渐趋向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中的俗成语部分,最后进入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
至此,可将这4个术语作一个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

图2 俗成语、雅成语、方言成语与类成语的空间分布
综上所述,类成语可试作如下定义:类成语游离于汉民族共同语成语系统之外,是近现代口头创作、口头运用的口语色彩很浓的二二相承的表述语或描述语,介于俗成语与类固定短语之间,更趋向于向类固定短语方向发展。比如:“鸡毛蒜皮”已基本演变为俗成语形式,“变化多端”则倾向于类固定短语。又如:框式结构“有A无B”中的“有教无类”为雅成语,但“有意无意”就更趋向于类固定短语。再如:方言成语“马马哈哈”(京津地区)、“憋里巴屈”(东北地区)、“四棱吊肚”(四川地区),恐怕很难再演变为俗成语。
2. 类成语与俗成语的3种宏观划界标准
类成语和俗成语根本语法性质的描写中都包含“二二相承的表述语或描述语”, 对这一本质属性的把握有助于更深一步认识这两种语类。 基于这一认识, 俗成语的3个层次及类成语的游离状态, 可能是操作性最佳的区分思路。 可以看出, 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对立状态是宏观层面的, 根本标准是在汉民族共同语系统中的空间分布不同, 顶层语法性质有差异。 除此之外, 曾提出词典收录情况标准和语用频率标准[18]等两条宏观区分标准, 不过这两个辅助标准局限性大于可操作性, 适用性存疑,较难作出一分为二的区分。
五、 超越差异:类成语与俗成语之间存在对立和纠结状态
1. 微观差异无法一刀切开
通过对已有成果的回顾发现,若采用非此即彼的做法,会让两者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图2中对两者的辖域描绘较为清晰:类成语虽然浮游于共同语成语系统之外,但有向俗成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类成语在微观语法特征上部分具备共同语成语的性质,有时甚至会更趋向于俗成语的发展方向,两者部分语法特征存在交迭也在情理之中。
面对这一现状,应该重视顶层语法性质的差异,淡化具体语法性质的比对。目前来看,要想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较为困难。正确的态度是把精力放在对语言事实的收集、描写、解释上,注重归纳式“上向研究”。从这个层面上讲,更倾向于认同白云飞通过实证性语言事实描写归纳出的类成语的各项语法特征。
类成语与俗成语都具有口语化色彩,且前者口语化程度强于后者,但这种口语化程度又难以用一个口语化梯级量表来衡量。而古人语感与现代人语感也存在很大差异,秦汉时期虽言文一致,书面语由口语加工而成,当时的成语今天看来仍然文雅庄重甚至有时会觉得有些深奥;魏晋以后言文分家,当时人民口头语言中的成语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古代书面语风格,同今天的成语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对俗成语的确认具有相对性,以前的俗成语现在看来大部分可能属于雅成语。另外,个体之间语感也不同,对于雅、俗的主观感知可能会正好相反,到底哪个更口语化的讨论意义不大。
2. 类成语与俗成语的“纠结”状态为事物间常态
不应过分执迷于类成语与俗成语的“纠结”状态,而应接受它们之间的“纠结”事实。把眼光置于“纠结”状态之下,不能简单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异,而应将它们放在更广的视域来分析。目前来看,至少有3方面根源。
(1) 事物之间存在渐次重迭过渡的“连续统”状态。“连续统”是数学及哲学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名为continuum或continuity,在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经常使用。屈承熹在《汉语认知功能语法》中将“continuum”一词译为“连绵性”,指出类似的个体,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而其间的异同又各有别,所以无法将这些个体再进而分成明显的类别。这些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渐次重迭、连绵渐进的关系[19]。吕叔湘这样描述“连续统”:在对有些对象分类时并不能都做到二分,二分仅能得到两个端点,两个离散的点,却忽视了很多中介(中间)状态,或者说过渡状态。……总体来看,(这些对象)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分类,即“连续统”[20]。许丹荔归纳为:在某个性质上具有连续的量变的一组元素构成的群体就叫做“连续统”,集合中的元素在某个性质上具有连续的量变,这一术语还能对两个范畴(存在相似性)间的过渡状态进行描述[21]。
反观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划界问题,与其纠结于在类成语、俗成语的具体语法性质差异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如把精力放在对语言事实进行尽可能穷尽性的搜罗,再进行细致地观察、描写和解释,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手段更加科学、研究视域更加广阔、研究深度更加拓展的时候,两者的差异自然会更加凸显出来。
(2) “语词分合”问题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类成语与俗成语两者“语”的性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但学界对词汇与语汇认识的不统一[22-26],导致一系列词语归属出现两难状况。从近十余年来网络新词语发展情况来看,“语词”似乎有必要进行分立,至少在表述上更有着落点。语词分合问题的讨论影响了汉语词汇学事实挖掘的深度,反过来也影响了对类成语与俗成语等边界模糊状态语言事实的区分。
(3) 中国人传统思维“包含关系”哲学范畴观的影响。沈家煊指出,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范畴观: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汉语常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一致。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27]。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包含关系”是常态,也就是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某些“连续统”情况,就像“如果你爱人和母亲同时落水且两人都不会游泳,你会先救谁?”这样的问题,并不非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中还有很多选择空间。这些语言哲学上的认识,大概能对“类成语”与“俗成语”的纠结与对立状态作出一定合理的解释。
六、 结语与余论
纠结状态是生活中很多事物表现的常态化特征,就如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一样,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本文虽为类成语与俗成语的纠结状态找到了“连续统”原因、“语词分合”问题、中国人思维“包含关系”哲学范畴观的影响等3个看似合理的因由,但“划界”似乎还远未解决。早在1993年,邢福义就对汉语复句与单句之间存在的对立与纠结事实作了精到思考,特别作如下提醒:不应该沉溺到“划界”问题里头,而应该集中精力对复句自身的规律性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作出有利于深刻认识复句的描写和解释[28],这种方法论理念对于我们如何更好地厘清类成语与俗成语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再进一步把眼光放到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网络语言场域中看,这些流行度不可同日而语、部分意义格式均不输传统四字格的网络新成语、网络成语或网络类成语等语言新形式,经过若干年的时间积淀与优胜劣汰,是否还有机会进入“类成语”“俗成语”这两个筐中?储泽祥通过考察网络中“各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推断出现实语言的语法化“历时厚度”突出,其渐变性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语料清楚地表现出来,而网络语言语法化“共时强度”突出、“历时厚度”不足,渐变性不明显[29]。也就是说网络语言的突变性很突出,难以看出清晰的演化轨迹。可以预测的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热议四字格形式,恐怕尚处于类固定短语层面,离凝固型更强的“类成语”层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网络时代汉语的发展,离不开用变和演变[30]甚至新造的协同推动,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定义、看待、使用新兴四字格,其传播流行争议的深层次演变动因、机制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