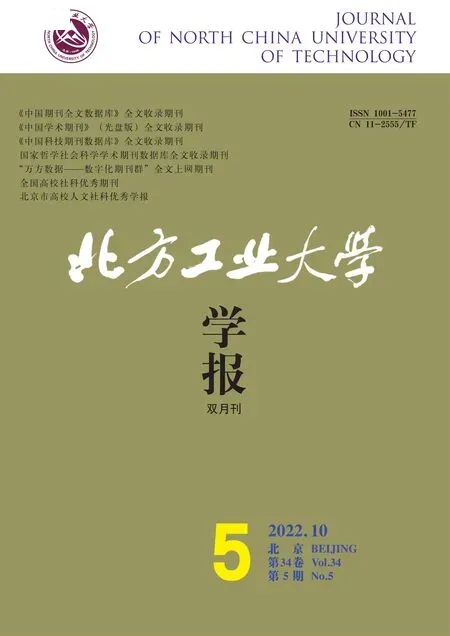论清代经学大师刘文淇的学派归属*
郭院林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扬州)
清末以来,学者讨论乾嘉汉学特色与区别时,往往按地域将学者纳入到不同派别,通常分为吴派与皖派,甚至还有扬州学派、常州学派与浙东、浙西、湖湘学派等,不一而足。 1902 年梁启超以地域划分清代汉学为二:“其俨然组织箸学统者。 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 吴派开山祖曰惠定宇……皖派开山祖曰戴东原。”[1]稍后,章太炎继承此说,[2]而刘师培则结合时代将学术地域更加推广扩大为浙学、关中、赣省、湖湘以及常州、皖北、浙中、淮南、燕京等。[3]以地域划分学派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其原因正如章太炎在《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 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4]“地齐、政俗、材性”是形成古代学术派别的三大主因,其中“地齐”即指地域,地域性特征对学派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刘师培撰写《南北学派不同论》,对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不同时期南北差异俱有论述,他认为学术之所以有地域差异,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舟车之利甫兴,而交通未广,故人民轻去其乡村。狉狉榛榛, 或老死不相往来。 《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5]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与地区,以地域划分学派是可以的;但在清代,江南水系交错,水运发达,尤其是扬州,作为当时的水运枢纽,既有长江沟通东西,又有大运河连接南北,学人无论赶考还是谋生,都会途经此地,他们或长期寄寓,或短暂客居;同时此地学人受到不同地域的影响,也会走向各地,因此形成多样的治学特色。 比如作为吴派代表惠栋和皖派代表戴震就相识于扬州转运使卢文弨署内,扬州学人江藩是惠栋的学生,而王引之又是戴震的高足,焦循、阮元治学体现出兼采的特色。 勉强以地域划分学术流派,不仅会将人静态地看待,而且会将复杂的学术传承简单化,遇到多元影响与丰富特色时,这种论述就会显得无所适从。 以清代扬州经学大师刘文淇为例,当初章太炎的学生支伟成将刘文淇归于皖派与地理学,并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记录询问如何看刘文淇学术与吴派与皖派的关系:
问:……仪征刘氏孟瞻父子祖孙及凌晓楼、陈硕甫诸先生虽出皖系,其笃守汉儒,实吴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吴否?
答:仪征刘孟瞻本凌晓楼弟子,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 ……盖吴派专守汉学,不论毛郑,亦不排斥三家;硕甫专守毛传,意以郑笺颇杂,三家不如毛之纯也,仍应入皖。[6]
从问答中可以看出,以地域来看学者特色,显得有些尴尬,很难单纯地将刘文淇归为哪一派。 下文笔者将惠栋、沈钦韩与刘文淇学术观点与治学特色相比较,结合时代与社会发展来分析刘氏治学的特色与归属问题。
1 刘文淇承继惠栋治学方向
提及仪征刘氏,学界多以其能世代相传,共治一经而赞叹不绝,常与吴门惠氏三传相比。 如汪士铎就认为:
国家以文德化成海内,百年来尤重经术。江、淮间,推仪征刘氏。 自孟瞻先生以经学纯德,师表儒术,余同年伯山继之,其良子恭甫又继之,三世通经精博,学者企若吴门惠氏。[7]
汪氏似乎仅从三代传经赓续形式上将刘氏比附惠氏,实际上单从刘文淇看,他对惠氏治经理念与具体意见接受颇多。 刘文淇(1789—1854),字孟赡,经明行修,与刘宝楠并称“扬州二刘”;治学尤肆力《左传》,成书《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长编已具,而未能卒业。 虽然刘文淇早年受学于皖籍学者,梅花书院山长洪梧指导生徒各自专治一经,包世臣给予研治《诗经》的建议,早年为阮元家庭教师,亲从问故,校书多受其指导,交游中除扬州刘宝楠、薛传均、梅植之、罗茗香、杨亮、王西御与王句生外,多为皖籍,如包世荣、包孟开等;[8]但仔细分析刘文淇学术著作内容与特色,却可以发现,他的《左传》学深受吴地学者影响,他的治学方式方法与惠栋一致。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他是最先明确打出汉学旗号,并确立汉学治经模式的经学大师。 章太炎论清代汉学兴起的过程时说:“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9]惠栋学宗汉儒,推尊汉说,尚家法而信古训。 他说: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 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 《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0]
“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11]他的《左传补注》六卷,无论其治学的宗旨,还是具体的考释方法,与他以汉学治经的脉络体系完全合辙。 《左传补注》为《九经古义》系列之一,由于最先完成而刊版别行。 该书援引旧训以补杜预《集解》之遗,书名由《左传古义》更改为《左传补注》。 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窃谓《春秋》三传,《左氏》先著竹帛,名为古学,故所载古文为多。 晋、宋以来,郑、贾之学渐微,而服、杜盛行。 及孔颖达奉敕为《春秋正义》,又专为杜氏一家之学。 值五代之乱,服氏遂亡。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 自杜元凯为《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 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 栋少习是书,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剌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 其中于古今文同异者尤悉焉。[12]
刘文淇从事《左传》研究,其出发点与认识与惠栋相同,都是对杜预《注》不满意,想恢复旧注(惠栋称为汉注):
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 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 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 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 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 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 泛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13]
洪榜概括惠栋训诂坚持汉儒的古义时说:“东吴惠定宇先生栋,自其家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汉经师以来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谓之‘古义'”[14]首先从恢复古字古音开始,以期还原《左传》本来面目。 惠栋大量指陈传文中的古文古字,或考证传文某字与某古字相通,主要依据《说文》所引《春秋传》,他认为:“许氏所据多古文,必得其实。”[15]因为许慎师从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说文解字》中引用《春秋传》都为《左传》内容。 依据的其他经典还有《礼记》《仪礼》《周礼》《诗经》《史记》《汉书》等经史之汉注,以及《经典释文》所存之异文,有时并考校于石经、碑文及宋本。 惠栋认为:“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义存者少焉”;[16]“古训之亡自杜始”。[17]惠氏着力辑存汉儒旧说,尤以贾、服为多。 他缀次古义、辑存古学目的,就是以古义纠杜之违,以汉学匡杜之失。后来,发明贾、服之学,匡正杜《注》之讹,成为汉学家研治《左传》的主流。
汉学的价值在于“去古未远”,在于汉儒有师承家法。 所谓“去古未远”,就是“去圣未远”。[18]惠栋追求汉注,刘文淇恢复旧注,二人在推尊汉说的方向上一致。 刘文淇认为:经学要先专后博,要守家法师法;先通一经,然后通群经,而不是相反。 “刘自孟瞻先生《青溪旧屋集》出,精蕴内敛,若弓之受檠,田之有畔,谨守师法者宗之。”[19]刘文淇在《题黄春谷先生承吉一经授子图》诗中说:“古读一经通群经,思无越畔农功好。今习群经经反荒,甫田不治田生草。”[20]诗歌用耕田的方式作比,强调各经要有“田畔”,亦即范围与约束。 同诗还谈到审音识字的观点“我闻读书先识字,字义不明经难晓。 我闻识字先审音,声音不明义难了。”[21]刘文淇在《黃白山先生义府字诂序》中谈到从黄春谷那儿学习到“古人文字重声而不重形,故得其声,凡与声相近之字,皆可通假。 近为《文说》,发明以声为纲之义”。[22]“先生谓六经莫外于小学,小学者即载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训诂莫非本于声音,故凡字义,以所从之声纲为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迹之目。 又谓字义必视乎随文所用,而字之本义,则一核其本字之声。 斯义无不明,而其字义迁流之故,亦即于字中可见。”[23]
以“旝动而鼓”为例,可以看出刘文淇对惠氏的治学方式与学术观点的接受情况。 惠栋云:
贾逵曰:“旝,发石,一曰飞石。 《范蠡兵法》曰:‘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二百步。’”《说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从声。 《诗》云其旝如林。”《三国志》:“太祖为发石车击袁绍”,《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旝动而鼓’,说曰‘旝,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所云说者,即贾侍中说也。 杜以旝为旃,盖本马融。 (追,古文磓)。[24]
刘文淇所采贾逵注与惠栋完全一致,同时《疏证》内容也多相同:
《说文》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追敌。”用贾说。 追,古文磓,《释文》:“磓,古外反。 又古活反,本亦作桧” ,而亦引建木发机之事。 如《释文》说,是又有作桧之本矣。 《御览》三百三十七引《春秋》旧说:“旝,发石车也。”与贾同,当亦左氏家说。 《三国志》:“太祖为发石车击袁绍。”《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旝动而鼓’,说曰:‘旝,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惠栋云:“说者即贾侍中说也。 杜以旝为旜,盖本马融。”按:《说文》旝字下又引《诗》曰:“其旝如林。”当系三家传诗。 马融《广成颂》云:“旜旝掺其如林。”惠氏谓杜本马融以此,而《御览》三百三十七引杜《注》:“旝,旟也。”与今本“旝,旜也”又异。 《疏》但云“旜之为旃”,事无所出,说者相传为然,而引贾注驳之云:“按《范蠡兵法》虽有飞石之事,不言名为旜也。 发石非旌旗之比。 《说文》载之部而以飞石解之,为不类矣。且三军之众,人多路远,远何以可见而使二拒准之为击鼓候也。 《注》以旃说为长,故从之。”[25]
刘氏《疏证》一方面梳理各家见解的来龙去脉,认为《说文》对“旝”的解释来源于贾逵,另外增加《经典释文》与《太平御览》佐证贾说,同时对惠氏的见解指出依据。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述惠栋观点254 条,比如文字方面有“郑人来渝平”条引惠栋云:“渝读为输,二《传》作输。 《广雅》曰:‘输,更也。 与怿、悛、改同释。'《秦诅楚文》:‘变输盟刺',谓变更盟刺耳。 渝,更也。 平,成也,故《经》书‘渝平',《传》曰‘更成'。 杜《注》自明,而独训‘渝'为‘变',必俗儒传写之讹。”[26]地名考证方面有“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条肯定惠栋的意见:“惠栋《左传补注》云:‘蔑,本姑蔑。 《定十二年传》: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是也”;[27]礼制方面有“则公不射,古之制也”条引惠栋云:“此指祭祀射牲。 《夏官·射人》云:‘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传》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诸候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击豕',是也。 朱子据《传》曰:‘则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鱼,如汉武亲射蛟龙江中之类',恐未然。”[28]然后刘氏加案语指出朱子“弓矢射鱼“之说,系误仞矢鱼之矢为弓矢之矢,肯定惠氏驳之。
惠栋明确指出杜预“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29]乃援引旧训,尤以汉儒旧注为主而作《左传补注》,开启乾嘉学者缀次古义、集矢杜《注》的风气。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则是在全面辑佚贾、服等旧说的基础上,建立起《左传》新注新疏之代表。
2 刘文淇接受沈钦韩治学观念
刘文淇受吴派学者最直接影响的人物当属沈钦韩。 沈钦韩(1775—1831),字文起,号小宛,江苏吴县人,主要著作有《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春秋朔闰异同》。 据包世臣所撰凌曙《墓表》,凌曙曾师从沈钦韩问疑,由此“益贯串精审”,[30]则刘氏作为凌氏的外甥,也得以问学。 沈氏《与刘孟瞻书》和刘文淇讨论《资治通鉴》作者用心以及新旧《唐书》长短,指出刘氏认为《新唐书》“史笔谨严”之误,是“未免震秦之余威也”,而认为“一代信史,先务明白详赡,而后求其文章议论。”[31]
作为吴派经学名家,沈钦韩承袭同郡惠栋“汉学”宗旨,竭力张大“汉学”思潮。 在《左传》研究上,受惠栋《左传补注》的影响,表现为尊汉崇古,重视训诂与考据,维护古文经学《左传》。与惠栋及其后来的汉学家相比,沈氏更加强调古文学派的师承家法,追踪贾、服旧注,极诋力排《公》《穀》二传,而独尊《左传》;于杜《注》孔《疏》,批判尤为强烈,全盘否定杜预《集解》,以其详尽的礼制典章考辨,为《左氏》古学正本清源。
杜预之前,《左传》研习者遗文十数家,但杜预对《左传》旧注多有不满,特举四家之违失:“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 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32]孔颖达解释说:“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33]杜预袭用前贤成果而不标明,有违学术规范,成为清儒集矢的缘由之一,至有谓攘善剽窃者。 沈钦韩就说:“杜预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礼文者,蹶然为之解,俨然行于世,害人心,灭天理,为《左氏》之巨蠹。”[34]他在《与周保绪书》云:“为《左氏》之疻痏而得罪于圣经者,无如杜预也。 贾、服之注,今已不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孔《疏》惟摘其细碎以为嗤笑。 然他经如《周礼》《仪礼》疏中所引服氏,犹可想见向来经师之讲习、《左氏》之面目,未至颠倒变易。 杜预乃尽翻家法,移《左氏》之义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说,创《长历》以为牵附移掇之计,造《释例》以成其网罗文致之私。 疏家及后之为《左氏》者,动辄惑于其例。 于是《左氏》之学亡,而杜预俨然专门名家矣。”[35]而对于孔颖达《正义》,则云:“孔颖达等素无学术,因人成事,《五经正义》稍有伦理者,皆南北诸儒之旧观。 其固陋之习,最信《伪孔传》、杜预。 于郑氏,敢斥曰不通、不近人情;于服氏曰尚不能离经辨句,何须著述大典;尊崇杜预,谓《礼经》为不足信;狂惑叫号,而郑之他经,服之《左传》,由此废亡。 名曰表章经学,实乃剥丧斯文,可胜恨哉!”[36]
刘文淇学习沈钦韩所著《左传补注》,“窃叹《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先生披云拨雾,令从学之士复睹白日,其功盛矣”。 受此启示,刘氏覆勘杜注,发现其中错误横生,而稍可观者都是贾逵、服虔之说,“文淇检阅韦昭《国语注》,其为杜氏所袭取者,正复不少。 夫韦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贾、服、郑、唐旧说。 杜氏掩取,赃证颇多”。 他的疏证的作法是:
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贾、服、郑君之注,疏通证明。 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勦袭者,表明之。 其袭用韦氏者,亦一一疏记。 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皆左氏一家之学。 又如《周礼》《礼记疏》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 凡若此者,皆以为注而为之申明。 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其顾、惠《补注》及王怀祖、王伯申、焦里堂诸君子说有可采,咸与登列,皆显其姓氏,以矫元凯、冲远袭取之失。 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37]
刘氏对杜预《注》的观念与沈氏一致,沈氏观点多被采纳《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同时,刘氏治经的的家法与沈氏一致,尊信《左传》:“至若左氏之例,异于《公》《榖》。 贾、服间以《公》《榖》之例释《左传》,是自开其罅隙,与人以可攻。 至《春秋释例》为杜氏臆说,更无论矣。 文淇所为《疏证》,专释诂训、名物、典章,而不言例。 其左氏凡例,另为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释左氏。 其不知者,概从阙如。 杜氏以经训饰其奸邪,惠定宇微发其端。焦里堂《六经补疏》以杜氏为成济一流,不为无见,然以杜氏之妄。 并诬及左氏,则大谬矣。”[38]
郑玄《六艺论》论三传的特点:“《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39]唐初孔颖达等学者,已经承认或论定《春秋》可以当礼书看。 沈钦韩《左传补注》注重发明《左传》礼学之旨,以礼解经的特色更为鲜明。 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表述道:
礼者,奠天下之磐石也。 礼废则天子无以治万邦,诸侯无以治四境,卿大夫无以治一家。 时则下陵上,裔乱华,亡国破家,杀身如偿券。 孔子伤之,欲返诸礼,而无其位,故因《春秋》以见意,以为修整于既往。 ……左氏亲受指归,故于礼之源流得失,反复致祥焉。 周公、孔子治道之穷通,萃于一书。 ……以全《春秋》付托之重,然其以礼,爱护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 奈何杜预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礼文者,蹶然为之解,俨然行于世,害人心,灭天理,为《左氏》之巨蠹。 ……区区之衷,久怀愤懑,遂补注十二卷,发明婉约之旨,胪陈典章之要,象纬堪舆之细碎,亦附见焉。 注疏之谬,逐条纠驳,各见于卷。 则左氏之沉冤稍白,杜预之丑状悉彰。[40]
沈氏撰《惠氏〈左传补注〉后序》,亦曾论及《春秋》《左传》与礼的关系。 他说:“道有污隆,则礼为之变。 夫子作《春秋》,使纪事不失其实,以补礼之穷,维世之具,如是而已。 左氏作《传》,略举凡例,而详于言礼。 至于升降揖让、尊俎笾豆之间,曰是仪也,非礼巸已。 若左氏者,其深知文、武、周公致太平之道矣。 例不可以概论礼,则是非两端万变不穷,后之学者舍礼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为刑书,以书法为司空城旦之科,纷纭轇轕,跬步荆棘,大率尾牵皮傅以自完其例,而圣人经世之法,为其汨没。”[41]其《幼学堂文稿》卷一有《出母嫁母服议》《妻为夫之兄弟服议》《父为长子三年辨》《出后之子为本生祖父母议》《诸侯之臣为天子辨》;卷七有《答许凫舟问庶母庶祖母服书》。 这六篇文章,主要依据三礼考论丧服之礼;卷二则有《吊生不及哀解》《先配而后祖解》《大夫宗觌解》《用致夫人辨》《驳杜预与会位定论》《妾母不得为夫人论》《既献召悼子及旅召公鉏考》《叔孙豹违命论》《禘于襄公万者二人辨》等九篇,是关于《左传》礼制典章的专论。这些礼制典章研究之文,写作于《补注》撰著之前。 沈氏的礼学学养及前期成果,是他《补注》以礼解经特色形成的基础。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注例”,专门有“释《春秋》必以礼明之”一条:
《周礼》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礼明,而后乱臣贼子乃始知惧。 若不用周礼,而专用从殷,(原注:《公羊》家言《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殊误。)则乱臣贼子皆具曰予圣,而借口于《春秋》之改制矣。 (原注:《郑志》曰:“《春秋经》所讥所善,皆于礼难明者也。 其事著明,但如事书之,当按礼以正之。”所谓礼,即指周礼。)[42]
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原稿眉批曰:“哀十四年疏称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这一句也就表明了古文经学的立场,因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43]东汉《左传》学兴起与刘歆密不可分,在他的努力下完全实现了《左传》的传化,确立了《左传》学的历史理论和逻辑理论,所以刘歆当之无愧是《左传》学的创始人。[44]但是刘歆等研究成果留存极少,而贾逵、服虔注释却在《左传正义》和其它典籍保存不少。 刘文淇回到了刘歆的立场,也就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为期疏证旧注奠定了基础;对外则与汉代的《公羊》学乃至《谷梁》学划清了界限。[45]汉朝制礼用《左传》。 孔子作是因为礼崩乐坏而作以示褒贬,那么《左传》要传经,必归于礼。 《左传》有一个明显而一贯的历史观,这是“礼”。 作者把当时一切的兴亡成败的原因都归结到人与人,国与国间相互交往时有礼或无礼……即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以礼为共同遵守的准绳,并以有礼与无礼为文明(华)或野蛮(夷)的分别。 所以刘氏强调《左传》的礼学意义,正得其要穴。 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二有《既殡后复殡服说》《亲丧既殡后见君无税衰说》二文为论事说礼,同时有《朱芷汀夏小正正义序》,校《礼记训纂》(朱彬撰)。 他的治礼事业为后人继承,儿子刘毓崧著《礼记旧疏考正》一卷,孙刘寿曾著《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曾孙刘师培更著有《礼经旧说考略》《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逸礼考》等多部专著。
沈钦韩《左传》学精于地理,详考制度。 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多取于沈氏,共计711条。 礼制方面如“发币于公卿”条引沈钦韩云:“《聘礼》:归饔饩之明日,宾朝服向卿。 卿受于祖庙。 庭宾设四皮。 宾奉束帛入,致命降出。 又请面如觌君之币,毕乃饩宾。 此所谓发币于公卿。主人朝服迎外门外,再拜,宾升一等。 大夫从升,再拜受币。 此敬宾之礼。 而凡伯不然。 故戎嫌之。”[46]刘文淇以案语肯定沈氏之说“发币”。 再如“针子曰:‘是不为夫妇。 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条引沈钦韩《补注》云:“《聘礼》大夫之出,既释币于祢;其反也,复告至于祢。 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庙,以逆其妇。 反而不告至,径安配匹,始行庙见之礼。 是为堕成命而诬其祖。 又先配后祖解云:盖礼有制币之奉。 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义。 况昏礼之大者乎? 然则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将传宗庙之重于嫡,而惜跬步之劳于祖,已即安伉俪焉?是为诬其祖也。”又云:“针子曰:‘不为夫妇',是则孔子未成妇之义也。”刘氏以为:“沈氏不用贾、服、二郑君义而言庙见,言未成妇,仍贾、服义所有也。”因为“其说礼意甚精,谨附著之。”[47]地理方面如:“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条引述沈钦韩云:“《一统志》:‘瓦屋头集在大名府清丰县东三十五里。 或谓盟于瓦屋即此。'《纪要》:‘瓦冈在滑县东。'《水经注》:‘濮渠东迳滑台城南,又东南迳瓦亭南。'当是此瓦屋。 杜预谓周地,非也。”[48]“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条引述沈钦韩云:“《方舆纪要》:‘汶水出泰安州莱芜县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 《水经》所谓北汶也。'《运河记》:‘汶水自泰安州经宁阳汶上县界,又西至东平州,注济水,比故道也。'应劭云:‘水北为阳,南为阴。'盖在今兖州府宁阳县北。 汉置汶阳县,在曲阜县东北四十里,非此汶阳也。”[49]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隐公传“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条,旧注列“服云:偾,仆也。”刘文淇疏证不仅对偾意进一步证实,而且补充济水在何处,涉及字意理解与地理方位。 所引有《释言》、舍人注、《水经注》、沈钦韩注、《元和志》,指出杜《注》与《正义》理解错误,杜错在全凭臆说。 全文如下:
《释言》:“偾,僵也。”舍人注:“偾,背踣意也。”《水经注》:“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至巩县北入于河。”沈钦韩云:“《方舆纪要》:大清河在长清县二十里,自平阴县流入境。 又东北入齐河县界,即济水也。 郑伯之车偾于济,盖在县界。 《元和志》:刘公桥架济水,在郓州卢县东二十七里。 又北去济州长清县十里。”杜《注》:“既盟而遇大风。 传记异也。”《正义》曰:“车踣而入济,是风吹之坠济水,非常之事。”文淇案:传文无风吹事,杜注意为之说。[50]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集《左传》研究之大成,取著广博,资料丰富。 “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左证。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51]近人著述,多采入其中,或作佐证,或作驳论。
3 刘氏治《左》的时代局限
刘寿曾将扬州学人的学术渊源追溯到江永,他认为:
国初东南经学,昆山顾氏开之,吴门惠氏、武进臧氏继之。 迨乾隆之初,老师略尽,儒术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穷乡,修述大业,其学传于休宁戴氏。 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 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 先大父(刘文淇) 早受经于江都凌氏(曙),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劘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 先征君(刘毓崧)承先大父之学,师于刘先生。 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达为近。 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征君为执友者,又多缀学方闻之彦,是为江氏之四传。 盖乾嘉道咸之期,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无能与比焉。 ……江氏生于孤特,不假师承,犹且开扬州之风气,以大昌其学术,今距四传之时,渊源濡染,近不越十余年,岁会月要,锲而不舍,其为江氏之五传,盖无难也。[52]
江永系统研究《左传》的代表性著作《春秋地理考实》,成于晚年。 全书着重探讨并考证《春秋》以及《左传》文本中地名所涉及的地理位置与区域沿革等多方面的问题。 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述江永观点139 条,如“戎伐凡伯于楚丘”引江永曰:“《汇纂》:‘今兖州府曹县东楚邱亭是也。'今按曹县今属曹州府。 二年戎城,亦在曹县。 则此楚邱为戎邑,非卫邑也。”[53]再如“哀侯侵陉庭之田”条引江永云:“翼,今平阳府翼城县东南七十五里有庭城。 《志》云即陉庭也。 又《水经注》:‘紫谷水出白马山,西迳荣城南,西入浍,亦在翼城南。'则陉庭即荧庭,亦即荣庭也。”[54]
但江永治学无门户之见,汉宋兼采。 他在具体考释《左传》地理时,面对古今众说,毫无成见,既兼收博采,又考疑辨误,惟是之求,表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胸襟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春秋地理考实》多处采录了《公羊传》《穀梁传》的说法。 如桓公四年《经》:“公狩于郎。”江永据《公羊传》云:“讥远也”,考此年之“郎”,当为《左传》隐公元年费伯帅师所城之郎,在清兖州府鱼台县东北。[55]夏銮与胡培翚讨论当时学术,谓“兼汉学宋学者,惟江慎修。 江氏书无不读。 人知其邃于《三礼》,而不知其《近思录集注》,实撷宋学之精。”[56]刘氏《左传》学强调家法,追求旧注,与江氏之学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大家、当时学界中心人物之一,弟子及再传弟子甚多,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诸人。 受戴氏影响者亦不少见,尤其是扬州学者,如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 王昶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一文中这样评价戴震:“东原之学,苞罗旁搜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 本朝之治经者众矣,……端以东原为首。”[57]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 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58]而且戴氏于义理、考核、文章能得其源,由博返约。 在考证方法上,戴震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而且戴学最可贵之处在于“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穷理。”“格物者格物类也,穷理者穷实理也,与宋、明虚言格物穷物者不同。”[59]如果从考据学这方面看,刘氏《疏证》旁征博引,或近于戴学。 但刘《疏证》仅引戴说3 条,似与其关系不大。 相比较而言,刘氏就缺少义理这方面的思考,学术上多继承,思想更多趋于保守传统。 刘寿曾从扬州学者多从戴震受教立论,但以此来断定刘氏与皖学的联系,似乎流于形式,从刘氏具体情况看,所言并不准确。
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述多家,仅《春秋》《左传》类初步统计就有29 部,经部88部,比如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李富孙的《春秋三传异文释》、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等。 惠栋确立汉学宗旨,其《左传补注》为汉学发皇,羽翼声张者甚众。 在他们的《左传》著述中,表现了由惠栋开启的相辅而行的两种学术趋向,一是缀次古义,还原古学;一是批判杜《注》孔《疏》。 《左传》多古字古音,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是汉学家考据《左传》的主张,所谓“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60]清人追踪《左传》汉学古义,专门辑存贾、服旧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总结清代《左传》学时说:“治《左氏》者,自顾炎武作《杜解补正》,朱鹤龄《读左日钞》本之,而惠栋《左传补注》、沈彤《春秋左传小疏》、洪亮吉《左传诂》、马宗琏《左传补注》、梁履绳《左传补释》咸纠正杜《注》,引伸贾、服之绪言,以李贻德《贾服古注辑述》为最备。 至先曾祖孟瞻公作《左传旧注正义》,始集众说之大成。”[61]该书特色也在于“掇拾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末下己意, 以定从违”[62]因为体大思精,要归属于哪一派也是不容易的。
章太炎认为吴派“好博而尊闻”,“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皖派“综形名,任裁断”,“分析条理,皆缜密严傈,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63]这样的分析要让吴派心服恐怕未必。倒是刘师培清代汉学分期论更为合理,他依据学术发展时代展示的不同特色划分为:怀疑派(顺、康之交)——征实派(康、雍之间)——丛缀派(雍、乾之际)——虚诬派(嘉、道之际),征实派“长于比勘,博征其材, 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 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 此派虽以江永、戴震为显著,但不排除吴派学者,如“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书》,虽信古过深,曲为之原,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然融会全经,各申义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 律以江、戴之书,则彼此二派,均以征实为指归”,这是一个时代的特色而非地域的特征。刘氏家学兴起于嘉庆、道光之际,介于“征实派”与“丛缀派”之间,而后刘氏子弟处“丛缀”学风下笃守“征实”之代表。 刘师培对此阶段考据特色论述道:
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 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 此风既开,转相仿效,而拾骨、襞积之学兴。 一曰据守。 笃信古训, 跼蹐狭隘,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 二曰校雠。 鸠集众本,互相纠核。 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 三曰摭拾。 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碎璧断圭,补苴成卷。 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 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 四曰涉猎。 择其新奇, 随时择录。 或博览广稽,以俟心获。 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 ……然所得至微![64]
以乾嘉学风治经,刘文淇是《左传》学之总结。 刘文淇应该知道历代学人对《左传》的认识和评述不乏史学的定位。 东汉桓谭肯定《左传》记事的价值,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65]唐代刘知几也是从史学的角度肯定《左传》,他说:“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 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矣。”[66]但《左传》毕竟疏于义理,所以朱熹说:“《左氏》是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是经学,理精而事误。”又说:“《左氏》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吕大圭也说:“《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67]刘文淇出于古文经学家的家法考虑,崇汉尊《左》,治经对象个体与方向地选择更多在于发掘《左传》中的“古”的东西,包括文字字形、训诂以及名物制度等。 《左传》客观记录了当时的礼制,但仅是客观反映,并没有统一的礼学观念与礼制思想。 刘文淇舍弃义理的研究,从礼制作疏解,堕入丛缀派。 虽然材料比前代学者更为丰富,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架床叠屋,耗费四代人的精力,最终也没有完成,成为遗憾。
正如本田成之所说:“清朝的学问很严谨,不过只是小学训诂的学问。 把经书视为神圣,对于汉儒也太过重视,当然是由宋儒大胆批评的反动,其弊不免怯懦。”[68]梁启超一方面肯定汉学的勤奋,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对于社会的无用:在《清代学术概论》评论道:“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 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他认为这些新疏大都“博通精粹,前无古人”,“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69]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认为:“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诬也。”但是“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70]
我们研究《左传》,复原其中的礼制当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来看,更要看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有何不同,为何产生? 如果不从历史语境考察,唯古是求,一方面很难理清孰是孰非,另一方面也是将经典博物馆化,而要让经典活化起来,则不能不研究其时代性,亦即不同时代学者研究经典时对时代的回应,他们内在精神以及对当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