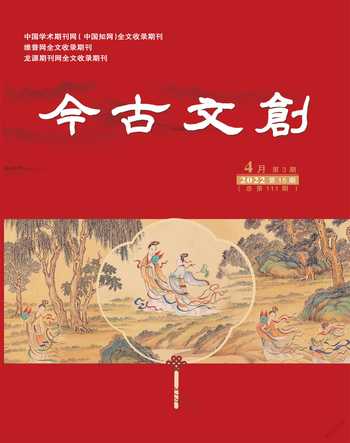网络语言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化现象探索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极速发展对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新兴的网络用语层出不穷。除了外在环境的浸染,语言内部的子系统也不断更新演变,其中语法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词类的划分和词的派生。网络用语中也不乏语法化的痕迹,但是新事物的诞生也带来了一些疑问:语法化对于网络用语的形成有什么贡献并且这些网络用语是否符合现代汉语的使用规范,以上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用语;汉语语法化;汉语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5-007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22
网络词语是在互联网上使用的一些特殊语言或文字,是伴随着互联网而诞生和发展的词语[1]2。究其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为了提高人们在网上交流和信息检索的效率。从1995年互联网覆盖了整个中国开始,人们就有序地踏入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从有声地探讨转变成无声地互动,从动嘴转变成动手。在屏幕前,沟通速度的要求和打字输入变慢之间产生了矛盾,自此,错别字满天飞,出现了严重的词不达意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人们正常交流,语言学家们也进行了种种实践,网络语言也就渐渐成型;二是为特定人群的交流需要而产生的网络词语。平时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和彷徨的上班族在网络的世界里不用顾忌年龄、身份和环境,可以畅所欲言。人们用汉字、数字、表情、别字和谐音来创造新的文字和符号,也是打破传统限制创新的体现。
作为一种新现象,近10年的网新词热度不减并且持续攀升,形式也更加多样。比如纯汉语词、表情包、数字、字母詞和谐音入词等,其中“老江湖了”“打工仔”和“追星族”都有语法化的痕迹。那么什么是语法化呢,语法化对于网络用语的形成又有什么贡献呢?
一、语法化现象
语法化大致相当于我国传统语言学所说的“实词虚化”,是指语言系统中一些原来有实在意义的词(或叫“词汇词”)在语法的演变中变为只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2]59这是语言随社会发展变化,内部子系统随之更新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现代汉语的语法化主要表现在动词会虚化成语气词、连词、介词等,而名词则会变成类词缀。比如“把酒问青天”中的“把”在古代是动词,但它在后代渐渐虚化。“把卷看”的“把”就不再是纯粹的动词,就转向介词的范畴,在名词前表示方式,再后来“把书拿给我”中的“把”,已经不再是动词了,就完全变成了介词。
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无论怎么虚化,这些词在语言的语音、语义、语法方面都有所表现。在语音方面,音节变轻变短,有合音趋势,比如在“花儿、苗儿和魂儿”之中做后缀的“儿”,就变成轻声“huar”;在语义(词汇)方面,在“孩子”中做后缀的“子”,其词汇意义没有完全虚化,补充了“孩”的语义;在语法方面,在“老虎”一词中充当前缀的“老”,完全没有年龄大或陈旧的意义,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补充词的结构,构成双音节词。
那么,在名词语法化成为词缀帮助构词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新现象,它叫做类词缀。之所以把他们称作类词缀,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3]26
随着现代汉语中人们对于双音节词的构造需求和外来词的侵入,有一些词汉语里本没有,后面因为人们的使用被固定下来。比如“半”这个语素在现代汉语里是不单用的,“半数”和“一半”这样双音节的搭配比较常见,且在这两个词中“半”是以词根的身份和其他词根组合搭配的,即表现了一个词的主要意义,成为一个词的核心成分,那“半数”和“一半”中不难看出“半”的词义是没有大变化且成为了整个词义的主要承担者。而“半导体”中的“半”是没有完全被虚化的类词缀。“半导体”的“半”是指在常温下导电性能在导体与绝缘体之间,并不是只有一半导体。所以在这个结构里,结合释义,可以推断出“半”是否是类词缀,但是在这个结构中也有反例,比如“半身裙”里的“半”就不是类词缀了。
类词缀构词同样在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一些新表现。语音方面,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所以人们也比较倾向给双音节词加上类前缀或类后缀去构成新的派生词,这样构词也符合类推作用,比如“月光族”和“追星族”;在语义方面,类词缀的语义并未完全虚化,在组合中构词能力很强,并且能标明词性。它的形式简洁,内容上又能浓缩语义,满足了语言的经济原则。比如“零收入”和“零形式”,从意义上来看,“零”量的含义渐渐虚化,没有的含义日益凸显,其词义主要朝着“没有、否定、不、无、空的、虚的、达到极限的程度”发展[4]3;在语法方面,它强大的构词能力和灵活简便的形式体现了类词缀的语法功能。“留学热”和“国学热”中的“热”就不符合热的本义,即给食物增温或者基本义温度高,而是狂热,即形容人们前仆后继去留学、学国学。在这里,“热”的词义虚化且语法意义显化,在整个三音节结构里起到了简约结构、表情达意的作用。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上文提到的一些词比如“留学热”等都是网络词语,那么网络中也应存在语法化现象。
二、网络中的语法化现象
综合2020年的网络热词,现将涉及语法化的网络词语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容人的类词缀,一类是反映社会现象的词。
(一)形容人的类词缀
2020年里出现的形容人的网络词语有很多,如“干饭人、逆行者、up主等”。
比如“打工人”,前两年还有“打工仔”的说法。要说语法化的现象,“打工仔”这个词里面的“仔”本义是指幼小的儿子,在“打工仔”一词中“仔”是指从事某种职业的年轻人,其含义被泛化。不过,在2020年,“打工人”的热度更高一些。
比如“逆行者”,“逆行”就是向反方向走,“逆行者”就是因为职责和信念在发生重大事故时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的那一群人。在2020年,“逆行者”有了具体又特殊的时代背景,即在疫情面前,勇往直前打响疫情阻击战的个人及集体先进分子代表。“者”在现代和其他词根结合,组成了比较固定的形容人的搭配,“作者、读者、长者、记者……”在2020年又出现了“逆行者”。这是“者”这个类词缀又一泛化、虚化之后组合生成的新词。
比如“后浪”,这个词其实起源于一部五四宣传片,该宣传片反映了某站up主的形象,并将其称之为年轻有为的“后浪”,这里的“浪”,并不是指浪花,而是只年轻的后起之秀。原本也有后浪一词,但它本义指的是晚辈,随着时代的发展,“浪”从不指人再到可指称人,再到指年轻人,且与“后”组合紧密,为人们所熟知使用。
以上就有一些形容人的类词缀,这也是2020年以来比较有特色的网络新词。
(二)反映社会现象的热词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一点,网络词语中的隐喻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而隐喻是语法化的一种。语法化的“首要功能是用一个事物来表达另一个事物的概念化。这种功能并不局限于语法化,它大体上是隐喻的主要特点”[5]90。2020年的通过隐喻而产生的网络词语数量颇多。隐喻是指“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外一种事物,以及从基本的、一般是具体的意义转变为更为抽象的意义”[5]98。
隐喻表现在不同的语言之中,它考虑两种意义的相似性。比如英语,它是屈折语,形态变化丰富,又是表音文字,但英语的隐喻也以词汇为主要表现方式,“从表面上看,隐喻经常涉及字面上的理解往往是虚假的命题”[5]105 例如:“Karina is a block of ice.”(卡瑞娜是一块冰)明显人和冰块从本质上不能画等号,那只有从感情色彩的角度,把人的冷酷和冰的冷酷相比较了;而汉语是孤立语,缺少形态变化,用方块字既表音又表义。比如“菜鸟”这个词,“菜”单独使用是名词,在这个词里“菜”又有形容词的意味,隐含差的、技术不好的意思,“鸟”在这个词里就不单纯指鸟了,而指人。那么这个词并不像表面一样意为“菜的鸟”,因此“菜鸟”通过隐喻的手段表现出其语法化倾向。
2020年疫情期間,人们居家关注疫情讯息的同时,也开始了比往年更长时间更集中的网上冲浪生活,一些反映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网络新词鱼贯而入。
比如“老江湖了”,类似于老油条,是老练圆滑的意思。“老江湖了”中的“江湖”,本来词性是名词,但它所处的位置在副词之后,有了形容词的用法,江湖也不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江湖了,有了形象和感情色彩。
比如“正道的光”,网络上只要有正义的事迹被宣传,播放页评论区就会有这样一句话:“正道的光照在大地上”,可见“正道的光”的“光”也绝非指光线,而是指光明和正义,这也是语法化的一种体现。
再比如“内卷”,它原本是社会学术语,指的是社会的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目前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很多高校学生用内卷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卷”本义是把东西弯转裹成圆筒形,“内卷”中的“卷”是指倾轧、竞争,这里的“卷”已经脱离了它原本的含义,被投射到一个更具体更现实的环境里。
三、现代汉语语法规范
普通话有一套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6]97。那么一个合乎规范的词语就要具备这些要求。
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有时也不是万能且唯一的标准。现代汉语的诸多词汇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严格按照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标准被断定为合格的词,就是人们能看到的正规正式的出版物,央视的节目中所涉及的现代汉语;一种是完全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词语,网络上的谐音文字比如“耗子尾汁”和“火钳刘明”这一类,只能在网络上流传或者以口语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交流中,但不可能成为民族共同语继而被人们沿习相授,那么这些词不日就会被淘汰;还有一种是虽然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但是被人们普遍使用且广泛接受,那它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打毛衣、打扫、打理、打领结……”其实这些语素组合的方式和词义并非不符合人们的社会生活习惯,“系领带”或“织毛衣”更符合人们的认知,但是“打领结”和“打毛衣”人们也普遍使用。
由此可知,能不能被大众接受运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一个词语这两个条件一个都无法满足,那就会被淘汰。
四、语法化对规范网络用语的帮助
目前来看,网络词汇没有特定的规范系统,只能随着标准词汇内部的语音语法词义做出新的调整,因此客观层面上,网络词语也能被规范。
在这两类网络词语中,比较合乎规范的很明显是类词缀。且不说前几年有很多语言学家对类词缀做了很多研究探索,就语言学界就有不少关于类词缀的研究理论。贾泽林和王继中学者表明译外来语的译介是类词缀产生的直接原因,与古代汉语中的外来词相比现代汉语外来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打破外来词单纯表示对等概念的静态形式外来词中的成分被语素化和词缀化在汉语中产生了很强的构词能力。[6]97“超、准、软、亚、非、化、半、热、吧……”等都是外来的词缀,就从网络词语的角度入手“打工仔、真人秀、追星族、上班族……”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能被全民族广泛使用且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那另一种反映社会现象的带有隐喻含义的词,就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接受度及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了,“割韭菜、舔狗、白嫖、实锤……”在书面语体的作品中十分少见了,因此也就没有那么高的群众认可度和接受度。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类词缀的涌入对网络词汇的规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类词缀的灵活形式和构词能力为社会中源源不断产生的新现象提供了语料,既满足了新词的造词需要又满足了生活的表达需要,而且它能在合乎规范的词语内部依据标准调整自己的语音语法和语义,有极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斌.现代汉语专题[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周日安.数词“零”的缀化倾向[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3).
[5]鲍尔·J·霍伯尔,伊丽莎白·克劳斯·特拉格特.语法化学说[M].梁银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6]贾泽林,王继中.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形成及其与外来词的关系探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4).
作者简介:
李怡文,女,陕西西安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