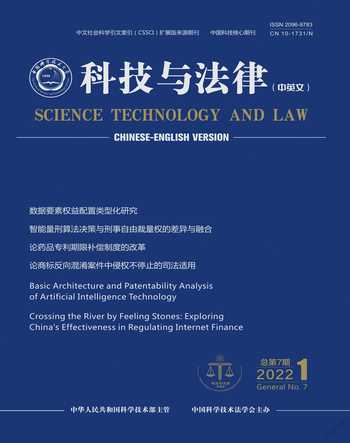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差异与融合
李立丰 齐弋博
摘要: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为刑事司法领域带来诸多便利,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类案同判”。人工智能量刑系统是以数据模型运算为工作原理,通过逻辑运算形成算法决策。刑事自由裁量权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而赋予法官的裁判权力。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不仅价值立场不同,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权力属性上也有区别,但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了避免法官量刑的“恣意性”和智能量刑系统的“机械性”,应当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目标要求下,首先,坚持法官在量刑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明确算法决策介入司法领域的边界;最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人机协同的司法治理新模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量刑;算法决策;法官量刑;刑事自由裁量权;人机协同
中图分类号:D 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9783(2022)01-0010-08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横向课题“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公务研究:以ZJ省检察实践为范本的实证研究”(TY2019-FW129-ZFCG129)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智慧法院”和“智慧检务”的建设规划意见。在此背景下,2016年,杭州推出“法小淘”。随后,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相继推出了“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法院构建“206”智能刑事案件輔助系统。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提高了司法审判活动的效率,有效解决了“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实现了对量刑裁判的技术赋能。
未来发展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①的法治思想,将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同时,关注新技术与传统量刑模式的差别,寻找将两者进行规制和优化的有效规则,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对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作出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量刑的发展也应该以此为导向,实现整体上的量刑公正。
一、问题的提出
在“Loomis(Loomis v. Wisconsin)”案件的判决中就存在关于风险评估算法的应用。COMPAS就是在该案件中承担风险评估的智能算法系统,COMPAS智能算法系统将Loomis评估为一个再犯风险高、并且对社会构成高风险的人。由于COMPAS评估时使用的算法模型属于商业秘密,因此评估公司仅能将评估结果提交给法院。初审法院在判决量刑时参考了COMPAS的评估结果,判处Loomis六年有期徒刑和五年社区监督。Loomis提出上诉,他认为初审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对COMPAS评估结果的依赖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力。威斯康星州法院裁定COMPAS的评估结果不是初审法院拒绝其假释的唯一理由,因此法院的决定并未侵犯Loomis的正当程序权力。
该案件引起人们对人工智能量刑两个方面的担忧:首先,人工智能量刑的工作方式是输入案件描述,而后输出裁判结果,这种“算法黑箱”裁判方式增加了被告人对裁判结果的怀疑;其次,人工智能量刑具备裁判效率上的比较优势,运用人工智能的法官难免会形成依赖惯性甚至惰性[1],进而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在规范化量刑改革背景下,智能量刑和法官量刑应分别承担哪些任务?如何实现智能量刑和法官量刑的深度融合?须进一步分析和澄清。
二、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考察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形成算法决策,它是通过数据和模型运算得出的逻辑结果。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刑事司法人员享有的裁判权,它起源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范和语言的不确定性。
(一)智能量刑中算法决策的原理
人工智能量刑中算法决策是以数据库和算法模型为基础,裁判文书属于非结构化的文字数据。通过大数据操作,对刑事裁判文书进行要素标注,分析量刑过程,将“法定刑、基准刑、宣告刑”三个维度的数据准确标注,抽取案情中影响量刑结果的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和影响量刑的历史因素,建立量刑预测模型[2]。
具体来讲,需要先对裁判文书进行规范化处理,提取文书中的相关要素,将其分为一般要素和刑期属性要素。案发地点、当事人等属于一般要素,针对31个常见罪名提取了29个刑期属性要素[3]。刑期属性要素与量刑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在量刑时需要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例如,抢夺罪中存在是否多次抢夺、携带凶器抢夺、抢夺金额3个属性,其中,前两个属性是二值属性,只有不发生或者发生两种情况,分别取值0、1;抢夺金额属于多值属性,有数额不大、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情况,分别取值0、1、2、3。
量刑预测模型分为三个模块,文本表示模块、属性表示拼接模块和输出模块[3]。文本表示模块是将输入的案情描述转变为词向量序列;属性表述拼接模块是将前面的词向量序列通过最大和平均化操作②,得出一般表示和带有刑期属性的表示,将两种表示进行线性拼接;输出模块将属性表示拼接模块得到的最终表示映射为刑期类别概率分布,最后输出量刑预测结果。
(二)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考察
空缺结构是人类语言的一般特征,任何选择用来传递行为标准的规范都将表现出不确定性。当人们试图去清晰地、预先地使用法律调解某些行为领域时,会遇到两种不能摆脱的困境:其一是人类对事实的相对无知;其二是人类对目的的相对模糊[4]。这决定了抽象的法律规范和具体的案件事实不可能完美契合,刑事司法过程要面临三个不确定性因素,即事实的不确定性、规范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的不确定性[5]。在这三种不确定性因素的纠葛中,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将以上三种不确定性因素确定化,以实现刑事司法过程的有效衔接,通过语言的确定实现从规范到事实的适用,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目的。
三、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差异
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带来诸多挑战,司法领域也不例外。在传统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所有任务都由司法人员来完成,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智能量刑系统打破了传统的办案模式,使用以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运算方法进行算法决策。算法决策与法官裁量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不同,两者的权力属性和价值立场也存在差异。
(一)事实认定上的差异
智能量刑算法系統先对案件描述中的要素进行标记,将这些标记的案件要素输入算法系统,通过大数据运算预测量刑结果。智能量刑算法的可靠性与大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紧密相关。从公布数据来看,2014年是裁判文书公开的第一年,发布了550多万份裁判文书,2015年又将总发布量相比2014年提高了60%以上,推测公开发布的文书应该占总文书的50%左右[6]。从量上来看,裁判文书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数据资源,但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充分的数据化转换。有些公开的裁判文书由于书写错误、制作不规范而不能被有效利用[7]。“部分裁判文书中,对于案件处理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未必都写进判决书。对案件酌定情节、特殊加害—被害关系等特定事实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因人而异。”[8]
如果说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也对案件事实进行要素提取,那么法官裁判就是以主要事实为主要裁判依据,以其他事实为辅助裁判依据。因为法官所进行的案件调查是对案件的整体了解,不同于智能量刑系统的选择性提取方法,也就是说,法官在量刑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实均对量刑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在智能量刑算法中,只有当被标记的案件事实要素与数据库中的特定要素存在对应关系时,该事实要素才会被提取为考量对象,进而对量刑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公布实施后,法官可以直接根据修正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智能量刑系统需要根据新法条重新建立模型,这个过程要耗费大量时间,容易造成案件办理超期,有损司法公正。
大数据的可靠性需要以收集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基础,但同时存在数据收集的负面清单[9]。部分事实要素面临取舍两难境地,如性别、种族和经济状况是否可以作为量刑要素进行标记。例如美国“比尔登”案(Bearden V. Georgia),佐治亚州评估了一个初审法院的决定的合宪性,该决定撤销了对一名无力支付法院命令的贫困被告的缓刑判决。法院推翻了初审决定,认为由于被告无力支付而将其监禁相当于违反宪法的财富歧视。在量刑中对性别的明确考虑一直很普遍,并且很少有人为这种做法辩护,但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明确禁止在量刑中对性别进行考量。学者们同样大多将性别差距视为“不必要”的量刑差异[10]。在弗吉尼亚州,政府开发的风险评估系统故意将性别排除在算法之外,虽然这样做违反了基本的统计需求,但是这是避免歧视的有益尝试[11]。因为,性别、种族属于行为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特征,行为人没有选择的可能性;经济状况属于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特征,没有人会故意恶化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行为人在短时间内不具有选择可能性。如果算法模型直接将行为人不具有选择可能性的特征作为量刑要素进行考量,有违公平原则,必然导致算法歧视。虽然算法模型可能为具有相似特征的被告群体提供合理精确的平均预测结果,但是对于单个人来说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换句话说,个人有权被视为个人。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使得法官可以对每一个案件作出具体分析,类似判例可能会让法官形成刻板印象,但是不会形成必须遵循的算法逻辑,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之优势所在。
(二)法律适用上的差异
智能量刑实质上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类案推送解决方案,包含案件要素提取、案情画像构建、案情语义匹配和个性化类案推送等[12]。智能量刑系统的积极作用在于提高了量刑建议精准化及量刑效率,也预示了新的办案机制正在形成[13]。现有的知识图谱构建和应用重点主要在于静态数据的录入、分析和处理,如概念、实体和属性等[14]。也就是说,以当前的知识图谱为基础构建的智能量刑系统在类案检索等数据搜集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司法裁判中仍然有很多关键问题须解决。法官在裁判量刑中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和综合考量在当前智能量刑系统中仍然难以实现。
首先,智能量刑的数据库存在局限性。智能量刑以完备的数据库为基础,数据库的绝对完整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承认数据的完整性。以上海“206”量刑辅助系统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系统录入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948 384条、办案业务等各类规范性文件638件[15]。录入的数据不可能穷尽所有规范性文件,如一些地方性规定、某时期的刑事政策等。这些规范类似于“特别法”,往往对裁判量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智能量刑面临的第二重障碍是主体价值判断的缺失。智能量刑系统依靠逻辑判断进行裁判量刑,逻辑判断的缺陷在于缺少灵活性,当面对一种新的犯罪类型时往往束手无策。具体来说,新犯罪类型的部分事实要素已经超出了系统中逻辑判断的前提要素范围,进而导致智能算法无法得出合理结果。例如,在孙伟铭案件中,其行为到底符合“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很大争议[5]。从构成要件上看,其行为同时符合两个罪名,如果将罪名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能够充盈该罪名的构成要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但法院最终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③。原因在于该案件是全国首例无证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案件,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和社会危害性。众所周知,“量刑应当确保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④,因此将罪名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种判断不仅是单一的法律事实判断,而是需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法官在面对这类案件时,尚且有点无所适从,需要反复揣摩和论证才能作出决定,更何况以逻辑运算为主要工作原理的智能量刑系统。
(三)司法权的演变
传统上,法官在司法裁判中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宪法第131条为这一点提供了法律保障[16]。司法权专属于司法工作人员,随着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司法权的结构和属性发生了转变,智能算法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行使司法裁判权。
首先,司法权力结构的演变。传统上,司法权的主体是公安人员、检察官和法官,法官拥有实体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其他司法人员行使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权[17]。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淡化了司法人员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证据类别、证据标准、诉讼期限以及诉讼阶段都是在特定的运算模型中推进,司法人员只需要按照要求或者提示进行诉讼工作。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由主动变为被动。司法人員在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和部分实体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已经让渡于智能量刑系统的算法决策。由此,司法权的主体演变为智能量刑系统的算法决策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且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次,司法权力属性的演变。智能系统的研发需要司法人员和数字技术人员共同合作,并且数字技术人员在算法模型的研发以及运行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任务。例如,在上海“206系统”研发的人员中,64位是来自上海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业务骨干,215位科大讯飞公司的高精尖技术人员[15]。在智能系统应用过程中,系统后台的运行管理、数据模型的调整和信息数据的增减等,都须依靠数字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操作。智能量刑系统能否实现司法正义和裁判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人员所建立的数据模型,最直观的表象就是同一案件输入不同的智能量刑系统中会得出不同的量刑结果。由此可知,数字技术人员也在间接行使司法权。
四、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深度融合
智能量刑系统在应用中形成算法决策,对算法决策的规制则需要依靠法官发挥司法能动性。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裁判过程中通过发挥自身的司法能动性依法对案件进行裁量,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非时时刻刻都可靠,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化约束。智能量刑算法决策和刑事自由裁量权之间正好形成一种张力,算法决策可以防止由于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而诱发的司法不公,同时刑事自由裁量权可以纠正智能量刑系统在个案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实现个案正义。
(一)智能量刑算法决策的规制
智能量刑为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在发展智能量刑技术的同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规则,即在保证刑事司法人员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前提下,构建精细化和透明化的人工智能量刑系统。
1.优化大数据的管理与运用
数据采样要设立严格准入标准,信息数据的可靠性是保证智能量刑结果公平正义的第一道门槛。在传统的法官量刑中,法官的业务素质只能对经由该法官办理的案件产生影响,而智能量刑的普及应用使得数据库变成了公平正义的“源头活水”。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判例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法官对每一个案件的裁判依然独立进行。在智能量刑中,系统检索到的类案判例等数据信息对裁判结果具有直接作用,智能量刑是以检索数据为基础的逻辑判断结果,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对数据库的管理和运用非常重要,这些工作的实现有赖于司法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
其一,在数据信息录入过程中对数据进行筛选[18]。一般情况下,大数据库的建立以数据的全面性为导向,数据收集越全面则统计结果出现偏差的概率就越小。但有些案件的裁判标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审级的法官在业务经验、业务素质上存在个体差异,难免会出现部分严重偏离正常判决结果的裁判。数据信息主要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其中包含重复文书、空白文书等无效数据。因此必须借助数据筛选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由法官根据裁判经验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先行判断,对于无效和错误信息进行标注,建立数据筛选系统。
其二,对数据信息的合理运用。裁判文书网上的信息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因此,简单的描述性分析方法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往往束手无策。为了提升大数据的利用水平与分析效能,需要将社科研究中普遍使用和相对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如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统计学分析方法等运用到大数据分析中,还要熟练运用SPSS、SAS等统计分析软件深度挖掘隐藏在法律大数据之中的宝藏[19]。在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量刑数据模型。
2.智能量刑的公平、透明化
公平、透明化是消除算法偏见,防止权力异化的有效方法。公平是社会的重要价值之一,智能量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司法裁判措施,必须具备公平的价值属性。美国最高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Brandeis. Louis)曾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因此,将智能量刑系统的运算过程和原理公开可以有效约束算法决策。
首先,智能量刑的公平化。量刑算法的歧视或者深度学习方法的歧视实质上是社会偏见在智能量刑中的外化体现[18]。因此消除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社会中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培植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培养司法人员的公平法律思维。在算法或者数据模型中也要排除歧视因素,防止算法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差别对待,同时防止算法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算法歧视。换句话说,不能由于某些犯罪中同时出现某一个普遍要素,就认为该要素与该犯罪之间有极大的相关性,比如,种族、性别和生活环境等。在算法模型的设计和应用过程中需要法官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及时对可能出现的算法歧视问题进行预防和纠正。当数据模型在适用过程中出现部分功能失灵时,及时转交法官进行判断,保证量刑工作的公平化。
其次,智能量刑的透明化。智能量刑的透明化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被告人对量刑过程有知情权,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有抗辩权[7]。智能量刑算法需要以大量数据为基础,数据采集样本过小或者样本中存在大量偏离数据时,都会影响算法结果的准确性。数据透明化可以对数据采集过程进行监督,具体分为数据来源透明、数据内容透明和数据处理透明。算法透明化是抚平“数字鸿沟”的唯一解决办法,之所以将智能量刑系统称为“算法黑箱”,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量刑方式,法庭中的抗辩模式变为“输入要素”“输出结果”的运算模式,因此需要对智能量刑过程进行解释。解决“算法黑箱”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设计系统来解释算法如何得出或预测结果。如果法官对设计者提出解释要求,他们将在塑造“可解释人工智能”(xAI)的性质和形式方面发挥开创性作用[20]。
(二)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司法人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个案正义的核心。在当下,司法人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往往存在很多问题,主观上是由于司法人员个体素质的差异,客观上的原因是刑事案件经常受到其他社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为滋生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首先,智能量刑以逻辑运算的技术理性排除法官的主观任意性和无关社会因素的干扰;其次,智能量刑系统将司法人员的集体裁判经验进行模型化构建,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化运用提供指引,从而消除腐败根源,实现裁判量刑的公平正义。
1.司法人员主导地位的运用
在使用智能量刑系统进行刑事裁判时应明确司法人员的主导地位。法官的审判权来源于人民,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2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其一,司法人员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主导地位。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发挥辅助性作用,刑事证据的审查依然需要司法人员作出判断[21]。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大多运用复杂的形象思维,比如证据材料中的图像资料,法官需要根据图像资料在脑海中进行“场景再现”。再比如对音频证据进行分析时,需要根据说话语气揣摩说话人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人工智能虽然在一些方面实现了“模拟思考”,但是在这些关键领域仍然难以突破。人工智能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思维能力强于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优势,提高刑事证据数学计算的准确性和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当证据链出现瑕疵或者漏洞时及时向司法人员做出预警提示。英国皇家检察署很早就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证据判断,在证据薄弱环节或者证据出现遗漏时提醒检察官进行补充。他们认为辅助系统是“仆人而非主人”,检察官在具备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可以推翻辅助系统的结果[22]。由此可见,在刑事证据判断中,司法人员必须处于主导地位。
其二,法官在裁判量刑中的主导地位[23]。“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并不能够完全预测个体未来犯罪的盖然性,凭借此来量刑的说服力尚有不足。”[24]以逻辑计算为基础的智能量刑提高了结果在逻辑上的准确性,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即智能系统无法全然应对案件中的价值判断、刑事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考量,故而不能完全取代司法人员的裁判[2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徐世亮认为,“审判是一种艺术,世界上沒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机器可以给办案人员做提示、指引,但最终的决定权在法官手里。”⑤应该将软件与处于审判支持状态的人类法官结合起来,并通过程序保障来规范其辅助判断的具体情况,以防止出现审判错误的风险[26]。
从目前的发展看,有的系统根据文件中提取到的情节匹配案件并提出量刑建议;有的系统根据法官选择情节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议;也有一些系统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刑事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责任刑还是预防刑的判断,其思维方式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都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27]。因此,法官必须坚守裁判量刑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智能量刑系统的工具价值,更好地实现量刑公正。
2.算法决策介入刑事司法领域
量刑公正的实现离不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如果不对其加以限制,容易陷入对自由裁量权“误用”“滥用”的司法腐败风险[28]。量刑规范化改革就是要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整体量刑的公平正义。“法官虽是改革活动中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如果想完成改革重任,还需内外兼顾,采取联动措施从法院外部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29]首先,应该清楚剥夺法官部分自由裁量权的不是“机器”,而是算法;其次,算法决策反对裁判的任意性,但是不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实质上是算法决策介入刑事司法领域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形成约束作用。为了确保法官在裁判量刑中的主导地位,有必要厘清算法决策介入刑事司法领域的边界。
其一,范围的框定,即算法裁判适用的案件范围。(1)对于智能量刑技术尚不成熟的领域,智能量刑应谨慎介入。智能量刑实质上是法官集体经验的模型化[30]。在面对新类型案件以及案件涉及新颁布的法律时由于缺乏先前裁判经验,往往表现出“无力应对”。如案例规则及其调整,还有刑事政策、改革试验等非正式规定等。(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应将智能量刑系统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轻罪案件⑥。目前,我国的智能量刑处于起步阶段,刑事司法、技术运用都尚未成熟,智能量刑适用于轻罪案件风险较小,可以在逐渐成熟后扩大适用范围[31]。(3)根据被告人的意愿。被告人有权利拒绝适用智能量刑系统,当存在多种智能系统时可以选择适用哪种智能系统。
其二,限度的把握,即算法决策介入刑事司法领域的程度。(1)算法决策的介入需要以司法权力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基本前提[32]。当前,智能量刑系统对法官办案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并通过数据运算对司法人员的办案活动作出辅助提示,司法人员拥有裁判量刑的最终决定权。(2)算法决策的介入要坚持法官的主体地位。智能量刑系统只能作为裁判活动的工具,帮助法官减轻工作负担,并提供量刑参考意见。
(三)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司法治理新模式
在当下,需要建立人机协同的司法治理新模式[33]。人工智能量刑是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算法模型得出逻辑运算结果,它的优势在于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它的缺憾在于逻辑运算忽略了不同案件的个别性。法官的集体经验甚至集体中共有的偏见相比较三段论逻辑推理而言,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治理人们的规则[34]。司法裁判中的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和真假善恶难以单纯依靠计算概率实现,因为算法只能进行逻辑上的推演,缺少对案件的实质性判断,这种实质性判断是达至实质正义的必要条件[35]。法官量刑正好可以弥补智能量刑的这种缺憾,它的核心是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即将法律规范和具体案件事实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与案件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质性判断。
人机协同司法治理新模式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明确科学技术对裁判量刑的赋能地位,杜绝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和技术模式,坚持法官在量刑裁判中的主导地位。人机协同归根结底要明确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差异,并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人类刑法文明史,就是一部为实现刑罚目的而不断探索量刑公正的历史。”[36]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为刑事司法领域带来诸多便利,如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类案同判”等。“Loomis”案件引发了对智能量刑实践的反思,即如何消除人们对算法决策的疑虑以及如何实现量刑公正。量刑公正的实现需要智能量刑算法决策和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深度融合,算法决策排除“恣意性”,对刑事自由裁量权形成规制效果;刑事自由裁量权克服算法决策的“机械化”,为实现个案正义提供可能。两者通力协作构建人机协同的司法治理新模式,从而实现裁判量刑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李训虎.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包容性规制[J].中国社会科学,2021(2):42?62.
[2]崔亚东.人工智能与司法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14?115.
[3]谭红叶,张文博,张虎,等.面向法律文书的量刑预测方法研究[J].中文信息学报,2020(3):107?114.
[4]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27?128.
[5]姜敏.刑事司法事实自由裁量权规制研究[J].现代法学,2013(6):114?121.
[6]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J].中国法律评论,2016(4):195?246.
[7]马靖云.智慧司法的难题及其破解[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4):110?117.
[8]白建军.法律大数据时代裁判预测的可能与限度[J].探索与争鸣,2017(10):95?100.
[9]黄京平.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负面清单[J].探索与争鸣,2017(10):85?94.
[10] SONJA B.Starr:evidence-based sentencing and the scien? 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discrimination[J].Stanford Law Re? view,2014,66(4):803?831.
[11] RICHARD P. Kern & meredith farrar-owens sentencing guidelines with integrated offender risk assessment[J].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2004,16(3):165?169.
[12]張德.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研究[J].信息与电脑,2017(17):33?34.
[13]孙道萃.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64?78.
[14]项威.事件知识图谱构建技术与应用综述[J].计算机与现代化,2020(1):10?16.
[15]严剑漪.揭秘“206”:法院未来的人工智能图景——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164天研发实录[J].人民法治,2018(2):38?43.
[16]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4(2):78.
[17]董玉庭,董进宇.刑事自由裁量权基本问题[J].北方法学,2007(2):49?57.
[18]刘友华.算法偏见及其规制路径研究[J].法学杂志,2019(6):55?66.
[19]左卫民.迈向法律大数据[J].法学研究,2018(4):139?150.
[20] DEEKS A.The judicial demand for 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ngence[J].Columbia Law Review,2019(7):119.
[21]纵博.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1):61?69.
[22] GREENFIELD J. Decision support within the criminal jus? tice system,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J].Computers&Technology,1998(12):169?278.
[23]朱体正.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J].浙江社会科学,2018(6):76?85.
[24]张福利,郑海山.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定位、前景及风险防控[J].广西社会科学,2019(1):92?102.
[25]冯洁.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理论的挑战:回应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21?31.
[26] AINI G.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applica? 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Chinese Studies,2020,(9):14?28.
[27]黄春燕.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与量刑公正的实现——兼论人工智能在量刑中的定位与边界[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3):136?145.
[28]王国龙.自由裁量及裁量正义的实现[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0(4):66?86.
[29]张勇.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路径[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2):108?117.
[30]白建军.基于法官集体经验的量刑预测研究[J].法学研究,2016(6):140?154.
[31]胡铭,张传玺.人工智能裁判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及其消解[J].东南学术,2020(1):213?248.
[32]王禄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话语冲突及其理论解读[J].法学论坛,2018(5):137?144.
[33]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N].人民日报,2019-11-28(06).
[34]小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35]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J].法学研究,2020(4):23?40.
[36]沈德咏.论量刑公正.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Sentencing Algorithm Decisionmaking and Criminal Discretion
Li Lifeng, Qi Yibo(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00,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tencing system brings many conveniences to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improves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realizes“consistent judgement in similar ca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 tencing system takes data model operation as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forms algorithm decision-making through logi? cal operation. Criminal discretion is the judicial power given to judges in order to achieve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 Intelligent sentencing algorithm decision-making and criminal discretion are not only different in value position, but also different in fact finding, law application and power attribute. Moreover, they maintain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 ship. In order to avoid the arbitrariness of judges sentencing and the mechanization of intelligent sentencing system, we should highlight sentencing reform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First of all, adhere to the judge leading position in sentencing. Secondly, define the boundary of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interven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Finally, ad? here to people-oriented and build a new judicial governance model of man-machine cooperation.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tencing; algorithmic decision; judge sentencing; criminal discretion; manmachine cooperation
①新華社: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这些要求。访问地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820633997130001&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6日。
②最大池化就是选择图像区域中最大值作为该区域池化以后的值,反向传播的时候,梯度通过前向传播过程的最大值反向传播,其他位置梯度为0;平均池化就是将选择的图像区域中的平均值作为该区域池化以后的值。
③参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刑更321号刑事裁定书。
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中量刑指导原则第3条规定: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⑤上海法院网:揭秘“206”:法院未来的人工智能图景——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154天研发实录,访问地址:http://sh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7/07/id/292107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0月8日。
⑥轻罪是指在刑期上为3年或者3年以下的罪名,根据近十年《中国法律年鉴》的信息来看,如果单纯以刑期为轻罪标准,轻罪案件的比例占所有刑事案件的比例约为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