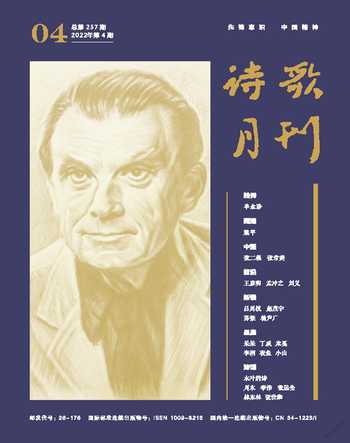消失的木叶
读木叶诗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冒冷汗的过程。这个冒冷汗不在于文本,不在于意义,也不在于节奏和气息,而在于一个读者、一个诗人同行读者对一个作者期望值的不断降低。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将作者自己不断剔除其诗作的过程——作为诗人,他可以被他背后的那些诗人替代;而作为文本,这些诗作既可以被别的类似的文本替代,甚至也可以被作者自己之前的那些文本替代。
其一,有评论家说木叶的诗作充满了“古今中西的镶嵌、碰撞与对话”,这句褒奖在我更接近一句贬语,在我的目力范围内,他诗作中的“古今中西”——尤其是“古”和“中”,其实不乏前例、不乏同例,也不乏后例,这一点在比他年长、与他同龄、后他而起的各地诗人尤其安徽诗人的作品中并不鲜见;而这种“今”和“西”亦然。作为一个成熟诗人,吸收得越多也即意味着失去得越多,在这一点上,木叶既消失在了那些“古今中西”之中,也消失在了那些靠“古今中西的镶嵌、碰撞与对话”写作的一眼望不到头的诗人队伍之中。
其二,木叶诗作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气息、节奏和破坏性,似乎成了他一种醒目的标志和异质性,也被很多批评家进行了指认和塑形。但是严格来说,这也并非独其一份,这一点,看看那些西方大师追随者们的作品就一目了然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独其一份也依然难逃“风格即死”的命运。是的,风格固然是一个诗人在诗作之外的个人特质的投射和延伸,固然是一个诗人通过诗作而苦心经营出来的作品特质,然而这也无异于一种内卷和自我重复,这是作者自己画出来的牢,是评论家为作者画出来的牢,又或者是前者和后者齐心协力画出来的牢。
所以,无论基于上述哪一点我都难以认同“木叶体”的命名。这种命名显见的与其说是木叶和“木叶体”,不如说是批评家们乏于制造历史的焦虑和抢占命名先机的急切。事实上,这种命名无论对诗学还是对诗人都害而无益,于诗学,这体那体的命名助长的是此起彼伏的标新立异,而非诗歌本体的价值增值;于诗人,一种体的成型是风格,同时也是魅惑,会大大增加诗人被投喂和诱捕的风险。
作为“木叶体”创立者——或被创立者,木叶虽然并未领受这个“体”,不过在他迄今为止的作品里我尚未读出他对这个“体”的警醒,更未读出他走出这个“体”的可能性。所以该冒出来的冷汗我還会继续冒下去,为一个诗人的“木”和“叶”消失在别的诗人的“木”和“叶”之中而冒,更为一个诗人的“木”和“叶”消失在自己年年生发出来的“木”和“叶”之中而冒。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成熟诗人——也不单单是诗人——来说,走到同温层和舒适区之外,走到“戏要三分生”的那个“生”里去,才是诗歌应有的和诗人该主动追寻的要义。
林东林,现居武汉。武汉文学院签约作家,兼任《汉诗》主编助理。著有《迎面而来》《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着诗人回家》《线城》《身体的乡愁》《谋国者》等各类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