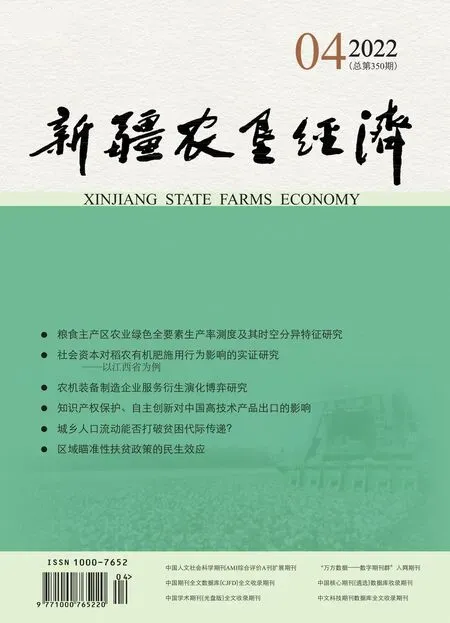社区支持农业下生产者高劳动投入的困境及经济学解析
——以张家农户为例
○ 谢彦明 赵娟 张连刚 唐金朝 佟元芃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一、引言
西方发达经济体农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产业化、资本化和化学化进程,在创造高产出和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水土资源及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更是成为萦绕在消费者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结”,作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应运而生。CSA 萌芽于日本、瑞士等国家,是一种社区附近农民和吃这个农民生产的产品的人之间的联系[1]。由于CSA 通过构建城市消费者与乡村生产者之间紧密的信任关系实现生态农副产品的产需衔接,在国外也被称为信任农业、公民农业和安心农业。在这一体系中,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户有了一个生态农副产品销售的及时性市场,作为城市的消费者则获得新鲜、安全、健康的本地产品[2]。从某种程度上说,CSA正是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为目的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旨在对原有食品系统进行改革与重构以获取绿色农产品[3-4],是对长链条的公司食品制度的一个替代方案。但是,CSA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中却遭遇了管理、人才、生产、消费和土地等方面的困境[5],高劳动力的投入更是首当其冲,让参与CSA从事生态种养的农户“不堪重负”,让准备加入的农户“望而却步”,正像BRANDI[6]所指出的那样,获得负担得起、可靠的劳动力往往是CSA 生产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CSA农场经营面积往往不大,但其劳动力密集型的属性却决定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才能成功,HAYDEN[7]更是直接指出,如果缺少一个积极的社区作为核心,CSA的生产常常会落在农民身上,而这会压垮小农场的运作。可见,农户生态种养实践的高劳动投入问题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破解这一难题,既关系到农户生态农业的高劳动投入能否缓解,也关系到作为“未来农场”和“新经济催化剂”的CSA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习惯于高化肥、高农药的传统石油化学农业能否成功转型为更富有价值优势的“后现代生态农业”。但遗憾的是,传统农户生态种养的高劳动投入强度的程度究竟如何?导致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困境的生成路径究竟是什么?在既有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农户可以采取哪些方法破解这一难题?其效果究竟如何?诸如此类问题,鲜有学者进行过深入而透彻的分析,急需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而又深入的剖析。为此,本文以加入CSA从事生态种养的张家农户为例,采用等产量曲线模型解析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访谈数据实证刻画了高劳动投入的程度及其原因,以期为传统农户转型从事生态农业实践提供策略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单案例多层次分析法,以加入润土帮帮城乡互助消费合作社的张家农户为例[8(]以下简称帮帮),以农户生态种养所带来的高劳动投入困境为切入点,采用等产量曲线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中,主要采用农户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观察体验、员工访谈和二手资料等方法收集数据资料,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获得可以进行多维度彼此验证的数据,提高获得数据的信度、效度。
1.农户访谈。张家是帮帮的6 个合作农户之一,合作最早、种养经验最为丰富、供给的生态农副产品最多。与其主要进行2次访谈,第一次是2018年12 月24 号,利用带领本科生到张家农户实习的机会,与农户张进光开展了持续2 个小时的访谈。第二次是2019 年7 月27 日至28 日,调研团队驱车来到农园,并于当晚和次日上午对张进光前后进行了各2个小时的访谈。期间,访谈人员做了大量现场笔记,并在访谈后24 小时内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之后立即进行研读,如发现疑问,便对张进光进行电话、微信、见面沟通确认和修正。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加入帮帮前后农园生产结构、模式和规模的转变,以及生态种养模式转变后劳动、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及变化情况,高劳动投入的应对方法等方面。
2.观察体验法。利用调查访谈的闲余时间,前后数次到农园进行现场观察与交流,与女主人共同除草、喂猪等农作体验,直接了解和掌握种养规模、类型、方式、地块分布、地势位置、自然环境等情况。这种观察与体验相结合的方法以相互印证、访谈补充的方式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支撑。
3.员工访谈。在帮帮书香门第消费合作社体验店,与帮帮运营团队创始人兼员工前后进行了总共4 个小时的访谈,第一次是2019 年7 月20 下午,第二次在2019 年7 月25 日,主要围绕帮帮与张进光的合作历程、生态种养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其他农户合作等方面展开。
4.二手资料。除了上述方法外,研究团队主要通过帮帮健康生活馆公众号中的去村里、吃土货、农友会以及合作社公众号中的乡村体验、农友档案和农事记录等网络平台间接获取农户的基本信息以及相应生态种养的基本活动信息,以进一步补充、修正和完善研究所需数据。
三、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表征与生成路径
(一)案例背景
张家农户是当地最早加入帮帮从事生态种养的农户。其农园地处安宁和禄丰交界的一个半山苗寨,位于昆明安宁市禄膘镇密马龙村委会滑石板村。该村海拔2 100米,森林覆盖率达94.5%,林地资源丰富。农园距离帮帮昆明店铺大约90 公里,车程近2个小时。目前,农园耕地面积18亩,共10块。户主张进光家现有3口人,他本人主要负责生态蔬菜的育苗、种植、收获、土猪宰杀及生鲜食品的运输,每周三和周六向昆明春之城小区帮帮生活馆定时定量配送。他媳妇主要负责土猪和牛的饲养、菜园日常打理等方面的事务。他儿子正在读书,在节假日才能从事部分农事劳作。与帮帮合作前,张家生计方式主要是“务农+打工”的兼业模式,农作方式主要为“化肥+农药”的常规方式,主要种植烤烟、玉米、白菜、土豆等传统大宗型经济作物和农产品,维持着半自给自足和半商品经济的生计方式。2015年加入帮帮后,开始了不使用农药、化肥和不喂饲料的生态种养模式实践,开启了传统兼业小农向现代生态农场的转型升级之路。
(二)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表征
金博士在《四千年农夫》中指出:中国农民对农业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已经达到了吝啬的程度,唯一不计代价和毫不吝啬投入便是劳动力。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劳与质朴特性仿佛如基因一样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加入帮帮的张进光及其家人的生态种养转型与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他说:“2018 年前,土猪的饲养主要是由我母亲料理,相当的辛苦。从2019年起,由我爱人管,要是按工算的话,一天至少要1.5个工。我母亲料理的时候,一般早上5 点钟起床,晚上10 点钟才睡下。所以一天最少要一个半工,一年至少要500个工,养猪用工相当多。过年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休息,我家的情况是这样,除非帮帮放假,一般是国庆节和春节的时候,我家就不供菜了,这几天休息了,其他时间都休息不了”。帮帮创始人徐国玉说:“特别是送菜的那两天,张大哥特别的辛苦,我们特意为他买了个临时休息的睡椅。周三、周六送的菜、肉卖完后,一般都下午两三点了。他匆匆吃一口午饭,会抓紧时间在睡椅上休息一会儿。起来后,还要开车往家里赶”。张进光说:“像送菜那天,早上起来我要准备菜,一般是天亮我就起来,一直准备菜,到下午的时候,我要做豆腐,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兼业小农向专业生态农场转型的辛苦程度与状态由此可见一斑,为进一步揭示张家农户生态种养劳动的投入情况,本文列示了农园男女主人2019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劳作时间(见表1)。

表1 农园男女主人不同季节的劳作时间表
(三)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生成路径的经济学解析
1.要素可变下的等产量曲线模型。为刻画CSA 情境下农户生态种养劳动投入水平的动态变化,在此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等产量曲线模型。它是要素投入与组合可变的长期生产函数,可以动态揭示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形成的机理,如图1所示。横轴X 表示以投工量为代表的劳动投入水平,纵轴Y 表示以农药化肥为代表的资本投入水平;AB 曲线代表以传统大中型农产品生产为主的等产量曲线;CD和EF代表以生鲜蔬菜生产为主的等产量曲线;OR 线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水平相同的等比例的生产扩张线,即资本与劳动投入水平比例为1∶1。在OR以上的生产可能性域是资本投入水平高于劳动投入水平的区域,代表资本密集型生产域,在OR以下的生产可能域是劳动投入水平高于资本投入水平的区域,代表劳动密集型生产区域;OM 代表资本密集倾向型扩展线,ON 代表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展线;OP 代表高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展线。其中,A点代表农户生态种养前从事以传统大宗型农产品生产为主状态点;G点代表农户生态种养后从事绿色生鲜食品生产为主的状态点。可见,由A点到G点,劳动投入水平由L1增加至L4,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水平是不言而喻的,其过程分解为由A—D—F—G三个过程。

图1 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路径生成示意图
2.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生成路径。如图1 所示,农户生态种养表现为由等产量曲线AB上的A 点向等产量曲线EF 上的G 点移动,劳动投入水平由L1增加至L4。可见,农户生态种养导致的劳动增加量,在劳动投入数量或人数不变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增加劳动的实际投工量来应对由于种养结构调整、规模扩大和方式调整所产生的劳动需求,具体过程可以表示为以下三个过程。
过程一:表征为农户种养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变化,体现为由传统大宗型粮食类农产品的资本密集型生产可行域向蔬菜、猪肉等生鲜食品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可行域的变化,体现为等产量曲线AB由A 点移动至等产量曲线CD 的D 点,资本投入水平由K1上升至K2,劳动投入水平由L1增加至L2,该过程主要是由于农户种养结构及其所带来的类型转变导致劳动投入水平的增加。
过程二:表征为由于农户种养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变化,体现为农户由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专业生态型家庭农场的转变与升级,由于生鲜蔬菜的种植频率和复种指数更高,导致农户生产规模扩大,表现为等产量曲线CD 沿着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展线ON平移至EF,资本投入水平由K2上升至K3,劳动投入由L2增加至L3,由于等产量曲线沿着扩张线ON移动,所以,D点与F点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比例不变。该过程主要是由于响应消费者对生鲜食品的持续性需求的高种植频率导致种养规模扩大带来劳动投入水平的增加。
过程三:表征为农户种养方式的调整所带来的变化,体现为由石油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农户采取有机或近似有机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使用传统化肥、农药和杀菌剂。在农业绿色技术缺乏的情境下,其生产过程主要是用农家肥和人工防虫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要素替代化肥、农药等资本密集型生产要素。表现为等产量曲线由EF上F点移动至G点,资本投入由K3降低为K4。劳动投入则由L3增加至L4,由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保持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对资本的替代能力越来越弱化,意味着用更多的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的减少。该过程主要是由于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效应导致了劳动投入水平的增加。可见,农户生态种养的高劳动投入不言而喻。为进一步揭示农户生态种养后以上三个过程及其转变对农户生态种养劳动投入水平带来的具体影响,基于对张进光的深入访谈,直接采用被访者的回答内容和相关数据,对农户生态种养的高劳动投入的成因、程度及其过程进行呈现。
四、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实证刻画
正如RYAN[9]所发现的那样,对CSA 理念的认同以及据此所形成的道德规范对生产者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从事生态种养销售相对高价格的生态农副产品提供了持续而稳定收入的激励;另一方,面对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那份强烈义务感也形成了对从事生态种养农户的强烈道德约束,要求张进光及其家人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从而陷入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强度的“自我剥削”境地。农户张进光对帮帮“支持小农生态种养、共享食物本真味道”的理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与认同,并在生态种养的实践中转化为生产高质量食品的实际行动,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10],他说:“要成为帮帮的一员,最关键是要认同帮帮的理念,我和帮帮、消费者就像是一家人,帮帮与消费者重来不欺骗我,我也从来不欺骗帮帮和消费者”。表2 展现了张进光加入帮帮前后,从传统种养向生态种养转型后生产结构、种养规模和投入产出等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从在投入产出看,加入CSA前,总成本、总收入和纯收入仅为11 476元、25 360元和13 884元;加入CSA后,从2015年到2019年投入产出水平显著快速增长,2019年总成本、总收入和纯收入分别达到87 814 元、256 850 元和169 036 元,显著高于农户转型前从事“务农+打工”兼业模式的收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收入水平也高于2017年至2019年的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2014年到2019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 299.01元、26 373元、28 611元、30 995.9元、33 488和36 238元。,而农户生态种养能否获得持续稳定且高于加入CSA 之前的“务农+打工”的兼业型收益,是农户长期坚持生态种养的关键[11]。当然,生态种养的高产出高收益需要高投入保障,高劳动力投入就是农户挥之不去的“痛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农户劳动密集型生鲜食品生产的转变、高频率高复种指数下种养规模的扩大和生态种养后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性投入三个方面。
(一)劳动密集型的生鲜食品生产的转变
蔬菜、猪肉等食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使得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12]。CSA 的嵌入消除了张家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生产方式由传统自给自足的模式转向现代商品化模式,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和劳动力的情况,张进光对种养结构进行了适应性调整,由传统大宗型粮食作物向劳动力密集型生鲜食品转变。由表2 可知,加入帮帮前的2014 年,农户的种养结构以生产销售风险低的传统大宗型经济和粮食作物为主。玉米、土豆和烤烟各种植7 亩、5 亩和5 亩,蔬菜种植1 亩和生猪养殖4 头,主要用于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加入帮帮后的2015 年至2019 年,为对接消费者对蔬菜的需求,农园种植结构调整为生态蔬菜为主,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到2015 年的7 亩和2016 年的13 亩。即使囿于劳动力的减少,蔬菜种植规模依然维持在2017 年10 亩、2018 年8 亩和2019年7亩的水平。玉米的种植面积则逐渐减少,2018 年开始不再种植玉米。而且,2018 年也开始不再种植土豆,供应主要由更适合种植土豆的小芳及合作伙伴来供应。可见,农户向生鲜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转型成为劳动投入增加的一个重要成因,表征为图1 中等产量曲线AB 上的A 点移动至CD 上的D点,劳动投入水平则由L1增加至L2。

表2 农户生态种养转型前后生产结构、种养规模和投入产出表
(二)高频率高复种指数下的种养规模的扩大
为满足消费者生鲜食品的高频率、持续性需求,仅进行由粮食型农产品向经济型农产品的转型是远远不够的。在生鲜食品供应时间的持续性、品种数量的多样性方面,能否及时准确对接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成为农户生态种养能否获利和成功的关键。为此,张家不断优化蔬菜种植结构,合理间作轮作以提高蔬菜种植品种和频率。当然,这需要增加劳动投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在蔬菜种植品种方面,2017年蔬菜种植的品种多达43个,张家蔬菜种植品种在不断进行优化和减少,2019 年蔬菜的品种下降为16 个。在蔬菜种植频率方面,以2019年蔬菜种植量较多的大白菜、青花菜、莲花白和番茄的种植频率为例,种植频率分别为24 次/年、24次/年、12 次/年和3 次/年,种植面积分别为4.8 亩/年、3 亩/年、3.6 亩/年和1.5 亩/年。可见,对消费者多品种、高频率的需求响应,显著增加了农户蔬菜种植面积和土猪饲养规模。这需要增加劳动投入水平与其相适应,主要表征为图1中沿着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展线ON,等产量曲线CD移动至EF,劳动投入水平则由L2增加至L3。
(三)劳动对化肥农药等资本密集型要素的替代
CSA作为一种有机的、可持续的农产品生产方式,消费者对农副产品的品质有着较高要求,生产者要采取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有机或近似有机的方式从事生产,其核心环节是利用劳动替代资本或者资本浅化来实现土壤改良[13-15]。他说:“一定要诚实,生态种养不能施用农药、化肥,就一定不能用”,而这需要用劳动投入替代化肥、农药、杀菌剂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免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家肥的收集、装卸、运输、渥堆、施用等诸多环节的劳动投入便佐证了这一事实。他说:“自2015年从事生态种植以来,7 亩菜地主要施用农家肥,2016 年买了3 拖拉机牛粪,100 元/车,2017 年使用了3 次羊粪,共50 袋,14.5 元/袋;2019 年使用了10袋羊粪,18 元/袋,每年大概使用30 吨的农家肥。以2019 年为例,种一批菜就要使用一车(拖拉机)的牛粪,大概2 吨/车,每年至少种植10 次,这就需要20吨的牛粪,猪粪则是直接背到地里使用”。锄草方面。针对番茄、大白菜、青花菜、卷心菜等需求旺盛的蔬菜,采取了3~6 茬/年的种植方式。如果没有覆盖薄膜,蔬菜至少需要人工除草3~4次/茬,即使覆盖地膜,蔬菜种植也要除草1~2 次/茬。这样算下来人工除草的投工量是巨大的。以2019年种植7亩地为例,按照最保守的复种3次计算,按照除草2 次计算,除草面积达到42 亩,按照1 个工每天除草0.5 亩计算,投工量要达到84 个工。可见,对化肥、农药等资本密集型要素的替代过程需要大量投入劳动,表征为图1中等产量曲线EF上的F点移动至G点,劳动投入水平则由L3增加至L4。
五、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破解的路径与策略
(一)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破解的路径选择
根据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生成路径,其逆向思维便产生了如图2 所示的高劳动投入破解的路径。意在实现农户劳动投入水平由L4降低至L7,即由等产量曲线EF上的G点变为等产量曲线IJ上的Q点,具体包括路径1、路径2和路径3三个过程,其过程表现为劳动的减少和资本的增加,即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等产量曲线上点的移动和平行移动,仅代表了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破解的可行路径和方向,并不代表农户劳动投入必然降低和调整的程度。

图2 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破解示意图
路径1:以有机肥和生物农药为代表的绿色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在保持生态农产品产出数量不变的前提下,主要用工业化的有机肥料替代农家肥,用生物农药替代人工式的虫害防治,表征为同一条等产量曲线EF由G点移动至F点,劳动投入水平由L4下降为L5,但资本投入水平由K4上升为K5。
路径2:以小型适用农用机械为代表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在保持生态农产品产出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机械替代劳动等劳动力节约型的小型适用农用机械的引入,实现等产量曲线EF 由F 点到H 点的移动,劳动投入水平由L5下降为L6,资本投入水平由K5上升为K6。
路径3:适应农户家庭的资源数量和生产环境规模调试优化。根据农户劳动力数量和农园海拔、温度、灌溉条件调试优化种养品种和结构,适度降低生态种养规模,使农户种养规模由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调整为规模经济阶段,表征为等产量曲线EF平行移动至IJ,劳动投入水平由L6下降至L7,资本投入水平由K6下降至K7。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指出的那样,土地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是跟着农业技术而改变的,若是农业中工具改进,或是应用其他动力,所需维持的人口也可减少。可见,降低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困境的关键是促进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其本质在于用资本替代劳动,摆脱高劳动力密集倾向型扩展线OP 的束缚,使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水平达到较为合理的投入比例水平,进而降低劳动投入。实际中,农户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为此,针对张家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化解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交流,以明确在既有技术、资源和条件约束下,农户生态种养的高劳动投入困境化解的主要方式以及效果。
(二)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破解的策略选择
1.公开共享的农业有机绿色生产技术。CSA深深的嵌入地方性食品生产系统,其众多利益相关者为农户提供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生态种养技术的获取渠道。依托云南生态农业年会、农友分享会、年初生产计划会等面对面交流活动,公开与共享绿色生产技术成为提高农户生态种养技术水平和有效降低劳动高强度投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张进光的回答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他说:“加入帮帮以来,我也是不断地再学习、再成长。2015年3月,我们曾到四川成都安龙村高家农户考察生态农业的生产。他家信佛既不养猪也不养鸡,只种生态蔬菜,水好,3亩土地,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17~18 万,增加了我搞生态农业的信心。2017 年6 月27日,乐施会又组织我们去了一次,我以为当时菜应该相当的多,但是,当时的菜相当的少,只有苦瓜、甘豆、茄子、辣椒和空心菜,主要是四川盆地气候不适合,温度太高,湿气太大,不适合种植叶菜类蔬菜。相对于四川,云南更适合搞生态农业”。“2017年6月,到梓萌农业考察番茄的种植,让我了解到,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生态与高效兼得,只要水肥足产量可以很高,高投入也意味着高产出,一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10 吨,而2018 年我种的番茄的产量才2吨左右”。
2.“干中学”式的生态种养技术的累积进步。藤田和芳在《一根萝卜的革命》指出:“刚从事有机农业一年的农户与坚持了三十年的农户,其技术和手法是完全不同的”[16]。生态种养的转型和有机农业的实践不仅需要农户在体力上投入数倍于化学农业的劳动,更需要农户付出智力上的努力,不断精进生态种养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技能。张进光在番茄种植技术方面的不断学习与精进证实了这一点,他说:“2015年刚开始种植番茄的时候,采取的露天种植方式。云南旱季和雨季分明,雨季的时候,土壤水分太大,番茄扎不了根,秧苗和青果腐烂特别严重,剩下的秧苗好不容易挂了果,由于太阳紫外线太强,导致番茄灼焦和爆裂。再加上病虫害,辛苦种下去的番茄产量很少,入不敷出啊”。“2017 年开始,投资0.9 万元盖了3 个番茄大棚,安装了简易滴灌设施、防虫网和生物防虫灯,基本上解决了灌溉和病虫害的问题,而且,番茄的种植可以由原来露天1 次/年提高到现在大棚种植的3 次/年。现在你看我有三个大棚,每个大棚有0.5亩,按季节依次种植。其中,第一茬番茄年前11 月份育秧,由于天气冷,3月份初才能移栽,6月份收获;第二茬3、4月份育秧,5月中旬移栽;第三茬下半年8月中旬种植,比刚开始种植时的效益好多了”。
3.种植品种、规模和结构的不断调试优化。2017—2019 年农户的蔬菜种植面积逐步减少调试为10 亩、8 亩和7 亩,供需缺口主要由2016 年加入帮帮的李家供应。且侧重于更适合种植的叶菜类蔬菜供应,由于农园海拔高、光照强和灌溉条件差,因此,相应地减少了叶菜类蔬菜的种植。农户不断调试与优化蔬菜种植品种和面积,品种由43 个逐步减少为16 个,面积由13 亩下降到7 亩。不断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到2018年不再种植,土猪饲养所需玉米饲料主要通过向本村和邻村购买。也不再种植土豆,土豆供应主要由更适合的小芳家供应。与此同时,农园休耕面积扩大至2018 年的10 亩和2019 年的11 亩,用于未来蔬菜的种植。蔬菜的种植也更多地采用地膜覆盖,以减少除草的人工投入,在蔬菜所需劳动力投入相对较多的种植和收获环节则采取雇工的方式。可见,基于家庭劳动力的减少和加入农户的分工协作,张进光对种养规模、结构和品种进行不断的调试与优化,以减少劳动投入水平,同时采取种养结合的传统经典模式,将有限的劳动投入到更适合农园生产环境和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和土猪等生鲜食品生产中,并在生产的实践中不断优化劳动力的配置。
4.构建支持农户生态种养的政策扶持体系。农户生态种养的实践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而且可以改善和保护农业资源环境,更可以提升消费者的健康水平,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重效益。相关的研究表明,向CSA农民提供金融和非市场形式的补偿对维护农户生计至关重要[17]。在推进我国农业社会化、生态化转型的进程中,政府更应该扛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一是建立农业绿色技术研发创新体系。依托农业绿色技术“产学研”创新联盟,在保护、传承和创新我国传统优秀农业绿色防控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现代农业绿色化、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创新和集成,构建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为重点,以先进适用的生态农业设施、设备和机械为支撑的农业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二是完善农业绿色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绿色技术推广服务人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绿色发展理念、掌握绿色生产技术技能的绿色农技推广人员,制定和实施差异化、在地化的生态农业绿色技术实施方案,强化地方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责任,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推广应用。三是建立农户生态种养实践的绿色补贴政策。积极发挥农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和提高绿色发展质量的政策改革取向,推出绿色直接补贴政策,支持农户所有者采用与保护环境、景观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农户超过强制性义务标准的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直接补贴[18]。
六、结论与讨论
CSA 情境下农户生态种养的实践既是一个种养结构、规模和方式转变过程,也是一个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调试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从市场效率逻辑向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回归的过程。它重塑了人与人、人与土地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毋庸置疑,CSA部分脱嵌于市场主流逻辑下农户生态种养的实践必然充满了困境、挑战和不确定性,高劳动投入强度和辛苦程度就是农户生态种养实践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尤其在小规模绿色、生态和有机种养技术欠缺的情境下,作为CSA生产者的农户往往陷入高劳动力投入强度的“自我剥削”的境地,尽管农户生态种养的高劳动投入让农户举步维艰,但这是农户为及时、准确地响应消费者需求而不得不经受的一段“炼狱”的过程。欣慰的是,在既有的劳动力、耕地资源和技术条件下,通过农业绿色技术的导入、“干中学”式的生态种养经验的累积精进和种养结构、规模和方式的不断调试优化,成为农户应对生态种养转型高劳动投入困境的主要策略选择,通过资本密集型绿色技术进步创新,即在同一条等产量曲线上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促使农户由高劳动密集型扩张曲线向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张曲线的转移,从而跨越劳动替代资本的低效率区间。通过中性技术进步,促使农户生产由劳动密集倾向型扩张曲线向资本—劳动等比例扩张曲线的转移,通过种养结构与规模的调试,实现了从规模报酬递减向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回归,从而克服了农户生态种养高劳动投入的困境。
囿于我国农业生产几十年的高药、高肥投入的惯性使然,加之农业经营效益的低下,使我国传统农户逐渐丧失了传统生态种养的“技能”,更逐渐失去了精耕细作的“耐性”。以至于产生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这应该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可喜的是,不同于当下农业规模化、商业化和资本化的主流趋势,CSA情境下张家农户生态种养的卓越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山区传统小农转型为现代绿色农业的一种可能。同时,该模式也为实现传统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更为在我国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的永续农业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当然,作为地方性食品体系再造运动模式的CSA,以及其嵌入这一社会网络体系中的农户生态种养的实践离不开消费者、消费合作社、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更离不开政府在理念上的认同和配套政策上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