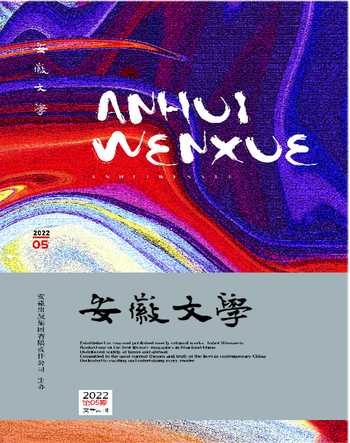融媒介语境下先锋作家的创作流变
李文静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多种媒介的交互与融合逐渐成为全新的时代语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阅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融媒介是继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介形态,包含了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有线网络、无线通信网等渠道,运用手机、电脑、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复杂多样的信息环境强烈吸引和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语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因素对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将以余华、莫言等当代先锋作家近期的创作活动为依据,探究从跨媒介的兴起,到各种媒介高度融合的时代语境下先锋作家的创作流变。
一、先锋创作与跨媒介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以黑马之姿闯入中国文坛,以马原、余华、格非、苏童、莫言等人为代表的先锋作家通过“叙事迷宫”展示着“先锋”的新奇与魅力,为急需人文精神关怀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之气。20世纪90年代,经过短暂的辉煌,在消费文化日益盛行的时代语境下,先锋小说因其晦涩难懂的语言和过于符号化的叙事,导致知音甚少,渐渐被大部分读者抛弃,陷入了较长时间的沉寂期。被莫言称为自己“登峰造极”之作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出版后读者寥寥,评论文章相比于莫言的其他小说数量急剧减少。而余华通过影视改编而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活着》在刚出版之时销量也少得可怜。不论是叙事的碎片化还是语言的狂欢晦涩,都让新鲜感过去的读者再也无法提起对“先锋”的兴趣,迅速的排斥与疏离不仅导致了小说销量的下降,也直接影响了作家们的后续创作。“昙花一现的命运,促使先锋派小说家,不能不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跨界糅合,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本土化味道的现代主义创作”(方维保《当代长篇小说七十年:时代潮涌与审美嬗变》)。在消费文化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语境下,寻找小说创作在现实社会的立足点成为“先锋作家”们的当务之急。此时,影视传媒悄然兴起,以张艺谋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将目光对准了先锋小说。1987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首先被张艺谋看中并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之后一举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百花獎最佳故事片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8项大奖。这让陷入困局的先锋小说家重新获得了青睐,1991年,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4年,余华的小说《活着》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活着》……相比小说文本的无人问津,改编后的许多电影一经上映就引发观看热潮并屡获国际大奖,小说文本和影视改编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与影视媒介联系甚密的王朔在20世纪90年代曾说,“用发展的眼光看,文字的作用恐怕会越来越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影视是目前时代的最强音”(王朔《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消费文化的时代语境之下,生存还是毁灭之问深深困扰着渴望实现自我突破的作家们,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成熟,以余华、莫言、苏童等人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和影视界导演进行了深度跨界合作,并取得了轰动性的效果,他们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随着电影的不断上映而节节攀升。在与影视媒介联姻的过程中,先锋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型。
在先锋派没落之时,另一个文学流派“新写实主义”也悄然崛起。和先锋文学沉溺于诗意的表达与历史叙事相反,新写实主义文学立足于“社会真实”,从司空见惯的、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中汲取诗情,不讲究叙事的技巧,也不关注宏大的历史,呈现的是小人物的生活风貌。“新写实”的成功也让先锋写作的误区一目了然:除了题材的刺激和外在形式的构筑,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丧失了基本的深度性探索,而被历史风情所缠绕,表现出一种精神体验的缺乏与亏空。在“玩赏历史风情”的批评之下,以余华、苏童、莫言等人为代表的“反叛”作家收敛起对先锋语言、形式上的尝试,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向;而以格非、残雪等人为代表的“坚守”作家则试图找到虚幻与现实的平衡点,继续发扬着先锋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了两种创作走向。
二、融媒介的发展与现实转型
新世纪以来,随着多种媒介的高度融合,作家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由最终的文本交流延展到微博、抖音、电视、纪录片各个领域。读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与作家进行对话,而作家也必须直面靠近公众所带来的所有改变。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影响下的“快餐式阅读”极大地冲淡了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很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迭出的作家近些年甚至陷入了完全的沉寂。与之相反的是近年来网络作家热度的持续攀升,一大批以言情、穿越、玄幻、盗墓等内容为题材的网络小说迅速崛起,这使传统作家在新世纪的突围之路布满荆棘。这也提醒文学创作者,信息多面传播的时代语境下,作家不再是单纯地将自己关在文本的世界里寻求灵感,而不得不关注媒介融合之后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追求的改变。现在很多读者听到一部文学作品的名字,不是想着去图书馆借阅或者上网购买,而是熟练地打开抖音、微博、腾讯、爱奇艺等视听软件,进行影像化的欣赏。在网络并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接收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文本的输出。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影视创作,读者或观众的审美体验可以通过多重媒介迅速地反馈到创作者身边,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关注读者的评价甚至做出回应,这让作家会更加谨慎地对待下一步作品的输出。近日一上映就引发广泛讨论的电影《第一炉香》,就证明了全民自媒体时代,读者(观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对于作品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炉香》作为张爱玲的成名作,奠定了其以后写作的风格基础,也收获了当代大批读者,改编此篇,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电影随着各种媒介的宣传如期上映之后,许鞍华导演等来的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此起彼伏的吐槽与恶搞。多位行业大咖集结、奢华的制作班底、金马影后的加持,都没能挽救这部电影的滑铁卢之势。“带着极大的好感进去看,瀑布汗皱着眉头回家”,“技术到内容表达全部失衡,两个女性主创的叙事视角符合原著吗?”,“男主角中气十足,饱经风霜,仿佛心机深重的健身教练,何来柔弱之感?”,“以为改了个《花样年华》出来,结果是民国版《小时代》”……在大批网民的持续声讨和质疑之下,许鞍华接受了梁文道个人谈话节目的采访,表示自己当初并没有关注网络,如果获知大众对于电影主演的反应是如此激烈,在开拍阶段就会把担任主演的马思纯和彭于晏换掉,换更适合的人来出演。这段略显无奈的回应并未平息网民的冷嘲热讽,并直接影响电影后期的票房。这一事件从侧面证明了融媒体的时代语境下读者期待将对作品产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显著的、不容忽视的反作用,文学创作者如果不充分考察当下的时代语境而闭门造车,其产出的作品有可能会无人问津。
随着影视媒介对小说创作的深度介入,坚守派与转型派作家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坚持先锋本色的几位作家近些年鲜有作品问世,除了格非近几年发表了几部新作,但在评论界似乎并未激起太大浪花;寻求突破与转向的莫言、余华等人,逐步脱离了符号化的叙事传统,其创作风格也由最初的历史叙事转向现代主义叙事。他们有意识地改进了曾经为人所诟病的叙事的杂乱、语言的不加节制、人物的符号化,而用故乡、苦难、童年等要素作为立足现实的强大根基。余华转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莫言后期的《生死疲劳》《蛙》等作品所塑造出的人物、所讲的故事已经变得更加清晰和立体,有着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图像化阅读时代,先锋作家的转型其实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需要提高自身作品内在肌理的技术含量,同时也得关注小说叙事在接受美学上的外部时代背景,尽量兼顾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只有扩大自己的小说的阅读群,首先生存,尔后才能使自己的小说得到发展空间”(丁帆《在“变”与“不变”之间——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剖析“先锋派”的沉浮》)。
三、媒介互动时代:新“传奇”的再造
随着融媒介的高度发展,作家和读者的距离也被极大地拉近,曾经让读者觉得遥不可及的文学创作者,经常会出现在各类公众号和访谈节目上与观众进行深度的交流。莫言在获得诺奖以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城市,做了18次讲座,签了几万个名,和无数读者做了频繁的互动;余华作为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的特邀嘉宾,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创作趣事,一时间还上了微博热搜,“余华式乡土幽默”,“被余华笑死”,“余华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吧”,“余华上脱口秀能亮4个灯”等话题成为网友的快乐源泉,也让读者看到了书本外更真实的作家。
人人自媒体时代,作家已经无法再忽视读者对于作品的重要意义,莫言的新作就明显受到了读者期待的影响。莫言早期的文字大胆自由、意象丰富,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青睐,但也有读者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文字,更读不懂他的小说。许多人认为他的小说里充斥着暴力、血腥与恶心,看他的文字仿佛在挑战自己的阅读极限,即便在他获得诺奖之后,仍有许多慕名而来的读者被其过于外露、不加节制的表达所吓退。蛰伏许久的莫言似乎吸收了外部的批评与读者的质疑,2020年8月,《晚熟的人》小说集出版,这部被评论者称为“新笔记小说” 的新作,和以往的魔幻叙事与暴力书写截然不同,莫言用质朴而克制的语言,展示了其“返璞归真”的创作态度。在这12篇小说当中,曾经汪洋恣肆的表达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平和简练的语言和促膝交流般的叙述。正如王德威所说:“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摆脱这些特色,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王德威《晚期风格的开始 ——莫言〈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云端发布会上,面对读者担心看不懂新书的疑问,莫言说:“我向你保证,你可以看懂。如果我年轻三十岁,我的小说你可能读不懂。我现在写的小说,你肯定可以看懂。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追求现代派,各种各样的西方流行的那些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但是随着人的慢慢成熟,才意识到用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语言把故事讲好,才能够显示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成熟来。”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莫言的新作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是作家深度地介入小说当中,并且选择了多元叙述和多重叙事视角。在首篇《左镰》的开头,作者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引,“各位读者,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数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的又写了铁匠”,“看过我的散文《洗热水澡》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我对三十多年前县城澡堂的描写,一定还记得我们是如何能够忍耐热水的烫泡”,“以上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些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的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相比于以往作品的沉浸式叙事视角,莫言在新作中大量采用了插叙和补叙,并与读者达成亲密的互动,仿佛刻意为了强调写作者对于文字之外读者的关注。第二是离去—归来的叙事模式。在这部小说集中,出现了大量的怀旧书写,莫言分别以孩童视角和离开之后载誉归来的作家视角,讲述了几十年间故乡的变化和其中的奇闻趣事。“鲁迅、欧洲或者美洲的很多作家也都写过类似的,一个人原来在这个地方出生,在农村出生,然后到外地去,过了若干年之后重新回来,这样一个返乡视角的小说有很多很多,而且其中也不乏成为经典的作品。这部小说依然延续了这个视角”(莫言《晚熟的人》发布会)。第三是小说文体的随笔性质。这部新作文字精简,叙述平易近人,并伴随大量的分章。讲的是故乡的奇闻轶事,兼具真实性与虚构感。杨剑龙认为莫言“延续了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志人与志怪传统”,将其总结为新笔记小说(杨剑龙《创作的转型:莫言的新笔记体小说》)。莫言通过深度介入与颇具传奇色彩的叙述,完成了其创作的转型,有着续写当代小说“新传奇”的姿态,也给了读者足够的诚意。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次莫言的文字虽然与现实有了更近的距离,却失去了以往让人血脉偾张的张力,有些内容的戏剧化处理也让人觉得有些突然。
无独有偶,2021年4月,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的余华长篇小说《文城》出版,这是余华封笔八年后的又一力作。小说讲述了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善良敦厚的富家子弟林祥福被一个叫小美的女子骗婚,之后带着女儿林百家前往“文城”艰难寻妻、最终客死他乡的故事。全书分为《文城》和《文城补》两部分,并且采取了不同的感情线描述同一个故事,拼凑出一个谜底的背后。小说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和以往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余华也在进行着创作的突破。“鲜血”“苦难”与“厄运”曾经是余华作品的标签,这一次,他不再沉迷于用冷酷的笔触去展示苦难,转而侧重于运用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语言去歌颂善良的人性。丁帆称赞其为“如诗如歌的浪漫史诗,是一部充满着浪漫传奇性的长篇小说”(丁帆《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杨庆祥热烈赞颂:“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文城》的故事牢牢抓住了我,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杨庆祥《〈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与之前的作品相比,余华此次创作表现出以下的特征:第一是传奇叙事与浪漫化书写。小说通过顺叙与补叙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一波三折的艰难爱情、基于传统信义的深厚友情和对抗天灾人祸时的动人乡情。在这些颇具神秘与传奇色彩的叙事之中,作者穿插了大量充满浪漫色彩的浓重描写,“晚霞在明净的天空里燃烧般通红,岸上的田地里传来耕牛回家的哞哞叫声,炊烟正在袅袅升起”,“陈永良见到的不是一个从灾难里走来的人,在霞光里走來的是一个欢欣的父亲”,“雪冻的溪镇,每一天的黎明从灰白的天空里展开,每一天的黄昏又在灰白的天空里收缩”,浪漫的书写让小说的叙事节奏相对舒缓,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第二是出城—寻城—返城的叙事模式。和莫言的新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林祥福在寻找与返回的过程当中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让读者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本来衣食无忧的林祥福因为一次骗婚事件踏上了漫长的寻妻之旅,他怀抱幼小的女儿风餐露宿、历经坎坷,时刻向周围的人打听小美和阿强的下落。在小说的许多叙述中,林祥福甚至沾上了“祥林嫂”的影子,后者执着于对人死后究竟有无灵魂的追问,前者沉迷于对于“文城”究竟在哪里的探寻,两者极为相似的名字似乎也暗示了最终同样悲惨的结局。第三是重返“先锋”的语言尝试。在这部长篇巨制当中,一以贯之的是浪漫化的传奇书写,但在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先锋”的影子,尤其是对暴乱场面的描写,呈现出余华早期的狂欢化叙事特征。在描写土匪血洗齐家村时,“四溅的鲜血让空气里飘满血腥气息,后面的女人看见前面的女人被砍下肩膀、砍下胳膊、砍下脑袋,仍然视而不见地扑向自己的孩子”,“两百多人的鲜血在空中飞溅,溅满晒谷场四周的树叶,又从风中摇晃的树叶滴落下来”,类似的描写比比皆是,让人不寒而栗,而在描写凄然冻死的小美时,这种狂欢意味达到了极致:“她的脸垂落下来,几乎碰到厚厚积起的冰雪,热水浇过之后的残留之水已在她脸上结成薄冰,薄冰上有道道水流痕迹,于是小美的脸透明而破碎了。”小说面世以后,与褒扬相比,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也很多,有人认为《文城》的叙事过于混乱,读到最后也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认为有些描写过于戏剧化和荒诞化,人物的符号化也颇为明显;王鹏程更是犀利指出“其一味逞奇写奇,情节逆情悖理,细节漏洞百出,甚至违反常识,表现出创作严重的准备不足和知识结构的先天性缺陷”(王鹏程《奇外有奇更无奇——余华〈文城〉的叙事艺术及其问题》)。有学者将余华新作中的缺陷归结为不自觉的影视化写作所致,从20世纪90年代到当下,大多数先锋作家已经深度参与到影视剧本的创作与改编中,他们的文学写作也变得不再单纯。
无论外界的评价如何,两位先锋作家的转型之作让被称为“明日黄花”的先锋小说再次出现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先锋”这个曾经红极一时又迅速衰退的词语重新被学界反复提及。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图像文化成为审美主流,如今多种媒介的跨越式发展与传播,让当代作家的创作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和影视媒介紧密合作的情形之下,先锋作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图像化和戏剧化的倾向,这种特写式的表达是否有利于文本信息的传达,的确值得商榷。无论曾经的“先锋”如今以何种姿态呈现,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先锋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探索精神,就是不停的自我突破,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创新意识”(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语境下,如何再造振奋人心的“新传奇”,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到文学的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找到精神的栖息之处,是当代作家亟须思考的话题。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