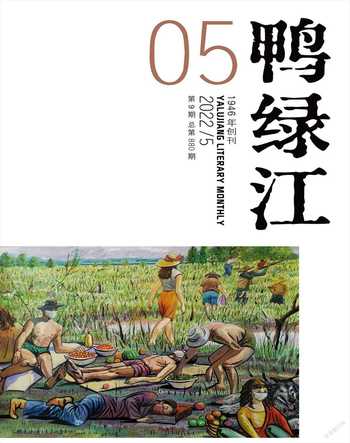一个故事的N种讲法(短篇)
年假来了,我作为公司最后走的一名员工,关上了电脑,拉下了所有的电闸,锁好了公司大门,在公司群拍了照片报备,然后赶往火车站,坐上最后一班回老家的火车。
坐在弥漫着烟酒气味和腐烂味道的绿皮火车里,我靠着窗户,数着向后奔跑的树,它们跑得并不快,从农村奔向城市,和我的方向正相反。经过了七八个小时,我抵达了离家乡最近的火车站,北方的太阳早就猫到了夜里,我搭乘朋友的老捷达奔向老家。
“半年不见了吧,福子。”何浩说,车里充斥着老捷达的异响。“福子”是我的小名,这个名字只属于我出生的村子,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我也属于这里。虽然我好久才回来一次。
“噢,上次是‘十一’回来的。”我应着说道,看着没有路灯长满杂草的小路,我有点慌张,明明熟悉每一棵树,却陌生得像个旅客。
“今晚你先回家吧,明天咱们再一起出去玩,明天好好喝点儿,哥儿几个都挺想你的。”何浩帮我搬着车上的行李,在凛冽的北风中顺手关上了后备箱,他帮我拎着两个口袋,向家门走去。
“送到这儿吧,明天早点儿来找我,今晚上我先回家陪陪我爸妈。”我告别了他,并期待着明天和他再次相聚,期待着明天中午和少年时期的几个發小把酒言欢,回忆那些又傻又可笑的往事,然后就着啤酒咕咚咕咚地灌下肚去,再一起打出一个嗝,看着彼此傻乐。
“妥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上午来找你。”说罢何浩关上车门,猛地踩一脚油门,脚力大到快要将他的捷达踩漏,一股浓烟窜出,他和他的野性座驾便消失在夜里。
与家人在年前团聚,是家庭的重要时刻,和母亲聊聊她这一年在乡村学校工作的日常,和父亲喝点他珍藏的泡了乱七八糟的我不认识的东西的白酒。炕烧得很热,我坐在炕头有点烫屁股。午夜将至,我们熄了灯,开始做梦。
天亮是三十儿。
冬天的北方天亮得很晚,我看看墙上挂着的陈年老钟,现在才刚过八点,急促的敲门声就响起来了。我父母早早出门去后街大姨家了,那么这个时候能来的就只有何浩了,但他来得也太早了些。
“耗子,你来得也太早了。”我睡眼惺忪,看着他在我家的门外焦急地扒着门往里看。我不紧不慢地打开门闩,这家伙却真的像个耗子似的一下子溜进来。他眼里有慌张、不安、局促,看了我一眼,又看向地上,又看向屋里,又看向我。
“没人,我爸妈去我大姨家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浑身发抖,像是出了很多汗,绝不可能是热的,因为这天气都能把人冻死,他出的是冷汗,他开始哆嗦了。
“我杀人了。”
我蒙了,他这句话我从没想过会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这句熟悉的话会出现在电视剧里、小说里、新闻里,但是不会出现在我身边的现实世界里,更不会出现在何浩的嘴里。但他真真切切地说出了这句话,对着我。
“你开什么玩笑?大过年的,说点正经的!”我心里已经有些不好的预感,因为有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他现在的状态如同我在城市中的那些演员朋友,我去看过他们演的戏,很真实但并不是生活,现在在我面前的何浩如果是演的,那么他配得上世界上任何表演奖项。
“等我锁一下门,你先进屋暖和暖和。”我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一瞬间我想到的是让他先冷静下来,把话说清楚。
“我没开院子门,我是从后边跳进来的。”他说话还是有些哆嗦,我把他扶进了屋里,然后摸着炕沿靠着墙边坐在炕头,他靠自己已经根本站不住了。
我走到挂在墙上的棉袄边上,翻了翻我的棉袄口袋,摸索出一盒芙蓉王,抽出两根,我先把一根烟叼在嘴里,再把另一根烟塞进他颤抖的嘴唇里。他差一点儿就把烟抖掉了。我拿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再给自己点上。我们俩坐在炕边,吞吐起来。
烟雾缭绕下,何浩缓和了一些。他来找我,我并不意外,从记事起我俩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俩一起偷过他妈妈钱包里的钱,一起摘过别人家的果子,一起逃过课,一起打过架。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因为没能考上,去附近的镇子上卖水泥,这几年也赚了点小钱。他说二十八岁之前一定要在镇里买上二层小楼,今年他二十七了。
“别着急,实在不行下午去自首,也判不了几年。”烟已经剩下一个屁股,我说出了这句话。
“操。”他这个字虽然简短,但是配合着眼里的泪水和哭腔,让我不能直视他的表情,就好像他心里的整片海洋装在杯子里,这个杯子被这一声震开了一个小口,然后整片海洋从小口泚出来。
“说说吧,和我,万一没啥事儿呢?”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让它在白色的瓷砖地面上划出一道黑线,像是把一块瓷砖劈成两半。
“万玲玲,我那个嫂子。”何浩颤抖的手拿着烟屁股,靠手的抖动就能将烟灰抖到地上。
“啥?你把玲姐给……”我有点惊讶,但还期待着他下边的陈述。
“不是,我从头给你讲。”我又给他点了根烟,他深吸一口,表面看起来冷静了下来,讲起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何浩去他家的大棚帮着摘菜。大棚,是东北农村种植蔬菜的地方,它一面是保温的土墙,一面是采光的塑料。无论冬夏,这里都是植物生长的天堂。在他家前边的大棚是他哥家的。他哥何勇今年三十出头,没念过什么书,在家靠着大棚种菜生活。何浩刚走到自家大棚门口,就听到前边的棚子里传来女人的叫声。那声音何浩熟悉,那是镇里的洗脚城二楼包房里才会传出来的声音。那是他嫂子万玲玲的声音。他凑近了一些,大早上就开始整这个,我哥可真牛啊,他想着。但一句话让他瞬间浑身发冷。“李冬,你别这样。”这句话清晰透明,穿透了薄薄的塑料大棚,穿透了冷冰冰的空气,穿透了何浩的身体。
何浩也没想太多,顺手抓过一块砖头,爬上大棚的墙头,破开薄薄的塑料膜跳将下来,仿佛神话之中的天神下凡,手持一块赤红宝砖,身着靛青夹袄,出现在两人面前。
对面的俩人都还穿着衣服,但是没穿裤子,万玲玲的手正扶着土墙,李冬的腰正顶在万玲玲的屁股上。俩人愣了,不对,是三个人都愣了。
何浩愤怒地骂了一句后就将手中的夺命法宝发射出去,直奔李冬的面门。僵直在原地的李冬根本来不及躲闪,红砖绽放出红光,红点喷射到各个方向。
李冬不再愣在原地,他直挺挺地倒下,向后。万玲玲直接哭了出来,一个女人,面对这种电光石火的变化,用哭来应对也情有可原。何浩呢?何浩慌了,他没想到眼前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他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他选择跑,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跑到一个让他信任的地方,跑到我这里来。
太阳渐渐出来了,但是转身又躲进乌云里,听说过年这两天有大雪,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下,这里的天气预报永远不准,所有人都只能随机应变。
说起来,李冬也是我们的同学。我想了半天,在脑海里刻画他的容貌。上次见他应该还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个混混头子,带领着学校里的一帮混小子干些混蛋的事情。他家承包着村上唯一一个鱼池,在经济上有点实力。他长得挺高的,还有点瘦,看起来挺狠的,实际上狠不狠我不知道,没什么交集。
窗外的雪花开始飘落下来,很大,像是从天上往下掉瓷碗。
“我出去看看。”我站起身,准备出去。
“你嘎哈去?”何浩依旧很紧张,我一动就破坏了原本安静和谐的环境。
“我去看看外边什么情况了。”我安慰着他。
“行,你去看看李冬死没死。”何浩开始说出一些理智的话语,让我感觉这个人已经恢复正常的状态了。
“他要是没死,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给他送到医院去,然后我去自首,或者怎么都行。”我看他已经有主意了,也就没多说话,只是问了一句,“要是他死了呢?”
“也先告诉我一声,然后报警,来抓我。”他淡淡地说道,好像已经看开了,看懂了一些事情。
“你就在这儿待着?”我问。
“对。”他说。
“要不要换个地方?”我又问。
“不,这炕上挺热,我暖和暖和,我不走。”
“把烟给我扔下。”他说。
我便也不再问下去,给他拿了几根烟,转身出去,推开门走入一片雪中。
这世界的变化来得太快,本来还约好了今天一起喝酒的人现在正因为自己可能杀了人而坐在我家的炕头,我感到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杀了李冬那么我算不算电视剧里的包庇罪犯,窝藏逃犯,直接给我扣上一个从犯的帽子。但他也说了,如果李冬死了,让我报警抓他,那这样来说我于法于德也都过得去,我心里一下就好受了起来,继续向雪的更白处走去。
小小的村庄本就不大,家家户户都离得很近,所有的大棚都在居住区的东北面。我走了大概五六百米,就看到了一片片整齐的大棚,躺在一片白色里,在白色的更深处有一团黑色,雪越下越大了,甚至看不清什么东西,前几天刚下的雪还没化,新的大雪又续上了。更靠近那团黑色,我发现那是一群人,团团围住的人,大概有二十到三十人,围成一个圈。在圈里躺着一个人,跪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我看得清楚,正是李冬,雪盖在他身上,省了白布,他死了。跪着的是他妈,站着的是他爸,他妈哭得震天动地,他爸哭得声嘶力竭。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都是熟悉的面孔,都是附近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娘在这儿议论着。我爸妈也在其中,看到我在人群里还拉了我一把。
“福子,你嘎哈来了?”我爸低声说道。
“我溜达到这儿了。”
“别上这儿溜达了,李冬死了,不知道谁整的,但是被砸死的,脸都砸烂了!别看了,睡不着觉,回家吧,回家!”
“好。”
“有人报警了,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一会儿警察来了就都散了。”我爸接着和我说道。
我爸把我推向人群的外围。但他还在黑色的旋涡中,随着人群议论着。
最近的派出所到这里也要一个小时,我应该还有些时间来和何浩说些事情。
我拿出了手机,想给他打电话,却突然感觉这里并不是能给他打电话的地方,于是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死了”。然后我点了支烟,在离人群几十米的地方,听着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伴随着那根芙蓉王慢慢化成烟灰落下。
我没想到这个世界的变化来得如此快,人在一瞬间变成尸体,要好的朋友在一瞬间变成罪犯,本来是欢天喜地的年节,在一瞬间变成了漫天飞雪的葬礼。真是无常。
警车在我附近停下,因为再往里就开不进去了。车门打开,从副驾驶下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听说她在镇里当警察,却没想到巧合又一次发生,她一下车就站在我的面前。
“好久不见了,林警官。”我尝试和她打趣,毕竟她是我的初恋,在学生年代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在上了不同的大学后我们才分道扬镳,她去了警校,我去学了计算机。
“一会儿再聊吧,王福,我先办案。”她冷冰冰的,像是嘴里也下着雪。
后边的车上也陆陆续续下来几个警察,毕竟命案是大案,整个派出所的民警估计都出动了,有十来个人,向黑色的人群旋涡走去。我一把拉住了林雪说:“我有线索。”
我本来不应该这么说的,说出这句话有点不妥,不说更不妥。或许是想和她搭话而突然言語不受自己控制,也或许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负责任,让我拉住了她,并说出了这句话,
“我有线索。”我又说了一遍。
“什么线索?”她转过头来,看向我,上次她这么看我应该已经是七八年前了,我们分手的那天。
“能上车说吗?我单独和你说。”我脑海中还在组织语言,渴望有点时间来缓和一下我脑海中的信息海啸。
“上车。”她拉开副驾驶的门,一把把我推了上去,手劲可真大。之后她从车头绕过去,到驾驶位上坐下,把车门关上。
我拿出一根烟,塞到嘴里,准备掏出打火机点燃它。
“这是警车,你注意点儿。”林雪斜了我一眼,我赶紧把烟又拿在手里,放回烟盒里也不是,夹在耳朵上也不是,这根烟和我都有点尴尬。
对讲机响起来,“现场发现被害人面部受到多次重击,凶器也找到了,是一块砖头。”
我愣了,这和何浩和我说的并不一致,他说他用砖头把李冬砸倒了之后跑了,但是现在对讲机里说的却是多次重击。
“不对。”我说。
“什么玩意儿不对,王福你是不是逗我玩呢?我没时间跟你在儿玩,我走了。”林雪说完就要开车门下车,又被我拉了回来。
“别走,事儿不对。”我说。
“人是何浩杀的,又不是何浩杀的。”我接着说。何浩让警察抓他,我觉得直接让警察把他按了也是对他好,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又有变化了。
我把何浩所说的一字一句都重复给了林雪,我完成了何浩对我的嘱托,让警察来抓他。但是我又违背了他的意愿,我现在想让警察查明白这件事再去抓他。
“何浩,万玲玲,先找到这两个人。”林雪冷静地说道。对讲机里还在传出嘀嘀的声音,我思维有点混乱,如果何浩把李冬打倒了没有杀他,但是李冬却因为连续受到重击而死,那一定是万玲玲杀了他。
是何浩在撒谎,还是什么其他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面前的大雪已经没过了脚踝,耳畔的哭声还萦绕着。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
我拨打了何浩的电话,没有人接,但是我相信他会在我家等我,等我带着警察回去抓他。何浩是个好人,也不对,他算不上好人,但并不是坏人。他至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值得信赖的朋友,我能确定这一点。
“他应该还在我家,几个人去就行,别吓着他。”我说完这句话,好像又有些不妥,在林雪面前,我经常做一些不妥的事情,这让我更不安了。
“一队,一队。”林雪拿着对讲机说话。
“一队收到,请讲。”
“一队来三个人到车里,剩下的人保护现场,疏散群众。”
“收到。”
“二队,二队。”林雪接着拿着对讲机说话。
“二队收到,请讲。”
“二队去找一个叫万玲玲的女性,三十岁上下。”
“收到。”
她拿着对讲机说话的样子和当年与我玩用纸杯加毛线做的土电话说情话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这副容貌下装的好像已经是另外一个灵魂,相同的蜡烛点燃两次就已经是不同的火焰。
一辆车上,五个人,没什么话,我只是将何浩和我讲的东西又大概重复了一遍,妈的,说了好几遍了,真烦。
到了我家,推开大门,何浩并不在屋里。我们五个人都不太惊讶,他在这种状态下做出什么决定、想到什么事情都并不奇怪,但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控制他,然后查明真相。
何浩去哪儿了?我想不出。
“走,去万玲玲家。”林雪说道。
“哦。”我应答着,和他们一行人往外走去。
“你还跟着干什么?你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了解了,回家待着吧。”林雪看着我说。
“不行,何浩是我兄弟,我得找他。”我有点和林雪较上劲了,以前我们也总是在一起较劲,像现在一样。
“别耽误我们办案,别的随你。”她扔下这么一句就钻上了车,关上车门,把我拒之门外。
“还跟以前一样。”我嘀咕着。
我掏出手机,又给何浩打了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也没有人挂断,我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却也有些失落。于是我给他发了条消息:“人可能不是你杀的,我听到说是多次重击致死。”还是没有回应,希望他能看到。
手机震动了两下,我拿起来一看,居然是何浩给我发回了消息:“带警察来后山,秘密基地。”
内容很短,秘密基地也很近,那是小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的秘密地点,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山洞,矮矮的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如今,我们都快三十岁了,这个秘密基地依然存在。
我跑出去,这么大的雪,警车开得也很慢,我几步就撵上了警车,跑得一身是汗。
“干吗?”林雪没开车门,摇下车窗对我说。
“开门,何浩他上后山了,这地方只有我能找到。”
“好,上来吧。”
我又爬上了警车,带着一车人向后山进发。
雪太大了,车有点走不动,我和林雪以及三名警员下车,在雪地里步行。刚才没脚踝的雪现在已经到了小腿深,有点儿见小了,从白瓷碗变成了白鹅毛。我们往山上去,我走在最前边,林雪和三名警员踩着我的脚印前行,五个人只有一排脚印。
“到了,那儿就是。”我指着半山腰的小小洞口,和身后的几人说道。洞口里还闪烁着微弱的火光,看来是何浩点了火,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在这个山洞里生火,烧东西,感觉烧点什么东西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后来我明白,那是无法创造就去毁灭的快乐,是我们年少的天性。
“耗子,我来了。”我远远地喊。
“你喊什么?别喊!”林雪用胳膊撞了我一下,生怕我把何浩吓跑了。
“没事儿,他让我带着警察来的。”我有点无奈。
探进洞去,其实洞很小,这些人根本站不下,更何况洞里本来就有两个人。
一个是何浩,一个是万玲玲。俩人围着一团火焰,也不作聲。
我有点蒙圈,身后的几个人倒是没犹豫,上去就把两个人给按住了。
“放了小浩吧,和他没关系。”万玲玲先张嘴了。
“都别扒拉我,我自己能走。”何浩推开了身边的警察,站了起来。
“行,那都和我回警察局吧。”林雪环视了一周,冷冷地说道。
对讲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队二队,收到请回答。”
“收到。”
“天气原因,所有路段都封闭了,今天无法离开平安堡子了。”
“收到。”
“那就不着急了,先在这里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林雪听完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也没什么变化,蹲坐在了火堆旁。
“都别紧张,事情已经发生了,大家都坦白了,对所有人都好。”林雪接着说。
我也蹲在一旁,用火堆里的火焰点烟。
“人是我杀的。”万玲玲低着的头又抬起来,对着我们說道,然后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李冬早就对万玲玲有意思,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身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万玲玲是何浩大哥何勇的媳妇,何勇为人踏实内敛,身体结实,一米八多的个子,一身干农活儿练出来的腱子肉,也不是好惹的茬子。于是李冬对万玲玲这个事儿一来二去也没什么下文,村子里的人也就没当回事儿。
但何勇最近这两年不光开始扣大棚,也研究上了蔬菜运输。开着他买来的二手三轮车,把自家大棚里的菜运到镇里的集市上去卖,收入上来了,但在家的时间更少了。何勇和万玲玲结婚快三年了,还没孩子,俩人的感情也出现了波动。李冬就乘虚而入,在何勇去镇上卖蔬菜时,进入万玲玲的生活。
今天早上,何浩发现了俩人的苟且之事,一砖头将李冬放倒。万玲玲怕事情败露,一时起意,痛下杀手,用那块砖头朝着李冬的面门狠砸下去,三五下之后,李冬彻底没了呼吸,整张脸都没了。她本想着李冬死了之后可以栽赃给何浩,但当她冷静下来之后还是决定自首,于是她给何浩打了电话,俩人约在了这里。
就是这样,万玲玲述说得很平静,也很真实,但我总感觉有点不自然。何浩在旁边不知何时也点起了一根烟,到目前为止,他没发表过什么意见。
俩人戴上了银色的铐子,有了点儿犯人的样子。
“你走吧,没你事儿了。”林雪看了我一眼。
“没我事儿了?”
“对,你还在这里干吗?”
“这么大的雪,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今天你们出不去了。”
“我们出不出去和你有关系吗?”
“和我没关系?”
“对,没关系。”
“我和你没关系?我和耗子也没关系?”
“何浩现在是嫌疑人,我们必须把他带走,咱俩就更没关系了。”
“行,我走。”
环视了一圈小小的山洞,大概五平方米的地方人挤人,警察同志把嫌疑人保护在中间,中间围了一团小小的火焰。
耗子看着我,没说什么。万玲玲也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林雪看了我一眼,像是在和我告别。
太平静了,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一个女人杀了一个她出轨的男人,现在还能平静地坐在火堆旁边烤火?她伸出一双白皙的双手,靠近火焰,右手的无名指上金色的戒指反射着火焰的光芒,我突然想起了刚刚聊起何勇被大雪隔离在了村庄之外。太不对劲了。
我走出山洞,往高处爬。这座小山是我和何浩小时候的乐园,我们曾经骑着自行车从小山包冲下去,摔得人仰马翻。我们也曾经藏匿一些小物件当作宝藏,幻想着自己是寻宝的勇士。如今这里变成了我把他交给警察的最后地点,我觉得有些恍惚。雪还在下,仍旧不小。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不能去耽误警察办案,也无法和何浩聊天,另外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听说出了这档子事儿都避之不及,我只能在这里漫无目的地走。这里是唯一一条出村的路,在山的另一面,积雪很少,所以相对要好走一些。在白茫茫的雪里,我看到了另一个身影,有些蹒跚,有些犹豫,好像在回头看什么。他好像看到了我,步伐加快。
我快速追上去,正常来说这条路不会有人的。这是属于孩子们玩耍的小路,前面快速在走的人明显是个成年人。我又加快了速度,前边的人开始奔跑,我也开始奔跑。虽然是山的背面,但是积雪仍旧很深,每一步都没到小腿,跑起来很累,两个人在如此深的雪地上奔跑着,带起两道雪浪。我逐渐缩短了和他的距离,在雪中我已经能够听到他的喘息声。更近了,我伸手就能触碰到他。他回过头来看我,竟然是何勇!他神色慌张,我更慌张,我之前感觉到的不对在这一刻全部应验,我奋力跳起,将他压在雪地上,压出一个人形。
他当即哭了出来。
我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哭声很大,像个孩子。他也三十多岁了,不再是孩子了。我从他身上起来,扑了扑身上的雪。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玩这种游戏,在雪地里撒欢儿、摔跤、打雪仗。更狠的就是拉开伙伴的衣领,把雪团扔进对方衣领里。最高礼仪则是把人放倒之后,大家围成一个圈,用雪将他掩埋。
过了十几分钟,或是几十分钟,他渐渐平息下来。我给他点了根烟,又怕他呛着了。声音断断续续,他开始对我诉说,对我忏悔,对我祈祷。我像个神父,像个佛陀,像个警察,但我都不是,我不清楚现在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在雪地里和他抽烟的人,他弟弟的朋友。
于是我听到了第三个故事。
何勇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很爱他。虽然没有一儿半女,但是两个人依旧非常相爱。去年开始,何勇不仅扣大棚种蔬菜,而且开着三轮车去镇上的市场卖菜,家里的收入翻了一番,俩人开始研究着去市里的大医院做试管婴儿。这个时候另一位主人公出场了。李冬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觊觎万玲玲的美色,很多年了,虽然差了好几岁,但是李冬经常说他是真心爱着万玲玲的,路上遇到了要说几句荤话,没事闲聊时也要扯上几句。他还经常在背地里说何勇不行,何勇忍了,但他又骗了何家的钱。李冬的父亲说要把养鱼池转给何勇,三万块。这是何勇和万玲玲想要下一代的钱,不过养鱼池收入可观,何勇和万玲玲研究了一宿,决定承包养鱼池。但是钱出去了,池子没包回来。老李家耍起了无赖,何勇一气之下,决定绑架李冬要钱。
他和万玲玲商量好,由万玲玲把李冬引到自家大棚里,埋伏的何勇跳出来,将李冬劫持。这是他们本来的计划。
谁也没想到,何浩神兵天将,一板砖将李冬掀翻在地。何勇傻了,直到何浩跑远,才出来和万玲玲面面相觑。此时李冬却醒了,指着何勇威胁说:“我要你全家死,我马上回去告诉我爸。”何勇慌了手脚,拿起那块砖头朝着李冬面门砸下去,一下,两下,三下。他心中的愤恨、不满、不安、痛苦、烦躁全集中到这一块砖头上。他把李冬的脸都砸烂了。
万玲玲已经哭成了泪人,何勇却异常冷静。他让万玲玲先联系何浩,让他别紧张,然后让她去自首,就说她是被强奸合理反抗,不会重判。
但何勇说他后悔了,因为何勇说他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很愛他。
所以我听到了这个故事。
我在想如果何浩没去找我的话,或许这件事还真就这么过去了。
天已经见黑了,冬天的北方黑得早。何勇和我一起返回了村子,他要去自首。
我给林雪打了个电话。
“你在哪儿呢?”
“审犯人呢。”
“我问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审犯人呢!”
“别他妈审了,犯人换了!”
“你跟我说话别总带脏字行吗?”
“行,你在哪儿呢?”
“村委会。”
“我带何勇过来找你,他要自首。”
“嗯,我这边也了解了。”
看来林雪审问也不是白审的,好像一切都明白了,我却依旧云里雾里。
雪已经停了,天也彻底黑了。走了十几分钟,我们到了村委会。这是一排小平房,屋里点着炉子,还算暖和。村里的几个干部也在。何勇走进了里边的小屋,我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找了个椅子坐下。我应该回家吗?还是在这里继续待着?我也不知道。
窗外有礼花炸裂,崩得漫天开花,过年了。
电话响起,是我妈叫我去二大爷家吃饺子,今年一起在二大爷家过年。
“妈,我今年就不去了吧。”
“嗯,也行。”
我今年不沾喜气,我这么一说,家里人也都懂。
“妈,今晚家里是不是没人啊,你和我爸都在我二大爷家吧?”
“对,晚上不回去了。”
“好,我知道了。”
“你小心点啊,儿子。”
“啊,我没事儿,也没我啥事儿。”
挂断了电话,我刚叼起一根烟,林雪就从小屋走了出来,把我的烟抢走了,塞到了自己的嘴里。我便又抽出一根烟,拿起打火机点着,林雪也将头凑了过来,我们俩在一团火下点燃两根烟,然后坐在村委会的长凳上。
“你怎么还不走?”林雪问我。
“抽完这根烟就走了。”我说。
“根据几个嫌疑人的证词,事情有些变化,我想了想,还是要告诉你。”林雪吐出雾气,她并不熟练,也不生疏,看来她确实经历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有所改变。
“还能有什么变化?难道李冬是自杀的?自己把自己的脸捶烂了?”我实在想不出事情还有什么变化。
“万玲玲和李冬确实是有事儿。”林雪低下头接着说。
“啊?”我一下陷入了恍惚,反应了一会儿,才听到林雪把整个故事讲给我。我已经记不清这是今天听的第几个故事了,我真渴望它是最后一个。
万玲玲和李冬,确实是有事儿。俩人在大棚里正折腾得热火朝天,何浩路过给了李冬一板砖,把李冬拍晕了,何浩就跑了。万玲玲也慌了,这个时候她给何勇打了电话。按理说她怎么也不应该给何勇打电话,但是她确确实实第一时间打给了何勇。何勇很快赶回来,还是用那块砖,把李冬杀了。后来的事,和何勇说的差不多,但其实那些事儿他早都知道。
林雪的故事讲得精简而准确。
“但我感觉……”林雪讲完之后看向我。
“你感觉什么?”
“我感觉啥地方有点不对。”
“哪里不对?”我实在不想再去思考这漫长一天里的任何一秒。
“万玲玲和何勇爱得挺深的,你说是不是?”林雪扭着头看我,雪花映着炸裂的烟花,透过村委会的窗户让她的脸呈现出迷幻而绚丽的色彩。
“那肯定的啊,我今天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这件事。”对此,我真的无比坚定。
“那你说,爱得那么深的人,会背叛吗?”林雪的烟灰挂在烟上,摇摇欲坠,仿佛弹一下就会变成雪落下。
“我觉得不会,相爱的人只会为彼此承担。”
“比如呢?”她问我。
“命?”我反问她。
“对了,何浩和何勇关系怎么样?”她终于抽完了一支烟,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
“很好,特别好。”我已经心不在焉。
“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两个人各自的表述里对彼此都不太友好。”
“你还能比我了解何浩?”我们两人对视着陷入了沉默,我头脑炸裂,无数的狂风裹挟着雪暴冲击着我的毛孔,我快要窒息。
“如果何浩骗了你呢?”她问。
如果何浩骗了我呢?我想。
我脑海中有了我自己的故事。何浩和万玲玲有事儿,俩人在大棚内热火朝天的时候,李冬不巧经过,俩人怕事情败露便用砖头砸死了李冬。何浩慌乱之中来找了我,和我说的那些话故意留下错误的线索让我为他开脱,即使最后发现是何浩杀了人,也不会怀疑他和万玲玲有那种事儿。
万玲玲本想说李冬强奸她,她在拼死反抗之下正当防卫杀了李冬。但没想到何浩直接跑到我家来和我说了那些话,俩人只能再次约到后山的山洞里,商量了那样的说辞,这样何浩和万玲玲的罪就都没那么大。
那么何勇呢?何勇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扛在自己身上?或许是那些事儿比罪、比命更重。为了那些事儿,他能不要命。
我想透过那小屋的玻璃看看三个人的眼睛,我想知道这故事到底有没有结局,这无底的洞到底能不能到底。
窗外烟花炸起,绚烂的烟火啃噬着无边的黑色,宣告着时间的结束与开始。
我和林雪坐在长凳上,烟雾弥漫,周遭是永恒的变化和相对的规律。
【责任编辑】安 勇
作者简介:
王冠楠,1994年出生于鞍山市台安县,毕业于沈阳大学中文系,从事过新闻编辑、文案、演艺等行业。有小说、诗歌、散文发表于《鸭绿江》等刊物。出版小说合集《盛京四俊》。现供职于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事宣传教育及编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