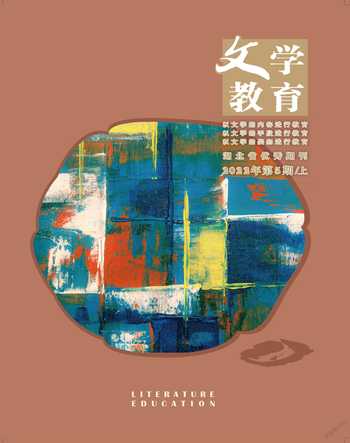萧红《生死场》中“场”的意义
谭爱平
内容摘要: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解读萧红的《生死场》,更接近作品的本来面目。《生死场》超越了阶级斗争视角,它指向女性本体。女性身体之“场”,女性承受来自父权制的重压而导致身体毁形或毁灭;国家民族之“场”实质是男性主导、女性缺失的空间。
关键词:萧红 《生死场》 “场” 女性
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一个主色调。同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奴隶社”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的。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比如,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胡风作后记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①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②
民族兴亡造成了男性批评家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而且,这种批评传统限制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以至今天人们仍很难绕开它去评价萧红的创作。我在此对萧红作品的解读试图为研究这位作家提出新的角度——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我这样做时强调的不是所谓女性自我或女性写作的发现与肯定,也不是对男人压迫女人的声讨(这常常是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反复纠缠的话题,它严重妨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而是为了揭示《生死场》中复杂的“意义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作者的复杂情感。
一.女性身体之“场”
就表现东北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来说,萧红的《生死场》同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八月的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稍作分析,就不难看出,两篇作品并无同工之妙亦无异曲之实。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重在描绘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
1.生育。自然生命的开端是从生育开始的,而生育是属于女性的特殊经验。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德波·伏娃认为,虽然男女两性都承载着繁衍着物种的责任,但男性在完成生育职责时,其个体性是得到保持的,而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却经历着个体性与异已性的斗争。新的生命孕育时,女性既是她自己,又不是她自己,她的个体性在成为母亲后逐渐消融,所以女性爱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被外力异化的过程。男子对生育抱以蔑视、冷漠的态度。男性歧视女性生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胎儿产生于精子与经血的结合,男性本原贡献了力量、活动、运动和生命,而女人只是提供了被动的物质。希波克拉底也坚持类似成见。③——西蒙娜·德·波伏娃这种关于生育的女性主義经典描述无疑在《生死场》中得到了很好验证。萧红对女性生育场面的描写简直是触目惊心,令从不忍卒读:
五姑姑的姐姐被迫赤身像一条鱼似的爬在没有草的土坑上生产——因为不能犯了“压柴,压柴,不能发财”的忌讳;她哀号了一整夜,“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到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准备葬衣……”她一边忍受着生产的折磨,一边还忍受着丈夫的打骂,“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
生育是妇人们逃不掉的刑罚,而萧红对生育的残忍逼近几乎是一种动物性还原。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萧红频繁地将人的生育与动物交配繁衍并在一起:
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里撞出来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通过对墙外墙内动物生产与女性生育的对比,造成一种人与物类的效果,从而提示了农村女已与动物一样沦为物种繁衍工具的事实:她被迫接受连续不断的生产,其个体的尊严与欲求被封建夫权践踏得体无完肤。有意味的是,为《生死场》创作封面,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触目的红色,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萧红正是通过对女性生育痛苦及生育痛苦的动物性还原来完成对女性幸福而崇高的生育神话的解构!
2.死亡。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着死亡……有杀婴,有绝症,有战争以及瘟疫。萧红对王婆自杀事件的描述将笔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生理外观及其所带来的身体残损上。她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她可怕的嚎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等身体情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在这里,唯一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美丽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她丈夫的折磨。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她们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膊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她亲眼从镜子中目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3.性。性本是人类最自然、最美好的景象之一,被称为“人本心理学精神之父”的马斯洛在描述著名的“高峰体验”理论时将倾听伟大的音乐、体育竞技上的卓越成绩、美妙的舞蹈和一次完美的性交相提并论,称之为真正卓越、极度幸福的人生经验,一种伴随着“高峰体验”的人类活动。④五四“人的文学”的潮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的“性意识”的复苏、苦闷及其发泄,由此形成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
《生死场》的着力点不在两性间的“和谐”与“高峰体验”上,而在于通过乡村妇女的性经历(这份经历总是与怀孕有关)来体现女性之身躯任人摆布的无望。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这种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咱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种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了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得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是,两个蝴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玉米田上的稻草人。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义却十分暖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一通过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的。在这里,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一种身体的畸变(邪异),将她腹中的非法胎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类社会中面对的走投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
女性的身体在《生死场》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与“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生”,在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引起的形象是肢体迸裂,血肉模糊的母体;“死”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让人看到肉体的触目惊心的变质和毁形,而绝无灵魂的超拔。萧红在这里苦心经营了一个女人的叙事,它向读者展示女人是怎么活的;她与周围的世界怎样发生联系;为什么身体的经验对于女人又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反过来,萧红也向男权——父权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批评不仅针对男权——父权的等级制度对女人的压迫,而且还暴露了萧红的写作同男性写作的根本冲突。对于萧红来说,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
二.国家民族之“场”
如果说〈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蕴,那么在小说的后七章(全书共十七章)中,萧红笔锋一转,从女性世界伸向宏大的民族国家世界。在女性之“场”中萧红是抗拒父权制的,但是在民族国家之“场”,民族国家话语在萧红的理解中并不等于父权制(当然有交叉的万分)。
在《生死场》中,不论是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都是悲哀的。国家的劫难,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遇到的种种苦难,却激发了男性农人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得以克服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去向他们的女人传播新的福音。比如,王婆的丈夫老赵三,就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说教有着极高的热情,并热衷于向寡妇宣传:“那夜老赵三回来得很晚,那是因为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把儿子从梦中唤醒,他告诉他得意的宣传工作:东村那个寡妇怎样把孩子送回娘家预备去义勇军。小伙子们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你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势,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在老赵三心目中,他的宣传工作提高了他自身的价值。李青山的演讲明确地传达出国家民族话语的性别含义:“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是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响应的呼声却先从寡妇群里传出:“是啊!千刀万剐也愿意!”寡妇们自觉的加入了“弟兄们”的行列。
如果说,在《生死场》中男人们固然是奴隶,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穷苦的男性农人藉助“国家民族主义”掩盖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在新的权力话语中仍努力将自己置于主体位置。
如果说在《生死场》中男人固然是奴隶,那么女人则是男人的奴隶。文中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惧怕丈夫(王婆是唯一的例外)、诅咒丈夫。十七岁的爱的“憧憬的追求”被成业的诱惑破灭了,成业在金枝病着的时候仍被本能不停的要求着:“管他妈的,活该愿不愿意,反正是干啦!”成业在成天劳累的金枝怀着孕的时候仍然只管自己欲望的发泄,做了寡妇的金枝在城里谋生时惨遭强暴。成业是所有男性的代表,男性之于女性的“爱”更多的只是一种欲望和占有,这些在他婶婶那儿间接得到了证明:“年青人什么也不可靠,你叔叔也唱这曲子哩!这时他再也不想从前了!那和死过的树一样不能再活。”出嫁不到四个月的金枝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在萧红笔下,从“爱的憧憬”到“恨中国人”。那么,在男性心目中“神圣”的民族观念又是怎样的呢?文中反复这样说道:
“爱国军”从三家子经过,张着黄色旗,旗上有红字‘爱国军’。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么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
在小说中,作为寡妇的女人只可能有两个下场:或是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加入到“弟兄们”的行列,却无法分享那些男人所占有的自尊与地位;或是像金枝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男性和女性之间,成为“中国人”的过程是十分不同的。二里半与金枝的比较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里半是个破脚,因此可以说他的男性特征被象征性的阉割了;不仅如此,他同动物之间那种不寻常的依附关系也使他的身份更接近女性。正是这种“女性”特征妨碍二里半像别的男人一样爽快地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当村民说服他交出羊作为献祭仪式上笨牺牲时,他却设法找到了一只公鸡去代替,从刀下救出了老山羊:
只有他没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甚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别人的眼睛,尤其是老赵三的眼睛在骂他:“你这个老破脚的东西,你,你不想活吗?”
二里半最后還是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男性”——小说结束在二里半寻找革命军的情节上——但那是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世之后。父权——男权体系是以财产来衡量确立男子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而妻子儿女正是男人的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日本侵略者奔赴他们时,二里半才起来反抗。从一个“自私”的农民转变为一个爱国者。与之相比较,作为女人的金枝与二里半的结局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后去城里作缝衣妇又被强奸,这一经验使她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深切的认识。因此,当王婆斥责日本兵切开国孕妇的肚子,残杀女人和婴儿的暴行时,金枝的反应是: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在此,金枝虽然也恨日本人,但金枝却没有像二里半那样成为民族国家主体的承载者。在金枝那里,丈夫和强奸者给她带来的身体经验都是痛苦,男性和日本侵略者都是她苦难的制造者。
萧红漂泊一生,一直都在追求独立,却又一次次失望于抗争中。在临终时她说:“我一生的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生死场》里,她对女性的悲惨命运充满了无限同情、悲哀和愤怒。在萧红看来,女性身体之“场”承受着命运之重,国家民族之“场”又忽视了女性的独立个体位置。萧红在《生死场》中对“场”的意义的思考,实质是对女性生命和命运的思考。由此,她对女性的关注从外部世界回归到女性本体,从女性历史的空白中现出,开掘了被男性文化遮蔽并且被女性自己忽略了的女性自身的体验与文化部分,在重新认识女性生命的过程中,做出了深刻的探索。
参考文献
①②《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③[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第29—30、10页,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④[美]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中译本)第17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武汉生物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