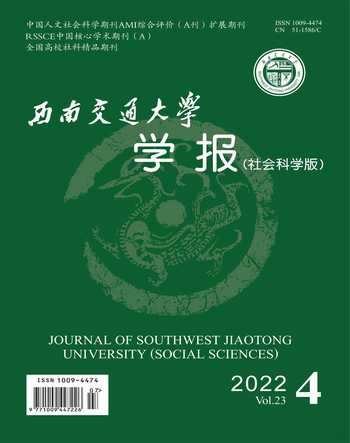中国法史学的发展路径:基于三个问题的思考
摘要:在我国现行学科体系下,欲回答“法史何为”的追问就有必要坚持法史学的“法学化”取向,即法律史研究需要借鉴历史学研究方法,但其学科属性归于法学而非历史学,否则不利于有效解释将“法律史”放在“法学”学科下的设置意义。为发展繁荣法史学研究事业,将法史学“方法化”是一个可操作的路径。统合“向外”与“向内”及“历史”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法史学的方法论价值所在。有效回答“何为法史”、“为何法史”以及“法史何为”三个子问题(简称“法史三问”),对于促进法律史学研究的转型以及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法律史;学科体系;历史学;学科融合;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历史法学;比较法学
收稿日期:2021-10-15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法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政法制度的形成与运行研究”(61040061910007);教育部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18JJD820005)
作者简介:孙康,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法律史和法理学研究。E-mail:Scorpio@126.com。
法律和历史是每个民族都拥有的基础要素,是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法学研究主要面向现在,但同时也面向过去与未来;既重视实践,也不能忽略理论。历史研究可以拓宽人的心智,把历史学的某些知识或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之中,可以扩大法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法史学(或“法律史学”“法律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在法史学研究领域,“知识”和“方法”是惯常的两种取向,但人们往往更关注知识性的研究,方法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关注。
在现行学科体系下,法史学被定位为法学而不是历史学专业的子学科其学科代码是法学一级学科0301下的二级学科030102,排名第2位。,这不仅仅是出于使法史学保留在法学院(法律系)的考量,更是由法史学科自身的设立初衷决定的。法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法现象产生、发展、变迁、演化的内生理路,把法史学放在法学院更能凸显其学科价值。然而,由于法史学所需人文积淀更多、研究产出较慢、社会科学属性相对较弱、和现实结合不够紧密、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场合较少等原因,其在法学院中长期遭受低估乃至忽视,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法学院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解决法律史在法学院身份尴尬的窘况,需要从“何为法史”、“为何法史”以及“法史何为”等三个具体方面进行探讨。笔者关注到已经有部分学者把法史学作为一种方法(as a method)予以探讨此类型主题论文,如朱振:《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74-90页;陈煜:《论作为法律科学的中国法律史》,载张中秋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5页;王志强:《我们为什么研习法律史?——从法学视角的探讨》,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6期,第30-44页;王志强:《类型化分析与中国法律史学》,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2018)第17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4页。。例如有人提出“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这个论题包含了中国法律传统切入当下法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问题〔1〕。这种认识论转向,对于法史学在法学研究、学科体系及法学院中的应有位置所具有的价值,值得注意和探讨。
一、何为法史?
(一)法史学科的定义
法史学是把历史作为知识或方法应用于法学研究当中的一门学问,它结合了“法律”和“历史”两大要素。广义的法史研究,主要包括国内法史研究、国际法史研究以及比较法史研究。在我国,按照国别可以划分为中国法律史和外国法律史,按照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制度史,此外比较法学(比较法律史)也持续存在。法史学被赋予自身的学科任务:从应然层面,它具有鲜明的法学问题意识导向,其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属性本质上不是历史学;从实然层面,历史学界也有部分学人从事法律史方向的研究,往往被置于专门史的门类下。不过,历史学者往往不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即法学视角)对法史学进行研究,而多以还原历史真实为旨归,以考证为常用办法,用功于法律史之历史事实的澄清。
法史学的研究可用以理解法律制度的产生及发展变迁,乃至于掌握法律概念的起源,更深入理解法律概念及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尤其是法律制度背后的社会历史。没有法史学的智识支持,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用历史方法研究法学有着悠久历史。法律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波伦亚(Bologna)注释法学派,其后评注法学派、优雅法学(人文主义法学)等也都大量运用历史方法。故埃利希(1862—1922)指出17至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大学者们都可以被恰當地称为历史法学家〔2〕。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是最主要的使命必然在于表明法条和法律制度是从整体的民族生活、从整个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中成长而来的。”〔3〕就历史法学派称“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这一观点,也有批评者认为它们不过是历史的权力斗争与观念斗争的产物例如,萨维尼(1779—1861)就曾指出:“非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在任何时刻是经由具有立法权的人运用意志而产生的,完全独立于先前时代的法,仅仅依据最好的信念,例如目前形成的信念。”参见[德]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1814—1840年)》,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但无论怎样,法的形成总是跟历史有关。法史学设立和兴起的初衷,就是从历史中发现法律难题的症结,从过往中寻找回答现实的理由。
在现代中国,法史学研究产生在20世纪上半叶,在20世纪50年代曾处在一个稳定发展期,当时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受前苏联的影响,附丽于传统历史学的框架之下,并与政治研究有着紧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科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事业恢复之初,法史学研究硕果累累,为中国法学的复兴做出了显著贡献。然而什么是“法学研究”,在时人的头脑中并非清晰显见。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教授戴逸提出“法学是幼稚的”的观点,即在特定的历史原因下中国法学基本上处于“幼稚”的状态。当时中国法学界为了摆脱“幼稚病”的帽子,一度取径于历史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资源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随着法学学科的分化与完备,法史研究的先导性地位也在逐渐衰落,对时代需求(如市场经济)的回应减弱。法史研究的精细化,促使法史学逐渐向更加精细却趋于冷僻的考据学靠拢,虽固有其学术价值,但在回应时代需求、引领理论创新方面难以继续肩负重任。
(二)法史学科的窘境
法史学科在实然层面确实存在某些操作窘境,全球法律史研究的式微已成“新常态”,这部分是由法史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的,该属性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但与之相对的是它往往缺乏现实关注——它较少关注现实,现实也难关注它。现实关注的阙如,是当今史学学科整体面临的窘境之一。法史学面临这样的不利局面,笔者认为大致有五个原因。
第一,历史学与法学在属性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司法实践当中,历史论据也往往遭到忽视。人们追求的是最新,也就是与时俱进的事理和法理。不过,与之矛盾的是,法律本身的特点就是滞后性,几乎不存在所谓的超前立法,且法律当订立之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法律是在时时滞后又时时回顾的过程当中发展自己的。其实从实然角度看,历史学与法学都是“向后看”的,但法学更追求与时俱进的因素,一部历史上曾经存在、现已废止的法律不太能引起使用法律者的兴趣。正如莱塞尔所言:“尽管法律史努力为其论点提供数量、经验上的证明,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缺陷,即其解释可能具有很大的推测性,更可能具有时限性。”〔4〕
第二,难以有效地从规范性角度研究法史学,或者法律史研究的规范性较弱,普遍未能旗帜鲜明地融入规范研究的阵营。部分法史学研究论文只是在文末强调研究对象对于现实法学的“借鉴价值”,但是论证相对仓促、肤浅、苍白,存在以史代论、有史无论等现象。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本质抓取不够精准,没有讲明其中的法文化价值;二则是惯常见到的对于法律规范性的忽视,且缺乏体系性的研究。古代的法律与现代相比,尽管它的立法理念未必成熟、立法体系未必周延,但也存在一定的规范性。法律在历朝历代都是规范性最强的文本,这一点和文学作品有着本质区别。如何把握历史上法律的规范性,实际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研究者不仅应该研究当时的法律文本,更要结合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等各种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判。
第三,法史学的学术定位不清。法史学存在人为划分界限的情况,依靠的是简单的二分法。目前,外国法律史研究走“比较法学”的路径,主要强调“有选择的移植”。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资源十分宏大,主要强调“有批判的继承”。二者的研究也存在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的问题。但是如果破除人为界限、将法史学整体作为一种方法,法史学将在学科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有利于促使自身的功用从隐性迈向显性。
第四,法史学研究本身艰深复杂。首先是研究素材浩若烟海,如官方法律典籍、笔记野史、案牍判词、契约文书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其次是法史学研究对于研究者的基本功要求较高,至少需要兼具法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功底,使得研究难度较大、耗时长、产出少。最后是法史研究各主题较为零散,碎片化程度高,研究者“各自为政”,不易形成稳定协作的研究群体。
第五,科研量化指标对法史学知识产品的片面忽视乃至拒斥。科研量化指标对法史学知识产品的接受度不高,这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大环境所决定的,从长远看目光是短浅的。对于法学学科来讲,法理学(法哲学)和法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比较法学等)是它的基础。基础学科最易于为人们所察觉的特点就是“无用”。“它没法给我们带来‘即刻的益处,也没法给我们提供‘即刻的指南。它只是以潜在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且持续的影响。”〔5〕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学主流期刊(所谓“CLSCI”)对法史学的采稿量较少,与其他学科的发文量对比,法律史学的发文量相对较低,仅高于知识产权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社会法学〔6〕。与相对丰富的中国法律史资源相比,这种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发表的情况,确实不太相称。在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法律古籍的校勘、辑佚等基本学术工程,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但是,现行科研评价体制对于非学术论文类的学术成果的认识层次还有待提升。放眼国际,知名的法律史学国际期刊,如美国的Law & History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欧洲的Journal of Legal History(英国)、Comparative Legal History(英国)、Legal History Review(荷兰)、Legal History Library(荷兰)等,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蔚然成风的研究。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法史学界的核心期刊甚至普通期刊都稍少当然,在中国法学界,按照二级学科办刊目前本来也不多见,但学科办刊的细化应该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趋势。。中国台湾地区由中国法制史学会主办的《法制史研究》杂志自2000年创刊至今,已出版37期,是华语世界权威的法史学刊物。在近期的中国大陆地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西法律传统》成为有正式刊号的连续出版物,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科点主办的《法律史评论》也首次成为CSSCI来源集刊,这些或许都是有利于中国法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为研究提供发表平台将吸引更多学人从事法史学的研究。
此外,关于是否让法史学“回归”历史学科,本身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类似地,有历史学者提出让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传统党史学界所谓政治性、党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只能说党史和普通史学有一定的区别,但均不能作为划分学科属性的基础。”〔7〕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学科可能比人文学科更加容易回应时代需求,相较于传统历史学而言,法史学可能会有更明确的问题导向,為现实起到参谋和擘画的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发展机遇。把法史学留在法学院,对于弘扬法史学的研究初心与本旨具有鲜明意义。此时明晰法史学在法学院中的地位才是当务之急。当然,法学院应当打破“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这一狭隘观念。参照过往与现实,把法史学留在法学院而不是“回归”历史学,也不会影响历史学者的研究热情。发展法史学关键在于加强科际整合与交流,毕竟学术发展的未来是交叉融合。让法学院的法史学与历史学系的法律专门史的研究成果充分交流融合,有利于互相弥补短板,促进法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所以不妨以前者为“本土”后者为“飞地”,将法史学塑造成为学科交叉的“典范”。此时,挖掘历史学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成为沟通“本土”与“飞地”的有效路径。
二、为何法史?
“为何法史”旨在讨论的是法史学科的研究意义,不免从一种功利性的角度思考。法学学科形成时间较历史学科要稍晚,历史学对法学的教益较多。在西方法学史上,有不少经典著作既是法学名著,也是历史学名著。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英国梅因(1822—1888)的《古代法》等,既是饮誉世界的法学经典,其本身也是法史著作,里面很多内容来自于法律史的视角。也可认为,正是这些著作中的法史因素才让其变得更为深邃厚重,从而更易藏之名山、传于后世。笔者认为,法史学研究可以担当重任,主要有两个原因:在知识经验层面,法史学可以实现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的统一;在方法经验层面,法史学可以实现史学方法与法学方法的融贯。
(一)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的统一
社会记忆的制度创造了“无时间性”,即人们习惯认定之“传统”,往往和“经典”相对应。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1910—1995)认为:“传统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通过人类的行动、思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代代相传。从逻辑上讲,被传下来并不意味着它是任何规范性的、强制性的主张。来自过去的事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明确的期望,即它应该被接受、欣赏、重新行动或以其他方式被吸收。流传下来的传统包括实物、对各种事物的信仰、人物和事件的形象、实践和制度。”〔8〕所谓传统,是对今天依然发生影响的文化,即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津梁。如果说一种事物已然形成了一种“传统”,那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固定下来,并将发挥持续而稳定的作用。可以说,传统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结晶,它是“永不过时”的。没有法史学角度的切入研究,法律思想的意蕴和法律制度的内涵将难以挖掘,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以说,这是法史学者难以为他人替代的优长所在,亦是重任所系。
法律史、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提供智识贡献。法律天然具有历史性,法史学和传统历史学有共性追求。这就要求法史学不能仅仅定位于研究过去的法律史,也要着眼于未来,研究法律的“演化史”。法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法律与法学,属于传统的范畴。传统是联结过去与现实的桥梁,我们今天的法律思想与制度并非凭空创造,它一定难以逸脱某些传统框架的影响。例如,近年来《监察法》《民法典》等重要法律的论证和制订,就离不开对历史依托的追寻。即使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部门法研究者也不会否认,法史学因素的引入将会使他们的研究显得更为厚重,进而更有说服力。
(二)史学方法与法学方法的融贯
与历史知识相比,历史学的方法论价值对于包含法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甚至也包含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具有强烈的实用价值。使用史学方法,既是对学术史进行梳理,也是对研究对象整体发展过程的回顾,更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和把握,可谓“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指出:“方法决定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所能运用材料的范围。”〔9〕方法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单纯地为达致学术目标而服务。史学方法与法学方法存在着某种暗合之处。法律的现代化系于法学方法的认识、接受与应用〔10〕。方法意指通往某一目标的路径。在科学上,方法是指这样一种路径,它以理性的,因而也是可检验和可控制的方式导向某一理论上或实践上的认识,或导向对已有认识之界限的认识〔11〕。法学方法主要包括法学内部的研究方法,如法律解释、补充、适用、校正等。笔者提倡的是把史学(在法学领域则是法史学)作为认识和研究法学的外部视角。人们通常称法学为“法律科学”(legal science),其实史学也有属于自己的科学性,因为在二者之中知识都是推论的或推理的〔12〕。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是综合的,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专行的,它们有系统化的概念、原理、方法、技术,常能集中分析、丝丝入扣,但是它们也未必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因为社会有多方面,文化的性质每不尽同,古今中外时或相异,历史可以帮助它们,提供若干个案〔13〕。所以我们常常讲,历史是一座宝库和富矿。
史学和法学作为方法相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学方法的功能性价值在于,知道一项法律制度的源流,对法律进行历史透视,可以更好地促进它的执行。在西方,1600年以后,历史与法律研究联系了起来,这在德国新教地区的耶拿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黑尔姆施泰特大学、哈雷大学以及哥廷根大学尤为显著。早些时候,德国的法律学者发现,史学方法有助于解释他们中很多人认为恒定且统一的自然法的多样性。哥廷根大学的学者将历史在法律研究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使自己成了19世纪对法律做历史解释研究的先驱〔14〕。法学研究方法融入史学方法,可以充分彰显史学家的品格。“史学家研究历史,应当冷静、严肃”〔13〕,这一点与法學研究者倡导的风格可谓别无二致、不分轩轾。可以说,在法学研究中使用史学方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值得大加提倡的。促进史学方法与法学方法相融合,是法史学科的使命和宿命所在,作为方法的法史学是未来发展突破的重要方向。
三、法史何为?
“法史何为”,是在全面探讨“何为法史”与“为何法史”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出的一个方向性追问。笔者认为,成功的学术研究离不开明确的问题导向、新颖的研究方法、宽广的学术胸怀以及高远的学术抱负。故此,逐一从“明确问题意识”、“创新研究方法”、“破除畛域之见”以及“重述中国法史”四方面回答“法史何为”的方向之问。
(一)明确问题意识
有历史学家指出:“在构建历史学对象的过程中,提问题的作用是根本性的。”〔15〕仅仅堆砌史料而欠缺问题意识的导向,将无法做出真正具有意义的研究。正如梁启超曾说:“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16〕刘子健(1919—1994)也指出:“(历史学)最明显的遗憾就是在方法上过于重视窄而深的研究。”〔13〕当然,不可否认考证学也固有其价值,但法史学能否与时代同频共振,从长远角度决定了法史学科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克服对史料的单向依赖,弃文存质,有效平衡史论和史料关系,加强法律史理论的创新性。提倡开展专题而非单纯的断代、国别研究,在既有专题的基础上,借助知识的积累和方法的创新,继续提出新的可以持续、深化、集体研究的学术议题。
(二)创新研究方法
梁启超曾谓:“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16〕笔者所指的创新研究方法,既是向内的,也是向外的。向内是指研究法史学本身时,既要采用考证等常规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也要注意使用包括规范分析在内的法学研究方法,以形成属于法史学自身自觉的研究取径。研究法史学,切不可轻视法学方法,否则就难以纵深发展,因为“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更进一步发展大大有赖于专门学科方法论的进步”〔17〕。在此基础上,转而向外,追求“作为方法的法史学”。作为方法的法史学不是历史方法的单纯引入,而是法学和史学重新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方法,完成研究范式的突破与革新。法学不是一门冰冷的社会科学,它与生活联系紧密。将史学理论与法学理论有效结合,可以提升法学的人文学倾向、平衡法学的社会科学倾向,促进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进而嘉惠整个法学学科。从科际融合的立场出发,除历史学以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其方法,都可以通过这种路径为法学研究所采鉴,这可能与近年来流行的所谓“社科法学”理念部分相契。例如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法律史学,在食货法律等领域的研究可能奏效,成为法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之一。
(三)破除畛域之见
所谓破除“畛域之见”、捐弃“门户有别”,旨在提倡一种“大法律史”的研究理念,主要有三大场域。第一即是突破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藩篱。我国20世纪形成的对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史的二元划分模式,以如下描述为典型代表:“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作为中国法律史这同一学科的两个分支,虽有密切的联系,在研究中不能不相互涉及,但它们仍有显著的区别,最主要的在于法律制度是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所制定的,法制史所反映的只能是按照当权派的法律思想制定的法律制度的历史。而法律思想史则不仅要反映统治阶级中当权派的法律思想,而且要反映统治阶级中其他阶层、集团、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特别是还要反映被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18〕。这种思维定势或思想慣性早已不合时宜,应当打破。事实上,制度和思想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它们关系颇为复杂,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相互促进,有时则互为掣肘。缺了思想,就难以理解制度;缺了制度,思想也会稍嫌空泛另一个例子是,在法学学科,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被归为诉讼法学科,但实际上,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联系、民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联系更密切,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反倒联系没那么紧密,划在同一个学科当中,就显得牵强。。制度史和思想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划分方式,它无法回答制度史与思想史之间互动的问题。在法学领域,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之复杂交织关系的典型性尤为明显,不能单纯地将历史学系的制度史或思想史研究类比为法学院的法史研究,所以在法学院的法史学研究中更应力破制度史和思想史二分的桎梏。第二是跨越中法史和外法史(或称“世界法律史”)的“绝对界限”。中法史和外法史是存在界限的,但这种界限是相对的,并不是浑然天成、牢不可破的藩篱。中国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兴起,整个世界逐步迈向一个“整体”,给中国法制转型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此时恪守夷夏之辨、中外之别已不现实。只有把中国放诸国际,才能取得更全面、更系统和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三是破除法史学与部门法学的之间的畛域之见,有效推进部门法史学的特色化研究。法律史中有着每个部门法都需要的智识资源,可以由部门法学者参与探讨,以获得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更有效地推动法史学研究方法的传播与普及。
(四)重述中国法史
在中国,法史学研究的重镇、主流和长处均在于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史是一座理论富矿,可以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就是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以新领域、新史料、新方法,积极推动中国法律史创新工程的开展,推广中国法律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合作,提高中国法史学研究在海内外的学术话语权和主动权,需要把三点作为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敢于破除历史上不准确、不科学、已过时的既存成说,以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完善既有的合理成说,重新叙述中国法律史。杨一凡指出重述中国法律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出土、新发现的大量法律资料和传世法律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表明,以往法史研究存在严重缺陷,认识误区较多,未能全面、正确阐述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二是传统的法史研究思维模式已不适应法律教学和文化建设的需要。”〔19〕从这个角度看,繁荣法史学科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当代法史学人应有相当高度的学术使命感,如此法史学也必将大有可为。
第二,少数民族法律史是值得重视的本土资源。我国领土幅员辽阔,人口由主体民族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构成。与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度相比,中国法学界既有的研究对于少数民族法律史的关注稍显不够,此时法史学者若转向对少数民族法律史的研究,也能创设科际整合的新场域。
第三,要推动中国法律史研究走向世界,这是新时代加强文化自信的必然战略要求。在现今世界范围内,中国学研究学者群体广泛存在,国内学者可以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合作。中国也可以创办本国的法律史研究国际期刊(中外文版),在学术标准、办刊理念上与国际接轨,以开放互动的学术态度促进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法律史是体现中国风格、反映中国气度、呈现中国立场的重要场域,也是最容易产生国际学术影响的学术领域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宣示价值,能够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法学智慧,繁荣世界法学学术的发展。
四、结语
法史学是法学院中一门重要的理论法学学科,它可以避免使法学沦为一门纯技艺性的实践学科。它同时亦有必要调整自己,追问“何为法史”、“为何法史”以及“法史何为”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利于加深对法史学科起源、现状、发展的基本认知。法史学作为一种方法,是全方位认识法史学性质、地位及未来的新颖视角,是解决长期以来法史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相脱节问题的一种崭新思路,也不失为促进中国法学学科迈向更加均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1〕朱振.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4):76.
〔2〕谢鸿飞.法律与历史:体系化法史学与法律历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3〕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525.
〔4〕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M〕.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
〔5〕吴彦.CLSCI与中国法学的封闭——谈诸如“法史学”和“法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之衰败〔EB/OL〕.〔2022-03-18〕.https://www.sohu.com/a/361144988_655273.
〔6〕潘晨子.2020年CLSCI期刊法律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10年发文量较稳定 中国政法大学发文总量居榜首〔EB/OL〕.〔2022-03-18〕.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761822.
〔7〕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J〕.江海学刊,2021,(4):203.
〔8〕Edward Shils.Tra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3.
〔9〕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10〕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序.
〔11〕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
〔1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1.
〔13〕康乐,彭明辉.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132-133,114,130.
〔14〕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三版)〔M〕.黄艳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90.
〔15〕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M〕.王春华,译.石保罗,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0.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53,224.
〔17〕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M〕.张家哲,王寅,尤天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40.
〔18〕《北京大學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50.
〔19〕杨一凡.重述中国法律思想史〔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4):6-7.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Thinking Based on Three Questions
SUN Kang
Abstract: Under China's current discipline system,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legal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legalization” orientation of legal history, that is, the research of legal history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but its discipline attribute is law rather than history, otherwise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tting of “legal history”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law”.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prosper the research of legal history, it is a feasible path to “methodize” legal history.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outward” & “inward”, “history” & “law” is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legal history. Clarifying the three sub questions of “what is legal history”, “why study legal history” and “how to study legal histo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ree questions of legal histor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ts achievements.
Key words: legal history; discipline system; history; discipline integratio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legal methodology;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comparative law
(责任编辑:叶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