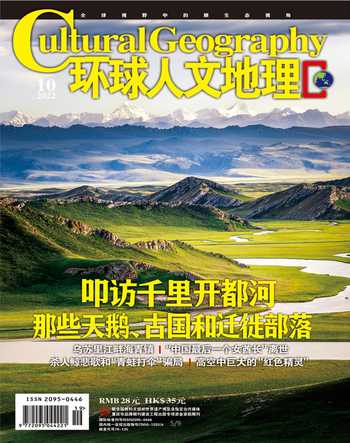博斯腾湖
姚力


开都河下游的故事,大多围绕博斯腾湖与孔雀河展开。
和巴音布鲁克的人迹罕至不同,博斯腾湖所在的焉耆盆地和孔雀河所指向的罗布泊,在我国历史上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丝绸之路要冲、兵家必争之地。焉耆古国和楼兰古国就曾存在于此,它们一度爆发出文明的高光,然后随着水源退化被湮没在戈壁下,给今人留下诸多谜团……
一个湖与两条河荒漠中的绿色生机
250万年前,地壳运动让新疆焉耆盆地强烈沉降,开都河水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在其地势较低的东南面,形成了一个面积约1600余平方公里的山间陷落湖,这就是博斯腾湖。《隋书》记载,此湖有“鱼、盐、蒲、苇之利”,西域诸多聚落赖此为生。现今的博斯腾湖是国家重要的芦苇生产基地,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湖中的淡水鱼更是一绝。
关于博斯腾湖,曾有许多传说:一人长的大鱼,2米高的野人……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大抵只是当地渔人虚构的饭后谈资。细想起来,大概是因为博斯腾湖周围环境优美,芦苇生长茂密,让人难以望见湖的全貌,加上人们对未知空间里的一切充满好奇与想象,所以才有了这些传闻。事实上,不用搜寻奇闻逸事,在荒漠化的地理环境中,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博斯腾湖的存在及其养育的周边上百万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谓吞吐湖,是指根据湖水的补给条件划分的一种类型,这种湖既有河流流入,又有河流流出。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孔雀河又从这个大湖中流出。
位于博湖县的宝浪苏木喇嘛庙,是奇迹的见证者。瑞典探险家尼尔斯·安博特写下的纪实作品《驼队》,记述了其中一位喇嘛的故事。曾经的博斯腾湖周边气候恶劣,民不聊生。蒙古人请求宝浪苏木喇嘛庙的布赖盖特喇嘛,去平息暴躁的湖水。在圣典启示下,喇嘛发现湖水暴虐,是因为一个邪恶的妖魔。于是他手持宝盒与妖魔展开激烈较量,并取得胜利,平息了风暴。喇嘛去世时,让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入湖中,以镇妖邪……
与传说中的记述一样,博斯腾湖并不总是温驯。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甚至建议将博斯腾湖“消灭”,让开都河与孔雀河直接相连,减少湖面的水分蒸发,这样一来便可以多灌溉十几个农场。今天看来,那显然是无法成立的狂想,位于下游的孔雀河,历史上常常因人类的活动面临断流危险,一度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连罗布泊这样的大湖都因为水源改道、干涸而消失。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博斯腾湖的调蓄,如今的这条绿色走廊会变成怎样的光景。
博斯腾湖的危机不仅于此,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威胁。博斯腾湖水的含盐量正在逐渐增加,已经进入微咸湖的行列。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变成难以利用的盐湖。若是如此,周边绿洲也会随之消失,博斯腾湖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罗布泊,带来一场生态危机。幸而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已经展开了博斯腾湖生态的研究工作,依靠不断发展的治理手段,这片绿洲正在复苏。
长度近800公里的孔雀河是罕见的无支流水系,博斯腾湖是它唯一的水源。开都河水在博斯腾湖里缓缓积蓄的力量终于在孔雀河得以释放。河水在库鲁克山冲出了一条峡谷,也冲出了古丝绸之路。闻名中外的铁门关就在这条峡谷中。唐代诗人岑参曾在安西都护府担任幕僚,于《题铁门关楼》中描写了铁门关之险:“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不知为何,如此不羁的孔雀河穿越铁门关之后,却收起了性子,滋润出一片片绿洲,最终流入罗布泊,孕育出一个个古老的文明。时光荏苒,随着罗布泊逐渐消亡,倚湖而生的灿烂文明大都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留下无数未解之谜。
一条路与两个国丝路之上的千年沧桑
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开都河到孔雀河流域就已分布着诸多小国,后被纳入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国家依靠河水滋润出的绿洲而生,又随着水源的消失而亡,今人熟知的楼兰古国就是其中的典型。而在三十六国中,最为强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要数焉耆古国。焉耆位于博斯腾湖上游,楼兰位于孔雀河尽头,分别是丝绸之路北道、南道的交通重镇,见证着丝绸之路的千年沧桑。
楼兰古国建国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史记》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所指就是罗布泊。楼兰古国建立于罗布泊滋养而出的绿洲之上,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繁荣一时,东汉时人口达到14000人,每年往来于此的旅人不计其数,各种奇珍异宝在这里汇集,令人目不暇接。但祸福相依,楼兰位于交通要道,因中西交往而兴盛,也因此屡受兵灾,被迫在中原王朝和匈奴之间左右摇摆,以求自保。汉朝曾多次派人俘虏楼兰王兴师问罪,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大概要数傅介子。为了慑服西域诸国,傅介子以楼兰杀害汉使为由,当场诱杀楼兰王,携其首级回到汉朝,楼兰大小官员兵士竟无一人敢阻止。西汉末年,中原动乱,无力西顾,楼兰又投向匈奴怀抱。百多年后,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在樓兰境内杀死匈奴使者,迫使楼兰再次臣服于汉朝……楼兰成为中原王朝心中西域治理的风向标,也是建功立业之所。李白就曾在《塞下曲》中,以“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诗句直抒胸臆。
然而不过短短数百年,气候环境的变化让楼兰从一个势力争夺的香饽饽,突然变得无人问津。东晋高僧法显西行途经楼兰城时,写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事实上,公元4世纪前后,消失的古国远不止楼兰一个。若是将目光投向整个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区域,人们就会发现这条线上包括楼兰王国在内的所有古城,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突然消失。这正是罗布泊旱化加剧的时期,最后整个湖泊干涸,楼兰不再是沙漠绿洲。缺水的楼兰人尝试过引水解决困境,可惜终究不敌自然的力量。
楼兰古城因为水源问题而被放弃,最终淹没黄沙中,长达千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探险队来到罗布泊地区探险,才意外让楼兰古城重见天日。


和具象的楼兰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人们一度只在古籍中才能看到焉耆古国的身影。焉耆,秦时称为敦薨(这个词被认为从吐火罗发展而来),在《佛国记》《水经注》中记作“乌彝”。《汉书》记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有户四千,人口三万二千一百,军队六千人……”焉耆位于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中转站。丝绸之路有两条古道经过焉耆:一条是由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现称“哈顺戈壁”,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西域”的起点),先至高昌,然后到焉耆;另一条是西出阳关,经白龙堆沙漠,由罗布泊北至焉耆,又被称为大碛道。因此,汉唐两代均将焉耆国视为安定西域的重要战略支点。
汉武帝时期,焉耆被选作屯田之所;公元前60年,随着匈奴日逐王归汉这一大事件,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焉耆便在治下;唐代设焉耆都督府,归安西都护所管辖。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前往天竺取经,都曾取道于此。武则天设立北庭都护府后,夹在庭州和龟兹之间的焉耆地位略显尴尬,被碎叶城取代,这以后,焉耆的名字逐渐式微,走上历史舞台的安西四镇变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朝廷调动大量边军进入内地平叛,通往西域的道路防守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让安西都护府驻军与唐朝中央政府失去联络,成为一支孤军。但当地唐军并没就此投降,在末代安西大都护郭昕率领下,坚守孤城长达半个世纪,甚至一度大败吐蕃军队,不过终究未能扭转历史大势。失去唐朝庇佑的焉耆又先后依附多个政权,直到蒙古帝国崛起才完全灭亡,融入西域民族……
一座城与两处遗址古老文明的遥远回响
焉耆古国都的确切所在,历史上有许多争议。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献比对,主流观点认为,就是位于今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处的博格达沁古城遗址。




博格达沁,维吾尔语中意为高大宏伟的城。古城的周长达到3公里有余,与中原的大城市相比有些偏小。但在地广人稀的西域,与城垣长度常常仅有一二公里的古城相比,博格达沁无疑算得上一座大城。古城旧称“员渠城”,出自《水经注》的记载:“城在四水之中。”也就是说,城的四面均有水环绕。然而西域的水是多么善变啊!如今遗址周边已是盐渍荒漠,仅有一条古河道从西北方向而来,沿古城北、东两面而过。古城城墙已经损毁,大多仅余墙基遗址,不过依旧可以看出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城中的建筑也如西域太多故城古国一般,化为了大大小小的土堆,轮廓难辨,仅能从其大小依稀想见昔日的风光。
除了行政官署所在地点的遗址,焉耆古国还留下了宗教文化遗址。毕竟它曾是路过的高僧大德一再称赞记录的佛国。法显路过焉耆时写道:焉耆僧徒“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唐代玄奘法师亦有记载:焉耆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可见佛教在焉耆显赫一时。
焉耆古国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佛教遗址是位于博格达沁古城外约20公里处的七个星佛寺遗址。所谓“七個星”,在维吾尔语中是“一千间房子”的意思,整个佛寺建筑规模超过4万平方米,规模宏大,是焉耆国的国寺。从整个西域范围来看,历史上这一片战乱频发,气候条件多变,诸多遗址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在这个大前提下,七个星佛寺遗址显得弥足珍贵,是目前我国新疆发现的唯一的同时保有佛塔、佛殿、石窟的遗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