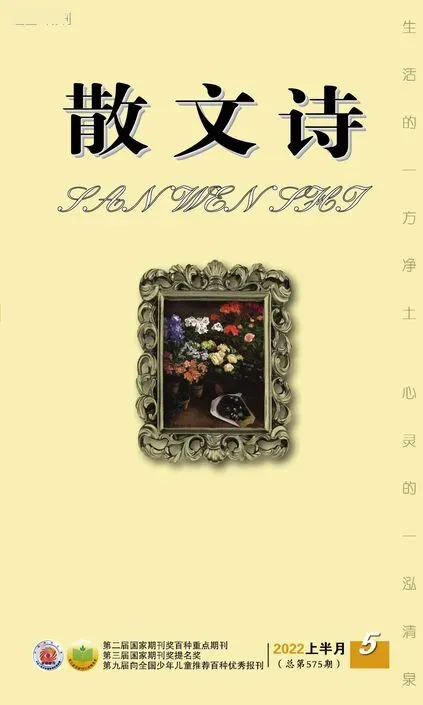写花的人也种花
◎蓝花伞

写花的人也种花
不是被子植物开花的地质纪年。当世界开始美得阵痛,花蕾才一路开到睫毛前。
那些人生如朝露、零落山丘的彻悟,家国和命运的跌宕,暂退一边。
“湿花随水泛”,“小桥穿野花”,怎样的瞬间,美开始驻足、显形、呈现文本可能?
明眸望过日月、经年,同质地喟叹:“三春过后花随风”,“风轻花落迟”,“细数落花因坐久”……均静谧,且感伤。
流光徘徊,美成高格。
梅,兰,菊、荷,最诱惑,翻涌成花带。
即使边关征战,也有——不落的剑花,漂泊的泪花。
为了海伦征战多年,古希腊的摇篮高挂盲诗人垂天的诗篇。
花朵在牵引,花朵在迷醉,带着记忆不可多得的美。时而稀疏,时而繁密,排列在时间两岸。
一直在书中行走、呼吸,或在星空俯视。
写花的人也种花。
一截走廊
鼻息、长发会背叛,衣服也会背叛,甚至包括许多拐弯的回忆。
不管意念走得怎么快,飞得多么翩然,那些气味,依然会追上你。
一截走廊,烟气缭绕。
一截走廊,就突然一直在等着捕获脚印。
如果出门就可以一笑大江横,进门就可以谈笑有鸿儒。如果出门就有同类白羽的亲切呼唤,而自己面对涟漪,不会恍惚倒影的存在。
亮光、阴影,大调和小调。
命运的指触在敲花岗岩的四壁。
毋须回眸,一截走廊,就在那里,浅浅,深深。
冬日的蘑菇
冬日的蘑菇,没错。在树林。在野地。
脚踏枯索落叶,眼望冰的前锋。唉,蘑菇的季节真的过去了。心里不禁回旋一小节小调。
可就在几分钟后的一转身,一棵老柳树下部,竟然藏有两嘟噜蘑菇的颤音。
层层叠叠,好新鲜的蘑菇,似乎刚刚萌发,可一摸,却冻硬了,俨然静悄悄的雕塑!
蘑菇的花期多在10月中旬。但都是即开即败。那是怎样的不管不顾,又是怎样压抑不住的悸动!依然顶着结冰的北纬40度,呼啦啦出生。像一群寻找童话和奇迹的孩童。
一绽放就获得不朽。一绽放就点燃一季的灯盏。
当
脚踝淌过水声,一圈圈涟漪,共振的浪花;雾气缭绕的荒原打开章节,承接一缕缕照耀;88个哑默的琴键,等待抚触。
微笑提升海拔,顿悟打开透明,意念的翅羽纷纷出发。
书房,光亮的囚室,世界的窗口。
当伟大的心灵,独步而来。
一点的窸窣也如电闪雷鸣,半句的呢喃也似铅锤敲门。与其说是借豪杰的视野重新发现世界,还不如说是世界在一次次战栗着新生。之所以激荡、振动,是因为 “千古一心”。而黄庭坚的“移胎”“接木”,不得不令人莞尔。应该说,是在不自觉中,心灵就会蒸出菌芝。
期盼这样的时刻,纷至沓来。
初冬的三棵丁香
不是一两个枝丫在发芽,而是整棵树;不是一棵在萌动绿意,而是绵延到三棵。在雪覆原野的初冬,单位花园的几株丁香摇动惊喜。
我环视花园其他的丁香,她们的芽苞都萎黄干瘪,一如收紧的北纬40度。难道是因为我今年经常悄悄在这三棵树边跳舞么?难道她们也和我一样,内心不断扑闪着五月,就像舞曲里唱的“我还是从前的那个少年,美呀美呀”,竟然忽略了迎面而来的季节、风雪、琐碎?抑或是她们用冬天不寻常的绿,来引领我时而枯索纷乱的思绪,逐渐返青,内心那辆小马车憩息其中。
丁香树,无视季节的残忍,只聆听自己内心的钟摆;
丁香树,绿在灵魂的此前、此后。宛若梦境。
春
时而白,时而转眼又迷离,灌木和小树间翻波逐浪,小鸟急着调校恋爱的竖琴。
老柳树松开拳头,小河掀动裙摆。泥土一寸一寸让出柔软。
露出等风的羽毛。一段春天的未知,种子纷纷爆荚。
依然是花朵的表情,池塘矮下身段,荷叶挣脱休止符。
灰鹊衔着树枝来去,布谷鸟试着抖开翅膀。
纷纷溃退。那些淤积的棉衣外套,整整一季的理性。满世界都是融化的味道,湿漉漉的鼓点。
远处的树梢,笼着如有似无的淡黄烟霭,告诉我春天;墨染的湿地,冰雪的残白,小鸟不休止的口弦,告诉我春天。
赭红的榆芽像扉页压不住的火。不动声色,我的舞姿和柳条一起返回轻灵和柔软。
每一个春天都是一个春天。
每一个人却不是一个人。
伤 口
伤口多了,伤口重复了,痛在复习,一个质地。
伤口多了,伤口重复了,痛会麻木,了无新意。
为什么总被伤于石头的棱角?是因为脚步的绵软;为什么那些石头总立起棱角?是因为远远嗅到了你的味道。
你孩子般的奶香,剔透。你孩子般的无力和转身,依然无邪和童真。
那些石头啜饮你,就像喝酒一样痛快。那些石头遇见你,都纷纷变成神秘园。
而你只是人世留存的一个意外。
一块石头立起,其他的石头也纷纷效仿,甚至昔日的好友,也把你的言辞悄悄献出。
这是最深的伤口。
再多的伤口,也会被浮云带走、时间带走。再多的伤口,也会愈合,用文字,用音乐,用大自然的一朵初花,一片落叶。
在伤口中茁壮,在伤口中依然保持心灵细瓷般的完好、优雅。
据说,还有一种美丽的伤口。那一定是月亮的潮汐,虚妄而又存在。在晨梦方醒,感性和理性尚没分野的时刻,开成雾中浅蓝的花瓣,笛孔中的颤音。
祈祷伤口,不要被身体记录、累积。若如此,也要逢光去暗,遇水搭桥。关键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要被周遭的气象左右,方能拯救和涅槃。
每一天,都当是命运的赐予。
雨中采桑葚
两天的雨,把那些络绎不绝采摘的手,都封在梦境的入口。
而我仍是独自冒雨来了。
高处主枝条上的果子个个肥美硕大,在油绿的叶子中央争相比黑。要么跳脚,要么爬树,要么用伞把钩。那些本属于小鸟、蜜蜂的幸福,此刻竟落入我的篮中。
侧枝和树冠下,那些紫星星般小小的、密集的桑葚,如同那些庸常细碎的幸福,似乎是神分发给众生的,这一次我毋须理会。
站在树冠下仰望,看不清有多少果子。
一棵树要跳出一棵树。甚至有时要站在另一棵树下。
雨声淋漓,我的采摘酣畅。任这些密而不宣的幸福,在我的心壁摇动万千旗帜。
伞已形同虚设。在一个人的桑林,在一个人的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