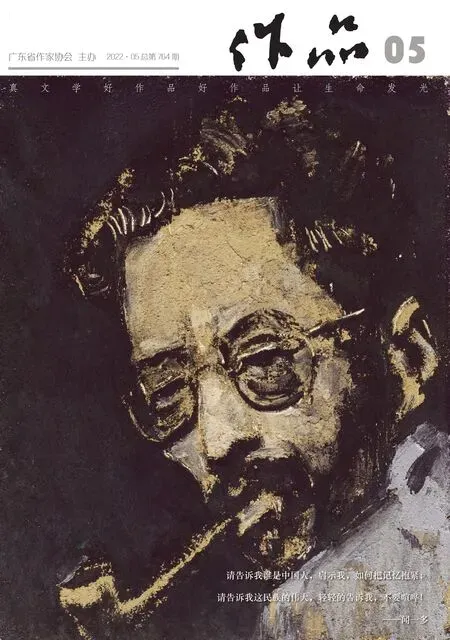货车(短篇小说)
洪霖(湛江科技学院)
推荐语:黄碧群(湛江科技学院)
《货车》以晓畅淡定、略带戏谑的语调讲述一个成长故事,结构精心设计,明暗双线并进:一是“我”的高中生活,打游戏、泡吧,看似玩世不恭,实则蕴含深沉;二是“我”的原生家庭故事,父母感情淡漠,几年前哥哥被一辆大货车辗毙,这一意外事故使整个家庭笼罩在厚重阴霾中。“谁会在乎这个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群体里,有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呢?”个体遭遇对于社会来说,连个水花都不会冒一下,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
作为家庭幸存的孩子,“我”一再被濒临崩溃的母亲诘问为什么还活着?“我是作为我哥的影子活着。”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一个带泪的锐角,紧紧地顶着主人公的咽喉。体现了生命内在与家庭因素的冲突与碎裂,而这种被“辛辣和冰涩浸透的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一个少女的成长及其生命价值认知。
通篇于平静叙述中潜藏汹涌暗流,小说结尾如约而至的雨与开头天气预报呼应,使故事形成一个回旋的时空,独特而巧妙。文中“货车”无疑是一个隐喻。人生永远不是轻装上阵,承载着太多东西,这些承载与我们的生命处于紧张、明暗、角力的双向关系。它既寓示一种外来的不可抗力,又喻指人经历着挫败又将怎样负重前行。
小说犹如一块精致的生活切片,让读者看到各种流行元素与家庭关爱的缺失情状下,网生代成长背后的价值体系和自我内在核心。述说的仍是人的孤独,对爱的渴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确认。《货车》带给我们进一步的深思是,无论哪个时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爱永远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
天气预报说,凌晨一点到两点的时间段有中雨,气温26度左右,所以现在才会这么热。
我看着手机里的气象网,一本正经地对同桌说。同桌的外号猪哥,前几天的体检数据是80千克,165厘米。走起路来像一颗蹦跶的橄榄球。
“姐,你说这还不如行行好,把你的小风扇借我一下,这教室真的又闷又热,我都快学不下去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又扯了一叠纸巾,小眼睛难受地眯着,胡乱擦着从油光发亮的胖脸上流出的汗。
“呸,说得好像你多爱学习似的,爱学习你怎么不坐到前两排去啊,你看看,教室吵成这样,他们也热,不一样在专心写作业吗。”
胖子不说话了,因为他王者的排位开了。
“啧。真学习不到三秒钟。”我在他肥软的手臂上拧了一下,也打开了王者荣耀。
从我的初中到高中,好像所有的教室都这么泾渭分明,前排的都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后排都是混日子的。只是,高中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这是市里最不入流的高中。
晚自习从来都是闹哄哄的,除了前排寥寥的几枚火种外,其他人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闲聊,追剧,有时候男生还会打架,躲进窗帘里扭成一团。坐在我后边的几人在玩炸金花,用瓜子作筹码。我原想叫后桌带我打游戏的,不过他今晚牌运不错,面前已经堆了一大堆的瓜子,我就不耽误他发财了。
这间闷热的教室里塞着六十多人,没有空调,几支沾满了灰尘的大叶扇吱吱歪歪地扭动着,不时落下几缕凝成条的灰尘。我歪着身子蜷缩在墙角,手指正专注地在屏幕上操作,开了大的小乔正在往人堆里冲,突然间屏幕上弹出了一条微信,一不小心点进了对话框,退出了王者荣耀。
我坐直了起来,爆了句粗口。
连忙切回游戏界面,却发现屏幕已经变成灰了。
叹了口气,一下子就没了兴致。看看那条微信,是排骨的。
“出来喝酒不?”
“在哪?”我咬着奶茶的吸管,只剩一点了,剩下的全是椰果粒。我口渴得要命,站起身伸手拿过前座的可乐,他也在打游戏,戴着耳麦带妹妹吃鸡。
排骨发了个定位给我,我喝了口可乐,仔细看了看位置,睁大了眼睛,“怎么到那了?”
“强哥昨晚欧洲杯赌球发大财了,今天他请客。”
“哦,那等我,我打辆车去,一会叫强哥报销。”可乐是冰的,铝罐的瓶身上湿漉漉的,这样闷热的晚上,最适合的就是冰可乐加凉烟。
我起身,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他站了起来到走廊上,手里还专注着操作,“我先走了啊。”
胖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我背后喊道,“那什么,明天给我带包芙蓉王。”
我们的高中可以说是这座城市里吊车尾的高中,封闭式的管理,原则上所有人都要住宿,除了星期五回家外,不能随便进出校门。
学校附近是一片看起来很荒凉的工业区,疏落宽敞的街道,白天来往时都不见什么人影的。小吃店,台球桌,网吧,超市,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得到两条街外的工业区入口处才有。学校的墙很高,除了白天也闲着没事翻墙出去上网的体育生外,其他人很少会翻墙出学校。
似乎很顺理成章的,这些块头很大的体育生垄断了学校的地下烟草生意,比外边超市要溢价四五块。曾经也有人想插手,据说被十几个体育生堵在宿舍里打了一顿。
我用软件叫了一辆网约车。从五楼到一楼,楼梯上坐着好几对忘我的情侣。
还有一个是我的前男友。从他身边经过时,我吹了声口哨,顺便在他的蓝白色鞋上踩了一脚。
他是个体育生,我们的认识很简单,我室友说他“体力好”,然后我加了他的微信,仅此而已。
相处一个月后,他给我的分手理由是:你的头发太短了,不像女生。
在停车场的围墙上,有两条被掰弯了的栏杆,是平时拿外卖的地方。我很轻易地从这条缝隙里钻了出去,约好的车已经等在了校门口。
我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酒吧就在我父亲的五金店附近,一条马路的距离。
自从我记事起,我父亲一直守着他的五金店,到了深夜才回家。脱了鞋袜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抽烟,偶尔和我妈吵架。
父亲对我和哥哥的期望很高,他一直都想我哥哥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当个公务员或者老师,能有稳定的工作。
每次我和哥哥跟他要生活费的时候,他都慢吞吞地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现在五金店的生意不好做了,施工队的单都交给他们自己的亲戚,我们平时只能靠散卖,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虽然当时哥哥上的是一所不入流的高中,老城区户口的分数线只要三百多分。
我们都开玩笑说,“中考的时候用脚在答题卡上踩几下,就能考上。”
在四年前的一个深夜,我的哥哥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大货车撞倒。司机是酒驾,哥哥再也起不来。四年间有很多东西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潮玩,歌单,网红,我喜欢的明星,这座小城市新建了一座大型商场,哥哥喜欢的电竞战队在一段时间的低谷后,春季赛爆种夺冠。
当时体育班那些无法无天的男生直接在教室投屏看比赛直播,喊得整栋楼都在作响,最后把保安都招来了,以为他们是在打架。
父亲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哥哥去世三年后,我进了哥哥曾经就读的高中,父亲在我穿上这身和哥哥一样的校服时,多看了我几眼,什么话都没说。
母亲在哥哥去世后,歇斯底里地扯着我的衣领,诘问我为什么还活着。
我只是安静地看着母亲,在被衣服勒得快喘不过气的时候,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作为我哥的影子活着。”
这是个标准答案。
母亲愣了一下,细细地端详着我,然后喜笑颜开地松了手,“对,你哥哥还活着。”
这样的日常在我初中的时候经常性地上演,像是在排练什么话剧一样。如果我妈的菜不变得那么咸,米饭不变得经常夹生的话,我想,我能演得更像一点。
某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母亲拿着把剪刀坐在床边,浑黄色的鱼珠眼睛里胀满血丝,神情痴痴地看着我,而我的脖子和脸上痒痒的,我摸了一下,全都是头发。起身时感觉头上轻了好多,而枕边,床边,地板上散落了很多的头发。
我去理发店,把一头碎发修成了男式的短发,哥哥曾经的发型。理发师皱着眉头问我是谁把我的头发剪成这样的,我说是我哥哥剪的。
理发师说你哥哥是在发疯。
确实没错。哥哥去世后,母亲就疯了。可是谁会在乎呢?
我哥哥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的父亲不在乎,因为他一天到晚都不在家。其他人也不在乎,因为每天早晨我家那个老旧的小区楼下,随处可见和我妈一样的家庭主妇:常年款式相似的睡裤或运动服,脸庞憔悴蜡黄,身材变形,染着红色或黄色的短发,连手里提的菜都是可怕的相似。
谁会在乎这个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群体里,有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呢?
酒吧的单层面积不算很大。中央还留着一块乐队表演的场地,今晚的演出还没开始,昏幽的灯光下,只有空空的架子鼓和几个黑色的乐谱架,马蹄形的散座大厅坐满了人。
我喜欢被骰子声和喧哗声包围的环境,或许不尽是喜欢,只是它们早已同香烟的辛辣和啤酒的冰涩浸透了我的生活。
我在角落找到排骨他们。排骨是我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人长得很瘦,一米八几的身高,体重才不到一百一,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筷子”。
另外几个男生都是高二的体育生,他们和排骨能玩到一起,纯粹是因为排骨他的堂哥在经营一家小超市,有渠道能拿到大批廉价的假烟,然后,体育生再以高价在学校售卖。
同桌猪哥在私底下抱怨说,他们卖得贵就算了,还全都是假烟。所以如果我晚上有到学校外的话,他都会托我帮他带包烟。虽然在外边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今晚除了我,还有两个女生,一个是菲菲,高二的学姐,还有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女生,叫冰冰,是菲菲的表妹,还是第一次见。
他们叫了些烧烤,鸡米花,鱿鱼干,还叫了两瓶威士忌,说是兑绿茶口感贼好。确实挺好的,绿茶饮料的清甜中和了高度酒的烈味,加了冰块以后,凉凉的,甜甜的,像是在喝饮料。
这是他们拿来在酒吧骗小女生的惯用伎俩。兑过了的威士忌没有什么酒味,很容易忽视了它其实是高度酒。不知不觉就喝上了头。
无论是什么样的酒吧,厕所从来都不会干净的。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酸味和酒味,夹杂着各种香水味,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果然门后摊着一大团糊状的呕吐物。
强哥玩了十几轮骰子,就带着喝懵的小冰走了,说是结好了账,让我们继续玩。
从酒吧里出来,已经过了学校宿舍的宵禁。我跟着排骨去了他家,排骨的父母都是在外边做生意的,家里常年没人。他在一所私立高中上学,说是明年会出国去读预科。
事后我有点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到浴室洗了个澡。找不到吹风机也无所谓。简单用面巾纸擦了擦,简短的头发差不多干了。
天气预报很准,凌晨一点多,外边果然下了雨。淅淅沥沥的小雨掉落在小区的海枣树叶上,噼里啪啦的脆响。
我坐在飘窗的窗台上,抽着排骨的烟,安静地看了一会外边路灯下飘洒的雨丝。从床头柜拿到手机,打开王者荣耀打游戏到五点多。没有叫排骨起床,穿好鞋子到小区外边,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包芙蓉王,找到了辆共享单车骑回学校。
睡眠不足的人早上精神反而是亢奋的。一种病态的亢奋。沥青路面上湿漉漉的,路上没有什么车辆,一个人孤零零地骑着共享单车。
如果这时有一辆集装箱里压沉货物的大货车,如果那个长期作息颠倒的司机喝了酒,如果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手把歪了一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如了我母亲的愿。
“你哥哥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像是所有的过往抓着我的心脏往下拽,沉沉的甸甸的,有时候恍惚,过长时间地凝视她那张近乎扭曲的面容。凝视地越久,情绪越发汹涌,直推着我的心往外跳。
恍惚间我好像听到了大货车的鸣笛,尖锐的,刺耳的,像是一只蛰伏的猛兽扑到你面前发出的嘶吼。
天旋地转中,眼前冒着闪烁的金光。在这一刹那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和哥哥周末到父亲的五金店里玩。哥哥趁父亲不注意,偷拿了店里的小货车钥匙,带着我爬上驾驶座,钥匙插在钥匙孔里,哥哥试图启动,却怎么也点不着。我脱了球鞋,翘着腿光着脚架在驾驶台上,轻轻哼着许嵩的歌,透过车前窗玻璃,看着上方一角的水洗蓝天。
身子狠狠砸中地面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喉咙里咳了出来,我躺在地上,才发现今天早晨雨后的天幕,其实也如天蓝色的海水般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