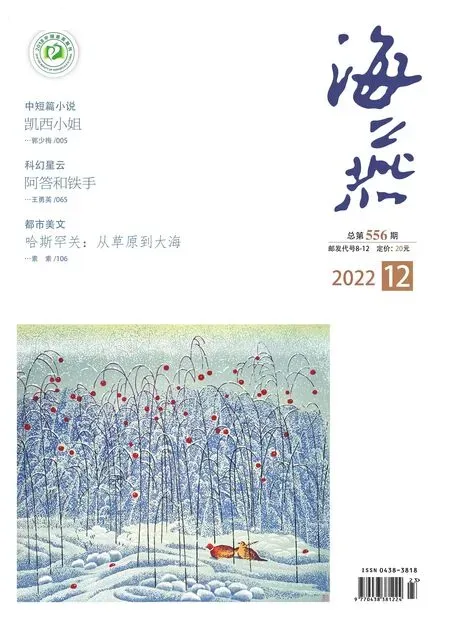苏格拉底的诡辩
赵树发

我给格格限定的酒量是:白酒一杯,果酒一瓶,啤酒三瓶,而且这三样还不能混着喝。超过这个限度,格格就很容易失态。所谓的失态,倒也不是打人毁物那种,无非就是磨人,混不讲理,或者浑身是理。
格格是学播音主持出身,大学时参加过几所高校组织的大学生辩论会,获得过“最佳辩手”。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地市级电视台,合同制,主要做访谈节目。可能就是因为她格格不入的性格所致,迟迟没有正式调入体制内。但电视台也确实认可她的才气,所以也一直“容忍”着她,别人都是早八晚五坐班,她可以是弹性工作制,有任务就去上班,剩下的时间由她自己支配。
在一次访谈节目里,格格现场采访一位多次下水救人的老英雄。她一开始还是按照台里给草拟的采访提纲,问一些常规的问题,问着问着,她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结果把那位老英雄问得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最后就剩下了四个字。我们来还原一下那次对话。
问:是什么力量使得你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水救人,而且无怨无悔呢?
答:我是党员,群众有难了,咱能见死不救吗?!
问:现场那么多人围观,为什么只有你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人?
答:别人我不管,谁不下去我也得下去,谁让我赶上了呢。
问:是不是不管什么人掉进了河里,你都能下去救他?
答:是啊。
问:为什么?
答:我会水呀。
问:为什么好几次都能让你赶上呢?
答:我会水呀。
问:假如你救人失手了,你会后悔吗?
答:会的。
问:为什么呢?
答:我会水呀。
后来,不管格格问什么,老英雄就用“我会水呀”答复她。就是因为这个“我会水呀”的访谈节目,格格获得了省里的一个挺大的新闻奖,而且被访者本人,也因为这句透着质朴、无私和无畏的话,感动了身边的人,成为省级道德模范。格格说,这叫灵魂追问,问到对方忘记了事先准备好的套话,才能看到其骨子里的善良。
我和格格相识于前年的“梨花诗会”上。我的一首诗入围了这次主题征文,当然在应邀之列,格格是主办方邀请的朗诵嘉宾。本来允许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考虑到我的地方口音太重,怕糟践了自己的作品,我就坚决地推辞了。主办方说,那好吧,我们请专业人士给你朗诵。于是就请到了格格。其实有没有我的这首诗格格都可能被邀请参加,一是她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再就是她热衷于参加这类风雅的活动。但后来格格跟我说,要不是我的这首诗打动了她,她这次真就不能来了,我姑且信了她的话。那天,格格穿了一件淡雅的梨花图案旗袍,脱稿朗诵了我的那首《花海漫城》。她美妙的嗓音加上撩动心弦的古筝曲,把那首诗演绎得浑然天成。现场的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听完后随即表态说,这个节目保留,准备上市里明年的春晚。
吃饭的时候,主办方特意把格格安排在我旁边的座位。主人介绍完彼此的身份后,我真诚地说,谢谢你的二度创作。格格马上回我说,是赵老师的作品好,我还怕没发挥好呢。我说我没觉得这首诗好在哪儿,是你的朗诵让这首诗升华了。主人在一旁打圆场说,你俩都别谦虚了,依我看,都好,诗写得好,朗诵得也好,珠联璧合。格格一开始看我还有点怯生生的样子,这让我很诧异,心想,不能啊,在台上她落落大方,侃侃而言,台下怎么可能拘谨呢?格格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跟我解释说,在我敬重的作家面前,我确实有点放不开。
席间,我们俩几乎没再怎么交流,大部分时间是应酬一拨又一拨来敬酒的领导和认识不认识的嘉宾。那天格格喝了点红酒,面若桃花。我发现她居然很适应这种场合,应答自如,张弛有度。快结束的时候,格格已经完全放开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主动跟我说,赵老师你收我做学生吧,我想跟你学写诗歌。我说,你给我个理由吧。她说,在看到你的《花海漫城》之前,我感觉我的周围充满了铜臭味,俗不可耐,是你,确切地说是你的这首诗,让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感。我不知道她的这番话是不是恭维我,但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她了。后来我们就互相加了微信,算是正式结了师生缘。
格格本名叫苏格,格格是她的艺名,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格格还有个外号,叫“苏格拉底”,这是我后来的后来才知道的。格格说,虽然她叫苏格,但不一定就会扯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何许人也?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是也,柏拉图的老师,雄辩天才,是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屈指可数的伟大先哲之一。他能把一个“正义者”诡辩成一个“善于盗窃钱财”的人,足见其能耐之大。格格的这个外号当然也跟她的雄辩天赋有关,更主要的是得益于那次大学生辩论会。
那次大学生辩论会的辩题是苏格拉底的名言:“别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格格是反方的主辩手,她要证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是荒谬的。坦率地说,这很冒险,也极富挑战性。因为我们通常对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是认同的,他把人的生存意义上升到了精神高度,或者说上升到了智慧层面,如果反对这句话,就很容易把自己归为庸庸碌碌、混吃等死之辈。但是,格格毕竟是格格,她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格格在最后的陈述中直奔主题,她说,包括故作清高的苏格拉底在内,谁活着都是为了吃饭。然后,在一连串的设问中,她咄咄逼人,让对方难以招架。格格说,还有谁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吗?有的人一心走仕途,那他吃的是当官这碗饭;有的人有经济头脑,商海里随便游了游就发了财,那他吃的是商业这碗饭;有的人没什么文化,就有一副好身板,那他吃的是体力这碗饭;有的人书念得好,念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也不要紧,他可以吃学问这碗饭……格格还引经据典地说,苏格拉底在和阿弟曼图斯辩论时说过这句话:“人没有仅仅欲求饮,而是求好饮;人没有仅仅欲求食,而是求好食。”(见《理想国》第四卷)他若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否认是肉体在支撑着精神,不妨饿他几天试试,看他去不去找柏拉图借钱买吃的?格格巧妙的语言组合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犀利口风,赢得了在场师生的一致好评,最终毫无悬念地摘得了“最佳辩手”的桂冠。
毫无悬念的事情还在延续。
我和格格慢慢地就熟络起来了。当然,格格一开始确实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跟我学写诗歌的,我也把我好为人师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我让格格先拿几首习作,我好有的放矢,加以点拨。格格很快就发给我十来首诗,有她以前写的,也有刚刚写的。那些习作严格地说还不算诗歌,语言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她总试图在诗中讲道理,这就有点别扭了。我跟她说,给出答案是小学生作文的思路,写诗要培养用意象说话的能力,诗歌只管呈现,把内心的价值观和自己的判断隐去,要奇绝而贴切,要有辨识度还要有结构。如果可能,还应当上升到思想境界……格格听得一头雾水。她说,赵老师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听不懂,你能不能说得通俗点,我现在甚至连什么是诗都不知道了。我那时刚刚出了一本诗歌理论集《一目了然的诗歌》,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送给了她。那段时间,格格一直恭恭敬敬地叫我赵老师。
格格的悟性很高,时隔半年,她再次拿出她的诗歌手稿时,已判若两人,下笔果敢而坚定,思维恣肆,语言凌翘,诗意渐入佳境。但我对她的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承认我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格格的诗歌语言突兀、跳跃,不是从课本上学来的,她的脑海里自有一套语言的编制程序。没有现成的词汇,她完全可以自己整合一个;没有搭好的桥梁,她宁可保持语言的峭壁。显然,我的那本《一目了然的诗歌》对她没有多大启发。我试图说服格格迎合一下读者,但格格不以为然,她说如果没有个性就不是她了。我说如果读者不接受你,你的个性一文不值。她说赵老师你怎么出尔反尔呢?是你告诉我要有辨识度的。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再也无力辩驳了。
格格的本职工作非常轻松,时间也宽裕,一两个月做一期访谈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她看我稿约不断,而且大多是商业写作,就主动承担起“助理”的职责来。我除了写诗之外,主要精力是为企事业单位写文案,或者接个电影、微电影之类的活儿。格格替我承担了所有的外事活动,敲定价钱,签个合同,追收费用等等。她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每次她去谈价,差不多都能超出我的预期,而且对方还一脸的心甘情愿。我的应酬几乎是应接不暇,经常推杯换盏。格格说,赵老师你不能这么糟蹋身体,这样吧,以后酒桌上我也替你应付,你只管安心写作。后来再有这种场合,我基本上都带着格格,偶尔有一两次格格有事没到场,总会有好事者调侃我:怎么没把你助理带来?格格有时候也带我出入她的圈子,那时她介绍我,还叫我赵老师,她的朋友也都规规矩矩地喊我赵老师,把我捧得像文学大师似的。半年下来,我就摸清了格格的酒量,就是我开头说的:白酒一杯,果酒一瓶,啤酒三瓶,不能混着喝。每次超过了这个界限,格格都把我磨得不轻,刁蛮、任性、混不讲理。也不能说混不讲理,她是把苏格拉底的诡辩天才用到了我的身上,最终驳得我哑口无言。再后来,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上升到感情层面了。
格格心高气傲,我知道追求她的人不少,但真正能入她眼、动她心的人几乎没有。跟她走得很近的男性朋友我差不多都认识,格格从不回避我。格格心冷的时候真冷,冷得让人胆寒。这是我逐渐体会到的,当然,这是后话。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忙碌,还是像以前一样频繁出现在各种附庸风雅的场合,格格就像一贴黏膏药一样紧紧粘在我的影子上。其间,我又收了几个学生,有写诗歌的,有写剧本的,有写文案的,也有什么都不写就愿意在这个圈子里混的。格格跟他们不怎么来往,见面只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好像只有她自己才是我正门正派的学生,那副傲慢的态度即使当着我的面也毫不收敛。时间长了,那些人对她也就敬而远之了。
我49岁生日那天,学生们偷偷策划了一个庆生晚宴。在此之前,我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也没有人张罗给我过生日,有好几年,我稀里糊涂就错过了这个日子。这次不知道是谁的提议,他们只是约我晚上吃饭,别的什么也没说。我到了才知道是他们预谋好的。格格也不知道内情,她还像以前一样,只当是陪我去应酬。那天的场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切蛋糕、吹蜡烛,然后痛痛快快地豪饮。他们每个人都备了一份小礼物,格格因为事先不知情,显得有点尴尬。我当然是坐在主宾席的位置,他们把左侧的空位主动让给了格格,右侧是我年龄最大的学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讲究,随便找个座位就坐下了。晚宴当仁不让地交给了格格主持。格格稍加思索就发挥了她的特长。格格说,我们选择在今天这个日子给老师庆生,是希望老师把青春永远留在49岁,49岁还可以拽住青春的尾巴。49乘以2,是98,我们当然希望老师长命百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老师在98岁高龄的时候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在老师百岁之时,还为他庆生……格格的这番即兴开场白,听得大家目瞪口呆,赢得了阵阵掌声,事后我再回忆起来,简直哭笑不得——她到底说了些啥?无非是一些正确的废话。
那天大家都没少喝,我也尽力了,达到了方酣的状态。宴席结束后,大家各自散去,照例还是格格送我回家。我要打车走,格格说老师咱俩走走吧。那天的夜色特别美,斗大的月亮挂在天空,像月老一样,慈祥地关照着天下有情人。我借着酒劲儿,一边走一边酝酿着一首诗。那首不太成熟的诗顺着嘴就溜出来了:“今天,我笑着说,人生不易/我含在嘴里的酒是辣的,咽进肚里是甜的/其间的辛酸已经发酵,或者挥发/今天,我先入为主/自囿于圆满/蛋糕是圆的,鸡蛋是圆的/圆桌之内,一团和气/其间的祝福也已发酵,或者挥发/今天,我笑着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狗日的中年……”快到家时,格格很平静地说,老师,他们都送你礼物了,我事先不知道啊。我说,拘泥那点小节干吗?我也不差什么。格格说,老师,我不知道你以前的故事,但我知道你现在是孤身一人,我也孑然一身,今晚我把我送给你吧。格格说这话时,我还沉浸在那首诗里,等我回过味来,发现格格正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我呢……
那天之后,格格对我的称呼也变了,她去掉了我的姓氏,直接叫我“老师”了,这也仅限于社交场合,平时我们单独交流时,她连称呼都没有了。格格身边的男性朋友逐渐在减少,以至于后来我再也听不到她有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这对我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从内心里讲,我得承认我喜欢她了,是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那样的喜欢,而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偏爱。我开始在意格格曾经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时不时地拿她以前的事调侃一番,我们之间为此吵过好几次架。
格格对我也越来越“放肆”了,谁看我的眼神儿不对了,谁跟我走得近了,或者我跟谁说话暧昧了……她都喋喋不休地警告我,甚至指名道姓地规定我跟某某人说话的距离和语言的分寸,有时候弄得我很没面子,她却是一副开心的样子。另外,我还发现她经常偷偷地查看我的手机,我没有当面指责她,因为我一旦开口,她的理由就会像连珠炮一样喷薄而出,我很难招架。后来我把我的手机设置了开屏密码,她也就无可奈何了。
我本来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不拘泥于体制,不迷恋于仕途,喜欢交朋友,往来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为格格的出现,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限制,这让我很不爽。我几次试图说服她,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的歪理邪说底蕴太深厚了,深厚得让我经常怀疑人生。我跟她讲道理,她跟我谈感情,我跟她谈感情,她跟我使性子,等到我跟她使性子的时候,她就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刁蛮了,我不任性了,我不混不讲理了,那就是我不在乎你了……每次说到这儿,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感觉我和格格之间已经出现了代沟,尽管我没比她大多少。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就扯到了爱情这个话题。她问我什么是爱情?我说爱情就是遇见。她说,如果一个猥琐的乞丐向我求婚,说把他的身家性命都给我,我是不是应该答应嫁给他呢?我没有正面回答她,我知道她接下来的问话一定会把我带到她设计好的圈套里。她绝对有这个能耐,先顺着我的话说,然后用我自己的话否定我自己。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反问她,如果我没考上大学,现在还是一个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你会爱我吗?格格说,你这个假设没有前提,如果你还是个农民,如果你不是个功成名就的诗人,你不可能有现在的学识和风度,不可能有现在的交际范围,用你的话说,我们不可能遇见。
格格的女性朋友少得可怜,我感觉她根本就没有什么闺密。她跟现在的同事之间也刻意保持着距离。但是她很奇怪地和高中同学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每每有同学从外地回来,她都主动参加聚会。有几次格格也曾邀请我参加,都让我回绝了。我感觉跟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在一起没有可谈的话题,去了会很尴尬。但那次,格格几乎是把我裹挟去的,我实在是推托不了。格格的一个男同学从国外回来,还带来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媳妇,格格让我去给她壮壮门面。见面的时候,格格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先生。当时所有人都愣了,我赶忙解释说我是格格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那位高中同学,曾经是格格疯狂的追求者之一。散场之后,我问格格,你怎么介绍我是你先生呢?她反问我,“先生”和“老师”有区别吗?我说当然有了,她问我区别在哪儿?我想了半天也说不清区别在哪儿,格格就笑了,那种笑明显带有诡谲的成分。
突然有一天,格格让我给她一个准确的名分。我说名分都是你自己设定的,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吗?格格说,你少跟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要什么。我说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格格说你干吗总跟我对着来,咱俩对等吗?我知道你想要自由,这个我给不了,但是我要的你可以给呀。我说既然你给不了我,凭什么要求我给你?
格格说,咱俩是谈交易吗?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世俗?这不是你呀?你的儒雅哪去了?你的风趣哪去了……格格一连串的问号又把我问蒙了。我感觉我们不能再纠缠在一起了。说实话,我让她磨怕了。我跟她说,我现在还无法给你你想要的,我需要恶补一下轴心时代诸位先哲的智慧,尤其是苏格拉底的诡辩艺术。
格格听了这句话之后,毅然决然地离我而去,从此人间蒸发,杳无音信。她倒是没拉黑我,但是微信已经把我屏蔽了。在之后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忍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想联系她,又不想联系她,那种感觉,就跟撕心裂肺一样。为了打发空寂的煎熬,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海,我把我们从相识到分手,每一个细节都想了一遍,我写了一组诗——《此前,此后》,总计18首,在情人节那天,通过微信发给了格格。诗发过去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格格连一个字都没回复我。
又一届“梨花诗会”开始了。这次我没有作品,我是作为颁奖嘉宾被邀请去的。让我没想到的是,格格也去了,这次她朗诵的是自己的作品,题目叫《葬花词》,内容我没有记全,还能回忆起来的有这样的句子:“摘下沁入骨髓的灵性/如同从一颗心脏里撕出另一颗心来/那么疼/裹上半块红布/连同芳香一起埋葬/在你我之间的一米阳光里……”
吃饭的时候,格格主动坐到了我的身旁。我们俩从见面到落座,一直相视无语。格格重现了最初见我时怯生生的样子,让我也有些不知所措。主办方招待我们的是精酿的地产南国梨白酒。格格主动要求喝一杯,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言语。一杯喝完之后,她还要喝,这时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我说,你知道你自己的酒量吗?格格说,知道,白酒一杯,果酒一瓶,啤酒三瓶,不能掺乎着喝。我说,那你怎么还要喝呢?格格说,葡萄酒是果酒吧?我说是。格格说,山楂酒是果酒吧?我说是。格格说,苹果酒是果酒吧?我说是。格格说,南国梨酒是果酒吧?我说是……当我反应过来我被她带进沟里了时,格格已经给自己又斟满了一杯白酒。
在送格格回家的路上,格格躺在我怀里,软软的,像个委屈的小猫咪。不知道她是真的醉了还是装作醉了,嘴里不住地说,南国梨酒是果酒,你说的,你说什么我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