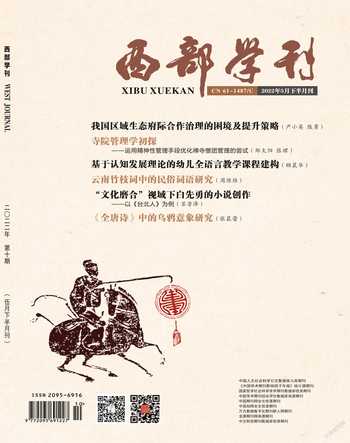“文化磨合”视域下白先勇的小说创作
摘要:通过文化磨合的视角分析《台北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主题意蕴,重新阐释白先勇丰富多变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一)磨合的人物。白先勇笔下的人物群像塑造,主要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渗透和西方现代意识的注入来实现的;(二)磨合的叙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深深地植根在白先勇的脑海里,而留学西方的经历又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叙事中既有中国传统的诗学意味,又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光怪陆离的象征色彩。(三)磨合的主题。白先勇通过塑造各阶层的人物角色试图揭示一种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的主题:世事沧桑和命运无常,又仿佛展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困境。白先勇这些为中国读者重现了充满传统意味的新故事,也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崭新视窗,并重建了在西方读者眼里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文化磨合;白先勇;主题内涵;叙事方法;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0-0150-05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都呈现出多元并容、交互辉映的局面,但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研究的重视却并非对等。但是,如果我们以文化磨合的视角重新考察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是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范畴里,通过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摩擦,形成中国特有文化的场域。这种“磨合”一方面体现在现代作家们对传统文化的隐性继承,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理论及叙述技巧的大胆融合。许多作家在自己的访谈中毫不回避地承认在西方现代思潮涌入的时候,仍然默契地保留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和热爱,白先勇就是其中之一。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热爱,导致了学术界对白先勇的研究与评价都是相当复杂的,有些学者将白先勇视为前卫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家,因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运用熟练,但也有一些学者格外重视他对中国古典抒情传统的继承和模仿。那么对一个作家而言,评论界对其创作风格和创作手段的研判如此不一致, 本身就足够我们再次深入研究和探讨他的创作。本文就通过文化磨合的视角分析 《台北人》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主题意蕴,重新阐释白先勇丰富多变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以期在新的视角下重新界定华文文学作家在20世纪文学史中的定位和价值。
一、磨合的人物:精神与心理
人物作为小说的灵魂,一直以来是作家们着力刻画和塑造的重点。《台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更加直观地告诉读者,白先勇要写的就是与台北有关的人。作家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往往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尤其是他接受的文化观念,是形成人物个性心理的主要动因。白先勇因其家学渊源,对古典文化知之颇深,所以在写作中将中国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方式不自觉地运用其中。又由于他的留学经历,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后,融合现代派的象征和暗喻手法以及意识流技巧,着重塑造人物的内心世界。白先勇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以对话和言行刻画人物的传统,在分析人物心理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技巧,这种中西结合的艺术手法将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小说中穿插的意识流描写,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让读者想他所想,闻他所闻。因此,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是中外文化磨合交融后的全新人格,个性鲜明。而这些丰富的人物群像,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文化的共同塑造来实现的: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渗透。“一个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总是在其哲学和宗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这样当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时,着眼点自然会放在作为中国哲学与思想主脉的儒道释三家之上。”[1]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儒、佛、道既相互排斥,又互为注解。白先勇的小说深受这三种文化的滋养,这也是作家本身复杂人生观的体现,尤其是《台北人》中的人物,能明显看到他们呈现的都是受这三种文化纠缠影响的多样性人生。首先,儒家文化的家国情怀。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纲领文化,同时它也影響了一个民族基本的思维逻辑。《台北人》中的多篇小说里出现了许多国民党军官人物,抑或是士兵子弟。比如,王孟养、赖鸣升,等等,这些军官们,都曾投身过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付出过青春。这些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浸染着儒家文化的家国情怀。其次,道家文化的神秘色彩。道家文化是一种超脱于俗世的文化观念,修道人往往通过修行最终超脱轮回,羽化登仙。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中国古代王朝的大部分君主最终走向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而白先勇也抓住了“长生不老”这一道家文化符号,在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尹雪艳。小说开篇第一句写下“尹雪艳总也不老”,这就将其塑造成一个终生不老的超然的女性形象。并且,小说中还提到了尹雪艳的命格特殊,命中带煞,克他人,这是道家文化中“八字批命”的常用说法。白先勇将尹雪艳的“终生不老”与“命中带煞”放在一起,突出了这个女性角色不同于常人的一面。将人性与“非人”性特质形成冲突,在读者心中打下尹雪艳充满神秘色彩的深刻烙印。最后,佛家文化的无常性。《大般涅槃经》中提到过一个观点,即无常观。我们常说人生无常,就是指它不是恒定的,反而充满了变数和未知。《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一生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人生无常这四个字。生活中本来平顺的他,突遭战乱,被迫离乡。满怀希望地打算战争结束后,回到大陆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结婚。结果,世事难料。无法回到故土的卢先生无奈地选择了与一个洗衣女结合,但是,洗衣女又背叛了他,让他尝尽世间冷暖。最后,卢先生在命运无常的折磨中,抑郁而终。积聚的财物终会散尽,登到至高之处必然会坠落,相聚终会分离,而人们活着终将走向死亡。这是人生无常的痛苦,不可避免。可见在白先勇的笔下,卢先生已然占据了所有方面的无常,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慢慢地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神鬼传说总是充满了好奇,这就导致了许多作家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喜欢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增加人物身世的复杂性来吸引读者。通过传统文化的渲染,人世命运的无常性更容易被凸显出来。这也正是白先勇在《台北人》中最为常用的叙述手段之一。
第二,西方现代意识的注入。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大批中国台港澳知识分子涌向国外,形成了轰动一时的留学热潮。这一时期许多作家们都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白先勇作为留学大军中的一员,同样深受新思想的感召。这些思想深刻影响着他塑造人物的方式,并且为人物增舔了先进前卫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把控上,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以形传神”的艺术手法,而是通过意识流、象征等艺术手段直接分析人物内心。白先勇磨合了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所刻画的人物,既有生活面的广度又有心理层面的深度。比如在《游园惊梦》中,蓝田玉因为昆曲脑海里浮现出往昔;又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离开夜总会之前的意识流动;再如《国葬》中秦副官在李将军的遗像前追忆当年在战场上的种种……这些意识流描写,都有助于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除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刻画人物心理,白先勇还善于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的命运多舛。《孤恋花》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就是一种象征,这里所提到的“花”,就是这篇小说中的两个女性角色。娟娟和五宝如同花一般的娇嫩,她们的命运又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一样难以经受磨难与摧残。白先勇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的小说所透露出的韵味,是人世无常的沧桑感。这种沧桑,不仅仅体现在家国动荡后的寂寥,也表现在人在时代更迭下的无力。尤其是那些受压迫的女性,在不堪受辱后的挣扎和内心崩坏中,弥漫出的沧桑。自古以来,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是弱者,而她们的遭遇是我们现代社会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但是,女性又有非同一般的韧性和坚强,她们擅长隐忍。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和痛苦后,积聚起来的怨恨和报复极具破坏力。于是,娟娟和五宝选择了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报复方式——死亡,将自己早已被无情的权力社会扭曲的命运拨正。整个小说没有写出生物学意义上的花朵,而是塑造了两个花朵一般的女性角色,娟娟和五宝就是柔弱花朵的化身。
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渗透,都为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注入了不一样的灵魂。不同于单一文化的影响,在多元化语境的融合下,白先勇的人物才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既有中国古典美学的傲骨和悲情,又有西方荒诞美学的冲动和困惑。以文化磨合的角度重新审视白先勇的小说人物,是将其放置在“古今中外大文学”视域下的恰当选择。这不仅可以将人物特征从单一的扁平化语境种解放出来,还可以立体化思考作者塑造这一角色背后的情势。
二、磨合的叙事:诗意和象征
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常常是伤怀与感慨为主的。对历史兴替的感叹,对物是人非的怀思,对际遇无常的悲吟。这种抒情传统深深地植根于白先勇的脑海里,而留学西方的经历又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所以在他的笔下既有中国传统的诗学意味,又融合了西方光怪陆离的魔幻色彩。
白先勇小说中的诗学意味,最直观地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恰如其分的直接引用,这些引用往往暗合着人物此时此刻的特殊心境。《孤恋花》中那首如泣如诉、悲悲切切的小调贯穿始末,为两位女子凄苦的命运增加了悲切的因素,也为小说创造了浓厚的悲天悯人的艺术氛围。除了诗词的运用,小说中也会增加许多与古典文化相关的元素。比如,《梁父吟》中对朴公书房环境的描写,其中悬挂的郑板桥的对联和文征明的画。这些环境描写足以说明白先勇本人对古代充满诗意生活的向往,白先勇也将自己喜爱的昆曲穿插在了小说的情节中,成为小说发展的线索。《游园惊梦》中,昆剧名曲《牡丹亭》的各种选段,是小说中隐含的线索,串联着过去与现在,甚至可以说是前世与今生。往昔这段昆曲成就了蓝田玉将军夫人位置,却也让她失去了可心可意的情人郑参谋,且在唱戏的时候失声;今朝又被窦夫人请来小聚重唱《游园惊梦》,引得众人喝彩和自己的思绪翻飞。可以说蓝田玉成也《牡丹亭》,败也《牡丹亭》,可悲的是,这也影射了她戏子一般的梦幻人生。白先勇用《游园惊梦》来当作这篇小说的灵魂,其中较为出名的选段,游园、惊梦与寻梦,恰恰暗合了蓝田玉在追忆往日情境的几段思绪转折。除了这些古典词曲的引用,诗歌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更是概括主题,升华主题的点睛之笔。在《台北人》这部集子的扉页上题有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2]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野草和燕子等意象,表达了时移事易感慨,并且警告那些沉浸在繁华美梦的世家大族,一切美好终会消散。小说中这些“没落的贵族”,通过纸醉金迷的生活状态,逃避现实的苦难。然而,时间的车轮从来都没有停止向前,物是人非的经历时刻警醒着所谓的“世家子弟”,早已不再拥有往昔的喧嚣与繁华,回归正常而普通的现实,才是最终的归宿。
以暗示、隐喻、对比、衬托等方式表达复杂的情感内容,使主体人物和作者创作意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契合关系,并获得抽象内容的具象化的效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传统的情感表达艺术方法。而现代西方文学的寓言式象征形象则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理基石,更突出了其理想性、思辩性,并运用了荒诞、变化等手段来构造人物形象。从《台北人》的诸篇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二种表现手段的磨合。白先勇的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用了“杜鹃花”这一意象,不仅沿用了古典文学中“杜鹃啼血”的悲情,还增加了思归的含义。小说中的主人公王雄通过一次偶然的遭遇,参与了战争。被迫离乡的他将对家乡的思念,寄托在了丽儿身上。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丽儿成熟之后逐渐远离王雄。这样无言地拒绝,让本身孤独的王雄再也没有活下去的信念了。于是,“王雄变得格外沉默起来,一有空他便避到园子里浇花。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3]王雄不可见光的爱情和思归的乡情,如同墻边那丛鲜红的杜鹃花一般,热烈开放但却寂寞无声。不同于杜鹃花这一传统的中国意象的运用,《台北人》的另一篇《秋思》中的菊花意象则充满了荒诞的意味。文中借用华夫人的眼睛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丫上,像是一只烂馒头,有的则委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4]这一段对菊花的描写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的菊花形象,其不在于歌颂菊花的圣洁,而是着重描写菊花枯萎生病的样貌。传统文化中菊花象征着高洁淡然的品格,但这段描写中,把菊花的残败和腐烂的一面描绘出来,让读者不禁感叹到被誉为花中隐者的菊花也有这样衰败的一面。小说中作为抗日将军遗孀的华夫人不屑其他太太亲日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如同病毒,污染了原本纯洁美好的菊花,使其慢慢溃烂,直至凋谢。华夫人坚决不崇洋媚外的品格也代表着千千万万华夏儿女的坚贞品格,而腐烂的菊花除了传统意义中的淡然与高洁,又传达着中华民族在发展中,仍旧有某些腐烂溃败的一面,需要时时警惕和祛除的决心。无论是诗意的渗透还是象征的运用,小说中不同人物以及他们不同的命运在白先勇笔下交织,而贯穿小说的是同样的主题思想,即人物沧桑和命运无常。
多变的表达技巧和叙述方法是作家们彰显自己语言能力的方式之一,白先勇将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象,通过异化、变形等手段,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含义。同样,在小说的讲述过程中,又恰当地将古典文化元素作为故事的背景,暗藏其内,形成了一个中西文化磨合的场域。在这片文化场域中,白先勇自如地转变中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构建了一个有别于五四文学的艺术空间,这也正是以文化磨合的新视角,重新看待白先勇等其他台港澳作家们创作的意义。
三、磨合的主题:命运无常与生存困境
《台北人》中的人物,无论是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或者是官家小姐,梨园名伶,这些人生来便是悲剧的承受者。白先勇通过塑造各阶层的角色试图揭露这样一种人生哲思:生命无常,人生短暂,多少繁花似锦顷刻间便灰飞烟灭,化作尘土,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是无可抗争的,它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短暂消逝,然后又重新归于寂灭。
小说《思旧赋》就传递了一种被命运裹挟下的无力感。全篇小说没有具体写到公馆的主人李长官,而是通过两个公馆老仆的对话,慢慢还原了公馆的人与事。在两位老妇的对话中,提到了夫人的死亡,丫鬟盗取财物和寄养在李家的小王私奔,公馆正经的小姐给有家室的男子无名无分地生了孩子,从国外回来的少爷痴傻,李长官被这些污糟的家事气得要出家……的确,李长官所遭遇的这些人事,让他顿感人生的无常,谁能想到往日的家庭和睦与儿女纯孝演变成今天的模样,于是想要出家寻求解脱。但是李长官被家里老仆提醒,还有生命的羁绊不能放下。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环境描写,公馆破旧的大门,杂草丛生的院落,满地的虫尸……这些入眼的满目凄凉都在昭示着李公馆早已不复往日的繁华与富贵,走向了破败和衰落的结局。白先勇在叙述的时候没有直接说明公馆衰败的原因,但是通过仆人的追忆和对话,已经表达了人生无常的沧桑和落寞,走向这样的结局也许是家人们行为的偶然,却是命运的必然。个体的无常与环境的动荡总是相互影响的,人作为渺小的个体,无力抗争命运无常的悲剧是白先勇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基调。
存在主义哲学将人的个体存在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拥有其他一切选择的前提,尤其是在生存困境下,活着与否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人类只有先活着,才能去追寻精神需求。白先勇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时刻关注着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困境与个体生命价值问题。因此,白先勇在其小说中思索和探讨着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问题,如《花侨荣记》中的米粉店老板娘原本是营长太太,为了生存,不得已开了一家米粉店;《一把青》中的朱青,原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学生,见到“我”的时候,是害羞而内向的,然而在她的爱人死后,她迫于生活的无奈,去卖唱,这个时候的她,已然不再羞怯,可以自如大方地在舞台上表演,再后来变得风骚放荡了许多。面对生存的困境,营长太太放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去经营琐事繁杂的饭店,朱青也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习性去军队里唱歌;秦淮河只卖艺不卖身的艺人也可以委身于年长自己四十多岁的男人;《冬夜》中的余教授,年轻的时候也是时代的弄潮儿,如今的自己疾病缠身,靠着大学教书的工作勉强度日。年轻时文学是他的热爱,而现在,文学研究仅仅是自己获得生存的手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几乎都是弱者,当个体发生生存危机处于一种困顿状态时,大家都选择平庸地活着,而不再谈激情与梦想。这与白先勇留学异国时的心境是一致的,美国社会的冰冷、功利让作者感到生存的艰难和远离家人的孤独。异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冲突,更增添了他作为“他者”的文化乡愁。无论是在异国物质生活的贫乏,还是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困惑,都为《台北人》中同为流落异乡的“他者”填充了悲剧内核。
值得指出的是,白先勇在这种悲观的个体生存困境中找寻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存态度,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去勇敢选择,向扭曲的环境作不屈的斗争,在行动的过程中超越虚无和荒诞。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放手去行动,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向悲剧抗争,这也是白先勇通过他的小说所要透露给读者的信息。虽然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总是被无常的命运捉弄,但无论是《岁除》中的赖鸣升,还是《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与荒诞的命运作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从而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尊严。
结语
从白先勇身上,可以看到20世纪这一批留学出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的碰撞磨合中,实现母文化的突围和转换,从而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可以说,作者以求同存异的心态,探索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既交融又独立的发展状态,实现了本民族文化再生与重建的完美过程。这些作家们在双重语境的文化加持下,以其开放的文学视角,成为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最佳纽带与使者。他们在写作思想、文学形态与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并创作了一大批值得被人们反复阅读与研究的文学佳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善于实现将“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磨合的智者,经由他们的创作与实践,不仅开创并建构出了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传统的另一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也促进了与中国文明相关的文化产业的持续产出。这些为读者重现了充满传统意味的新故事,也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崭新视窗,并重建了在西方读者眼里的中国形象。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升为人类普世性价值而使之得到世界性传播,又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中丰富了中华文化传统”[5],对中国现代文化贡献卓著,也对如今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
[2]白先勇.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
[3]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8.
[4]白先勇.秋思:白先勇文集第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31.
[5]黄万华.百年欧华文学与中华文化传统[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3).
作者简介:苏芳泽(1991—),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陕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