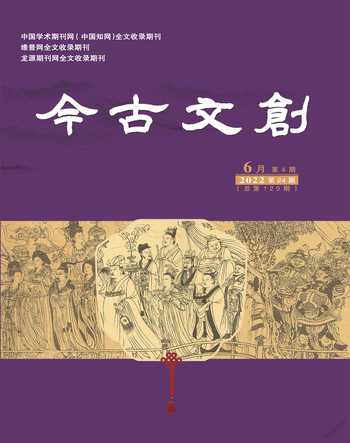朱熹与黄宗羲人物之性的比较
陈阅师如
【摘要】“理同气异”与“气异理异”是朱熹对人物之性的整体把握。朱熹虽极力排佛但仍受到佛教影响,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流行发育万物,天地纯然至善“天地之性”因此是纯然至善;“气质之性”是受到气禀夹杂的“天地之性”。而黄宗羲坚持理气一元论立场,提出“一本万殊”命题,重新梳理了理、气、性、心之间关系,进而认为人与万物同处在于“一本”即均由一团和气生化,“万殊”则在人禀得“有理之气”而物禀得“无理之气”。
【关键词】性;理同气异;气异理异 ;一本万殊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4-005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4.018
“理同气异”与“气异理异”是朱熹对人物之性的整体把握,朱熹的人物之性论说旨在佛教“以心观心”“作用是性”的影响下,以“性即理”来挺立传统儒家“性善”观;黄宗羲看到朱熹性善论理论之不足,无法突出人为万物之灵的价值,进而提出“一本万殊”的性善论,确立恢复了继孟子以来传统儒家“性善论”。
一、朱熹人物之性
(一)理同气异
在朱熹处,人物之生有理有气,因此“性”被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多用“性”指人物所禀的天地之理,也可称为“天命之性”,此天地之理纯然至善,人禀此理为性,这也正是“性即理”命题的真实表达。
朱熹的“理同气异”命题之“理”指“太极”即本然之性,朱熹以“太极”为“理”。此“理”是理一、理同。但此“天地之理”受气的影响,所禀之气不能全然相同,必有清浊薄厚之分别,因此得“天地之理”禀受气而落实在人物中形成的“气质之性”就会有差异。
理与气的关系,在朱熹处,理与气是相即不离开的,人与万物之生均是得理禀气的,此“理”即“太极”“天地之理”,理与气不相离而生人物,太极阴阳而生万物,人与物均具有其源、其理,此谓之“同”。但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必然变化万千,禀气之不齐即所谓“异”。
朱熹以此对孟子,告子进行评价。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他认为孟子已经体察到“人性善”之源,认为唯人具四端之德行,可擴而充之;但认为孟子缺乏对“气质之性”的考察。
首先,人物之生得理禀气,缺一不可,孟子尽说此性善,缺乏对气的考察,只顾说“本然之性”,忽略了“性”禀有气在内,受到气的影响“性”就不能是至善的了。其次,孟子的“性善”明确的说是“性之本体”,朱熹认为能称“性”时,已经是受到气的夹杂熏染的结果,因此受到气的影响的“性”不是纯善的;孟子的“性善”应是没有受到气的参杂的“本然之性”,只有没有气的参杂的性之本体才能说是至善。
对于告子的人性论,朱熹认为告子只看到了受到气的熏染之后的“性”,理气参杂成此性,而忽略了未受气参杂熏染的至善的“天命之性”,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1]所以告子认气为性,不知人之“本然之性”纯然至善,独有仁义礼智之理。
“性即理”是人性为善的先天根据,也是人性的道德本性的来源;人之所以会生恶,是因为“气”,气禀的影响即气禀是人性不善的先天根据。“继之者善”,承接天地之至善之理,谓“天命之性”;“成之者性”气赋予禀承的理,合而成之称作“性”。
此天地之理落于人与物之时,气随之附着形成形体,进而构成人物之性。在人在物就其一源处,可谓无人物贵贱之差异,此可谓“人物同处”;但这样就会违背传统儒家“人为贵”价值观,因此,要确保“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儒家传统价值,朱熹要讨论人与物之差等关系。他认为人得的是清明和正之气而为人,得昏浊偏阙之气且受蔽塞者成为物。论万物一源处可谓无不同,但人禀气真且通,物禀气偏且塞,以此观之便自有贵贱之差等,谓之不齐即“人物异处”。
人与物均有知觉运动,人有知觉运动,物亦有亦能,是气之作用,以气观之;只有人禀气正且通,所以能通天地之理无闭塞,为仁义礼智之德行,而物禀气不全亦偏,是故无所通天理。
“理同气异”还表现在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精明者,但人与人亦有差别。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2]
理只是一个理,阴阳五行运动不息,人物禀气也千差万别,有的人禀的木气多些,那么他恻隐之心,同情心相对较强烈,只有禀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恰到好处,四端不偏不倚才成为圣人贤人;所以,恶之根源的主要起源于气禀昏浊造成的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方面的表现。
因此,理同气异命题,所同者即人与万物之本源,得天地之理皆相同;所异者即人与物之差别在于气禀之万殊。
(二)气异理异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理同气异”与“气异理异”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其次,“气异理异”是以“理同气异”为先在条件。
“气异理异”与“理同气异”之“理”并非指的同一个理,“理同气异”的“理”是指“天地之理”纯然至善即性理(本然之性);而“气异理异”之“理”应当指“天地之理”坐落在人物之内的、受到气的熏染的分理即“气质之性”。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宝珠落在至汙浊处,然其所禀亦间有些明处,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3]
不是天地之理、天命之性本有偏全,人物之性本是同源,只是因为人物禀气的差异,所以理的发见显现才有不同。“本然之性”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人与物受气禀的影响,进而所显现或展露出的分理是万殊的。宝珠比喻说明人与物均具有此宝珠,此宝珠落在清澈水中,其发见显露的光芒就越多越清晰;若是落在淤泥中,其光芒被遮蔽,掩盖而不能显露。是气禀不同致使所赋之理亦有偏全,此为气异理异之内涵。
问:“气质有昏浊不同,则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4]
人与物之气均有昏浊闭塞之处,但由于人得气正且通,所以即使受到气的熏染闭塞,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恢复显现仁义礼智之性,所谓“有可通之理”;而对于植物动物来说虽禀有仁义礼智之性,但由于其气禀不能通,所谓“生得蔽塞之甚,无可通处”,所以原有的仁义礼智之性就不能完全显露出来,只能显露一德或二德,“如一缝之光”。如蜂蚁只有义之德、虎狼只显示仁之德。需要注意的是,仁义礼智仍普遍内在于一切品物,只是性理似应有质和量的双重规定性。人与物都无例外地禀有仁义礼智四德,但物因气禀之偏,故所禀受的仁义礼智有偏少(或仁少,或义少,或其中二德少、三德少四德皆少)然虽偏或少、仁义礼智四种德行总还是有的。[5]
综上,并不是人物之本然之性有异,而是由于人物禀气有昏浊薄厚之不同,进而造成的理的展露有异,这便是“气异理异”之内涵。
二、黄宗羲人物之性
然朱熹的“理同气异”与“气异理异”看似坚持了先儒性善论,但与孟子性善论有本质的差异。
在孟子处,犬牛人之性同无疑是荒谬的。人先验的、普遍的具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具对良好德行的向往与向善的能力,这是禽兽并不享有的,从而明确在人与禽兽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人与草木鸟兽不同类,故物性与人性决然不同。人与禽兽之差别极其微小,仅仅在于人具有这四心即道德的发端,而禽兽根本没有。
在朱熹处,朱熹的“理同气异”将草木鸟兽等物地位提升到与人同位,人性与物性之同,取消了孟子人物之性的鸿沟,那么人与禽兽等之性的差异仅仅在于受气遮蔽的多少进而影响性的显现的不同。这与孟子在本源上区分了“人之性”与“犬牛之性”有明显的不同。
作为清初大家黄宗羲,对于人性善恶的传统儒家问题,他坚持孟子“性善论”,认为人性至善,对宋儒“人之性论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分析了人物之性不同的根源。最后,阐明恶的来源即由于后天的影响。
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极须理会,单为人性言之则可,欲以该万物之性则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据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谓人物皆秉天地之理以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 如虎狼之残忍,牛犬之顽钝,皆不可不谓之性,具此知觉,即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不知物之知觉,绝非人之知觉,其不同先生乎气也。理者,纯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 人虽桀纣之穷凶极恶,未尝不知此事是恶,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绝,岂可谓偏者犹在乎? 若论其统体,天以其气之精者生人,尘者生物,虽一气而有精尘之判。故气质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虽有昏明厚薄之异,总之是有理之气,禽兽之所禀者,是无理之气,非无理也,其不得与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6]
黄宗羲指出程子“性即理也”只适用于人之性,不可以言万物之性。对于人之性与物之性的浑然未分是造成二程、朱熹等宋明理学家对孟子性善说的错误认知的关键所在。“性即理”只可言人不可言物,因为仁义礼智等德性唯人独有。对于“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观万物之异体”人物理有偏全,也内涵逻辑错误,若人与万物“皆秉天地之理以为性”,所得之理应同得其全或同得其偏,怎得有偏全;理犹如太极纯粹至善,亦不可有偏全。
在黄宗羲看来,朱熹“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的言论亦有局限性,诚然,人与物同有知觉,知觉为人、物共有之特质,但草木鸟兽亦有性,但与人性决然不同,所谓“一本万殊”。
(一)理气观
黄宗羲提出“一本而万殊”旨在说明天地间充盈一团和气生人生物,但气有精浊之分,人人禀有理之气,禽兽禀无理之气。
人与万物虽均本于气,但人为最贵,最有智慧,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禀得灵明之气,而物禀得昏浊沉浊之气。在黄宗羲思想中,理即气之流行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被分割的,所以不能以偏全论。气是本源的是第一性的,气与理只是一物而两名,并非是两个物体。理只是气升降沉浮流行不息的内在规律或条理。宇宙间只是一团和气,运行不息生人生物,其无过与不及,不爽失称作理。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 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7]理与气不得相离,理便是气之理。理是内在于气之中的、是气运行而不失的內在约束准则,即气之流行的客观规律。
(二)心性论
对于心性的概念,黄宗羲从一气流行角度来说明性与心都是同源于气的。在黄宗羲处,人由“气”所派生,作为人独有的灵气的特征,归根结底也离不开“气”,求心性不能离气。心是气之灵处;性是心之条理,性见于心之运动中,并不存在超然的、独立的性。一团和气落于人,人得此气化成心;心的流行不息而不乱不杂不失条理处便是性。既然心由气生化而成,理气为一物那么心性就不得说是两物了。
性是心的内在规律,不存在宋儒所谓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区分,认为天以精明之气生人,昏浊之气成物。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关性上事?性则通天彻地,只此一物,於动极处见不动,於不睹不闻处见睹闻,着不得纤毫气质。[8]
在黄宗羲处,人、物之性不同的根源就在于所受之气的不同,即“有理之气”与“无理之气”。人与物之性的差别在于,人禀有理之气,物禀无理之气。需要注意无理之气并非无理,因为理气一物,旨在说明物与人之间的差异,草木鸟兽不得与人禀得相同有理之气。黄宗羲以此批判朱熹的“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人与草木鸟兽的差异不在于人物禀气有昏浊薄厚之不同,所造成的理的展露有异,而在于生成人物时所禀之气的不同。理纯然至善是不可论偏全的,穷凶之人不会不知事物的善恶,只是陷溺其中,无论人的气质清浊昏暗有何差异,本身所具有的条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依旧存在;而禽兽所禀是无理之气,是没有仁义礼智之德性的,有的只是知觉运动。
黄宗羲认为后儒虽然也坚持性善论,但将义理与气质相杂糅就已经堕入“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误区,是受到佛教真俗二谛的影响,流入不善;又受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影响逐渐流入泛性善论。他用“有理之气”与“无理之气”的区分说明了人之性与草木鸟兽物之性不同的根源,世间万物唯有人得有理之气即有仁义礼智之性,与物之性是绝然不同的。
综上所述,朱熹虽然极力批判佛道二教,认为其害处甚多“异端邪说”,极力排佛,但在宋代佛道二教之兴盛、儒释道三教关系补充融合的大背景下,其理论思想仍不能完全摆脱佛道的影响。朱熹一方面受到佛教影响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另一方面,朱熹仍要坚持传统儒家价值即天地之间人为贵,强调人与万物的等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朱熹肯定“性者,万物之一源”的基础上,提出“理同气异”,肯定人与万物之性本源,所禀天地之理皆相同;所异者在于禀气的清浊明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用“欠阙”“气异理异”“理有偏全”“气近理异”等命题说明人与万物之性的差异。人贵在“知反”谓有“可通之理”,人之性得仁义礼智之全,即使受到气的熏染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彰显出仁义礼智之德;而草木鸟兽虽也禀又仁义礼智但受气的影响,仁义礼智是受遮蔽、有偏少的,物又不知“反”所以只能显示出相对有限的一德或两德。这样既肯定了万物皆具善性,又确定人为最灵。
在黄宗羲处,也极力排佛,认为佛教:“佛氏以气为幻,不得不以理为妄”但也不赞成朱熹“理同气异”“气异理异”将理气、心性二分的做法。他认为,理气并不是两物,而是一物两名,理只存于气中是气的内在规律。人与万物同处在于“一本”即均由一团和气生化,不同处在人禀得“有理之气”,物禀得是“无理之气”即“万殊”。只有人才有仁义礼智之德行,具有道德属性,而草木鸟兽等物只有最普通的知觉运动,没有仁义礼智之性。黄宗羲“一本万殊”命题重新梳理了人与物的关系,将先儒泛性善论拉回先秦孟子传统性善论立场。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05.
[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華书局,2020:198.
[3]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03.
[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20:58.
[5]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00:135.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35.
[7]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1061.
[8]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