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蒂姆·英格尔德的造物和设计人类学理论
文/关晓辉(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
“造物艺术论” 最早由张道一先生提出,他希望在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和西方设计理念之间构架桥梁以促进设计学科的发展[1]。在其影响之下,近年来以“造物” 为切入点的设计学研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研究者对造物原理的探究也不断深入。 本文认为,此时有必要引入西方参照理论, 帮助我们从本体论层面延伸造物原理的研究空间。
在此背景下, 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格尔德 (Tim Ingold) 进入本文的视野, 他从生物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维度对造物和设计进行别样的解读,更新我们的认知。 其主要观点有: (1)“造物如同生长”(making as growing),即物的形态生成于力的场域中, 如同有机体生长;(2)“设计即预见”(design is foresight),设计与造物共生,且面向物的未来。 对设计学研究而言,他将造物和设计视为“参与”和“促成”物的形态生成的活动, 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二者的本体属性和特征; 此外他对于实践和环境关系的论述也启发我们思考二者的生态观问题。
一、英格尔德及其生态人类学观
英格尔德自称40余年的学术生涯是从科学到艺术又回到科学。 他进入剑桥大学时报读生物学专业, 一年以后发现自己对人类生活比自然世界更感兴趣, 于是转向人类学, 1970年和1976年分别获得人类学的学士和博士学位。 他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长达25年, 并将主要精力放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之中。 之后, 他入职阿伯丁大学,一直至今, 在这期间他将研究重心相对地转移到艺术领域。
长期以来, 西方思想学术体系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 自然和人文二分的情况一直存在。 在踏入人类学世界之初, 英格尔德就意识到这一根基是不稳固的,怀着成为 “人类学界的伽利略” 的宏愿, 他把弥合自然与人文的裂缝作为奋斗目标。 他认为这种二分局面的根源在于人到底属于有机生物体还是社会文化产物, 于是他尝试解决人的生物和社会维度二分的困境。 在认真阅读发展生物学、 生态心理学和现象学的作品以后,他找到了有效路径。 他自称获取这一顿悟是命中注定: 在一个寻常的下雨天, 在赶去乘车的途中突然领悟到生物体和人类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不需要分开的。 因此,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从自然和人文两个领域重构人类,而应该消除已有的区分,整合为一个讨论人类生活的整体路径[3]。英格尔德所说的整体路径便是生态人类学。 他把相关的理论思考集合成《环境的感知:生计、栖居与技能文集》(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2000)一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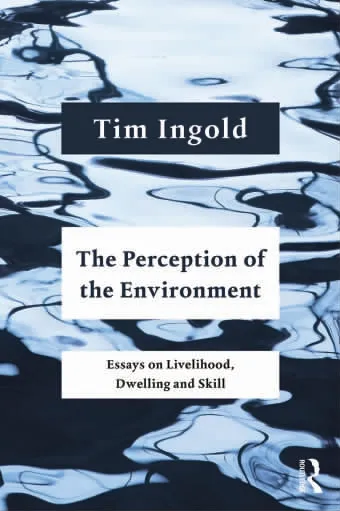
图1 《环境的感知:生计、栖居与技能文集》封面
在英格尔德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首先是“建造视角”(building perspctive), 指人在其栖居之前便在自己的观念中建构了世界。 在此视角下观念在前而行动在后,作为自足个体的人面对着可分离的环境。 其 次 是 “栖 居 视 角”(dwelling perspective),指人建造的形式(无论是在观念还是现实中)发生于他们涉及活动的趋势中,处于与他们的环境互相浸入的具体语境中, 人的存在被定义为“环境中的沉浸”。 英格尔德认为,造物人是在“栖居视角”下的实践活动,与实践者的环境形成动态构建关系[3]。
在入职阿伯丁大学之后的几年中, 英格尔德对于人类学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之前坚持的 “栖居视角”依旧没变。 他把这一期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集合成另一部作品 《造物: 人类学、 考古学、 艺术和建筑》(Making:Anthropology, Archaeology,Art and Architecture, 2013) (见图2)。此书除了涉及造物理论, 还有两章专门讨论设计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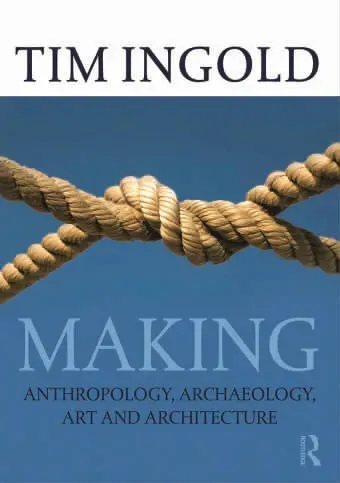
图2 《造物: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建筑》封面
二、如同有机体生长的造物
2.1 从“形式质料说”到“形态生成”
西方古典造物观认为, 造物是将物质材料改造成人心目中的样子, 当物质材料获得形式时此过程就结束,最终成品被称为“人工制品”。 事实上,此观念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 亚氏认为创造物质就是把“形式”(morphe)和“质料”(hyle,相当于物质) 结合起来, 或者说, 人首先设计 (构思) 形式, 再改造质料, 设计在前而行动在后。
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质料说” 影响深远, 其潜在逻辑是形式和物质的关系并非对等。 很多现代哲学家对此表示质疑,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哲学家吉列斯·德勒兹 ( Gilles Deleuze) 和费利刻斯·加塔利 (Fix Guattari)。 两 人 在 阐 述 “游 牧 学”(Nomadology)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此观念。他们指出:“‘形式质料说’最大的问题是假定形式是固定的,而物质是同质的。 因此,它无法承认物质的可变性(包括其张力和弹性,流动性和反抗性), 另一方面是它无法解释物质调变时发生的形塑和变形……在现实中,物质处于运动和变化的状态,我们只能跟随这种物质的流动……对于造物者来说,他们就像徒步旅行者,其任务是发现世界生成的纹理, 并跟随它的踪迹。 ”[4]正是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英格尔德形成自己的造物人类学观。
英格尔德对西方古典造物观同样表示怀疑并希望予以替代。 他说道:“我最终的目标是推翻 ‘形式质料说’模型, 用新的本体观取代它。 这种观念重视形塑的过程而不是最终成品;重视物质的流动和转变而不是其状态。”[5]英格尔德希望从造物活动内部寻找促成形塑的推动力, 以此解释其原理。 此时, 他又接触到生物学家达希·温 特 沃 什·汤 姆 森 ( D'Arcy Wentworth Thompson) 的理论。 汤姆森在 《论生长和形态》 (On Grow and Form, 1961)中指出, 贝壳的外形是在“形态基因场域” (morphogenetic field) 中生长而形成的, 而这个场域是指自然进化过程的综合作用力[6]。英格尔德想到, 既然有机体是在内部推动力的作用下获得形态, 那么人工物为何不能这样理解呢?
于是, 英格尔德把造物和有机体生长联系起来: “我想把造物设想为生长的过程……大理石雕塑的形塑过程和螺壳的没有什么区别, 每一次的敲打和雕凿都对大理石雕塑的成形产生作用, 就好比每一次自然因素对螺壳的成形产生作用一样。 当雕塑完成后,它会受到雨水等外力磨损,形塑的过程还会持续, 但不再有人为的干预。 ”[5]可以说,他的造物观是从时间维度出发,把形塑作为一个“形态生成”(morphogenetic, 这个词来自汤普森)的过程。 英格尔德把生物学理论应用于人类学和哲学中, 以全新的视角解释造物原理,更新我们此前的认知。
其实在之前, 德勒兹和加塔利已经从一项古老的西方手工技艺——冶金术——中看到造物的生命特征。 在这项技艺中, 工匠们需要反复把金属放入火中, 然后在铁砧上捶打, 而金属的形状会不停变化。 “在冶金术中,材料在工匠的推动下展示出特有的生命力, 它使物质的内在力量被激发出来,使其成为世界的存在。 ”[4]英格尔德则认为, 不仅是冶金术, 织造、 建造等其他活动都有这种特征。 他对于造物者也有清晰的定位:“在造物活动中, 手艺人要使他的动作和姿势与材料结合起来, 参与并跟随物质成形的作用力和流动性。 ”[5]从“形式质料说”到 “形态生成”,物质重新获得积极、能动的身份, 而造物者也从支配者转化为过程的参与者。
2.2 造物的“织造性”
在阐述完造物原理之后, 英格尔德进一步论述具体实践活动以验证其观点。
他选择了“织造”(weaving)作为讨论对象。 他首先从博厄斯的 《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1927)中留意到这种活动的特殊性:“编织匠人的双手好像处于自动状态,左手平摊在篮身上,右手拨动竹条绕过篮身, 动作力度和竹条之间的距离是绝对均匀的, 使得篮子表面平整规则,弧度流畅自然。 ”[7]此外, 他在1991年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塞皮克省进行田野考察, 亲眼目睹特勒封(Telefol)人制作绳编背囊的情景。 他对于织造者肢体动作的熟练和流畅表示感慨:“特勒封人编织的动作就像一条河中流动的水, 劳作中的身体并不像物体在运动, 而是成为那种流动的一部分。 ”[8]
在西方古典造物观念下, 人们通常看重设计的形式即最终的成品而不是物质逐渐变化的过程。 如英格尔德所说:“我们所称造物的 ‘织造性’(texitility)越来越被贬低,而它的结果往往被强调。 ”[8]在他看来,“织造性”扭转了传统的造物观, 因为它会使人们认识到是行动本身促成物品的形塑。因此, 英格尔德希望 “织造性” 可以重新得到重视,他写道:“一般认为,织造属于造物, 相反地, 我提议我们把造物当作一种织造的模式。 我相信,这种扭转对于理解我们与所有物品及其环境的关系打开一个新的空间。”[8]
具体来说, 英格尔德通过3个层面分析 “织造性” 的特征。 首先是“界面”。 除了物质的表面之外, 界面还指人与物质、 环境之间的互动交界处。 织造物界面的成形十分接近生长的过程, 因为它们是通过材料 (竹条、 藤条、 绳子等) 的内外缠绕而逐渐形成的, 同时材料的表面没有发生变化 (与石头、 木头等材料不同)。其次是 “力的作用”。 这里的 “力”主要指织造者的技能。 正如博厄斯所描述的, 织造者的技能表现为有节奏感、 重复的运动。 这种运动使材料受到均匀和规律性的 “力” 并使其逐渐完成形塑。 最后是 “形式的生成”。英格尔德观察到织造与其它造物方式不同, 因为其形式随时间的推移经历自我生成的过程。 他对此进行总结:“织造物的形式不是产生于构思, 相反, 它们是通过力的场域—— 由实践者和物质的积极参与所构成——的逐渐展开而自我生成的。”[8]
三、与造物共生的设计
3.1 设计的过程:构思与制作同步
英格尔德对设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建筑领域, 并且将时间范围延伸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在现代社会, 建筑设计师通常负责构思, 他们只把建筑最终完成的状态绘制出来,其余的工作就交给建造者。 设计师把建筑想象为一个完整的形态, 而建造者把建筑当作一个过程——地基、 墙面、 屋顶等都要一步一步地完成。 也就是说, 设计和建造是分离的。
然而, 英格尔德在查阅古代手抄本和相关文献时发现中世纪教堂的设计和建造并非如此。 中世纪教堂的建造者基本是泥瓦匠和木匠, 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 其中的杰出者被称为“建造大师”(master-bulider)。他们要掌握一座教堂从开始到完成的完整规范, 以确保它最终呈现出构思的样子。 具有才华的“建造大师”会把这些规范用素描的方式记录下来。 如13世纪法国泥瓦匠大师维拉·德·奥内库 特(Villard de Honnecourt),他 把 哥特式教堂的造型、结构,材料、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等绘制成一部小册子[5]。
从这个角度来看, 像奥内库特这样的中世纪工匠身兼设计师的角色。那么,在中世纪到底有没有专门的设计师呢? 著名的建筑史家弗朗西斯·安德鲁斯(Francis Andrews)给出答案:“没有任何一座中世纪教堂是由单独一个人构思出来的, 他只是坐在那里进行设计, 把方案绘制出来, 然后监督其他人去执行。 这样的人没有必要存在……所需要和确实存在的是诚恳工作的人, 他在完成工作时会得到众人的尊敬。 因此, 没有只是设计的建筑师。 ”[9]
在今天大多数设计师眼中, 记录构思的图绘是纯粹的设计; 而在中世纪工匠那里, 图绘和建造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例如, 他们在雕刻石头窗饰前要画出窗的大小和装饰的造型, 这样切割石头才会更加准确。 英格尔德认为“他们兼顾绘图、设计和工作。 设计是工作的一部分, 而不是观念的反映。 ”[5]应该说, 这种工作方式正好符合他对设计的设想, 即构思与制作同步。 或者, 我们还可以通过design的原型designo去理解。 Designo一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 它在当时是指构思和图绘的结合。 如果把designo看作一个硬币的话, 那么它的一面是头脑中的观念, 另一面是纸上的视觉表达。 同样地, 在英格尔德看来,design也应该是一个硬币, 它的一面是构思, 另一面是造物的行动轨迹(制作)。
3.2 设计的本质:预见未来
与其他设计研究者不同的是, 英格尔德的知识背景来自人类学、 生物学和生态学, 因此他的设计理论颇为另类。
英格尔德对设计本质有所思考,是因为受到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的 启 发。 道 金 斯将生物隐喻为 “钟表”, 因为它们的形式、 结构和功能像钟表那样复杂和巧妙。 他还将生物的设计者隐喻为“钟表匠”, 设计其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 事实上, 他所说的设计者就是自然界的进化规律。 道金斯写道: “一个真正的钟表匠洞悉前面的方向: 他设计齿轮和弹簧,以及它们的连接部位,在他的心灵之眼中有一个未来目标。自然选择,则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就像达尔文所发现的那样。 在我们目前已知的, 所有关于生物外部形式的解释之中, 没有哪一个和主观目的有关。 如果说,有自然界的钟表匠的话,那么他是失明钟表匠。 ”[10]
按照道金斯的思路, 生物外部形式的变化受自然选择的指引, 设计因子已经被埋入有机体的体内, 就像自动更新的数据存入DNA一样, 所以设计者是盲目的。 将设计与自然选择联系起来确实是富于启示性的想法, 因此被一些设计理论家所采纳。 例如,英国建筑史家菲利普·斯蒂德曼(Philip Steadman) 指出, 地方建筑的形式是自然和地方文化选择的结果,它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1]。 这类观点充分考虑到设计的生态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但忽视了人的创造性。
与上面观点 (认为设计是外部“力”选择的结果)不同的是,英格尔德认为设计主要靠内部“力”的推动。 他通过观察真正钟表匠的工作状态来探讨设计本质。 他找到一张1949年拍摄钟表匠在作坊中工作的照片, 其中一个钟表匠坐在工作台前,戴着放大镜,正在全神贯注、 小心翼翼地装配细小的齿轮和弹簧。 英格尔德写道:“一个真正的钟表匠要一直有提前一步的知觉。 他需要有一种‘预见’(foresight)的能力,也就是说,当面对一堆散乱的零件时,他能够‘提前看见’一只正常转动的手表。 这样他才能动手装配零件,使它们协调运作, 形成一个运动的整体。 ”[5]由此,英格尔德将设计本质与洞悉物的未来状态的能力联系起来。
应该说, 关于 “预见” 的论述正符合造物理论的时间维度, 两者都反映英格尔德对过程和行动的强调。 如荷兰设计理论家拉斯·斯伯伊布里克(Lars Spuybroek) 所说:“如果设计者想参与到造物过程中, 他不仅要保持开放性,还要有预见性,洞悉未知但可以把握的未来。”[12]我们不妨把“预见”看作一条通向未来的路径, 不过它的终点充满各种可能。 英格尔德把 “预见” 作为设计的本质所在, 因为他觉察到有智慧的设计总是先于制作的。他进一步解释道:“设计不仅要看见事物目前的状态, 还要感知它们往什么方向发展。 我把这种感知能力称为‘期待 性 的 预 见’(anticipatory foresight):这种预见并不是构思和最终制品之间的连接, 而是与这种连接成垂直关系的‘中介’,跟随物质形塑的趋势,使造物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 ”[5]
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 设计就是用行动去实现对于物的未来状态的期待。 如芬兰建筑师朱哈尼·帕拉斯马(Juhani Pallasmaa) 所说,“设计永远是那种对前面未知事物的探索。 ”[13]可以说,设计的“预见”本质与造物的生命特征相互契合, 两种活动都参与物的生命流动过程。 在这种前提下, 设计者和造物者成为跟随者或促成者的角色: 跟随物延伸向前的流动, 或者促成物完成其未来状态的转化。
事实上, 确实有设计师实现这些角色。 例如德国建筑师弗雷·奥托(Frei Otto), 他所设计的膜结构建筑,不仅呈现轻盈和轻巧的造型特点, 还展示膜材料本身的三维形态生长性(见图3,1972)。 与其他建筑师不同的是, 奥托不是简单地先构思后执行,而是一边设计一边建造, 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调整设计, 以探索膜材料的流动性和生命轨迹。

图3 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主场的膜结构建筑
四、结 语
英格尔德曾经感慨, 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质料说” 对西方世界影响长达2 000多年, 设计和造物一般被认为是分离的。 因此, 他清楚造物和设计一体化的观念不在主流思想之列, 自己的造物和设计观未必得到太多重视。 不过, 随着高科技制造材料的普及, 他的理论将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正如贝奈·格索伊 (Benay Gursoy)所言:“在过去十年中数码创作工具和技术高速发展, 我们开始讨论设计和造物一体化的问题。 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会把设计者和造物者合二为一, 把设计的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 ”
此外, 英格尔德的理论还让我们重新思考造物和设计的生态观问题。在他看来, 造物和设计是人主动介入到物的生命流动中的活动, 在此过程中人应该洞悉并整合人—物—技术—环境的关系, 使两者具备有机和共生的条件。 我们不妨设想,这或许将为构建两者生态观念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