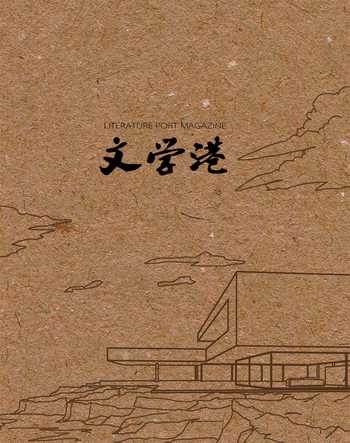东钱湖畔
高丽娜
一
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靠近韩岭一面的东钱湖畔,有一根高大笨拙的烟囱,高约二十米,巨人一般守候在湖畔的一隅。我见到的时候,它从未冒过烟,也很少看到有人走近过它。每每坐着中巴车经过它时,我看着它,觉得它很落寞孤独。但它似乎却稳稳地站在那里,又有些笃定。我就拿不准它到底落不落寞、孤不孤独了。拿不准了,我就不想了。我只欣赏着黄昏的东钱湖。夕阳金黄的光晕里,琥珀色的湖泊就像一个沉睡的公主被时间封住了一般,宁静而充满诗情画意,又似乎带着微微的感动在里面。一个写意般的白影从湖面低低地掠过,发出低沉的鸣叫。靠近湖畔的地方,有几丛芦苇。整齐秀美,笑逐颜开,随风飘荡。
说是不想了,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丑陋的旧烟筒,是什么时候站立在这片柔美阔大的水域边的呢?它静静地伫立着,像在深思些什么,却又是无言的。每次的相遇,我们似乎都在期待着对方,却又做得有些漫不经心。我似乎从来没想着要询问当地人。只是每当远远地从它身旁经过时,我的目光总会穿过它纵横斑驳的裂缝向更辽远的湖面望去。
湖面照例是明净的,静谧的,安详的。偶尔会遇到渔人收网的场景,这幅静态的画会被暂时打断了。对我来说,东钱湖简单而素朴的美,却有一种让人宁静,并能沉下心来,真正地进入一种冥思境界的力量。
二
我还记得,那根古旧的烟囱前是一排排独幢别墅:红顶白墙,一座座环湖而居。它们无门无窗,无人居住。空荡荡的,像一个个独守空房的妇人。时间久了,潮湿的湖水包裹缠绕着它们。一些幽幽的气息就流窜到了每幢别墅里,远远地,散发出一股悒郁之气。
有几丛芦苇点缀在别墅的周围,像它们长长的披肩发。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在秋冬时节看这几丛芦苇。我称它们是我“前世的姐妹”。现在看看年轻时的文字,花哨而矫情。可能,现在也有这个毛病,但我不自知吧?但是,当再一次落笔“东钱湖”三个字时,我心中易泛滥的情感,与喜欢文采的习惯就像多年的老隐疾一样,纷沓而至。
我当然还清晰记得第一次知道“陶公岛”的“陶公”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范蠡先生时的那种震惊。原来,我与历史这样近!近到我有些不知所措!那时我路过东钱湖时,不仅要看旧烟囱,赏芦苇、观晚霞,还会想象着陶朱公与西施一起泛舟在东钱湖的场景:他们讲的是苏州话,还是已经会讲地道的莫枝话了?他们如果真的就隐居在这方水域,会不会和许多夫妻一样,不再相敬如宾,而是有着平静相守的粗粝:也会赌气,也会吵嘴,最后和好?
就是在这样的欣赏与想象里,一晃多年过去了。我用一个北方女子粗粝的内心来感受这方水域隐秘的温情或是热情。我和东钱湖的渊源,也延续在我和东钱湖人之间。我的学生中有许多是东钱湖人。
比如说晓露。她妈妈是村里还是镇里的妇女主任,她爸爸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不记得了。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她爸爸有些文弱。那时候的晓露微微有些黝黑,却有着一股子健康蓬勃之气。她身上有着一般江南女孩子没有的泼辣和飒爽,做事很有条理。高二时我接手她们班当上班主任,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憨直的姑娘。我任命她为班长,她也很快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毕业后,他们玩得好的一帮小伙伴相约着,每逢过年时到我家里来。我招待他们的主打菜大多是大盘鸡、凉拌三丝或火锅什么的,其他的就是零零碎碎的一些小菜了。他们特别喜欢吃大盘鸡里炖得绵软的土豆块,当然鸡块总是抢得精光。倒是加在里面的宽面条每人吃几条后,就吵着要米饭吃。每次他们一来,整个楼道里都响着他们青春的嗓音。无论是在明楼那个逼仄的陋室里,还是后来搬到了波波城,大家欢聚着快乐着聊着吃着。
有一年的夏天,晓露给我送来了东钱湖水上乐园的三张门票。那一年,东钱湖水上乐园还没发生过后来小孩子卡在水管里没有出来的事。我说,心意领了,让她和朋友一起去玩。她说票是他们村人的福利。她已经玩过了,还说让我们带着依依妹妹一起去玩水。依依那时正是爱玩的年纪,开心地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我只记得在酷暑下,水里果然清凉无比。刺激也是一浪接一浪地来。那是一个美好而难忘的暑假。
大概是两三年前,晓露来看我,面色不像往日那样明朗。我们随意地聊着,当我问起她的父母还好吗,晓露面色悲凄:“我爸爸在鄞州人民医院住院,情况很不好……”她说她刚从医院出来,想来看看我。我说我去看看他,晓露说,她回去问问。结果第二天晓露说,他爸爸说这几天他形象特别不好,见高老师不礼貌,等他身体好些再去。我说好。没想到几天后,晓露说,她爸爸已经走了……
一切快得如同一场秋风中的银杏叶。我都没反应过来时,一个人就这样又被吹回到了东钱湖里。我似乎才慢慢地觉察出了东钱湖人骨子里的那种注重细节的内心和苍茫的气质。
我到了新單位后,晓露和冯坡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冯坡也是东钱湖人。他颇为瘦削,说话很温柔,文字却很是有力道。我们原来单位的大排是很有名的:有皮有骨有肉,肥瘦相间;不光个大,关键是烧得透香:酱汁调料腌制得够入味;浓汁收后,酱油的浓香,肥的地方油而不腻,精肉的地方也不柴;火候掌握得是刚刚好!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学生都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食堂去抢着打大排,晚一点总是抢不到。所以,最后这节“吃饭课”,学生们最讨厌老师拖课。但没有办法呀,铃声响起时,文科老师后面的半句话可以随时咽回去,但理科老师已经推算到了最后的两个步骤,如果今天不讲完,明天还是要重新推算,既花时间,学生又没有掌握最后的要点,所以就会再拖个一两分钟把它讲完。这对于学霸们没什么,但对于不是学霸、又特别想吃大排的学生来说,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有时,叫冯坡回答问题时,同学们会发出善意的笑声。我爱怜地对他说:“一定要多吃大排!你太瘦了!”
高三毕业前,冯坡在他写给我的《两年须臾 气息不朽》一文中曾写道:“回想起那段青春的路程,是温馨的,荣耀的,刻骨铭心的。我们相逢的那段路程,你提着灯,我借你的光前行,你为我瘦削的肩膀披上你的斗篷,指引着我前行。”当我读到它时,感动自不必言说。我有幸在他们的青春时期成了他们的倾听者。我陪着他们走过了青春年华,在陪走的过程中,倾听着岁月的风声静静地敲打着我日渐苍老的容颜。但彼此的记忆里还拥有着对方,这就够了。
璐也是东钱湖人。那时候刚开始她是住宿生,后来就申请不住宿,每天公交车来去。早上公交车时间不太固定,她偶尔会有迟到,显得时间很紧促。我和她妈妈的交流就多了起来。一次我让大家写随笔,看到她写的东钱湖的庙很有味道。特别是她的字很漂亮,一行一行如砖块一样,整齐地摆放在素洁的笔记本里,真是舒服极了。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的字,还有关于她的点滴。当然,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她笔下东钱湖的庙宇。她美好的童年回忆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记得当时我打印好后,让两个年幼的同学欣赏她的文章,小伙伴们一下子就知道她的文章写得好。后来我投稿给《未来作家》。那是我第一次给学生在这个刊物投稿,当接到编辑老师的电话,让我写点评时,我像一个初次学写作文的小学生一样,认真而充满了神圣感。
璐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2014年暑假7-8合刊上了。知道消息后,她和她的妈妈开心极了。那时距离她高中毕业已经一年了。离开小镇后半年,快放寒假了,璐还到家里来给我讲这段时间的得失,并带来了肥美的咸蟹和笋干,说她妈妈还问我城里的学生乖不乖。
如果你从宁波出发,前往东钱湖的话,沿着东钱湖走一段时间,韩岭那里竖着高高的教堂尖顶,一下子把辽阔的天空分割开,将人的视线从缥缈的仙境拉回到人间。从韩岭开始的那一段公路是曲折而又起伏的,但旁边的景色也是最美的。田地和山上的植被全都像童话世界里的一样,厚墩墩、毛茸茸,似乎可以在你的心底温柔地挠你痒痒;在靠近小山的地方,还竖立着一间粗陋的茅草屋。车子到这一段都会比较谨慎,司机都是一再地踩着刹车往前开的。这一段路还比较窄小,想超车很难,因为顺着山转弯,后面的司机是很难看到对面的车子。
再往前走,公路就不再弯曲,也就到了璐住的俞村。记得璐毕业后的第二年寒假,她妈妈一定要请我去她家里,让我给璐好好叮嘱一定要考会计本科。原来她还有个妹妹。妈妈平时在家帮亲戚做工,工件可以领到家里来做。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对璐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子女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找对象也容易些。她说亲戚家的孩子学了会计专业,现在工作很好,收入也很高,所以就希望璐在学校里别荒废了学业,进行专升本考试,希望她以后能学会计。后来我们还去爬了古道。光滑的小石子铺成的小径,石缝里钻出小小的新绿,旁边是江南的冬天一些赭色的杂树,斑驳而饱含生机。
旁边的璐一再地提醒我:“您慢点,小心点……”
后来,璐果然考上了本科,学校还不错。她还专门给我报喜,语气里是遮掩不住的兴奋。如今她在宁波一家公司做会计。
三
一次,晚上去湖邊,看到湖边系着一条小船,周围无一人,有大风呼啸而过。就想起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这是难得的清静时光,没有那么多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匆匆的脚步,更没有那么多贪婪的目光。
我颇喜欢王应麟笔下的《东钱湖》:“湖草青青湖水平,犹航西渡入空明。月波夜静银浮镜,霞屿春深锦作屏。丞相祠前惟古柏,读书台上但啼莺。年年谢豹花开日,犹有游人作伴行。”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竟然不知什么叫“谢豹花”。百度了后,才知道它是杜鹃花,在北方它叫山丹丹花。
东钱湖因为有着王安石、史浩、王应麟等人的心胸和诗句,所以从不露怯。它的内里隐藏着沉静倨傲的心,巍然峭岸的外表里有浩然之气。
雪后的东钱湖,仿佛还原了本色,一片素雅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