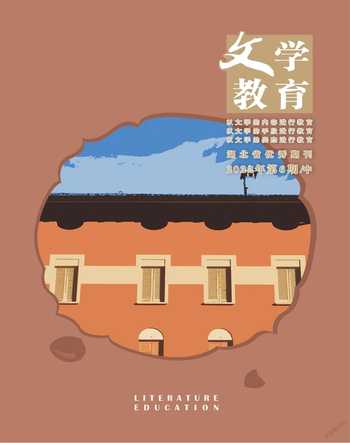孙频《乩身》的现实主义解读
刘雅琪
内容摘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女作家孙频的小说《乩身》进行解读和分析,作者以冷静的视角切入最底层社会,将社会和人性强化集中于一点,两位主人公的命运极具震撼的力量,揭示了底层人的悲剧,令人难忘。不得不说,作品虽然色彩阴沉压抑但却富有张力,也因此,发现和深入发掘其中,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关键词:现实主义 孙频 《乩身》
孙频,2004年开始创作,已发表了近200万字的小说,因其冷峻的写作模式以及对人性的深刻透视,被评论者称作是当代的张爱玲。孙频是80后女作家,她的创作总是体现出跨越青春写作的苍凉与凛冽,与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风格非常相近,她曾谈及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50后女作家的小说,并被她们严肃的文学观和鲜明的女性书写所影响。也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有许多的底层女性。而在外国作家中,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孙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正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指出的:“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同时作为“80后”的女性作家,孙频也不同于韩寒、郭敬明这些典型的80后作家,她有着自己的独特创作领地以及表达方式。
孙频非常善于描写人们的卑微与孤独。无论是生活于乡村抑或城市,她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卑微地生活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孤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抱残守缺,而是试图做出抗争。比如在《乩身》中她写到:“他是一個被阉割了的男人,而她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女人。他想做男人而不得,她却是想做女人而不得,他们是两个在人群中丢失了性别的生物,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亲人。”
相对于其他作家而言,孙频小说中人物的抗争是病态的、暴力的,通过这种病态的、暴力的抗争手段而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在《乩身》中,则表现为当马裨和自焚,自虐的行为来表达抗争。)孙频的这种写法,既有她对生活在吕梁山的人们生活状况的耳闻目睹,亦与她的阅读经验相关,从而使得她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乩身》是孙频的中篇小说,乩读“机”,乩身,就是通过神鬼附体占卜问吉凶。《乩身》的主要内容:为了避免被别人欺侮,因生病失明的常英被捡到她的爷爷当成男孩来养育并被改名为常勇,常勇在爷爷死后艰难地自食其力。那个原先偷盗后来蹭死人饭的杨德清也被人嫌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互相抱团取暖,他们做求神祭祀的马裨、占卜先生,最后凄惨地离开人世。
孙频的这篇小说主要是从我们平常生活所触碰的点来写就我们所处时代的最深处,是由底层的女性视角去描述隐藏最深的疼痛,试图从人的精神里身体里挖到一个最深最疼痛的地方,然后把这份疼痛无限放大。这些从人心里长出来的丑恶、恐惧、无助深深刺痛了每一个看到的人。
一.典型性
1.典型环境
小说中常勇的命运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命运”不是因果,不是报应,命运是一个非常大而神秘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命运是虚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一种东西起着跟命运相似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比命运的力量更大呢?
命运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词汇,它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如果我们认为作者把剧中的悲剧看作是由于残酷的“命运”导致的,这是不对的,应该改成“社会悲剧”,这才是能够比拟命运而又真实存在的力量,常勇的命运正是社会环境整体的悲剧造就的,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义。
(1)地理环境。交城这个地方,这里地处吕梁东边,被山川阻隔,生活在小县城里的人们的卑微与苍凉。作为内陆省份的小县城,它自身的闭塞酿就了幽深却也逼仄的世界,使得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无来由地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人们似乎还沉溺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却又单调的生活轨道中。因而,他们的生活境遇及其精神状况还带有那种血腥野蛮的痕迹。
(2)文化环境。常勇生活的晋中小县城保留了部分的傩文化每逢过年的时候人们就要在成汤庙迎神祭祖,还要二十八宿天神来值日,一般赛期为三天,按照历书排列,选定二十八宿中的三宿当值。为了表示对迎神的虔诚,也为了人与神之间的畅通无阻,每次迎神赛社上都需要几个马裨。马裨是代表神来驱鬼辟邪的,扮演马裨的一般都是最底层的人。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不洁的东西往往能抗拒其他不洁的妖魔鬼怪,只有用不洁的底层的人才能镇压那些更邪恶的东西。马裨在迎神赛社中要表演神灵附体,神灵附体后的马裨不同于常人,所以在表演中,马裨往往要用一些自残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真的是被神灵附体了。有的马裨用六七寸长的匕首穿透自己的手腕,有的马裨用七寸长的钢钎刺穿自己的两腮,还要抡着两米长的钢刀,为上香会开路。还有的马裨用带环的钢刀往自己前额上乱砍,满脸是血地往前走。
2.典型人物
经典马克思主义创作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立志把社会、历史、人生境遇,尤其是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从里到外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来。
《乩身》这个故事虽然不算太长,但完整的展现了常勇的社会生存境遇,从生下来被抛弃,到被爷爷收养,从被逼着成为男人,到爷爷死去以算命为生,从偶遇杨德清到杨德清之死,紧密相连的故事全面地反映了常勇被压迫地一生。恩格斯在评论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时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孙频在对典型人物的设置上可谓别出心裁,她选择的是很有年代特色的苦难人民形象。
二.整体性
《乩身》是孙频的中篇小说,作为中篇小说里的佳作,它结构完整,寓意深刻,最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所表达的内容含有内在的整体性。《乩身》的整体性特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常勇个人成长时间上的整全性,二是常勇社会身份上的多样的整全性。
1.成长时间上的整体性
常勇在一岁半以前其实是叫常英的,一岁半时候的一场高烧把她的两只眼睛都烧瞎了。
小说中常勇被比作是嫁接在常英身上的一株植物,常英则是“一截枯树桩”,常勇从这“枯树桩”里,就着常英的“血液”,从她的“身体内部”长了出来。并且“居然也活了二十二年”。但无论他向着空中长出多高,他终究是从她的“身体内部”长出来的,终究是一个女子而非男子,这也预示了后文的悲剧。
在常勇十三四岁时,作者交代了常勇来月经时的事情。常勇的爷爷他告诉她一定不能把月经带晾在院子里,一定不能被人看到,而只能“藏到最阴暗的角落里”,只有这样她才不会被别人发现是女人,她身上不能拥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因为任何一点女性特征都可能把她置于死地。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特征成为了她的一种疾病和耻辱。
常勇十八岁时长成了交城县里一种崭新的人种,“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人”具体表现为留男人的短发,穿男人的衣服和松紧口布鞋。但是她有着女人才有的尖细的声音,“胸部虽然被束平了,但那个肥大的屁股却是搁哪儿都要自己跳出来跳进人们眼里的,男人能长出这么肥的屁股?真像是嫁接在枯木上的一朵繁花。”
作者从时间顺序上罗列了常勇的成长经历,包括:一岁,十三四岁,十八岁等。展示出了常勇所处的生活悲惨之境遇,作者的这种描述,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实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很多细节也可以看出作者所赋予的内在整体性。
2.社会身份上的整体性
我们知道,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份描写非常重要,而多重的身份描写更是能体现出人物形象的丰满和整全。对于常勇来说,她所拥有的不同身份,不仅完善了她独具特色的个人形象,而且也间接的揭示了她人生的悲剧。
小说中对常勇个人存在的刻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作为瞎子的常勇。常勇的眼睛因幼時生病而失明,这是她一生悲剧的开始。她因此而被父母抛弃,又被好心的工厂大爷所收养,残疾人,就是她的第一社会身份。
常勇的第二重社会身份是被迫成为男人的自己。她的第二重身份跟第一重身份其实也有莫大的关联,爷爷之所以严厉的逼迫常勇适应男人的身份,正是因为盲人的常勇如果被发现是女人就无法保护自己,任何一点女性特征都可能把她置于死地。为了成为男人,常勇付出了很多,为了从根子上杜绝女儿身,她被要求从小站着小便,她像男人一样撒尿,她不能戴胸罩,常年用布带给自己裹胸,把乳房压平压实了,恨不得“像夯地基一样把这两只乳房夯进肉里去”,她也不敢拥有任何的女性特征,因为这会害死她。常勇的第二重社会身份是一种极度的挤压,是为了生存而走向畸形的开始。女性成为了常勇的一种疾病,一种耻辱,男性才是常勇的“真实”身份。
常勇的第三重身份是作为孙女的常勇。常勇在与爷爷的相处中,无疑是开心的,小说中整体的压抑的格调也掩盖不了这一点。因为爷爷是真的爱常勇,即使爷爷常常严厉的让常勇假扮男人,也是为了她好,这时的常勇是幸福的常勇,还在爷爷有力的保护中,是一个静待转变的常勇,因为在爷爷死后,她就要“变成”女人。文中很多处都体现了这一点:人们每次对常勇的性别进行猜疑时,爷爷就把它拎到街上,说“那是我孙子,我们爷俩到西头走走”。
常勇的第四重身份是作为算命先生的常勇。算命先生是爷爷给常勇准备的职业,为的是常勇能够在自己死后勉强生活下去。算命先生的社会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常勇后来发疯的条件,作者把算命先生的角色赋予在常勇身上,有一种巧妙地意味,一方面这是常勇发疯地某种符合,另一方面,又是在讽刺当时人们地愚昧。比如:“她知道算命不是人应该干的事情,她只能算半截人,另外的半截只能是介于鬼神之间的一种生物。”常勇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而成为算命先生,正是接近鬼神而脱离人的一种方式。
常勇的第五重身份是作为自我的个体。小说中描写了常勇第一次给人算命时候的事情,她在装神弄鬼完后得到了她的报酬,别人留下的一张钞票,常勇捏着那张钞票,突然笑了起来,她笑自己刚才装神弄鬼,这是她自身对于给人算命的一种不屑与抗拒。作为一个不得不算命谋生的人,却笑自己装神弄鬼,这正是作为自我的常勇和被压迫的常勇之间的鲜明矛盾。
作者通过塑造常勇的多重身份,更鲜明地刻画着这个人物,但身份地多样化并不能说明常勇这个人物地分裂和破碎,作者将多重身份之间地联系内化在小说中,具有很强地整体性意味。
三.真实性
纵观全文,一个核心的事件是常勇之死。小说中提到,常勇身上发生的一切,是她的“命”,这是作者的一种反讽,常勇的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命”。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常勇死的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原因比较明显,就是常勇住的那条街要强拆了。县里出了文件,要求老街的街道拓宽重修,临街的老店铺老宅子全部要拆掉,包括常勇的铺子,常勇于是以死相逼,用生命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第二原因内涵在整篇小说中,就是杨德清的死和常勇所受的苦难压垮了她。这两个原因都是对现实比较真实的描写,强拆事件在现实中真正发生过。在小县城封闭愚昧的社会中,因为人们观念的狭隘而对女性的压迫也经常发生,孙频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塑造常勇的生活,也借此塑造了她的命运,这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反应,也是对现实中不好的一面进行的批判,意义深刻。
文中还有一处描写非常精彩,是还未过世的爷爷教常勇数步数,教常勇量出去麻油店要几步,去杂货铺要几步,去粮店要几步,去车站要几步,包括去县委大院要几步。这一段描写非常真实,贴合实际,早年间,对于盲人来说,还并没有什么专门的学校和便利设施,只能用这种粗浅和直接的方式,教会盲人生存。这一段也体现了爷爷对常勇真实的爱,交城的阴郁,掩盖不了爷俩的浓浓亲情,即使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四.阶级性
《乩身》这篇小说虽然篇幅比较短,但是生动的表现了常勇充满悲剧的一生。常勇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无产阶级人民在特定时代命运的整体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常勇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把一个瞎子带大是常英的父母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当时都在铅矿上工作,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一个小瞎子。所以,常勇的父母决定放弃常勇,把她扔掉。在作者的描写中,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亲情,放弃自己的孩子,这无疑是一种底层人民的悲哀,面对生活的压迫,珍贵的亲情变得随时可以抛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说已经被逼的失去了人味儿,成为这座小城里的一块儿腐肉。
其次,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常勇在失去爷爷后的悲惨生活,没有什么人找她算命,爷爷留下的钱也没了,为了不至于饿死,每天晚上到了十一二点,她就去城边的垃圾场上找吃的。对于一个盲人女性来说,又是生活在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常勇一边饥寒交迫,一边又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以免被欺辱,这种生存状态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是由什么导致的呢?是对女性的敌视和不公平导致的,是社会阶级残酷剥削导致的。
文中杨德清在劝常勇去当马裨的一段话令人深刻,他说他和常勇是这个县城里最烂、最不干净的人,算命和神灵附体不过就是给人看的杂耍,只不过算命这杂耍不用流血、不用死人,而马裨这杂耍是要用命来玩的。这里作者借杨德清之口诉说了算命和马裨的真相,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常勇和杨德清因为生活所迫又必须去当这个马裨,即使伤害自身,这是小人物的悲剧,是底层人的命运。
文中还有一段描写乩身的事情,杨德清曾听说,只有被神灵附过身做了乩身,人们才会从心里敬畏,才会有人来找你算命,才会把你当神供着。他说文水的一个女人做了乩身后,当地人和当官的都开着小车来找她算命,她现在住着洋楼开着小车,每天有人把她当神仙供着。
作者阐述这个女人的例子,鲜明地表现了底层人民的无奈和悲惨,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在生存资料稀少的年代,想吃饱饭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一件充满黑暗的事。
就小说本身而言,《乩身》让我们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小说构思独特,兩个主人公常勇与杨德清就像两条相互交织的线,两个人的交织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互补,都互相从对方的身上找到自己所缺失的东西——一个是做男人的能力,一个是做女人的能力。两人的命运极具震撼的力量,作者以冷静的视角切入最底层社会,将社会和人性强化集中于一点,揭示了底层人的悲剧,令人难忘。不得不说,作品虽然色彩阴沉压抑但却富有张力。
参考文献
[1]刘涛.入乎张爱玲内——一论孙频[J].创作与评论,2013(03):47-50.
[2]阎秋霞.孙频小说叙事研究[J].文艺争鸣,2012(09):122-124.
[3]康馨.从“自我同一性”看“80后”写作主题的精神变迁[D].山东大学,2017.
[4]唐诗人.极致叙事与怜悯之心——孙频小说论[J].文艺评论,2017(12):42-50.DOI:10.16566/j.cnki.1003-5672. 2017.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