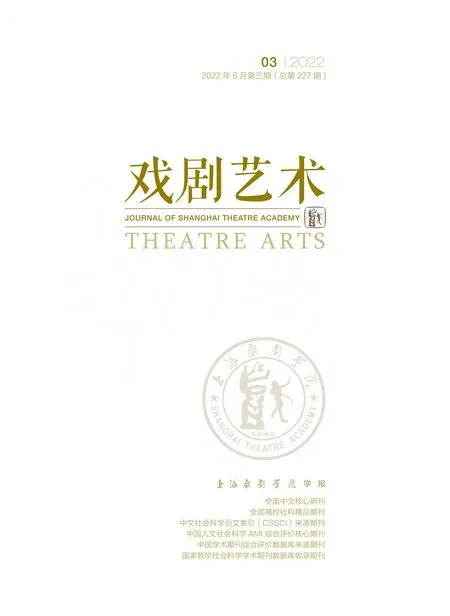抗战剧本选与沈蔚德《民族女杰》考论
——从沈氏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四封信札说起
高 娜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戏剧艺术界在日益紧张的形势之下,形成了支持和鼓动抗战的统一战线——先后在上海和汉口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组成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在前线及大后方宣传演出,并定于每年十月十日举办中国戏剧节。这一时期的戏剧活动以其最大的宣传效能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形成“一条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战线”。戏剧的抗战宣传作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战时戏剧教育功能的实现,政府确立了明确的工作目标、设置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制定了详细的教育方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建立完整的战时戏剧社会教育体系”。国民政府推行戏剧教育的主要机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其主要负责协同其他戏剧教育的行政机构(如中央宣传部的电影戏剧事业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行政院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推行与管理戏剧出版、上演审查、剧场管理和戏剧教育业务。之后,教育部拟定并修正通过的《推进戏剧教育方案》在“实施要项”中对“话剧之改进”提出多项要求,其一便是“评选并推荐优良剧本”,正式将剧本创作与出版纳入战时社会教育的范畴。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沈蔚德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多封往来书信,呈现了教育部于1939年组织抗战剧本选拔、审查及出版的诸多细节。此次剧本选拔活动,使得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国立剧专以及曹禺、洪深等剧界翘楚多方联动,这不失为一个考察抗战时期戏剧政策、图书审查及戏剧观念的生动案例。在寻绎新见史料的基础上,一方面,尽可能还原社会教育司于1938—1941年间发起、组织“征选抗战剧本——剧本审查——演后修改——剧本出版”的完整过程,以管窥国民政府将戏剧纳入社会教育范畴之后的具体举措与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则在抗战戏剧与女性戏剧的研究框架内,重新审视“抗战剧本选”的桂冠之作《民族女杰》(原名《新烈女传》),兼察女剧作家沈蔚德在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及其剧作中所浮现的女性意识与立场。
一、 《民族女杰》评选、审查与出版始末
“抗战以来,剧运随着抗建宣传和普及民众战时教育的迫切需要,而得到广泛的开展”,使得“‘剧本荒’成了一时普遍的呼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抗战戏剧的观众主体的变化直接相关,“战前以城市为中心,以市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要观众,亦以其生活和心理的描写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话剧”跟随着各类戏剧团体深入广大农村,戏剧的高度流动性对剧本的创作主题与内容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所谓的“剧本荒”其实是指具有大众化与教育性的“好的剧本在闹荒”。基于此,国民政府多次开展了征选优良剧本活动,“除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征选剧本,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奖励剧本而外”,教育部也分别在1941和1942年公开征选过历史剧本和各种革命纪念节日剧本。而1939年由社会教育司组织的“抗战剧本选”则以其征集剧本之多、征选范围之广,成了抗战时期官方选本活动的集中体现。另据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一则史料显示,教育部还在1943年组织过“三十二年度优良剧本选”,参选者包括曹禺、老舍、郭沫若、陈白尘、沈浮、于伶等剧界名人,头奖《桃李春风》(老舍、赵清阁)奖金高达两万元。从剧本选拔的组织次数和酬金额度,足见国民政府对于用戏剧推动社会教育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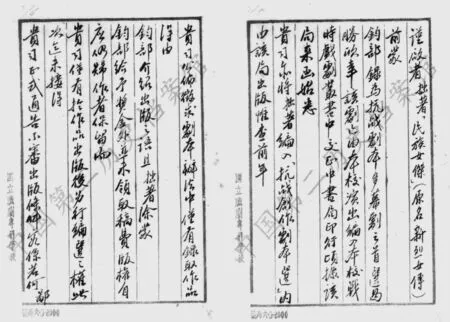
沈蔚德亲笔函信(部分)
从档案资料来看,社会教育司早在1938年底就开始筹备此次抗战剧本选拔,其出台的《教育部征求抗战剧本办法》先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下简称国立剧专)拟定,后经社会教育司修改并定稿。《办法》规定应征剧本不出下列范围:
(1) 阐明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提高人民为国家民族效忠之信念者。(2) 鼓励各界同胞化除一切成见,澈底精诚团结统一意志,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实现抗战建国之国策者。(3) 暴露日寇之暴行及其野心者。(4) 说明全面长期的抗日战略,以坚定人民最后胜利之信念者。(5) 提倡生产建设节约,献全国民兵役义务劳动,出钱出力以增强抗战力量者。(6) 表扬忠烈,铲除汉奸,消灭苟安与颓靡思想,以巩固后防者。(7) 其他有激动民心裨益于抗战建国之壮烈史迹或有益于世道人心之现代故事者。
此次抗战剧本选拔原定于1939年8月告结,然因“重庆被敌轰炸后,各机关疏散,有一部分评选委员他迁或公务繁忙,未能如期将应审剧本审毕送还,以致迭相延误”,直至1940年3月才完结。“抗战剧本选”评选委员会共由13位评选委员组成: 国民政府教育部前常务次长张道藩为主任委员;余上沅、曹禺、黄作霖、赵太侔、洪深、阳翰笙、王平陵和李朴园负责评选话剧剧本;王泊生、朱双云、舒舍予和卢冀野负责评选歌剧剧本。各委员从剧本的剧情、结构和台词三点进行评分。另外,为保证抗战剧本征选活动的公平性,《教育部征求抗战剧本评选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定“委员对于评定剧本之评语及分数应严守秘密”,“委员姓名亦不对外公布”,同时“初选及复选每一剧本均以经委员三人之分别评定为准则,由主任委员就应征之剧本编号分配之。但每一委员不得兼任统一剧本初选及复选之评定”。可见,无论是从抗战剧本评选委员会的“专家阵容”还是匿名的“三阅三审”制的评选规则来看,此次剧本选拔都是较为严谨与公正的。截至1939年3月底,此次“抗战剧本选”共征集剧本162种(包括自请抽回1本、无台词不参与审查4本、已发表不审查3本),其中多幕剧75种、独幕剧67种、歌剧12种。1940年3月23日,参选剧本经“三阅三审”后终告完竣,沈蔚德的《新烈女传》以92分的终审成绩,超第二名《自由的兄弟》(潘传烈)2分,摘得话剧组桂冠。
沈蔚德得知《新烈女传》获奖喜讯,其间正随国立剧专在重庆劳军公演,她想借机当面领取剧本酬金,而致函一封至社会教育司询问相关手续。现将全函迻录如下:
谨启者:
蔚德此次随国立戏剧学校来渝公演,见报始悉拙作《新烈女传》已蒙入选,无任感愧。惟迄未收到通知,想已寄往江安矣。蔚德拟乘在渝之便,当面领取奖金,未知手续若何?可否请该项通知补发一份,或详为示知,倘可领取,请汇至城内以省手续。如需人证明者,则余校长上沅先生可为作保。再者,关于拙作之出版问题为何决定,原稿是否可由著者先行领回?蔚德在渝之日无多,约本月十九号左右即返江安。尚请早日示复,以便赶办各种手续。来教请寄重庆瓷器街大楔子口大华饭店二〇七号,国立剧校余上沅校长转交。
此上
社会教育司
沈蔚德谨上
四月十一日
4月17日,社会教育司寄出简复,称《新烈女传》的奖金已按原地址寄送,而关于剧本的出版问题,将由社会教育司汇印剧本选,原稿暂不退回。应该说明的是,信中提到的“汇印剧本选”,是与遴选抗战剧本配套的举措——社会教育司原定在各剧本试演之后落实编选《抗战剧本选》一事,并于10月17日将合作出版方定为正中书局,委其负责剧本的出版事宜。次年1月4日,社会教育司(甲方)与上海正中书局(乙方)签订《抗战创作剧本选印行合同》,此项合同对于“稿费”和“版权”分别在第四、五条作出详细规定:“剧本选各稿,业经甲方分别给予奖金,乙方当照版税办法印行,分别订约于出版后,依实销部数,照正常定价抽取版税百分之十,每年两次结算,汇由甲方转交各原作者”;“剧本选各册版权为乙方与原作者共有,每册发排时,双方订定契约,原作者不得将稿本全部或一部在他处出版或发表”。
抗战剧本选公布结果后不久,社会教育司即向国立剧专和山东省立剧院发放通知,要求以上获奖剧本,先由国立剧专和省立剧院“先行试演,所有试演结果,应分别拟具意见报部备夺”。此项决定是国民政府戏剧审查政策之一,但从戏剧的可观性来说,同样必要。一方面,戏剧是舞台艺术,需通过舞台演出让观众验证效果;另一方面,各剧本也可根据演出实际反响,对剧本诸细节进行有效修整。1940年9月12日,国立剧专向社会教育司呈交《教育部应征得奖剧本试演报告》包含“试演手续”“修正范围”“修正本之编定”“总评之决定”(甲、修改意见择要;乙、试演总评)四大部分,其中对十五种话剧剧本的修改意见十分详尽。该报告对《民族女杰》评价很高:“剧情结构人物描写以及对话均臻上乘,不愧为抗战剧中之佳作”,其中八处“微瑕”则在“修改意见择要”一一列举出来,并将修改后的《民族女杰》拟定为国立剧专公演剧目。10月27日在《国民公报(增刊)》(成都)刊载的《一个荣誉演出——〈民族女杰〉》(余上沅)和《〈民族女杰〉导演话》(郭蓝田)两文应是对试演成果的评述,然因资料散佚,笔者无缘得见。不过,从题目来看,校长余上沅对该剧的评价应是很高的。或许也正因如此,剧校遂将其定为“本学期第一次公演剧本”,11月2、3日由郭蓝田导演的《民族女杰》作为国立剧专第35届公演剧目正式上演。
《民族女杰》公演后,由沈蔚德接续修改。1941年1月15日她主动致信社会教育司函询《民族女杰》编入《抗战创作剧本选》的版权事宜,并提出“每千字以十元计”的稿费要求。该信寄出一月后,并未得到社会教育司回复,沈氏“深以为念,诚恐前函或已遗失”,所以将原信重新抄录并于2月20日再次寄出。沈蔚德函示: 她对于《民族女杰》编入《抗战剧本选》之事“极感荣幸”,但希望社会教育司能将剧本的版权费“于付印以前,一次付清,否则敢恳暂缓编选”。可见,她对《民族女杰》这部剧作具有较高的创作自信,而且很重视剧作版权。全函迻录如下:
谨启者:
拙著《民族女杰》(原名《新烈女传》),前蒙钧部录为抗战剧本多幕剧之首选,曷胜欣幸。该剧已由本校演出,编入本校“战时戏剧丛书”中,交正中书局印行。顷据该局来函,始悉贵司亦将拙著编入《抗战创作剧本选》内,由该局出版。惟查前年贵司公布征求剧本办法中,仅有录取作品得由,钧部介绍出版之语,且拙著除蒙钧部给予奖金外,并未领取稿费,版权自应仍归作者保留,而贵司仅有于作品出版后,另行编选之权。此次迄未接得贵司正式通告,示审出版条件究系若何?鄙意贵司既欲代为出版,自属极感荣幸之。惟以手续关系,拟请先将拙著版权收买每千字以十元计算,拙稿五万字,共需稿费五百元,请于付印以前,一次付清,否则敢恳暂缓编选。俾本校得以先行出版,盖拙著既经本校演出,例须编入本校丛书之中。而本校演出本,系根据实际演出情形订正,出版时应以演出本为宜也。为何之处?请即,裁示为祷。
此上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沈蔚德 谨上
赐覆请寄江安本校 转
不久后,社会教育司对于沈氏所说的稿费和编选国立剧专“战时戏剧丛书”两个问题一一回应: 首先,《民族女杰》是“本部征求创作,业经试演修正,自应依照本部计划,编入《抗战创作剧本选》,一并付印”,但是剧本的版权仍属作者,并由印行书局抽送办税,等到印行抽税办法签订后,会一一寄给作者;其次,拒绝将《民族女杰》编入国立剧专战时戏剧丛书,一因国立剧专未将此事提前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提请,二因《民族女杰》虽在国立剧专先试演后公演,并不代表此剧本归国立剧专所有。沈氏对社会教育司各项回复,没再提出异议。数日后,她再次致信社会教育司提议在《民族女杰》正式出版时,应以经过公演效果验证的“演出本”为准。社会教育司对此表示同意,但此前的“修正本”应“存本部备查”。全函迻录如下:
谨启者:
接读二月十八日第〇六二三五号来示,敬悉一是。拙著《民族女杰》一剧既经决定须由贵司出版,鄙人无函遵命,惟付排稿本究以何种为准,深觉有考虑之必要。按贵司所保存者,系经国立剧校试演后之“修正本”,但其后经剧校正式公演时,又就实际公演效果,由鄙人复加修改,而成为之最后订正之“演出本”。两两相较,后者实属更为完善,更切实际。故鄙意愿以此“演出本”为准,兹该“演出本”已案存于正中书店,除另函该书局根据“演出本”付排外,并请贵司亦对该局加以通知,而将上项“修正本”作废退交鄙人。为何之处?烦即查照,复示函致。拙著再纠迂延,而得早日问世,于愿是矣。
此上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沈蔚德 谨上
二月廿七日
1941年8月,《民族女杰》正式印刷,定价一元二角。12月12日,书局寄给沈氏《民族女杰》样书一册、优待券及勘误表一份。次年1月20日,沈氏因“购书优待券”、出版契约和样书数量等由,给社会教育司写了第四封信,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暂未得见社会教育司对该封信件的回复。不过至此,“抗战剧本选”的选拔与出版过程已基本呈现。兹将函信迻录如下:
谨启者:
大函颂悉,所案拙著《民族女杰》样书一册暨作者购书优待券一币,均已收到。惟该优待券上注明为残痕君之《通缉书》,想系误投当。因鄙人急欲购买《民族女杰》,已将该优待券直接案交正中书局,嘱其补发,兹为顾及手续起见,拟请贵司再为接洽。无论更换或补发,俾鄙人得凭券购书是幸。再者,刻接正中书局来函,诏拙著契约已交贵司查。契约原为作者权利之保障,按理应归作者自己保存用,特来函恳请,即行挂号案下为盼。
此致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沈蔚德上
一月廿日
再者,书局赠送作者样书,按诸出版略,常例少则十册,多则二十册,均于契约中载明顷者,鄙人仅得一册,不知何故?请即再向正中交涉,嘱其照数补发案下。倘贵司欲保存若干册者,当由鄙人另行奉赠也。
此致
社会教育司
沈蔚德 又及
二、 “两种描绘”: 沈蔚德基于现实主义的女性塑造
沈蔚德(笔名维特、沈维特)是国立戏剧专科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她“1935年进国立剧专话剧科,1937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编剧’‘戏剧理论’和‘表演基本训练’”。抗战爆发后,沈氏在迁往江安的“剧专研究实践部从事研究工作,兼任曹禺助手,写读剧报告”。在教研工作之外,她潜心创作并参演话剧。沈蔚德活跃于公演舞台之上,参加过多个名剧的首演,包括贝克《群鸦》中的费太太(1936年5月底)、《雷雨》中的鲁妈(1938年7月重庆初演)、《蜕变》中的丁大夫(1939年秋冬间),其演技备受好评。而沈氏的戏剧创作则集中在抗战期间,包括独幕剧《自卫》(1938)、街头剧《我们的后防》(1940)、三幕剧《女兵马兰》(1940)、四幕剧《民族女杰》(1941)及五幕剧《春常在》(1945),早前她还翻译过苏联剧作家凯泰耶夫的三幕喜剧《方枘圆凿》(中华书局1937年版)。在同仇敌忾的全民抗敌时期和文化界以民族国家为集体修辞的特殊时期,身为女性的沈蔚德通过戏剧创作,主动表达了抗战话语中的女性立场,以及女性意识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连接。其实,放眼战前及战时戏剧艺术界,女剧作家都是极少数的存在。正因如此,她们的声音才更为可贵。对此,戏剧家田禽表示:“假如没有像赵清阁,赵慧深,沈蔚德……这几位女剧作家活跃于战时剧坛,那么,在这个大时代里女性以写剧生涯服务于抗战的,可就更显得冷清了!”在创作之外,作为国立剧专研究部一员的沈蔚德,紧随剧专“研究戏剧艺术”“辅助社会教育”的办学宗旨,并在研究部“近半年来之研究实验,及其参加各种演剧工作所得”的基础上,负责编选了“战时戏剧丛书”两种,分别是《新型街头剧集》(丛书之三,1940年1月正中书局初版)和《抗战独幕喜剧选》(丛书之六,1940年5月正中书局初版)。此两种书目集聚了抗战时期街头剧与独幕喜剧的上乘之作并体现了特定时期的戏剧审美取向,也彰显了戏剧研究者沈蔚德对时代脉搏的掌控力。而其剧作《民族女杰》经由张道藩、洪深、曹禺等权威评选委员的层层筛选,在百余种抗战剧本中突出重围这一事件本身就已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另一则史料显示: 1942年6月,为深入戏剧在民间的教育功用,教育部令国立编译馆编选民众读物和《话剧丛刊》等书目。在国立编译馆呈送教育部的《话剧丛刊编辑办法》中,沈蔚德是拟约作者名单中唯一的女剧作家,与此并列的皆为剧界颇有名望的剧作家(张道藩、顾一樵、余上沅、曹禺、老舍、熊佛西、洪深、吴祖光和老向)。以上诸点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身兼戏剧教育家、戏剧研究者和戏剧创作者等多重身份的沈蔚德及其剧作《民族女杰》的有力基点。
余上沅曾在《民族女杰》单行本的《序言》中着重赞扬了该剧“女主角性格描写的成功”:“这样一个秉性刚烈、坚韧不拔、而终能杀敌报国的女性,确是抗战的大熔炉里应该可以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典型”,他还指出,剧中这个“无知”却敢于英勇抗敌的女主角,不仅是作者“个人想象的产物”,而且真实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因此很适合“用在乡村宣传上”。可见,余上沅对《民族女杰》的评鉴包含“戏剧的大众化”和“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两方面的肯定,这也是抗战戏剧在创作上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抗战以来,戏剧理论和批评界针对创作界整体庸俗化的创作倾向,曾展开集中性讨论,其中“‘人’的观念的深化为核心的认知论和戏剧创作论的发展”,成为抗战时期深化现实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葛一虹认为: 剧作者应描绘“各样人物”,“抗日游击队员不必全是十全十美的民族英雄,描写的敌人也不必都是奸淫掠略的兽性者。”陈白尘也指出:“对于抗战……应该从各式各样的人物身上去反映它”……就这一时期批评界对戏剧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要求来看,《民族女杰》对“女杰”孙四姑娘的描绘确有其可圈点之处——她冲破了社会传统对女性形象的规训,体现了底层妇女参与社会的自主性现实追求。无论是作为女剧作者的沈蔚德,还是女主角孙四姑娘,皆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对自身处境及生存方式的清醒与豁达。
(一) 《女兵马兰》中的“陌生化”敌人形象
沈蔚德曾将住在她心中的一个女人的面影描述如下:
她热情而明智;机警而不是油滑;她也许很恣肆,但不是放荡;她其实很单纯,但决非无知。她有强健的肩膊,不会因一点小小的打击便被压倒,她有着一切“男性”的美德,——假如“男性”这两个字真是代表了冷静、坚强、果断、勇敢、负责任、好斗争……这些意义的话——然而也并不知道因此就该争女权,穿男装,到处开会演说。因为她终是女性,有时也会被感情驯服得像匹温柔的小猫儿。她觉得“女性”就是“女性”,就和“男性”就是“男性”一样;而无论男女都是“人”,这就够了。
由此可见,沈蔚德对女主角的塑造是以“人”为起点,这是一种在清晰地了解“男人”与“女人”的特性之后,依然选择做“女人”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一个女性,在沈蔚德笔下被描绘了两次: 第一次是混迹于男兵队伍中的性格坚强、行动粗野,有着百发百中枪法的士兵马兰;第二次则是城镇酒店里时而温柔恬静,时而满脸杀气的老板娘孙四姑娘。《女兵马兰》讲述了马兰与日本俘虏原扶治郎同困于荒岛并彼此互生情愫,但当日本战船经过荒岛之时,俘虏却劝马兰向日本投降,马兰抛开情爱之念,当机立断将其枪杀并英勇迎敌的故事。虽从剧情来说,《女兵马兰》与《重逢》(丁玲,1937)、《自由魂》(赵慧深,1938)、《生死恋》(赵清阁,1942)等其他女性剧作一样,都未超出“视爱情与战争为对立的双方”的冲突框架,但剧中的人物塑造却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女兵马兰》不仅“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位别具特色的女孩形象”,还浓描了一位区别于一般抗战剧中妖魔化的敌人形象。沈蔚德塑造的日本俘虏外形姣好,他“身体很魁梧……身上穿着很讲究的军服……头上有着很黑的浓发,脸上修剃得很干净,眼睛里一对漆黑的曈子,奕奕的射出光芒”(第一幕),他还“念了很多书,有过不少的高超的理想”,时常研究文学并会作诗。在对原扶治郎一系列好感化的形象铺垫之后,沈蔚德借俘虏之口从侵略者角度反思了战争,他在剧中深情自述对于和平时代的向往和对战争的厌恶:“不必想到仇恨,不必时刻提防那烧着火一样的仇恨的眼睛,到处都在寻找着你;不必想到战争,那些刺人鼻孔的硝烟,血肉横飞的惨状,不是别人毁了,就是自己毁了。”(第三幕第二场)尽管此处的反战思想具有文学性的理想化色彩,但《女兵马兰》大胆的故事立意与矛盾性的人物塑造,无疑为抗战戏剧增添了别样风采。沈蔚德在剧中将一向被符号化、贫困化的敌人形象以“人”的标准去描摹,本身就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观念的一次訇响。最后,为贴合宣传抗战的现实需要,沈蔚德笔下的原扶治郎在后半段呈现了“中日亲善”的伪善面容,使得《女兵马兰》在主题上转向了“抗战高于一切”的国家话语。
(二) “女性就是女性”: 《民族女杰》对女性意识的探赜
沈蔚德善于塑造人物的创作功底同样体现在《民族女杰》之中。如果说女兵马兰从装束到性格所体现的男性气质是源于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剧作者不自觉地剥离女性气质、逃离女性身份的一种症候,那么在《民族女杰》中这种症状则几乎消隐了。剧中的孙四姑娘毫无遮掩地展现着颇有情色诱惑力的女性身体,她有着“苗条身段,瓜子脸儿,一笑两个酒窝”,并且“秋波那么一转,就能勾走你的三魂七魄”(第一幕)。店中酒客、街头混子、驻军金营长、日本军官无一不对她想入非非。萦绕在孙四姑娘周身的这些凝视目光强化了她对于自身的认知,一方面她懂得利用自身特质博得金营长喜爱,并想藉此激起她的窝囊丈夫史长兴的怒气;另一方面,她也善用美色掩盖抗敌行动,以此斩获歼灭敌人、保家卫国的正义果实。当然,女性魅力的展现远不能包罗孙四姑娘的人格特质,当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之后,她形象大变,不加修饰地以“一身家常的粗布衣裳”出场,“天天浆浆洗洗,烧饭作乐,空下来再做点活计,和小兴儿搅合搅合”(第二幕),圆满地复现了一个传统家庭主妇的模样。可见,沈蔚德对孙四姑娘的塑造的起点,便是拒绝消隐她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传统品格。在此基础上,她还将孙四姑娘塑造得“更懂得男性,也更了解自身,更明白两性关系包括爱情的底细,也更知道如何把握分寸以立身存命”。因此我们看到,孙四姑娘虽欣赏英勇无畏的男性,却能对毫无男子气概的丈夫不离不弃,并试图通过“女性的方式”改变他软弱的性格。她对丈夫的这种态度,并非受制于封建婚恋观念的禁锢,而是清醒、主动且拒绝媚俗的新女性观。在笔者看来,沈蔚德以两性关系为切口展现孙四姑娘独立人格的这一妙笔,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康蒂妲》(, 1897)不谋而合。《康蒂妲》一剧由陈瘦竹先生首译于1941—1942年间,在“译序”中他专辟一节分析《康蒂妲》的“新女性观”: 萧伯纳的女性观点,是“在两性关系中,女子处于‘主动’地位,并且……在结婚后,她就成为‘一家之主’”,这是一种“对当时男权主义的挑战”。萧伯纳笔下“冷静明智”“善良而有牺牲精神”的“强者”的康蒂妲与沈蔚德笔下的孙四姑娘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从侧面反衬了《民族女杰》在人物塑造上的先锋性特质。
沈蔚德从两性关系出发的巧妙构思上深化了孙四姑娘独当一面的形象,并推动她成为剧中男性的启蒙者角色——孙四姑娘先是以“女性的方式”引导她的丈夫从软弱无能转向勇敢无畏,而后又为即将迎敌却留恋儿女私情的金营长鼓舞士气。这样,在这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身上同时体现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担起的民族责任,双重性的身份模糊了一般的戏剧创作中女性与国家话语的潜在界限。剧终,孙四姑娘站在火堆旁仰天高喊:“中国的飞机,中国的弟兄们……来呀!把炸弹都丢在这儿!炸吧!烧吧!”(第四幕),对于她的牺牲,金营长说:“你是我们的民族女杰,我们永远记得你!”,这个情节自然地赋予了女性身体一种崇高的政治意义,也使得孙四姑娘在民族国家的指认中获得了自我崇高感。可以说,沈蔚德在以抗战为旨趣的戏剧创作中所塑造的孙四姑娘这一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男性成就的参照,孙四姑娘已经走出了“‘弱者’的阶段,成长为没有任何软弱、牺牲品、需要拯救和等待施舍等附带意味的纯粹的女人,成长为有能力、有才智去以女人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女人”。
质言之,1939年“抗战剧本选”的桂冠之作《民族女杰》是以清醒独立的女性形象塑造来契合抗战的统摄性话语。而对于《民族女杰》的综合考量,无论是从抗战戏剧的大众化维度,还是抗战戏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层面,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再兼及沈蔚德在抗战时期的其他戏剧活动,我们理应在抗战戏剧尤其是40年代女性戏剧的史述中为之增添更多的笔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