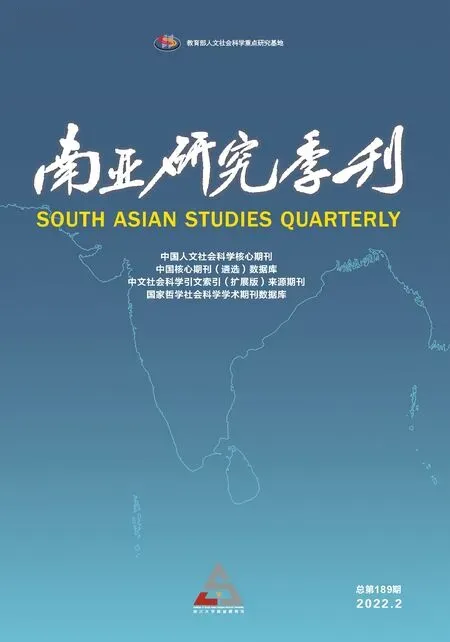威胁制衡视角下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
谢晓光 杜洞光*
【内容提要】 在当前权力转移加速的进程中,美国致力于推动其领导的亚太“轴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结合“威胁制衡”与“社会网络”基础上的“联盟网络”理论,能够有效解释美国推动印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动力。鉴于“轴辐”联盟体系存在诸多弊端,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与伙伴从制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根本考量出发,推动其印太联盟向“网络化”转型。该趋势会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格局与国际秩序造成持久影响。中国可以从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性质与方向、鼓励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巧用楔子战略与弹性竞争策略等方面从容应对。
一、引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确立了两种典型地区秩序,一种是跨大西洋的北美-欧洲“网络化”联盟(1)“网络化”联盟或联盟“网络化”是指美国与其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相互交织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安排的混合型联盟体系。参见:Matteo Dian,Hugo Meijer,“Networking Hegemony: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no.2,2020,p.132.,以北约为代表;一种是跨太平洋的美国与亚太国家“轴辐”式(hub and spokes system)联盟(2)“轴辐”联盟体系是指不同盟友(辐条)与美国(轮轴)有着深厚的双边战略关系,但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关系。参见:Luis Simón,et al.,“Nodal Defence: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4,no.3,2021,p.361.,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澳同盟、美泰同盟为代表。美国在1950年寻求建立一个多边“网络化”联盟——《太平洋公约》,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菲律宾。(3)Victor D. 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no.3,2010,p.189.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东亚的“轴辐”联盟体系依然存在且占据主导地位。(4)Yasuhiro Izumikawa,“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no.2,2020,pp.7-50.近年来,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盟友和安全伙伴已经开始在与美国的双边联盟框架之外,扩大和深化以国防事务为主的各领域密切联系,即美国大力推动其在亚太地区的“轴辐”式联盟体系向北约“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例如,美国着力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该机制意欲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呈现打造“四方+”架构的趋势;再如美、英、澳签订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简称“澳英美联盟”)。除此之外,美国着手打造“印太版北约”的鼓噪亦不绝于耳。(5)Anders Corr,“China Threat Requires an Asian NATO,” 15 October 2014,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Anders-Corr-China-threat-requires-an-Asian-NATO,29 April 2022.美国亚太“轴辐”联盟体系(见图1)在未来将会增加更多节点与连接,极有可能成为一张更大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见图2)。那么当前美国为什么更加致力于将二战后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轴辐”联盟体系向欧洲北约式“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的行为会为地区与国际秩序带来什么影响?作为崛起中的中国如何有效应对美国的“网络化”联盟?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本文将通过澄清“轴辐”联盟体系与“网络化”联盟体系的关系机理,深入解读美国当前的联盟实践,进而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图1 美国亚太“轴辐”联盟体系示意图(作者自制)(6)该图仅展示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务安全条约的盟友。

图2 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示意图(作者自制)
二、美国建立亚太与印太联盟体系的理论述评
在关于美国建立亚太联盟体系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文献中,有大量著作研究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联盟,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学者对美国在该东亚地区不断演变的大战略、美中关系中的合作/竞争动态,以及中国崛起的地区影响做过广泛探讨。
第一,现实主义流派学者从两方面探讨美国强化亚太与印太联盟体系的原因。其一,中国崛起论。康灿雄(David C. Kang)认为,“东亚的和平、稳定和中国的包容是一个难题,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传统上将大国崛起与战争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7)David C.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7.现实主义者对战略威胁的回应是建立联盟关系,基本认为中国是寻求地区霸权地位的“修正主义”大国,其崛起必将改变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及其东亚盟友和伙伴应利用美国领导的联盟防务体系,从外部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8)D. E. B. Soumyodeep,and Nathan Wilson,“The Coming of Quad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Th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4,no.9,2021,pp.111-122.其二,美国衰落论。理论界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作为推进联盟“网络化”的主要变量。21世纪以后,美国推动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重要动力来自于削减自身的投入成本,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以便继续维持霸权地位。如左希迎认为,美国领导权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意愿下降(9)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64-65页。,但出于霸权护持的考量,美国依旧会将联盟体系外的国家拉入其在本地区的安全体系中,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国安全诉求的同时,也实现对美国“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y)的合法化。
第二,建构主义者认为,联盟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强调身份在形成和塑造盟友关系中的作用。(10)Anna Michalski,and Zhongqi Pan,“Role Dynamics in a Structured Relationship: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C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5,no.3,2017,pp.611-627.如乔纳森(Jonathan A. Chu)指出,领导人通过使用强调国家共同利益的修辞工具获得公众对联盟的支持。(11)Jonathan A. Chu,et al.,“Commanding Support:Values and Interests in the Rhetoric of Allianc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47,no.3,2021,pp.477-503.美国可以在亚太地区通过强调共同价值观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如拜登政府强调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进行合作,可以加强与盟友的团体关系,从而达到“网络化”效能。另外,一国倾向于与意识形态相似的他国结成联盟,因为他们眼中的“民主国家”可能发展促进合作机构出现的集体身份,并形成“价值共同体”。(12)Ole R. Holsti,et 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Comparative Studies,New York:Wiley,1973,p.215
第三,英国学派学者质疑结构现实主义范式所声称的权力结构变动导致的联盟转型。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中国对东亚基于规则秩序的物质和规范性支柱的选择性竞争引发了区域大国对该秩序的重新整合。(13)美国领导的东亚霸权秩序的规范性支柱是指:承认大国地位、尊重主权、自由贸易、威慑和国际法、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争端解决体系。参见:Barry Buzan,et al.,Conte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具体而言,区域大国试图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扩大这一地区霸权秩序的构成:一方面,应使这一秩序涵盖更广泛的美国盟友和伙伴,目的是加强集体能力,抵御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部分融入了秩序本身,以此鼓励中国继续获得在稳定性和持久性方面发展的既得利益。如马特奥·迪安(Matteo Dian)和雨果·梅耶尔(Hugo Meijer)认为,地区大国并没有参与针对中国的外部平衡,而是试图通过抵制和迁就的混合方式,在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引导和塑造中国的崛起轨迹,以维护美国领导的东亚霸权秩序。(14)Matteo Dian,and Hugo Meijer,“Networking Hegemony: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no.2,2020,p.133.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学派的中国崛起论夸大了中国崛起导致东亚秩序不稳定的程度,中国没有成为“修正主义”大国,而是参与了对现有地区秩序的“选择性竞争”,除日本外,多数地区国家对中国和美国采取的是对冲策略。(15)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47-77页。而且,美国衰落论忽视了历史现实,1952年8月杜鲁门政府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5/2号文件指出:“美国应鼓励并在适当情况下参与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其中包括将日本作为重要成员。”这表明,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便希望在东亚发展多边安全体系,而不只是在自身实力衰落的背景下打造“网络化”同盟。另外,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解释过于理想化。一方面,集体认同与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并不能左右地区国家在选择结盟还是独立维护自身安全等核心利益上的战略抉择;另一方面,地区国家在推动联盟“网络化”过程中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而往往是被动与接受的一方。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网络”理论与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谱系中的“威胁制衡”理论,阐述“网络化”联盟是在制衡威胁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前者也是后者的延伸与放大。通过这一跨学科的理论融合方法,以战略性与全局性的视角,来审视联盟政治运作的根源,并试图勾勒出联盟政治中网络关系的互动图景。
三、威胁制衡与联盟网络化的关系机理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威胁制衡”联盟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本身、二元联盟以及联盟间层次问题。他将联盟视为独立的行为体,并主要考察其塑造、影响与瓦解过程。通过将社会网络理论运用到“威胁制衡”的联盟关系研究中,在控制其他层次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与联盟网络结构相关变量,可以从新视角解释联盟内部所有国家之间的复杂联系。
(一)“威胁制衡”联盟理论的核心观点
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多数研究旨在解释国家面对威胁的反应。沃尔特认为,当面对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大国时,国家拥有制衡(Balancing)或追随强者(Bandwagoning)两种策略选择。当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结盟对抗普遍存在的威胁时,就会出现制衡;而当国家加入或与危险源结盟时,就会出现追随。(16)〔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20页。按照现实主义的隐含逻辑,各国可能会将较小的领土争端或历史遗留问题的外交分歧视为威胁。因此,更高程度的政治或外交冲突将要求作出更严厉果断的反应。除了沃尔特概述的安全威胁的决定因素——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17)同上,第17-38页。之外,我们还可提炼出一些关于安全威胁的示例,包括:领土争端、两国之间对第三国影响力的竞争、民族主义行为和情绪、军事演习频率、贸易行为所衍生出的胁迫倾向等。
(二)以“社会网络”解释“联盟网络”的演变机理
社会网络分析涉及由节点(nodes)之间所定义的连结(ties)关系,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或国家,网络分析主要处理节点之间的关联,而不是特定节点的属性。(18)Stanley Wasserman,and Katherine Faust,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在国际关系中,网络通常被视为一种促进集体行动与合作、发挥影响力或作为国际治理手段的组织模式。(19)Hafner-Burton,et al.,“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no.3,2009,p.560.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结构就是单元间的物质能力分配,而网络分析将结构定义为行为体之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结合国际关系权力理论,根据位置与关系进行推断,大致可以得出关于联盟网络的四点结论:第一,在联盟网络中,行为体(节点)的连接数量越多,那么其他节点与该节点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深,则该节点国际权力就越大;第二,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于其他行为体与之形成的连结关系,即网络结构产生关系性权力而非行为体本身的物质性权力;第三,行为体权力亦来源于相对位置的差序格局,即行为体在该网络中的位置分布,权力的分配决定相对位置,相对位置再赋予行为体再生性权力;第四,行为体的权力是一种互惠性权力而非冲突性权力,且犹如社会资本一样具有自我放大和再生的能力。在此,可以将联盟“网络化”定义为盟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机制化,横向联系大幅加强,美国与盟国、盟国与盟国之间开展小多边合作,使得单线联系的“轴辐”联盟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20)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页。
(三)“威胁制衡-联盟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国家行为假设
沃尔特认为,制衡的一般形式为: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构成威胁的国家;追随强者的一般形式为: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将与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结盟。因此,制衡比追随强者更普遍。(21)〔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28页。在这里需要指出,制衡与追随强者并非对立策略,追随强者的行为假定中,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并非一定将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还有可能与域外强国结盟反手制约该地区的潜在霸主。所以制衡与追随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策略,即通过追随强者来制衡威胁。在地区中,中小国家的最优策略还是追随首强国来制衡本地区强国,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将社会网络植入到二元、三元、多元联盟关系中,国家可以通过“网络化”联盟制衡威胁,国家联盟义务的累积效应就称为网络效应。(22)Skyler J. Cranmer,et al.,“Toward a Network Theory of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8,no.3,2012,p.296.一方面,制衡与追随强者的行为假定在互相作用的同时还有利于产生联盟“网络化”效应;另一方面,“网络化”联盟所产生的聚集效应提高了地区中小国家因受益于制衡与追随带来的好处而增强了对首强国的依附性,进而形成关系更为密集与牢靠的联盟网络。基于上述,本文在此提出国家在“网络化”联盟中结盟行为的三个地缘政治图景。图景一:在地区之内,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比面临较低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更有可能与首强国结盟,形成共同制衡威胁。图景二:在地区之内,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相较于其他中小国家更有动力与意愿去与面临较低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合作或结盟,形成共同制衡威胁。图景三:在地区之内,首强国与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的合作或结盟将产生示范效应,且二者倾向于扩大联盟合作范围共同制衡该地区潜在强国。
四、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动力学解释
“轴辐”联盟体系曾在历史上稳定了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但目前陷入了一系列困境。根据“威胁制衡-联盟网络”的分析框架,美国通过塑造威胁并借口诬蔑中国为地区威胁的方式,基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重考量,联合其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对抗威胁,推动亚太“轴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
(一)“轴辐”联盟体系的困境
“轴辐”联盟体系是美国于二战后在亚太地区构建的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基本框架。虽然上述建构的“威胁制衡-联盟网络”分析框架侧重于联盟关系中广泛的网络结构影响,但联盟的基本单位是二元的,且二元化联盟只能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因此,如果不考虑联盟的国家和二元层面的决定因素,联盟的网络分析是不完整的。“轴辐”联盟体系在历史上乃至当代发挥过重大作用,但相较于“网络化”联盟体系,其制衡威胁的效应大大减弱,不足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的行为实践。
首先,“轴辐”联盟体系不同于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具有双边性质和条块状特点。少数联盟关系的破裂虽然并不影响整个安全架构,但如果竞争对手集中战略资源向美国单个盟友施压时,压力最终只会转移到美国身上,其他盟友难以进行战略支援。(23)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66页。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安抚盟友需要美国在领土争端、贸易竞争或军备威慑等各项议题上有更大的意愿对抗对手。如澳大利亚防务状况的第一个可能制约因素来自其与中国密切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这一关系促进了国内繁荣,但也造成了对不对称脆弱性的强烈认知。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在印太地区上升的安全联系以及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困境(24)Fontaine,et al.,Networking Asian security: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der in the Pacific,Washington,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7,p.27.,假设中国向澳大利亚在安全方面施压,澳大利亚只能向美国寻求更全面的防务承诺。
其次,“轴辐”联盟体系内的亚太国家内部纷争极为棘手,影响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导致其共同制衡威胁的效率大大降低。例如,韩国与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在低级政治领域,韩国与日本不断爆发贸易争端的同时,两国也因为诸如领土纷争、二战强征劳工赔偿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未达成妥协而互相攻讦;在高级政治领域,冷战之初,美国将驻韩美军部署在非军事区沿线,主要是为了保卫韩国和维持半岛威慑,驻日美军则肩负维护地区安全等更广泛的使命。根据联盟转型的目标,美国将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重新配置,为快速部署全球联网部队做好准备。如果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在未来几年内分别转变为区域机动部队,韩日及其部队很可能会受到压力。因为韩国发现其希望韩美联盟只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要求似乎被拓展(25)Chang-hee. Nam,“The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and US-Japan-Korea Security Network:A Case fo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acific Focus, vol.25,no.1,2010,p.36.,但这并不符合韩国利益。上述问题极大限制了韩日合作的空间及其与美国共同合作对抗威胁的能力。
最后,美国作为安全保证人为所有亚太盟国提供战略保护,只有当霸权国足够强大,可以向所有盟友提供更广泛的威慑承诺,并在应对联盟系统的所有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轴辐”联盟体系才会稳固。(26)Luis Simón,et al.,“Nodal Defence: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4,no.3,2021,p.366.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动摇了“轴辐”联盟体系的基石。美国相对衰落导致两种连锁反应,一是需要通过“网络化”联盟的聚集效应共同制衡威胁,另一种则是为其地区盟友“松绑”,让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如日本在解除安全限制方面更加咄咄逼人。《日本宪法》第9条虽然限制了其通过战争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行为,但日本近年来愈加先进完善的军事能力,实现了对宪法第9条的重新解释,放松对武器销售的限制以及进行了更富雄心的外交行动。(27)Daisuke Akimoto,The Abe Doctrine:Japan's Proactive Pacifism and Security Strategy,Singapore:Springer,2018,pp.6-7.日本的对外政策难免造成中、韩、朝的高度警觉,在东北亚乃至印太地区不排除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综上来看,“轴辐”联盟体系由于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战略支援、体系内部国家争端以及提供广泛的安全承诺等问题,从而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印太地区国际政治实践,故转型“轴辐”联盟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二)亚太“轴辐”体系向印太“网络化”体系转型的深层动因
除了将国家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作为制衡威胁水平的参考指标外,印太地区所特有的要素,如领土争端、军备扩张、贸易竞争、航线与能源运输安全、历史及殖民地问题、民族主义情感与行为、两国之间对第三国影响力竞争等,可再划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要素,二者共同作用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推动亚太“轴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的过渡进程中。
1.传统安全视角
近年来,关于当前国际格局是否转变为新两极格局的讨论不绝于耳。(28)赵华胜:“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结构:从多极到两极?”,《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3-20页;阎学通:“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6-8页。2017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且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9)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8 December 201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23 May 2022.在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中国再次被贴上“修正主义大国”的标签。(3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1 June 2019,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24 May 2022.在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关注印太地区是因为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但在印太地区最为严重”。(31)The White House,“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24 May 2022.显然,中国不再被视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建设性伙伴”角色。因此,可以预计当前美国印太联盟体系正在经历最根本的变化,因为在美国及其盟友看来,潜在的权力分配与威胁来源正在发生其最根本的变化。
首先,如果国家的总体资源能力(如土地、人口、工业)越强,那么给他国造成的潜在威胁就越严重。基于此,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将美国大战略的目标设定为联合其他国家,阻止亚欧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比美国更多的工业资源。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也正在与美国扩大和深化防务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合作正在传统的“轴辐”联盟模式内部建立新的联系,以往从未参与过该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架构的国家正直接或间接地与之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美国通过塑造中国为“地区威胁”推进联盟“网络化”。美国鼓吹中国正在以一种隐晦的竞争方式在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开疆拓土,“中国政府在常规外交和经济活动之外,强制性地使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网络和信息活动”。由于对“灰色地带”的竞争往往较少动用军事力量,美国将中国描述为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威胁”,号召其盟友伙伴抵制中国的军事演习、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并诬蔑“中国的‘灰色地带’战术旨在对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施压、惩罚、或破坏”。(32)Bonny Lin,et al.,Competition in the Gray Zone:Countering China's Coercion Against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22,pp.2-10.美国兰德公司列举出了80多个中国的“灰色地带”战术,号召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建立多边联盟来支持盟友和伙伴,为其加强防务承诺,并与之一起共同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战术。(33)Ibid., pp.2-10.另一方面,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并不排斥与美国的合作。例如,内部实行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FVEY)不仅逐渐增加合作项目,并还有吸收日本、韩国与印度的打算,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七眼联盟”或者“八眼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印太各国发展亚洲内部安全关系并与美国合作的动机也有规避中国崛起和美国在亚洲未来角色不确定性的考虑,这被称为对冲行为。(34)Singapor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ranscript of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K. Shanmugam's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and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14 January 2013,http:∥www.mfa.gov.sg/content/mfa/media_centre/press_room/tr/2013/January/transcript_20130114.html,30 April 2022.美国在印太地区发展错综复杂的“网络化”联盟,旨在制衡地区潜在霸主并护持其地区“帝权”与国际霸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图景三,即在地区之内,首强国与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的合作或结盟将产生示范效应,且二者倾向于扩大联盟合作范围共同制衡该地区潜在强国。
其次,在其它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军队数量、武器强度与地缘邻近等原因,拥有强大的军事进攻能力的国家比那些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的国家更可能导致对抗联盟的建立。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正在重塑既有安全框架,印太安全架构逐渐从非对称走向对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试图以亚太联盟为基础,推进印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掌握规则制定权,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安全秩序。拜登政府正在更新“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以推进一种“网络化”方法,“综合”意味着加强与与盟友之间的网络联系,深化盟友之间的军事安排,通过兼并、互通和联合培训的方式选择合作伙伴,以适应新出现的威胁场景。如“澳英美联盟”的核心是通过共享核潜艇等敏感军事技术来表明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决心以及印太盟国的团结和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的决心。(35)Jane Hardy,“Integrated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advancing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alliance,” 15 October 2021,https:∥www.ussc.edu.au/events/integrated-deterrence-in-the-indo-pacific-advancing-the-australia-united-states-alliance,2 May 2022.在拜登政府“综合威慑”的广泛愿景下,盟友和合作伙伴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为集体威慑做出努力,那些已经很好地与美国融合在一起的国家寻求与美国整合共同防御能力,例如在后勤安排、信息共享或海洋领域意识方面。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将联盟网络视为“综合威慑”的核心组成部分(36)Ibid.,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脱离了冷战时期的“轴辐”式联盟结构,或曰“轴辐”联盟体系正在发生功能性转变,越来越多地承担多边安全秩序维持和建设的功能。(37)Jae Jeok Park:“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24,no.2,2011,pp.137-15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图景一,即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比面临较低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更有可能与首强国结盟共同制衡威胁。
最后,地区国家对自身安全威胁的感知程度促使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大国拥有进攻的军事力量,然而其他国家永远无法确定该国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是否具备进攻意图,因此生存和安全是国家追逐的永恒目标。(3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44页。中国国防预算的总额和相对年度增长在该地区国家中是最高的,这引起了其他印太国家的关切,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相继提高了其国防预算额度。(39)D. E. B. Soumyodeep,and Nathan Wilson,“The Coming of Quad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Th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4,no.9,2021,pp.113-114.观察人士表示,印度的部分外交目标是让合作伙伴感到“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可怕,印度就放心”。(40)Cleo Paskal,“Indo-Pacific Strategies,Perceptions and Partnerships,” London:Chatham House,2021,p.27.可见对威胁的感知很重要。如果一国将另一国视作威胁,那么它必然认为后者既有实力又有意图阻碍其目标的实现或危害其国家安全。单极结盟理论认为,在单极条件下,由于受霸权威胁的国家即便结盟也不能完全制衡霸权国,于是会出现只与霸权国结盟而无反霸权结盟的现象。(41)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42页。这符合当前印太地区的结盟现状。越南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自中国开始在南海开展行动以来,越南一直在寻求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部分学者认为应使越南加入到“四方安全对话”中。(42)Sung Chul Jung,et al.,“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0,no.127,2021,p.57.越南政府也一直在加强与四方国家的合作。美国致力于在国防安全、海洋安全、军事交流等关键领域与越南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强调越南是美国双边关系中最强大的支柱之一。(4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U.S. seeks stronger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3 April 2019,https:∥dod.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804307/us-seeks-stronger-defense-relationship-with-vietnam/,25 April 2022.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承认,“澳英美联盟”针对的是中国。(44)“美官员承认建立‘澳英美联盟’是针对中国”,《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11202/2461648.shtml,2022年4月30日。印太地区中小国家的反应在反映图景一的同时也反映了图景二,即面临较高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相较于其他中小国家,更有动力与意愿去与面临较低外部威胁的中小国家合作或结盟共同制衡威胁。
2.非传统安全视角
虽然拜登政府承认美国与中国将会处于“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之中,但他认为这种竞争不应失控。在2021年11月16日举行的中美领导人峰会上,拜登建议给中美关系设立“护栏”以避免爆发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2021年7月在新加坡的演讲中强调,他正在寻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一条危机热线,以防止紧张局势不受控制地升级。可见,在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的极端竞争不再是无限的。与特朗普政府稍有区别的是,虽然中国依旧被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拜登政府已逐渐将政策对话从美国盟友和伙伴是否会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转向关注他们更关心的挑战。例如,奥斯汀表示,“我们并不要求该地区的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形容美国与东南亚的友谊“不仅仅是地缘政治”,而是对东南亚国家人民的“权利和生计”的担忧。(45)Derek Grossman,“Biden's Indo-Pacific Policy Blueprint Emerges”,23 August 2021,https:∥www.rand.org/blog/2021/08/bidens-indo-pacific-policy-blueprint-emerges.html,28 April 2022.2021年8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5次东盟线上会议所做报告将重点放在了跨领域的区域挑战上,如流行病救济、气候变化、人力资本开发、城市化和缅甸政变。(46)U.S. Department of State,“ASEAN-Related Ministerial Meetings”,4 August 2021,https:∥www.state.gov/asean-related-ministerial-meetings/,25 Arpil 2022.因此,美国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安抚行为旨在使后者认为大国竞争对它们的负面影响较小,安心追随美国是它们的最优策略。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的军事演习,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演习和相关区域的援助计划中,如对非法跨境、过度捕捞、网络入侵、气候灾害的联合整治。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增强“轴辐”联盟体系的一种方式,并与新的合作伙伴建立“网络化”联系。(47)Jane Hardy,“Integrated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Advancing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Alliance,” 15 October 2021,https:∥www.ussc.edu.au/events/integrated-deterrence-in-the-indo-pacific-advancing-the-australia-united-states-alliance,2 May 2022.由此不难看出,拜登政府从最初强调共同价值观已经逐渐发生改变,以更好地符合共同国家利益,特别是鼓励盟友和伙伴与美国合作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
五、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的影响及应对
美国在印太地区打造“网络化”联盟体系将对地区国家与印太地区格局造成持久不良影响,如果不能合理管控中美争端,那么将有可能致使印太地区陷入大国政治悲剧的深渊。鉴于此,中国应重点处理好大国关系,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性质与方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巧用“楔子”战略与“弹性竞争”策略。
(一)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的持久危害
第一,美国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是压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对抗型联盟体系。根据相关研究,“印太”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生存空间”地缘政治理论代表人物卡尔·豪斯霍夫 (Karl Ernst Haushofer)。最早将“印太”概念作为官方层面论述并使其富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的则是日本,日本也是鼓动美国将亚太“轴辐”联盟体系向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转型的始作俑者。(48)关于“印太”概念起源与发展的论述,详见杨慧、刘昌明:“美国视域中的‘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基于对美国主流智库观点的分析”,《外交评论》,2019年第2期,第59-86页;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35页。“印太”概念基本上为美国及其盟友接受,但中国政府一直使用“亚太”而非“印太”概念,因为后者在中国政府看来是遏制中国崛起、挑动地区争端的对抗性概念。如王毅在2020年马来西亚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所鼓吹的是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推行的是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维护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违背东亚合作中的互利共赢精神,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损害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49)王毅:“美国印太战略对东亚是巨大的安全隐患”,2020年10月1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498222414083055&wfr=spider&for=pc,2022年4月27日。
第二,美国推动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印太地区整体发展。美国通过在“轴辐”二元联盟架构的基础上吸引不同印太地区国家加入不同合作议程,实质上是搞“小多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就是美国根据不同合作事项选择不同国家结成盟友或合作伙伴关系;“伪多边主义”就是以少数国家的规则定义国际规则,以少数国家的秩序取代国际秩序。(50)外交部:“2021年4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ne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04/t20210426_9171254.shtml,2022年4月2日。这二者本质上都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主要排斥中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多边主义的实质是依法行事、照章办事。这个‘法’就是国际法,这个‘章’就是《联合国宪章》。只有遵守国际法、遵从《联合国宪章》,才能形成稳定、公正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才能给世界带来长治久安。”(51)同上。中国作为该地区名副其实的海陆复合型大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本身就与印太国家存有千丝万缕的相互依赖关系,排斥中国力量融入意味着本地区事务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处理不当就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国家间隔阂。
第三,美国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有可能成为僵化的联盟,不排除重演大国政治悲剧的可能性。传统联盟成立的首要条件就是共塑敌对国家。需要作出区分的是,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在共塑敌对国家的同时还共塑共同威胁,敌对国家代表首要威胁但并非代表全部威胁。归根到底,美国依旧没有摆脱传统联盟成立的初衷。根据肯尼斯·奥根斯基(A. F. Kenneth Organski)的观点,权力转移时期,尤其是在权力越来越趋近平等时期,战争的可能性有增大的风险。而大卫·辛格(J. David Singer)和马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试图把国际体系中的战争频率和联盟数量联系起来。他们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理论模型堪称外交领域中的“亚当·斯密模型”,即强调外交领域中“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机制中,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所有国家都有互相交往的自由,这将增进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利益。联盟会减少国家间互动的机会和国家选择的自由,所以联盟将促进体系内的极化,增大战争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推理,一个高度极化的联盟体系将大大增加战争的可能性。(52)Singer J. David,et al.,The Correlates of War I:Research Origins and Rationale, New York:Free Press,1979,pp.225-264.主导国如果在权力转移的危险时期不能合理管控争端,反而重构所谓制衡崛起国威胁的联盟,便摆脱不了大国政治悲剧不断重演的“国际关系史周期律”。
(二)应对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的基本策略
首先,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性质与方向,批驳沉渣泛起的“新冷战”论调,这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并非“新冷战”,给当前形势贴上这一标签无异于为中美关系火上浇油,还会造成中国与美国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动荡。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大战略在于遏制与反遏制,其前提是美苏基本没有依赖关系。当今中美在诸多领域已形成相互依赖关系,通过脱钩寻求遏制的提法不切实际;冷战期间尽管美苏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但二者的代理人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盟友的对抗与低烈度冲突此起彼伏,当前中美两国不存在直接热战或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条件。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因此,明确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与方向,对美国组建联盟体系的目的与行动具有约束作用。
其次,鼓励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伪多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必须带头主持公道,厉行法治,承担责任,聚焦行动。(53)外交部:“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活动并发表演讲”,2021年5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105/t20210526_9176881.shtml,2022年4月25日。美国所宣称遵守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由美国及其盟友组成的小圈子确立的规则,不具有全球代表性。在印太地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让凡是涉及该地区事务的国家都参与到合作或谈判中来,国际事务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商量着办,不搞排他性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而且,在亚太地区要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54)王毅说:“在亚太地区中,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支持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见外交部网站:“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2021年11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111/t20211120_10450855.shtml,2022年4月6日。
再次,巧用楔子战略。楔子战略是“分化者出于改变相对实力对比的目的,寻求对潜在或既有敌对联盟进行分化的一切努力”。(55)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4页。简言之,楔子战略就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分化敌对联盟的战略。既有研究将楔子战略的目标归纳为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分化、联盟冲突和联盟预阻5大类,(56)联盟重组指化敌为友,将对手从敌对联盟中分离出来并与之结盟;联盟解除指使对象国保持中立;联盟分化是指削弱敌对联盟合作,而非化敌为友或解除敌对联盟;联盟冲突指通过离间方式,使目标国主动与盟友陷入冲突,而分化者自己不参与斗争;联盟预阻指使对象国在未加人敌对联盟就保持中立。关于楔子战略目标的分类,参见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6-78页。实现这5类目标的难度也依次递减。使用楔子战略对抗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鉴于美国打造“轴辐”联盟体系中的日、韩、澳、菲、泰五国与美国联盟历史久远,故使其进行重组、解除或分化的可能性不大,预阻的目标已不能实现,但行为体可以通过塑造共同认知、奖赏、钳制或穿针引线等方式使敌对联盟形成冲突,即运用楔子战略增加其冲突项目,动摇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的基础。例如,2015年中韩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通过塑造中韩历史上被日本侵略的共同认知提升两国关系。其实美国并不希望其东北亚盟友出席中国的庆祝仪式,美国认为朴槿惠参加该活动有可能被外界认为会“破坏韩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尚未正式成为美国盟友但将要与美国合作的印太国家,可以采取联盟预阻的方式降低美国印太“网络化”联盟的威胁。中国需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与“亲、诚、惠、容”的和谐周边外交理念,致力于与更多印太地区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产品。
最后,对美国印太联盟体系善用弹性竞争策略。“弹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冲美国对华“弹性遏制”(57)拜登政府重拾人权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利用盟友,以及更为精准的制裁措施,其实质是灵活务实的“弹性遏制战略”。参见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5期,第9页。的战略抉择。“弹性竞争”是与美国及其印太联盟体系有原则、有选择、有程度和有灵活的竞争,而非全方位、高烈度的竞争。拜登上台之后将重建联盟体系、重拾盟友信任作为主要外交事项之一,中国不仅面对美国本身对华设置的重重阻碍,更要迎接来自美国盟友体系的层层压力。一方面,中国应主动采用弹性竞争应对印太联盟体系威胁。例如,中国积极推动成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应对美日印澳四国经贸合作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有力抓手。另外,适时在东海、南海地区与上合组织成员或其他国家组织联合军演、舰队跨洋航行,战机穿越第一、第二岛链等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应适时在印太地区中小国家之间采用反对冲策略。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已经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大部分国家不愿选边站队,而是采用对冲战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中国应该理解并尊重地区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不能为其对冲战略所累。中国应对地区国家对冲战略的最好办法为“将计就计”策略。例如,CPTPP成立之初便欲将其打造成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国际贸易圈子,但中国依然选择在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该协定,因为中国关注的并非其意识形态和反华主张,而是更看重其在未来地区经济合作中所蕴含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