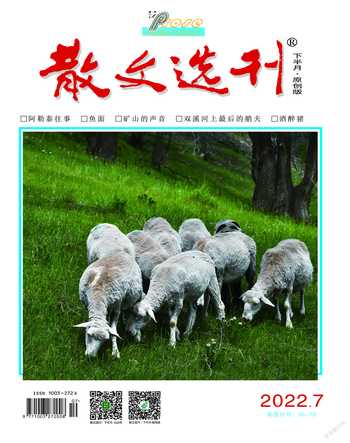双溪河上最后的艄夫
邹仁龙

这个抹不去的印象,还是在很小的时候跟着母亲一起去外婆家。
那次,是我第一次搭乘这个双溪河上那条篾篷船远行,我们是在一个吃过晚饭的傍晚出发的。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春来后的青黄时节。在这个时节里,麦穗是青的,菜花是黄的,当然,桃花也红了。但在那个年代,这个季节,果腹的食物也是最少的时候。
篾篷船的主人,是我爷爷家斜对门的邻居。艄夫的身形略显单薄,却也干练。平常的日子里,总见他穿着一件青灰色的布衣。天气热的时候,或是行船出汗时,便会现出贴身的那件一成不变的本白泛黄对襟汗衫来。大约于我五六岁记事起,就记得这个有着一个瞎眼老妈的艄夫,平时,总会于河边系着他家的那条船上出现,忙这忙那地打理他的运载工具。艄夫以船为业,以船为生,这就是他家的生计。
我从小到大,只坐过他家的船两次,一次便是与母亲一起去外婆家,还有一次是父亲带我去砀山。
那天与母亲一道去外婆家,也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那天在傍晚登船后,未行多久,天便黑了下来。东方升出的细瘦勾月,挂在河东岸的树梢头,淡淡的光,照映不出两岸的景色,只看到夜晚的浪花像碎银铸就,仿佛又很轻,零零散散地浮在水面。篾篷船从中划过,碎银两便向两边极速地躲开,像怕被人捡了似的避让开。只有裹在衣被中的昏昏睡梦,在船底处响起的汩汩流水声中,觉得了丝丝的河水清甜。
被子是艄夫从自家船舱中取出的一条薄被,还有我家自带的衣物,裹于胸前,遮挡些春寒的料峭。那日天朗气清,河道里很静,两岸也静得像睡了似的安逸。两岸边的树,葱茏葳蕤地罩在淡淡的薄雾中,淡淡的月光洒落,将雾里朦朦胧胧的树叶显得扑朔迷离。河面上靠近船沿处,偶尔也能看到模糊的菱叶从水下钻出的细嫩尖脸来,还能看到那些个嫩脸上,在淡薄月色的渲染中露出温和的笑意。
母亲坐在船头,于夜风吹拂中不时地与艄夫说着一些两岸村庄、闸口、河道上的陈年往事。故事与月光一道,倾泻进我坐着的篾篷顶盖下的中舱时,犹如一幕童话,帷幕拉开,外婆的身影便逐渐于童话中走进了我的视线。此刻,在我童年幼稚的心中,那个住着的外婆,便会幻变成雏燕的老窝,幻影成一片甘蔗田里漫过的水,幻化为外公鱼塘里摇曳的水草,幻想成那片垛田上的黄色风景。
此时,夜风已渐渐地大了起来,只见艄夫在船舱的中间隔断上的一个孔眼处竖起了一根竹竿,然后便扯上了一面不大的风帆。那面帆布竖起时,像以前在中学广场上放电影的幕布。艄夫则坐于船尾处,双手执着桨当舵,像个放映员似的专注。只是于这片幕布上,没有看到动画的影像,映照的,依然只有如旧的夜色。
一路夜行,于半夜时分,当篾篷船行到了中堡湖的一个出口前不远处时,我在船舱中便听到艄夫对母亲说:“不好,今天的闸口关了,出不去了。”母亲也起身眺望着说:“怕是要发水了吧?那我们就这儿上岸走去吧,只是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你是就在这等呢,还是现在回去?”艄夫将船靠向岸边说:“我就在这里等吧,兴许天亮了开闸也说不定的不是?”母亲说:“那就难为你了,在这儿又冷又饿的,也没个热汤热水的招待你,真是对不住了。”“没事的,没事的,只是你们行夜路方便吗?要不等天亮了再走?”母亲笑笑说:“怕什么?这条路从小就走,也就七八里地了,没事。”说着便收拾行李拉我上了岸。
行夜路,我的小心脏还是有点惧悚这小路两边的黑暗,但手牵着母亲的手时,体内的承受力似乎也正变得强大了起来。这也许是母亲的韧性在传导给我后起着作用吧!记得那条曾经走过的路,以及那些经历过的,并再也不会轻易忘记的日子,还有那个艄夫一人独自为了生计而留于河道上等待的影像,在以后的日子里,可能会在我的心里,于某时、某刻或某个触景的角落中,偶尔会不由得出现。
第二次搭他的船出行,是与父亲一道去砀山。那时约莫十一二岁,大抵正是少年好奇心最旺的年龄段。那时是我最好玩、好动的年龄段,刚巧又正逢学校放假时期,父亲的单位叫那个艄夫的船去砀山进酒时便顺带着假公济私,也才有了童年的我这段行程最长的水上记忆。
我对有山的地方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与兴奋,只要听到某处有“山”便觉得不能自持。于是,一上船,我便向艄夫打探这次去的那个叫“砀山”的地方有没有山,艄夫听了呵呵一笑:“那儿好像还真没有山呢!”我爬到船舱中嘴里嘟噜了一句:“怎么又跟茅山似的呀?没得山,还起个有山的名?”艄夫和父亲听了都笑了起来,接着只听艄夫说道:“这茅山以前是有山的,后来被挖掉填塘了,所以你现在也就看不到了呀。”我听了失落地问他:“那这个砀山也是被挖掉的吗?”这时父亲说:“江南的砀山是有山的,苏北的砀山没有山。”那个艄夫接过话头对我父亲问道:“这名字好像是按照河南芒砀山起过来的是吧?”父亲说:“大概是当初从江苏划过去时改的吧?具体也不清楚是咋回事,只知道那儿酒好,山的事还真的不知道呢。”
这时船已经行驶了很远很远,坐在船舱中的我伴着一个很大的小口酒瓮也醉醺醺地闻得不知了东南西北,耳中只听得艄夫与父亲聊着一些关于酒的话题,还有父亲与他谈论起的生活不易。男人之间的话题似乎总离不开如何挣钱养家,父亲很关心地问这个老邻居:“现在划桨的行当还行不行啊?现在你可是这片河道上最后一个吃这行饭的人了,有没有想过改行呀?”艄夫轻叹一声:“难啊!公路通了,又有机帆船了,像我们这种小船越来越难以为继,可是改行也不容易呵,岁数大了,再学别的学不来了呀。”听到艄夫感慨的话语,父亲也只叹息一声,无语以对。这时我再仔细端详他时,只觉得他与我五六岁时母亲叫他的船去外婆家时的样子是变了不少,看上去比以前更清瘦,腰也佝偻了些,在他前倾着上身,双手握住桨柄划桨时更觉如此。但他似乎对酒却很在行,而我父亲虽然滴酒不沾,但他卖酒,所以他与一个喝酒的艄夫聊起酒话来,倒也十分投机。
过去人常说:行船走马三分险。所以,像艄夫这种行舟赶途的人,喝些酒,我猜想:第一是暖身,第二可能便是行夜船时壮胆吧。
艄夫说起酒来头头是道,一路上只听他说着关于酒的醇淡浓烈。艄夫说:“我在砀山见过出酒,白酒用的窖池是条石筑成的发酵窖,在每次蒸馏出酒后都要把酒糟收起来,然后摊开、再凉凉,接着再堆起来发酵。等池外发酵完毕,再次放进窖池发酵。要经过多次发酵的过程,等窖池的酒糟发酵到家了,酒才可以出来的。”听这话,我便知道他是常去那地儿的了。父亲是卖酒的,对这些当然了如指掌。而且对这条水路更是熟悉,因为爷爷以前开过粮行,贩运粮食,走这条水路父亲自然深谙熟识。而对于酒的小麦糙、糯米绵、大米凈、玉米甜、高粱香这些经验之谈,他俩更是找到了共同语言,一路聊着老家的大麦烧、瓜干酒,再说到糁子酒,真像河水滔滔不绝。
其实要说到这糁子,父亲说它是算不得粮食的。我们家以前也种过几分地,到了锄草的时候,母亲还带着我们去稻田里拔掉这种长有一串像小米粒大小的杂草呢。但这东西便宜,价格不贵,于是烧酒厂便用糁子和碎米来做原料,经过蒸煮、发酵,再添加些酒匙,也就是兑酒的酒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酿造后,最终酿出糁子酒来。其色泽晶莹、透碧,香醇,隽永悠长,入口醇柔,柔而不激。就像艄夫所夸的那样:“喝着畅快舒心,多饮几杯也不上头的。”其实后来父亲告诉我,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糁子酒便宜。在那个年代,农民没钱,员工钱少,小市民们更是如此,也就只能喝些这糁子酒煞煞馋了。就比如这艄夫吧,他这么偏爱糁子酒,我觉得这价格的因素,肯定是占了不小的比例的。而今再想起那些曾经的岁月,让我于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中,慢慢地清空杂念,却能闻到一股岁月的酒香存档于腹中了。再回忆起那个站在船尾处荡桨的艄夫,一路划动船桨,偶尔于中途停泊,燃起他那个绿色的小煤油炉做饭,从舱盖下端出一碗咸菜烧成的鱼冻,泡一碗神仙汤下饭时的情景时,只觉得艄夫那手中的一根竹篙在揳入河水时,在他的双桨荡漾出一圈圈漪涟时,在他熟稔地升起风帆时,便觉得有一首歌谣从双溪的水面飘来,虽然最终被城市噪音遗憾地淹没,但一忆起那段恬静的傍晚,艄夫饮着一杯河水样浑浊的糁子酒,而于时间流逝中看到他脸上泛起的红润,悄无声息地显现于一片暮色晚霞中时,我便觉得有一份慰抚的心绪,在美妙的景色中得以释放。
后来,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艄夫时,约莫已是十几年之后的光景了。那時候见到他时,是在老家的大街上,他已变成了一个衰老不堪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只见他艰难地拖着一个吱呀作响轴承车,跟在他扫大街的老婆身后捡垃圾。我猜想,这个双溪河上最后的艄夫收桨的那一天,一定是他中风的那一日吧?当然,这是我的推断,或许并不准确,但估摸着也差不离。而他最远行船到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寒山寺半夜钟鸣的那会儿,那码头的客船中是否也有过他的篾篷船出现,我则更无从知晓。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我曾坐着他的篾篷船到过砀山,于他的船上看过他喝酒,还有行舟人受冻、熬暑、经风、历雨、扯帆、荡桨,以及种种日晒雨淋、日夜兼程的艰辛模样,像只匍匐于波浪上水鸟似的行游。这种感觉,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我只要一见到水的波动,便似乎总能于心中涌动起一阵难言的伤感情绪,好像记忆中有片轻飘飘的羽毛从那个篾篷船的尾艄处飘起。
忽然间,我觉得今年的春天有点冷,像冬的尾巴还未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