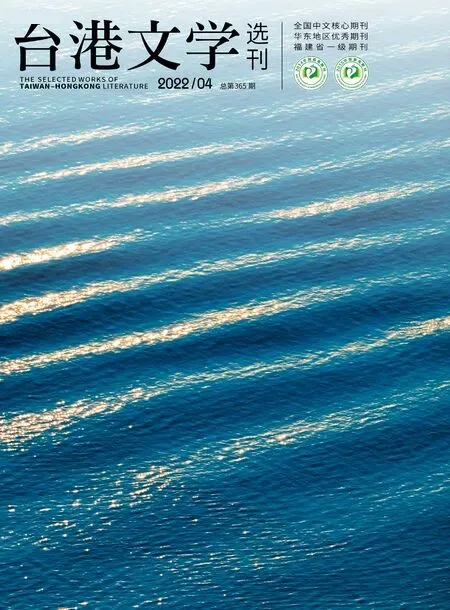代 价(外一篇)
■ 尤 今(新加坡)
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他的裤袋里有一把刀。六寸长,尖而利。握着刀的手,不但冷,而且抖。
“老天爷啊!求求您帮我一次忙吧!”他诚心诚意地祷告,“只要您让我渡过这个难关,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这晚有月,月亮很圆。仰头看月时,他看到的不是月,而是小康那圆得灵活乖巧的脸,才四岁,却懂事得叫人心疼。自从两个月前他娘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后,这孩子仿佛便在一夕之间长大成人,莫说无理取闹,即使有理时也不闹,成熟得叫他这做爹的感觉陌生。
他原本在一家货仓当看守员,收入不多,但省吃俭用,日子倒也不难过。半年前,公司倒闭了,他目不识丁,又无一技之长,在全国经济不景气而处处裁员的情况下,要再重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孩子的娘年轻,不懂得体谅,脾气又暴躁,伸手拿不到钱时吵、闹、喊、跳,最后,收拾包袱,一走了之。
妻子走了以后,他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典当了——能借的,能求的,能乞的,全都借了、求了、乞了。借钱给他的,都明白表示是看在孩子分上借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孩子,使他更难找工作。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时,孩子却染上了肺炎,连夜送进了医院。孩子入院四天了,但他不敢去看他,为的是没有钱缴医药费、住院费。
——孩子是命根,自然不能扔下不管。
他握着刀的手已被汗水浸透了。
“我只干一次,只干这么一次!老天爷啊,帮帮我!我愿付出任何代价!”他再次祷告。
这是一条僻静的巷子。他已观察过了,晚上有人取道于此回家去。在这里抢了,要逃跑很容易,因为巷子当中又分岔出一些支路,只要灵活地转几转,便能脱身。他甚至已拟好了逃跑的路线。
昨晚,11点过后,由这里走回家去的人,他算过了,总共有五个。可惜都不是理想的羔羊。男人,他不敢抢;老人,他不要抢;少年,他不愿抢;剩下的,就只有中年妇女了。
今天晚上,运气好像也不太好。他拿着一份报纸,站在巷口的街灯下,佯装读报,一双眼却毫不放松地觊觎走进巷子去的人。
一个,两个,三个,都是男的。
11点45分。啊,来了。一个约莫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走下巴士,手上提着一个袋子,沉甸甸的,腋下挟着一个古老的黄皮手袋。他听到了自己的身体发出了一种原始的鼓声:噗噗噗,噗噗噗。整个胸膛,几乎承受不了这猛烈的心跳而要爆裂开来了。
等妇女走进了巷子,他扔下报纸,以猫样的脚步跟在后面。
巷子很长,月光很亮,妇女从地上的影子里猛然惊觉他的存在,惊醒地加快了脚步。
良机不可失!他一个箭步飞上前,一只手搭上了她的肩膀,另一只手绕过去,大力捂住她的口,压低嗓子说道:
“别动,别喊!我只是要钱而已!”
妇女蓦然受此侵袭,吓呆了,腋下的皮包、手上的袋子全掉落在地,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他慌乱地说:
“你不要反抗,我一定不会伤害你!”
妇女拼命地点头,他松了手,没想到那妇女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呜咽地说:
“大叔,你可怜可怜我吧!我皮包里的钱,是借来还我孩子的医药费的!”
孩子?医药费?他如遭雷击,脑子嗡嗡作响,但与此同时,小康圆圆的脸却浮了上来。他不顾一切地拾起了地上的皮包,朝原先想好的路子逃遁,背后传来了妇女带哭的喊声,声音无力地撒在阒静的夜空里……
回家后,蒙着被子,嗦嗦地发抖,拼命地压抑自己想哭的冲动,电话铃响了好多次,他都没有去接。
凌晨2点,门铃声突然凌厉而尖锐地射进了他的耳膜。他从被窝里弹跳出来,奔向门边。从门孔望出去,他蓦然张大了口,惊得冷汗涔涔而下。门口站着的,赫然是一名警察。
“怎么来得这么快!”
他头脑混沌,完全不能思想。
这时,门铃再度响起了。
他好似面临山崩似的拉开了门。
警察手上没有手铐,目光温和,语气平静:
“张平先生在家吗?”
“我就是。”他木然地答应。
“我来通知你,你的孩子昨晚11点45分在医院病逝了。”
孩子,病逝?11点45分?
他双脚一软,昏厥过去。倒在地上时,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响自遥远的天边:
“你说过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
香 伯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来。
到老屋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它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面的那一层,还调皮地黏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粘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做饼的手艺,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没人知道。我只记得,当我还在怡保育才小学读书时,便常常看到皮肤好像古铜一样闪闪发亮的香伯,把他做好的香饼,放在纸箱里,用电单车载到菜市去卖。生意很好,才一盏茶工夫,便卖光了。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地生根。
长大以后,婆家在怡保,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来给我,说:“你尝尝,特地订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起;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粘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地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十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话预订,凡是贸然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来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来的饼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梅宏图双手抬起,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已经上传到网站的诋毁我公司形象的文章,与会的网站朋友一定要撤下来,换成形象宣传稿。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齐眉说,那个什么“焦点调查”网站的吴什么你一定要尽快联系上,叫他把那篇狗屁文章删除,打发给他叁伍仟块钱,省得他再像狗似的四处乱咬。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来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失学的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们,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地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地,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
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地照了进来,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源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让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幢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尤今的微篇小说《代价》写得惊心动魄。开头就留下悬念,很抓人。紧接着交代背景,抛出他握刀铤而走险的原因,然后是实施过程,最后付出的代价是,钱抢到了,却没有救下自己的孩子。
作者设计的情节是:他抢的钱是一位妇女借来还她孩子的医药费的。这使得抢劫者“回家后,蒙着被子,嗦嗦地发抖,拼命地压抑自己想哭的冲动,电话铃响了好多次,他都没有去接”。这是这篇小说“出彩”的一个情节,它有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是揭露现实社会底层人生活的状态,二是表明他还是有良善的一面。
《香伯》,香伯是制饼师,敬业,执着,收徒传艺,徒弟急功近利,香伯最后变得“古怪寡言”,“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李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