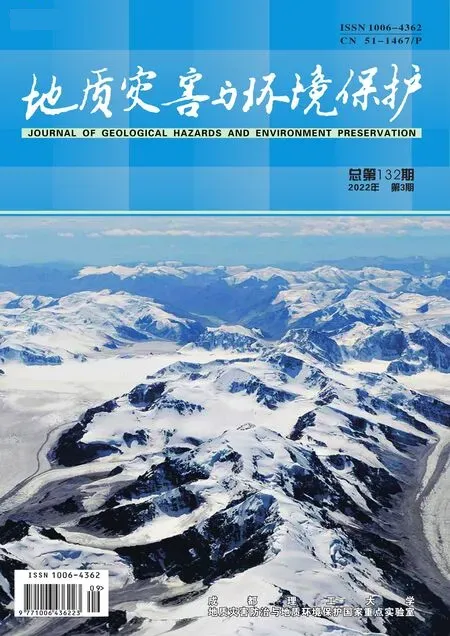高风险堰塞湖风险类型及防范对策
徐轶,蔡耀军
(1.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武汉 430010;2. 国家大坝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10)
1 引言
堰塞湖是由滑坡、崩塌、泥石流、冰川堆积物、火山熔岩流等堵塞河道形成的湖泊,堰塞体以较大的长高比、宽级配、结构非均一性等特点与人工土石坝相区别。典型高风险堰塞湖具有崩塌滑坡方量大、集雨面积大、蓄水量大、溃决历时短、破坏力强、灾害链长等特点,属重大水旱灾害[1]。由于堰塞湖无专门泄水设施,其水位随来水增加而不断上涨,不仅对堰塞体上游影响范围造成淹没等损失,一旦溃决将对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河道沿线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高风险堰塞湖风险防范与应对,对于提升我国防灾减灾能力及健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堰塞湖的风险包括不良地质体堵江致灾的可能性及堰塞湖溃决后可能造成次生洪灾的可能性。我国专家学者对堰塞湖的风险管控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2000年,我国成功处置易贡堰塞湖[2],首开世界上人工处置大型堰塞湖的先河,针对堰塞湖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也自此开始。2008年,唐家山堰塞湖的成功处置,进一步推动我国堰塞湖减灾管理工程和灾害风险管理研究[3]。2009年,我国编制了世界上仅有的2部堰塞湖处置技术标准,其中《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标准》(SL450-2009)对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及堰塞体安全性评定作出了明确规定[4];《堰塞湖应急处置技术导则》(SL451-2009)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堰塞湖处理的技术方法,通盘考虑了处置堰塞湖相关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5]。此后,又成功处置了以舟曲、红石岩、白格为代表的多个高风险堰塞湖,均实现了无一人因次生洪水致死的重大成就,形成了系统的应急处置技术,引领了世界上堰塞湖处置技术的发展。
目前我国堰塞湖风险管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堰塞湖形成后的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且应急处置的风险管理及决策方法仍以既有经验为主,具有较强的探索性。由于堰塞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灾害链系统,孕灾源头在岸坡不良地质体,致灾核心在河谷堰塞区,承灾载体涉及河道上下游及沿线岸坡范围,其风险管控涉及的不确定因素较多[6]。需要对堰塞湖风险从孕育到形成、消亡的全生命周期进行防范和应对。
本文在分析典型高风险堰塞湖致灾危害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潜在堰塞湖险情类型对堰塞湖早期风险识别及其防范措施进行了归纳梳理,从堰塞湖风险评估、风险处置、风险后评估及后续处置等方面对堰塞湖风险应对措施及其研究展望进行了总结,以期为堰塞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2 堰塞湖的危害
堰塞湖是全球性的自然灾害,统计显示22%的堰塞湖在1 d内溃决,50%在10 d内溃决,83%在半年内溃决,91%在1 a内溃决[2]。一般可依据堰塞湖存活时间,将其分为高危型堰塞湖(形成自然灾害险情)、稳态型堰塞湖(形成天然水库或湖泊)和即生即消型堰塞湖3类[7]。典型高危型堰塞湖险情一旦形成,将对影响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危害,并产生各类次生灾害(包括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
2.1 直接危害
堰塞湖直接危害包括产生涌浪、堵塞河道、淹没损失等。其中,滑坡入江引发大规模涌浪,易对沿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内外均有诸多记录。如1963年10月9日,意大利瓦依昂水库近坝左岸发生方量达2.5×108m3的滑坡,涌入水库后产生了高达250 m的涌浪,翻过大坝,造成下游2 500余人死亡[8]。2018年金沙江白格“10·10”堰塞湖由右岸西藏方向的白格滑坡引发,滑坡体从高程3 200 m突然冲下,形成高达62~100 m的堰塞体,堵塞金沙江,并在对岸产生百米高的涌浪。
2.2 间接危害
堰塞湖间接危害包括:
(1) 溃决后产生区域性超标准洪水,且具有洪量小、洪峰大、历时短、破坏性强的特点。
(2) 溃决洪水对水库、梯级水库产生安全影响,造成漫顶、冲刷破坏、连溃等破坏性后果。
(3) 溃决洪水对沿岸居民构成重大威胁,对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4) 溃决洪水对生态的影响,包括河道淤积、河岸冲刷、河势改变、岸坡失稳、耕地砂化,以及高含砂率、高速水流对水生生物带来的灭顶之灾。
2018年金沙江白格“11·3”堰塞湖溃决后形成区域性超标准洪水,堰塞湖至奔子栏河段全线超万年一遇,至塔城衰减为千年一遇,行进到石鼓时达百年一遇,最后平稳进入梨园水电站有序泄放[9]。堰塞湖溃决洪水造成的淹没、冲刷、淤积作用对沿岸居民、基础设施,对河道河势、沿岸耕地、水生生物都产生极大影响。苏洼龙、叶巴滩等水电站设置的鱼类增殖站,遭遇堰塞湖溃决洪水冲击,沿江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被冲毁殆尽,种群刚刚有所恢复的鱼苗在滚滚洪流后难觅踪迹。
3 堰塞湖风险类型
由于温室效应不断累计,全球气候变暖呈加剧趋势,引发高原地区冰川融化后退;在青藏高原隆升背景下,区域地震活动趋于活跃,极易诱发潜在地质隐患;人类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和扩展,流域梯级开发逐渐成形,西部山区临河城镇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各类堰塞湖灾害呈频发态势,引发的次生灾损及风险在不断增大。相对于堰塞湖形成后应急抢险面临的水陆交通不便、周边环境危险、处置时间极为紧迫、排险技术难度巨大、极易造成灾难性后果等难点,早期风险处置具有时间裕度大、措施空间灵活、减灾效果显著等特点,因此,提前布局干预、防灾关口前移是处理重大堰塞湖隐患、提升处置效果的必然选择。有必要展开系统的研究,在堰塞湖灾害发生前及早发现堰塞湖隐患、分析预测潜在堰塞湖风险,进而提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来规避或降低堰塞湖风险。
结合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水文气候、社会经济等特征,对典型堰塞湖风险类型可总结如下:
3.1 已存在堰塞湖(或残留堰塞湖)风险
根据堰塞湖存活时间的统计数据,约91%的堰塞湖1 a内溃决,也有一些堰塞湖因堰塞体结构稳定、湖水上涨后另寻出路,或来水量小,得以长期保留,形成稳态型堰塞湖。如重庆小南海、黑龙江镜泊湖、五大连池、西藏然乌湖,均为堰塞湖成因的湖泊。但此类堰塞湖并非一成不变,其长期演变过程中仍有可能受气候变迁、水文条件改变甚至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影响而产生溃决。
如1911年塔吉克斯坦地震后形成的萨列兹(Sarez)湖,堰塞体高达600 m,是世界上最高的堰塞体,库容170×108m3。该堰塞湖形成已有百余年,但堰塞体溃决的威胁仍然存在,受影响范围涉及4个国家、数百万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水文监测预警[2]。
对于这一类已存在或残留堰塞湖,应开展分布、规模及演变趋势等的调查与研究,评估其成灾风险,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提前进行风险防范。
3.2 潜在地质隐患点的堰塞湖风险
河谷崩塌滑坡堵江是最为常见的堰塞湖类型。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严重、受威胁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西南山区构造地质背景复杂,河谷岸坡高陡,大型崩塌滑坡堵江地质灾害频发,具备形成大型堰塞湖条件。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我国金沙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嘉陵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堵江事件和次生超标准溃决洪水,目前仍分布大量规模巨大的不稳定地质体隐患点,同时该地区地震、暴雨频发,具有诱发崩塌滑坡外部因素,未来发生潜在地质隐患点崩塌滑坡堵江的可能性大,对流域水利水电工程、沿江居民和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如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形成的红石岩堰塞湖,因水位上涨迅速,严重威胁下游居民和天花板、黄角树两座水电站的安全[10]。
有必要针对西南山区具备形成大型堰塞湖条件的地质隐患点加强调查评估、监测预警,建立流域尺度的堰塞湖基础信息管理平台,研究风险防范措施,提前布局干预、进行综合治理。
3.3 流域梯级水电开发背景下的堰塞湖风险
近年来,我国金沙江上游、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加快,将来梯级水库群形成后,可能因蓄水引发不良地质体失稳堵江风险。通过流域梯级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对堰塞湖灾损风险处置时可以发挥上游拦洪减灾、下游腾库纳洪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梯级水库群连锁反应,一旦发生滑坡涌浪漫顶或溃决洪水漫坝,堰塞湖的影响效应及灾损风险将会显著放大,需要高度关注。此外,大型水库区一旦发生巨型滑坡或泥石流快速入库,还可能引发破坏力惊人的湖啸现象,长距离快速传播后对上下游水库大坝造成致命伤害。
因此,有必要就可能对梯级水库群构成安全威胁的地质灾害隐患及避险措施开展研究。一方面,从流域规划、坝址坝型选择等角度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从地质灾害防范和制定流域梯级水库群联合调度机制等角度考虑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构建流域梯级水库开发安全与应急综合管理平台。
3.4 西部高山冰碛堰塞湖风险
我国西部高原地区存在的大量高山堰塞湖,其中部分属于冰碛堰塞湖/冰湖,它们多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海拔3 000~5 000 m的冰川前缘,冰川消融、冰崩、冰湖溃决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灾害链时有发生,构成巨大的潜在堰塞湖隐患。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冰碛堰塞湖存活时间可达数百、数千、数万年。但全球变暖背景下,冰川消融、跃动、崩塌,冰湖快速扩张,冰湖溃决灾害风险持续增加。调查显示,1990~2015年喜马拉雅冰湖总数增加了401个,冰湖面积扩张14.1%[11]。该区域历史上多次爆发冰湖溃决洪水,产生重大次生灾害。2021年2月份印度北阿坎德邦冰川断裂导致冰湖溃决引发巨大洪水[12],冲垮两座水电站,死伤近300人。
目前,我国对整个高原地区冰碛堰塞湖最新分布和近年变化的认识有限,制约了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应高度重视冰碛堰塞湖风险及其次生灾害对流域安全的影响,采用空天地多元技术手段加强青藏高原地区冰湖分布调查,对冰川活动成灾前兆进行全面调查评估、风险源识别和监测预警,积极主动防范冰碛堰塞湖及其次生灾害。
3.5 西部山区临河城镇泥石流堰塞风险
我国西部山区临河城镇多建于狭窄河道的两岸,如甘肃舟曲、云南德钦县、盐津县,人口密集,且属山洪地质灾害多发区,泥石流入江造成洪水阻塞,产生极大次生危害。如2010年“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堵塞白龙江形成堰塞湖,造成近2 000人失踪或死亡,是新中国历史上造成伤亡最惨重的泥石流灾害[2]。2016年“9·17”云南元谋县泥石流,在金沙江支流龙川江上形成堰塞湖,致全县10个乡镇8 000余人转移安置,成昆铁路中断运行[13]。
西部山区临河城镇泥石流堰塞风险一方面是生态环境破坏、水土严重流失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迅速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在规划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西部山区临河城镇泥石流堰塞风险的调查评估及监测预警,研究制定避险措施,同时从城镇规划建设与移民安置开发、生态环境修复与水土保持防治两方面着手,降低致灾风险。
4 堰塞湖风险防范与对策
对于堰塞湖早期风险,可从上述5个方面的风险源出发,对潜在的堰塞湖险情及其灾损风险,加强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具体防范应对措施见表1。对于已经形成的堰塞湖险情,则应针对如何快速应对有效化解其致灾风险进行研究。

表1 防范应对措施
堰塞湖风险应对是在堰塞湖险情出现后采取的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后评估及后续处置工作。堰塞湖风险应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风险评估:堰塞湖险情出现后全面收集评估资料、迅速开展风险等级评估。
(2) 风险处置:制定风险处置方案,开展应急处置决策;对于风险较高的堰塞湖,要通过应急处置尽量降低风险、减少灾害性损失。
(3) 风险后评估及后续处置工作:对应急处置后的堰塞湖风险及其上下游影响区潜在的次生灾害风险进行评估,当后续再次堰塞风险高、流道不满足设计洪水标准、可能发生重大险情灾害时,应进一步开展应急后续处置以降低和消除风险。
4.1 风险评估
科学合理评价堰塞湖淹没及溃决致灾风险是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和避险方案的重要前提。国际较为常用的堆积体指数法(BI)、无量纲堆积体指数法(DBI)等均只用于评价堰塞体的安全[2],并不能对堰塞湖上游淹没、堰塞体危险性、下游溃决洪水影响等整体致灾风险进行评价。我国《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标准》(SL 450-2009)基于风险的理念,建立了考虑堰塞湖致灾、孕灾、承灾全过程的全因子评价体系,并提出了堰塞湖风险等级量化计算法。为便于应用,同时提出了简化后的6因子风险等级快速评估方法,按堰塞体危险级别、堰塞体溃决损失严重性分级等综合确定堰塞湖风险等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堰塞湖致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仍在不断完善。堰塞湖溃决控制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相关研究逐渐深化,基于堰塞体溃决机理的堰塞湖风险快速评估预测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如构建了由上游来水量、库容、堰塞体形态、堰塞体物质d50组成的堰塞体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14]。但是,堰塞湖风险评估仍面临基础信息匮乏缺失、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困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评估资料快速获取能力。同时,风险评估应进一步向综合考虑生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损失等致灾后果多因素综合性风险评估发展,由静态评估模型向考虑致灾演变进场动态评估方法发展[15]。
4.2 风险应急处置
目前国内外针对堰塞湖应急处置开展的研究均较多。我国自易贡堰塞湖开始堰塞湖应急处置的系统性研究工作,2009年颁布实施的《堰塞湖应急处置技术导则》(SL451-2009)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堰塞湖处理的技术方法,对风险应急处置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进行了系统总结。水利部于2019年颁布《水利部堰塞湖应急处置工作规程(试行)》(办防[2019]103号),进一步规范了堰塞湖水利应急处置工作。堰塞湖风险应急处置相关规程、规范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采用“排险与避险结合、工程与非工程措施互补,避免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的策略是我国堰塞湖风险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在排险过程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充分利用自然或人工力量减轻灾害[16]。历经西藏易贡、四川唐家山、甘肃舟曲、金沙江白格等近30座堰塞湖应急处置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堰塞湖风险处置技术体系,引领世界堰塞湖应急处置技术的进步。
随着水文监测及信息技术、堰塞体溃决洪水预测技术、工程抢险技术及装备的不断进步,应急处置技术仍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是,堰塞湖风险处置仍存在应急决策成效差、快速可控的抢险技术装备缺乏等薄弱环节。需针对不完整信息条件、情势紧迫条件下快速决策响应机制与方法开展研究。此外现有技术装备处置效率受水陆交通、装备、施工作业条件等因素的严重制约,还难以适应高风险堰塞湖“争分夺秒”的应急抢险需求。应进一步加强堰塞湖排水疏通技术及开槽引流人工控泄技术的研究,强化快速抢险专用装备的研发,进一步提高堰塞湖风险处置技术水平。在国家“13·5”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标准化的堰塞湖疏通排水技术、堰塞湖控溃技术、引流槽高效连续开挖专用装备、溃口自适应控溃装备即将面世。
4.3 风险后评估及应急后续处置
应急处置后,堰塞湖风险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风险。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同一地点重复形成堰塞湖并溃决的事件。如台湾云林县草岭地区在1862年、1898年、1941年、1942年、1951年、1979年、1999年曾发生过7次滑坡堵江事件,多次产生严重危害[2]。2018年10月10日至11月3日,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金沙江白格和雅鲁藏布江加拉,分别在同一地点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和冰川泥石流,滑坡、冰川泥石流堆积物分别两次堵塞金沙江和雅鲁藏布江干流形成堰塞湖。四川岷江叠溪堰塞湖自1933年溃决后,多次发生局部溃决并引发洪水。因此,开展堰塞湖风险后评估及后续处置,避免堰塞湖风险重复产生、减免次生灾害十分必要。
堰塞湖风险后评估及应急后续处置是对应急处置后残留堰塞体、泄流通道、堰塞体物源区斜坡、堰塞湖区重大地质灾害体开展综合评估和后续处置。通过综合评估安全风险,制定后续处置方案,进一步降低和消除堰塞湖后续风险。有条件的堰塞湖还可进行永久性改造利用,如2014年云南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从除害兴利、变废为宝的角度出发,将堰塞湖改建为水电站,既消除了堰塞湖风险隐患,又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
堰塞湖风险后评估及后续处置的关注点是残留堰塞体和不稳定边坡。残留堰塞体与人工土石坝相比,具有不连续宽级配、非均质等典型特点,堰塞体安全评估及其拆除或加固技术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一些部位因特殊的地形地质条件,崩塌滑坡频繁发生,造成堰塞湖事件频繁出现,应对高危边坡、频发堰塞湖的综合治理措施进行系统研究攻关。
5 结语
高风险堰塞湖的风险防范及应对属世界性难题,其信息快速获取、风险快速评估、风险处置与快速解危、风险管控预报等方面技术仍较为薄弱。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堰塞湖已经呈现高发态势,关口前移、从预防着手,是高效防范和减轻堰塞湖灾害的必然选择,有必要在堰塞湖灾损发生前及早发现隐患、分析预测潜在风险,进而提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来规避或降低堰塞湖风险。堰塞湖风险评估理论及评估方法取得明显进展,但相关知识的普及率较低,影响了堰塞湖应急处置决策成效。堰塞湖应急处置专用装备开始取得突破,但高效的进入运载技术仍是一大短板,应针对堰塞湖应急抢险特点开展系统研究,以期整体提升重大堰塞湖灾害应急处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