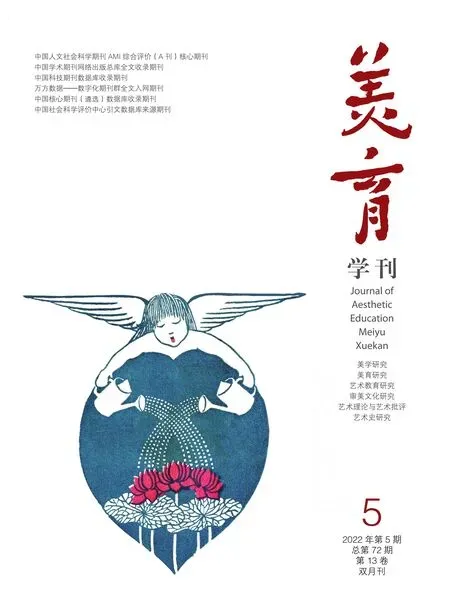翁贝托·艾柯的中世纪艺术美学研究管窥
——基于《中世纪之美》的思路述评
苏梦熙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中世纪为人类遗留了许多艺术珍品,但却未能形成系统性的艺术理论为自己辩解,这使得一千多年的艺术创作被后来的古典主义者嗤之以鼻。古典主义批评那些衣着褴褛的苦行圣徒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瘦骨嶙峋的基督木雕、哥特式大教堂高而尖的塔楼、玻璃花窗前昏暗礼拜堂的堕落艺术风格。致使后来的人们不断询问:中世纪真的有对感性的热爱与以其所定义的美吗?中世纪人对美的描述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艺术?国内近期出版的翁贝托·艾柯最重要的艺术美学研究著作《中世纪之美》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应之一。他试图梳理中世纪艺术实践与神学美学的矛盾与融合,并勾勒出中世纪艺术理论的大致轮廓,重点探寻中世纪人所推崇的生机之美是如何体现在艺术品之中的,而这也是以维也纳美术史学派为代表的西方艺术风格理论研究的倾向所在,自温克尔曼时代以来,美学与艺术史学再次联合,但这一次并不是为了古典艺术,而是为其所鄙视者——中世纪艺术来正名。
一、中世纪艺术美学中个体与共相的结合
人们说中世纪没有艺术理论仿佛是有道理的,这并非中世纪对艺术的轻视所造成的,而是与中世纪美学的论述方式有关。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称,善和美在本质上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二者都建立在同一个真实的形式上面;但它们的意义却不相同,因为善与欲望相对应,其作用恰如最后因(最高因),而美则与知识相对应,其作用有如形式因。各种事物能使人一见而生快感即称为美。朱光潜在评价中世纪美学时也提到,美与善合二为一,造成的结果便是“通过感性事物的美,人可以观照或体会到上帝的美。从有限美见出无限美,有限美只是到无限美的阶梯,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但艾柯指出,在艺术实践层面,中世纪的经院美学并不区分美和功用或善,而是试图在形而上的层面将美与这些价值融合起来。
首先,艾柯驳斥那种认为中世纪人不懂将美的形而上概念与他们对艺术技巧的认识联系起来的观点。他指出,无论是在信徒还是在神职人员那里都能发现中世纪人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有着感性的回应,并有意识地融入了神学对于美的理想化表达。回顾中世纪的艺术创作,我们确实能找到许多案例,例如早期哥特式教堂的肋架拱顶,像伞架微微撑开,流畅的曲线联结着建筑华丽的支撑柱,就像灌木低垂生长的形态,又像花朵绽放,它不仅优雅,而且把视点往上拉,还掩盖住了拱面的接缝,展现了教堂力的结构所在;教堂外部扶壁拱的发明是中世纪人对于一种轻灵美感的重要追求,哥特式教堂用扶壁拱把罗马巴西利卡建筑的侧廊屋顶提升到视点又不是对屋顶的支撑,把建筑物外部变为骨架,显得轻盈高耸。将中世纪人所追求的形式美与神学思想融合表达到极致的是盛期哥特式建筑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设计和修建。从教堂整体设计来看,内部拱顶距地面36.5米,扶壁和爬墙柱向外剧烈凸出,充分强调了纵向线条对于教堂高度的延伸,外部扶壁拱呈沉重阶梯状,给人以沉稳敦厚的感觉;从教堂装饰上来看,著名的圣母彩色玻璃花窗在内殿上方呈现出光色折射的幻境,地面上神秘的迷宫则让人在其中摸索着道路,进行智力的游戏。这所教堂之所以完美融合了力学、数学与宗教的知识,是因为工匠对于形式的和谐与美有着自己独特的融合,而不是专门听从于哪一种知识进行修建。
艾柯指出中世纪人对美的看法既有对美的共相的指认,又有对自然经验的吸收。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来说,低级的美是物质世界提供的感官享乐,而高级的美是脱离物质的,只有在对上帝的领悟中才能得到。但是作为概念论者的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却指出,普遍概念的有效性存在于事物本身,也就是说,美的共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的事物存在。在小说《玫瑰之名》里,艾柯借主角之口重新坚定了这一思想:玫瑰之名尽管是想象力的一个产物,但是显而易见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作为事物之根基的一个产物。因此艾柯才将小修道士的春宵美梦写得如梦幻一般,将身体的概念之美与欲望的动态之美相融合。除此以外,艾柯还与另一位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布里丹(Jean Buridan)对共相的阐释立场一致,按照《玫瑰之名》中主角威廉对马的解释,“马”这一普遍概念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对世界的认识形成实用性的观点,而非由于“马”这一概念来源于更高的理念。在神学体系主宰知识界的同时,中世纪经验论者前仆后继,既想要保留美的共相论断,又要为美的个体性振臂高呼。
艾柯认为,中世纪艺术最高的目的是对所有想象的、超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存在于被默观的物体和向超越开放的宇宙之间。波伊提乌斯(Boethius)的“宇宙音乐”理论正是符合这一观点的艺术美学思想。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指出天体的和谐运行产生一种至高的音乐,但是人类由于感官的不足而无法听见。宇宙音乐催生了“美存在于宇宙循环中,存在于有规律的时间流逝和季节交替中,存在于元素的组成中,存在于自然的节奏中,存在于生命的运动和精神中:简言之,存在于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总体和谐中”的构想。这一构想事实上还是基于人类自然经验感性的想象。除了这样宏观的宇宙艺术实践之外,在微观艺术实践中也具有和谐的比例之美的运用。艾柯回归到他熟悉的符号学领域,指出比例的原则在建筑、纹章、文学语言、乐谱的书写等方面的实施甚至对中世纪圣像学产生了影响。这种从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中萌生出来的美指示着柏拉图思想的应用,用数字四来举例,“四”是人的身体(人展开双臂的长度与身高等同)、世界的方向(四方)、世界的时间(四季),而最终,四从形式数字转化为道德数字,指示一个人的道德诚实正直。美的形式也是善的形式,这是微观艺术上升到宏观艺术的根源,艾柯以琴尼尼(Cenino Cenini)的《艺匠手册》、奥内库尔(Villard de Honnecourt)的《画集》等著作为例提醒读者,中世纪所有关于具象艺术的论述都展现出一种野心,即想要在数学上将具象艺术提升至与音乐一样的高度。
二、中世纪的质性美学内涵及其表现
宇宙音乐理论并不是中世纪艺术美学的全部,艾柯将中世纪人这种对于比例的喜好概括为量化美学。与此不同,中世纪另一种对自然物的审美感受,就是中世纪人对于光与色彩的热爱,被艾柯称为质性美学。后者甚至比前者(量化美学)更加自为自主,“他们对于比例的热爱最初表现为理论学说,后来才逐渐进入实践领域,形成准则。相比之下,他们对于色彩和光的热爱是一种自发的反应,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直到后来才在中世纪人形而上学的系统里得到科学的表述”。也就是说,中世纪人首先是出于感性才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光色体系,而后再试图给予其超验的意义。
中世纪人对于颜料制作的技术把握程度比今天所想象的还要宽广,他们认识到了色彩与光照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到牛顿时才被有意识地整理成为科学学说),他们观察到玻璃因其颗粒的大小进行色彩散射的情况,因此通过研磨有色粉末来改变色度;除此以外,中世纪人对于金属在色彩中的运用也是遵循了光照规律,尤其是他们发现铜和金等金属其实呈现了一种暗红色,这使纯金箔和红色颜料在中世纪的艺术创作中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常搭配在一起)。艾柯也提到了中世纪的色彩使用情况,包括色彩种类繁多,色彩搭配强烈。例如林堡兄弟《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15世纪)里的插画以大面积的宝蓝色和朱红绘制而成,白色、淡绿及土黄色点缀其中,形成非常愉悦的观感;爱尔兰《凯尔经》(8世纪)福音正典表薄薄一页上同时出现了十余种色彩,光红色就有三种,黄色和橙色也相邻出现、互相区分,使得背景中的古典宫殿拱廊斑斓如彩虹;还有藏于纽约摩根图书馆的贝雅图斯抄本(10世纪)中的启示录以并列的红黄绿三原色色带作为背景,使画面增添了强烈的视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对色彩的运用或许与近东艺术有关,著名的图像学家埃米尔·马勒指出,萨珊王朝的挂毯和拜占庭的织物都模仿了波斯艺术,它们或呈金黄色,或呈火红色,有时候也呈灰色,但总会镶嵌上蓝色或玫瑰色。

不过艾柯发现,中世纪美学中存有一种将量化美学和质性美学共存的思想考量,这就是象征和寓言的文化特征。如果你是一位中世纪人,那你的生活中将会出现烦琐的各类神秘符号,而你要依靠对基督教知识的学习才能在生活中作出正确选择。“在一般情况下,中世纪人会就因果关系,从起源解读事物。但是中世纪人的头脑中也存在一种思维‘捷径’,这种理解模式不将事物之间的关系看作因与果的联系,而是看作意义和目的织成的网。”这样看来,中世纪的象征体系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固定的,有时需要依赖人类充沛的想象力与直觉。在诸多手抄本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神圣图像的形成往往与各式各样的审美认知有关,如荆棘中的红玫瑰和白玫瑰象征着被迫害的圣女和殉道者,这完全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联想。
中世纪的世界“像一本由上帝之手写就的书”,其间万事万物都披上了上帝的神性光辉。这意味着中世纪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艺术”(他们甚至不使用这一名称),“人们将自然视作对超自然的庞大的、寓言式的再现,而艺术也被置于同一层面上”。无论是诗篇、传奇,还是哥特大教堂的雕像与花窗故事,都在讲述超自然发生的一切神圣故事,观者则通过visa(意为看,也包含被感知、被知晓的意思)接触美且善的形式,这是一种智性的认知行为。艾柯指出,正因为中世纪美学是将智性放在优先地位的理论(例如在阿奎那的理论中),决定美的事物审美体验的显然是其客观特性,这些特性依然需要在看见中被实显化,它们是需要被某人知晓的特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中世纪美的客观性的看法。
三、中世纪哲学与艺术中的“有机体之美”

艾柯提到中世纪对“有机之美”的创造,他认为有机体之美比形式之美的表述更符合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美学,这是因为在阿奎那这里,“存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形式与质料合二为一而不只是形式的呈现,有着更为深邃与坚实的含义——生命。艾柯举阿奎那关于人的存在的描述作为例子来说明:在人的身上,弱势的感官能力被手的优势能力添补了,手解放了人的其他器官,促进了人脑的发展,人的直立站姿使人脑的敏感得到保持,同样使视觉得到异常发挥——观赏世界及世界之美。可以说,阿奎那的功能主义美学理论为贯穿中世纪的情感提供了系统化的表达。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画》中将哥特式大教堂与阿奎那关于空间的观点进行整合,提出“系统空间”(systematic space)这一表达。潘氏指出,中世纪艺术史的使命是将曾经众多的个体(无论彼此之间多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融合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共相)。雕塑也摆脱了古代幻觉的所有痕迹,将一个充满绘画感和激动人心的表面、一个被光影打散的表面,转变为一个立体浓缩的表面、一个由线性轮廓勾勒出来的表面。
艾柯指出,除了阿奎那,中世纪著名的实在论者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的“此性”(haecceitas)理论也是中世纪有机体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此性”,指的是一种赋予物体个性的特性,它的功能不是完善形式,而是将实在的个性给予复合物。原本依据阿奎那的视角,感知有机体意味着将其作为本质的范例来感知,但对于司各脱来说,单个物体就是其自身。赋予个性的原则并不与事物相结合,而是在逻辑上不分彼此。实际上,“此性”理论是关于个体独特性的描述。艾柯指出,这一理论是司各脱对于他所处文化环境的哲学回应。与人们想象中的中世纪不一样,13世纪的中世纪文化环境是极为重视个性和多样性的,对艺术中类型的敏感性逐渐被对个体的敏感性取代,从看似枯燥的学院争论中诞生出来的形而上学,却实际上回应了当时的文化气候。
与中世纪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艺术气氛不同,那时的社会残酷而多磨难,虽然从事工匠(艺术家)工作的人已经进入行会,有了一定的生命与财产保障,但也常常面临着失业和来自比自己更高阶层的压迫,更不要说席卷中世纪的瘟疫与各种疾病,无论哪个阶层都难以幸免。这么看来,中世纪人对于自然美的喜爱离不开时代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的珍惜,也许正因为世界充满饥荒与斗争,所以人们对于生机勃勃的自然充满期待,把再现自然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勒指出,哥特式教堂柱头上松展的芽孢、舒展的叶片,以及整个以树枝、玫瑰花茎和葡萄藤来作为教堂门楣的装饰,这些装饰没有特殊的象征意图,艺术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美丽而选择了它们。饰物上的叶子经过了简化,但并没有变形;内在的结构与整体的形态依旧是天然的,我们很容易辨别出其中的大部分植物种类,例如圣沙佩尔教堂中的金凤花,布尔日大教堂柱头上的羊齿花,巴黎圣母院各个角落里出现的车前草、菊花等。绘画艺术亦如是,在著名的《马内塞古抄本》(14世纪前后)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甚至是在战争杀戮之中,自然也必不可少,与士兵的奇装异服形成绝妙的撞色效果,更不要说在广为流传的《独角兽在花园里休憩》(16世纪前后)的挂毯图像上,各色花草围绕着独角兽,形成一个天然的规范,使它得以被愉快地驯服。
值得注意的是,有机体之美的理论不仅被亚里士多德派的经验主义神学家所持有,中世纪后期流行的神秘主义也并未远离这一观点。德国艺术史家,同样也是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后学的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指出了神秘主义对有机体之美的间接推动作用。沃林格用李格尔所创立的“艺术意志”这一概念来揭示北方日耳曼人在创作哥特式教堂时的心理变化,一个从弃绝世界到认可世界的过程,“由于人类灵魂神性的观念,一股更为柔和的感觉的浪潮涌入到了严峻的北方世界,不但是神性,而且还有自然也都被纳入到精神性的感觉经验范围里”。“自然曾经被经院主义理解为僵硬的存在,现在却成了神的家园。”按照沃林格的主张,因为神秘主义的到来,感性美与超越美融合得更加天衣无缝,艺术更具抒情性。
四、中世纪艺术美学与风格学研究相呼应
中世纪并非没有艺术理论,只是他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与今日相异。艾柯《中世纪之美》一书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辨明与分析,得出了“中世纪艺术理论的两个主要特点是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一结论。他总结说,中世纪艺术是根据物体自身的法则来构造物体的科学,将功能与美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科学的艺术,什么都不是。艾柯对此进一步解释道,在中世纪人看来,艺术不是表达,而是构造,是以达成特定结果为目的的操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世纪关于艺术的特性对于后来的古典美学来说是异类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早已把艺术品当作一种传达思想内涵的形式物,故而其大力支持古典艺术,而从未去考虑艺术是一种制作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艺术品的“未完成性”是后来现代艺术而不是古典艺术关注的,但是中世纪人早早地深刻把握住了这一观点。
艺术品的“未完成性”着眼的是艺术这一构造过程背后的精神能量的发散,这也是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对中世纪艺术研究所持的重要主张之一。在德沃夏克对哥特式教堂立面的人像的分析中,他指出了这些人像紧绷的外表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观众“紧张的情绪”,这些造型背后除了日耳曼民族天生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开始详尽观察之外,展现的是精神背后的生命图景——雕像为何要眼窝深陷,因为生命整体的运动是迎接悲剧、歌颂牺牲,以及怀抱去往天堂的希望。因此德沃夏克说道:“这种新自然主义是从一切生活关系精神化的倾向中派生出来的,而一种具有世俗理想主义特点的艺术新取向也产生于这同一来源,换句话说就是艺术与那些感动人性的观念及情感的新关系。”沃林格谈到北方哥特式艺术的曲折线条时也强调了其情感“表现”的特点,由于情感压抑,“铅笔在纸面上狂野、剧烈地运动,取代优美、圆转、有机和谐曲线的是一种坚硬、角状、不停地被切断的曲折线条”。中世纪艺术依靠与自然、生命之间紧密的关系进行再生与转型,并从中滋生了文艺复兴艺术。到了17世纪意大利雕塑家贝尼尼的手中,特蕾莎的幻象成真,肉体所感受到的真实痛苦与精神所领会的甜蜜以明晰的方式向观者袒露。
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对中世纪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像艾柯这样立足于对中世纪朴素自然观的理解之上,他们更偏重对于精神图景的整体把握,例如李格尔用“艺术意志”来阐述罗马晚期的美术状况,这样的研究方法有时会过分强调民族与环境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精神”(观念史)自身内部的嬗变。事实上,正是中世纪人最先创造了“自然女神”这一神祇(与古代哲学中所说大地之母不同),这个拟人化的寓言形象在自己的作坊日夜锻造新的生命体,让死亡无法摧毁世间所有的生命。虽然古老的经院主义以层级划分宇宙,将万物分门别类地放入合适的秩序之中,试图以行动跟随存在来解答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哲学家们才发现这一观点与现实是背离的,是“活动的源初方向才规定和设定了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行动,这才逐渐走向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与作用。
艾柯总结道,中世纪美学对艺术的认知不是仅停留在对客观性的感性直观,只有经历抽象的逻辑推论之后,只有在对幻象的反思之中,智性才能知晓可感物。审美体验虽然使人愉悦,但是艺术家要做的恰恰就是要超越这些对艺术感性美的追求,最终触碰到上帝的智慧。正如中世纪著名的泛神论者尼古拉(Nicolas of Cusa)指出,当艺术家在一段木头或一块石头上寻找国王或王后的面容时,他将木头或石头中除了面容部分之外全部舍弃,那面容在被他雕刻出来之前,对于他(艺术家)的眼睛来说还属于未来,但是对于他的精神来说却已经成为现实了。延续艾柯的视点,我们会看到,中世纪艺术之所以能够在艺术史上承载更多的意义,是因为其最终还是走向了自然的怀抱。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其早期作品《哥特复兴》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哥特风格之所以在18、19世纪的英国再度复苏,是由于普金等艺术家为其建筑的自然原则辩护,这一自然原则就是对于古老植物的研究,是罗斯金所说的对自然真实的书写。据于此,我们看到了中世纪在近代自然主义艺术中的复苏,当然,借由有机体之美,它在现代抽象表现主义中同样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