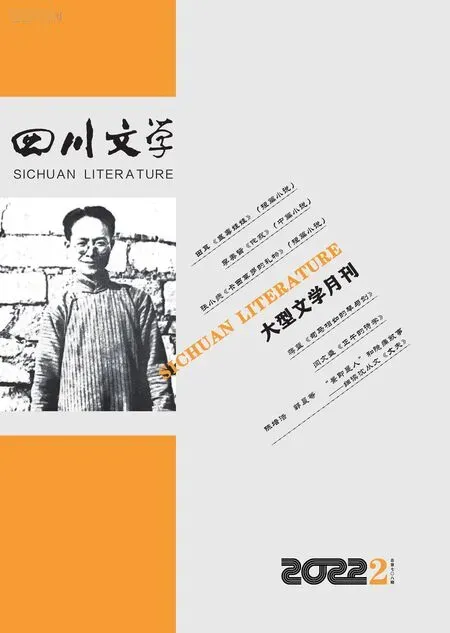匠人记
□文/虞燕
补网师阿月
她说,渔网从海里拖上来,就跟英雄从战场归来一样,挂彩很正常,得修复,得医治,拾掇得好模好样再出场。
她在渔网边踱了几步,眼睛探照灯般来回扫射,蓦地,半蹲,双手拽住网的一边,扬起双臂上下摆动,渔网起伏如绿色的海浪。一缕头发从她耳后溜了出来,有节奏地颤动。
周边三三两两几人,均心不在焉,在岛上,渔网、织网、补网实在常见,没啥看头。某渔船的船老大小跑过来,神情中带着探询,又透着点恭敬,等着她对那些网的命运给出结论,或者,报出修补的费用和时间。她从不扭捏,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像嚼炒黄豆,咯嘣脆。
临走,她抬起脚尖,轻轻触碰了下渔网,仿佛那些尼龙、聚乙烯、聚酯等合成纤维织成的网是她老友,得告个别。然后,掉转身,两只手插进衣兜里,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地走了。
她是岛上的补网高手,男女老少通通叫她阿月老补网。这个老,不是指年纪,是说她手艺好,阿月不到三十岁就被叫作老补网了。阿月的父亲是渔民,阿月的男人也是渔民,当然,这跟她从事补网并无绝对关系,但似乎又与之脱不了干系,小时候,她母亲常被父亲叫去补网,那会儿,渔网破了,渔民们率先想到自己的女人,会补网的便拎着一大篮缠满线的梭子奔赴码头和渔船。小阿月跟着母亲,好奇地看着母亲忙活,无聊了,一个人在渔网上打滚、数浮子。有一次,家里的小抄网被老鼠啃了个洞,十二岁的阿月先修剪,后手持梭子,穿来绕去,除了网眼排得不够齐整,其余没毛病可挑。成年后,阿月对补网的热情远超其他人,推敲细节,总结经验,男人船上的渔网正好被她拿来练手。
不知什么时候起,岛上的渔船若需拼网补网,头一个就找她。
阿月生得小巧,肩窄腰细腿伶仃,屁股却大,跟整个身子不大相称,像一条鳗鱼吞进海螺,卡在了中段。有人说长年累月坐着织网补网,屁股会坐大。这也许是真的。她的手很瘦,手指似乎常年缠着一圈布胶带,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手,不是这个手指就是那个手指,像戴着意义非凡的戒指,舍不得摘掉。
补网第一步,叫“定眼子”,就是给断开的网绳配对、重新编织网眼。这一步最为关键,若配错,接下来的步骤无论做得多完美,网都废了。阿月拉过渔网,如钢琴师摸到了钢琴,手指在千丝万缕的网绳中跳跃,很快,几个绳头被她抽出,紧捏于指尖,另一只手伸向工具箱,一把竹梭子听话地贴在了手心。梭子头尖身细,崭新的网线缠绕得满当当,来回几个穿引,原本断开的渔绳打出了多个绳结,新的网眼形成了。
如果说“定眼子”是定音,那么,接下来便是行云流水般的演奏了,修剪断开的绳头,顺着破洞的边沿编织,梭子如鱼在海里游跃,牵着网线划出各种弧线,她的一双手上下翻飞,那圈布胶带宛若一只白色的蝴蝶,恣意蹁跹。
“演奏”从低音滑到高音,又从高音徐徐降落,一片网修补完毕。
补网师的工具箱实在普通,灰不拉叽,与随处可见的旧物什无异。装了补网刀,剪刀、梭子多把,大小长短不一,尺板却无几,因为阿月几乎用不到尺板。对于一个优秀的补网师来说,该编多大的网眼,全凭临场发挥,网具那么复杂,破损程度更无法预估,岂是几个定好尺寸的尺板能胜任的。医用布胶带跟蛤蜊油混于其间,有些突兀,好像正规军集训时突然跑来了两看客,却是阿月老补网出门补网必备品。海边补网,风吹日晒,蛤蜊油或可缓解面部手部皲裂,而割网修剪难免受伤,扯一段胶带包上即可,即便后来有了更方便的创可贴,她也要再粘一层布胶带,粘得牢牢的,才不影响工作。
有个裁下的网片,面积不小网眼却小,我捡起,觉得可以缝成小网兜,去河里捞鲫鱼和泥鳅。正补网的阿月瞅过来一眼,下了结论:“不好,鱼会跑光。”补网间隙,她将网片从中间劈开,剪子蜻蜓点水似的点了几下,捏起,抖了抖,剪断的线头纷纷而下,剩余部分夹于两个膝盖间,开始编织。没待看清,网兜已成,网底小,上面慢慢放大,深度恰好。我接过来,碰到她的手,触感像外婆的,干而糙,能把蕾丝衫勾出丝来,而她的年纪跟我大姨不相上下。
阿月的梭子可比她的手滑溜多了。这些小工具,以多年生的青竹为坯料,表面平整,竹质均匀,加上长年与肌肤、网线厮磨,被汗液甚至血液浸润,愈加色泽沉稳,肌理温润,散发出温吞的旧气,还有,挥不去的主人气息。它们顺服于阿月的手指和手心,熟滑地穿过网眼,打上网结,一张又一张的网自此重生。
补网不同于织网,补网是补救,是修复,无章法可循,得看“病”下“药”,灵活机动。补网师拿起梭子,就如医者手执手术刀,必须下得准而稳。经验、胆大、心细、责任心,缺一不可。渔网创口各异,被鱼噬咬的,被礁石割裂的,被船沿蹭刮的,辨别、清理“伤口”后,选择线号,找到合适的搭界点,横着编,竖着编,一个个网眼伸腰蹬腿,手拉着手,一眨眼就连成了片,奔着与上下左右“接壤”而去。填补一个普通的窟窿,花不了几分钟。若网线颜色雷同,还压根看不出修补迹象,相当于手术很成功,没留下一点疤痕。
岛上的人说阿月“粗头粗脑”,意思是说话动作等大大咧咧,不是个细腻、婉约型的,但她一补起网来就不“粗”了。像修补网眼,对补网师而言,简单,却又不简单。补好的网眼大小直接关系着收成,网眼大一分可能放跑捕到的鱼,小一分呢,又可能把不该捕的小鱼苗兜上来。阿月修补的网,网眼都刚刚好。这个刚刚好里,铁定少不了细致。而渔网“上纲”和“下纲”的比例、网叶连接在“网纲”上的跨度、浮标和铅坠挂什么位置效果最佳……更需费心琢磨,反复与船老大沟通,再结合实际生产不断修正。
让残破的渔网物尽其用,变废为宝,是补网师的责任,也是挑战,更是荣耀。网被礁石挂住,网线断得横七竖八,大部分被撕烂,损毁太严重,已经失去修补的意义,阿月就想办法把两张网拼成一张。比起补网,这个工序更繁杂、严谨。渔网摊开在地,像一条大鱼被尾部沿背脊直劈头部至嘴端,大幅度展开,阿月拿着卷尺,撅着大屁股,从这头蹦到这头,又从上头蹦到下头,忙乎一通后,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操起大剪刀“咔嚓咔嚓”。彼时的阿月是裁缝,渔网如布匹,裁好的待用,边角料、废料弃之,梭子成了针,她坐在矮凳上穿针引线,用上多种编织法,终将原本不相干的网片“缝”在了一起。一张全新的渔网诞生。
阿月捏着网,提起梭子在头发上划了两下,说:“日子缝缝补补地过,渔网当然也要缝缝补补地用。”
修补或拼接后,渔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这个“生命”也得讲究质量,拼好补好只是表象,它必须经过幽昧的深海和乖戾的鱼群的检验。一张重生的网,若在实际捕捞中不易破损,少挂鱼,生产效率高,才是成功的,才彰显出补网者的高超手艺。
不是所有会补网的人都有资格被尊称为补网师或“老补网”。
休渔期,码头及其附近,拖风网、围网、拖虾网、大捕网、雷达网、流网……常常聚集,要么堆如座座小山,要么像巨蛇趴于路的两边,逶迤着伸向远方。来自深海的鲜腥气味四处弥散,熟稔地羼杂进岛上的空气里。
阿月领着她的补网队浩浩荡荡而至,无须多言,她们一个个迅速散落在渔网间。她们头上戴的草帽,盖的毛巾,样式花式皆素洁简朴,未坐上小马扎先提起梭子,这个起范儿,竟有那么点赏心悦目。
渔网破损处,为防止漏点,扎起了五颜六色的布条,阿月朝我们几个招手:“看,多喜庆,像插了彩旗。”她随手扯掉一个布条,撑开网,伸出手掌比一下,而后,一手持梭子,一手拿剪子,轻捷地舞动。碰到心情好,她会一边补网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比如,海蜇为什么呒魂灵,毛虾怎么帮鲤鱼跃龙门,我们跟浮子似的缀在她身旁,一动不动。她还问我们,以后要不要跟她学补网,几个小孩齐齐点头。然而事实是,后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会补网,甚至没有一个留在岛上,成年的我们已经不认为补网是个厉害体面的行当了。
日头西落,无数个橙红色的光晕从水天交接处涌来,涌上渔港,涌向马路,渔网一半在霞光里,一半在隐晦处。补网队准备收工了,阿月水杯里的水已饮尽最后一滴,原本缠满线的梭子也都空了,她起身,跺几下发麻的脚,身后,是她的补网之路,修补好的渔网呈半摊开姿势,静卧一边,她瞥过去的目光有一点温柔,又有一丝得意。
阿月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安家,把母亲接了去,可阿月没住几天就回到了岛上,说手痒,城里又没网可补。岛上的人说她真不会享福。
如今,阿月胖了,背不挺了,补网要戴老花镜了,但她一坐到渔网边上,架势依旧。
木匠全福
圆滚滚的粗木头被捆绑于大树,一把大锯子架上,全福和他的徒弟左右各站一边,一个上一个下地拉锯子,来来回回。“嚓啦,嚓啦”声不绝,锯末纷纷扬扬,乍一看,以为树下飘起了雪。终于,将木头如鱼鲞般彻底剖开,全福用手指轻轻地敲,微仰着脸,两只小眼睛眯起,跟戏迷听到了好曲似的。围观众人便知,这是个上好的木材,主人家乐呵呵地奉上好烟,全福手上点一支,耳朵夹一支,不说话,绕着木材转圈,青烟氤氲间,他一脸沉思状。
这是全福开工前的老习惯,大概要把接下来的锯、砍、削、凿、刨等一系列工序在脑子里过一遍。
全福的木匠手艺是祖传的,他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木匠,想当然地,他早就准备好要把技艺传授给儿子,可偏偏,儿子不愿做木匠,嫌木匠辛苦又没见识,一辈子困在小岛上,他想当海员,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港口都跑遍,有时还能上岸休闲,公费旅游似的,多潇洒自在。几番劝说无效,全福气得冒火,拎起一把斧头追得儿子满院子跑。儿子勉强妥协,初中毕业后跟他做了一年木工活,结果,连个梯子都做不好,还时不时地搞废木材,不情不愿没有用心是其一,只怕也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全福死了心,这人跟树木一样,樟木可以做上等的衣箱书柜,柳木呢,也就能做做菜板拐杖之类,调反了,用错地方了,要么怀才不遇,要么不成器,罢了罢了,随他去吧。
全福长得如同他做的箱子,方方正正,个不高但壮实,两肩宽而平,两腿粗直,站在那儿四平八稳的。他的大鼻子很是显眼,鼻头肉圆,一喝酒就发红发亮,偶尔蓄两撇小胡子,微微翘起,我们小孩私下里叫他阿凡提木匠。眼睛却特小,像不小心在眉毛下割了细细两条缝,睁再大也就两条缝。弹墨线前,需目测,旁边的人若不特地留意,恐怕发现不了他两只眼睛正一睁一闭、一闭一睁,尔后,用木工笔在木头上画个红色记号,墨斗循着记号垂下来,“啪”,一条墨线弹了上去,分毫不差,动作简直有点帅气。待吸完一支烟,低头,依着弹好的墨线开锯、凿孔等,他一用劲,脸部肌肉就紧张,咬牙歪嘴的,顺便牵扯大鼻子一扭一扭,甚是滑稽。
我们有事没事老往全福那儿跑,一进他家院门,木头的香气必先上来迎客,悠悠的,恬淡闲适。全福的工作场地在堂屋,摆放的长木凳、矮桌子便于加工木料时削和刨,木头工具箱造型像个长方形篮子,有个提手,可以拎来拎去。均出自他手。木匠的工具繁多,看得人眼花,斧头、锯子、刨子、锛、弯尺、墨斗、凿子、榔头……似乎每一种都分型号、大中小、长中短,如锯有长锯短锯,斧头有大斧头小斧头,而刨子,分粗刨、细刨、光刨、槽刨等。工具箱自然是不够放的,大型点的工具便倚在屋角、墙边,我每次见到它们,总感觉有种生人勿近的威严,带着警告的意味。
全福不许我们进堂屋,工具不长眼,会伤人,我只好坐在木门槛上。工具也长眼,它们只认全福,年轻的徒弟有一回就被“咬”了,大概工具跟人一样,相处久了会对你生出感情,老木匠全福用它们锯长短、削厚薄、刨平直,经年累月,于是,它们甘愿臣服于他的手,温顺又卖力。
所有工具里,我最怵斧头,刀口呈弧形,薄而亮,寒光闪闪的,瞧着就心里发毛。全福砍削木头,有时两只手握住斧柄,有时只用右手,抡起、落下,一下,又一下,像锄头锄地,也像舂头搡捣。夏季,就算把堂屋的两扇门都开了,依然燠热,全福穿一件白色汗衫背心,用干布擦擦手心的汗,斧头举过头顶,“梆——梆——”手臂的肌肉一鼓一鼓,仿佛钻进了只青蛙,木头如干裂的泥土般迅速豁开,我感觉身下的门槛颤了几颤。这么一通下来,汗衫背心的后背前胸均已湿透,他接过徒弟直接从水缸舀起的水,一饮而尽。斧头也不是时时这么粗暴的,它还能干细活,比如削木楔、砍边,有句话叫“快锯不如钝斧”,这时的斧头在全福手里就像玩具一般,轻盈跳跃着,点哪是哪,快而准,木片木屑“唰唰”地掉,简直如削豆腐。事毕,全福起身,弹弹粘于皮肤的屑末,大鼻子里哼出个曲儿,好似他敦实的身体里有根弹簧突然松了,变得柔软、懈弛起来。
一块原木到一件成型的木器,须经过多道木匠工序,一道接一道,万不可乱了次序,总得先开料才能刨吧,而开榫凿眼肯定得是光滑的精料。刨木可能是唯一一个需要木匠全身运动的工序,我们小孩觉得最好玩。全福粗短的左腿弯成弓形,右腿在后,用力绷直,那个气势,好像要把地面蹬穿。他双臂伸直,双手握住推刨,顺着木材纹理使劲往前推,身体亦顺势前倾,随着“刺刺刺嗦嗦嗦”的声响,刨子欢快地吐出薄而卷的刨花,一朵连着一朵,又成串成串盛开在地上。即使被废弃,也要美丽绽放。推刨中途不得缓劲,一推到底后,猛地顿住,接着,连人带刨子紧急后撤,此间,全福会扭动一下脖子,再重新发起“进攻”。
刨木就是给木板做美容,无数次的推刨,疙瘩啊疤痕啊被抹平的抹平去除的去除,直至变得光滑细嫩。刨花一圈一圈簇拥着全福,全福双脚一动,它们便窃窃私语,不知在埋怨还是在夸奖。刨花粗粗细细,宛如女人头上的大波浪小波浪,越堆越多,终于,像海浪涌到了门槛边,我们开心了,一朵朵捞起,放到鼻子边闻,套在手腕当装饰,当作蛋卷摆在破瓦片里……最后,我会通通装进塑料袋里带走,奶奶生炉子,说用刨花引燃效果好。全福笑我,那么点儿够什么好,得拿编织袋装。还真有人拿了编织袋,也有人拿铅桶,编织袋装刨花,铅桶装锯末,锯末发酵后掺土里,对种菜种花都有益。
全福声明不接急活,慢工出细活,浪费了木料或做的木器有瑕疵,口碑要坏掉。尤其做嫁妆,那是姑娘一生中的大事,也是证明娘家实力的风光事,马虎不得。全福带着工具入驻主人家,先看做家具的木头,抬起一根掂掂,摸过另一根弹弹,或用他比木头还粗的腿踢踢,再拿出卷尺量量,心中有“尺度”,执斧凿才能有神。这根可以做啥,那根用来干吗,挑出来的都分类放好,在全福眼里,它们已然是一个个具体的几何图案。
主人家早已辟出开阔的场地供全福施展,此后几天,那里不断传出“砰砰啪啪”“滴滴笃笃”的声响,木头经过全福的手,变成各种长短宽窄的木材,堆于一角,再由木材拼成奇形怪状的半成品,那些木头与木头咬合、连接而成的构件,平衡有序,有的能一眼瞧出是某木器的一部分,有的像个谜,怎么也猜不出。各个颠三倒四、横七竖八的木构件,接下来会被敲敲打打,条条框框、板板块块依照一种组合关系天衣无缝地融合,终成一体。
主人家对木匠师傅怀有敬意,好菜好酒好烟招待着。全福爱喝点酒,但不贪杯,喝酒跟做工一样,要掌握好分寸感,喝过量,手会不稳,手不稳,哪出得了好活。最后一日结完账,全福收拾好工具,看看摸摸亲手打造的家具,小眼睛眯起,轻轻颔首,大概是对自个的手艺表示满意。然后,一只粗腿向外一旋,大踏步走了。
其实,全福也接过急活。那年,岛上有个海员在海上遇难,急用棺材,全福和另一个木匠在那家夜以继日赶工,寻回的遗体才得以尽早装殓。两个老木匠没收一分工钱,也没吃饭,全福说这跟做寿棺不一样,不好意思收钱也没心情吃饭。在岛上,做寿棺寿坟是喜事,老人们把最终的安身之所安排妥了,心里就轻松了,必须好好宴请木匠泥水匠,有的人家还要办上几桌呢。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木匠这一行似乎也进入了电器时代,全福购入了电刨子电锯子,干活省力多了,适合逐渐年老的他。全福选了好木,给自己做了一口寿棺,逢人就说很合心意。完工那天,他让老婆备了好酒好菜,那回,他喝得有点多。
篾匠阿爷
一根茶口杯粗细的竹子,竹头抵住墙脚,竹尾握于阿爷左手,他右手挥刀,往中间部位一扎,“嚓”一声轻响,裂了个口子,顺势推篾刀,“噼噼啪啪”,像燃放鞭炮,竹子被一节节劈开,破开后的竹子对剖,再对剖……阿爷手持篾刀,左劈右劈上下翻飞,手指的骨节一突一突,如拉面一般,变出了无数根细长柔韧的篾条,一甩,“沙啦啦”,恰似清风穿过竹林。
地上的篾条堆了起来,长的、短的,带皮的、不带皮的,粗细均匀,青白分明,散发出竹子特有的清香。阿爷起身,抖落身上青绿色的竹屑,两手一会儿交叉,一会儿来回搓,不知在舒缓劈篾后的疲劳,还是为接下来的编篾热身。阿爷个头不大,那双手却特大,手掌厚,手指长,指关节粗且弯曲,一用劲,手背上青筋暴起,像爬进了好几条蚯蚓。手上遍布小沟小壑,老树根般粗糙,很怕他摸到我衣服,一摸,要么起毛要么抽丝,新衣也成旧衣。怕影响做活,阿爷每每把指甲剪得光光的,而做篾匠多年后,便很少剪了,他的指甲长得缓慢,有的甚至停止了生长。
阿爷其实并不老,那会儿也就个中年人,因跟我亲爷爷是表兄弟,辈分大,故喊他阿爷。阿爷年少时羸弱,坐个渡轮都要晕船,父母怕他禁不起风里浪里颠簸,海员和渔民就别想了,学门手艺吧,小岛上,手艺人是吃香的。在木匠、漆匠、泥水匠、篾匠里,他选了篾匠,阿爷幼时常钻竹林,做竹管枪,取竹叶吹哨子,觉得自己跟竹子更亲近些。
篾匠活讲究取材,春竹不如冬竹,冬竹又以小年的为宜,韧性好。根据竹子的粗细、颜色深浅,阿爷能辨别其生长年份和阴阳面,何种竹器用哪类竹,他胸中有数,如向阳的隔年青用来编凉席甚好,几年的大苗竹制箩筐牢固,篓子筛子可用年轻的小桂竹,虫蛀的竹子易断裂,做正料太勉强,只能做辅料……让竹子各尽其材,是好篾匠的标准之一。
砍下来的竹子必须趁新鲜剖篾。篾匠活儿,看似轻巧,实则都下过无数苦功,如劈篾这项基本功,宽窄厚薄全凭手指感觉和个人经验,略厚嫌粗拙,过薄怕欠牢,难就难在刚刚好。还不能统一型号,不同的竹器、同一个竹器的不同部位,对篾条的要求各不相同。对篾匠来说,剖出细如发丝或薄如蝉翼的篾条,简直成了一种快速证明自个实力的方法。
阿爷自是功力了得的。青篾、头黄篾、二黄篾、三黄篾……一层又一层,剖得利索。其中有个动作,他将篾刀刀柄往腋下一夹,嘴巴向前伸,咬住剖开的竹篾里层,刀子轻轻推进,他的厚嘴唇似乎抖了一下,三条额头纹跟着一颤一颤……我在一旁有点紧张,把咳嗽都硬压了下去。两层分开后,再如此反复,一层,又一层,剖出的篾条轻薄似纸片,且每一层都均匀、齐整。眯起一只眼,透过篾条朝外看,可见朦胧的光,恍若晨曦映进了玻璃窗,遂朝阿爷嚷:“就像蒙描纸,都能印画啦。”阿爷两瓣厚唇使劲往旁边咧,露出了上牙左边的那颗银牙。
篾匠的工具相对简单,小锯、篾刀、篾针、剪刀、度篾齿……这门精细的技术活,大概最重要的工具是篾匠的手指。阿爷系上围裙,往小马扎上一坐,扁而薄的竹篾在他指间舞动,犹如起网时小鱼群弹来跳去,他的十根手指似有磁性,各款篾条被吸得牢牢的,任怎么拨、拉、挑、压、穿等依然服服帖帖不离不弃。“哗哗”声中,篾条来回穿梭,纵横交错,偶尔用篾刀敲打经纬交叉处,可令其交织得更紧密紧实。一个不注意,竹器的底部就编好了。光一个底部,编法花样百出,米字形、斜纹、平编、三角孔等,什么器物配什么花纹的底,从手指与篾条相触时便定下了。
阿爷常在自家院子里做活。院子铺了石板,石板与石板的缝隙总会钻出一丛绿,与墙边码着的几根翠竹相映。篾条一部分堆在地上,还有些挂于院角的楝树枝上,微风拂过,翩跹而舞,旋起一股竹香。成品与半成品散落四周,筐子、提篮、筛子、簸箕、摇篮……方的、圆的、扁的、长的,形状大小各异。有种竹篓子,口小肚大,状如某种坛子,我们叫“克篓”,阿爷几乎可以闭着眼编,底打好,篾条一折一压,开始编织圆鼓鼓的身子,快到头时猛地收紧,形成细如头颈的口子,可一手掐住。在当地方言中,“克”有“掐”的意思,“克篓”这种易进难出的特点,很适合装活蹦乱跳的渔获物,去海边扳鱼,少不了它。阿爷编的“克篓”锁口严密,篓身不易压瘪踩歪,一不小心就成了畅销货。
不知道阿爷是天生不爱说话,还是因长年做篾匠活而变得沉默,他坐在那,长长的手指忙着与篾条纠缠,三条额头纹如捉摸不定的海浪,忽而聚集,忽而舒展,眼不斜视面无表情是他的常态,可以数小时不挪动,不讲一句话。若有邻人相问,他头不抬,手上也不停顿,简洁回一句便不再吱声,两片厚嘴唇跟两层石磨似的,牢牢叠在一起。小孩们在旁边叽喳、转悠,只要不搞破坏,阿爷不会赶我们,也许是懒得理我们,他正沉浸其中,把心中的那些立体图形,通过指间的钩拈转折来实现。竹篾到底能成为怎样的竹器,全凭篾匠的一颗匠心。
等我们玩了一圈转回来,阿爷还是那个表情、那个姿势,小收音机也依然在他脚下开着,只不过已从评书转到了戏曲,或从广播剧换成了天气预报。阿爷背后,楝树枝叶繁茂,一大团的绿浮在半空,晚霞放肆地将天边涂成了橙红色,一束红光从檐角闪进来,落在即将完成的箩篼上。
阿爷做的那么多竹器里,小孩子瞧得上的,唯有阿爷给小女儿编的小玩意儿,小花篮啊小箩筐啊,最惹眼的数那张袖珍竹编床,造型别致,纹理细腻,布娃娃睡上去肯定舒服。阿爷做活时,我们帮他扶竹子,给他递篾条,殷勤献得太明显,被他看穿了心思,他眉毛一扬,额头纹迅速向发际靠拢,说干脆做一个大家都能玩的东西。可直到阿爷扎结收边,我们也没瞧出那是个啥,状若簸箕,但簸箕又没有那么深,锁口跟筐子一样,用剖得很薄的外层竹皮,竹皮卷紧后在铁锅里烧煮过,方便穿绕且不易断裂。
小孩们东猜西猜,阿爷嘴角微翘,拿根粗麻绳往楝树上一甩,麻绳像两条结实的手臂,从大树垂下,稳稳“抱”住“簸箕”,我们齐声大叫:“秋千啊!”于是,一个个轮流坐上去,轻轻地欣悦地荡过来荡过去,风也来凑热闹,鼓起我们的衣衫,树叶在头顶飒飒作响。
那年,阿爷大女儿出嫁,阿爷早就编织好了一套嫁妆,针线笸箩、礼篮、蒸笼、竹箱、竹席……漆成红色的篾条穿插其间,有的收边时编了一圈漂亮的红色花纹,有的,在提把或盖子上嵌入了红色“囍”字,看起来那么喜气、祥和。
等小女儿出嫁时,人家说已经不时兴这样的竹编东西了,阿爷不吭声,从早到晚地劈篾,编结,打造了一套同样的嫁妆。有一次,一向寡言的阿爷从厚嘴唇迸出一句话:“纯手工的东西金贵。”他的大手在空中一划一点,像为自己的话加了个感叹号。
如今,阿爷已年逾七十,仍在做活,多数是些小竹器,编起来轻松些,比如花器、水果盘,造型多样,基本都是顾客订制的,他说,还是要动动脑动动手指,可以防止老年痴呆。阿爷的皱纹真是多啊,横的、竖的、斜的、并行的、交叉的,仿佛把篾条的编织图纹都印在了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