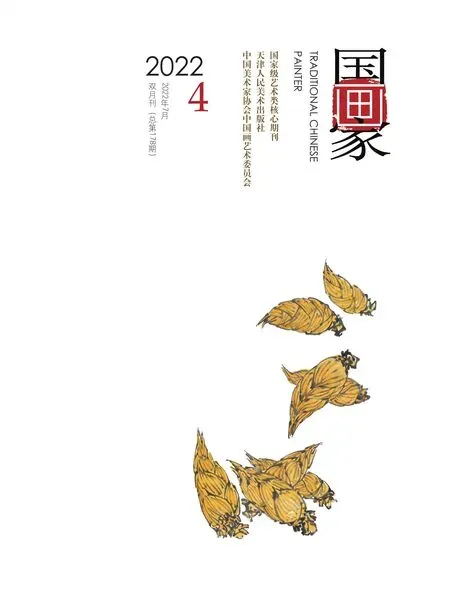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书法史价值及意义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石澍生
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研究此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吐鲁番出土书迹的书法特征和书史研究价值略作探讨,疏漏不足之处,恳请专家指教。
一、吐鲁番出土书迹的书法特色
吐鲁番出土书迹从书法角度言,具有出土数量多、书迹种类多、世俗文书多的特点。数量上,晋唐时期吐鲁番出土的各类汉文文献达数万件,这还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书。种类上,吐鲁番出土书迹主要包括世俗文书、经籍写本、墨迹墓志三大类。文书亦称“尺牍”,举凡各类公文、契约、籍帐、衣物疏、书信等为是。吐鲁番出土书迹种类较敦煌写本要更为丰富,敦煌主要为佛经写本,而吐鲁番出土世俗文书占比更重。
吐鲁番出土书迹书法上整体具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是与中原书法关联紧密。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先后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等几个不同时期,郡国时期虽然是地方割据政权,但统治阶级皆为汉人,与中原时常往来,而640年唐朝收复高昌设立西州后制度更是与内地并轨。当地较薄弱的汉文化根基使得书法上不会自身孳乳繁盛,更多见于中原书法向当地的渗透和影响。二是书法水平参差不齐。毋庸讳言,吐鲁番出土书迹是古代人民书写后无意识保存至今的墨迹,书写水平相对平庸,与书法史上名家名作不可同语。但这些书迹毕竟是晋唐真迹,笔触生动自然,且各类书迹不乏佳作,如早已为人所熟知的两晋南北朝写经和高昌墓表。三是书写内容丰富。社会各阶层人士将书写技巧和书法审美自然而然地融入书写行为中,真实鲜活地反映出社会日常书写的情境。可以说,吐鲁番出土书迹丰富的书法内涵,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晋唐书法史发展的一些问题和细节无疑有所助益。
二、吐鲁番出土书迹反映晋唐书法史整体发展脉络
现今东晋十六国时期出土的书迹特别是墨迹极少,而高昌郡时期的吐鲁番出土书迹作为目前十六国出土书迹最为集中丰富的部分,能大致勾勒出十六国书法史之面貌。特别是此时处在隶楷演变的较后期阶段,当地书迹在5世纪中后期(大致相当于南北朝早期)大体褪去隶意,是隶楷演变的重要参照。同时,我们将隶楷演变期的不同出土书迹类型大致归纳为“日常书写体”“写经体”“铭石体”三类,由于书写功能的不同,反映在隶楷演变的程度亦有所不同,其中“日常书写体”主要指日常往来用世俗文书,以行楷为主,是书体演变的先锋。
南北朝早期以后,由于楷书基本成熟,世俗文书、经籍、碑刻三者之间的书体差别愈发缩小。吐鲁番当地早期出有几件南朝写经,但不久后斜画紧结的魏碑体成为主流,这在此期写经、墓表以及日常往来文书均有所体现。南北朝后期,当地延续魏体书风,亦出现一定程度平画宽结体势的转变。但这种平画宽结的风格并不显著,或受到当时当地较为封闭的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其时南北书风而略显滞后。其中,当地世俗文书和写经题记中还广泛存在有一类宽结简率的行楷俗体,长横长捺转折等处多见圆弧形笔画而少顿挫之势。此类俗体也见于同期部分敦煌写经的题记中,如《大智度论第廿六》(532,P.2143)、《律藏初分卷第十四》(532,SH.021)等,这可能是其时民间较多使用的一种简便俗体。
至唐朝收复高昌,当地这种通行的俗体迅速消失,代之以王书、欧体等初唐流行风格,不乏精彩之作,如《法绍辞稿为请自种判给常田事》之险峻近欧体、《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为觅失迤驹事》之婉转近孙过庭草书、《唐□文悦与阿婆、阿裴书稿》之侧妍近王羲之尺牍。此后高宗武周褚体多出,盛唐书风渐肥而时见近颜体的行书,都较为鲜明地反映了唐代书风不同时期的变迁。至“安史之乱”后,当地失去唐中央的控制,短暂由吐蕃占据后由回鹘人长期统治,书法已是另一番光景了,本文也暂不涉及。
由是可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书法脉络与中原大体同步,其深入地体现出社会层面书法风格脉络的变迁,侧面反映出晋唐书法史的整体进程。
三、吐鲁番出土书迹对书法史重要问题加以补充
一般而言,讨论敦煌写经特别是早期写经往往涉及吐鲁番出土写经。吐鲁番出土写经书法水平亦高,且在早期敦煌所出写经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吐鲁番写经更突显其价值。如现存学界普遍认为可靠的最早的写经《诸佛要集经》(296)出自吐鲁番。再者,几件南朝写经极为重要,如南朝人写《持世第一题记》(449,SH.161-6),西川宁先生认为是真正代表楷书成熟的写本。
吐鲁番出土墓表墓志学界讨论已多。这批墨迹墓志搭建了研究铭刻写与刻关系的桥梁。吐鲁番出土墓志受时风所限,又掺入世俗写法,不同形式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而呈现出简率、变造、融合等多种变化,反映出墓志使用中向社会中下层渗透时其艺术特征更多的复杂性。
吐鲁番出土文书存在大量具名、署名的情况,且各类官私文书具名署名遵循一定的规律或格式。由是可探讨文书背后的书写群体的性质。官文书书写者以吏员为主,他们数量庞大,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作为连接官员(精英书写)和平民(民间书写)的中间阶层,构成了日常书写的主体力量。私文书书写人情况更为复杂,署名随意,代笔亦多,但也呈现出社会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群体均参与书写的事实。
吐鲁番出土的习字类文书反映书法教育有关问题。吐鲁番出土习字类文书种类丰富,既有《千字文》《急就篇》等蒙学教材,又有王羲之《尚想黄绮帖》、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卫夫人《与释某书》等以名作为范本的习字。总体而言,晋唐时期的官方书学教育规模很小,但“写本时代”信息沟通、文化传播等都依赖书写为渠道,社会普遍需要受教育人士具有一定的书写能力,这多在各类官私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书法教育中得以落实。
吐鲁番出土书迹应是晋唐书法史资料的重要补充。它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共同构成了晋唐书法墨迹最为直接生动的研究材料,二者又在时间先后、书迹种类等方面各有侧重,又不乏精品,是构建书法艺术殿堂取之不尽的宝库。
[1]古丽努尔•汉木都、李亚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数量及语种》,《现代妇女》2013年第10期,第196-198页。
[2][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从出土书迹言,大致上,日常书写体可对应于行狎书,经籍写本对应于章程书,碑刻墓志等对应于铭石书。此言恐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书体功用的认识。
[3]华人德等,《中国书法全集14: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荣宝斋出版社,2013年,第230-236页。本文以下所列书迹出处,如不作特殊说明均用学界之通用简称,如“P.”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编号,“SH.”指《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全三册,东京二玄社,2005年)书中编号,《图文一》至《图文四》分别指《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一至四册。
[4]分别见《图文二》,第28、58、150页。
[5][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佛典1。
[6][日]西川宁著、姚宇亮译,《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63-265页。
[7]荣新江,《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载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6页。
[8]李红扬,《吐鲁番所见“〈孔子庙堂碑〉习字”残片考释》,《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2期。
[9]张艳奎,《吐鲁番出土〈唐人习字〉文书初探》,《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