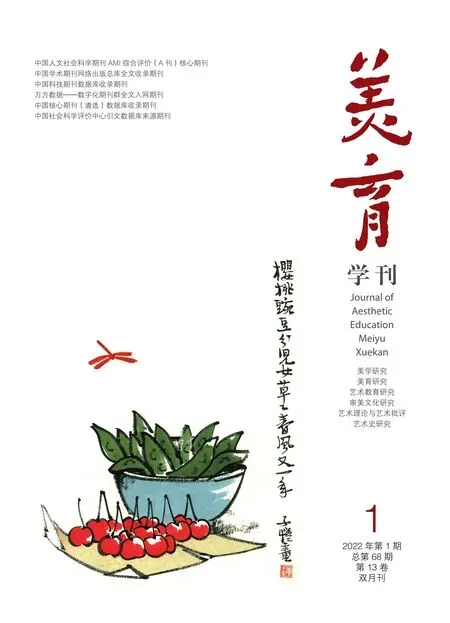论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三重性
胡 南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魏晋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双重契合的重要时期,开启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儒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现实主义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奠定了该时期“出则仕,入则隐”的行为基础,共同催生了有志之士顺势应变、返观自我的人生哲思,琴棋书画诗酒花则成了名士抒情隐志的重要途径。文人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分支,自古秉承着“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艺术精神,文人阶层将“诗意栖居”的追求凝聚于艺术之中,故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境为世人所推崇,并通过音乐这种输出途径使得人的“性”“情”得到调和。因此,本文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以魏晋时期文人音乐活动的“游戏性”外在表现为切入点,以“玩乐于掌指之间”的“移情”情怀为事实根据,揭示魏晋时期文人音乐“伦理性”的边缘化及“审美性”的核心化,进而论述魏晋时期文人音乐话语的游戏性、伦理性和审美性内涵。
一、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游戏性
自人类初始,人与世界的相处之道就构成了“游戏”的基本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游于艺”(《论语·述而》)这一说法最早体现了儒家先贤对“游戏”与艺术关系的理解。“游”作为中国人极富特色的生存态度和生存理想,于外是合道,于内是自适,指的是人类精神无限的游度。“游”与“戏”几经演变,延伸出“游艺”一词,即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一种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的精神文化活动。先秦以降,音乐主要以“习礼”作为社会功能的游戏规则贯之,是一种有用意的形式,有其严肃性。《左传·昭公元年》云:“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这种严肃性直到汉末仍占统治地位,如蔡邕在《琴操》卷首载:“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御邪辟,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古有士无故不撤琴瑟”本身就是“礼”的体现。直至魏晋时期,曹操施行的求才三令以及“唯才是举”等系列举措,使得个体的才能、性情能得以在艺术领域中崭露头角,即“性”与“情”该如何存在的这一难题在音乐艺术中找到了回应。诚如嵇康于《琴赋》中开宗明义:“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他将音声的表达视为一种娱心自乐的游戏,这种自适感如伽达默尔所言:“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藉此,文人阶级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开始觉醒,形成独立于宫廷、民间之外的又一文化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文人群体历来以一种“和”的认识对“人的性命”加以解读,并将这种解读推向对游戏精神的观照,这种观照不仅成就了“高山流水”式的曲高和寡,也实现了对“下里巴人”的理解与容纳。
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游戏性,外显为一种文人雅集的音乐活动,如兰亭之会、金谷之会等。不论是汉朝的“建安七子”、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期的金谷“二十四友”,还是东晋时期的“三戴”,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深受释道哲思影响,游离于“名教”与“自然”之间,其思想是矛盾却极富思辨的。因而表现出独特的因兴而作和适性而奏的音乐行为,彰显了主体精神的极大自由。根据康德的观点,这种行为能够弥合主体的分裂,是构建主体性的重要环节。席勒也指出:“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因此,携琴会友、诗文互答的“游戏”形式,以及因兴而作、适性而奏的主体音乐行为,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文人们交往的常态,如《晋书·苻坚》载:“坚送丕至灞上,诸氐别其父兄,皆恸哭,哀感路人。赵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坚笑而不纳。”就创作旋法而言,作者赵整经常诗谏上位者,所作琴歌不拘泥于起承转合之定式,而是根据当时的离别之情来进行即兴创作。就表演形式而言,坐地而席、援琴歌唱的方式也表现出去除严肃的礼后所呈现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也体现在音乐旋律曲调上,这一时期清商调的大发展就是证明,如《晋书·乐志》载:“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又云:相和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曲调的互鉴也促使民间的俗乐(清商曲)发展成为可以在宫廷演奏的雅乐(清商调)。由此表明,文人的恣情肆意,滋生了因兴而作的音乐行为,自由而灵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外延。
此外,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游戏性还展现出适性而奏的表演特征。荷兰文化学家约翰·胡伊青认为“人是天生的游戏者”,与动物相区别,“人的游戏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作为人的最固有标志的理性可以确定自己的目的,并且有意识地去努力实现这种目的,人的游戏可以包含理性而且又可以不具有带有目的理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来看,深受“黄老思想”人生哲理影响的魏晋文人音乐活动,是“自我觉醒”的主体游戏精神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艺自觉的契合过程,在“无目的理性”遮蔽下既呈现出一种“格人”与“格物”相互协调的“戏”的追求,又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游”的推崇。对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而言,“游戏”本身象征着精神境界的分野。一是鼓琴娱己,如《晋中兴书》所载:“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艺,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闻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对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为王侯伶人。’”可见戴逵尊崇自娱的心境,故不鼓琴与人,乃至破琴明志。一是鼓琴娱人,如“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阮瞻作为名士,对于听琴者无一不应,欣然鼓之,其洒脱性情可见一斑。对于阮瞻和戴逵的琴艺,自古有定论:戴逵“清”,阮瞻“逸”。虽然后世之人多认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阮瞻和戴逵对音乐艺术的把玩是相通的,他们都视音乐为恣情肆意的性情活动。这种性情的抒发,才是音乐之所以被称为艺术的内涵。故而,容肇祖将魏晋自然主义在人生观上的表现概括为“适性主义”是合理有据的。
藉此,因兴而作和适性而奏的主体音乐行为,不仅催生了魏晋时期文人所特有的爱“啸”的风尚,以实现“箕踞一长啸。忘怀物我间”的坐忘心境,同时也深化了琴自身的参照价值。如嵇康所作诗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又如《晋书·隐逸传》载:“……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弦上声”这种类弦之物仅被当作获得“琴中趣”的工具与手段,表明音乐的最高境界不在于音响形式和技法,而在于游戏者超越具体的音声去寻求心声之美,以期达到“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的目的。同理,《淮南子》曰:“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其感发意志(性、情)来自“人”,琴弦只是发声之载体,不是悲伤的原因,现实的人却可以借助审美的超越力量挣脱现实的束缚来“以心游物”,求得个人的自适与逍遥。故而,乐之音和人之啸的完美契合,形成了“琴啸相谐”的文化镜像,它将魏晋文人放荡不羁、自由率性的情怀展露无遗。
总的来说,人自身的“习”“性”等先天气质与后天形成的喜、怒、爱、憎等情感反应,是一种主动建构和自我生成的精神。不论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他们的“游戏”心态实现了由重道轻器转向道器并重(或道器一元)思想的“自我返思”,即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第一种自由的关系。这种“自我返思”的共通感对今人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历时语境是至关重要的,不管任何年代、任何民族,“游戏场”的设立都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如果我们简单地拿它当作孤立的现象,就不能了解它原来的存在性质和意义。我们要将这些文人的音乐活动看作生存环境与社会机能,在仅有的界限中,我们只能通过和他人、历史性的文本的对话去理解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存在,从而了解我们自身。也只有谦卑地参与对话,使感性和理性趋于和谐统一,才能在“自我”与“非我”的游戏场域中获得完满的人性,使游戏者成为真正的人。因而,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形成了借由“游戏”(音乐行为)而进行客体自身的观照。这种观照一方面由对话性的意义得到确立;另一方面,其“对话场”的游戏方式又被游戏的“精神仿照”隐喻,实现了对“对话场”的默认。文人群体的音乐哲学观念恰恰是建立在自由的个体所选择的实践行为上,而“自由”的本性使他们的活动更加合乎情理。于是,与“载道”关系较远的艺术形式便成了政教伦理鞭长莫及却因而能满足情感愉悦的新的安乐处了。
二、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伦理性
“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者,德之华也”,都表明“乐”有着伦理上的教化作用,强调音乐艺术作为一种人类实践的精神活动,其行为是受道德伦理、秩序规范引领的,其内核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有机统一。官方将其纳入礼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传统的“和乐”思想。如《乐记·乐象》云:“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儒家认为,只有摒弃淫溺之情,调和自己的心志,并“各以其类相动”,效法好的榜样才能实现君子之道。可见,“礼”与“乐”的统合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环节。同理,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礼”与“乐”的分离也就有其必然性。处于乱世之争的年代,三国皆以法代儒,重务实而轻礼法,对音乐从礼制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夏侯玄针对阮籍《乐论》一文而写的《辩乐论》中言:“夫天地定位,刚柔相摩,盈虚有时。尧遭九年之水,忧民阻饥;汤遭七年之旱,欲迁其社,岂律吕不和,音声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数,非人道所招也。”此外,《声无哀乐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进行了七难七答,揭示了音声有其自身的感知方式和美的内涵,从理论上将音乐从礼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在艺术实践中,“礼”与“乐”并不能彻底分离,其各环节发展受到诸多“人”的限制。如音乐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不论物质层面的“器”,还是精神层面的“技”与“乐”,都需要音乐人才来完成。因而,传统意义上的“人”与“礼”是一体圆融的。一方面,“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等的制度,实质上是“才”与“德”的较量,从不同程度推动了文士阶层的交融与发展,这些举措使得民间与官方的话语边界逐渐模糊。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礼乐仍是统治阶级保证自身话语权力的重要手段,礼乐从思想具化为制度是绝大部分统治者建立统治的必要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音乐,特别是雅乐与权力话语的结合。音乐的神圣性被转移到了统治者身上,旨在构造起完整的礼乐形式。在此情形中,在保有权力的统治阶层的影响下,仍然保持着“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的国家礼乐体系。这种统治阶层试图仍以礼乐维护统治的守旧思想和文人阶层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相碰撞,在文化格局更替频繁的大背景下,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音乐伦理思想。这种特殊的音乐伦理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音乐神圣性的泯灭和音乐话语权力的再分配。
有史以来,音乐一直被视为人与超越之物沟通的渠道,因而将音乐赋予了极其神圣的表征而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如《韩非子·十过》载:师旷认为“清商”即“亡国之音”而不能听,德薄的人不能赏“清徵”“清角”一类的琴曲;公孙尼子在《乐记》中指出,“乐者,德之华也”。这些都将音乐视为超越语言的通途,以一种情感兼具道德的对话形式造就了主体精神的观照,形成了一种独有的“共生性道德气质”。然而,在“汉末大乱,众乐沦缺”的三国时代,文人尽管在用乐观念上仍然秉承上古遗风,但音乐的神圣性却黯然失色。如曹操一生作乐府诗二十一首,虽秉持“王官采诗”的三代旧制,反映当时战乱所导致的凋敝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但更多的是隐含了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如《蒿里》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种不拘泥于礼乐本身的框条,追求自身情感宣泄的表达方式,是独属于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意境。这种特殊语境造就的集体意象,代表着中国音乐艺术行为目的不再是社会文化的整体阐释,而是对人与自然生命关系的观照,其“神圣性”开始从音乐中被剥离,音乐本身的伦理显现出来。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情欲源于自然人性,合乎天道人伦。换言之,魏晋时期音乐的角色,由社会的共生性道德气质向个人的性情气质的载体转向。
这种音乐神圣性的泯灭,并不意味着魏晋时期音乐活动与伦理道德的完全分离。如嵇康所著《声无哀乐论》的主客之辩中可看出,虽然在音乐何以移风易俗上有所争论,但对于音乐功能性即音乐与伦理的关系上没有异议。如“秦客”认为音乐与伦理的关系互为表里,故而能由表及里,而“主人”认为音乐与伦理的关系相互平行,需要由此及彼。嵇康借助“主人”之口,将音乐从传统伦理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音乐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获得了自身意义的真理——美。再则说,正由于音乐常与美紧密联系,其音声的美感作用与疏导性情甚至移风易俗的作用是并驾齐驱的,进而使艺术与伦理的关系显得更为融洽。这种对于音乐本身之美的认识,也促使这一时期各门阀士族纷纷将音乐视为维护家族团结、教导后人的重要手段。如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墓志铭上都有类似记述:“艺单六德,学尽琴书,击剑投锋之术,谈天镂素之能,弯弧骋驰之功,神机譬悟之略。”印证了音乐被暗喻为文士阶层普遍接受教育的重要一环。于是,文人以“家学”的方式进行音乐传习,以期通过音乐的较量来突显对社会观念、精神价值的确认以及文化的认同。
无论从发生机理还是运行机制来看,伦理与音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伦理讲究秩序规范的普适性,在由此而引发的个人或与他人的行为关系中,致力于以“善”为总体目标的主体设定。可见,伦理与音乐,二者本质上并没有对立与冲突,甚至在“是非无措也”的情况下可以在君子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中国艺术强调美、善的统一,强调艺术伦理的情感感染作用,一直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秦汉时期文人以儒家为主流,文人音乐的实践活动无不根植于“礼乐文化”,其艺术精神的形成自然与社会、天地万物诸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一种此物联接彼物的符号媒介,如“和乐”“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地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汉魏之际及此后的长期动乱使得早期儒家所宣扬的名教成了空洞的代名词而为时人所不耻,新思想、新观念由此普及开来。然而,后世文人多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少论“矜尚不存乎心”。从“合乎于礼”的秦汉音乐伦理发展为“美以善为前提、善以美为追求”的魏晋音乐伦理,本质是不同时期文人音乐作为各时期的精神产物,它们都是在其所处的社会发展中由人创造并为人的目的而存在,“礼乐皆情,情是礼、乐的文化原型”,音乐与伦理常以情感为中介发生关联,进而通过自身的表现形式隐喻地观照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色的实践理性之美。
三、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审美性
魏晋时期,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文人发现。这种审美思想的觉醒有复杂的因素,该时期以儒家为主流的文人阶级思想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大批名士求助于佛、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艺术思潮的转向。如阮籍一生思想有过两次转变,第一次于正始时期(240—249),阮籍的《乐论》和《通易论》引老入儒,对于音乐美虽仍然持儒家传统之见,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但相对于传统儒家将“善”视为“美”的归属和终极,阮籍援引老子思想,从“道随时移”的角度,剥离了音乐和礼制的关系,将音乐的审美情感归之于“自然”。而在正始之后,阮籍更是著《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开始摒弃礼法,强调“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追求个体极致的逍遥和完全的审美自由。可以说,阮籍思想的两次转变是魏晋时期文人群体思想的缩影。他们极力推崇从无限的宇宙中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的情怀抒写正是主体精神张力的表达。各门类艺术如书法、绘画在这一时期步入了文人的视野而被作为审美对象来进行观照。表征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状态,最终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显现,这种显现随着审美主体的建构和审美主体经验的积累,而进一步拓展事物的存在边界,以求获得趋向无限的意趣,为审美世界的可能性揭开帷幕。
魏晋时期文人音乐审美世界的构建,首先表现于人格美的“再发现”。对于人格美的推崇,滥觞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离骚》中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就是这一时期对于人格美的阐述,重神而忽视形。其后秦汉仍然秉持这种观点,故而大音乐家李延年才会被史书称之为“嬖臣”,列入《佞幸列传》。不同于春秋、秦汉时期重神轻形的人格美,魏晋文人音乐中所追求的人格美追求形与神的并举,所以魏晋的“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包括“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诸般要素。纵观文人群体的种种行为,他们看似无视礼教,率性而行,却暗含了魏晋文人人格之美的真正要义。故而有“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正是人格美的最大化认同,是魏晋时期文人对于人格美真正要义的阐述。而将这种思想延伸至音乐之中时,文人群体或假借或托物,在看似游戏的表现和对伦理的蔑视之下,其音乐呈现了另一种“非礼”的音乐审美意象。如东晋大将谢安喜爱俗乐,竟然因乐而废政事,对此王坦之数次去信劝阻,遭谢安辩解:“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谢安的辩解正是魏晋时期文人阶层的真实心理,认为音乐是人们借物表意、抒情隐志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的重要通途。换言之,束之高阁的音乐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种艺术存在。这些审美意象极大地扩充了我国文人音乐蕴含的美学思想,不论是“以悲为美”,还是“融情于景”“游于物外”,文人在进行创作时经常数种意象并举。“形神并举”最终形成了对于完美人格,即“天际真人”的追求,彰显了生命永恒的价值。
如果说“人格美”是魏晋时期文人对于前代的继承与发展,那么“自然美”就是独属于魏晋文人的审美追求了。自然美的“新发现”源自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所受的由黄老转变而来的玄学自然观的影响。玄学自然观是和谐的宇宙自然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黄老思想发展而来的玄学尊崇万物自有的规律,认为“道”应以自然为法则,自然是最高行为标准。故而,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两难境地奠定了该时期“出则仕,入则隐”的行为基础,外显为“自然”与“名教”的冲突。与“名教”相较而言,“自然”具有一种先天和谐的品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调和,实质上是在理论上为伦理秩序、制度的续存寻找合理性,祈望借由宇宙自然界的和谐来调解人生在世的社会关系。随着时局利弊的激化,则有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生成,并非对存在的探索,而是将这种存在有机地融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这种形而上的存在演化成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实在,并形成了一种范畴意义上的实践论。具体到音乐艺术来说,就是人性与心性相互调和的方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自然被视为与人的主体精神、心灵建构的相互作用的实在对象,个体自然性情的应激,成为该时期的审美风尚。如《文心雕龙·明诗》载:“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由此,音乐被看作自然的化身,并与自然同构,具有同样的和谐品性,强调乐的本质是“和”,即是音乐的自然属性。进而由对音乐的认识论衍生出对音乐本体论的认知,所谓“若夫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泅滨之磐,其物皆调和淳均者,声相宜也,故必有常处以大小相君,应黄钟之气,故必有常数”。此处的“常处”和“常数”两者都是构成音乐的自然属性,而此种自然属性又与乐的移风易俗功能紧密相关——“有常处,故其器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贵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黄老的自然思想帮助阮籍弥散了功利主义的汉儒音乐观,强调“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将人性赋予自然,将八音五声与自然物相统一,天之道就成了乐之道,人心就成了乐心,人性则成了乐性。于是,天、地、人与音乐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共鸣,天人合一的伦理就被音乐的审美驾驭,音乐移风易俗的功用由此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人格美与自然美共同构成魏晋文人音乐审美中对于自然的向往。这种向往一方面促使魏晋文人对于人格的更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帮助文人音乐摆脱礼教束缚,为建立独立的乐论体系奠定基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论何种美学意象都受到两种不同处世哲学的影响:出世哲学决定了音乐文化形态,入世哲学决定了音乐文化精神。人与世界对话的处世哲学在文人音乐中最大化地展现出来。这些文人音乐作品一方面体现着文人含蓄内蕴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另一方面则散发出文人恬静淡雅、淡泊名利的隐逸之意,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人主体的审美性特征。“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成为这一时期文人意识中的思维模式,“圣人”与“贤者”相互碰撞形成镜像。因此,如果说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游戏性是其外在表现,伦理性是其传承框架,那么对前两者进行驱动的就是审美性表述。这种特殊的表述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文人仍受儒家影响,祈求在不偏不颇的愉悦心态中得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升华,如对琴曲《高山流水》《幽兰》的推崇。另一方面,这时期由于社会巨变,文人群体深受道家玄学影响,从人的本性出发,顺天地之律、成万物之性,玩于世间,为了本体的修养在自由心态中获得自然本质的生长,摆脱“比德”的束缚。如嵇康的《广陵散》《渔舟唱晚》、阮籍的《酒狂》《潇湘水云》等琴曲的诞生,由此文人雅士开始寄情于山水之趣。从“比德”到“畅神”,显示了音乐从社会功用向精神慰藉的调适,从而实现了道德功用向审美功能的转换,使中国文人音乐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独特审美品格的有意味的形式。“徇情道性、崇尚自然”的磨合即是文人“本我”与“超我”游戏辩证的结果。因此,魏晋时期文人音乐既可以看作是文人群体发展的偶然,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交融的必然产物。
四、结论
宗白华这样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的文人将儒家的“治世”、释家的“因果”、道家的“自然”相互融汇,凝练出了具有时代特质的哲学思潮。李泽厚注意到了魏晋士大夫、伦理政教与主体情感三者的微妙关系,并指出,尽管“士大夫知识分子都经常是伦理政教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大都赞成或主张诗文载道,但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传统的伦理政教毕竟管不住情感的要求和变异”。这种微妙的关系反映在文人群体的音乐思想中,就形成了以审美为基、以伦理为界、以性情为纽、以游戏为实在的一套相互辩证的音乐美学体系。这一时期的音乐主体开始向内发展,追求声音、情感与自然的一体圆融。在此过程中,为了调和人与世间万物、万象之间在性质、形态、等级等不同维度上的差异和矛盾,音乐本身的伦理价值必然被削弱,其实质是人与对象之间“吐故纳新”过程中的互生共生的平衡状态。魏晋时期文人重视存在生命的情感体验与表达,以游戏形式外化、以审美内核表达的过程,在秉性自然的状态下,催生了艺术自觉的萌芽,进一步回答了人何以为人以及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