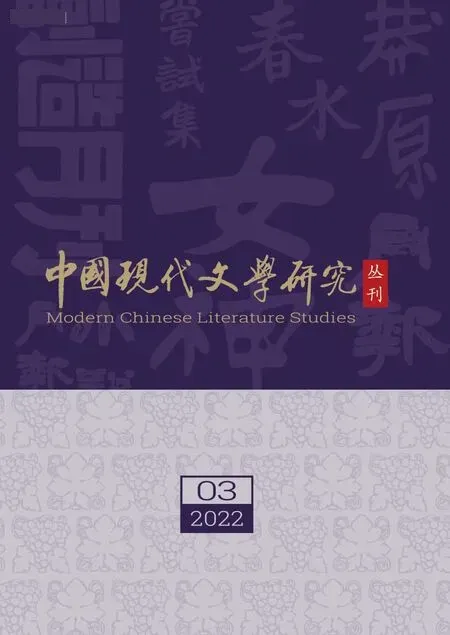《有生》与先锋小说及新历史小说比较论
王金胜
内容提要:胡学文创作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生》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及个人化叙事、日常化审美之间有着耐人寻味的隐秘关联,其历史叙事显示着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注重文学性、文本性的“纯文学”基因遗传。同时,作家力图摆脱技术化审美的窠臼,通过当下现实与历史、生命个体与历史的对话,重构文学的真实性。作家取径“小历史”进入大历史,超克传统/正统历史主义叙事和新历史小说的局限,确立了小说鲜明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
本文从“历史”叙事入手,以先锋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为具体观照点,对《有生》与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历史”叙事之关联进行比较分析。这一关联隐含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文学“历史”叙事的某些症候性问题。由此入手,可在特定视角中窥见中国文学在近三十年间的转换与调适、赓续与更新,亦可见出带有后现代意蕴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路径和方式。
一 个人化入思与叙事的自由
《有生》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个人化和“叙事性”特征。小说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如花、毛根、喜鹊、麦香、宋慧、白礼成等,尤其是具有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的女祖奶性形象,传达了作家对个人/女性生活、情感、心灵及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有生》着力探寻和表现的并非历史脉络、趋势和规律,作家自觉放弃对历史/现实的社会性史料的关注,而以敏感的心灵进入人物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通过其生命体验来感受、认知和描绘“个人”的历史——这一“个人”既是小说人物意义上的,也是主体入思意义上的。同样,《有生》虽注重历史/现实的相关性,实质上却是对历史、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不可预料的命运之描述。
小说着墨于“个人/女性”的“生”“活”和“命”,她们在日光流年中的生活和生命流程,关注其情、其爱、其心之被叙述被讲述和描述的状态。与“历史”相比,《有生》更突出对历史氛围和历史体验的叙事,更突出历史“叙事”和历史叙事中的“主体”——个体/女性意义上的双重主体。与通常的历史叙事相比,《有生》更具想象性、叙述性和文本性。在文学的想象、叙述和文本与历史的历史、事实和“史料”之间,作家更多体现出对前者的青睐。《有生》的“历史”呈现为个人化、感觉化(由祖奶的听觉嗅觉生成)的回忆和体验。这不仅提供了个人/女性/民间/底层维度上对历史进行把握和阐释的另一种可能,也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真实,勾画出被遮蔽的历史本相,扩展了历史叙事的审美空间。
在放逐了历史公共权威之后,《有生》没有被动记录历史的轨迹和烙印,作家获得了以更为灵活独特的个人化方式重写历史的自由。作为小说人物,祖奶的个人史、婚姻家庭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纠缠在一起;作为主叙述者,祖奶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其“历史”讲述通过不时被“现实”打断的回忆展开,在历史/现实交错的非线性叙述中,“历史”呈现出片段化和不确定性。
就此而言,《有生》中的“历史”毋宁说是祖奶这一叙述者建构的,通过“叙事”生成的。从写法和价值取向上看,《有生》属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体现了从历史材料和事实中“发现故事”的敏感性和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作家在当下“复活历史”的价值取向和“建构的想象力”。《有生》情节的结构组织,个性人物的塑造,对某些因素的抬高或贬低,叙事声音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对历史事件做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的处理,包括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赋予,较之更具事实性和公共性品质的历史,更具审美想象和艺术创造空间上的个人性、自由度。在《有生》用想象构筑和“复活”的历史中,读者感受到以往少为人知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被人们长久忽略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触摸到一颗颗在历史长河中饱受苦难的痛苦或麻木的灵魂。这种历史是从日常生活和个体感性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它虽由虚构和想象生成,却更有朴素而刻骨的真实。
《有生》体现出散文化、片段化的“历史”叙事美学。小说既有鲜明的史诗性宏大叙事诉求,又有突出的日常生活叙事风格;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细节等方面,具有现实主义典型化特征,又有明显的散文化结构和片段化形态。
一方面,《有生》塑造人物心理、性格,描述其遭遇和命运,不乏戏剧性和偶然性因素。毛根、如花、北风、喜鹊等主要人物乃至花丰收、钱宝、麦香、黄板、乔秋、乔冬等次要人物都有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尽相同的“执”性特征。命运多舛的祖奶先后经历三次婚姻,有过三位丈夫,生育九个儿女。其漫长人生充满难以言明的偶然性因素和突如其来的戏剧性事件。首任丈夫李大旺死于猛兽之口,次任丈夫白礼成趁回老家之际带着幼女白花莫名消失,音信皆无,第三任丈夫于宝山实为隐藏身份的土匪,发现后被枪决。她的多位子女死于非命。《有生》中的“历史”充满不期而至的偶然与巧合,常会改变人的生活道路,使其命运飘忽不定。这与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极为相似。
另一方面,小说在叙事结构和形态上却又偏离情节型戏剧型小说模式,在总体上采用历史与现实、回忆往昔与描述当下彼此交错的结构,有意识地打破连贯的情节线索,破坏故事的连贯性。在叙述方式上,时常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加入风景习俗描写和入物的思想、情感描述,叙述者也不时将当下的认知、情感渗入“历史”,这进一步消解了“叙事”构成的有机性,强化了散文化、片段化和弥散性。《有生》这一叙事美学特征,解构了现实主义“叙事”之整体性、总体性和有机性,由此亦可见出其与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另一关联。
那么《有生》形构这一叙事美学,原因何在,有何症候性意义?
首先,小说以个人化、民间化立场和视点,解构国族性、政治性立场、视点及其叙事范式,凸显个人世界和民间社会的丰富驳杂和自由精神。作家走入个人的生活、情感和心理深处,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借助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书写日常“小历史”。更进一步说,《有生》讲的与其说是曾经被“大历史”压抑的“小历史”,不如说它讲的是“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主人公之间的联系颇为松散,他们是以“祖奶接生的孩子”身份,在作家有意识地设置的“伞状结构”中建立联系的。小说有意放弃历史的宏大、壮阔、厚重和建立在历史行程与规律之上的整体感,专注于祖奶等人物琐细的人生经验铺展而成的生活流程和生命轨迹,此举裂解了宏大历史的偶然、具体、个别因素和精细、别致的碎片,建构了别样的历史叙事诗学:悠长、细腻、舒缓是基本叙事语调,伤感、凄凉、幽婉、苦痛,是叙事情感基质。
其次,强化历史/现实叙事的技术含量,追求文本化、审美化的叙事策略,让历史/生命通过“文本自身”得到更内在、更具“普遍性”的表达。在这一点上,《有生》的新历史小说气质,使之游离于经典现实主义叙事美学原则和主流历史叙事话语范式。小说由历史性(时间性)向共时性的转换,由历史的仿真性、模拟性向虚拟性、虚构性的偏移,由“历史”向“小说”乃至“文本”的倾斜。作家的想象力、叙述能力、修辞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叙事更精细,文本更精致,技术含量和艺术纯度更高。这并不是说,《有生》中没有对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客观描写和作家对乡村生活经验的熟稔以及对历史的理性认知,而是说,相比之下,小说的想象性、主观性更为突出,作家赋予人物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更多的感性生命色彩,换句话说,作家更多以感性方式呈现未经“聚合”的自然、生活和人,赋予其根本性的“生命”认知。实质上,这种“呈现”固然说明作家细腻真切的情感和扎实的写实能力,但也离不开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风潮过后遗留下的文学遗产的催化和淬炼,离不开作家个人主体性和“纯文学”意识的确立,以及对“自我”“内面”生命隐秘的青睐。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及作为其“后续”的新历史小说对不确定性、偶然性、荒诞性的浓厚兴趣,可视为文学丧失了现实观照的整体视野和历史纵深感的典型症候。但是,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历史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已经固化僵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和方式。胡学文便是其中一位。历史/现实整体性的消失,释放了生活和生命空间,也释放了文学的想象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大叙事”解体后四处弥散的“小叙事”,如何在“小叙事”之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使之超越碎片化无机性存在,重建文学的超越性理想性维度。《有生》对历史/现实的个人化、片段化处理,既是对“小叙事”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认同,也是其重建“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前提。作家以“小叙事”为基础,尝试在历史/现实、过往/当下的关联中有所寄寓。这是小说立足当下、个体,重返历史、超越个体的价值选择和美学呈现路径。
二 “文本性”的解构与“真实性”的重构
因个人化叙史的基点和路径,想象力、技术性与故事性的调和以及民间野史秘史的写法,将《有生》划归为新历史小说,自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二者之间亦有不可忽视的差异。
新历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对“大历史”及其正史化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对于《有生》来说,新历史小说及其反叛对象是一个坐标,却不是唯一的坐标。从建构性维度上看,《有生》具有传统/正统历史小说的基因;从解构性取向上看,亦不乏新历史小说的遗传。但从整体品质和内在精神向度上看,《有生》是一部诞生于新世纪的建构性或重构性历史叙事。
从小说主人公形象上看,“祖奶”饱含作家的深情与真情,笔法庄严正大,代表了一种穿越历史苦难和时代风云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祖奶”与莫言《丰乳肥臀》的主人公“母亲”上官鲁氏有极大相通处,都在多灾多难的历史/生命历程中,表现出坚忍、顽强、超拔、伟岸的意志品质,都能从容自若地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共同拥有宽容、包容的“大地”品格。“母亲”和“祖奶”都是历史与现实中“女性/母亲/母性”的象征,她们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都生育了九个儿女,“祖奶”更是以接生婆的身份将万余生命引领到这个世界。同时,她们也都是历经苦难和磨难的底层民众的象征,体现着作家对自我、人民和民族认同的深切思考。
在此脉络中,《有生》可看作对《丰乳肥臀》(及《白鹿原》)的承续和转换,也是作家胡学文摆脱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的实践。
莫言赋予“母亲”强烈的野性和反叛性格,其生育也带有突出的反叛和复仇意味。或因此,“母亲”和《丰乳肥臀》遭受了激烈的道德化指责和非议。相比之下,“祖奶”形象是在母亲和接生婆两个层面上塑造的。作为母亲,“祖奶”的九个儿女中,除了长子李春是被歹人强暴的结果,其余子女都是常态感情和婚姻的自然产儿。最小的三个儿女于秋、于冬和于枝,本是她与隐匿身份的土匪于宝山所生,但在于宝山身份暴露被枪决之后,三个孩子改随母姓,“那一页翻过去了。至少暂时翻过去了”。“祖奶”的生育,是女性之本,人性之常,不像《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一样与“性”关联甚大。在“祖奶”漫长的生育过程中,唯一的也是最为强烈的生育欲望,出现在死神夺走五个孩子之后,“生育的欲望强烈而又疯狂”,她“只在乎他壮实的身体”。但这显然也是在“我要生更多的孩子”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性”的意义上。作为接生婆,无论在接生技艺和医德上,“祖奶”是一个近乎纯粹完美的,被乡民看作观音再世的神圣形象。如果说,“母亲”上官鲁氏兼具解构性和建构性,那么“祖奶”乔大梅更直接更完整地体现了小说正向建构性品质。
其次,文本性与真实性。新历史小说的“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叙述性、文本性,历史成为“文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是作为事实而是作为语言的编织物和叙事的后果或效果存在,因而其意义和价值也处于不断的重构中,呈现不稳定不确定状态。这既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有关,也从解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叙事学理论中获取动力,后者恰恰是作为当代中国“纯文学”想象巅峰的先锋小说以及作为其转换和遗绪的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小说可称为“叙述主义的历史小说”。从深层看,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实验、文本革命与“放逐历史”之间构成无法剥离的形神关系,“‘历史’固然是新潮作家逃离现实的一种表现,但更是他们的创作得以充分发挥的温床。在‘历史’的庇护下,新潮作家可以不顾一切既成的文化和文学规范的制约,对于整个世界(包括历史和现实)进行纯审美化的自由建构与创造。正因如此,在新潮小说中‘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被新潮作家彻底消解了,经由新潮作家的误读与改写,历史最终只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的思维载体和媒介”①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92页。。叙事形式和语言的游戏化,是历史的空洞化和时空结构的非理性化与非逻辑化的美学表征。其“新”恰在对传统历史观和真实观的颠覆,对历史和真实之性质的重新认识。新历史小说提供了不同于权力话语操控、修饰和叙述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另一种“历史”和“真实”,这一真实往往是在个人、民间、性别等价值维度上建构,与偶然、具体、个别、零散以及历史之无常、暴力与人性之恶等因素有关。
《有生》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人称等方面多有先锋性操作: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以个人化、边缘化视角呈现多样化历史图景,凸显个人/民间叙史立场;使用当下叙事者的回忆方式,建立后设式叙事视角,强调“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之间的距离,使叙述者自由出入历史/现实的不同时空,完成历史/现实的对接和勾连;同时,叙述者“祖奶”在讲述自身经历和过去的故事时,也站在此时此境中对彼时彼境中自己的言行和心理作出评价。
以上种种,昭示着《有生》某种程度的具“先锋性”或后现代性因素的“文本性”特征。但“文本性”只是《有生》使历史“陌生化”,获得新的文学性的艺术手法和技术手段——《有生》藉此重新释放出历史/文学的双重能量。
《有生》具有朴素的温和的现实主义风格,似乎一切叙述和描写无不具有细腻入微、亲切动人的真实感。但随后作家却告诉我们,这一切包括祖奶都是“虚构”和“臆想”。胡学文在《后记》中以虚构和“臆想”的形式抵达“真实”。接下来,他写道:“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写家族的鸿篇巨制甚多,此等写作是冒险的,但怀揣痴梦,难以割舍。就想,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①胡学文:《我和祖奶——后记》,《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41、942页。进而是“伞状结构”和祖奶及其他五个人物设置的叙述视角——作家之所以不以祖奶一个人物的回忆做叙述视角,亦是出于作家个人的“叙述”趣味,“省劲是好,只是可能会使叙述的激情和乐趣完全丧失”②胡学文:《我和祖奶——后记》,《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41、942页。。《后记》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叙述”:虚构与真实,叙述形式、叙述结构和叙述视角。而“家族百年”“长篇小说”则寄托着作家的宏大叙事欲望;将“祖奶”视为“宋庄的祖奶”“塞外的祖奶”亦情词恳切、寄托遥深。可以说,《有生》有效地实践了作家的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其“叙述/形式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叙述/形式”念兹在兹,既是为了突破既有家族史叙事模式,亦是为了敞开历史/现实的多元景观。这一目的是通过主叙述者祖奶和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等“视角人物”达到的。通过五个小说人物作视角,《有生》以个人化的零散的方式,散点透视历史/现实之广度、深度和复杂、斑驳。但小说中多种声音的混杂和片段化故事、场景的驳杂,并未使其陷入彼此疏离和弥散状态,究其原因,一在作家有意设定的祖奶与视角人物之间的接生与被接生的“拟家族”关系;二在所谓视角人物之本质是小说人物,由其观照和讲述的“现实”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背离关系,毋宁说,不同的“现实”之间构成互补,不同的“现实”连成一体,形成整体性“事实”;三在小说虽有五个视角人物,但五个人物的“现实”讲述并非以第一人称而是以第三人称作叙述视角。这与新历史小说的解构性多视角设置有着根本不同。二者虽均以个人化视角来呈现多样化历史图景,但后者意在通过个体/边缘视角所内蕴的价值取向消解宏大叙事的同质性,且在深层隐含当下理性主体的缺失和历史/现实之仅作为某种修辞效果的存在,“先锋小说本来可能在‘话语讲述的年代’中隐含更为明确的历史理性的批判力量,然而,事实上,‘讲述话语的年代’是以‘遗忘’的方式缝合进这个‘话语讲述的年代’,并且其寓言功能也是在无意识水平上完成的。历史/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置换同样值得怀疑。其寓言式的书写仅仅是在对自我及其现实的‘遗忘’意义上才能读出‘讲述话语的年代’的隐涵”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苏童《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敌人》等小说皆是如此。《有生》以第三人称建立的个人化多元视角,则是建构性和互补性的,其意不在提供一则神秘隐晦、真假莫辨的“现实”和历史颓败寓言,相反,其“现实”是稳定的、可作出理性认知和判断的,并且尽管小说有意识地以祖奶的听嗅感觉和意识流动,“进入”历史/现实,但第三人称智性的介入,不仅使历史和现实具有可触摸的质感和可辨识的实感支持,且使历史(“话语讲述的年代”)/现实(“讲述话语的年代”)直接通过祖奶这一“智慧老人”的感觉、认知相联系,产生可信性和真实性效果;四在作为强大坚韧的历史/生命喻像,祖奶不仅是宋庄的、塞外的,同样是人性、生命和人类意义上的,其世俗性、现实性与超世俗超现实性,人性与神性兼具的品质,在根本上奠定了《有生》中历史/现实的“真实性”。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真实”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之物,而成为语言(叙述)问题。就《有生》来看,作家一方面认同作为一种语言事实和文化事实的“真实”,将之视为一种话语建构或理论预设,体现着语言的某种功能。因此他自觉地借助“叙述”“语言”营造自己的“真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有生》在历史/现实之认知及其表意形式的先锋性方面,隐含对语言之本体意义的凸显。另一方面,对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混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放逐、解构“真实”的激烈举措,胡学文有所保留,未必完全认同如下观点:“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①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有生》采取“折中”方案,既有对历史情景、社会生活和民俗世情的写实性客观性呈现,又以个人化、体验性、先锋性重构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三 “小历史”与“大叙事”
《有生》书写普通个人、乡间生活和中国民间生存的“小历史”。此处所谓“小历史”包括两层内涵。首先,小说中的“历史”是由祖奶通过回忆“讲述”出来的,实则是一部类似于余华《活着》的“口述史”,此时的叙述者仿佛一位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人类学者,他来到宋庄,听祖奶讲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村庄逸事。小说中的“历史”呈现为祖奶对过去的基于个体经验和体验、感悟和认知的“记忆”,既是个人化的,也具有人类学蕴涵和意义。小说中以宋庄为原点的“现实”,主要由两种方式得以获取和表现,一是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围绕如花、毛根、罗包、喜鹊、北风等“视角人物”和宋品、麦香、宋慧、花丰收、乔石头、钱庄、黄板等,做自然客观的写实性描述;二是通过人物如宋慧、麦香、乔石头等对祖奶的讲述和祖奶的倾听、感受,间接写及。
其次,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以小人物的人生故事,描述乡间社会、乡间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情态及其在百年中国的延续、繁衍。小说借用“大历史”框架并将之推远为朦胧的背景,使“大历史”转化为民间的日常生活史、情感史。无名的乡间百姓作为叙述主体,使沉默无言的小人物发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作家化身乡间社会一员,细致观察和描摹乡间生活和人物的细部,写出其自身生活和生命的鲜活颜色和丰富层次。
历史不是抽象的观念化的存在,它由无数的有名无名的个体生活组成,历史的生命便来源于此。可以说,《有生》是村落史、家族史、家庭史,乃至民间史、民族史,但更是个人生活史和个体生命史。在小说中,除了作为标题出现的祖奶、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等六位人物,“历史”部分出现的祖奶的父亲乔全喜、公爹李富、小姑子李二妮及祖奶的儿女李春、李夏、白杏、白果、白花、乔秋、乔冬、乔枝,“现实”部分出现的宋慧、麦香、安敏、乔石头、黄板等,都在个人的心灵史、情感史和命运史意义上被塑造。小说将普通人作为叙述主体,意味着他们作为生活主体和感性生命主体,也是作家眼里的历史主体。作家由对他们的外在观照进入内在发掘,呈露出日常化历史自发的生机与活力,“大历史”冲击和裹挟下生命个体沉陷与挣扎于其中的困顿与贫乏、困境与危机,以及个体生命应对苦难与困境的调适与坚持。
《有生》如此结构和写法,颇有意味。首先是,借鉴“口述史”写法,将人类学方法带入文学之中,使“历史”具有了当下的现场感,同时当下感受和当代意识也融入历史,用当下的体悟和“问题”来丰富和重塑历史。“现实”中时时浮现“历史”的影子,其深层积淀着祖奶的人世感悟和民族集体无意识,这一点在“蚂蚁”意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蚂蚁”既出现于“历史”即祖奶的记忆中,又出现在祖奶当下的感觉或幻觉中,出现于祖奶母亲、父亲和女儿死亡的时刻,也出现于当下祖奶焦虑不安的时刻。“蚂蚁”意象和“蚂蚁在窜”的幻觉、感受,反复出现多达数百次,更在深层有效地连接了历史与现实、历史记忆和当下体验。在此意义上,暴力、苦难、死亡等构成百年中国历史本然状态,而与其相关联的创伤、痛苦、压抑、烦闷等构成当下创作主体对历史/现实的根本体验和认知。而这一体验和认知,在小说中是通过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故事”和“蚂蚁”等细节来加以艺术把握的。也即《有生》的百年历史叙事,是充分文学化、艺术化的。
《有生》是一部“大叙事”作品。“大叙事”未必直接对应于“大历史”,由小见大、由小及大需大情怀大境界。《有生》超越常见的新历史小说之处,首在小说并未刻意设置“小历史”/“大历史”的对立。小说将历史从国家、民族层面向个体/民间层面的推进,具有反思传统/正统历史叙事和新历史小说的双重意义:尊重个体生命,关怀底层民众,描绘凡人世界的琐细卑微、喜怒哀痛,表现粗鄙却强旺的生命活力;同时,不流于对“大历史”的刻意解构以至亵渎,不将“小历史”置于“大历史”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加以保守狭隘的处理,不过分渲染、美化民间社会和凡人世界。因此,《有生》并不以土匪娼妓、流氓官绅、草莽流寇、帝王后妃等常占据新历史小说主角位置的角色为主要人物并为之标榜,小说以常性写“生”、写人,在常人常性中照亮幽暗,掘发微光。
在以感性个体生命探究“人”的生存之真和生命之真方面,《有生》与众多新历史小说颇为相似,但其差异也是明显的。新历史小说因对传统/正统历史叙事精神化崇高升华机制的反动,对“人”的生命化处理往往以本能化欲望化出之,“人”之恶、人性的贪婪自私、心理的扭曲变异,往往是被突出的因素,由这样的“人”构成的“历史”便成为个人的复仇史、暴力史、压抑无望的生存史,难脱陈陈相因的暴力循环和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窠臼。这种历史虚无的写作,放逐历史理性和主体之人,时或蜕变为自娱自乐的语言嬉戏。《有生》召回历史与主体之人,并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基底,藉由生命之径加以重构。小说中尽管有战争、杀戮,如祖奶的父母和两个儿子李春、李夏皆死于战争及引发的动荡、离乱;尽管也写到人性之自私褊狭,如李二妮、麦香;人性之恶,如赵再元;人性之软弱怯懦,如罗包,却并未将之视为人性的本质与真相,而是将其作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性事实做客观本然的描述。《有生》藉常人生活之厄运,凸显人性之美德,不仅将祖奶塑造为生生不息民族精神的化身,在黄师傅、祖奶父母、李富、宋慧、喜鹊、如花等人物身上,同样寄寓了人性伦理和道德魅力。
自清末历经现代、当代直至当下的漫长时空绵延,充满波折动荡的历史与时代变迁的整体观照,“拟家族史”架构关联各色人物,对历史的生命本真性认知,奠定了《有生》的史诗性品质——《有生》未尝不是一部“女性命运的史诗”或“个体生命的史诗”。《有生》描述个人命运的变迁和“拟家族”的历史沧桑,它是古老人性的悲歌,带永恒意味的生存寓言,也是生命活性与原力的深情歌吟。小说体现着作家“现在与过去”的强烈对话愿望——它既发生在思想文化层面,又发生在历史叙事美学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文化复兴和共同体重建的历史诉求,召唤出《有生》式的生命史诗写作,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历史性”,《有生》借此显露了与传统/正统宏大叙事和新历史小说的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