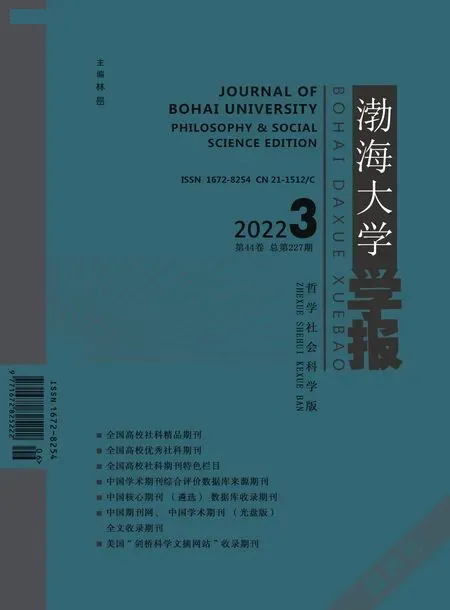现代性叙事的新变
——评津子围《十月的土地》
张红翠 田芳芳(.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6000;.大连财经学院公共教学部,辽宁大连 6000)
小说家津子围的文学写作令人钦佩地坚持了40年,他有自己相对明确的风格,但又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十月的土地》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叙事的传统经验,也打破了阅读进程的一般惯性,令人困惑,甚至显得“危险”,但深究起来,又令人意外、欣喜和佩服。总体而言,《十月的土地》无意实现塑造核心人物的小说意图——小说人物平静地来了又走,没有谁真正驻留在小说中心;《十月的土地》也远离了对现代之物的叙事兴趣,没有表达对现代与传统之间纷争的意见,最终也未必回到传统,呈现了文学观察的客观性与开放性。从根本而言,《十月的土地》将叙事的第一性存在归还给大地,完成了一次原乡书写——回忆大地景象、讲述“大地上的事情”。以此,叙事者向生养人类生命的土地致敬。
一、小说的中心人物
《十月的土地》有中心人物吗?阅读过程中,这个问题令人颇费脑筋,而这种叙事手法对阅读者(至少在我)而言也是颇令人疑惑的。直到小说最后,我才和自己确认——小说没有所谓中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中了小说家的“圈套”,或者说我们需要改变惯性的阅读思维,这个最后的判断则来自笔者阅读体验中的几次停顿。阅读《十月的土地》,笔者有几次不自觉的停顿和疑问,开始怀疑作者是不是真的如几乎所有的小说叙事那样,致力于塑造某个或者某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心人物?这种怀疑情绪分别出现在小说行文的1/5 处,小说行文的1/3处,甚至在读到小说将近3/4 的时候我还在和自己确认:作者并不是要塑造某一个典型的中心人物。尽管故事的行进紧凑而具有戏剧性,人物的塑造也极其用心,显示了叙事的投入和专注,但就人物而言,不论是谁似乎都不能从叙事中真正凸显而独立存在。如果真是这样,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这么多的人、写他们相互交叉又相互分离的纷杂故事,最终目的是什么?直到小说即将结束,章秉麟在昏迷的章文德身上附体自白,才使一切“真相大白”。
如果按照惯例,一部小说一定要有个“主人公”或者一个灵魂式的存在。我认为,《十月的土地》的主人公应该是章秉麟——这个在第四章一开场,在为自己准备的寿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消失在故事深处的人物。叙事到最后,在所有人都几乎遗忘了章秉麟的时候,章秉麟赫然出现,完成了叙事的闭合,宣告结束,而这个宣告和结束是相当有力量且意味深长的。章秉麟附体自白的叙事安排,使这个几乎完全消失的人物,重新回到叙事,并在结尾宣布——自己才是叙事者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主人公”,而不是表面看起来贯穿小说始终的章文德。不得不说原来作者之前不厌其烦的讲述、线索枝蔓的故事都不是他的重点,最后的这赫然一幕才是作者的煞笔之所在。确认了这一点,我们似乎就找到了小说叙事的结构与旨意的皈依,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十月的土地》中,小说人物驳杂,故事线索错综;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物被真正聚焦、被真正突出和“用心”刻画,反而都是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看似急切但又“漫不经心”。
我们还可以由章秉麟这个最后的端点向前回溯,在小说内部找到这种判断的叙事依据。除章秉麟之外,活动在小说中的驳杂人物序列包括子辈的章兆龙、章兆仁以及妯娌间的几个女人——章吴氏、曹彩凤、章韩氏等,孙辈的章文智、章文龙、章文德、章文海、章佳馨、章桂兰,以及与之相关的袁骧、肖成锋、郑四娘、赵阿满等人,还有与以上人物人生历程中有交集的姜照成、老庄头、丛佩祥、狗剩儿等人。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较为鲜明的特点,但又几乎势均力敌。叙事者对这些人物的交代几乎都是平均的,没有谁是叙事者特别偏爱或中意的对象,没有谁被叙事者作为中心人物特别暗示给读者。故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人物来了又走——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相互穿插。尽管我们也可以将故事线索的驳杂看成是叙事结构的复线策略,但从整个叙事效果和局面来看,这种多线索的作用似乎不是推动和突出某个小说中人物的核心地位,而更像是“自然地发生”。其效果更在于对人物特性和叙事存在的淡化,对小说人物被中心化、被聚焦化倾向的客观消解,对人物性格被突出化的阻止。因而,人物故事的相互穿插也是相互中断和彼此淡化,就这样和小说一起不温不火地奔向并无高潮可言的结尾。然而,在急速(匀速)甚至有些“平淡”的叙事之后,叙事者突然亮出底牌——章秉麟突然出现,小说的最终立意即刻清晰。同时,章秉麟的出现巧妙地在结构上完成了叙事的闭合动作,使得“平淡”的小说在结构上生出耐人寻味的“趣味”。这个闭合(回环)的结构的开始是小说的起首故事——章文德的濒死及章秉麟的救治,结构之完成则是小说最后章文德的迷幻之梦,以及章秉麟的附体独白。这个谜题与谜底似乎是叙事者故意抖给读者的一个意外。章秉麟在结尾处的出现就像一盏灯或一束光,向后照亮了整部小说(一直带着疑问走过来的阅读困惑),好像让读者突然间找到了叙事的深意和真正意图,并重新考虑对整部小说的理解。
当然,要接受这种解释的合理性颇有些困难,毕竟是章文德的故事贯穿着整个叙事的展开。然而,即便是从表层结构看构成作为小说主线的章文德,也算不上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小说也几次描述了章文德特异的对于土地的禀赋:他可以通过鼻子闻,确认哪种土壤适合种哪种农作物,被日本人岩下说成是“土地爷”;他可以辨别日本人农业实验室中不同试管中土壤的特性,表现了一个土地之子的特有气质。但是,尽管章文德对土地的痴迷眷恋,以及对农耕的用心钻研颇具戏剧性甚至是传奇性,但是他一生的故事,包括紧要关头的勇敢和最后的离世都还不足以让章文德立在叙事中央,宣告自己是叙事的核心人物。因为不管是章文德的故事还是他的人格,都没有被着以特别的笔色以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叙事并没有将章文德“价值化”,章文德自然也没有获得这种自我宣告的权利。尤其是,章秉麟的最后出现也揭示了章文德的“第二性”位置——“就在那天早晨,章文德恍惚在半梦半醒之间。……章文德的身子一抖,模糊的意识清晰起来,原来自己是章秉麟!章秉麟从章文德的躯体里钻出来,飘浮在半空中,他俯瞰着躺在土炕上的章文德,眼前是迈向老年的章文德,而童年的章文德仿佛就在眼前。”[1]章秉麟回忆起章文德濒死被送到郊外,自己救活章文德的过往,救治的过程中,章秉麟想:“如果自己的灵魂被置换到章文德的躯体里,他真的有勇气要放弃自己那个叫章秉麟的人生,而选择孙子那个叫章文德的人生吗?……那将意味着什么?……章秉麟越想头越疼,越来越不能自控,等那一切恢复过来时,为时已晚,他觉得自己已经进入章文德的躯体。”[1](365-366)
这个最后的交代让我们明白:从叙事的内在结构而言,确实构成了章文德之于章秉麟的“第二性”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使小说内部的人物关系——叙事意义上的,而非世俗意义上的——也逐渐清晰:章文德以及故事中的纷繁人生都是章秉麟飘浮于大地之上、出离于时间之外的灵魂所看透亦参透的“人生过往”,是他被风干的记忆而已。章文德只是一个浮在叙事时间之上的牵引,他拖曳的是悬浮在叙事上空的“章秉麟”的幽影(与之千年又回环往复),幻化成叙事的全能视角。这个视角保存着作者关于生命大循环的存在性认知,这个视角也照临了整个叙事与全部人生,照临大地上的一切景象——包括历史、包括人生,甚至包括“诗与远方”的理想。正如章秉麟最后所说的那样:“人情冷暖,恩恩怨怨,生离死别……不管是直的路还是弯的路,都得走过去,不管是深的河还是浅的河,都得蹚过去。很多事情都是重复的,春天来了,夏天到了,秋天过后,冬天走来。日如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知道他是在经历自己的事情,还是在经历孙子的事情。”[1](366)章秉麟的人生体验已经超越了个体的经验,回归到生命终将回归的大生命。在这一层信念中,只有永恒循环的生命的绝对形式在荡漾,流经每一个大地上存在过的人的身体和感知。章秉麟道出这一“秘密”并确定:“没错,所有细微的体会是没有人知道的,别人只知道事情,而独特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1](366)而这些事情,以及不能为人所知的感受,也会随着生命的终结和时间的推移慢慢模糊直至消散。由此又可见,章秉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在完成叙事功能,而是作为一个认识论来实现叙事的最后升华,没有这个升华,小说是“岌岌可危”的。
津子围在小说中对“中心人物”的悬置也许是要挑战或是提示读者:当我们一直期待在小说中寻找一个或几个形象突出的典型,甚至与叙事者一起来完成这个塑造任务的时候,小说家却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像我们一样要提供给我们一个期待中的人物;告诉我们,小说或许可以不必仅仅为塑造人物而操心。如果这种理解能够成立的话,或许这可以被认为是津子围又一次大胆的实验。这种实验是危险的,危险不在于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在于能否说服阅读者接受小说家的拓围。
二、小说关于现代与传统的意见
我本也以为小说要谈一个关于“现代之物”与东北古老土地相遇的、东北早期现代化的故事。因为小说曾交代章文智对改良农作物种植技术,以及对诸如像瑞士钟表这些洋玩意儿的喜爱和着迷;说到日本人岩下对章文智说起要把莲花泡变成“新工业区,到时候,这里到处是机械,有楼房和高高的烟筒……章文智被他描述的前景所吸引,目光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想了想,问岩下,到时候,这儿可以骑洋单车(自行车)吗?岩下说不仅可以骑自行车,而且还有汽车”[1](34);也讲到“望着火车冒着白烟消失在山湾里,章文智对章文德说:‘咱应该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很多新鲜玩意儿咱都没见识过’”[1](36);讲到手摇电影、现代教育、体制与内容等。这些情节都极易让人以为作者要讲述东北早期现代化的故事,以及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社会学、文化学观察。
但是,故事后来的发展推翻了这个感觉和推断。章文智迷恋现代之物的故事最终因为被石龙二兄弟绑架不了了之。这个“打乱”显得荒诞突兀,给人无厘头之感;而与之呼应的,则是后来章文德因痴迷日本农业实验技术并接受邀请进入日伪农业研究院,只是没过多久,章文德就从日本实验室逃离,至此,日本的现代农业技术便不再提及。这使得章文德与现代之物的会面与接触很快无疾而终,草草结束。从小说叙事的整体来看,这前后的两个故事之间构成了结构呼应和意义互文——章文德的故事确认了章文智与现代之物的分离,取消了叙事对现代之物,以及现代文明进行价值化赋予的可能,同时也隐证了作者无意书写东北早期现代性症候的态度。即作者对写一个东北的现代化故事似乎并没有兴趣,那些新的外来之物并没有在小说中构成一个有影响的力量和线索,而是短暂出现、闪瞬即逝,仅此而已,他们参与了历史,但并不代表历史的绝对方向——这种观念确实形成了与时下(许久未经反思的)观念的一种对比。小说家也许是要我们留意流行已久深入人心的观念——并不是大地限制了小说中那些爱土地、忠于土地的人的想象,而是诱惑鼓动了现代人几个世纪的“远方”理想、价值与追寻,无论多么绚烂,最终都将落回到大地之上,成为大地上曾经的存在。但是这种提醒又十分隐晦,甚至不能成为一种叙事者的主张和价值,而是将其转换为飘散在大地上的丝丝忧伤的飞絮,即便是小说家的雄心也同样只是这种飞絮中的一缕罢了。所以,《十月的土地》没有简单讲述有关现代的故事,也不走向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因为这种反思现代的疏离态度、这种文学的立场和叙事策略已经不是新路。这种客观超然的叙事呈现,恰恰体现了写作者的开放性态度——对还来不及判断的历史绝不做轻易的判断和结论。正如作者所说,写作者就是要尽量客观地呈现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把某种知识作为既定的结论或者价值兜售给读者。
三、土地——第一性的存在
至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章秉麟构成了叙事的第一性存在。但是,章秉麟的存在就是绝对的第一性吗?似乎并非如此。整体来看,小说真正的第一性存在应该是“土地”。土地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它保存了所有生命活着的痕迹和回忆,当生命穿过永恒的时间之流归于大地的时候,世间仅存的便是我们和大地之间的纯粹关系。土地将一切的纷争都收拢在自己的胸怀里,一切纷争都归于平静。无论是伟大高贵的人还是卑微低贱的人,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都一样,最终将消失在大地的苍茫之中,没有谁能够留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痕迹,因为历史也将消失在大地的苍茫中。只有大家共同传唱和吟诵过的“诗”(谚语、童谣等)……成为流经每个人的永恒形式,与大地上的景象长存于大地之上。叙事者将这些比人的存在更持久的存在筛选了出来,并仔细记录下它们的样子——它们是与天地、山川自然及童年有关的农谚(天有骆驼云,冰雹要临门;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瞎话(大年三十亮晶晶,正月十五黑咕隆咚,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顺口溜儿(雨天下雪,冻死老鳖……)、歌谣(迷楞迷楞摸摸,里面住个哥哥……)、对联(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风流;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不畏风霜向晚欺,独开百花已凋零;人性直节生来清,自诩高洁老更坚……)和俗语俗段子(四大黑、四大白、四大红、四大瘪故),是韭菜的样子(起阳草,春香、夏辣、秋苦、冬甜)、豆角的种类(兔子翻白眼儿、大姑娘挽袖、长豆角、油豆角、刀豆角、胖孩腿、玻璃翠)……
这些声音留在东北土地上,在不同时空中持存并沉淀成为一种永恒和绝对的形式,在土地上发生作用,人就是这种作用。不论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性都要经过这些永恒的形式,或者说被这些永恒的形式经过。当小说在细数这些童谣的时候,兴高采烈,饶有兴味。当读者读到这些俗谚、听到这些童谣的时候,也几乎忘却身份、地位,似乎被吸附进一种原始的初生形式,被抱慰、被无差别对待,也好像回到了没有差别烦恼的纯粹之境;而土地上的无差别又是土地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作者通过这些农谚童谣赞颂了土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然而,这些永恒的形式背后所记录和保存的,却是多样性生命消亡之后的苍茫感和悲凉感。
这种感受在小说中被表达,短暂含蓄却让人难以忘怀。在章文德离家抗日之后,阿满一个人带孩子逃难,遇到改嫁他乡的郑四娘,穷困的郑四娘收留了她们娘三个。阿满和郑四娘两个女人惺惺相惜,忆起往事,互相打听故人的景况:“在露水河的时候,阿满听郑四娘(顺便说一下,郑四娘的故事不可以读成东北民间叔嫂之间简单和低俗的关系,在和章文礼及曹双举的关系中,郑四娘从来没有享受‘大嫂’的主动和‘大嫂’的‘地位’。这种委屈在历史上的民间女子中又何止郑四娘,但叙事者并未展开,而是把抚慰交给大地的诉说)说起过曹彩凤……郑四娘向阿满打听薛莲花的情况……阿满也向郑四娘打听过小货郎和小丁姑,她经常听章韩氏和章文德提起这两人,记忆中有好几个关于小货郎和小丁姑的故事,可不知为什么,郑四娘说她从没听说有小货郎这个人,也不承认在小货郎手里买过东西……”[1](349)多年以后,两个故人相遇,念及过往的人和事,凄然而沧桑地相互打听——最温暖也最悲凉——时间流逝的丧失感在两个多年未见的女人艰苦患难的相逢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极尽人情。这种打听就是隔着时间的回忆,回忆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回忆本身。如章秉麟最后所说:“人的魂儿被身体囚禁,而人的身体却被大地囚禁着。那种感觉,就像不知不觉流逝的岁月,人是大地的记忆罢了。说到底,无论你怎么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烂成为泥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1](366)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小说被赋予“十月的土地”之名,“十月”是叶落归根的时节,是大地将一切收回的过程——包括历史(无论是大写还是小写),包括所有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包括各种价值信念(现代文明也好,传统蒙昧也好)。以此为参照,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叙事对几乎每个人物故事的讲述都没有给予明显的倾注,因为所有的留驻都将成为曾经的生命,曾经的、最终灰飞烟灭的活动过程而已,谁也不能站在时间的中央,成为一个“典型”的存在。所有的存在都将让位于大地的形象——并无形象可循的存在。
结语:传奇性与哲学性品质
小说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传奇性与哲学性。
首先,传奇性特点。小说借由对东北民间风俗的描摹,囊括了“关帝庙”“成精”“阴曹地府”及“附体”“拘魂码”等传说,这些符号在小说中的出现,使小说呈现了“传奇性”特征。这种特征,与其比类于马尔克斯的魔幻之影,不如说是中国文学悠久的“传奇”性基因的现代复现。自上古神话开始,中国“传奇”就蕴蓄着旺盛的文学创造力。“传奇”的叙事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面相之一,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在西方及西方之外的文学流脉中,这种趣味也作为根基性的审美而存在,表达的都是多样化的人群在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的想象和向往、悲苦与达观……只是,在科学主义的标准化审美尺度下,在大数据的技术生产催生的标准化审美趋向的文化品位中,这种传奇的、无法用标准尺度来“驯化”和衡量的异质性文学经验已经被逐渐遗忘;而《十月的土地》重寻那些冰封在尘土中的文学景观,不仅还原和保存了多样化的、民族本土的审美质性,也暗藏着突破标准化、统一化现代文化规范边界的叙事努力,形成对现代生命经验的镜照。因而,辨认小说中的传奇特性并将之与中国文学自身的传奇性相连接是我们续接文学传统的重要方式。
其次,哲学性品质。小说一开始便讲到12岁的章文德快死了,叙事者说:“他不会把自己的感受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当然,也不明白自己事实上处于濒死状态。”[1](1)这不经意的一句拓展出对生与死、有形与无形世界的思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顿然洞开,也奠定了小说叙事的哲学性品质:即小说在摹写出东北大地上的事情的同时,还写出深深的哲思与悲悯。这决定了小说后来的展开在向下细摹东北日常生活之时,又始终有另一维度的超越性视角在盘旋,这是小说全能视角的深层动因;而这一视角的作用,与章炳麟的叙事功能、小说的闭合结构,以及土地的第一性存在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是小说超越性境界和哲学品质的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