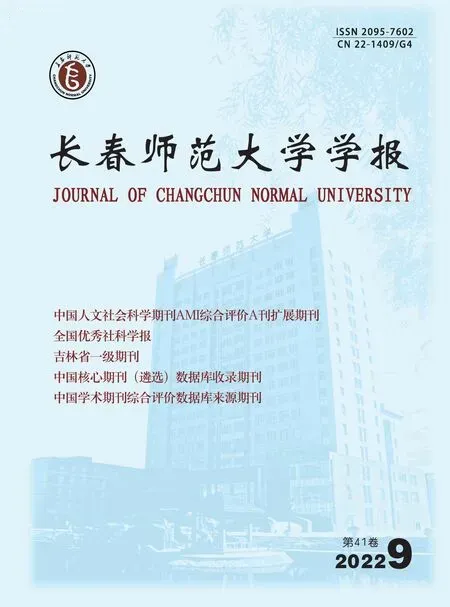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起源与嬗变
杨 帆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作为西方乌托邦文学创作的理论源泉,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变化和演进深刻影响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创作与接受。因此,有必要从梳理西方乌托邦主义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结合西方乌托邦文学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历史嬗变进行分析和述评。
一、西方乌托邦文学探源:西方乌托邦主义
“Utopia” (乌托邦)①一词由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所创。1516年,莫尔写成《乌托邦》(Utopia) 一书,近代第一部乌托邦小说就此问世。为给书中那个神奇的海上小岛命名,莫尔将希腊语中的否定前缀“ou”与表示地点的“topos”合并,并增加后缀“ia” ,用“utopia”表示“不存在的地方”[1-2]。莫尔笔下的神奇小岛是一个世外桃源,处处充满着人类社会理想——人民不仅长相俊美、具有神力,且远离苦难、无比富有;社会自由、民主、博爱,生产力发达,科技先进。在《乌托邦》结尾部分的那首六行诗中,莫尔将这个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小岛称作“eutopia”(优托邦)[3]。可见,“想象中的好地方”正是莫尔想要表达的乌托邦的含义。
在西方世界,莫尔并不是对想象中的好地方进行幻想的第一人。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想象中的美好地方或生活,最早出现在犹太经文和古希腊文学作品之中,如 《旧约》和《荷马史诗》。《旧约·创世纪》中记载的“迦南之地”(Canaan)[4],意思是流着奶和蜜的应允之地;《旧约》中的《阿莫斯书》《何西阿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列王纪上、下》和《以西结书》均记载了希伯来诸先知的预言,为人们带去美好生活的希望。在《荷马史诗》中,“厄鲁西亚”(Elysium)指的是可供悠闲生活之地,它位于大地的尽头,是长发飘洒的拉达门苏斯的居住地[5]。“应允之地”和“厄鲁西亚”的例证充分说明,在古典文献中,对极乐世界和应允之地的神往建立在西方神话和宗教宿命论的框架之下。反观莫尔的《乌托邦》,其中则包含思维的革新:其一,它明确表达了“乌托邦”之想象性,也即它是“nowhere”, 是并不存在的地方;其二,它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对新的生活模式进行的主动规划,《乌托邦》实为莫尔对其所生活时代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社会的讽刺与反抗;其三,它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重申,目的是呼吁人们通过理性创造幸福生活。在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时代的大背景下,《乌托邦》中描绘的自由、富庶的小岛生活预示着建设美好社会的可能。强调乌托邦的想象性及批判性特征,被后世认为是乌托邦包含否定一面的依据,也即乌托邦不仅包含对美好社会想象的积极一面,也包含对现实世界否定的消极一面。
除此之外,莫尔的《乌托邦》还开启了一种新的文体叙事模式,即乌托邦叙事。在乌托邦叙事中,主人公往往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记叙一段旅程。在该旅程中,主人公首先到达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随后在当地人的带领和解说下,详细了解那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方式。一般来说,故事末尾常常暗示,主人公将以“信使”的身份回到故乡,带去在那段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传递出一种他者的生活方式[2]。
随着历史的变迁,“乌托邦”的内涵始终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上半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对乌托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曼海姆树立了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研究范式,他用“超越现实”和“打破束缚”两个短语概括了他所定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学价值,不仅强调现实与乌托邦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且将落脚点放在其具有的革命功能之上,凸显了乌托邦在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时作为促成集体行动的思想工具而发挥的作用[6]。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赋予了乌托邦主义严肃的哲学内涵和使命,乌托邦作为肯定的、代表希望且能带领人类走向美好社会的思想倾向得到最大程度的肯定。也正因如此,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学说被乌托邦主义拥护者奉为圭臬,且成为对后来的“乌托邦已死”[7]论调进行驳斥的重要理论工具。在布洛赫的论述中,乌托邦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希望和为希望进行社会改革的精神而存在,二是指代一种能够解决现代社会根本性危机的现实方案和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布洛赫认为后者是马克思所提倡的唯物主义辩证法[8]。
当代乌托邦研究基本上沿着前人所开辟的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哲学研究道路进行。但是对于社会发展前景的可能性和乌托邦实现的必然性问题,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先前风光无限的乌托邦精神及其所预示的美好社会前景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不论是乌托邦学者还是乌托邦作家,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已发生转变。继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之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连续发表巨著,掀起了敌托邦书写潮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通过讨论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推导出人类未来将走向民族—国家衰落、人权终结的结局;郝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等人从发达工业社会人与制度的一体化、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和殖民主义在当代的新表现等视角入手,呈现出当代社会异化的人、支离破碎的社会状态及可怖的未来走向。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指责与声讨,将人们过去对乌托邦的美妙憧憬砸得粉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西方持续了几千年的乌托邦美梦被蜂拥而至的讨伐声惊醒,“乌邦已死”的口号再难平息。从此,乌托邦一词被深深地刻上了“否定”和“糟糕”的标记,甚至一套敌托邦理论或者所谓的“反乌托邦”②社会理论也在逐渐形成。正因如此,在晚近对乌托邦主义的研究中,鲁斯·列维塔斯(Ruth Levitas)和萨金特对乌托邦主义的内涵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列维塔斯抓住乌托邦愿望的表达这一核心原则,提供了一个既适用于多视角研究又能覆盖乌托邦主义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三方面表现的基本定义;里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给出的“三个面向”[9]为乌托邦主义扩充了社会学语义维度,即增加了对共同体主义和乌托邦社会学理论尤其是敌托邦社会理论的指涉。
总之,西方乌托邦主义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和发展,内涵不断丰富。广义上,它是人们对异于现实的生活方式的幻想, 最初是一种对美好地方或美好共同生活的幻想,源于一种原初的乌托邦精神,即认为社会是可以通过改进以符合理想的[10]。 但是,在莫尔之后,尤其在现当代社会背景下,其否定和消极的内涵被不断挖掘。如今,除了“想象中的好地方”这一基础词义外,西方乌托邦主义还指乌托邦愿望、乌托邦功能、作为文学体裁的乌托邦、共同体主义及与乌托邦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进化理论和反乌托邦社会理论等。
二、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古典乌托邦文学时期(1516年以前):神学与政治的结合
古典乌托邦文学时期泛指莫尔发表《乌托邦》之前的历史时期,即公元1516年之前。在此期间,乌托邦文本的主要来源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神话故事,二是宗教经文,三是哲学政治及法律类著作,四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第一类文本以黄金时代的神话故事为代表,如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奥维德 (Ovid) 的《变形记》。赫西俄德描写的黄金族美好生活以及奥维德书写的黄金时代符合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因而成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第二类文本以新旧约中对伊甸园、天堂的描述以及对来世的预言为主,如《创世纪》和《启示录》。宗教教义中传播的美好的天堂形象、千禧年愿景及末世论思想使得西方人对天堂及来世这两个未来世界充满神往。另外,天主教和基督教关于团体修道理念和戒律的书写,如《圣本笃戒律》和《圣方济各修道院章程》也需要关注。因不满教会世俗化而产生的西派教会修道制度,倡导通过集中修行来消除欲望、抵达圣境从而得到救赎,因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第三类文本以古希腊—罗马时代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芝诺(Zeno)的《政制》及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为代表,其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因阐述“理念之国”而成为体现乌托邦思想的经典之作。在中世纪乌托邦文献中,《上帝之城》流传最广,也最具代表性。圣奥古斯丁的乌托邦愿望是构建一个建立在上帝之爱基础上的人与人互相联结、互相爱护的极乐世界。他对“上帝城”和“凡人城”的划分,是对神权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重申和辩护。应该说,《上帝之城》建立在基督教末世论的基础之上,是神学政治论的产物。第四类文本以维吉尔(Vergil)的《牧歌·第四首》和贺拉斯(Horace)的《抒情诗之极乐岛》为代表,两首诗都呈现了对未来岁月完美生活的设想。
从黄金岛到天堂,再到理想国与极乐岛,古典乌托邦文学在古典神话、宗教、哲学和文学文本的并行书写和交织过程中进行,而其中古希腊神话和犹太—基督教中包含的乌托邦思想,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言、弥赛亚救赎和末世论思想,构成整个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思想源泉。由于《理想国》中传递的道德观念、政治观念与基督教神学价值观存在冲突,其被基督教世界翻译和接受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直到15世纪中期后才被译为拉丁语、英语和法语等其他语言。但书中构建的理想城邦是启发后世进行政治乌托邦书写的重要精神来源和参考文献,且因其内容的虚构性和开创性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乌托邦讽刺小说的发端。
(二)近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516—1887年):人文主义与启蒙精神的相遇
近代乌托邦文学时期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 为开端,一直持续至19世纪末。自古典走向近代,在漫长的千年之中,欧洲经历了十字军东征、黑死病、造纸和印刷术的引进、海上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由此引发的地理边界拓宽、劳动阶级觉醒、新知识的传播、社会改革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激发了新的社会哲学的诞生。在此背景下,包含乌托邦思想的文学作品如浪潮般涌来。
17世纪的乌托邦文学见证了基督教乌托邦从繁荣走向结束。面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对欧洲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教会权力的动摇和重构,泛智派希望通过将新科学主义注入基督教文化,建立一个以理性和有序科学为基础的基督教世界,从而为处于风雨飘摇的欧洲社会提供一种有利于社会团结稳定的解决方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托马索·康帕内拉(Th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之城》、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的《大洋国》、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基督城》均构建了各自的基督教乌托邦。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教育常常在乌托邦社会中扮演促进社会团结的角色;在个人财产、私人土地和是否存在社会阶级划分的问题上,则情况各异。
自18世纪开始,西方乌托邦梦想不再囿于基督教乌托邦原型,而是朝着多元化发展。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文学文本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讽刺小说。例如,在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笔下,《格列夫游记》中的小人国复刻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腐败;《鲁滨逊漂流记》在为新兴资产阶级传递信心和力量的同时,也回溯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发家史;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中的叙事虚实结合,既有对现实社会中残酷和冷漠的讽刺,也有对理想中平等自由的黄金国的构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抨击了法国封建专制。二是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启蒙思想家们试图通过理论建构来解决现实矛盾,从而抵达理想社会。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通过契约方式解决人类自然本性和理性的冲突;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论证分权制衡理论如何从政体和公民两方面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三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如摩莱里(Morelly)的《自然法典》宣扬财产平等,巴贝夫(Babeyf)的《平等派宣言》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重农主义平等共和国。尽管各思想派别给出的乌托邦方案不一致,比如启蒙思想家希望建立起摆脱王权和神权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则希望建立平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总体而言,比起基督教乌托邦中对基督教主义、弥赛亚主义、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宗教和哲学理念的大段讨论,18世纪的乌托邦社会文本中呈现出更多的对客观现实的陈述和表达。
19世纪被誉为西方乌托邦文学的黄金时期。此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业已确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成为困扰西方世界的最大难题,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成为乌托邦文学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占主导的乌托邦社会理论是空想社会主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分别在各自理论著作中提出“劳动公社”“实业制度”和“新和谐公社”三种乌托邦方案。不仅如此,欧文和傅立叶还将改造方案付诸实践,在英美分别进行了劳动合作社和新和谐共产主义新村建设实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上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阐释,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小说文本方面,作家伊丽莎白·沃德(Elizabeth Ward)、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塞缪·巴特勒(Samuel Butler)、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各自作品中对理想社会进行了书写。霍桑在《红字》和《福谷传奇》 两部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理想公民海斯特的形象和建立在美国现实乌托邦实践基础之上的布鲁克农庄[11]。
综上所述,近代乌托邦文学见证了基督教乌托邦从繁荣走向衰落这一过程。随着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双重推进,旧的社会秩序被破除,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既面临与旧势力持续博弈的挑战,也直面两者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局面。19世纪中期以后,提倡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改造方案一路高歌猛进,受到广泛追捧,乌托邦社会实验也在英美遍地开花。由于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文本以乌托邦讽刺小说和社会政治理论为主,乌托邦文本便由近代以前以神学和哲学为核心的虚构小说和哲学论著转向以批判和改造社会现实为主要目的的乌托邦讽刺小说和社会政治论,乌托邦文本中的未来社会也从最初的天方夜谭和奇闻轶事逐渐转变为可行的社会实践方案甚至社会实践本身。
(三)现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888—1944年):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在西方乌托邦文学史上,第一个拉开现代帷幕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88年,贝拉米的小说《回顾:2000—1887》成功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早将近30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乌托邦小说中的隆重登场,在西方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在《回顾》的影响下,美国国内掀起了国家主义的热潮。国家主义积极分子先后创建了165个国家主义俱乐部(Nationalist Clubs) ,贝拉米本人也投身相关社会和政治活动,并于1891年创办 《新国家》(The New Nation) 杂志。1897年,《回顾》的姊妹篇《平等》公开发表。在第二部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中,贝拉米提升了妇女在婚姻和劳动中的地位,也优化了国家政治制度,如宣称政治平等权需要公平经济保障,给予公民更多直接的政治参与权和控制权。
在整个现代乌托邦文学发展时期,与贝拉米齐名的还有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和郝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89年,莫里斯在对《回顾》的书评中指出,贝拉米式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中组织生产和劳动的问题,反而将导致个体责任心的丧失;如若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问题则将得到更为有效的解决,原因在于精细化管理能够调动个体在生产劳动中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并促进分工协作,这才是共产主义追求的真正目标[12]。可见,莫里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前途的态度是悲观的。他还坦言,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不平等无法轻易消灭,而贝拉米“英国佬梦想中的天堂(a cockney paradise) ”[13]不但已经过时,还是不切实际、过分乐观的幻想。鉴于此,在后来出版的小说《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乌托邦模式,即一个通过武装革命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强调乌托邦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蓝图,也不是某种必定能实现的社会模型,而是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这类自身努力才能实现的乌托邦愿望,这正是莫里斯对乌托邦的革新之所在。
在发表《时间机器》十年之后,威尔斯提出“动态乌托邦”③的概念,为现代乌托邦作出全新注解。威尔斯强调乌托邦的关键在于其“不受时空、死亡和批评捆绑之想象性”[13]。帕特里克·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认为,这正是“元乌托邦”(meta-utopia)核心要素所在[14]。在后续的小说和评论文章中,威尔斯继续诠释他的乌托邦主义和现代乌托邦小说写作策略。他的“动态乌托邦”概念以及作品中对人类性恶的讥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创作。
20世纪上半叶,“敌托邦三部曲” 在乌托邦文学舞台隆重登场。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 在《我们》中塑造了一个公民被进行彻底机械化管理的极权社会。尽管俄国小说有其自身的敌托邦传统,但《我们》仍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前景实现必然性问题的最振聋发聩的回答之一,书中预示的集权主义和军事主义也在后来几十年中得到逐一应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走向了乌托邦和敌托邦的两极。一方面,书中的世界国(World State)解决了人类的重要需求,如性需求、生殖需求、睡眠需求和学习需求;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先是利用生物基因技术将人类胚胎进行阶级分层,后结合心理操控和行为主义实验的手段将被统治阶层牢牢掌控。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 1949) 中,受“老大哥”操控的极权社会令人窒息和恐惧,奥威尔左翼作家立场也表露无遗。奥威尔的敌托邦写作受到扎米亚京和赫胥黎的影响;另外,担任缅甸警察和参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历,使他目睹殖民主义的残暴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党对党内进行清洗和迫害;加之数年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累积,促使奥威尔将多年以来对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担忧和对极权统治的防范通过刻画一个变形的敌托邦社会的方式全部呈现出来。权力腐败、现代性破坏力、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奥威尔所言,已经部分成为现实。从《动物庄园》到《1984》,奥威尔对社会敌托邦倾向发出连续警告。
由前所述,现代乌托邦文学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第一,贝拉米开启了现代乌托邦文学的重大主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乌托邦道路的探索;第二,以莫里斯为代表的乌托邦小说家意识到社会改良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故将目光投向武装革命的道路,从此,西方乌托邦文学由浪漫主义走进现实主义;第三,“敌托邦三部曲”清晰地呈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对极权主义、殖民主义及科技主义的抵抗,是激进现实主义的表现,它们为当代乌托邦文学奠定了敌托邦的基调。
(四)当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945年至今):时代的变奏
1945年之后,尚未走出战争阴霾的西方又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经济萧条、民权运动、冷战对峙、生态恶化、技术伦理危机等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世界现代秩序在建立、推倒、重建中走向继续充满不确定的后现代和未来。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乌托邦文学 (1945至今)经历了从二战后的缓慢前行逐步开始加速发展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一些描写机械化社会、战时极权主义和战后末世的敌托邦小说陆续出版,以《自动钢琴》《华氏451》和《蝇王》为代表。进入60年代,“布拉格之春”(1968) 和“五月风暴”(1968) 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叛狂潮,目不暇接的美国社会平权运动更是将欧美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推向顶点。在科学技术方面,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工程学突飞猛进。在社会和技术双重变革的重大回响中,“乌托邦主义”再次被重温,各式各样的乌托邦社区成立,乌托邦小说创作数量也随之骤增。《发条橙》和《飞越布谷鸟巢》聚焦行为控制和现代惩罚制度,质疑现代政府在对暴力和精神疾病管控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70—80年代,以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乌托邦作家借由虚拟现实为乌托邦未来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的同时,又陷入对技术伦理、主体性和乌托邦社会制度设计的一系列拷问之中。除此之外,政治身份和自然生态题材乌托邦小说也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90年代后,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开始将乌托邦试验场拓展到星际空间,星际移民书写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说题材。20世纪末的星际冒险小说和少量反转历史的重现提醒我们,人类必须未雨绸缪:共同体的毁灭性事件可能再次来袭,人类不得不去寻找地球以外的栖息之所。进入新千年的头十年中,除了“9·11事件”引发乌托邦小说对公共安全的特别关注之外,乌托邦小说主题基本是对上个世纪的重复,如极权主义、战争、气候灾难、流行疾病、经济危机等,末世论调丝毫未改。到了第二个十年,乌托邦小说主要关注大型科技公司对社会的政治占领和管控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生问题,如食品安全和生存环境。
总之,在70多年的发展中,当代乌托邦文学显示出以下特点:第一,当代乌托邦文学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具有敏锐的时代性。第二,当代乌托邦文学沿着批判技术理性和拓展科技乌托邦梦想的双重轨道发展。第三,当代乌托邦文学在发展中了出现敌托邦转向和潮流。
三、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现在与未来
伴随着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变化和演进,西方乌托邦文学从古典时期的神学与政治结合走向人文主义与启蒙精神相遇的近代,历经基督教乌托邦由兴盛到枯萎的衰落过程之后拉开了现代乌托邦的序幕,最终在当代敌托邦的潮流中艰难地履行其被赋予的孕育更美好世界的职责。
然而就乌托邦本身而言,不管是如曼纽尔所论,它是为了炮制用来抵抗未来占卜术和空想家纷繁社会实验的解药的希望艺术,是任一时代都迫切呼唤的最高道德需求[1];还是如萨金特所言,是人类不愿坐以待毙而欲打破一切不满和束缚的欲望[15],其归根到底不过是莫尔最初命定的事实,即它是一个存在于梦想之中却无法抵达的“乌有之乡”(nowhere) 。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乌托邦文学的本质——它是对希望的言说和书写。以此为前提展望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未来,我们便有理由相信:西方乌托邦文学将继续秉承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直面现实,为激励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注 释]
①“utopia”一词由戴镏龄译为汉语“乌托邦”。详见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②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反乌托邦”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现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反乌托邦即反对乌托邦主义。如学者萨金特认为,反乌托邦是对乌托邦主义或某种优托邦的批评,它源自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的堕落,人类无法对生活进行改良和优化,因此不可能实现“优托邦”。其二,反乌托邦即反面乌托邦或恶托邦,未来社会并非走向社会改良,而是社会恶化。如克里尚·库玛提出,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存在对立性区别特征,即乌托邦提供正面的内容;反乌托邦则作出否定回应,倾向于将反乌托邦视为描绘一个与乌托邦的完美社会或者人间天国相反的社会图景。弗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提出,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代表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苏联乌托邦小说和奥威尔小说中有集中体现。国内学者王一平提供了辨识反乌托邦的五个层次的要素,但未对反乌托邦进行清晰的定义。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具合理性,反乌托邦应指对乌托邦主义或优托邦的批评和驳斥,否定的或反面的乌托邦(negative utopia)应称为敌托邦或恶托邦(dystopia), 它描述的幻想中的社会劣于现实社会。
③威尔斯在小说《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中提出“动态乌托邦”(kinetic utopia)概念,称现代乌托邦应区别于达尔文主义之前的“静态乌托邦”(static utopia), 即过去那种完美的、不存在任何社会不安和混乱的和谐幸福社会;现代乌托邦应该是动态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模式,而是一个承载着希望又能引导人类不断攀登更高阶梯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