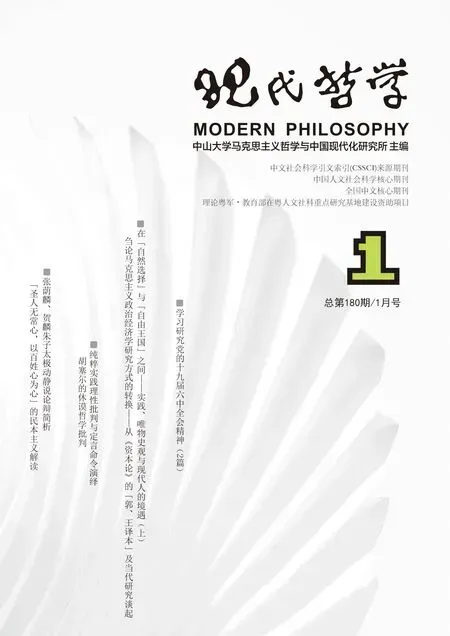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
李云飞
“现象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0页。译文据原著略有调整。,这是胡塞尔关于现象学与近代哲学传统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基于这种认识,胡塞尔对近代哲学传统的考察诉诸于一种“目的论-历史的”(teleologisch-historisch)批判性反思。他认为近代哲学发端于笛卡尔的原创立(Urstiftung),这种原创立包含两个对抗性要素,“笛卡尔既是近代的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观念的原创者,又是突破这种观念的先验动机(transzendentales Motiv)的原创者”(2)E.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rsg. von Walter Biemel,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4,S. 74;译文参见[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2页。(以下简称Hua VI,随标注德文版页码。)。这两个对抗性要素不仅构成笛卡尔哲学的内在张力,同时展开为近代哲学发展的内在张力。笛卡尔的“先验动机”贯穿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它从历史的深处规定着各种特殊的哲学形态,表现为不同哲学形态的隐蔽的统一性追求。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则表现为这种“先验动机”不断突破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束缚而趋向实现的过程,表现为一种从不同的哲学路线朝向现象学发展的隐蔽的目的论(Teleologie)。根据这种“目的论-历史的”观点,胡塞尔对近代哲学传统的考察聚焦于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近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的作用方式和阻滞性因素,旨在阐明通向一种真正的哲学开端的方法和形态。
休谟对哲学传统的怀疑论批判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姿态,他的哲学无疑是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实行其“目的论-历史的”批判,胡塞尔将休谟哲学织入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着力揭示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休谟哲学中的作用方式及其与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之间的根本冲突,旨在阐明一种真正的哲学开端的可能性。因此,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本质上是以休谟哲学为切入点对整个近代哲学传统的的系统反思。它不仅澄清了现象学的历史必然性,深化了现象学的自身理解;而且为我们如何对待哲学传统、如何实现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胡塞尔眼中的“休谟问题”
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一方面回溯笛卡尔的“先验动机”,考察其在休谟哲学中的作用方式和阻滞性因素,以揭示休谟的深层哲学意图;另一方面则前瞻休谟与康德的思想关联,考量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解释和回应的哲学效应。通过这种“回溯-前瞻”的关联性分析,胡塞尔试图将休谟哲学织入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以“目的论-历史的”视角把握休谟的真正的问题性和哲学趋向。因此,对传统的所谓“休谟问题”的解释就构成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的切入点。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源于对“休谟问题”的解释和回应。康德坦承,正是休谟惊醒了其独断论的迷梦,为他的哲学研究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3)[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释本),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休谟坚持经验主义(Empirismus)原则,反对“把理性的应用推进到一切可能经验的领域之外”的理性主义独断论(4)同上,第98页。。休谟对理性主义独断论的批判聚焦因果性问题,试图单纯依据经验探究因果判断的可能性。理性主义独断论将因果性归于实在世界本身,素朴地认定理性认识这种实在的因果性的不言而喻性。针对这种独断论的伪称,休谟提出质疑:理性“有什么权利设想某种东西能够具有这样的性状,即如果设定了这种东西,就必须必然地设定某种别的东西”?(5)同上,第3页。休谟的认识批判无可辩驳地证明,理性绝不可能先天地从概念上设想这种必然性的联结。与传统的解释不同,康德认为,休谟所关切的并非因果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而是因果概念的起源问题:“这个概念是否能被理性先天地思维,以及是否以这样的方式具有一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内在真理性?”(6)同上,第4页。在康德看来,“休谟问题”的实质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尽管他局限于因果判断这种特殊类型而没有在普遍的意义上提出这一问题。康德批评休谟的问题提法的局限性,因为“因果联结的概念远远不是知性用来先天地思维事物的联结的惟一概念;毋宁说,形而上学完全是由这样的概念构成的”(7)同上,第5页。。他主张将休谟的问题加以扩展和普遍化。由此,休谟的“孤立的”因果性问题获得一种普遍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纳赫(Adolf Reinach)指出,康德是把握了“休谟问题”的普遍意义的第一人(8)A. Reinach, “Kant’s Interpretation of Hume’s Problem”, trans. J. N. Mohanty, The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6, Vol. 7, No. 2, pp.161-188.。
关于因果联结的必然性问题,休谟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拒绝先天地构想因果联结概念,而诉诸经验的考察。在他看来,“因果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9)[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32页。,在经验中所感知的只是原因和结果这两种现象的恒常结合,而不是二者之间的必然性联结。因此,休谟认为,因果联结的必然性既没有“理性论证的”确定性,也没有“经验推论的”确定性。对他来说,所谓的“因果联结的必然性”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习惯性联想的虚构。这样,休谟就在哲学反思层次上根本否定了因果联结的必然性。在他那里,由于因果必然性联结构成一切关于“实际的事情”的认识的基础,因此,对因果必然性联结的否定就引申出对一切关于“实际的事情”的认识的否定。对康德来说,这意味着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否定,因此休谟成了怀疑论者,他“把自己的船弄到浅滩(怀疑论)上,让它躺在那里烂掉”(10)[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释本),第7页。。
康德宣称,“休谟问题”切中了认识批判的基本问题性,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使他认识到“在纯粹的理性真理和形而上学的客观性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可理解的鸿沟”(Hua VI, 96)。对他来说,理性的构成物如何恰好是关于客观现实的认识这一点现在成了问题。但是,康德完全不赞同休谟的怀疑论结论,尽管他像休谟一样拒绝理性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的运用。他批评休谟预先从经验领域中排除理性这一做法的盲目性,主张“我们的理性不要把可能经验的领域视为对它自身的限制”(11)[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释本),第98页。译文根据原著略有调整。。胡塞尔认为,康德对于“休谟问题”的反应是由其理性主义的立场决定的(Hua VI, 94)。在康德那里,“休谟问题”只是一个刺激性的出发点,他努力筹划一种既能克服理性主义独断论、又能避免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新方案。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使他试图在经验中探求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据;与之相对,康德在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要独立于经验来探求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据。作为对休谟的回应,康德将其先验哲学视为“休谟问题”的解决方案,因而是对休谟的怀疑论的克服。与康德的观点一致,黑格尔也认为,休谟的怀疑论只是跃向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跳板(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4页。。由此,确立了关于休谟哲学的传统解释。这种传统解释直到胡塞尔才得以突破。
胡塞尔对“休谟问题”的解释始终紧扣笛卡尔的“先验动机”。这种“先验动机”是“回溯到一切认识形成的最终源泉的动机……一种纯粹由这种最终源泉被奠基的、因此是被最终奠基的普遍哲学的动机。这种源泉就是我自身”(Hua VI, 100-101)。因此,它标明了一种回溯自我寻求普遍哲学之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这种彻底主义“乃是哲学成为可能的原始条件,它从一开始——并且永远——规定着哲学意图的根本意义”(Hua VI, 430)。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先验动机”将“关于纯粹主体性的基础科学的必然性的意识”(13)E. Husserl, Erste Philosophie(1923/24). Erster Teil: Kristische Ideengeschichte, hrsg. von Rudolf Boehm,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6, S. 185;译文参见[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册,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45页。(以下简称Hua VII,随文标注德文版页码。)引入到历史,尽管它在笛卡尔那里只是以一种萌芽的形态隐含地存在着,但却决定了近代哲学发展的先验趋向,即朝向一种先验的主体主义(Subjektivismus)。根据笛卡尔的“先验动机”,我思原本应当作为一切客观有效性奠基的最终源泉。然而,囿于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成见,笛卡尔将我思解释为心灵,一种与自然实体相对的思维实体。它缺乏内在性,只是一个单纯的“阿基米德点”。胡塞尔认为,笛卡尔“误解了他自己的良好的开端”(Hua VII, 73),错失了“一度已经到手的那种伟大发现”(Hua VI, 76),背离了自己的“先验动机”。因此,他没有将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贯彻到底,即回溯到一切客观有效性的最终源泉以寻求普遍哲学的绝然奠基,以至于他曲解了先验的问题性,而“没有把握住一种重新彻底被奠基的哲学的问题的最深刻意义……没有把握住一种植根于我思之中的先验的认识奠基和科学奠基的真正意义”(Hua VII, S. 64)。最终,他止步于先验哲学的门槛前,而未能踏上先验主体主义的道路。
洛克是“从笛卡尔的我思寻找通向有关我思的科学之道路的第一人”(Hua VII, 144)。他将我思看作一个绝对自身被给予性的领域,要求回溯到我思这一直观明见性的源泉以澄清认识的本质,由此开启了内在的直观主义(Intuitionismus)哲学路线。休谟继承了洛克的经验主义遗产,笛卡尔的我思在他那里不再是空乏的阿基米德点,而是由印象和观念构成的纯粹体验领域。作为直接被给予性的领域,它是一切认识的最终源泉。休谟将洛克的经验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将一切认识的推论都严格限制在直接被给予性的领域内。根据这种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世界一般、自然、同一性的物体的宇宙、同一性的人格的世界,因此还有认识它们的客观真理的客观科学,都变成了虚构”(Hua VI, 90)。这意味着一切客观认识的破产。因此,休谟的怀疑论开显出笛卡尔的基本考察中的隐含洞见,即“全部的世界认识,前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谜”(Hua VI, 9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休谟的怀疑论以悖谬性的方式显示出“一种判断世界的客观性及其整个的存在意义,以及相关联地判断客观科学的存在意义的全新方式”,它蕴含着一种本质洞见,即“意识生活是具有成就的生活,是成就着存在意义(正确地或错误地)的生活”(Hua VI, 92)。诚然,休谟的怀疑论以虚构主义(Fiktionalismus)告终;但虚构也是一种意义构造,虚构物也有其本己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有效性。对休谟来说,问题实际上在于:如果世界是一种在主体性中成就的有效性,那么世界及其认识的客观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这种将世界本身主观化的彻底的主体主义?胡塞尔认为,“这是最深刻和最终意义上的世界之谜(Welträtsel),即世界的存在是源于主观的成就的存在这个世界之谜”,而“休谟问题正是这个谜”(Hua VI, 100)。
主体性的成就如何能要求一种客观真实的有效性?胡塞尔认为,这本质上是近代哲学的普遍的认识论问题,它“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有其意义的根源”(Hua VI, 83)。然而,囿于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成见,笛卡尔实际上将自我与世界之间认识上的奠基关系看作两种实体之间的实在论关系,从而曲解了先验的问题性。他没有认识到,“整个世界本身可能是从多样性地流动着的思维活动之普遍综合中产生的思维对象”(Hua VI, 93)。因此,原本先验的问题性最终蜕变成“内在性的思维实体如何能切中外部的物质实体”的问题。根据胡塞尔对“休谟问题”的解释,正是“休谟激活了笛卡尔的基本问题并加以彻底化”,从而“深刻地动摇了‘独断论的’客观主义”(Hua VI, 93)。而康德对笛卡尔的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是陌生的,他从未受到笛卡尔的直接推动,从未注意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论步骤中所蕴含的先验的问题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康德从未深入到笛卡尔的基本考察的精奥之处,他也从未被他自己的问题性所推动,到笛卡尔的基本考察的精奥之处寻求最终根据和裁定”(Hua VI, 102);而休谟“试图具体地、系统地-普遍地阐明在笛卡尔《沉思录》中首次作为纯粹直观地被把握和有条理地被阐明的最终基础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在他那里“显露出一种隐蔽的意图,即补回笛卡尔所错失的东西,由此获得对笛卡尔的原初意图本身的理解”(Hua VI, 437-438)。
如果说笛卡尔只是在萌芽形态的意义上提出了近代哲学的普遍的认识论问题,那么休谟则立足内在直观主义立场,以怀疑论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笛卡尔原本的先验问题性,即客观认识的绝然奠基的问题。就此而言,尽管康德也要求绝然的认识奠基,笛卡尔的问题是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他的认识批判中;但是,在康德那里,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已失去了力量。对他来说,绝然性(Apodiktizität)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康德没有深刻感受到笛卡尔对哲学开端的无前提性要求,他没有回溯到主体性的自身被给予性这一最终源泉。他的主体性不是真正的主体性,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先验权能。因此,他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开端,未能从最终源泉出发提出真正的普遍的认识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康德没有勘破休谟怀疑论的真正洞见,没有看到“隐藏在休谟怀疑论的悖谬性中的动摇客观主义的真正哲学动机”,因此“康德所理解的休谟并不是真正的休谟”(Hua VI, 91, 99)。
二、胡塞尔对休谟哲学的现象学阐释
胡塞尔将“休谟问题”解释为“世界之谜”。在他看来,康德之所以未能把握真正的“休谟问题”,原因在于康德是被《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而不是被《人性论》的休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的(Hua VII, 198),《人类理解研究》的认识批判局限于因果必然性联结问题,缺乏系统性和彻底性,只有《人性论》的系统的认识批判才显露出休谟的深层哲学意图。
休谟的认识批判最初是沿着洛克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前进。洛克缺乏笛卡尔的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他没有“从对一切科学和经验世界本身加以怀疑开始,而是完全素朴地假定诸种新的客观科学的有效性,他更将被经验的世界的在此存在看成是不言而喻的”(Hua VII, 79)。与此相应,他将笛卡尔的“我思”“以客观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方式素朴地理解为人的心灵”(14)E.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rgänzungsband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34-1937, hrsg. von Reinhold N. Smid,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S.111.(以下简称Hua XXIX。)译文参照了郑辟瑞先生尚未刊印的中译稿,特此致谢。。对他来说,心灵是“第二自然”,“就像物质自然是一个由实在的物体构成的时-空的宇宙一样,心灵也是一个由实在的心理材料构成的宇宙”,因此“感觉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心理学构成认识论的基础”(Hua XXIX, 111-112)。休谟遵循洛克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线,试图将他的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Sensualismus)彻底化。在贝克莱的物质实体批判的基础上,休谟进一步批判心灵实体,在他那里,“心灵甚至不能与白板相比”,因为“心灵不是一个各种体验存在其中的物”(Hua VII, 158),而是一个由直接被给予的感觉材料构成的绝对自身封闭的自然,在其中,“除了堆积的印象和观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间接地被证明是真正存在着的,而在其中冒充实在的自然和世界一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可从心理学上得到说明的虚构”(Hua XXIX, 112)。这样,休谟就将感觉主义扩展到一切经验领域,将全部存在都还原为单纯事实性的感觉材料。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原子论解释相似,休谟的彻底的感觉主义将心灵消解为意识原子。作为最终的事实性元素,这些意识原子就是各种印象和观念。与自然的规则相应,在心灵中规整意识原子的是源于习惯和联想的各种心理规则,它们按照共存和相继对各种心理体验进行纯粹事实性的规整。但是,对休谟来说,心理规则与自然规则的相应性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毋宁说,“心理规则是一切存在的真正的根本规则,一切存在连同一切所属的和臆想中独立的规则性都按照这些内在的心理规则被还原为感知和感知的构成物”(Hua VII, 159)。
鉴于其认识批判的无前提性原则,休谟没有停留在对心理规则的素朴设定上,而是从直接被给予的心理材料出发,完全依据经验(empirisch)确立这些基本的心理规则。在他那里,一切存在和认识都必须由这种“无前提的心理学”来说明,根据这种彻底的心理学解释,“整个世界连同一切客观性都无非是一个由假象构成物、由虚构构成的系统,这些假象构成物和虚构必然在主体性中按照内在的心理学规则产生;而科学则是主体性的自身错觉,或是一种为有利于生活目的而进行虚构的艺术”(Hua VII, 159)。显然,休谟的“无前提的心理学”已与客观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严格区分开来。基于这种“无前提的心理学”,休谟克服了洛克对内在经验的认识论与客观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的混淆,将其向前推进到一种真正的基础科学。胡塞尔认为,休谟在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意义首先在于,“他看到在贝克莱的理论和批判中显露出一种新型的心理学,而且在其中确认出一切可能的科学总体的基础科学”,并且试图“系统地阐明这种科学”(Hua VII, 15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指出,“休谟创立了一种本质上新型的彻底的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这种心理主义将一切科学奠基于心理学之上,而且是奠基于纯粹内在的、同时是纯粹感觉主义的心理学之上”(Hua VII, 155)。但是,休谟的新型的心理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他将这种纯粹内在的感觉主义心理学确立为基础科学,试图藉此实现最终奠基的认识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却必然导致虚构主义的怀疑论。二者之间究竟如何调解呢?
休谟在《人性论》开篇就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15)[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 译,郑之骧 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7页。。据此,他认为认识批判的唯一途径就是回溯人性本身,因为“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阐明人性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16)同上,第7-8页。。因此,休谟的认识批判的目标就在于确立作为基础科学的人性科学。但是,《人性论》为此目标所诉诸的认识批判却导致了怀疑论的结果:诸如因果性、物质实体、自我的同一性等一切客观性范畴都是虚构。对他来说,这种悖谬性似乎成了一切哲学反思的宿命。休谟公开承认这一怀疑论结论的悖谬性:一方面,哲学的反思揭示了自然态度的素朴性和客观认识的成问题性;另一方面,当它试图在哲学上确立真正的客观性时,它发现“它并不能借明白有力的一串论证,或任何貌似的论证,来辩正这个新的哲学体系,这种企图是超过人类全部才干的力量的”,因此,它“看到它自己陷于极端迷惑的境地中”(17)[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135页。。休谟认为,“这种怀疑论的惶惑,是一种疾患,这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因为它“既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于对那些题目所作的深刻而透彻的反省,所以我们越是加深反省(不论是反对着或符合了这种惶惑),这种惶惑总是越要加剧”(18)[英]休谟:《人性论》,第246页。。根据传统的解释,休谟哲学就是以这种悖谬性的怀疑论告终。
休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吗?对此,休谟本人曾说:“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是否真心同意我所不惮其烦地以之教人的这个论证,我是否是那些怀疑主义者之一……那么我就会答复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而且不论我或任何人都不曾真心地并恒常地抱着这个意见。”(19)[英]休谟:《人性论》,第209页。显然,休谟并非“真心地”要否定一切存在和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他相信“自然借着一种绝对而不可控制的必然性,不但决定我们要呼吸和感觉,而且也决定我们要进行判断”(20)同上,第209页。。这意味着,我们关于存在和认识的客观性的素朴信念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怀疑论的结果对休谟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甘于怀疑论的结果,就会陷于认识上无所依归的绝望;而遵循“自然的倾向”又违背理性的良知。因此,认识批判带给休谟的似乎只能是“惶惑”,以至于在哲学反思与自然信念之间无所适从。然而,正是这种“无所适从”的思想状态透露了休谟的深层哲学意图。诚如胡塞尔所言,当休谟“宣称科学是未被论证的或者不可论证的时”,其实是“将一切认识和科学都搁置起来”,“让一切认识和科学成为问题”(21)[德]胡塞尔:《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郑辟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24页。。事实上,休谟的“绝望”只是就传统的哲学反思而言,他既反对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也拒绝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因此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怀疑主义者,不但怀疑他的哲学的信念,也怀疑他的哲学的怀疑”(22)[英]休谟:《人性论》,第304页。。在《人性论》第一卷结尾,休谟袒露了他的真实意图:“我的惟一希望只是:在某些点上使哲学家们的思辨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23)同上,第304页。无疑,休谟在此仍属意于人性研究,只是不再寄望于传统的哲学反思,而是想要开启新的哲学维度。
这个新维度指向胡塞尔所谓的“世界之谜”问题。在《人性论》中,休谟对“感官方面的怀疑论”提出批评:“我们很可以问,什么原因促使我们相信物体的存在?但是如果问,毕竟有无物体?那却是徒然的。那是我们在自己一切推理中所必须假设的一点。”(24)同上,第214页。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外物实存的信念是无可否认的,作为自然的信念,它构成一切哲学反思的前提。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立场一致,休谟并不怀疑世界的实存,也不否认世界实存信念的正当性,而是想探究这种自然信念的起源。显然,这指向胡塞尔所谓的“世界之谜”问题:“如何能够使世界确然性的素朴的不言而喻性……成为可以理解的呢?”(Hua VI, 99)毋庸置疑,这种提问方式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姿态。对休谟来说,问题根本不是要从哲学上证明世界的实存,而是要阐明世界实存信念的“素朴的不言而喻性”;相应地,问题不是要证明超越性认识的客观有效性,而在于澄清认识的超越性的起源。休谟的虚构主义以悖谬性的方式表明,意识生活是构造性的生活,自然的信念源于心灵的构造。因此,如果想要阐明世界实存信念的“素朴的不言而喻性”和澄清认识的超越性的起源,就必须回溯到心灵中的印象和观念这一原初经验的基础,纯粹按照心灵的自然本性揭示它的隐蔽的活动。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休谟将他的感觉主义心理学确立为基础科学的真实意旨。
休谟的怀疑论洞见揭示了世界实存的不可理解性。胡塞尔认为,这种揭示实际上是对世界实存信念的悬搁和论题化,因此“休谟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现象学的问题提法,而正是这种全新的问题提法使他超越了整个近代哲学传统。与笛卡尔一样,休谟也信奉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但是,二者的问题指向迥然有别,前者试图证明一切存在和认识的客观有效性,而后者旨在澄清自然信念和客观认识的起源。对休谟来说,“实行认识批判意味着考察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观念’,即探究它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原初的印象相符”(Hua VII, 160)。显然,休谟遵循洛克的内在直观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将一切认识都回溯到其在意识中、在内在经验中的直观性起源,从这些起源澄清它们”(Hua VII, 144)。但是,与洛克对心灵的白板式解释不同,休谟对人格同一性的批判,将心灵纯粹作为“印象”和“观念”的领域设为前提。因此,在休谟那里,内在经验不再是世间统觉性的心理学经验,而是直接的经验被给予性,即纯粹的感觉材料。休谟将其确立为一切认识的最终基础,他的认识澄清首先致力于这种纯粹的感觉材料的证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休谟的方案称为“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Hua VI, 64)或“材料实证主义”(Datenpositivismus)(Hua VI, 98)。这种证实的结果表明,一切存在和认识都只不过是虚构;但是,休谟没有停留于虚构主义的结论。在他看来,心灵中的自然信念和认识观念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它们既不能诉诸于经验的证实,也不能诉诸于理性的证明。作为虚构,它们源于心灵的自然倾向的构造,因此虚构也是意义构成物,具有自身的存在类型。鉴于虚构本身的“不可理解性”,为了获得彻底的认识澄清,休谟立足于纯粹的感觉材料领域,试图通过考察心灵的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在观念间联结中的活动方式给予虚构的起源以一种心理学的说明。因此,胡塞尔认为,“休谟是第一位认真对待笛卡尔的纯粹内在态度的人”(Hua XVII, 263)。事实上,在《人性论》中已可看到“一种对纯粹的体验领域(Erlebnissphäre)进行系统探究的最初尝试”(25)E. Husserl,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 hrsg. von Walter Blemel, 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968. S. 328.。通过对纯粹的体验领域的具体分析,休谟试图纯粹基于直接明见的经验被给予性,澄清“超越的客观性是如何在纯粹主体性、在纯粹意识的范围内被构造起来的”(Hua VII, 348)。在他那里,作为直接的经验被给予性,纯粹的体验不仅构成超越的客观性的基础,而且构成世间统觉性的心理学经验的基础。心理学经验只是想像力遵循心灵的自然倾向对纯粹的体验进行操作的产物,因此,纯粹的体验对于心理学经验是构造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休谟已试图站在现象学的地基上构想了“先验构造”(transzendentale Konstitution)的问题性(Hua XVII, 263)。
在康德眼中,“休谟问题”本质上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只不过是以怀疑论的否定形式提出的,他的批判哲学正是要为“休谟问题”提供一种先验的解决方案。而在胡塞尔看来,休谟已开显出“先验构造”的问题性,因此“休谟问题”不只是一个应由先验哲学解决的问题,而本身就是一个先验哲学的问题。胡塞尔认为,休谟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位把握了先验哲学的普遍的具体问题的人”,他通过对纯粹的体验领域的具体分析,已经认识到“一切客观之物都是由于一种主观的发生(Genesis)而被意识到”,因此必须“将一切客观之物都作为这种主观的发生的构成物进行研究,以便从这些最终的起源出发使一切对我们而言的存在者的合法的存在意义成为可理解的”(Hua XVII, 263)。诚然,休谟将“主观的发生”归因于心灵的想像力的作用,他关于“先验构造”的问题性的研究则呈现一种心理学的形态;但是,休谟的心理学“只想利用直接明见的意识成分,而且就在这个领域内……探求据以获得心理学说明的心理学规则”(Hua VII, 157)。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作为证明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无非是虚构的科学,它不可能是以人的经验现实性为前提的心理学,胡塞尔称之为“先验的心理学”(Hua VII, 173)。尽管休谟的认识澄清采取感觉主义的心理学说明的方案,而且以怀疑论的虚构主义面目呈现,但“这种休谟式的心理学实际上是对于纯粹的意识被给予性的科学的第一次系统的尝试”(Hua VII,156-157)。胡塞尔强调,如果将《人性论》的心理学说明方案斥之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那就误解了休谟的真实意图,因为休谟“已经超出了在自然-实在的意义上的心理学领域”(26)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Marly Biemel,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1,S. 154.,他的虚构主义正是要以怀疑论的方式消解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us)。诚然,休谟的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心理主义”(27)[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或“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Hua XVII, 264);但“他的心理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已经完全活动在‘先验的’地基上,活动在先验的内在(Immanenz)的地基上”(Hua XXIX, 114)。因此,胡塞尔认为,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学“是关于具体的构造的问题性的第一个系统的和普遍的构想”(Hua VII, 157)。
休谟的《人性论》的原初意图是创立一种基础科学,即关于人性的科学。传统的解释往往聚焦其怀疑论的结果,而忽视其原初意图。对此,休谟曾抱怨说:“人性研究是关于人的惟一科学,可是一向却最被人忽视。”(28)[英]休谟:《人性论》,第304页。事实上,即使最后身处怀疑论的悖谬性绝境,休谟也绝未放弃创立一种基础科学的目标,试图开辟哲学的新道路。因此,尽管他的怀疑论呈现一种否定传统的哲学姿态,但他不可能停留于单纯的否定上。毋宁说,对哲学传统的批判在他那里只是一个步骤或手段,他想要藉此揭示哲学的新维度。因此,在《人性论》中实际上存在双重的问题性和哲学维度。
传统的解释通常将《人性论》视为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系统表达,就休谟的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必然导致怀疑论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只是《人性论》表层的问题性,在这个层面上,休谟的认识批判同时构成对哲学传统的否定。但是,对哲学传统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否定哲学本身。当休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怀疑论结果时,他同时也怀疑“哲学的怀疑”本身。他不甘于否定性的怀疑论结论,试图将哲学“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这种“转向”意味着超越哲学传统,开启新的哲学维度。因此,从休谟的怀疑论的悖谬性中,胡塞尔看到一种全新的哲学姿态,它借一种新的问题提法展现出来。这种新的问题提法意味着对传统的哲学问题的悬搁。对休谟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证明存在和认识的客观有效性,而在于如何澄清我们的自然信念和认识观念的起源。与这种问题提法的转变相应,休谟的认识批判转变为对认识起源的澄清。诚然,他的认识澄清方案是一种基于习惯性联想的心理学说明;但是,他将自己的工作严格限制在纯粹的感觉材料领域,试图立足于直接明见的经验被给予性构造性地澄清一切心理学经验和心理学规则。因此,休谟的认识澄清开显了先验的经验维度,他所诉诸的感觉主义的心理学说明本质上是一个先验哲学的方案。如果我们从这种先验的观点回头再看休谟的认识批判,那么他的怀疑论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悬搁。借助这种彻底的悬搁,休谟的哲学转向实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转向,它开显出一个先验的哲学维度,即作为认识之构造性起源的直接的经验被给予性领域。因此,《人性论》在表层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问题性之外,还蕴含着先验构造的问题性,前者属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的维度,后者属于先验哲学的维度。当然,《人性论》的双重的问题性和哲学维度是统一由经验主义怀疑论表达出来的。对此,胡塞尔指出,休谟在《人性论》中“已经构想了先验的问题性的完整体系,而且以先验的精神全面思考了这个体系——尽管是以一种因彻底的悖谬而取消了的感觉主义的怀疑论的否定主义形式思考的”(Hua VII, 241)。也就是说,《人性论》的先验构造的问题性和哲学维度“隐含”在经验主义怀疑论的形式下,只有当经验主义怀疑论因彻底化而达到自我否定的悖谬性时才显示出来。在胡塞尔看来,休谟的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既是对经验主义怀疑论的终结,“同时又是迈向先验的基础科学的决定性的准备步骤”(Hua VII, 157)。的确,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学,作为一种对认识的起源进行构造性澄清的方案,实际上充当了先验的基础科学。因此,胡塞尔认为,“休谟的《人性论》是有关纯粹现象学的第一个构想”(Hua VII, 157),是“一种真正的‘先验的’现象学,尽管是一种被感觉主义颠倒了的现象学”(29)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Marly Biemel, 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1,S. 155.。对他来说,《人性论》开创了先验哲学的传统,将近代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宣称“休谟的《人性论》……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Hua VI, 91)。
毋庸讳言,在现象学的光照下,《人性论》展露出先验哲学的面孔,呈现了一个与传统的解释完全不同的休谟形象。当然,胡塞尔并不否认休谟的经验主义出发点,也不否认其哲学的怀疑论特征;但是,他的现象学阐释聚焦休谟的深层哲学意图。从这一聚焦点看,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只是其先验哲学的实现步骤,它最终以一种否定主义的悖谬性方式扬弃自身。基于其现象学的阐释,胡塞尔确信,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先验哲学的形态。作为“一切可能的科学总体的基础科学”,它趋向作为先验的基础科学的现象学。与此相应,休谟的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主义,而是一种内在的直观主义。这种内在的直观主义不是洛克式的经验主义的直观主义,作为“第一个具体的和纯粹内在的认识论”(Hua VII, 157),它是一种纯感觉主义的主体主义;作为一种纯粹内在的哲学,“它是唯一真正的直观主义哲学——即现象学——的预备形式”(Hua VII, 182)。
三、胡塞尔对休谟的怀疑论的批判
根据胡塞尔的“目的论-历史的”观点,“哲学本身的意义和由这种意义所要求的方法的意义推动我们走向一种直观主义”,而“休谟的怀疑论的深远意义就在于……一种直观主义的和纯粹内在的哲学”(Hua VII, 147, 181-182)。因此,休谟的直观主义的哲学路线“整个看来并不表示它是一条歧路”,相反,“它是哲学发展为了达到方法上的完成形态绝对必须采取的唯一未来的道路”(Hua VI, 195)。在胡塞尔眼中,休谟由正确意图支配,“尽管眼睛有一半被蒙住,他仍是漫步在正确道路上”(Hua VII, 352);但尽管已踏上直观主义哲学的正确道路,休谟却无法摆脱怀疑论的惶惑,因而未能实现创立先验的基础科学的原初意图。那么,休谟为什么未能克服怀疑论的幽灵呢?
从休谟的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的立场看,休谟绝不缺乏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他受笛卡尔的“先验动机”的推动,试图以一种无前提性的彻底主义实现认识的最终奠基,但“他的彻底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彻底主义”(Hua VII, 160)。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的本质在于,它不是以素朴的方式开始,而是以对一种彻底的开端的沉思而开始的。而休谟完全缺乏这种笛卡尔式的奠基性沉思。胡塞尔并不否认“休谟从印象和观念开始的这个出发点毕竟是完全正确的”,这在现象学上正意味着从直观的明见性出发;但“他并没有明确讨论这样开始的正当性”,没有考究“普遍的和绝对的认识之正当性证明的方法”(Hua VII, 352, 160)。诚然,休谟的认识批判采取了“将一切观念还原到印象的方法论形式”,对他来说,“印象是能在意识上进行明见性证实(Evidenzbewährung)的直观的认识论标题”(Hua VII, 160, 165);但是,这种对直观的明见性证实的方法论诉求与其对印象的感觉主义解释相抵牾。在休谟那里,印象作为纯粹的感觉材料,是一种心理事实。对此,胡塞尔严厉指出,“单纯的事实以其事实性的特性而是其所是,它们作为事实而存在,但它们并不意味任何东西,它们不意指任何东西,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不具有任何意指与被意指物的区分”;因此,单纯的事实“不证实任何东西,而且在自己本身中没有任何进行证实的东西”,而“只有对事实的自身直观……才能进行证实”,因为证实意味着对事实的单纯意指与对同一事实的自身把握相合(Hua VII, 163, 165)。在他看来,休谟没有认识到,作为一种明见性证实的意识,印象应当“具有一种双重性,即正是作为有关自身被给予它的东西的自身给予性的意识”,(Hua VII, 165-166),而单纯事实性的印象根本无法满足明见性证实的方法论要求。因此,胡塞尔认为,休谟“缺乏关于最终奠基的方法的彻底沉思”(Hua VII, 160),以至于直观主义的澄清要求被曲解为向事实性的印象的还原。
同样,休谟也缺乏对经验主义原则的彻底沉思。这一原则的意义由洛克关于认识澄清的直观主义获得规定,在《人性论》中,休谟只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素朴地继承了这一规定,用作创立一种基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没有看到,这种经验主义原则本身无法还原为事实性的印象,根本不可能在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而按此原则对一切认识所提出的奠基要求,也对这种原则本身有效。也就是说,这种原则本身同样需要一种最终奠基。因此,胡塞尔批评休谟缺乏对其“构想的基础科学的意义所要求的方法的彻底沉思,而且首先是对这种基础科学本身的意义的彻底沉思”(Hua VII, 167)。诚然,休谟为创立一种基础科学的动机所支配,试图回溯到认识澄清的最终源泉。他的人格的同一性问题是对自我概念的彻底批判,由此他重新构想了笛卡尔的我思,将其把握为一个纯粹体验的领域,开显出认识澄清的先验地基。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休谟没有将其“先验动机”贯彻到底,他的认识澄清并不单纯基于纯粹的意识体验,而且诉诸一种从属于纯粹的意识体验的心理权能——想像力。这意味着,休谟的认识澄清“虽然不用自然的世界观来进行操作,但却同样是在用超越来进行操作,即用超越的权能或法则”(30)[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第145页。;因此,休谟像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一样,陷入一种“先天思辨虚构”(3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76页。。
根据胡塞尔的批判分析,休谟的开端沉思的不彻底性根源于他的自然主义立场。诚然,他以怀疑论的虚构主义消解了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但是,他的感觉主义批判实际上只是对洛克式的自然主义的彻底化。因此,当休谟站在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立场上试图开启先验的哲学维度时,他已预先从洛克那里继承了自然主义的遗产。正是这种自然主义的成见,从根本上规定了他的整个哲学的性质和趋向。在休谟那里,自然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回到实事本身”的严格科学的哲学动机,即通过直接经验的明见性证实清除一切客观主义的成见,以确立认识澄清的最终基础。为此,他在贝克莱的基础上对洛克的内在直观主义进行彻底纯化,将心灵的内在经验还原为印象和观念。于是,自然和心灵都成了虚构,通常意义上的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根源消除了。问题是,休谟仍然按照自然事物的样式理解纯粹意识,这必然导致意识自然主义(Bewuβtseinsnaturalismus),其特征在于“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32)同上,第9-10页。。
在休谟那里,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原子论解释相似,整个心灵被消解为意识原子,消解为处于共存和相继中的感觉材料。作为感觉材料的复合,心灵的存在“被看作意识的准-空间中的自然似的事件过程”(33)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Marly Biemel, 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971,S.156.。由于这种素朴的自然化,意识领域被看作实在的感觉材料的领域,而实在的感觉材料作为一种事实,由事实性的特征标识,于是,意识本身固有的特性被忽略了。在胡塞尔看来,尽管诉诸直接的经验被给予性,但休谟“却从未真正实行这种纯粹经验,从未看到它的真实成分,从未在它的范围内进行真正的分析”(Hua VII, 90)。他的意识分析实质上是一种事实性的描述。休谟没有看到,使印象成为印象、使观念成为观念的东西并非意识的事实性要素,而是意识本身固有的特性——意向性,因此,他总是以事实性描述替代对意识的意向性分析。这种“替代”本身就是悖谬的,因为事实性描述只有借助意向的分析才是可能的,而且事实性的感觉材料是在直接经验的明见性中被给予的。鉴于这种对意识的事实性解释,“印象与观念的区别被看成单纯的事实区别”(Hua VII, 162)。因此,在休谟关于印象和观念的谈论中,以及在他为一切观念指明相应的印象的要求中,一切都被粗暴地敉平了。他没有看到,印象与观念属于本质不同的意识类型,而且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层次结构,“如果这些意识类型被偷换成只是具有其事实性特征的心理事实,那么在印象与观念之间的这整个区别,以及将观念回溯到印象的要求,就变得完全无意义了”(Hua VII, 162)。胡塞尔认为,休谟以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形态呈现的内在直观主义,“只是一种假的直观主义,或只是一种假的经验主义……所谓它向经验的回溯,向自身把握的直观的回溯,并且以事实和事态本身考量任何被陈述物,只不过是一种假象”(Hua VII, 136)。
休谟的意识自然主义表明,他所诉诸的直接经验的被给予性只是事实性的心理原子。因此,休谟的自然主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而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或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胡塞尔认为,“由于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只看到在无本质的虚空中漂浮的一堆材料,而看不见意向的综合的客观化功能”(Hua XVII, 264),因此,“它使我们难以看到‘本质’‘观念’;或者,由于我们可以说是始终看到这些‘本质’‘观念’,因而不如说:它使我们难以承认这些‘本质’‘观念’的本己特性,而是相反地对它们进行背谬的自然化”(34)[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第34-35页。。在胡塞尔看来,休谟的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只知道关于个体之物的经验,将直观简单地等同于感性直观,“完全看不到普遍直观”,“试图通过以特殊的个别物的自然关联掉包的方式变戏法般地消除一切普遍思想”;休谟没有看到“普遍之物、概念的普遍性和事态的普遍性可以直接明见地被看到”(Hua VII,172, 171)。因此,“观念”“本质”等普遍之物被消解为感觉材料的复合,导致“观念”“本质”的自然化。最终,休谟陷入虚构主义的怀疑论。
当然,休谟本人并未作出彻底的怀疑论结论,因为对他来说,关于“观念间关系”(Relations of Ideas)的认识具有先天的真理性。像理性主义一样,休谟也主张“一切科学的正当性证明的根源在于先天(Apriori)”,“先天性(Apriorität)是科学的特征”,先天“不是天生性,不是作为事实上属于人的精神之原初备有的东西”(Hua VII, 351),而是一种内在的先天。这种内在的先天就在于,“我们通过考察、分析和比较我们的观念……而发现的某些与它们的普遍本质不可分割的关系,某些奠基于它们的本质之中的事态”(Hua VII, 351)。对胡塞尔来说,“休谟将先天等同于‘单纯存在于观念中’,这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是“‘单纯存在于观念中’被理解为普遍的明见性”(Hua VII, 353)。只有如此理解的观念,才是作为普遍之物的先天。问题是,休谟并没有将“单纯存在于观念中”理解为普遍的明见性,“他没有看到,当观念按他的意思被理解时……我们所有的就是单个的个别物,而且他没有看到,当关系必然属于这种个别物时,这些关系首先也只是事实性的关系,是单个材料上的单个事件”(Hua VII, 359)。囿于其感觉主义的成见,休谟不可能将感觉材料意义上的观念看作是普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的单纯例示,不可能从感觉材料意义上的观念转向普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尽管休谟以“观念间关系”的形式承认了纯粹体验领域的先天,即“现象学的先天”(Hua VII, 390),但“他在体验中所看到的是无心灵的感觉材料……他将先天阐述为事实,即不变地从属于他的意义上的、而非本质意义上的‘观念’的关系材料的事实”(35)[德]胡塞尔:《文章与演讲(1911-1921)》,第123页。。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对先天的感觉主义曲解以及“对本质与——作为‘印象’之对立面的——‘观念’的实证主义混淆”,使休谟错失了真正的先天(36)同上,第37页。,以至于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怀疑论。
如果说意识的自然化使休谟看不到真正的经验,那么观念的自然化则使他看不到普遍本质。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阐释,休谟的认识澄清旨在创立一种内在直观主义的先验的基础科学。但是,如果普遍本质没有被绝然地确立起来,那么这种认识澄清的目标就会沦为一种空想。对休谟来说,似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在于,使内在的经验事实达到经验的概念,然后以归纳的方法确立经验的规则”(Hua VII, 170)。但他很清楚,归纳性的规则不可能被绝然奠基,因为归纳性的推论只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只是心灵的习惯性的自然倾向。因此,归纳性的规则只具有主观的必然性,而没有客观的有效性。正是由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休谟成了怀疑论者,他不甘于自己的虚构主义结论,却又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事实上,由于诉诸经验归纳的方法,休谟作为基础科学来建构的感觉主义心理学与其所要奠基的自然信念和认识观念具有同样的素朴性。正如胡塞尔所批评的,休谟缺乏对基础科学本身的意义及其所要求的方法的彻底沉思,而看不到他的基础科学的要求与其经验归纳的方法之间存在的根本冲突,因此,他的“这种心理学的基础科学完全悬在空中”,以至于“从这种原始基础实行最终的认识奠基的整个计划失去了任何意义”(Hua VII, 171)。
根据胡塞尔的批判性考察,休谟的根本错误在于他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而究其根源则在于,他的认识批判背负着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成见。一方面,囿于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成见,休谟按照自然事物的样式理解纯粹意识,不仅将意识自然化,而且将观念自然化,以至于他为一种虚假的直观主义所引导,径直回溯到纯粹感觉材料,以之作为认识澄清的最终基础。这种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使休谟“关于心理之物本身所确立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看到的东西,不是从意识生活本身的固有的本质中获得的东西”(Hua VII, 126),因此他的意识分析不是真正的意识分析。另一方面,囿于经验主义成见,休谟预设了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这首先表现在他划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领域,即“观念间关系”和“实际的事情”,将事实与先天绝对对立起来。因此,尽管他确认观念间关系的先天真理性,但他看不到将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经验规则理解为同样具有先天真理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先天真理存在于事实领域之外,它与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经验规则毫不相干,因此,不存在将经验规则回溯到先天真理以寻求绝对的正当性证明的可能性。这种二元对立还表现在,休谟预先从内在经验领域排除了理性,而“将纯粹意识仅仅看作不合理性的场所”(Hua VII, 171)。他看不到意识的综合功能和客观化成就,否认普遍本质的经验被给予性。尽管休谟已认识到意识生活是有所成就的生活,但他所谓的意识成就只是想像力的习惯性联想的产物,本质上只是一种心灵的虚构。因此,囿于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成见,休谟没有遵循意识本身固有的特性回溯到认识澄清的最终基础,他作为最终基础所确立的纯粹体验实际上只是事实性的感觉材料,而不是真正的原初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只是一种假的经验主义,一种假的直观主义。在他看来,“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是无法医治的”(Hua VII, 126),它不仅使真正的认识论不可能,而且使真正的心理学不可能。因此,休谟哲学只能以怀疑论告终,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悖谬性境地。
四、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的意义
尽管具有自我否定的悖谬性,休谟的怀疑论仍以其对哲学传统的批判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趋向。休谟既没有像理性主义那样使经验服从理性,也没有像经验主义那样使理性服从经验,而是试图通过回溯心灵的本性和活动,展显经验与理性的统一根源。因此,他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既不能被归于传统的理性主义,也不能被归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尽管他背负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成见。事实上,在《人性论》的怀疑论表达中始终隐含着休谟的深层意图:以感觉主义的怀疑论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基于纯粹体验这一原始基础揭示人性的原理,创立一种先验的基础科学。这种深层意图是他的怀疑论悖谬性背后所涌动的“先验动机”。这种动机激发了哲学变革意识,使休谟试图将哲学“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但是,休谟被自己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蒙住了眼睛,他看不到意识的意向性,看不到其中可能开显的新的哲学维度。诚如胡塞尔所言,尽管休谟已展现出超越传统的新的哲学趋向,但他看不出这种对传统的批判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种对传统的超越究竟该指向何方。因此,历史面临新的选择,休谟本人已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根据胡塞尔的“目的论-历史的”观点,笛卡尔的“先验动机”是贯穿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动机,它藏在哲学家们的意向深处,隐蔽地规定着各种特殊的哲学形态。只有揭示这种隐蔽的“先验动机”,才能捕获哲学家们“在意向深处的隐蔽统一性中最终所要‘追求’的东西”,从而开显出“指向新维度的全新的目光转向的可能性”(Hua VI, 74, 16)。但是,只有当哲学发展出现了转折,即“哲学的可能性和真正的意义形态变得成问题”时(Hua XXIX, 417-418),这种“先验动机”才会清晰地显露出来。为了揭示这种“先验动机”,胡塞尔聚焦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哲学家的思想。就此而言,休谟哲学无疑构成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的一个聚焦点。
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首先聚焦休谟哲学的内在张力。在他看来,这种内在张力源于休谟的深层哲学意图与其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之间的根本冲突。聚焦这种内在张力能够清楚地呈现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休谟哲学中的作用方式和阻滞性因素。其次,胡塞尔采取“目的论-历史的”视角,着眼于休谟在近代哲学发展中统一的思想关联。一方面,他将休谟哲学看作对笛卡尔的“先验动机”的具体贯彻,通过回溯笛卡尔的原创立,考察这种具体贯彻的状况,阐明休谟哲学的先验洞见和盲点。另一方面,他将康德哲学看作回应休谟的怀疑论的方案,借助休谟与康德的思想关联,尤其是二者问题性的对照,凸显休谟的怀疑论悖谬性背后所蕴涵的哲学革命意识及其所预示的全新哲学趋向。通过这种“回溯-前瞻”的关联性分析,胡塞尔将休谟哲学织入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使对休谟哲学的批判构成其近代哲学传统批判的关键性环节。最后,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不是单纯历史性的思想考察,而是试图突破休谟哲学表层的特殊思想外壳,纯粹就其所代表的直观主义哲学路线进行一种类型化的批判分析。就像他在考察洛克哲学时所说的,“我们总是在一定距离上进行批判,以使批判变成对洛克所奠立的这种新型哲学的整体批判”(Hua VII, 141)。因此,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实际上构成对整个自然主义的直观主义哲学路线的批判。
鉴于此,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而是深化现象学之自身理解的哲学思考。作为现象学研究的“目的论-历史的”道路的关键阶段,它构成现象学的认识批判的本质要素,对于充分阐明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明确界定现象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针对休谟的批判意味着超出休谟。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构成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双重批判,但他却看不出这种批判应该指向何方。囿于经验主义的成见,休谟预设了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因此看不到新的可能的哲学维度。胡塞尔的“目的论-历史的”批判,一方面透过休谟思想的怀疑论外壳,揭示其背后所涌动的“先验动机”;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其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批判,澄清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成见。由此,胡塞尔阐明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实践的可能性”(Hua VI, 16-17)。
其次,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阐明了先验的基础科学的观念。笛卡尔以一种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将“关于纯粹主体性的基础科学的必然性的意识”注入近代哲学的发展中。休谟哲学具体贯彻了这种“意识”,但却是“以一种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形态得到贯彻的”。胡塞尔的批判揭示了这种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悖谬性,阐明了一种关于先验主体性的基础科学的观念。
再次,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根源于他的意识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将意识和观念自然化,导致对经验的感觉主义歪曲,抹杀了经验本身固有的特性。因此,尽管休谟试图纯粹立足于经验确立一种内在的直观主义,但它只是一种假的直观主义或假的经验主义。胡塞尔的批判以现象学的眼光指明了休谟在纯粹经验的被给予性中所真正看到的东西和他所建构的东西,彻底清除了休谟的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的成见,揭示了经验的固有本性,从假的直观主义中解析出一种真正的直观主义,即现象学的直观主义。
最后,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开辟了彻底克服怀疑论的道路。囿于其自然主义的感觉主义,休谟的先验洞见深陷怀疑论的泥潭,以至于他最终未能创立一种先验的基础科学。与康德不同,胡塞尔对于休谟的怀疑论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他来说,怀疑论构成一切认识批判的必要的出发点,因此,他“没有停留于单纯证明怀疑论的错误和悖谬性,而是要通过积极地批判有效的内在动机以满足怀疑论的真实内涵”(Hua VII, 185)。勘破怀疑论的真理,意味着在更高的层次上彻底克服怀疑论。胡塞尔在《人性论》中看到了更高层次的真理,即彻底的主体主义。为了实现彻底的主体主义,胡塞尔对休谟的内在的先天概念作了现象学的改造,由此将休谟的坏的主体主义改造成彻底的主体主义,即现象学的主体主义,从而彻底克服了怀疑论。
毋庸讳言,胡塞尔的休谟哲学批判首先表现为一种现象学的自身思义。它以“目的论-历史的”反思方式深化了现象学的自身理解,揭示了现象学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也正是借助休谟的哲学传统批判所达到的历史转折点,胡塞尔厘清了现象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分界,宣告了与传统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