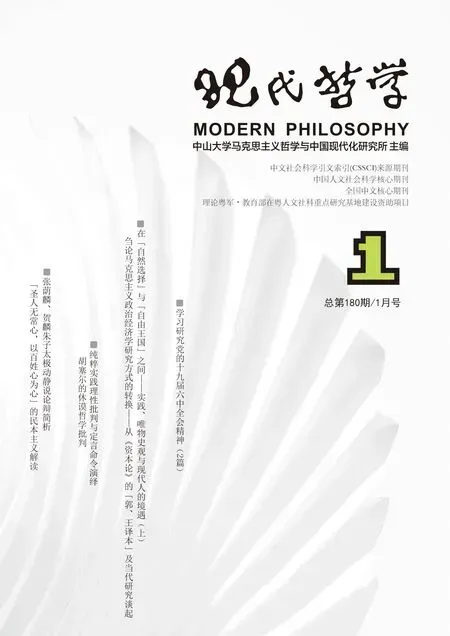罗钦顺哲学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再探讨
秦晋楠
一、从刘宗周、黄宗羲的问题谈起
自从刘宗周提出罗钦顺论理气与论心性不统一的看法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便从未偃息。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仅继承古代理学家的一些精彩分析,还得出很多更新的、更深入的结论。当然,不论是古人的分析还是哲学史家的研究,都出现过因为评论者自己的立场而裁剪甚至歪曲罗钦顺哲学的情况。故而,本文首先尝试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梳理,对在这一问题域下具体被讨论过的问题进行归纳,然后尝试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罗钦顺的理气、心性论间的融贯性、一致性问题。
对罗钦顺哲学理气论和心性论不融贯的批评,影响最大者当属刘宗周、黄宗羲。刘宗周对罗钦顺的批评见于《明儒学案·师说》部分,其核心如下:
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1)[明]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页。
按照刘宗周的理解,性心与理气的结构一致,它们都既不可混,又不可分。罗钦顺讲“理只是气之理”,强调理气是一,但又严判性心,主张心性是二,这就有矛盾了。刘宗周对于罗钦顺强调“理只是气之理”是赞赏的,只是觉得罗钦顺没有同时强调“性即是心之性”有些问题。
黄宗羲接过刘宗周的批评,做了相似的阐述,引述如下: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2)[明]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107页。
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批评的逻辑,而且更进一步,直接包含了对罗钦顺哲学心性论部分的改进意见。在他看来,“正确”的心性关系应该是:心之感应纷纭中的历然不昧就是性。
可见,刘宗周和黄宗羲的批评在于:罗钦顺的理气论有新的创见,即理气一物说,但是他的心性论却沿袭朱子学,即心性二分说,故而造成两部分本该融贯的理论间出现不协调。他们的改进意见在于调整罗钦顺“错误”的心性论,让心性关系由“二”变“一”。
二、目前所见两种回应思路
对于刘宗周、黄宗羲的批评,有两种可能的回应思路。
第一种可能的回应思路是否认刘、黄对罗钦顺理气论或心性论的描述,重新讲出罗钦顺哲学两部分的一致性。在这一条思路上又有两种不同的方法。部分学者采取重新描述罗钦顺理气论的方法,代表者如钱穆。在《罗整庵学述》中,钱穆首先指出“梨洲此辨,整庵实难自解”,但认为整庵思想在《困知记》的《续记》中有不同于《前记》中的“新悟”,这是黄梨洲没看到的(3)钱穆:《罗整庵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7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第63-64页。。他认为罗钦顺的新悟即就气认理,理气不离不杂,而这与朱子的理气论“欣合无间”。虽然钱穆指出了罗钦顺心性论中一些特殊的(他说是“可疑”的)部分,但他最终的结论是“整庵固不认理气为二物,亦未认心性为二物,非所谓不能自一其说而有大悖存焉,如梨洲之所讥也”(4)同上,第67页。。综合而言,在钱穆看来,罗钦顺的思想有前后两期,前期思想确实有黄宗羲所批评的理气心性不统一的问题,而后期事实上并没有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后期罗钦顺已经修正了他对朱子的“错误”批评,认识到“不离不杂”就是“真正的”理气关系。可以发现,钱穆关注的核心在于罗钦顺的理气论,他虽然提到罗钦顺心性论有四点“可疑”,但并未进一步展开分析,而是直接通过前后两期的分判说明了后期罗钦顺理气论与朱子的一致性,从而跳跃到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具有一致性这个结论。从钱穆的回应可以看出,他完全看懂了刘宗周、黄宗羲的批评逻辑,他解决这个批评的方式在于否定罗钦顺在理气论的最终定论中有本质上不同于朱子的新创见(5)陈代湘受钱穆影响也持此见:“罗钦顺既反对认理气为二物,又不同意把理气看成一回事的观点,与朱子并无二致。罗钦顺自已也夸大了他与朱子在理气观上的区别。”(参见陈代湘:《罗钦顺理气心性论之我见》,《求索》2007年第6期。)。
本文认为,钱穆的思路并不成立,他的这一回应方式需要面对至少三重挑战。其一,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是否本质上就是朱子的不离不杂说?虽然当代的研究对于罗钦顺的理气论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是以张岱年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范式,冯友兰主张的“一般-特殊”理论,还是陈来讲的“去实体化”进程,都不认为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就是朱子所讲的不离不杂说(6)参见秦晋楠:《重思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学术史与哲学史交织下的新理解》,《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换句话说,当代研究的代表性解释路向都不同于钱穆的思想。其二,钱穆所指出的罗钦顺心性论中的可疑之处主要是其心性体用的表述,这部分与朱子学有较大差异。他通过“说法可疑-先后分期-后期才是定论”的逻辑,将这部分思想内容划归为前期,从而剔除了这部分思想内容,但是并没有论证前后期分期的合理性。事实上,《困知记》最先完成的部分成书时,罗钦顺已经过了60岁,他自己多次说《困知记》是自己几十年思考的结果,即最终定论。而且,目前流传的《困知记》是罗钦顺去世前一年整体整理过的,换句话讲,如果罗钦顺自己没有讲出一个前后期,我们只能认为他主观上不会同意钱穆前后二期的划分(7)嘉靖二十五年,《困知记·四续》成书,嘉靖二十六年罗钦顺去世。罗钦顺在《自志》中说:“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六卷”的提法只可能成于此时,指《前记》两卷、《续记》两卷、《三续》《四续》各一卷。可见,在《四续》成书后,罗钦顺又整体编辑整理了《困知记》。《附录》中的内容虽非一时写就、编成,但系统整体编辑并定稿于《困知记》书后,应该即此时所为。(参见[明]罗钦顺撰、阎韬点校:《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2页;林展:《明嘉靖年间理学领袖和经典的塑造——以罗钦顺〈困知记〉的撰写与传刻为例》,《台大历史学报》2020年第66期;林展:《罗钦顺〈困知记〉版本源流考》,《文献》2019年第6期。)。此外,罗钦顺所讲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困知记》及附录论学书信中的讨论都没有见到明显的前后期差异。这一史实判定问题是钱穆立论的硬伤。其三,刘宗周、黄宗羲在批评罗钦顺时,主要的攻击点在于罗钦顺理气论与心性论不统一,其前提是罗钦顺的理气论相较于朱子的理气二物不离不杂说完成了革命性的创新,即理气一物。换句话说,钱穆的回应看似在解决刘宗周、黄宗羲的批评,事实上在根本预设,即罗钦顺的理气论是创造性的理气一物说还是与朱子无二的理气不离不杂说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和刘、黄南辕北辙。钱穆的回应其实不应该被叫做一种回应,而应该被理解为对这个问题的取消。
在这一条思路上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方法,即不仅重新描述罗钦顺的理气论,而且重新描述罗钦顺的心性论,代表者如赵忠祥。他说:
因为理为气之理,此理之在人则为性,此理或此性是在人受气成形的过程中而获得的,不再具有先于气而存在的可能。而心作为受气成形产物,它只是人的具有认知、感悟、记忆、推理的思维器官,是主体精神产生的物质根源,由于其认知的神妙功能可以体认和呈现在天之理和在人之性,所以是人之灵处,是性之所在,心与性都是以气为根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并不矛盾。(8)赵忠祥:《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北方丛论》2005年第3期,第84页。
赵忠祥指出,罗钦顺哲学中心、性(理)都以气为根据,是人受气成形的过程中获得的,没有理在气先,也没有性在心先,所以心性论和理气观并不矛盾。如果我们把这条结论对应于刘宗周、黄宗羲的批评,则赵忠祥的论述核心是理以气为根据,心、性也以气为根据,所以理气并非二物,心性也并非二物,故而刘、黄批评罗钦顺哲学有矛盾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找到一个究极根源的辩护方式似乎错过了理论细部的差异性,并没有回答罗钦顺“理气-心性”这一具体结构之间是否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虽然这种说法在罗钦顺的哲学中有据可循,但是似乎刘、黄的问题并不是被解决了,而同样更像是被避开了。
第二种可能的回应思路是:跳过刘宗周、黄宗羲理气、心性架构一致的理论预设,重新讨论一致性问题本身,此思路的代表者如李存山。他说:
首先,气不能等同于心,气是指化生世界万物的物质本原,心并非一般的气,而是“人之神明”,是气之殊的一种机能。罗钦顺将气之理作为性而立于心之先,并不关涉“理能生气”的问题。第二,气之理应该是指气这一物质本原具有的一般运动规律,罗钦顺和黄宗羲等人都把气之理作为性而赋予其道德准则的意义,这是错误的。第三,心并不本然包含道德准则的“条理”,道德准则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心必于社会生活有所反映(或积淀)才能形成道德观念。就此而言,罗钦顺将心性二分并没有错,其错在于将性——道德准则立于心之先。(9)李存山:《罗、王、吴心性思想合说》,《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第45-46页。
按照李存山的思路,其一,心不等于气,故而理在心之先不等于理在气之先;其二,气之理和道德准则无关,罗、黄此处都错了,言外之意就是性、理不同,即质疑理学最基础的“性即理”这个原则;其三,心并不本具性理,故而心性确实应当二分。综合上面三点,李存山的结论是:理气之间没有先后关系,但是心性确实应当被分判为二,因为气之理(运动的规律)和性理(道德的准则)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可见,李存山的论述在根本上是同时在评述罗钦顺的哲学与刘、黄的批评。一旦颠覆了理学的基本原则“性即理”,不仅刘宗周、黄宗羲对罗钦顺的批评没有了意义,他们的哲学甚至整体都是混乱的。从“物质-规律”“自然-社会”“运动-道德”等分析范畴的使用可以看出,李存山的回应超越了理学的基本原则,展示了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毋宁说更像是一个更为宏观的对理学整体的批评。
三、“理气-心性”之外
如果我们站在理学内部,肯认“性即理”这一根本原则,且承认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确实相较于朱子的理气不离不杂说做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改变,又不另找基石,避开“理气-心性”这个基本关系问题,那么刘宗周、黄宗羲对罗钦顺的批评是不是就铁板钉钉、再无可论呢?本文认为并非如此,而且问题的根源就在刘、黄所说的“理气-心性”这个基本关系。
在理学中,太极、物理、性理三个概念在微观上虽有差别,但就宏观而言又可以是同一的,即天理。理气论层面的“理”在心性论层面对应于“性”,这一点是理学整体都承认的共识。与此相对,理气论层面的“气”可以对应于心性论层面的“气质”“气禀”,这是程朱理学可以接受的思路。罗钦顺也是这样看的,并且主张天命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没有脱离了气质的纯粹的天命善性。刘宗周、黄宗羲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更进一步,把气与心直接关联起来,从而主张性只是心之性,这才有了上引刘宗周所说的“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心与气之间的这层关系是罗钦顺的哲学所没有的。对此,不仅上引李存山的论文曾指出过,陈来在其对刘宗周的研究中也讲到过:“从明中期以来,理学心学都把心当做属于气的一个范畴,认为心与性的关系就是气与理的关系,这在刘宗周更为明显。”(10)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张学智也曾指出这一点,他在论述刘宗周特殊的心气关系后,还提到由此延伸出的刘宗周的四德七情说,并总结说:“刘宗周这一思想是独特的,他要纠正前人天道论与心性论、心性论与修养论不能统一,整个思想缺乏统一的物质基础的偏弊,欲把它放在统一的基础上……这些方面,是刘宗周融和程朱陆王,又吸收王廷相等的合理见解熔为一炉所开出的一条新的理路。”(11)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5页。可以发现,刘宗周批评罗钦顺的这一点,其实正是刘宗周本人的哲学与前人相比的特色之一,这是本文想要首先指出的。
在传统朱子学框架下,从概念上讲理气论中是“理-气”格局,心性论中是“心-性-情”格局,中间的枢纽在于人一方面禀气而生,所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另一方面人禀受纯善的道德善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在理气论与心性论的关系中,“理”可以直接与“性”相平行,但“气”不直接平行于“心”“情”。如果站在罗钦顺的立场,这一基本框架他并不反对,他只是会调整为:理气为一物的理(气)对应于“心-性-情”中的“性”,它不是脱离气禀的纯然天命善性,而是气质之性。
在本文看来,刘宗周、黄宗羲的问题可以被分为两个层次:从原则上讲,理气论和心性论应该融贯;从具体结构讲,理气应该直接平行地对应于性心。对刘、黄而言,只有做到了第二点,才算是做到了第一点,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两个层次。本文想要指出的是,虽然理气论与心性论应当融贯是理学整体的共识,不论朱子、罗钦顺还是刘宗周、黄宗羲,亦或是陆九渊、王阳明,都会赞同这一原则,但这种融贯是不是一定要体现为刘宗周、黄宗羲主张的“理气-性心”平行地直接对应这种具体结构?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问,朱子学的“理气-性气-心性情”结构是否也是理气论和心性论融贯的一种体现?一旦明确了这重二分,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承认:虽然罗钦顺没有直接地将理气与性心平行等同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说罗钦顺哲学的理气论部分(“论理气”)与心性论部分(“论心性”)不融贯、有矛盾。更进一步,当我们梳理清楚了朱熹、罗钦顺和刘宗周三人对于理气论和心性论间关系的看法,就可以发现罗钦顺的看法大致可以放在朱熹与刘宗周的中间位置,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非常显著,刘宗周对罗钦顺的批判也构成他自己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这对于我们回看与定位罗钦顺的哲学很有意义。
四、两种心与两种心性
如果我们不在刘宗周的特殊哲学理解下,而是在朱子学的背景下看,那么罗钦顺论理气与论心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矛盾。如果一定要说罗钦顺哲学存在矛盾或张力,本文认为,罗钦顺的心性论中既有性体心用说,又接续了朱子学中非常重要的以知觉神识讲心的传统,这两种对心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更进一步,两种不一样的对心的理解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心性关系。准确地说,罗钦顺哲学的矛盾或有张力之处存在于心性论内部,而非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
在罗钦顺对心性关系的界定中,性体心用说是核心命题。如他说过:
动亦定,静亦定,性之本体然也。动静之不常者,心也。圣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体常自湛然,了无动静之别。常人所以胶胶扰扰,曾无须臾之定贴者,心役于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虽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顺其理而应之,亦自无事。然而明有未烛,诚有弗存,平时既无所主,则临事之际,又恶知理之所在而顺之乎?故必诚明两进,工夫纯熟,然后定性可得而言,此学者之所当勉也。(12)[明]罗钦顺撰、阎韬点校:《困知记》,第29页。
上引材料清晰地反映出,在罗钦顺看来,心属于现象层面,是个体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性的、情境性的,与此相对,性是本体层面。性体本身不可能在时空中显现,但作为本体的性体可以以心这一现象展现在具体时空中;心不论动静,都是对性的体现。
此处的性心体用关系与朱子所讲的心具众理有所不同。用罗钦顺自己的话说,其间的核心差异就是心性为一还是为二的问题。对此,罗钦顺曾说:“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误。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13)同上,第51页。在他看来,一方面,心性不是两物。并非是说性体、天理作为一个完满、独立的单一体驻在心体中。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与他对理气关系的看法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心与性两个概念的所指又非全等的,它们各有所描述的侧面,心是作为本体的性的现象,而性是作为现象的心的本体。在这样的理解下,一个理论后果是:动静无常之心也必是性的现象,性就不能单纯在至善无恶的意义上来讲。后文将指出,罗钦顺对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关系的讨论恰恰就是沿着这个逻辑线索展开的。
朱子在中和新说后与张南轩等人辩论《知言》,他反对《知言》所说的“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提出“用是情,不是心。性情相为体用,性心则不为体用”(1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可以说,成熟朱子学的心统性情的说法,恰恰是在与性体心用思想相对正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按照罗钦顺此处的性体心用说,性为本质、心为现象,现象必有本质,本质也必以某种现象表示出来。心不论动、静皆有“定”与“不常”两种可能状态,所以一个合于逻辑的推论是:所谓心之不常也必须是性的表现。这就必然要求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合并为一而非分裂为二,因为心之不常无论如何不是单纯的朱子意义上的天命之性的现象。并且,按照逻辑推演下去,性体心用、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合并为一等这样的命题与性具于心这一命题是矛盾的。更进一步,心性论上的性体心用说必然要求理气论层面破除理与气为二物的主张。综合来看,与成熟朱子学不同的性体心用说,才是罗钦顺心性论的核心。
从心性体用这个角度说。在理气论层面,罗钦顺强调过理对气的主宰是“不宰之宰”,因为作为理之现象的气已经不同于朱子所讲的独立于性理的气质,罗钦顺所主张的气是自然有条理的。相应的,如果全面推展“性体心用”这一思路,罗钦顺在此处也应该强调性对心的主宰是“不宰之宰”,作为性体之用的心应该自有条理。张学智曾说“根据他的理气论,他的心性论应是如后来戴震所谓情之不爽失者”(15)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第323页。,就是这个道理。需要说明的是,在性体心用的关系下,虽然体用不是二物,但体与用也不全等。虽然情之不爽失、心发而中节就是性的现象,且不能脱离现象而设置独立的纯粹至善性体,但是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还是既和“喜怒哀乐”也和“节”有区别的。不过,作为性体之用的心肯定不再是朱子学意义下的七情或欲,它只能是朱子学意义下的四端之心。
从知觉神识这个角度说。认识必然要分出能、所,所识与能识显然不是一回事。具体到理学常常讨论的心性关系问题上,不能认为心可以知觉到善性,心就是善的,更不能把知觉神明虚灵洞彻的某种状态直接与具有善的德性相等同。在知觉神识这个意义上讲心的时候,心可以认识性;反之,性最多只能指导心、在心开始认识之前给出一个方向。但不论如何,这两种关系都难讲为心性一物。现代研究者往往认为,阳明心学中心被诠释为一个集认知、情感、意志等全部能力、面向为一体的大心,良知学说本身又强调德性带动知性,是一个大综合。可以发现,罗钦顺在心的层面更多保留了朱子学中纯粹的认知心这一面,与阳明有所不同。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罗钦顺在《困知记》第一条就提到“理之所在谓之心”(16)[明]罗钦顺撰、阎韬点校:《困知记》,第1页。,看上去与朱子所讲的心具众理、理驻著于心中这一思路相仿。然而在《困知记》中,罗钦顺最常用来分判心性为二的理据还是性是理而心是觉。如他说:“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17)同上,第1、2页。
正如赵忠祥已经指出的,“罗钦顺的心性之辨更多的是在辨别儒佛和批评心学心即理时加以阐述的”(18)赵忠祥:《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罗钦顺讲心性为二时多针对心学和佛教。在对他们的批评中,所谓“识心”不是说他们认识到了作为性体之用的心,而是他们只认识到虚灵知觉神明之心。朱子学中的性驻著于心中、心具众理这一脉思路罗钦顺倒是没有强调。
罗钦顺突出性心之别,但是强调理气一物,这是判定罗钦顺哲学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融贯的核心因素之一。但是正如冷静的学者们已经看到的,罗钦顺所讲的理气一物并非是取消理,并不是把理化约为气,而是指出理气之间的“本质-现象”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理堕于气的不离不杂关系,当然也不是理气全等。罗钦顺心性论对于心有两个向度的强调,一方面虚灵知觉神识描述了一种作为认识功能的心,另一方面心性体用这个思路描述了一种作为性体的现象的心。心的如上两个层次的意义必然引发出两种不同的心性关系,其中心性体用的关系和理气论中的理气一物较为融贯,而心性能所的关系则与此不太融贯。虽然罗钦顺肯定没有像批评他的刘宗周、黄宗羲那样直接主张心与气的平行对应关系,但是以朱子学作为衡量标准,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没有明显的不统一。只能说罗钦顺哲学在心性论内部因为对心的定义有多层,所以心性关系并非形式上只有一层,这里会产生形式上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