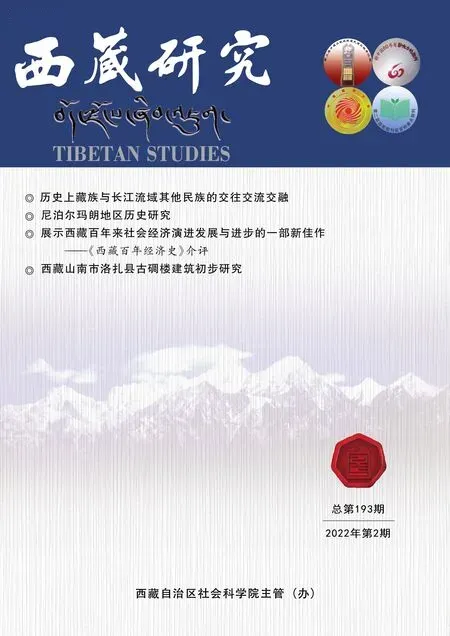藏族格言诗汉译史考
赵春龙 李正栓
(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49;2.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一、引言
藏族格言诗以13世纪上半叶萨迦·贡嘎坚赞(1)由于音译原因,萨迦·贡嘎坚赞被不同学者译为萨迦班智达·根呷坚赞、萨班·贡噶江村、萨班·贡嘎江村等。为了保持文中姓名前后一致,本文除在介绍文章标题或引用内容时使用其他名称,其他地方均使用“萨迦·贡嘎坚赞”或“贡嘎坚赞”。(1182—1251)的《萨迦格言》成书为标志正式形成,后经历代藏族学者的创作,内容日趋丰富,逐渐形成独特的藏族格言诗文化。现有贡嘎坚赞的《萨迦格言》、班钦·索南扎巴(1478—1554)的《格丹格言》、贡唐·丹白准美(1762—1823)的《水树格言》、罗桑金巴(1821—?)的《风喻格言》、居·米庞嘉措(1846—1912)的《国王修身论》、南杰索巴(生卒不详)的《土喻格言》以及诺奇堪布阿旺朋措(生卒不详)的《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流传于世。藏族格言诗形成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被翻译成蒙古文、满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汉文、日文等十余种语言。
藏族格言诗最早译介始于蒙古文翻译。“据考查,《善书》(《萨迦格言》)的第一个翻译本是十四世纪索纳木·卡拉译的八思巴译文,无疑这是世界上《善书》的第一个译本了。”[1]由此开启以蒙译和汉译为主的域内翻译。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汉译。研究藏族格言诗的汉译历史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藏族格言诗的真正汉译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文化的重视、保护和宣传,有利于国内外读者全面了解民族政策关照下的藏族文化发展状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铸进程。其次,藏族格言诗的汉译、民译和外译时常在交互翻译的情况下进行,爬梳藏族格言诗汉译史有助于厘清藏族格言诗民译、汉译和外译之间的译介路线。再次,藏族格言诗的思想内容借鉴吸收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思想文化,其形式和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藏族格言诗的汉译和蒙译历程反映出汉族与藏蒙等少数民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关系。最后,兼懂民族语、汉语和外语的翻译人才缺乏成为民族文化典籍外译障碍。“从目前国内民族典籍英译实践看,民族典籍译为英语基本上都要经过汉语中介才可转换为英语,特别是汉语的转译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2]藏族格言诗汉译为其民译和外译提供了更多选择,其汉译史的梳理有助于译者更广泛地选取文本资料。因此,从民族典籍研究和藏学研究出发全面考察藏族格言诗汉译史极为重要,也极为必要。
二、藏族格言诗汉译史分期
王尧根据“在中国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藏族及藏文化”的原则,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藏学史”划分为8个时期,即“(1)中国藏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40—1911);(2)中国藏学研究的创立时期(1912—1937);(3)中国藏学研究的艰难发展时期(1938—1949);(4)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1950—1965);(5)中国藏学研究的沉寂时期(1966—1976);(6)中国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1977—1985);(7)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86—1995);(8)中国藏学研究的稳定发展时期(1995以后)。”[3]25王尧综合考察了国内藏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对中国藏学史的时期划分具有普遍适用性。藏族格言诗作为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汉译历程符合藏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然而,由于起步晚,藏族格言诗汉译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汉译传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略过了现代中国藏学史前面的两个研究时期。结合现代中国藏学史的普遍发展规律和藏族格言诗汉译的特殊发展进程,笔者将藏族格言诗汉译划分为5个时期(2)藏族格言诗汉译符合中国藏学研究分期的一般规律,但也有其特殊规律。由于藏族格言诗汉译在1977—1995年整个期间呈现出全面汉译的特征,本文没有完全按照中国藏学研究时期进行划分,将这个时期列为藏族格言诗汉译的全面时期。,即(1)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时期(1938—1949);(2)藏族格言诗汉译新生时期(1950—1965);(3)藏族格言诗汉译沉寂时期(1966—1976);(4)藏族格言诗汉译全面时期(1977—1995);(5)藏族格言诗汉译深入时期(1995年至今)。
(一)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时期(1938—1949)
“本时期学者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到边疆问题,因此,在边疆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藏学在这样的艰苦环境和特定背景下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91藏族典籍汉译本逐渐见诸报端或成册出版,《萨迦格言》进入学者研究视野,出现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
据考证,藏族格言诗汉译始于郭和卿。郭和卿(1907—1986),四川雅安人,我国著名藏学家和藏族典籍翻译家。1984年,四川雅安因修县志需要征集本县名人资料,郭和卿应此要求于1984年7月27日回信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其中特别提及,“《萨迦格言》系萨迦班智达所著。这是一部叙述修身处世的格言。内容分九章。系我于四十年前译出汉本,约五万字。系用文言翻译(不合出版的要求),以此作为存稿。”[4]1996年出版的《雅安市志》印证了信中内容,“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3)刘文辉(1894—1976),爱国将领,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原西康省主席等职,于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邀请格西绛巴默朗到雅安讲经,经师推荐郭(和卿)任刘文辉藏文翻译,后刘又邀请西藏格西、广化寺堪布昂旺朗嘉至康定讲经,对郭执弟子礼。郭先后担任翻译十一年,佛学、藏语文学有很高造诣,曾用文言文翻译西藏史学名著《一切宗义明镜》(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和文学名著《萨加格言》(萨加班智达·根呷坚赞著),还被聘为班禅驻成都办事处和西康省政府藏文秘书。”[5]《雅安市志》的记载与郭和卿回信的内容基本吻合。由此断定,《萨迦格言》为郭和卿于1944年左右在原西康省工作期间翻译,但由于其文言翻译不符合出版社的出版要求,故将其作为存稿。郭和卿的《萨迦格言》汉语全译本这一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没有得到充分发育,颇为遗憾,但藏族格言诗汉译由此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
(二)藏族格言诗汉译新生时期(1950—1965)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典籍抢救、整理及翻译活动促成其在中原地区的真正译介。”[6]该时期藏族格言诗汉译特征表现为:译者少、译作单一且为节译。
1956年,王尧汉译的《萨迦格言》部分诗节刊登于《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启《萨迦格言》汉译的新历程。1956—1957年期间,《人民日报》刊登王尧汉译《萨迦格言》格言诗212首,该汉译诗广受欢迎。1958年2月14日,《民族团结》期刊(现用名《中国民族》)二月号(总第五期)刊登王尧汉译《萨迦格言》的6首诗,同时刊登王尧《贡噶江村和他的哲理诗》一文,简要介绍了作者贡嘎坚赞及其作品《萨迦格言》。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01期刊载王尧的《谈西藏萨班·贡嘎江村及其哲理诗》一文。1958年5月,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日报》文艺版刊登的212首诗,名为《西藏萨迦格言选》。该译本除了212首诗外,还包括一个简短的译者序和32条注释。译者序简要介绍了作者贡嘎坚赞及其作品,32条注释解释了西藏地区和藏传佛教中特有的文化意象。《人民日报》《民族团结》《光明日报》以及青海民族出版社等重要出版单位的联合推介使得《萨迦格言》很快为国内读者熟悉。
(三)藏族格言诗汉译沉寂时期(1966—1976)
1966至1976期间,藏族文化研究呈现荒芜景象,藏族格言诗汉译活动受此影响,陷入“沉寂时期”,仅产生《萨迦格言》一个汉译本。本时期藏族格言诗汉译特征表现为:集体翻译,译作单一且为选译,译本以内部资料进行传阅。
1974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翻译专业印制由其71级和72级学生共同汉译的内部传阅资料《〈萨迦格言〉选批》。该译本为手写油印本,译有42首诗,藏汉对照排版。在译者序中,译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萨迦格言》中的封建思想内容进行全面批判,但同时肯定了《萨迦格言》的民族文学经典地位,指出《萨迦格言》的思想与孔孟之道同属一个思想体系。译者的否定与肯定矛盾地彰显出其对于《萨迦格言》的批判与推崇。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该译本在部分民族院校之间进行了传阅。1974年12月,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研组翻印了该译本,进一步扩大了《萨迦格言》的读者面向群。
(四)藏族格言诗汉译全面时期(1977—1995)
这一时期,民族典籍整理和翻译工作得到快速发展,藏族格言诗的汉译本呈现“井喷式”增长。相比前两个时期,这一时期藏族格言诗得到全面汉译,呈现出以《萨迦格言》汉译为主,兼顾其他格言诗汉译的局面。这一时期藏族格言诗汉译特征表现为:翻译形式多样,汉译作品全面,译本多为选译,传播方式多样。
在《萨迦格言》汉译方面,该时期结集印刷了3个汉语全译本(4)在本时期,除了中央民族学院、王尧、次旦多吉等的3个汉语全译本以外,还有耿予方的《萨迦格言》汉语全译本。耿予方在其《试论〈萨迦格言〉》一文中标注“所引格言原文,均系笔者翻译初稿。最近,西藏人民出版社已正式出版汉文译本,可查看。”但笔者多方查找,并未找到耿予方的《萨迦格言》汉译本。笔者结合该文引用格言诗近50首且格言诗编号至455首(《萨迦格言》共457首诗)和耿予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译《格丹格言》《水树格言》以及《国王修身论》的翻译经历,认为耿予方汉译了《萨迦格言》的全部诗节,故将耿予方译本归为全译本。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耿予方译本,故没有将该译本列入并做进一步介绍。、一个汉语选译本。1979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古藏文研究生指导小组印制了《〈萨迦格言〉讲稿:附格言及注释译文》,该书为藏语教研组的课堂讲义,介绍了《萨迦格言》的作者生平、成书背景、篇章结构、思想内容、写作特点、艺术特色,肯定了《萨迦格言》的思想价值,并附有释文故事和汉语全文翻译,诗节为藏汉对照排版。1979年9月,西藏自治区文化局资料室印制何宗英翻译的内部传阅资料《〈萨迦格言〉释文》,该译本以51个故事解释了《萨迦格言》51个诗节。何宗英汉译本得到学者和专家的认可。1981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藏研究》创刊号刊登了何宗英的《〈萨迦格言〉释文选载(二则)》。198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次旦多吉、王之敬、丁有希、贾湘云、廖东凡、平措朗杰汉译的《萨迦格言》全译本。该译本出版后广受欢迎,1980年第一次出版发行了8000册,1985年第二次出版发行了10000册。此外,1983年《西藏研究》第4期刊登了《〈萨迦格言〉选录——观察学者品(一)》,文中包括次旦多吉等人翻译的两首诗。可见,次旦多吉等人翻译的《萨迦格言》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译本继续受到关注,并得到逐步完善。1980年,《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刊登《〈萨迦格言〉选录》,文中包括王尧翻译的《萨迦格言》11首诗。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尧翻译的《萨迦格言》全译本。
在其他藏族格言诗汉译方面,该时期出现《格丹格言》《水树格言》以及《国王修身论》的汉译全译本各一本。此外,《水树格言》《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各出现一本汉语选译本。1984年4月,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耿予方汉译的《格丹格言》和《水树格言》。1984年10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李午阳、王世镇、郑肇中汉译的《藏族物喻格言选》(藏汉文对照本),该译本选译了《木喻格言》58首、《水喻格言》66首、《火喻格言》10首、《铁喻格言》12首、《宝喻格言》16首。1986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印制了耿予方翻译的《国王修身论》汉译本;1987年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译本。
另外,一些学者在期刊或图书中刊登藏族格言诗汉译诗节,构成藏族格言诗汉译本的又一传播途径。1979年,《宁夏文艺》第5期刊登高景茂的《〈萨迦格言〉选译》,包含6首诗汉译文。1981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以藏汉对照的形式刊登延恺、唐景福汉译的《〈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论格言〉选登》,三部格言诗均选登10首。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刊登佟锦华的《试论〈萨迦格言〉》,文中列入佟锦华汉译的57首诗。此外,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佟锦华主编的《藏族文学史》列入佟锦华翻译的《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的大量诗节。1984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第4期刊登星全成的《从格言诗看历代藏族学者的治学观》,文中以藏汉对照的形式列入星全成汉译的《萨迦格言》12首诗。1986—1987年,台湾学者萧金松在台湾《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7期和《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上分别发表《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萨迦格言〉第一、二品译注》和《〈萨迦格言〉第三品观察愚者品译注》,两个译注均为藏文、汉译、对音(采用Wylie系统)与语词对照四栏排版,另加释文和附注。1987年,《西藏研究》选登耿予方汉译的《国王修身论》59首诗。藏族格言诗在期刊和图书的选登说明其文化价值和译本价值为学界所认同,同时也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藏族格言诗汉译深入时期(1995年至今)
本时期藏族格言诗汉译继续深入,呈现出“丰厚翻译为主,翻译现象多元,出版形式多样”的译介特征。藏族格言诗汉译仍以《萨迦格言》汉译为主,且以丰厚翻译居多。同时,《水喻格言》《木喻格言》《火喻格言》和《风喻格言》均产生汉语全译本,这些译本同样为丰厚译本。
索达吉堪布《格言宝藏论释》(上下卷)的出版标志着藏族格言诗汉译深入时期的到来。1996年,索达吉堪布的《萨迦格言》汉语全译本《格言宝藏论》和《格言宝藏论释》(上下卷)在寺院和网络传播开来。《格言宝藏论》包括《萨迦格言》的457首诗;《格言宝藏论释》(上下卷)除了457首诗之外,还包括译者结合现代社会实际为每首诗增加的阐释部分。藏族格言诗汉译本日趋丰厚,传播方式日渐多元。
1997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均以“藏族格言诗+故事+图画”的形式分别出版《藏族格言故事连环画丛书》和《藏族格言故事选》,内含部分格言诗,增强了藏族格言诗的趣味性。2000年,“台湾蒙藏委员会”出版台湾学者萧金松的《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喻译注》,收录了《水喻格言》《木喻格言》《火喻格言》和《风喻格言》的全文,并将藏文、汉译、对音与语词对照四栏排版,另加释文和附注。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结集仁增才让和才公太的汉语全译本以及约翰·达文波特(John T.Davenport)等人的英语全译本,以藏汉英对照的方式出版《〈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开启《萨迦格言》译本出版新模式,该译本于2010年、2015年、2018年3次再版。201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以藏汉对照的排版形式出版班典顿玉和杨曙光翻译的《萨迦格言》全译本,附有图画说明。201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王尧的汉语新版本《萨迦格言:西藏贵族时代诵读的智慧珍宝》,增加诸多注释。201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百种藏汉文对照惠民图画书编委会编纂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国学启蒙经典诵读——〈萨迦格言〉》,藏汉对照排版,附有藏文评论,增加图画说明。此外,龙冬汉译《萨迦格言》30首诗于2010年在博客发表;孙德仁于2014年汉译《萨迦格言》部分诗节和《蛋喻格言》,收录其《仁者行吟译记存稿》;李钟霖汉译《格丹格言》及其注疏,于2017年出版《藏汉对照格丹格言诠释》。
近年来,藏族格言诗的汉译和传播趋向多元化和整体化。首先,藏族格言诗出现转译现象。2014年,多伦多教育出版社出版李正栓、耿丽娟转译塔尔库《萨迦格言》英译本APreciousTreasuryofElegantSayings的汉译本《雅言宝库》;201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正栓、赵春龙转译达文波特《萨迦格言》英译本OrdinaryWisdom—SakyaPandita’sTreasuryofGoodAdvice的汉译本《普世智慧:萨迦班智达劝善良言宝库》,进一步丰富了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其次,藏族格言诗结集出版。202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藏族嘉言萃珍(藏汉对照绘图本)》,内含仁增才郎汉译的《萨迦格言》和《王侯美德论》(《国王修身论》)、龙仁青汉译的《水木格言》和《格丹格言》;同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格言大全》(4卷),不仅包括王尧汉译的《萨迦格言》、耿予方汉译的《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文扎汉译的《风的格言》《月的格言》《宝论格言》《火的格言》《铁的格言》《地的格言》,还包括其他30余部藏族格言(诗)及其汉译本,极大丰富了藏族格言诗宝库。
三、藏族格言诗汉译特征
藏族格言诗汉译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译介特征。循着各个分期汉译特征,从历时角度全面考察藏族格言诗的汉译特征,发现藏族格言诗汉译呈现出跨学科的诸多特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呈现出民族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点。对少数民族典籍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绘制出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网络图景,是翻译出版界的重要研究领域。”[7]藏族格言诗的汉译特征符合民族典籍汉译的普遍特征。从民族学分析,藏族格言诗构成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汉译历程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从翻译学分析,其涉及丰厚翻译、转译、翻译目的等翻译学内容;从传播学分析,其出版方式和传播途径多样;从语言学分析,其涉及藏、汉、英等多种语言。
(一)起步晚,发展快,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
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真正译介始于20世纪50年代。相比14世纪初期开始的蒙译和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英译,藏族格言诗的汉译明显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从汉译萌芽出现到当前深入译介,藏族格言诗产生近20个汉译本。相比早期的蒙译和英译,藏族格言诗的汉译发展快速,成果丰硕。
藏族格言诗汉译的每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均与彼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伴随着民族典籍译介的发轫、发展和深入,藏族格言诗汉译同样经历了相应的译介阶段。藏族格言诗汉译本产生较多的时期有3个,即1950—1965年的汉译新生时期、1977—1995年的全面汉译时期以及1995年以后的深入汉译时期。新生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组织整理和译介了大量民族典籍。全面汉译时期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民族典籍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翻译。深入汉译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持续深入,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近年来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8]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社会文化快速进步,藏族格言诗汉译呈现丰厚性翻译和整体化传播。
(二)译者以诗译诗,传递多元翻译目的
自藏族格言诗汉译以来,除郭和卿的《萨迦格言》汉译本为文言文形式以外,其他汉译本均保留了诗歌形式。藏族格言诗汉译者以诗译诗与译者身份密切相关。藏族格言诗汉译者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精通藏汉语言文化的学者、精通诗歌翻译的学者、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师。这些译者尽量以诗译诗以传递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
通过阅读比较各个译本的副文本,可将译者的翻译目的归结为四类,即传播藏族文学文化、宣传佛教思想、挖掘教育价值以及渲染政治色彩。在这四种翻译目的中,传播藏族文学文化占据主流。王尧、何宗英、耿予方、次旦多吉、延恺、景福、佟锦华、李午阳、李正栓等从这一角度出发汉译或转译藏族格言诗,在前言后序中肯定了藏族格言诗的文学文化价值。“格言诗,是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千百年来,它不仅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颇有影响,而且在祖国文学宝库和世界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9]“它(《萨迦格言》)不仅为我们研究西藏文学史、思想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也可作为文艺创作的借鉴。”[10]
索达吉堪布和班典顿玉、杨曙光从宣传佛教思想的角度出发汉译《萨迦格言》。索达吉堪布在前言中特别提及《萨迦格言》对佛教弟子修行的重要性,并指出王尧“未将本论之前后礼赞、回向等颂译出,也未按原版藏文字数相同的格式翻译,且所译用语与原版藏文特指的佛教用词之含义(内涵)差距甚远。”[11]由于过分强调《萨迦格言》的字数对等和格式相同,索达吉堪布汉译本通俗性欠佳。班典顿玉为了弥补索达吉堪布译本的不足,更加广泛地传播佛教教义,与杨曙光合作汉译《萨迦格言》,旨在把其汉译本打造为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均能读懂的诗体译本。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古藏文研究生指导小组和百种藏汉文对照惠民图画书编委会注重挖掘藏族格言诗的教育价值。前者将《萨迦格言》作为大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在学校刊印,以藏汉对照排版的方式进行印刷,并增加诸多副文本,为学生学习藏文提供诸多便利。后者通过藏汉对照排版,附加藏文评论,增加图画的方式解释了《萨迦格言》中31个诗节内容,此外,该译本被列入国学丛书,突出藏族格言诗的教育价值。仁增才让、才公太、达文波特的《〈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采用简朴易懂的语言,以藏汉英三语对照排版的方式为藏族学生提供学习汉语和英语的课外读物,同样凸出《萨迦格言》的教育价值。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族文学翻译专业71、72级学生和萧金松的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政治色彩。前者的《〈萨迦格言〉选批》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为“阶级斗争”服务,该译本对《萨迦格言》中蕴含封建思想的诗节进行大力批判。萧金松的藏族格言诗汉译本文学性较强,但其《〈萨迦格言〉第一、二品译注》发表在台湾地区1986年的《边政研究所年报》,《〈萨迦格言〉第三品观察愚者品译注》和《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喻译注》被列入“台湾蒙藏委员会”的《蒙藏专题研究丛书》进行出版,这为其译本沾染了一定政治色彩。
(三)汉译以《萨迦格言》为主,译本逐步趋向完善厚重
《萨迦格言》的问世开创了藏族格言诗创作的先河,后世藏族学者争相模仿《萨迦格言》,并创作出大量格言诗,由此形成“藏族格言诗文化”。由于《萨迦格言》开创性的文学地位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萨迦格言》成为最受译者欢迎的藏族格言诗。在藏族格言诗汉译活动中,《萨迦格言》汉译本数量最多,且不断有新译本问世出版。同时,《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火喻格言》《风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等格言诗也得到整理和汉译,其中大部分格言诗均有汉语全译本存在。
在藏族格言诗汉译过程中,其汉译本趋向完善厚重。一方面,藏族格言诗由《萨迦格言》单部格言诗的汉译逐步扩展至藏族格言诗的全面汉译。藏族格言诗汉译以1944年左右郭和卿汉译《萨迦格言》为开端,随后的40年间产生六七个《萨迦格言》汉译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其他格言诗的汉译本。20世纪80年代,藏族格言诗汉译取得重大进步。藏族四大格言诗《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均出现汉语全译本,《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出现汉语选译本。另一方面,大部分藏族格言诗均经历了由节译到全译的翻译过程,并且副文本内容逐步厚重。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译本最能体现该特征。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由1956—1957年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到195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其汉语全译本由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初次出版到201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重新出版,其内容由节译到全译,愈加全面,其文本体例逐渐增加,愈加厚重。
(四)汉译本出版方式和传播途径多样
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在出版方式上呈现多元局面。出版方式多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单位在地域上分布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国外;二是排版方式多样,含有一种语言单独排版和多种语言对照排版。
藏族格言诗汉译本的出版单位包括青海人民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台湾蒙藏委员会”、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福建莆田广化寺、中国藏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多伦多出版社等,分布在青海、西藏、甘肃、台湾、四川、福建、北京、河北等国内省市以及加拿大。在排版上,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呈现多样形式。例如,王尧、何宗英、次旦多吉、耿予方、索达吉堪布等人的藏族格言诗译本为汉语单独排版;中央民族学院、班典顿玉和杨曙光、百种藏汉文对照惠民图画书编委会的《萨迦格言》汉译本为藏汉双语对照排版;李正栓等人的《雅言宝库》和《普世智慧》为英汉对照排版;仁增才让、才公太、达文波特(美)的《〈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为藏汉英三语对照排版;萧金松的汉译本为藏文、汉译、对音、语词四栏对照排版。
由于独特的文学性和宗教性,藏族格言诗呈现出多样的传播途径,其中图书发行为主要传播方式,报纸连载、期刊选登、内部传阅、课堂讲义、寺院与网络传播等方式备受瞩目。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次旦多吉等的《萨迦格言》汉译本在成书之前分别在《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上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刊登;高景茂、耿予方、佟锦华、星全成、萧金松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延恺、景福的《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论格言》的汉语选译本以及耿予方的《国王修身论》汉语选译本均在期刊上进行刊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翻译专业71级和72级学生的《〈萨迦格言〉选批》和何宗英的《〈萨迦格言〉释文》为内部传阅资料;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古藏文研究生指导小组印制的《〈萨迦格言〉讲稿》为课堂讲义;索达吉堪布的《格言宝藏论释》通过网站、博客、光盘、电子书和寺庙流通读物的形式进行传播。多元的传播途径促进了藏族格言诗在国内的全面传播。
四、结语
藏族格言诗汉译史是我国民族典籍汉译史的缩影,其汉译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典籍的汉译特征。同时,藏族格言诗汉译史大致反映了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历程,其每个汉译时期与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基本保持同步。将藏族格言诗汉译史纳入民族典籍汉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史的范畴进行考察,丰富了民族典籍翻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凸显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以藏族格言诗汉译史为纽带考察其民译史和外译史,具体映射出藏汉民族间的密切关系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藏族格言诗汉译史的系统梳理丰富了民族典籍汉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史,为进一步具体分析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和传播奠定了资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