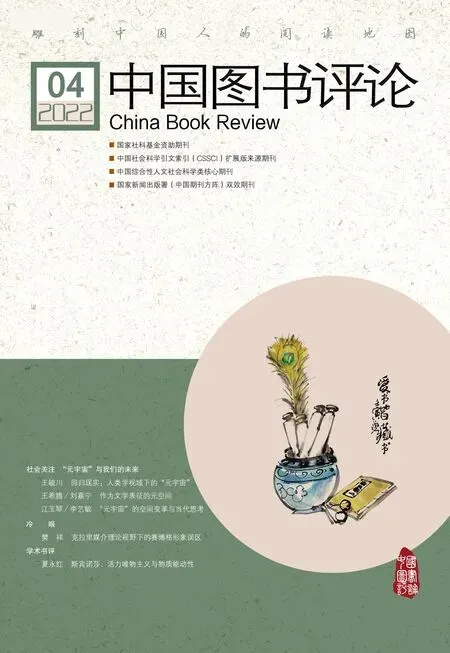从“奇辞”到“琦辞”
□牛 军
【导 读】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先秦名家是中国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思想流派。公孙龙子名实之论背后隐含着与印度佛学,西方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对话的契机。尤其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风潮下,公孙龙子的学说获得了新的阐释。《公孙龙子文献撮要》一书就呈现了《公孙龙子》接受史的整体风貌和其由奇僻之说到可贵精深之语的转换过程。
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先秦名家是中国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思想流派。《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1]2851但同时又说:“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1]2851这道出了名家思想的两面:一是名家学说缴绕难辨,二是名家在控名责实方面则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上述特点使得名家思想在后世流传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影响。与老子的 “无名”思想、孔子的“正名”思想迥然异趣,公孙龙子的名实之论背后隐含着其与印度佛学,西方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对话的契机。尤其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风潮下,公孙龙子的学说获得了多维阐释的空间,并敞开了它的多重面向。纵观公孙龙子接受史,历代学人对其人其说的研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或隐或显、或褒或贬,从而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思想风尚。
公孙龙子的思想有其丰赡的蕴含,他留给后世的诸多看似诡辩的“琦辞” “怪说”,令人宛若走进语词的迷宫,迄今仍有不少命题众说纷纭,难有确解。对历代累积起来的相关文献的梳理,是破解公孙龙子学说迷思的基础。孙秀昌教授与其博士生黎佳晔合撰的《公孙龙子文献撮要》(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黄克剑先生为该书作序)一书就是对公孙龙子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成果,该书呈现了《公孙龙子》接受史的原初风貌与发展阶段,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爬梳历代公孙龙子文献的著作,对公孙龙子学说史乃至中国名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受该书启发,本文拟对公孙龙子接受史中的相关问题做一番探讨。
一、公孙龙子接受史中的三次高潮
在清中叶之前,公孙龙子的学说并非显学,相关研究较为零散。《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迄于唐代仅存六篇。宋人谢希深所撰的《公孙龙子注》是今天可见的最早注本,然而他已在《公孙龙子序》中慨叹仅存的六篇“多虚诞不可解”,其注释亦“私心尚在疑信间”。《公孙龙子》原书虽散失大半,但毕竟有六篇得以保存,这六篇成为后世研究公孙龙子的基础文献。此后在犹如猜谜的破解和研究过程中,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不断与公孙龙子的学说进行碰撞与会通,形成了公孙龙子的接受史。大致说来,在公孙龙子接受史中曾有过三次高潮。
清代中叶以后考据之风兴起,先秦诸子之学重被阐释。汪中、毕阮、辛从益、张蕙言、陈澧、俞樾、王先谦、孙诒让等学者对子学的勃兴功莫大焉。其中,辛从益所撰的《公孙龙子注》(刊刻于1851年),以及稍后陈澧所撰的《公孙龙子浅说》,重新激活了北宋谢希深之后沉默已久的《公孙龙子》研究。孙诒让在其《墨子间诂》一书中,亦常常引《公孙龙子》之言以证《墨辩》。[2]清代中晚期形成了公孙龙子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下,公孙龙子的思想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资源,公孙龙子研究遂迎来第二个高潮期。尤其是西方逻辑学的引入,为这一时期的公孙龙子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1902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穆勒的《逻辑学体系》,并以《穆勒名学》为之命名。严复以“名学”翻译“逻辑学”,已显现出将名家思想与西方逻辑学做比较的视角。胡适1922年出版了《先秦名学史》(英文)一书,10年后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问世,此外还有王时润的《公孙龙子校录》(1931年出版)、张怀民的《公孙龙子斠释》(1937年出版)等,这些著作均从西方逻辑学的角度对公孙龙子进行了解读。虽然这类的解读难免产生误读,但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也使得公孙龙子的思想成为探究中国思想中有无类似西方知识论的重要资源,同时大大提升了公孙龙子研究的热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理论资源的重新引入,公孙龙子研究的热度再次陡增,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从而形成了公孙龙子接受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这一时期,西方语言学成为阐释公孙龙子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受“语言转向”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界热议的话题。公孙龙子关于“名” “言”的论说,可以说与语言学、语言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王宏印的《白话解读公孙龙子》(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王左立的《〈公孙龙子〉的语言意义理论》(南开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刘利民的《语言切分出的意义世界——索绪尔与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曾祥云的《〈公孙龙子〉辩题求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湖湘论坛》2009年第4期)、陈玮的《论“白马非马”的语义学价值》[《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朱长河的《〈公孙龙子〉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哲学观》(《外国语文》2012年第1期)等。黄克剑先生的《名家琦辞疏解——惠施公孙龙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可视为运用语言哲学阐释公孙龙子思想的代表作。黄先生从价值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出发,对公孙龙诸多奇诡而耐人寻味的论题做了自成一家的疏解,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名学思想的价值祈向:“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这种解读为公孙龙子学说与西学的融通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可能,即形而上学的层次。
纵观公孙龙子的接受史,我们可以发现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为公孙龙子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公孙龙子的思想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一个桥梁。在儒道两家那里很难找到的认识论、知识论、科学等因素,在公孙龙子这里却较为丰富。当然,在西方思想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即印度的佛学。例如,章太炎在《齐物论释》(日本秀光社1910年版)一书中,就借用了佛学术语“境”与“识”来分辨“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中的 “能指”与 “所指”。此后,景昌极在《学衡》1922年第8期上发表论文《中国心理学大纲》,将名家视为“中国心理学上最大之成就”。景昌极认为,不同于儒家、道家、墨家等注重实践的诸家,名家注重学理,忽略实用,创立了“唯象主义”。在他看来,名家所正之“名”不同于儒家偏重的道德之“名”,其更偏重于科学上的名。值得注意的是,景昌极是借助佛家唯识论的思想沟通名家与西方心理学的。这显示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下中西印文化的互动状况。
二、现代新儒家学者的阐释
在西学东渐的学术风尚下,现代新儒家学者立足本民族文化,融合西方文化,“返本开新”的主张较之于全盘西化的文化策略更具深意,在深度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现代新儒家学者都专门研究过名家思想,成为公孙龙子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冯友兰曾于1930年6月在《清华学报》发表《公孙龙哲学》一文。冯友兰运用现代新实在论关于个体之物与概念之存在方式不同的观点来阐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并将之视为打开《公孙龙子·指物论》的一把钥匙。他写道:“现代新实在论者谓个体之物存在(Exist);概念潜存(Subsist)。所谓潜存者,即不在时空中占位置,而亦非无有。如坚虽不与物为坚,然仍不可谓无坚。此即谓坚‘藏’,即谓坚潜存也。知坚藏之义,则《公孙龙子·指物论》可读矣。”[3]冯友兰进而指出公孙龙子的学说从理智概念的角度来言说,与我们的感觉不合,这是公孙龙子学说“然不然,可不可”的原因所在。
1932年7月,牟宗三在《百科杂志》发表《公孙龙子的知识论》一文。在此文中,牟宗三指出公孙龙子的名实之论与亚里士多德诉诸“质料”“形式”二分的知识论有暗合之处。他还从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大哲关于符号与本体(公孙龙子所谓的“物”)的论述阐发公孙龙子的知识论。牟宗三以自己广博的西学视域审视公孙龙子的思想,由此文便可略见一斑。牟宗三此后又多次论及公孙龙子的思想。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了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一书,他在此书中分辨了名家之 “形名”“名实”与魏晋之“名理”的异同。1979年台湾学生书局又出版了牟宗三的《名家与荀子》一书,该书旨在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中重智之一面,并明先秦名家通过《墨辩》而至荀子乃为一系相承之逻辑心灵之发展”[4]。这显示出牟宗三将名家置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思考。1983年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一书中,牟宗三再次谈及名家。该书第十讲题为“先秦名家之性格及其内容之概述”,牟宗三在此讲中认为公孙龙子的思考方式与柏拉图、胡塞尔的思路相近。他写道:“公孙龙可以作Plato、Husserl式的分析。Husserl现象学的方法就是要让对象自己呈现,这是纯粹的客观主义。公孙龙主张每个概念各自独立自存,就有这个倾向,所以说他属于西方式的思路。”[5]牟宗三进而指出中国文化中有重智的传统,但未能充分发展。名家正是重智传统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并非“苛察缴绕”“琦辞怪说”。牟宗三将公孙龙子的思想置于中西文化之辨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既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发掘它的思想价值,又在与西方诸多理论的会通中探索它的现代学术意义。
唐君毅196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香港人生出版社)一书,其中第一编第十八、十九章对名家思想进行了阐释。他同牟宗三一样看到了公孙龙子名实之论与西方逻辑学、知识论的不同之处,同时反对比附儒家之说阐释公孙龙子的思想。唐君毅写道:“不必先存西方之逻辑知识论或存在论之说在心,以释公孙龙之言。亦不可以公孙龙之引及孔子之言,为装点门面语也。”[6]328可见唐君毅认识到运用西方理论、其他诸子思想来阐释公孙龙子的不足。在他看来,公孙龙子专注于名的客观事物的性相种类,去除了名的价值意义与情意意义。这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区分了名的不同层面的意义,显示出思想的精密化。但同时去除名的价值意义与情意意义则是对名的意义的贫乏化。因此,他主张应该将公孙龙子的名实论思想置于中国传统的名言论的大语境之中,既看到公孙龙子的名实论“亦原属儒墨道之名实思想之大流中之一节”[6]328,又在此背景下关注其中含有的逻辑、知识论或存在论之成分。这体现出一种较为客观的研究立场,对以往的研究趋势有救偏补弊之功。值得关注的是,唐君毅还结合尹文子的“名有三科说”,对中国传统名言观进行了分辨:“尹文子乃谓名:有只表客观之事实形状者,有表主观对客观之价值判断者,有表主观心理中情意状态者。故谓名有三科。”[6]347唐君毅的这一观点厘清了中国传统语言观的内涵,颇值得注意。
此外,徐复观、钱穆对公孙龙子及名家的思想亦有精到的阐释,这里不再赘述。总体上看,这些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公孙龙子的阐释,基于中、西、印的文化视角,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志在开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今日看来仍值得借鉴。公孙龙子在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文化创建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探赜索隐的新进展
孙秀昌、黎佳晔新近出版的《公孙龙子文献撮要》一书在探赜索隐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该书以历史发展为经,分为五编——先秦至清代公孙龙子文献、民国时期公孙龙子文献、新中国前30年大陆地区公孙龙子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公孙龙子文献、港澳台地区公孙龙子文献,并将汉译与日英法德文公孙龙子研究文献(目录索引)附于书末,基本呈现了公孙龙子文献史的原初风貌。但此书亦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对海外相关研究仅存目,未能展开对相关研究的分析与评述。公孙龙子在近代的兴起与西学的传入关系密切。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侧重运用西方的种种理论阐释公孙龙子的思想,试图发现公孙龙子思想中的知识论、科学因素,以便与西方文化展开对比与交融。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恰恰可以与此形成一种对照。他们如何以西学切入公孙龙子,如何评价公孙龙子的思想,都值得关注,这类文献必将对中西文化的融通具有启示意义。西方相关研究所提供的他者视角,或许包含着一定的误读,但在误读之中将包含着一些创造性的读解。此方面内容的阙如,不得不说是此书的一大遗憾。
此外,国内文献收录亦有不全之弊。例如,牟宗三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关于名家思想的论述,此书未及收录。当然,这类散见于其他主题研究中的相关文字,梳理起来难度是极大的。这或许可以成为后来者的努力方向,或者寄希望于此书的修订再版。
公孙龙子的研究史折射出公孙龙子思想与诸子思想的复杂关系,亦显示出西方学术引入之后,从最初的比附、格意到逐渐走向研究自觉的过程,显示出中国现代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兴起的原初形态。这些信息不仅有益于公孙龙子思想研究本身,而且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
《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名家“治怪说” “玩琦辞”。黄克剑先生对荀子所谓“琦辞”的新释恰可用来形容公孙龙子思想研究在近代以来发生的重大转变。他写道:“‘琦’通‘奇’,‘奇’有怪异、冷僻之义,亦有新奇、精辟之义,荀子在前一种语义上以‘琦辞’为怪僻之辞,这里则在后一种语义上以‘琦辞’为奇异、精深之语。此外,‘琦’之本义为‘美玉’…… ‘琦辞’亦不无称叹其珍奇可贵之趣。”[7]公孙龙子的思想乃至名家思想的历史遭际,由奇僻之说到可贵的精深之语,其中蕴蓄着研究者不断的探索,也反映着时代更迭中思想风尚的变迁。公孙龙子思想的深入阐释依然有待诸种研究范式的碰撞、合作进一步探赜索隐,新时代的学术风尚或许亦会为公孙龙子的阐释打开新的可能与面向。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孙秀昌,黎佳晔.公孙龙子文献撮要[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2.
[3]冯友兰.公孙龙哲学[J].清华学报,1930,06(01):5.
[4]牟宗三.名家与荀子[M].台北:学生书局,1979:5.
[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1.
[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黄克剑.名家琦辞疏解——惠施公孙龙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