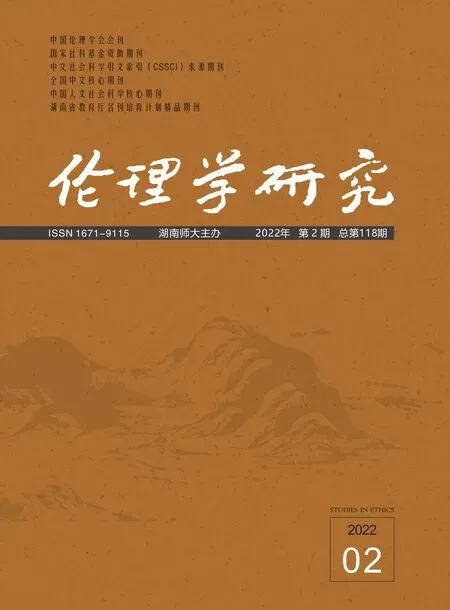应对老龄化困境的儒家伦理方案
张容南
衰老不仅对个体是一种挑战,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它也被看作是一种危机。在关于衰老的各种叙事中,最夺人耳目的是世界银行1994 年的提法,即我们已经步入“老龄化的危机”。世界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被形容为不断铺展开的“银发浪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世界各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克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政府的核心要务之一,因为人口老龄化暗示着经济前景的惨淡,同时,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将导致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系统的负担相应增加。由于老年是人的一生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因此它也是伦理学必须处理的一个议题。这篇论文将分析针对“老”的悲观态度背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我批评仅仅将老去界定为疾病和衰老的一种客体化思路,并寻找看待老去的一种内部的伦理视角。我认为,根据前一种视角,老人面临失去尊严的挑战,而内部的伦理视角则肯定了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讨论年老带来的规范性困境的基础上,我将从儒家伦理学那里汲取养料,提出应对这一规范性困境的建议。我将指出,依据儒家的尊严观,有尊严地老去是可能且可欲的。
一、医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老去
老去之所以被看作是衰老,与人的机能衰退和精神僵化有关。在医学中,“老年”被重新概念化为新的生命医学的客体,医院为老人开设了专门的“老年病科”,老人被视为身体机能运转不良或失常的客体。一些老年患者更是根据疾病来定义自身——疾病解释了他们的身份与自我认同,在极端情况下疾病还会挑战他们归因于自身生命的价值。以此方式,老去的复杂性被化减为一种病态的衰老,而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著名和令人恐惧的疾病。在这些关于疾病和衰老的叙事中,老人成为“非生产性的”和“依赖性的”,因此是社会难以承担的重负。理查德·休格曼(Richard Hugman)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常老去的生理特征被刻画为丧失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很重要的个人特质,即作为劳动者具备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质[1](195)。老人被视为社会福利和照料的被动接受者(国家和政府的依赖者),从而强化了世界人口统计学的论述,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社会危机。在一些社会中,关于老龄化的叙事还引发了代际冲突,年轻一代被描绘成肩负着“老龄化的负担”。人们谴责社会中的老人消耗了“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这些消耗却以年轻一代的辛勤劳动为代价。在将老去视为依赖性、疾病和被动性的叙事影响下,关于老龄化的世界人口统计学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美国医生约翰·罗伊(John Rowe)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恩(Robert Kahn)想要改变这一叙事。他们试图切断衰老与疾病之间的必然关联,从而论证老人的生活也可以是积极有为且富有尊严的。为此,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即“成功的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成功的老龄化“包括三个主要因素:疾病和与疾病相关的残障的可能性低,认知和身体功能高以及对生活的积极参与”[2](433)。尽管他们认识到“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他们尤其关注“人际关系和生产活动”[3](434)。这种定义结合了一种针对衰老的医学方法,并侧重于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责任和随着年龄增长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老年医学专家对何为“成功的老龄化”或“积极的老龄化”(active aging)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这个概念常常与“健康”、“生产性”或“成功老去”等概念交织在一起[3](1078)。在相关研究的推动下,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 年对“积极老龄化”给出了一种全面的定义:“积极的老龄化是为了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而优化其获得健康、参与社会生活和安全等机会的过程。积极的老龄化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它使人们能够在一生中实现其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健康潜力,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同时在需要帮助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护、安全和护理。‘积极’一词是指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和公民事务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指参加体育活动或参与劳动的能力。”[4]
这些论述旨在描绘一种老年生活的乐观图景。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的定义相对全面,但大多数有关积极老龄化的西方话语仍显示出对经济生产力的强烈偏好。批判理论家认为,这属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积极的老龄化强调对老人的生产潜力或社会潜能的利用。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积极地老去被定义为一种“双赢局面”[5](94),即这对老人和社会都有好处。但这种理解将老人的尊严建基于他们的生产能力或社会能力之上,忽视了老年阶段特有的脆弱性。且从实践层面来讲,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不同阶层、性别、族群的老人老去之后面对的生活前景是不同的,过分强调老人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责任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将社会压力转移到(尤其是那些弱势的)老年个体身上,其结果是为老人带来更大的养老负担。
二、审视老去的内部伦理视角
如果老去仅仅意味着衰老、衰退和疾病,意味着你只是被劳动力市场消耗殆尽的一具躯壳,一个社会或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那么老去似乎只有悲观和黑暗的一面。恐惧“老”的另一面是对青春的迷恋,即对肉身性的迷恋。虽然再美的人都会老去,但“小鲜肉”的层出不穷给人带来一种幻觉,即我们可以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永远停留在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使得“老”成为一种可怕的丧失。衰老的身体是没有美感的,它同时意味着欲望和力量的减退,意味着在消费空间中不再被视作可包装的范例,而成为一种人类退化的存在形式。所以克服“老”的方式是尽可能地延迟衰老,通过医学、健身和美容等各种方式保持我们的体型和能力,让我们显得年轻而有活力。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会带来对老人的尊重,相反,它恰恰贬低和排斥了年老的正常经验。
年老是人的自然生命的一个正常过程。在资本主义隐秘地排斥年龄的动机背后,在年龄被赋予社会化含义的同时,检视生命的意义仍存在一种来自个体内部的视角。现象学家戴维·卡尔(David Carr)对这一内在视角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身体的老去与物品的老化进行对比: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椅子会慢慢老化,并带有裂口或划痕等老化迹象。当它快要坏掉时,它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法令坐在它上面的人感到舒适。人的身上也会留下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给他们打下的烙印。身体遭遇的事故和它的习惯会留下其标记,最终削弱了大多数人的身体机能。这些变化,就像椅子上的变化一样,对外部观察者是可见的。但人与椅子不同,人会从内部经历这些变化。也就是说,人不仅累积了过去的痕迹,他们还能意识到这些痕迹来自何处。他们能够感知其能力的下降,并意识到能力衰退对未来的可能性产生的影响。从这种观点来看,人体验生命的过程取决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视角或观察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过去和未来。随着我们观察视角的变化,过去与未来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6](183)。从该角度来看待老去,意味着将其视作一个自我塑造和自我解释的创造性过程。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寿命长短也许保持不变,但不断变化的视角赋予了我们重新看待生命的可能性。老去一方面意味着实现变更计划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另一方面,随着我们接近生命的终点,我们也更多地开放了重新解释生命意义的空间。
对于这种重新阐释的可能,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给出过一个精妙的论述。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10)。对这段话的通常理解是孔子展示了一种道德发展的过程,一个人从立志为学开始,经历了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磨砺,最终达到了一种道德自由的状态。但根据另一种解读方式,孔子在此展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的生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转化:从立志为学的少年,到人格挺立的中年,从面对生命的困惑到知天之所命,从物我、人我、内外的贯通到天人之间的通达,最终抵达圣人之境[8](7)。这是“老去”的另一面:它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有意义的经历中不断改变他的视角,意味着一个人自我认识的加深以及他通过努力最终达到的天人相通之境。在此意义上,老去虽然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过程,但生命也随着老去变得日渐丰厚而深刻,一个德馨寿高的老者是其终生为学的回报。
每个人所具有的这种内部视角对于过一种伦理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恐惧和排斥年老就人类想要去过一种伦理生活的意愿而言是糟糕的,因为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生老病死。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生活意义不仅来自对欲望的积极满足,还取决于如何以个体和群体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生命中的消极面向。在此背景下,衰老、疾病、痛苦和死亡意味着生命中的一些特殊时刻——它们带来了某种中断,从而向我们开放了重新审视生活意义的机会:恰是这些人类脆弱性的展露激发起了我们对有意义的交流的渴望,对彼此的帮助和同情的依赖,对团结的需要,以及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意识。“这些维度属于成熟的和反思性的自我知识的阶段,因此属于一种真正有意义的、自我反思的存在。”[9](360-361)
三、应对老去的规范性困境
与医学中通过疾病来定义衰老的客体化思路不同,从一种内部的、伦理的视角来看,老去与个体内在的生命历程有关,一种积极自修的“老去”可以带来内在生命的丰厚与精神的自由。这对于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规范性困境是有帮助的。
萨缪尔·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指出,老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规范现象,因为老去面临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丧失。随着我们生命中重要之人的一一离世,我们为之行动的理由将发生巨大的改变。他指出,当那些活生生的关系随着关系中一方的死亡而被迫终结时,这种关系就不再是活跃的关系,而成了“存档的关系”(archived relationships)[10](506)。如果一个人有幸活得足够长,那么他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关系都会成为存档的关系。谢弗勒规定说,这一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将这些人称为老人。而老去指的就是一个人重要的关系越来越多地成为存档的关系的过程[10](507)。由于老去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重要关系被归档,由这些关系产生的行动理由就变得越来越少。老人不再有理由与去世的朋友共度时光,向他们寻求建议,与他们一起制定计划。他们为之忙碌、操心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也愈渐失去活力。因此,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消除或避免这种迫在眉睫的规范性的真空。
为了避免老去带来的规范性困境——由人际关系变少带来的行动理由的减少与生活意义的缺失,通常有两种应对方法:一是去发展新的个人计划,二是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但对于后一种方法,谢弗勒提出了一些质疑。假想一个老人太快地发展新的关系来取代旧的关系,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他究竟有多么珍视那段旧的关系。这与一个计划失败而转向另一个新计划不同,人们往往认为后者是富有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表现。换言之,如果我们真的珍视一段关系,那么即便这段关系被归档,它仍有可能继续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规范性的理由。但沉溺于过去也会带来一种新的风险,即我拒绝与世界产生新的关联和活跃的互动。走向极致的话,我就可能退出世界,去过一种衰退的生活(reduced life)[10](515)。谢弗勒的讨论带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背景,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下,退出对于老去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对老人而言,退出不仅可能是空间意义上的,即我能够自由出入而不受伤害的活动范围变小;更有可能是心理层面的,我感到我无力再去参与有意义的人生计划,或建立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让许多老人感到不安的不仅是身体机能的衰老,还有这种无能的感觉,一种退出世界的孤寂感。
对于退出的可能性,儒家提供了两种有价值的方式来应对:一是“学”,二是“孝”。这两种方式一个侧重于个体维度,另一个侧重于关系维度。“学”是一种积极自修的过程,“学”令我们积极地进入到与世界发生关联的各种活动中。孔子认为,学以成人,属为己之学。“学”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学习某种具体的活动或技能,尽管人需要通过不同的修身实践来获得自我知识。儒家所说之学是成人之学,即体悟生命之学。学习带来了反身性的思考,这令任何指向外部的实践活动最终都导向了我们对自身的性与命的体认和领悟。“学习说到底就是学会成长,从生理的成长到心智与精神的成熟,这种成长本身就是生活的全部。”[11](105)学习和自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成长和生命的快乐,就像孔子“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7](65)。如姚新中指出,拥有美德是“乐”的前提,有美德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充满智慧,过着愉快的生活,而一个品德低劣的人充满了忧虑和焦虑,因此永远无法拥有真正的快乐[12](229)。这种快乐不是来自外部,不是由名利的获得或欲望的满足带来的,相反,这种快乐来自生命内部,它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一个人通过自修而摆脱了困惑、烦恼和恐惧,抵达了无忧无虑的圣人之境。如果说获得一种外部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名利的获取——依赖于我们的能力、机会和运气,对老人而言获得这些快乐的机会是逐渐变少的;那么获得一种内部的快乐正好依赖于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的生命积淀,它需要我们从足够多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一种自我转化。当然,这不是说一个老者没有可悲之事,正如孔子哀叹:“天丧予!天丧予!”颜回的早逝对孔子来说是极其悲痛之事,“子哭之恸”[7](102)。尽管如此,由于知晓天命,所以孔子对生命中的丧失有一种坦然的态度。
“孝”与“学”不同,它更侧重于关系的维护而非个体的自修。“孝”生发于伦理生活的自然过程中: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完全依赖他的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获得了独立,他与父母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到父母年老时,成年的子女必须照顾父母。子女有尊敬父母的义务,而父母有责任以慈爱之心抚育孩子,教会他们人情与美德。人伦在时间上是代际更迭的: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一方面需要养育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需要供养他的父母。尤其是他在养育自己子女的过程中意识到过去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情时,孝的意识就开始出现了。如张祥龙指出,孝即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的发端,不忍见年老之父母有凄凉晚景。这种意识的出现将人与动物彻底区分开来,成为儒家道德教化的基础[13](110)。“孝”是“仁”的本源,也是道德教育的根基,但孝之现实可能性在于代际之间亲情与美德的教授和传递。养的两种形式——父母养育孩子和孩子供养父母——虽然在共时的意义上存在一种非对称性,却在历时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对称性和互惠性。孝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应对谢弗勒提到的随着活跃关系的归档而产生的规范性困境:因为子女需要供养年老的父母,不仅是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敬,要令其身心愉悦。这正是由儒家开启的孝亲传统,相比物质上的奉养,它更看重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拓展到整个社会,它要求年轻人在社会上尊敬长者,如《礼记》中所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14](19)。它要求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尊老养老的措施,借助治国策略和礼法之功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敬”。
虽然“学”与“孝”有助于让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但“学”与“孝”的当代实践面临着新的挑战。就“学”而言,儒家之“学”要求我们确立起一种内在的生命态度,“学”是为己之学而非为他之学。但在现代社会,“学”指向外部社会,技术的快速更迭不仅让社会急速变化,也让人们的“技能生命周期”缩短,使得很多老年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数字鸿沟”。许多老人尝试通过网络来学习,包括通过社交软件来了解世界、结识朋友。网络上呈现的海量信息一方面丰富了老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如网络诈骗、养生骗局等。大量信息以各种方式涌入老人的生活,要求他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理念,提高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针对这种情况,儒家伦理学的建议是,通过社区和家庭的力量帮助老人建立终身学习的机制,不管是社区的公益服务,还是家庭成员互助,都可以帮助老年人习得一些基本技能,使其能够无碍地接入网络构筑的公共空间,实现行动和社交的自由。这一积极老龄化的方案与西方老龄化的方案一样旨在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但在目标取向和方式方法上存在一些差别。从目标上来说,它并非建立在对老年群体生产力的偏好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老年群体终身“学习”的可能性上,它的目的在于“人的完善”,而非“对人的利用”。从方式上来看,它通过构筑社交网络邀请老年人向年轻人学习,一部分老年人向另一部分老年人学习,通过学习的方式来增进代际互动和人际互动,实现儒家“成人”和“成己”的目标。提供这种互动的场所可以是大家庭,若是家庭不足以为老人提供相应的支持,则可以通过社区服务来补充,因为老人对熟悉的社交圈有更高的信任度。
“孝”的实践也同样面临挑战。首先,若没有生育作为前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便无法确立,孝之实践也就无法落地,而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其次,在当今中国,由于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到城市务工,很多农村老人处于缺乏照顾的境地;城市老人进入子女生活的方式多是隔代抚养,这种相互帮助为父母与子女进入彼此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通道,但这种方式也常常以牺牲父母的生活计划为代价。最后,依据孔子的看法,孝必须以敬为基础,而敬在现代社会中有其特殊的困难。在崇尚平等的现代社会,由于父母难以对子女的人生规划提供经验性的指导,他们的权威在子女成年后已大大减弱。但父母权威的衰减不等于代际关系的弱化,亲子间的互动从“顺从”转向“尊重”,使得中国当下的孝道实践从“权威型”转向了“情感型”[15](214)。两代人通过交换经济资源、劳务资源和情感资源来维系家庭这个共同体,使得家庭的资源可以相对顺利地完成代际间的传承。这种交换关系的存在,让年轻人对其父母有更多的感激和尊敬,同时也增强了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影响力。这在许多城市中产家庭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换言之,“孝”在当代中国的代际实践中远远没有退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情感团结的形式。这使得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采取了多种方式相混合的策略:一方面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经济支持和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从与子女家庭的融合互助中获得情感支持和精神寄托。农村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农村老人因为绝望而自杀,除了经济上陷入困境,由于子女孝道的缺席而产生的意义危机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要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从社会保障体系和乡村伦理建设两个方面同时着力。
四、有尊严地老去:一种伦理生活的可能性
对儒家伦理的重新诠释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老去带来的规范性困境,还为我们思考老去的伦理意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因为儒家伦理对人性和人类生活有一种时间性的和生成性的视角。根据这一视角,人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存在者,这一有待完成的存在者必须通过参与社会互动来实现自身。人通过修身而成为自己,且通过修身的过程与自身、他人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我们存在的意义部分源自我们所建立的这些有意义的关联。聚焦于有意义的关联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体能力的消长令儒家文化有一种机制去对抗人的生理性衰老。如孔子被问到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7](46)可见令“老者安”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它离不开良好的伦理关系的构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的这一差别也集中体现在它们各自对尊严的看法上。
在关于尊严的西方理解中,衰老是对尊严的一种巨大威胁。老年意味着一种退化,因为老去是一个身体的各种机能逐渐衰退的过程。这种衰退暗示着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丧失。它可能是活动范围的收窄,或者对想做之事的力不从心,甚至是身体自主性的丧失。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不再能够自己随意活动或进食洗澡,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尊严的丧失。由于西方文化将尊严等同于自主性和能动性,将后者等同于独立性,因此依赖性和脆弱性是不被赞赏的,它们往往被看作是对人的尊严的威胁。“独立通常被称为自主,因此依赖就被视为自主的缺失或减少。由于自主性(根据自己的善观念指导自己生活的能力)是意义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自主性与独立性等同起来就意味着依赖性会损害人的尊严。”[16](234)要改变对老人的隐性歧视态度,其中一个关键的任务是挑战这种对尊严的理解。
我认为,对尊严的这种理解方式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它忽视了人类存在的时间性维度以及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完整性,而将尊严等同于人在特定的生命阶段内所具备的理性自主能力。它将自主性和独立性视作绝对好的,而将依赖性和脆弱性视作绝对坏的。这是对人类个体的理想化。问题在于,没有人可以永远保持在成年状态,或在其生活的所有阶段都维持独立自主。老年是人生的一个独立阶段,就像青春期或成年期一样,它有自己需面对的挑战,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老年人的尊严首先体现为一种地位尊严。地位尊严不依赖于人的自主能力,而取决于人在其伦理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它甚至要求我们更关注那些自主能力减弱的群体或个体,因为他们对尊严的需求更迫切。在西方传统内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她指出,人是脆弱的、依赖性的、有需求的涉身性生物(embodied creatures)。这意味着我们的理性和社会性都具有时间性,它们会生长、成熟和衰亡。我们的社会性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在成年与其他人发展出对等的关系,也意味着我们在幼年和老年会与其他人发展出不对等的关系,我们需要他人的照顾。然而,即便在这些非对等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互惠和真正的人类功能的实现,即人类尊严的实现[17](160)。在努斯鲍姆看来,尽管在一些特殊的人生阶段,我们不能施展出足够的理性能力或自主能力,但依旧可以运用动物性的能力来获得繁荣,我们的动物性也享有尊严。努斯鲍姆以能力来界定尊严,认为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就是一种人类核心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生活,政府有义务帮助公民发展其核心能力,这包括向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士提供施展其能力的机会,让其融入公共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学说带有功能主义的特点,它会赞同积极的老龄化,即前面提到的帮助老人实现其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健康潜力,使其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生活中。这对于老年生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其不足在于它以能力来界定尊严,忽视了人类尊严的主体间向度。
儒家伦理也注意到人类存在的脆弱性和时间性,但它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与努斯鲍姆略有不同。儒家同样重视个人能力的发展,但它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伦理关系的联结,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克服依赖性和脆弱性。依赖性和脆弱性虽不是人类追求的正面价值,却是人类伦理生活之所以必要的限定性条件,它们催生出人类的团结、关爱和责任意识这一类关系性的价值。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应对依赖性和脆弱性的挑战来发展人类德性。例如,孔子认为,孝不仅仅对年老体弱的父母是好的,孝也提供给子女一个修身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去磨砺自己的品性。因此,孝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可以很好地响应人类存在的时间性维度,它是仁的出发点。由于老去必然意味着丧失,丧失机能,丧失记忆,丧失亲朋好友,因此,对老人而言,从子辈那里获得伦理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通过伦理关系的建立来克服老去的依赖性问题,儒家也提倡一种积极有为的老去,即前面所说的,在时间中通过积极的自修而获得一种内在生命的丰厚和精神的自由。一个有尊严的老者比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在应对生命的各种挑战时会更加得心应手。在此,老者的尊严来自其深厚的德性中自然生发出的德行,而缺乏与其年龄相匹配的德性的老者会被批评为“为老不尊”。这一批评提示,在儒家对尊严的理解中,尊严不是去时间化的,而是与时间紧密相关的。人作为时间中的存在者,若没有发展出与其年龄相称的德性,他的生命是缺乏(成就)尊严的。与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相比,儒家所提供的理解老去的这一维度有其独特的贡献,因为它更少诉诸人的身体机能,更多诉诸人的德性养成。
诉诸儒家的德性思想来论述老人可以享有德性的尊严,可能会招致批评说,这种思路会带来严重的排斥性问题,即那些缺乏德性的老人是没有尊严进而不值得尊重的。然而,儒家伦理号召人们去追求德性尊严,与它肯定所有人都享有地位尊严并不矛盾。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使人人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要求政府承认每一个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并基于这一道德地位给予其相应的对待。享有同等的地位尊严并不排斥每个人基于德性的修炼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尊严。成就尊严涉及一个人运用其能力过上了何种意义的生活以及对其生活如何进行伦理评价的问题。成就尊严就人获得道德地位而言不是必需的,但对于过一种美好生活而言它是可欲的。对老人而言,由于机能衰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因此,发展德性的尊严或成就尊严不失为一种化解老去的规范性困境的出路。它使得老人不仅是脆弱的被关怀者和被照顾者,还可以凭借其德性对生活意义的贡献而享有成就的尊严。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老人,不管是为子女家庭尽力操持的老人,还是活跃于社区参加志愿服务的老人,都在发挥生命余热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回避年老带来的规范性困境,但这一困境并非无解,我们的传统中有化解这一困境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体现出新的形式。与医学和社会学将老去界定为衰老的一种客体化思路不同,儒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去的内在的、伦理的视角。依据这一视角,年老并不只有丧失和衰退,年老还可能带来内在生命的丰厚和精神的自由。当然这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它需要人们为之付出道德努力,也需要社会为老人创造伦理生活的条件。所以,年老并不会必然导致尊严的丧失,因为尊严不仅取决于人的行动能力,还取决于人对其能力的运用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去维护老人的尊严。有尊严地老去对老人来说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这既需要老人通过积极的自修而获得一种面对生命的从容态度,也需要家庭和社会尊重老人的意愿和生活方式,为老人安享晚年创造条件。
最后,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讲,老去的焦虑和人之必死性相关。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是确知的,但何时何地死亡是不确定的。一种好的可能性是先行到死,看到沉沦于日常的操劳和操持,并重新激起了直面生活的热情,在向死存在中获得本真的生存的可能性[18](363)。按照这一理想,老年生活仍是可欲的,只要它活出了生命的连贯性、活力、深度和成熟这些维度[19](65)。但在儒学看来,生命并不只有本真与非本真两种截然区分的状态,我们并不必然要先行到死才可活出本真的自我,投身于日常生活的自我一直在不断地转化,从自然生长的趋向向伦理心境转化,最后走向道德自由之境[20](80)。在此意义上,老年可能通向伦理生活的成熟阶段。当然,老年有其特殊之处,在此阶段,随着我们行动能力的下降,我们积极外求的可能性变少了,但与此同时,我们沉思和反思的机会增多了。生命进行到此向我们敞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终于可以抛开世俗生活对我们的各种要求而享受生命纯粹的快乐了。回想一下孔子与弟子言志的场景,孔子向往的是曾晳所描绘的生活愿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7](109)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