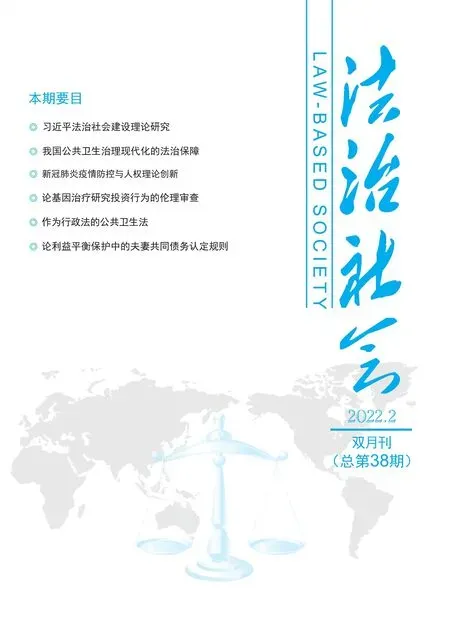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人权理论创新
王晨光 张 怡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着全球公众的生命健康,也是对各国人权保障的严峻考验。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形成了不同的抗疫模式,但取得的抗疫成效却大相径庭。这既有制度实践的问题,也有制度背后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人权观念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因素。因此,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所反应出的中西方人权观的差异,值得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推动人权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 是近百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着全球公众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各国政府都以人权理念为指引,推动本国的疫情防控。然而,实践中各国的抗疫效果却大相径庭。为何中国能够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抗疫成效,而一些发达国家却在疫情的冲击下摇摆不定、损失惨重? 这需要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权理论及其现实应用,结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推动人权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中的创新与发展。
一、人权理论的兴起及其内在张力
自二战结束尤其是 《世界人权宣言》 颁布以来,人权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学术界的显学,而且从宣言式的 “软法” 到一系列公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 “硬法”,逐渐发展为国际法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人权法,成为建构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之一。同时,人权理论也对战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权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各国的宪法和国内法,成为具有操作性的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体系。
(一) 人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在欧洲封建社会衰败和新兴市民阶层兴起的新老交替时期,人权的概念和理论逐步成型。1215年,英国 《自由大宪章》 首次提出了 “人权保障” 的概念。①参见[英] 詹姆斯·C.霍尔特:《大宪章》(第二版),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把“天赋人权” 作为其政治宣言。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 明确规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②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1776. https://uscode.house.gov/download/annualhistoricalarchives/pdf/OrganicLaws2006/decind.pdf. accessed 25 Feb 2022.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 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每个政治联盟的目标都是保护人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③See Declaration of Human and Civic Rights of 26 August 1789. 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sites/default/files/as/root/bank_mm/anglais/cst2.pdf. accessed 25 Feb 2022.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家和革命家们对于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主张,奠定了西方人权理论发展的基调。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权利的确立。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列宁起草的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被载入1918年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明确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和免费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④参见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1918年)》 载明德公法网,http://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119,2022年2月22日访问。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 第二编 “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 不仅全面详尽地规范了公民权,还纳入了受教育权、健康权等大量经济社会权利。⑤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Reich / August 11, 1919 / Translation of Document 2050-PS / Office of U.S. Chief of Counsel.
1941年1月6日,带领美国逐步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的“四个自由” 理念。⑧See Franklin Roosevelt, ‘The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6 January 1941). http://avalon.law.yale. edu/20th_century/decade01.asp. accessed 25 Feb 2022.其中,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属于传统的权利法案的内容,而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则属于新兴的经济社会权利,为罗斯福总统推行的 “第二权利法案” 奠定了基础。⑨参见龚刃韧:《〈联合国宪章〉 人权条款的产生及其意义》,载 《人权研究》 2020年第1 期。尽管他未能在任期内将这些权利纳入美国宪法,但是其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后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时,进一步将 “四大自由” 所代表的 “第二权利法案” 纳入了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 的序言之中,更是奠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类型和相关国际公约的产生。⑩参见[美] 玛丽·安·葛兰顿:《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刘轶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 页;[美] 凯斯·桑斯坦:《罗斯福宪法: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毕竞悦、高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77 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实行的侵略战争促使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揭示了关注人自身权利的自然法理论在法学界复兴。与自然法理论复兴同步,或者说作为其中主要部分之一的人权法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发展。1946年,联合国在起草 《世界人权宣言》 过程中,由于各国代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差异甚至对立,各国就哪些权利构成基本人权展开了激烈而又冗长的争论。值得庆幸的是,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不仅把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传统权利列为基本人权,也把受教育权、健康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纳入其中。⑪参见王晨光:《健康权——当代卫生法的基石》,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9年第2 期。随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 《经社文权利公约》) 以及一系列区域性人权公约相继出台,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战犯法庭(前南、柬埔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和区域性机构陆续成立。尽管人权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理论争议,其法律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但这些国际人权文件的出台和国际人权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人权理论以及相应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和制度正在逐渐形成。
(二) 人权理论的内在张力
人权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人权究竟包含哪些权利? 如前所述,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世界人权宣言》 起草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权利导向,《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和《经社文权利公约》 就是不同权利导向的产物。围绕人权的具体划分,中西方学术界展开了激烈论争。
1. 不同权利导致人权理论内在的张力
人权是一个集合概念,人包含众多具体的权利,例如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健康权。根据不同的标准,人权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首先,根据人权的内容是否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可以将人权分为“永久性人权” 和“阶段性人权”,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永恒不变的人权,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人权。其次,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可以把人权划分为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民主性人权” 和基于东方发展中国家集体主义的 “庇护性人权”。再次,根据是否需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为标准,又可以将人权划分为“消极人权” 和“积极人权”。消极人权是指不被政府干预、限制和妨碍的人权,而积极人权则是指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人权。传统西方人权理论认为,无需政府干预即可实现的消极人权才是真的人权; 那些需要政府、社会和其他人帮助,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人权,不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和纯粹自由市场理论。因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健康权等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实现的积极人权不是真正的人权,而是政府公权力的扩张。⑫参见王晨光:《健康权理论与实践的拓展》,载 《人权》 2021年第4 期。
此外,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代际人权的概念。⑬参加钱继磊:《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5 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是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相对应的概念,确立的是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则形成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确立了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第三代人权则源于二战后亚非拉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代人权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集体权利为核心,具体包括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等。⑭参见蒋银华:《新时代发展权救济的法理审思》,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5 期。
2. 当代学者的反思及批判
人权的二元划分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批判人权二元划分存在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论证的,即便是传统西方人权理论所认为的消极人权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例如,政府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和机制,提供配套的资源和服务,并通过公权力来进行规范和处罚,以确保人格权、人身权、选举权等消极人权的实现。⑮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 《清华法学》 2012年第4 期。因此,消极人权和积极人权不是绝然分割或绝对对立的。正如在1993年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达成的共识,一切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地对待人权。因此,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要与传统的自由权一样,能够获得司法救济。
当前,那些把消极人权与积极人权完全对立,甚至否定积极人权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观点在国际人权学界已经式微,但是在各国人权保障实践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影响,有时甚至成为不同团体和族群对立的因素。这种现象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也可见一斑,值得人权理论界和法学界深思。
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发生以来,严重威胁着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为有效应对疫情,各国政府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人权理念为指引,推动本国的疫情防控。然而,实践中各国的抗疫措施则五花八门,效果也大相径庭。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2月23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逾4.24 亿例,死亡病例达589 万例,⑯数据来源:https://covid19.who.int/,2022年2月23日访问。其中中国确诊病例约27 万例,死亡6066 例。⑰数据来源:https://covid19.who.int/region/wpro/country/cn,2022年2月23日访问。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冠确诊和死亡人数却高居不下。以美国为例,截止2月23日,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约7773 万例,死亡病例高达92.6 万例,百倍于中国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确诊和死亡总数的六分之一。⑱数据来源:https://covid19.who.int/region/amro/country/us,2022年2月23日访问。为何中国能够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抗疫成效,而某些自喻为人权卫士、以健全的人权保障体系著称的发达国家却在疫情的冲击下政策反复不定,应对不力致使人员伤亡惨重? 这不得不使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从这一角度讲,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每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各国人权保障体系的严峻考验。
(一) 中国防疫中的人权保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响应,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价值理念,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要考虑的战略地位,由财政兜底对新冠肺炎患者施行免费救治,坚决做到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实现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这不仅是党和国家明确提出的政策指引,更是贯彻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规定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 和“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的核心理念,以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的方针。⑲参见前引⑫,王晨光文。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全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疫情防控成效斐然,再次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⑳参见秦刚:《抗疫斗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载 《求是》 2020年第12 期。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认为,“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全社会防控措施成功避免或者至少预防了全国范围内数十万病例的发生。”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联合考察报告》,2020年2月29日。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不难看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健康; 也只有充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权,才能实现对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因此,不应割裂地看待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甚至将两者对立。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人权的最大化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履行了国际合作与援助的国际法义务,尽己所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帮助。目前,中国已累计向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20 亿剂新冠疫苗,确保了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履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团结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 西方防疫中的人权困境
为应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国也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例如,作为欧洲第一个面临新冠疫情蔓延的国家,意大利在全境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紧急管控措施; 此外,意大利还积极借鉴中国抗疫经验,搭建方舱医院以更好地收治新冠患者,缓解当地紧张的医疗资源,防止出现医疗挤兑的情况。然而,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把维持其执政地位放在首位,首先保证的是如何使其大选不受干扰;还有的国家首先考虑地是如何确保经济发展不受疫情影响; 有些国家则担心疫情冲垮其医疗卫生体制,结果导致 “该收不收”; 还有些国家不愿意把更多资源投入防疫,甚至采取群体免疫的消极策略。从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看,这些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同时,也反映了这些国家没有履行国际人权公约和本国法律所规定的保障生命权、健康权的积极义务。
以美国为例,尽管在新冠疫情初期,特朗普政府从武汉高调撤侨并关闭了美国驻武汉总领馆,但却一直未在美国本土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㉒《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720965/1720965.htm,2022年3月17日访问。事实上,早在2020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预警了新冠疫情在美国大流行的风险,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卫生官员和医学专家也多次发出警告,但特朗普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反而为了谋求连任而发布虚假疫情信息,误导美国民众。㉓中国人权研究会:《新冠肺炎疫情凸显 “ 美式人权” 危机》,载 《人权》 2020年第4 期。直到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才宣布美国因进入紧急状态,㉔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Concern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 Outbreak.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declaring-national-emergency-concerning-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outbreak/. accessed 16 March 2022.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窗口期。最终,以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完备的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体系著称的美国,新冠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高居各国之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因新冠疫情,2020年美国人均期望寿命较2019年减少1.5 岁,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大降幅。㉕US C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Declined a Year and Half in 2020. https://www.cdc.gov/nchs/pressroom/nchs_press_releases/2021/202107.htm. accessed 16 March 2022.这一结果显然是特朗普政府漠视美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权益而造成的。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坚持 “本国优先” 原则,奉行 “疫苗民族主义”,大量囤积疫苗,导致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免疫鸿沟” 不断扩大,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抗疫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就此问题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 次会议上敦促国际社会公平分配新冠疫苗。他还特别强调,“维护疫苗公平就是维护人权,而纵容疫苗民族主义就是罔顾人权”。㉖聂晓阳:《联合国秘书长:纵容疫苗民族主义就是罔顾人权》,载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408237432395023&wfr=spider&for=pc,2022年3月16日访问。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理论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坚持生命至上、促进团结抗疫是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权的应有之义。生命健康权是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㉗和音:《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载 《人民日报》 2021年7月13日第3 版。但在理论上,健康权与生命权之间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生命权一项不证自明的基于人之本性的天赋权利,㉘参见易军:《生命权:藉论证而型塑》,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1 期。对于生命权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健康权本身的权利品质,因此,有必要对健康权的来龙去脉展开必要的说明。
(一) 健康权的由来与发展
1. 健康权的历史发展
健康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才出现的现代权利。二战前,与健康相关的权利通常被归为社会权在个别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得以体现,但并未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出现。㉙参见前引⑫,王晨光文。例如,英国为应对圈地运动造成的贫困等社会问题而颁布的 《济贫法》(1601年),为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提供了基本保障。㉚See Lorie Charlesworth. Welfare’s Forgotten Past: A Socio-Legal History of the Poor Law. Routledge-Cavendish, 2009.墨西哥《宪法》(1917年) 明确了政府保障公共卫生的责任。㉛The Constitution of 5 February 1917.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exico_2007.pdf.accessed 22 Feb 2022.德国 《魏玛宪法》 第161 条规定了有关公共卫生和健康保险的社会经济权利。㉜Se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Reich / August 11, 1919 / Translation of Document 2050-PS / Office of U.S. Chief of Counsel.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nur01840.accessed 22 Feb 2022.1936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则对公民健康权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该法第120 条明确,“苏联公民在年老、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享受物质保证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保证是:广泛发展由国家出资为工人和职员举办的社会保险事业; 实行劳动者免费医疗。”㉝参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1936年)》,载明德公法网,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4102,2022年2月22日访问。
如前所述,二战后人类社会对大规模种族灭绝以及毫无人性的活体试验等战争暴行进行了深刻反思,健康权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 《经社文权利公约》 和其他一系列国际和区域性人权公约中。㉞承认健康权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5年) 第5 条; 《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1979年) 第11 条、第12 条和第14 条; 《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 第12 条;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年) 第25 条。承认健康权的区域性人权文书包括:《欧洲社会宪章》(1956年) 第11 条;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 第16 条。至此,“健康权” 作为区别于 “生命权” 的新型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中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在多数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并逐步建立起了以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为基础的健康权国际法律体系。在人权公约的示范和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健康权纳入本国宪法和法律之中。即使没有把健康权纳入本国法律的这些国家,在制定卫生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健康权的影响。㉟关于健康权实证化的模式总结与梳理,参见李广德:《健康权规范实证化的类型展开》,载 《人权》 2021年第4 期。目前,全世界共有171个国家批准了《经社文权利公约》;㊱OHCHR. Status of Ratification Interactive Dashboard. https://indicators.ohchr.org/. accessed 22 Feb 2022.109 个国家在其宪法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健康权。㊲See Eleanor D. Kinne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to Health: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ur Nation and World” , 34 Indiana Law Review, Issue 4 2001, p.1457, 1458.
2. 健康权的主要内容
《经社文权利公约》 第12 条被视为健康权的核心条款。该条文第1 款明确了健康权的定义,即“各缔约国承认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权利。” 第12 条第2 款列举了各缔约国为实现健康权应当采取的若干步骤,其中包括“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 以及“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㊳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 , Fact Sheet No. 31, The Right to Health, June 2008, No. 31.也即是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经社文权利公约》 各缔约国有义务尽其可提供的最大资源以充分实现健康权,包括传染病防控和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200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 《第14 号一般性意见》(General Comment No.14),对 《经社文权利公约》 第12 条进行了权威阐释,清晰且完整的健康权概念逐渐在国际人权法层面上形成。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4 号一般性意见: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公约》 第十二条),载于E/C.12/2000/4 号文件。针对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第14 号一般性意见》 明确,在突发事故、传染病和其他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公民有获得治疗的权利。各缔约国有义务建立一套医疗卫生应急制度,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各缔约国还应独自或者通过共同努力来控制疾病,包括提供相关技术,执行和加强免疫计划以及其他传染病的控制计划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特别指出,采取措施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以及对社区出现的主要传染病进行免疫接种是各缔约国应当优先履行的义务。
3. 健康权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发展
虽然我国宪法没有明确采用“健康权” 三个字,但如果对宪法进行体系性解读,不难发现一系列保障人权、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条款,为健康权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规范内涵。㊵对我国宪法中的健康权规范的梳理与建构,其代表性的文献和分析,参见陈云良:《健康权的规范构造》,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5 期; 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年第1 期; 高秦伟:《论作为社会权的健康照护权》,载 《江汉论坛》 2015年第8 期; 李广德:《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载 《云南社会科学》 2019年第6 期,等等。首先,我国《宪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同时,根据 《宪法》 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国家应当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从而增强人民体质、保护人民健康。
2019年12月28日通过并于2020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健康权,彰显了国家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决心。该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这一条款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保障公民健康权实践的法律凝练和理论总结,也是对宪法中健康权保障相关内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的健康权主要包括:公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获得紧急医疗救助权、个人健康信息权、健康教育权、医疗服务知情同意权、特殊群体健康保障权、健康损害赔偿权等权利。㊶参见王晨光、张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的功能与主要内容》,载 《中国卫生法制》 2020年第2 期。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六十九条特别规定,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公民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利和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 生命权与健康权在疫情防控中的价值优位
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中西方不同的人权价值观和人权保障的侧重点。人权是一个集合概念,人权概念下包含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健康权等各种具体的人权。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不难看出,面临全球大流行病等应急情况,全社会尤其是决策者如何看待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它们与其他权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尽管各国都高举人权旗帜,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保障人权,但由于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宣扬所谓的消极人权,否认积极人权的重要性,加上某些伪科学的误导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导致一些国家和民众在此次疫情防控进程中把自由权、集会权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为最主要的人权; 而生命权和健康权则有意无意地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使得防疫措施无法完全落地,从而导致疫情反复无常,出现大量死亡病例的可悲局面。与之相比,中国始终将生命权和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㊷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 页。为此,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的 “动态清零” 防疫策略虽然暂时限制了个人的出行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第6 条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1984年通过的 《第14 号一般性意见》 中进一步指出,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是在社会紧急状态下也绝不允许减损的最重要的权利。㊸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14: Article 6(Right to Life)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Right to Life, 9 November 1984.随后,该委员会在其《第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年) 再次强调,生命权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生命权得到有效保护是个人享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㊹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6: Article 6(Right to Life), 3 September 2019, CCPR/C/GC/35.换句话说,没有生命,自由权等其他人权也就失去了实际承受的主体。另一方面,生命的最佳状态有赖于健康,没有健康的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或毫无质量的生命。没有健康,个人就无法充分享有其他各项权利,甚至会丧失其他权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冠病毒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极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在疫情等紧急状态下,生命权与健康权紧密相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命健康权在众多人权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即生命健康权处于权利体系的首位。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发布声明,要求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各缔约国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境内所有个人及受其管辖的所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即使这些措施可能对享有公约所保障的其他个人权利造成限制。㊺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tatement on Derogations from the Covena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 Human Rights Committee, 30 April 2020, CCPR/C/128/2.
(三) 疫情防控中的人权冲突及其平衡原则
当发生全球大流行病等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突发事件时,生命健康权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基本权利产生冲突。例如,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而对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实施隔离治疗,从而对其人身自由权构成一定限制。生命健康权的价值优位意味着,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卫生或其他公共利益的目的,对自由权、经济权等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以便优先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权。
国际人权公约为生命权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健康权在人权体系中的价值优位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事实上,《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起草委员会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就认识到了不同人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因此特别设置了权利克减(derogation) 条款。㊻See Laurence R.Helfer.Rethinking Derogations from Human Rights Treati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51) 2021(1): 20-40.该公约第4 条第1 款明确,“如经当局正式宣布紧急状态,危及国本,本盟约缔约国得在此种危急情势绝对必要之限度内,采取措施,减免履行其依本盟约所负之义务,但此种措施不得只触其依国际法所负之其他义务,亦不得引起纯粹以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阶级为根据之歧视。” 简而言之,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威胁国家安全的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nation) 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根据公约第4 条第2 款规定,某些基本权利即使在危机国家安全的紧急状态下仍不得克减。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不受酷刑的权利、不受奴役的权利、非因不履行法定义务不受监禁、罪刑法定、人格尊严以及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 也包含了类似的权利克减条款。㊼参见刘小冰:《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的逻辑证成》,载 《法学》 2021年第7 期。实践中,已有近30 个国家通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和美洲国家组织,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相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由迁徙权、集会权等人权的减损。㊽See Laurence R.Helfer.Rethinking Derogations from Human Rights Treati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51) 2021(1):20-4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任意扩张行政权,无限制地减损其他权利。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利克减和限制条款,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了 《关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限制和克减条款的锡拉库萨原则》,明确了限制和减损人权应当遵循的程序和一系列原则,包括合法性、严格必要性和比例原则等。㊾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e 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8 September 1984, E/CN.4/1985/4.
结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本文认为,当政府在紧急(应急) 状态下为保障生命健康权而限制其他权利时,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 法治原则
首先,政府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启动和解除紧急(应急) 状态,采取行政应急措施控制和消除突发事件。法治原则又进一步分为: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和高效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权; 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国家法律予以限制; 防止粗暴执法和乱执法。比例原则要求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必须强度适当,并且采取该措施可获得的利益应当大于可预见的风险和损失。高效原则强调高强度和超常规的机制运行,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为标准。
2. 生命健康权优先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也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基本理念和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的方针。因此,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优位原则应当成为所有应急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相比较,人民的生命健康应被置于第一位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得到贯彻,即落实法律规定的“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
3. 以科学为基础的原则
政府所采取的所有应急措施都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依靠科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在此基础上采取最恰当的应急防控措施。
除了要坚持上述基本原则以外。还应当统筹推进防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疫情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生命权和健康权与其他人权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要高度关注生命权和健康权与其他人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强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首要地位,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隐私权、劳动权、自由权等其他人权的保障,而是意味着要正确理解各种人权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决然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一定情况下一段时期内的首要地位,也并不意味着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遭遇到风险,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障也就无法得以落实。因此,我国在防疫过程中提出的防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既突出了在疫情防控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首要地位,也强调了其与其他人权之间的协调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及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政策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果,也对人权理论中出现的新问题,即如何协调各种人权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动态调整各种人权的轻重排序,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