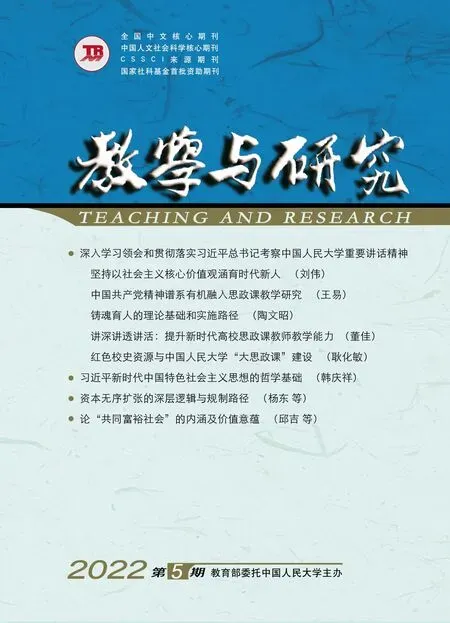社会哲学视阈中的需要与主体性
——卢梭、黑格尔与马克思*
任劭婷
如何理解主体(subject)与主体性(subjectivity)概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始终存在着一些相互竞争的,但却并未被明确区分开来的讨论层次,这种情况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理论困难。近些年来,由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强势,主体问题更多的是在政治主体和革命主体的意义上被讨论,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朗西埃、拉克劳、墨菲、哈特和奈格里等一众思想家对革命主体的理论建构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一激进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激活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或重塑一种新的革命主体。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问题的批判性讨论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从社会哲学视角出发的经典路径,这一路径既不同于上述激进政治理论,也不同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在社会层面批判性地考察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体性生成的困境,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病症进行诊断。莫伊舍·普殊同在论及社会哲学的不可化约性时也强调了它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区隔,即“由资本所决定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功能物;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无法被缩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1)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0.。具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主体必须首先是生产劳动的主体,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是权利的主体或革命的主体,与此相对,社会哲学中的主体则首先被理解为需要的主体或欲望的主体。本文正是从这一社会哲学的视阈出发,将其理论奠基上溯至卢梭,并集中讨论了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社会哲学层面对需要和主体性关系的看法及其理论交锋。
一、需要的扩张与自在主体的败坏
卢梭被霍耐特视作“社会病理学”的理论奠基人,这个称谓意味着,卢梭对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性分析切中了要害,成功地将“社会病症”这样的观念植根于社会哲学之中。卢梭笔下的社会病症主要在于现代社会内在具有促使个人需要无限扩张的倾向,这一倾向一方面使人们远离了原初自由,另一方面使人们不再珍视共同体价值。但正如卢梭在《爱弥尔》扉页上引述的塞涅卡的词句,他坚信我们身患的是“一种可以治好的病”。今天的研究者或许并不会赞同卢梭后来在《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著作中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诊治方案,并对在某种程度上深受卢梭鼓舞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恐怖统治耿耿于怀,但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由启蒙精神构建起的现代社会中,就无法对卢梭的批判视角和提问方式视而不见。卢梭在当代政治与社会理论中是持续在场的:一方面,卢梭对现代社会中异化现象、私有制问题和实质不平等的揭示构成了当代激进左翼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右翼学者也很难绕过卢梭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批评,只得转而将这些批评整合进自由主义的自我矫正之中。因此,在当代重新理解卢梭的批判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
卢梭对现代社会的全部批判都建立在抽象自然人性的假设之上,在他看来,“一切欲念的本源,唯一同人一起产生而且终生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爱。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而且,从一种意义上说,一切其他的欲念只不过是它的演变。”(2)[法]卢梭:《爱弥尔》,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18页。作为欲望本源的“自爱”(amour de soi)在卢梭的理解中本无所谓善恶,有的只是“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亦即自我完善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将卢梭的人性论立场归结为性善论是不够确切的,卢梭的自然状态之所以是和平状态并不是因为人天性善良,而是因为自然人极其局限的欲求。所以普拉特纳认为,卢梭对人性的评价甚至更低于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看法,“自然人过于简单(即愚昧),以至于只有最基本的欲望。这些欲望是如此的容易满足,因此,他们没有陷入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3)[美]普拉特纳:《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尚新建、余灵灵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现代社会的顽疾被卢梭归因于人性中的另一倾向,即amour-propre(4)在通行的中译本中,amour de soi一般被译为自爱,而amour-propre的译法则有较大争议,比较常见的译法有:自尊、自利、虚荣、骄傲、自私等。,amour-propre与amour de soi不同,我们已经说明,后者所指的乃是自我保存意义上的自爱之心,亦即对自身生命的关心,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并无差别;而前者则指向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人为的感情,它改变了人最初的目的,使人脱离自然、同自身相矛盾。这种由于与他人的比较而催生感情使“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得比他人为重,它促使人们互相为恶,它是虚荣心的真正源泉”(5)[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0页,译文有改动。。只知自我保存的野蛮人虽然也会有争夺食物的情况,但是这种打斗却并不是为了分出高下,“打赢了的人就吃,打败了的人就到他处另想办法:一切又都归于平静”。(6)[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对于文明社会中的人而言,仅仅获得生活必需品却是不够的,无止境的欲望会带来无止境的争夺,这是“越多占有越好的问题,然后是享乐问题、积聚巨大的财富问题和拥有更多的臣民及奴隶问题”(7)[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
野蛮人始终是卢梭诊断现代病症的重要参照维度,卢梭说:“野蛮人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8)[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当以这样的野蛮人为标尺时,卢梭就把现代社会中欲望的扩张归咎于理性和知识的进步。在这里,卢梭抛弃了自古希腊以来以理性节制欲望的实践伦理传统,认为理性非但不能承担亚里士多德所寄寓的对欲望进行“建议、责备或劝诫”的职能,反而是刺激欲望发展的重要诱因。卢梭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就已经表达了我们的灵魂会随着科学理性和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观点。当然,卢梭并不是一位反理性主义者,他坚信自己谴责的并不是科学理性本身,而是“要在有道德的人面前捍卫美德”(9)[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并且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要求不能复返于自然状态的人类依靠自己的内在理性而不是屈从于外在权威。但卢梭仍然在自己的学说中保留了对理性的审慎态度,究其根源,这份审慎乃是因为启蒙之理性早已不再是至上至善的价值理性,而是如休谟所言,是作为“激情的奴隶”的工具理性。卢梭认识到,这样的理性并无为现代道德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可能。
卢梭进一步认为,正是在生产活动的历史性发展中,需要找到了它无限扩张的现实基础。如果野蛮人永远只是独立完成劳动而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就不会产生日益繁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分工的发展破坏了人的“天性所许可的自由自在的美好的幸福生活”(10)[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卢梭以历史性视角描述了分工的发展过程,最初产生的分工表现为家庭内部的两性分工,这时人类的需要仍然十分有限,他们由于简单分工的产生和技术的发明开始能够拥有一定量的闲暇来追求物质的舒适享受,而当这些舒适享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习惯之时,它们就会成为“不可或缺的真正的需要”。卢梭评论道:“因得不到这些享受而感到的痛苦,远比得到它们而感到的乐趣大得多;失去那些享受固然不幸,而得到那些享受,也不怎么感到幸福。”(11)[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在社会分工随着冶金和农耕技术的使用逐渐普遍化之后,人类的欲望突破了自然需要的边界。此时,充斥现代社会的已经不再是自然的需要,而是“许许多多没有任何自然基础而是从新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为的欲望”。(12)[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卢梭说:“尽管自然的需要已经满足,但欲念却有无穷的奢望”。(13)[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这种奢望一方面源于对物质享受的贪恋,另一方面源于对外界承认的渴求。“奢侈之风,在那些贪图享受和希望得到他人艳羡的人当中,是无法防止的;由社会开始的弊病,经奢侈之风一吹,愈来愈严重。”(14)[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37、62、96、92、122、59-60、140页。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以下简称《一论》)与《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以下简称《二论》)中对欲望扩张的危害采取了不同的批判角度。《一论》以古代国家为参照,卢梭对奢侈的批评直指现代社会的商业道德,他将麦隆在《论贸易》中以奢侈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作为靶子,严厉抨击发展商业和追逐金钱有损于社会风尚和公民道德,使公民与“公共善”相分离。而《二论》则以自然状态为参照,卢梭对奢侈的批评指向了人为的、不知餍足的欲望对个人自由的损减。在卢梭那里,只有自然需要的野蛮人反而是更自由的,这种自由在于他们可以不受社会和他人的制约,随心所欲地依凭自己的天性与喜好行事。相比之下,现代人各种人为欲望的满足则要全面依赖社会和他的同类。更重要的是,虚荣之心或骄傲之心都是外向满足的,当现代人将他人的尊重作为欲求目标时,他就“把别人的脸色看作一把尺子:这种人对自己是不是幸福,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而是看别人对他所流露的表情。所有一切差别的真正原因在于:野蛮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终日惶惶不安的文明人的生活价值,是看别人的评论而定,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是以别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看法的依据的。”(15)[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3、62页。概而言之,无论是《一论》中的“古代国家”还是《二论》中的“自然状态”,都作为卢梭理论中规范性的价值维度审判着现代性的病态,而这也正是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卢梭用以攻击现代性的两种古典观念。(16)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58页。
二、需要的殊多化与自为主体的生成
卢梭曾是黑格尔在图宾根读书时最喜爱的思想家之一,但是随着青年黑格尔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阅读和接纳,他迅速远离了同时代人对卢梭的浪漫主义解读,并以承认现代自由的基本信念回应了将卢梭的“自然状态”或是“古代国家”浪漫化的历史复古主义论调。在我看来,正是黑格尔在这种思想转变中体验到的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为他提供了以体系性方式来调和诸矛盾的重要思想动因,不久之后的耶拿时期,黑格尔开始了他构建体系哲学的第一次理论尝试。
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到过一种以自然状态为纯洁无暇、以未开化民族之风俗为古拙质朴的思想,并批评道:这种思想“对于精神的本性和理性的目的一无所知”(17)。在这个对卢梭和浪漫派不点名的批评中,黑格尔针锋相对地指出,自然状态所谓的质朴风俗所包含的其实是“消极的无我性”及“知识和意志的朴素性”,精神必须在外化过程中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迈进,只有这样,“精神才会在这种纯粹外在性本身中感觉自己安若家居”(18)。这个理论交锋触及了欲望与自由的关系。黑格尔和卢梭的分歧在这里再明显不过了:对于卢梭这样崇尚自然状态的启蒙异数而言,自然的就是自由的,只有在自然状态中人才是只服从于自身的自由存在,这无疑也正是卢梭和他的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论争不断的重要原因。自然自由的核心在于“免受欲求之累”,而黑格尔则要求将自然与自由切割开来。对黑格尔而言,自然的东西是冲动、情欲和倾向等等,自然状态非但不是值得回溯的原初自由,反而只是精神的纯粹虚空,精神首先要走出自身以去除自然的质朴性。黑格尔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主体性的发展就无所谓自由,看似只顺从自己天性的野蛮人的自由实则是一种虚空的“任性”。卢梭的抽象人性论并不能给主体性提供生长的土壤,真正的主体性必须在对客观对象的以劳动为中介的扬弃中才能达到,而这正是黑格尔所认可的现代自由的基础。
就需要的产生和特性而言,卢梭设定的野蛮人只能感知“真正的需要”。他“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在宇宙中,他所知道的好东西,是食物、女人和休息;他所畏惧的唯一灾难,是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死亡,因为动物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惧,是人在脱离动物状态以后所获得的最初的知识之一”(19)[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3、62页。。这样局限性的需要使得卢梭赞美的野蛮人成为了“类动物”的存在。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人要证实自己作为“精神”的普遍性,就必须要越出动物局限性的需要及其同样局限性的满足需要的手段,“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2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2、202、205页。如果只局限于这两个文本片段的对比,我们很可能会把黑格尔和卢梭的对立单纯理解为关于“需要与自由”或者“需要与主体性”的意见之争,但是这里真正需要被讨论的,实际上是卢梭与黑格尔的观点介入现代社会的方式。卢梭诚然知道,风俗一经败坏,人类就永远不能复返于原初的自然状态,野蛮人的设定毋宁只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味的留恋,它仅仅代表了卢梭用以批判现实的价值维度。但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生命力却在于他要求自己的批判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而非超拔于社会现实之外,也因此,卢梭这种将“是”与“应当”割裂开来的讨论方式本身必然不能使黑格尔感到满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更具历史性的视角讨论了动物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的区分,他说:“人有居住和穿衣的需要,他不再生吃食物,而必然加以烹调,并把食物自然直接性加以破坏,这些都使人不能象动物那样随遇而安,并且作为精神,他也不应该随遇而安。”(2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206、206、206、208页。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人类由于越出了动物局限性的需要及其满足手段已经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困扰,都只能在社会的现实本身之中去寻求解决之法。
与卢梭类似的是,黑格尔同样关注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需要无限扩张的基本倾向,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单个需要被细分为若干需要;品味愈发精致,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区分”(22)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translated by Leo Rau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黑格尔在成熟时期的《法哲学原理》中仍然保留了《耶拿实在哲学II》中的判断:随着现代社会对人的需要的细分,“为特异化了的需要服务的手段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也细分而繁复起来了,它们本身变成了相对的目的和抽象的需要。这种殊多化继续前进,至于无穷……总的说来,就是精炼(Verfeinerung)。”(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206、206、206、208页。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黑格尔没有像卢梭一样仅仅把这一过程理解为需要的无差别扩张,而是将之描述为需要的扩张和需要的殊多化交织在一起的过程。黑格尔认为,文明陶冶的作用就在于把具体物分解为它的特殊性,当人被教化出具有“能理解差别的理智”时,需要就开始逐渐和脱离纯粹生存的领域,成为了精神的需要——“趣味和用途成为判断的标准,因此需要本身也受其影响。必须得到满足的,终于不再是需要,而是意见了。”(2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206、206、206、208页。这个区分的意义在于,一旦趣味与用途成为判断的标准,需要就不再仅仅是单向度的扩张,还存在着需求内容的差异。那么,卢梭对于需要扩张之后果的判断,即“愈不是自然的和紧迫的需要,想得到的心反而愈急;更糟糕的是,为满足这种需要而使用的暴力也越大”(25)[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页。,就不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在黑格尔看来,需要的殊多化反而有可能导向对欲望的抑制,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使用多数东西,那末他们对任何一种可能需要的东西的渴望心理,便不会那末强。这就表明需要本身一般说来不是那末迫切”(2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206、206、206、208页。。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动物性的需要是即时满足的,而人类可以延迟满足。现代社会中需要的殊多化和扩张未必只能导向非理性狂热,相反,黑格尔意在指出,殊多化了的需要使得人们有可能以一种更加平衡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与被需要的客体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和卢梭更为重要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对满足需要的手段的评判上。对卢梭而言,野蛮人因其需要本身的局限性而远远未触及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所以,他的自由也就体现为可以随心所欲地直接从大自然获取所需之物的自由。而黑格尔认为,将使用自然直接提供的手段来满足需要视为自由,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劳动所包含的解放的环节”,“自然需要本身及其直接满足只是潜伏在自然中的精神性的状态,从而是粗野的和不自由的状态,至于自由则仅存在于精神在自己内部的反思中,存在于精神同自然的差别中,以及存在于精神对自然的反射中。”(2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6、206、206、206、208页。在黑格尔看来,未经教化的野蛮人与熟练工人的区别恰恰在于野蛮人不会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将对象性事物改造为自己所需要的样态,也就是说,他不具备把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现实化的能力。而经过教化的熟练工人则可以生产出他主观上所期望的东西,从而在劳动对象化的过程中肯定自身,这种从实践教育中传达出的劳动的解放意义是黑格尔肯定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根据。在这个出色的论证中,卢梭有关“需要的扩张对主体性的败坏”的命题被黑格尔以“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中介环节)对主体性的生成”的命题代替了,这个视角的转换不仅使黑格尔超越了卢梭的自然自由,而且超越了仅仅在谋生活动的意义上理解劳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三、需要的满足手段及其抽象化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主奴辩证法”的隐喻对劳动概念作了哲学化改造,从而使之具备了交互承认与形式解放的意义,这也成为了黑格尔论证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哲学基础,并最终使得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呈现出与卢梭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主人、奴隶、物这三者之间,主人与物的关系同卢梭笔下野蛮人对自然的直接享用非常类似。这是因为,主人把奴隶放在了自己与物之间,主人与物的关联由此转变为未经由自身劳动的对物的直接享用。一方面,主人通过对奴隶的支配认识到自己得到了奴隶的承认;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由于奴隶在生死斗争中被还原为一个以物性为本质的意识,主人所获得的也就仅仅是以物性为本质的意识的承认,这种承认是不完全的。而奴隶一方的解放则是通过劳动这种塑造活动来完成的,奴隶通过劳动扬弃了他对于自然实存的依赖性,将意志贯彻到劳动对象之中,并在劳动过程中认识到独立存在的其实正是他自己。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劳动不仅塑造外物,同时也塑造了主体自身。但常常被忽略的是,黑格尔在这里赋予劳动的解放意义仅仅是形式的,在主奴辩证法的最后部分,黑格尔说道:“它(指劳动——引者注)也不是一个普遍的塑造活动,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技艺,这种技艺只能掌控少许事物,但却掌控不了那个普遍的势力,也掌控不了整个客观本质。”(2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因此,这种仅仅具有形式解放意义的劳动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在《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和《法哲学原理》等黑格尔的政法类文本中,我们则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劳动仅具有形式解放意义”这一判断的现实来源。
黑格尔从耶拿时期开始就关注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抽象化问题,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出发,这种变化意味着劳动对主体性的塑造作用被大大削弱了。随着需要的殊多化和现代分工制度的形成,人的大部分需要的满足都要依赖于社会性的劳动分工,市民社会也首先表现为一个“需要的体系”。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劳动分工对生产力的增进,他在耶拿时期的手稿中引用了亚当·斯密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一家英国的制针厂需要18个人的劳动。每个人承担且只是承担该工作的一个特殊环节。单个人或许无法生产20枚针,甚至一枚针也生产不出来;将这18份工作分派给10个人可以在一天之内生产出4 000枚针。但是把这10个人的劳动分配给18个人,每天则可以生产出48 000枚针。”(29)但在摘录了这个例子之后,黑格尔话锋一转写道:“劳动变得极端死板,进而成为了机械劳动,单个劳动者的技能无限地被局限起来,工厂劳动者的意识也枯竭至最为愚钝的地步。”(30)G. W. F. Hegel, System of Ethical Life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nd T. M. Know,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9, p.248,p.248.与斯密不同,黑格尔关注的重心并不是生产力的提高,对他来说,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也许有利于财富的最大化,但却是以机械劳动对流水线工人的摧残为代价的。现代分工制度的直接结果是个人与自身需要的分离。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他所生产的并不是自己所需之物,他仅仅为了满足某种抽象的自为的需要进行生产。这种需要亦不同于“主奴辩证法”中主人的需要,它不来自于确定的主体,而仅仅代表了某种一般需要的可能性。需要的抽象化使为了满足该需要的劳动本身也成为了抽象的,而劳动的抽象化又进一步造成主体的抽象化。正如黑格尔所说:“因为他的劳动是这种抽象劳动,他也就表现为一个抽象的自我——按照物性的方式表现——而不是表现为一个富有内容,统治并主宰着广泛领域的全面的精神;他没有具体的劳动,他的力量在于分析,在于抽象并把具体的世界肢解为许多抽象方面。”(31)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translated by Leo Rau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21,p.166.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劳动者与他的产品相分离,产品不再是劳动者自我意志的外化,随着这种塑形(formieren)意义的丧失,抽象劳动也无法再生成真正的主体性了。上述对需要和劳动的抽象化的批判处于青年黑格尔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其中不乏与同样接触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青年马克思有十分相似的批判性的锋芒,而这一批判视角是像卢梭这样始终站在现代生产方式之外的理论家所无法具备的。令人遗憾的是,耶拿时期这些颇具先锋性的讨论最后都缩减成了《法哲学原理》第198节中“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3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250、206-207页。这样一个模糊的回声,而愈发难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了。
黑格尔担忧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主体间关系的异化,现代主体间的承认不是基于意志本身,而是基于个人所占有的外部财富。这种承认关系的异化与现代生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满足特定需要的具体劳动是多种多样的,为了表达抽象的物的价值、实现普遍的可比较性,就必须有一种代表一切需要的普遍物,而“货币就是这种物性的实存的概念,是一切所需之物的统一性或可能性的形式”(33)G. W. F. Hegel, System of Ethical Life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nd T. M. Know,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9, p.249,p.249.。随着货币在现代社会取得统治性地位,主体间承认的基础也就异化为这一中介物,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Ⅱ》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所拥有的货币决定着他的现实性。自我形象已经消亡。”(34)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translated by Leo Rau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21,p.166.现代社会要求个人“用外部表示来证明他在本行业中所达到的成就,借使自己得到承认。这种表示是没有限度的。”(3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250、206-207页。在某些段落中,黑格尔不仅把货币理解为“纯粹的象征物”,他甚至将之理解为一种运动中的社会关系,并以此提示了一个马克思式的资本化视角。黑格尔说:“上升到这种普遍性(指货币——引者注)的需要和劳动为自身在众人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一个死亡的身体的生命在自身之中盲目地来回运动,并像野兽一样需要经常严格地约束和驯化。”(36)G. W. F. Hegel, System of Ethical Life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nd T. M. Know,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9, p.249,p.249.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批判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关系的倒置,他在一个颇有消费社会理论意味的判断中说道:“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3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250、206-207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不是从主体出发,而是从资本增殖的需要出发;商品本身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是为了被买卖而存在。用后来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也正是这些在黑格尔的早期政治著作中既已存在的具有惊人前瞻性的批判视角使得马尔库塞把他看作第一个洞察到了现代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德国人。
如上文所述,国内关注程度较低的黑格尔《伦理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等早期文本支持了一种更为激进的作为社会哲学家的黑格尔形象。黑格尔的批判诚然尖锐而准确,但无论是在早年的《伦理体系》还是成熟时期的《法哲学原理》中,他都始终认为,上述种种异化的社会状况是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下得到“医治”的。在政治哲学层面,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涌动的特殊性之上架设了一个普遍性的伦理国家,并将其视为客观精神的最终实现;而在社会哲学层面,黑格尔所提供的市民社会内部解决方案的核心则是要在原子式的个人和同质化的现代社会中加入更多伦理性的中介,即同业公会和等级要素。在黑格尔看来,如果一个人是同业公会的成员,那么他就不再需要用外部财富的量的积累来证明自己是“某种人物”,而是可以用具体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获得共同体的承认,从而解决劳动抽象化带来的承认意义的丧失并获得其等级尊严。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等级概念不能被理解为封建等级观念,它并非完全由个人出身决定,而是与社会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对黑格尔来说,与具有等级尊严的人相对的是沉沦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的个人,是纯粹的私人,也即等级这一概念在黑格尔那里的首要意涵仍旧是伦理性的。
四、拜物教理论中的需要与主体性
受到卢梭、费尔巴哈等人的理论影响,马克思在其青年时期也将异化理论作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武器,但马克思并没有从抽象的自然人出发,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已经将自然状态视作18世纪流行的虚构,并认为“每个世纪都会产生出自己独特的自然人”(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到现实的生产活动中揭示了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并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40),主动澄清了他与卢梭消灭异化的路径的区别,马克思直指卢梭的自然状态实质上是“非自然的简单状态”。他说:“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296页。马克思把卢梭那里的文明悖论纳入辩证的历史运动之中,认为“社会病症”的解决不能在被浪漫化了的过去中寻找,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3页。。就此而言,当维塞尔在其名著《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中称马克思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时乃是越过了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侈谈批判资本主义这一共同的价值立场,因而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了。而这里的研究方法正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历史性方法。无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讽刺“封建的社会主义”是过去的挽歌,还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浪漫主义对原始的丰富的留恋,认为“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都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始终反对轻率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相反,他认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要重新占有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异化方式建构起来的物质和文明。
如果说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囿于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模式,着重批判主体生产的客体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主体相对立这一异化事实,那么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拜物教理论中,他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异化劳动下主客体的对立,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客观性外观的主体间关系对主体的统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构成的拜物教理论进一步清除了其早期异化理论的人类学意味。在这一视角下,需要作为一个与使用价值密切相关的人类学范畴退居幕后,需要(needs)的历史性扩张被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wants)所代替,资本篡取了主体的位置,成为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这一分析视角同样有助于我们回应一个颇有理论市场的对共产主义的诘难,这种批评的声音往往以人的欲求的无限性为根据,质疑共产主义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实现按需分配”只是乌托邦式的呓语。一方面,马克思确实认为人的需要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此,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都是历史性的。像卢梭一样把需要还原为自然人局限的身体需要、把需要的满足还原为对自然物的直接取用是荒唐的。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扩张的需要绝不能作为分析的起点,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这种扩张并非基于抽象人性,而是社会构建的结果,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方式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变革的。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需要的“恶无限”是资本逻辑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与禁欲主义无关,与提倡节俭无关,也不能像卢梭在《爱弥尔》中所做的那样,把“社会病症”的诊治回溯到对个人德性的教养。对于马克思来说,要使人的需要脱离资本增殖的欲望必须以社会结构层面的根本转变为基础。
拜物教理论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彻底划清了与浪漫主义还原论的界限,也使得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某些核心判断失效了。黑格尔期待需要的殊多化能够产生对欲望的抑制作用,然而在拜物教的统摄下,人们所欲求的对象实际上是高度同质的,殊多化的物的背后是前所未有的单一和匮乏——“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就是资本形而上学最赤裸裸的表达。在消费社会,欲望与个人真实的热情和渴望无关,它仅仅在消费的意义上被理解、被强调、被计算。在鲍德里亚所称的符号价值的支配下,无论我们购买物的物质载体是什么,实际上消费的都是物所象征的被资本力量所塑造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意象,这是一个以符号物的差异构建起的非人的体系,在这里难以觅得主体间质性的区隔,有的仅仅是物的差异的表象。
更重要的是,这种主体向物神的臣服不仅仅是社会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存在论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2页。的双重完成。拜物教的双重内涵在齐泽克的当代阐释中被再一次激活,并焕发了巨大的理论活力。齐泽克曾讲述过一个与此有关的笑话,一个精神病人因为觉得自己是一粒玉米而入院治疗,过了一阵子后他终于治愈出院了。治愈的标志是:他现在知道自己并不是一粒玉米,而是一个人了。但不久之后他又回来了,说:“我遇到一只老母鸡,我担心它会吃掉我。”医生努力使他平静下来问道:“你害怕什么?现在你都知道自己不是一粒玉米,而是一个人了。”这个精神病人则回答说:“我当然知道这个,但那只老母鸡也知道我不再是一粒玉米了吗?”(45)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笑话理解为意识形态层面的讽刺恐怕并没有理解齐泽克的全部意思,这个笑话道出的正是拜物教作为意识形态和客观社会结构的双重性。事实是,如果将人视为“一粒玉米”的社会关系本身不被颠覆,仅仅翻转人认知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又有何意义呢?这正是齐泽克在其相关著作和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拜物教观念恰恰是资本支配人的社会结构在人们意识中的真实反映,在这样的社会中,欲望“总是不满足的、转喻的、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对象的,因为我实际上没有欲望我想要的东西。我实际上欲望的东西是维持欲望本身,延迟其满足的可怕时刻。”(46)[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最后,在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上,黑格尔那些调和意味浓重的解决方案在马克思的分析视角下是行不通的。黑格尔对同业公会寄予厚望,把它视为社会成员的“第二个家庭”,视为构成国家的第二个伦理根源;但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统治的世界容不下任何伦理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同业公会作为以具体劳动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组织,只有在一个关注使用价值的生产结构中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实却是抽象劳动取代具体劳动,交换价值统摄使用价值,同业公会与社会基础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由此观之,同业公会不过是某种被黑格尔嫁接在了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古典因素。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与劳动力的关系从黑格尔所说的“机器替代劳动者”转变为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统摄劳动力”,劳动者沦为机器的活的附件。而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劳动本身的去技能化也意味着建立在对个人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艺承认基础上的同业公会的彻底破产。黑格尔显然低估了资本的力量,在资本推动下,现代社会向着巨大的同质化和抽象化不断挺进,破坏了一切伦理性共同体的壁垒。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建立政治性的或伦理性的壁垒,以期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情况下进行内部调整的企图最终都将铩羽而归。欲望的无限扩张和劳动的抽象化的根本解决必然要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指向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和劳动分工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