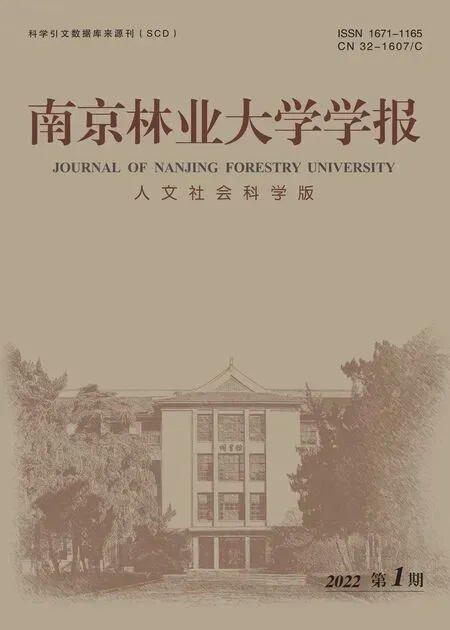“地方”与“自然”
——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刘亮程散文★
刘晓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任何作家和作品都不可能从真空中产生,具有地域色彩的自然经常进驻文本,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便使得自然书写在文学作品中占据大量篇幅,若讨论近年来的新疆文学和自然,刘亮程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作家。1995年,《天涯》杂志第5期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虽然此前他的诗作散见于文学期刊,但将这次亮相视为作家刘亮程的正式出场并不为过,从此,一个持续与家园、故土、新疆大地缠绵羁绊的西部作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专辑同时推出的推荐与研讨文章当即显露刘亮程的创作可能提供的言说空间,更有评论直接论及此次新疆书写中的自然,如李锐认为,正是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刘亮程才获得了对生命和语言的深刻体验;方方指出刘亮程散文唤醒了人类内心深处对万物的亲切感以及与草木为邻、与良禽为友的渴望。1998年,刘亮程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发行,此后多次增删篇目,几经再版,内容始终围绕他自己的生长之地——大漠深处的村庄黄沙梁。以黄沙梁为起点,此后十余年间,刘亮程开启了在新疆大地上的漫游,将视野从村庄生活扩展到城镇乃至新疆南北各地。2012年,散文集《在新疆》集合此前陆陆续续的关于库车城的书写,并延伸到北疆遥远的阿勒泰地区,作为整体的新疆进入了刘亮程的创作视野。无论是黄沙梁还是整个新疆,自然一以贯之地成为他的书写对象。
文学书写自然古已有之,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关怀更使人将目光聚焦自然,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开始重审既有文学作品想象、书写自然的方式,甚至催生了作为概念和文学类型的“自然写作”。刘亮程不曾将自己定位于专门书写自然的作家,人们也很难将刘亮程的散文归入严格的“自然写作”行列,但刘亮程的散文始终关怀自然,书写自然也是刘亮程散文始终保持在地状态的表征——扎根新疆、持续书写自己熟悉的新疆家园是他的愿望。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在新疆》,甚至包括小说《凿空》《捎话》等,刘亮程在新疆大地上辗转不停,而散文的创作轨迹最能直接、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身体位移及其带来的情感结构的转变。细读刘亮程散文中的自然书写会发现,前后十年,刘亮程的身体位移变化带来的人地关系变化最终影响了他对自然的感受和理解,新疆与自然的关系不只如以往地域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如文学作品体现何种地域特征,地域如何影响作家的审美取向或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基于不同的“地方”和“地方感”,自然书写内部呈现分化和变异。
一、“地方”:作为进入“地域”的一种方法
新文学诞生以来,区域空间内的自然便被捕捉进文本,只是自然往往扮演沉默的背景,较少受到关注。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提倡“乡土艺术”,提出“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周作人对地方风土的关注得益于其民俗学修养,“五四”落潮后,周作人的民俗研究越发回到个人兴趣上,从各地的饮食、植物、节日习俗等悟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的“自然之美”。1924年2月他创作的《故乡的野菜》细数春天的荠菜、黄花麦果、草紫,浙东气息拂面而来,文章虽云处处皆可为故乡,兴趣盎然的细述仍能传达周作人对生长之地的怀念。在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学尤其重视从对象社群中汲取在地文化持有者的情感态度、概念、文化观念等,周作人的“民俗学”虽然没有跟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分开来,但自觉进入地方内部,以内部视角观察地方的姿态和方式,在当时“启蒙”“大传统”不断抢占话语高地、意图向地方乡间社会进攻的境况下不可不谓罕见和珍贵。在文学创作上,以鲁迅的故乡书写为源起,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的乡土小说家们,共同抱持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策略进入乡村,乡土自然和恋乡情结仍难以抑制地从文本裂隙中洋溢而出,透出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厌地与恋地构成作家情感的两歧,地方自然在新文学发轫初期便如此被翻腾出台面,此后废名的黄梅竹林、沈从文的湘西山水、20世纪40年代北平诗人的漫天风沙、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直至近年来以刘亮程、李娟等人为代表的新疆作家笔下的自然风光,都延续着文学与地方自然的亲缘关系。
以往对文学作品中带有地方特质的自然书写的讨论和研究,往往从“地域”入手,考察自然书写的“地域色彩”。一方面是基于对自然物的归属、自然风景的描绘,认为地方自然是增添“地域色彩”的独到工具,一地自然物的出现使文学作品兼具对地方风土的认知功能和描摹风景的审美趣味。如“地方色彩”“风景风俗”“异域情调”曾被认作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标志性的审美特征,到了“十七年文学”,对宏大主题、重要题材、新人形象的强调挤压了地方风土的生存空间,孙犁、周立波、刘绍棠等人有限的农村题材小说偶有“风俗画”或“风景画”的残存,正是这些地方自然的出现拓宽了作品的审美空间,帮助小说在“十七年文学”实现“突围”。另一方面,当文学研究试图回答作品中的自然为何出现以及如何呈现时,往往援引地域因素来解释,认为地方为作家的性格养成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地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如当代文学相较于现代文学,主流作家的文化性格和作品质地差别如此之大,究其原因是与作家群体的归属经历了由江浙沿海到西北内陆的转移相关。对地域的关注还促成专门的“地域文学研究”,试图从具有独特地域性色彩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解释文学的独特性,如有研究者提出只有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才能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创作作出准确解释。[1]从“地域”出发的做法自有其有效性,无论考察文学中地域色彩的呈现,还是探究作品生成中地域因素的作用,都已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但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首先,若将“地域色彩”最终落脚到文学作品自身的内容扩充和审美功能的完善上,这样一种具有文学本体论色彩的做法实则画地自限,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部分。看似漫不经心的自然呈现往往暗藏玄机,自然为何以某种特殊面目存在于文本,这其中暗藏着人对地方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态度。如果仅停留在文本的评判而不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情感肌理,就会错失了文本潜藏的言说可能。其次,既往从区域角度出发考察地方对文本生成影响的研究,往往着眼较大范围的区域空间,对区域空间的自然环境、文化积淀等进行考察,获得静态的整体性描述,无法具体到作家真实接触到的周遭空间,最后的结果本质上是文化研究,而非考察人与地方的关系,而且这种考察涉及的多是作家群体,因而很难充分顾及个体人地经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从而对单个作家的创作机制、创作过程进行细致描绘。事实上,人接触地方自然的方式多种多样,具备敏锐感知力的作家对自然的体验更是绵密复杂,对自然书写中暗藏的个体经验的独特性的分析要求在以往“地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寻找进入文本的方法。
地理学自19世纪进入西方大学课程以来,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化的影响演化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二元结构,人与环境的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为反拨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地理学过分追求科学推理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它将人作为地理研究的出发点,重视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价值、意义等。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每个人的经验世界是有限的,人的感知行为必然具有某些独特性,也就是说,世界不只有一个,而有多个,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从了解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意义出发,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方”(place)进行了说明。相对于无意义的“空间”(space),“地方”宛若一个充满意义的仓库,它不单指一个抽象的区位坐标、一处单纯容纳社会关系的物质环境的场所,它要求地方具有其特殊性质,更重要的是人对于地方有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即“地方感”(sense of place)。随着城市化、全球化浪潮对地方景观和地方性产生巨大影响,人文主义地理学继而讨论因地方“贬值”所表征出来的“无地方”(placelessness)与“非地方”(non-place),分别说明人对周边环境认同的弱化和疏远使得“地方”渐渐失去情感意义,以及空间因同质化和移动性而无法变成一处稳定的充满特殊意义的“地方”。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分析和概括,人类真实生活中产生的情感体验或许很难被条分缕析地简单划归到某一理论的局部范畴中,但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其分支之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方”的强调,对“地方感”获得和丧失的讨论,给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抓手,这并不是要推翻之前的“区域”研究,而是借助“地方”重新进入“地域”,它要求结合作家个人独特的地方经验、行动轨迹来阅读文本,透视文本暗藏的情感结构。自然是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作家对地方自然的观察和感知必然受到其居处于一地时的状态的影响,这些个人化的自然经验和地方体验最终凝结为自然书写,如此对文本的考察就不会停留在归纳作品的地域属性或简单地指认地域成因,而是深入文本内部,深入作品生成的每一个环节,揭示自然何以如此现身。
奇异自然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使新疆成为思考生命伦理、审视现代性、反思城市化的飞地,基于新疆的书写因此具备某些相似性,这也是“新疆作家”“西部作家”的总体性研究陆续产出的原因,刘亮程就是经常被讨论的作家之一。尽管刘亮程的书写分享着“西部”“边地”“新疆”等共同特征,但文本仍保留他个人独特的经验理路。散文集的命名——《一个人的村庄》与《在新疆》——恰如其分地点明刘亮程散文创作的行动轨迹与地域基础。有学者梳理刘亮程写作的人文地理图:在地理空间上,刘亮程的写作对象由早期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黄沙梁转向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由早期的汉文化转向了维吾尔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对精神家园的指认从最初的一个村庄(黄沙梁)到一个县域(沙湾),最终到整个新疆,给了刘亮程一个看全国的视角。[2]从北疆的黄沙梁到黄沙梁以外的辽阔新疆,伴随身体位移,刘亮程的书写空间经历了范围的扩大和性质的变化,不同人地关系下衍生的生命体验和问题意识最终映射在文本中,使刘亮程的新疆自然书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
二、官感与孤独:黄沙梁内部的自然私语
人类感知的结果与感官的灵敏度、主观意图都是相匹配的,个体熟悉的只能是有限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学者洛温撒尔对“外部世界和人脑画面”进行阐述时,认为每个人的经验世界都相当狭小,仅仅覆盖整体世界的一小部分,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对个人世界的感知因人而异,基于这种感知的行为也必然具有某种独特性。刘亮程的散文从黄沙梁起步,《一个人的村庄》偶尔涉及黄沙梁外的城市生活,但黄沙梁始终是一个固定场域,黄沙梁的自然书写是其中的一个稳定部分。对刘亮程而言,黄沙梁与其说是隶属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沙湾县城的一个小村落,不如说是他放羊、种地、砍柴、漫步的地方,他在此度过了漫长的成长岁月,创作时对生活的种种感受都融进了字里行间。散文中儿时的“我”喜欢爬到房顶和草垛上注视整个村庄,嬉戏玩闹时发现了许多个隐秘角落;长大后,当其他村人靠一年年的丰收改建家园时,“我”仍然疏忽劳动,扛着铁锹在村外的野地上闲转,盯着村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甚至产生应接不暇的匆忙感。“我生怕一生中活漏掉几大段岁月,比如有一个好年成他们赶上了,而我因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出了远门,或者在我的生活中忽视了像挖鼻孔、翻眼睛撇嘴这样有意思的小动作。”[3]23(《冯四》)这样一来,“我”全部的学识就是对一个村庄的见识。在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里,“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片洼地的草一直没有人割。黄昏时夕阳一拃一拃移过村子。我知道夕阳在哪堵墙上照的时间最长”[3]123(《风中的院门》)。“我”甚至留意到,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村民们却因每天所见太阳的早晚不同,因接触渠水的前后有别,拥有不同的气质和禀赋。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这并非夸张和臆测,是“我”的真实感受,印证了“我”对日常生活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固定居所对人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村民终日在固定位置上对周遭环境累积和巩固认知。不同于奔波忙碌、四处流散的人们,刘亮程对这样一处固定的住所充满向往。“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3]50(《住多久才算家》)其实,黄沙梁并非阿卡迪亚式的牧歌世界,这里的生活“单调得像篇翻不过去的枯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3]62(《黄沙梁》)。然而正是凭借“熟读”黄沙梁时对地方产生的深深依恋,那些贴近生存最低处的东西,如一条颓然老矣的看家狗、深夜的鸟鸣、早晨的炊烟,甚至大雪降至时彻骨的寒风,本来无关痛痒,甚至败落荒凉,刘亮程却娓娓道来,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
加拿大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爱德华·雷尔夫(E.Relph)在《地方与无地方》(Placeand Placelessness)一书中讨论地方身份(the identity of places)时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一种精神空间的中心,置身于兴趣和依附性逐渐降低的同心区域中,我们所感知的地方,可根据体验的深度、经验的丰富程度作出划分,人类的地方经验因此有了内部性(insiderness)和外部性(outsiderness)的区别。地方的本质就在于和外部相区别的内部经验,是这些内部经验使地方从无属性的空间分离,成为对于某人而言的一个拥有有形特征、活动和意义的独特系统。内在于一个地方,就是归属并认同它,而且进入得越深,对地方的认同感就越强。[4]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区分似乎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二元论,但不妨碍它为我们提供观察刘亮程散文创作的一种方式。在漫长的生活中,“我”充分融入黄沙梁,了解和接受这里,看似游手好闲的生活做派让“我”和周围的村民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恰当的距离感使“我”有机会充分捕捉这里的自然信息,获得独一无二的地方体验。
作为黄沙梁的内部者,《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自然以家园为中心展开,出场的自然物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宛若和人交错生长为一体,不可肢解。大榆树是孩童捉迷藏的容身之处,麦子和玉米延续着村民的生命,杂毛黑狗和黑猫也是家庭成员,驴、牛等牲畜和人一起进行繁重的劳动。麦收之后,村民留“我”一人在野地看守麦垛,人迹罕至之地的自然世界令人心生畏惧,“我”跟荒野上角尖牙利的飞禽走兽们互不侵犯,关注的仍是更为温驯的、和人关系密切的野兔、老鼠,在无人的麦地与虫共眠、对一朵花微笑。(《剩下的事情》)“我”充分体验黄沙梁也意味着面对乡村自然时调动了自己的感觉器官,将自我向周遭环境充分敞开,与自然直接接触,在身体无障碍地与自然进行直接对话时获得对乡村自然的私人理解。于是,夏天的早晨,从草棚顶上站起来,站在缕缕炊烟之上,“我”的眼睛能够看出炊烟不同的颜色,有的黑、有的紫、有的青、有的蓝,一阵风吹过,全村的炊烟如一头乱发绞缠在一起。(《炊烟是村庄的根》)在冬天,“我”的皮肤能够感受到寒风的温度,靠肌肤对空气温度和湿度的感知能预感大雪将至。(《寒风吹彻》)在众人都已沉入梦乡的深夜,“我”的耳朵可以听到众狗狺狺(《狗这一辈子》),听到鸟粗哑却有穿透力的“呱、呱”叫声(《鸟叫》),听到夜晚风刮过荒野的麦垛,留下犹如女人的哭喊声(《剩下的事情》)。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人认识世界时,全部的感官都在同步起作用,只有这样,鲜活的自然世界才得以和人类展开互动。书写自然要求作家充分调动感官。有学者指出,自然文学作家描写自然,不仅仅描述自然界的风景(landscape),还运用听觉呈现自然景象,形成声景(soundscape),如亨利·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中用文字细致复现海浪之声。风景和声景的结合形成了自然的灵气和灵魂,它们与人类的心灵碰撞时产生心景(soulscape),风景、声景及心景三者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成为自然文学的独特之处。[5]这种说法虽然只提及视觉和听觉,但是说明了自然书写中感官体验的重要性。
刘亮程无意对感官捕捉到的自然作客观描绘,而是涂抹上自身的情感色彩,对自然展开诗意想象和情感投射,在与大自然的喃喃絮语中汲取力量和温存。他在黄沙梁长大,时常感到孤独,幼年失父使他变得更为敏感。在一次创作谈中,他回忆:“父亲死去那年春天我们一样等来了草绿和虫鸣,母亲带着她未成年的五个孩子苦度贫寒的那些年,我们更多地接受了自然的温馨和给予。你知道在严寒里柴火烧光的一户人家是怎样贪恋着照进窗口的一缕冬日阳光,又是怎样等一个救星一样等待春天。”[6]这种孤苦大概就是刘亮程将原本人畜共居的热闹村庄命名为“一个人”的村庄的原因之一。即便整个生命与其他村民一样深刻地沉浸在黄沙梁,但这份孤寂的心境将“我”与他人区分开来,“我”的心灵和目光始终能够在特殊的角落,对村庄的自然保持敏锐和自觉,捕捉到那些极易被人忽视的存在,对所有平凡的自然物都心有戚戚然。这里的鸟和“我”一样承受孤独:“这种鸟可能就剩下一只了,它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它话的生命。它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鸟语。”[3]46(《孤独的声音》)这里的牛和“我”一样忍受苦难:“常常是牛拉着我们,从苦难岁月的深处,一步一步熬出来。”[7](《卖掉的老牛》)这里的老鼠应该和人一样有个好收成,得以继续坚韧地活在这世上:“它们用那只每次只能拿一只麦穗、捧两颗麦粒的小爪子,从我们的大丰收中,拿走一点儿,就能过很好的日子。而我们,几乎每年都差那么一点儿,就能幸福美满地吃饱肚子。”[3]45(《老鼠应该有一个好收成》)对自然的个人化理解使得《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自然书写呈现出浓重的“私人化”色彩,不仅村庄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自然也是刘亮程一个人的自然,书写成为刘亮程的私语。在这里,自然不仅是日常观察的对象、娱乐的场所,它们还和“我”同频共振,共同寄身于小小的黄沙梁,承受这份荒凉、孤寂但不失甜蜜的命运。
三、致思与叹惋:游走在新疆的生态代言
当刘亮程走出黄沙梁漫游新疆,所到之处已非他所熟知的“一个人的村庄”,南疆是他除黄沙梁之外频繁书写到的地方。刘亮程在散文中回忆多年前的一次南疆之旅:
那是一次漫长而紧促的行旅,几千公里的路途,几乎没有在哪儿停顿过,沿途一阵风一样穿过的那些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村落城镇,就像曾经的梦境般熟悉亲切。低矮破旧的土房子、深陷沙漠的小块田地、环屋绕树的袅袅炊烟,以及赶驴车下地的农人——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个人,又永远地置身事外。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飘忽,一阵风一样没有着落。[8]41
如果说黄沙梁是刘亮程真切生活过的地方,此时的南疆于他而言宛若一幅风景画,仅供人匆忙一瞥。刘亮程看到的不是南疆的生活,而是南疆的“地景”①“地景”(landscape)是地理文本中经常伴随“地方”出现的概念,另可译为“景观”。区分地景与地方的差别,是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地方概念的一环。参见:克瑞斯维尔.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6:19-21。——一种可以从某处观看的局部表面、一种强烈的视觉观念。往南疆望去,人位于南疆地景之外,而非置身其中。再游南疆,面对一处陌生的地方,外来者进入地方的渴望闪现于文本间隙。在库车,“我”放低姿态,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走访民间故事。在巴扎集市上卖馕的维吾尔族妇女的红柳条筐是千年前的模样,她褐色的蒙面面纱并不比两千年的历史帷幕单薄(《一切都没有过去》),一位普通妇女竟能让刘亮程感到超乎历史的庄严肃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乡的大学生做着不挣钱的剃头生意平淡度日,“我”期望他能跟老剃头匠一般将一件小事做到底。(《生意》)世代传承的铁匠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打好每一把镰刀,挂在墙上等待它的买主,挥舞着它进行耕种这件千百年来恒定不变的事。(《最后的铁匠》)此外还有耗费数十载光阴进行的托包克游戏(《托包克游戏》),以及汉文化圈不曾有过的割礼(《木塔里甫的割礼》)。库车老城传统生活方式的缓慢和悠长成为刘亮程抵抗现代化的凭借之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焦灼感始终如影随形,这意味着刘亮程进入异地的失败。同样作为观察者,身在库车的刘亮程已然丧失了在黄沙梁时的从容和悠闲。《热斯坦巷早晨》记录“我”如何观看当地居民做礼拜。去热斯坦巷观看礼拜对于“我”而言是一次越轨的旅行,“我”想像当地人一样跪下祷告,却总是姗姗来迟,旅行结束又不得不匆忙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轨道。热斯坦巷从未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只是匆忙一瞥的窗口,正是在融入的渴望和旁观的隔膜的张力之下,这里清真寺的喊唤才变得如此具有吸引力,若即若离的情绪也说明“我”从未真正成为真主的信徒。当“我们”夜里开着汽车进入没电的阿格村时,看到被车灯照亮的维吾尔族男孩女孩们在漆黑的夜晚用“我们”不懂的言语聊他们的人生时(《阿格村的夜晚》),此时文章结尾处的心理描写可以被看作刘亮程游走于新疆大地时内心最落寞的独白:
就是那样的夜晚使我们之间变得遥远、陌生。白天我们有时走过去,跟他们一一握手,生疏地回答几句,用我们或他们的语言。我们想接近时,就会感到那些不可交换的言辞与言辞之间,手与手、眼睛与眼睛、呼吸与呼吸之间,横隔着无数个我们看不清的遥远夜晚。……我们再不会走过去,伸出手。那是一种永远的远,对于我们。[8]75
无论身处何处,刘亮程都对脚下的新疆大地保持热情与认同,始终意图将自己置身于地方内部。他强调自己属于整个新疆:“我是新疆人,在新疆出生、长大,这么多年未曾离开”[9],他所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熟悉并观察了半个世纪的新疆生活。但事实是,随着在新疆不同的地区穿梭,刘亮程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即便刘亮程将整个新疆指认为自己更大的精神家园,当走出黄沙梁面对新疆的其他地方时,仍然不由得扮演起旅客和异乡人的角色。无论是库车还是阿勒泰,刘亮程都将其理解为充满意义的地方,努力进入它、读懂它——让自己深处地方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隔膜和陌生可以被轻易消除。漫游新疆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步履不停之感,刘亮程快速地在不同区域间移动,没有长久驻足徘徊一地,这使他得以领略更多的新疆大地,但随即而来是他无法再如植根黄沙梁一般足够长久地与一地共处。尽管不同的地方在各自的景观呈现、历史沿革方面有所不同,但在作为游客和异乡人的刘亮程眼里,它们的区别已十分模糊,逐渐融合成同质的存在,仅剩名称和行政区划来标注各自的身份和属性。无论是南疆还是阿勒泰,甚至整个新疆,都不过是刘亮程怀揣着相同的问题和思考匆忙进入的地方,地方无法向他透露出自己的独特之处,究其原因是他无法和不同的地方建立起私人的情感联系,将空间变为独属于自己的地方。最终,面对着内部自然环境差异如此巨大的新疆,刘亮程的自然体验却完全雷同,呈现出书写自然的另一种模式。
和《一个人的村庄》相同,《在新疆》中的“我”仍然保持着对自然的亲近,但自然书写并不依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积累的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自然经验,作为异乡人的“我”面对黄沙梁以外的新疆大地的自然时,感官体验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用智识体悟自然背后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义,呈现在文本上,刘亮程不再回溯、反刍过去生活积累的经验记忆,而是挖掘与自然相关的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同样写驴,黄沙梁的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伙伴,时而沉默宛若沉思,时而充满野性和力量,“我”和驴一起生活,“我炒菜的油香飘进驴圈时,驴圈里的粪尿味也窜入门缝”[8]9(《通驴性的人》)。书写南疆驴时,刘亮程引用自公元三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中的库车驴的历史,以及《大唐西域记》中龙驴斗法的传说——千万头公驴对着龙池放草屁,战胜欲与母驴交合的好色之龙,保住了母驴的贞操。(《龟兹驴志》)夏尔希里这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山谷是草的王国,山谷草木背后是国家间互相征战的历史。这块土地曾被别国占领,在被占领的岁月里,“树在别人的国度里长粗,它里面的年轮还记得中国,外面的皮和枝条就不记得了”[8]126(《夏尔希里》)。同样地,喀纳斯那块看起来像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的风流石,牵动出一个生动的民间故事——女萨满用名为“锁”的法术牢牢抱住了牧主风流成性的儿子哈巴特。(《喀纳斯灵》)黄沙梁以外的自然物不再有私人生活的印记,给自然增添光彩和赋予意义的是自然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自然书写变成智性的操练和严肃的思考。在情感方面,由自然抚慰的个人疼痛转为面对生态危机时的良心之痛。现代都市的飞速扩张、都市人的“缺自然症”、人类生存对其他生物存续造成的压迫和威胁始终是刘亮程关注的问题。此时的新疆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局部,也是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片段。在新疆,自然同样曾经遭受并仍在遭受创伤。《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书写了人类开垦农田破坏植被、过度开采地下水的历史,而“沙漠将以裸露的方式永远地铭记人类的粗暴开垦。人们收获完土地上的棉花麦子,必将接受它漫天沙尘”[8]144。夏尔希里的花草在中哈两国争议的漫长岁月尚能安静昏睡于山谷之中,如今游人将至,必然扰其清梦。(《夏尔希里》)“以前,神话传说中的巨怪都在深山密林中。现在山变浅林木变疏,怪藏不住,都下到水里。”[8]133只有不可名状的喀纳斯湖怪还为神秘留有一席之地,让“我”保持对自然的情愫和敬意。(《喀纳斯灵》)漫步于新疆大地的刘亮程试图从新疆留存的农业传统找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这里的农民不如其他地区的农民勤快,将大地改造得只适于人的生存,库车老城外的田野上野草和果树杂生。在这里,不仅是粮食作物,万物都有它生长的权利。(《通往田野的小巷》)这里的铁匠仍遵守着农业时序的轮转规律,麦芒初黄打好镰刀,农民割麦时便转手打制坎土曼,年复一年地赶着时间做活儿,不能早一步也不能晚一步,自然生态时间的神圣权威将人与自然纳入和谐有序的共生循环中。作为努力认同和融入新地的异乡人、作为反思现代社会的行吟者,如同刘亮程在南疆的缓慢中为现代人寻找心灵的休憩,《在新疆》中的自然书写是一种带有问题意识的智性的创造,对自然的属性的理解和混沌的情愫退至幕后,自然是普遍人类的自然,生态关怀成为此时的显赫之旨。人类不应是自然的主宰,自然有自己的身份和历史,所有具体的自然物——人和非人都只应是自然序列中的一环,在相生相克中维持动态的平衡。
四、结语
从黄沙梁到整个新疆;从直接的感官体验到头脑的智性体悟;从日常生活经验的私人式表达到为自然声张的代言式书写;从在黄沙梁自童年起就已积累起来的对土地、动植物、风、阳光的强烈感情,到生态危机荫翳下对自然正义的呼唤,一种旧的自然书写模式被推翻,一种新的模式取而代之。这绝不是说这种转换荡涤了所有旧的印迹,《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自然也曾作为现代人反观都市生存的镜子,《在新疆》中的自然体验不可能完全剔除感官感受,刘亮程观察自然的眼光是所有过去的聚集,就像一个人曾有过多种生活,却不能忘记其中的任何一种。但是通过重新回顾刘亮程的书写轨迹,提取出这个过程中前后两种主要且有明显差别的书写模式,探寻刘亮程散文中的自然书写何以呈现此种质地以及如何汇合到当下的生态话语中去,方能够真正呈现刘亮程的写作动态,进而发挥个案的功能来帮助思考当下的自然书写。
在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都摇摇欲坠之时,重回地方自然似乎成为一种解决方案,如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不堪城市之累回归汨罗的返乡之作,韩少功在劳动中重新接触自然,与农耕语境中的农事、物候、气象、历法相连的虫蚁、家禽、草木、日月统统被纳入书写的范围;李娟关于阿勒泰的书写悄然走红也与其文本中自然书写所呈现的特殊的生命关怀息息相关。当地方自然不断在文学文本中涌现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何体验地方并和地方产生联系。以刘亮程为例,他从私人情感表达走向对全人类的生态关怀,增强了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感,但与此同时,也压抑和错失了淳朴、绵密的私人情感。他有意识地为自然代言,承担起生态伦理责任固然是一种进步,但私人情愫的撤离使得自然书写的丰富性被削弱,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黄沙梁时期那种人与自然懵懂混沌、休戚与共的情感联系不也珍贵?这些都从后来的文本中消失不见了。当书写自然越来越被重视时,除却普遍的和共通的责任感和道德伦理,人如何在具体的自然空间内获得与自然相处的多种可能,丰富对地方自然的理解?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