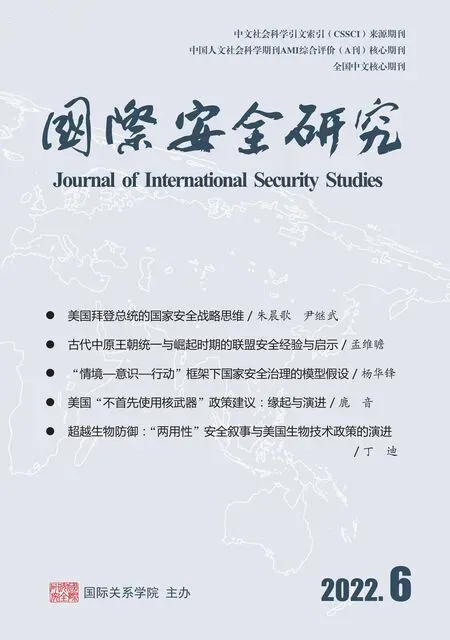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朱晨歌 尹继武
【内容提要】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小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 Jr.)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美国第46 任总统。对于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决策偏好,学术界和政策界进行了分析或预测,并对拜登团队已经推出的安全政策进行了初步评估。这些探讨集中在联盟管理①凌胜利、李航:《拜登政府的亚太联盟政策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 期,第19-27 页;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 期,第11-17 页。、地缘战略②Nick Bisley, “Biden Will Place Asia Back at the Centre of Foreign Policy - But Will His Oldschool Diplomacy Still Work?” The Conversation, November 10,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biden-will-place-asia-back-at-the-centre-of-foreign-policy-but-will-his-old-school-diplomacy-stillwork-148095.、多边合作③Kylie Atwood and Nicole Gaouette, “How Biden Plans to Undo Trump’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and Return US to World Stage,” CNN, October 31,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10/31/politics/biden-foreign-policy-plans/index.html; Thomas Wright, “The Quiet Reformation of Biden’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20,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3/20/the-quiet-reformation-of-bidens-foreign-policy/.、大国关系④Dominic Tierney, “In Search of the Biden Doctrin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9,2020,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0/11/in-search-of-the-biden-doctrine/;韦宗友、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21年第4 期,第93-109 页;叶江:《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走向浅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3 期,第28-41 页;达巍、黄婷:《拜登政府执政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继承与转向》,《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 期,第1-19 页。、核不扩散⑤Hamidreza Azizi and Maysam Behravesh, “Why an Iran-U.S.Detente Could Still Occur Under Joe Biden,”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11,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iran-us- detentecould-still-occur-under-joe-biden-166637; Parisa Hafezi and Arshad Mohammed, “Analysis: Biden Would Face Uncertain Path to Detente With Wary Iran,” Reuters, October 28, 2020,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iran-analysis-idUSKBN27D1D2;李喆、罗曦:《脱离现实的拜登核军控理想》,《世界知识》2021年第19 期,第34-35 页。、战略利益⑥Tracy Wilkinson, “Whom Might Biden Choose to Run State Department, NSA, Other Foreign Policy Jobs?”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8, 2020,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0- 10-28/biden-state-dept-nsa-cia-foreign-policy-advisors; Ken Bredemeier, “Biden Introduces Diplomatic,National Security Team,” VOA, November 24, 2020, https://www.voanews.com/2020-usa- votes/bidenintroduces-diplomatic-national-security-team; 孙冰岩:《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与对华政策认知》,2020年11月13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 table= article&id=23478;陈征:《谁在帮助拜登制定对华政策?》,《世界知识》2020年第19 期,第22-25 页;樊吉社:《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4 期,第1-19 页。和经贸安全⑦余振、王净宇:《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评估与展望》,《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4 期,第20-36 页;佟家栋、鞠欣:《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挑战与应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3 期,第102-120 页。等议题上。相关研究指出了拜登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产生的重塑作用,对我们初步认知拜登的决策倾向具有启发意义。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从议题层次上论证拜登政府的战略安全倾向与可能的政策表现,或是强调宏观的美国政府安全战略评估与倾向。对于拜登更具抽象性、整合性和个体性的安全战略思维,现有探讨尚不充分。①对于拜登总统政治人格、决策风格、认知特质的现有研究参见Gideon Rose, “Foreign Policy for Pragmatists: How Biden Can Learn from History in Real Tim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oreign-policy- pragmatists; Masoudi Heidarali, “Joe Biden’s Operational Codes i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Vol.12, No.2, 2021, pp.95-122; 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 期,第11-22 页。基于总统在美国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战略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总统本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因此,本文的目标是深入研究拜登的安全观及其战略效应。
一个关于决策者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及其战略支配能力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领导人的安全观念与战略影响。本文拟构建出一项领导人安全观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拜登总统如何定义美国国家安全,他倾向于采取怎样的战略手段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有的安全战略,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部署。本文将通过对拜登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分析,探究其对美国国家安全实践的影响能力。
一 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思维及其战略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兼具客观和主观的属性,国家安全既是物质现实,也反映在个体认知中。②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 期,第3-29 页。政治领导人是特殊的安全观主体,其特殊性体现在他们认知的信息来源以及认知结果的政治效应。领导人对于本国安全程度的判定,以及对于如何达成国家安全目标的决策倾向,是塑造国家对外战略的一项动力因素。特别是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超级大国领导人,他们“对于宏大国家安全体系的界定”,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乃至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动。③Joseph M.Siracusa and Aiden Warren, Presidential Doctrines: U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Barack Obam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218.
在政治实践中,领导人的个体政治信念未必直接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同阶段的领导人理念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表现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可以推断出在政治过程中,存在着影响领导人信念转化为政策的因素或行为体。安全战略决策可以具体分为观念生成、决策塑造与政治动员三个阶段。
(一)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要素
本文将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安全观)界定为:领导人对于本国安全问题的系统性判断。这一概念可以划分为领导人的安全环境评估、威胁来源识别和国家安全目标三个维度。
1.安全环境评估
对国家所处安全环境的性质进行系统性判断,是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维度之一。在政治实践与理论中,安全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追求的永恒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安全程度也会受到所处外部结构的制约。①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6 页。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认知,是推行特定安全战略的逻辑前提,因此是分析领导人安全决策倾向的一项特质维度。
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主要基于两个要素:阶段发展和趋势动因。从安全环境的阶段发展来说,对于动态的、变化的国际关系状态,决策者会随时关注安全环境在不同阶段的性质:其一是国家安全环境的现状如何,即国家所处国际环境安全程度在当前的具体特征与表现;其二是国家安全环境的前景如何,国家的安全程度是否会长期维持当前状态,或是产生何种变动。就安全环境发展趋势及其动因而言,决策者关注所处安全环境的变动趋势及其动因:国家安全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领导人需要基于上述观念作出维护安全的战略决策:增加有利于本国安全的因素,阻止安全风险严重程度加剧。另外,外部的重大安全事件也会影响决策者对本国安全环境的评估。②John Bolton, “Beyond the Axis of Evil: Additional Threats from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ay 6, 2002,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 beyond-the-axis-eviladditional-threats-weapons-mass-destruction-0.根据上述分析,对于安全环境阶段特征、变动趋势、状态动因的判断,影响着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思维。
2.威胁来源识别
对于国家潜在安全威胁来源的识别,是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维度之二。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对于所处环境威胁来源的认知,影响着其世界观、政治意识乃至政治行动。③John Duckitt and Kirstin Fisher, “The Impact of Social Threat on Worldview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4, No.1, 2003, pp.199-222.作为本国在国际行动中的直接决策者,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也影响着其国家安全战略倾向,进而在国内外政治结构限定范围内对本国安全政策起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①既有研究指出,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在建立安全联盟、敌对关系和解、国际机制参与、对外战略制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动因。参见Janice Gross Stei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Huddy, D.O.Sears and J.S.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64-394; He Kai, “Undermining Adversaries: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2, 2012, pp.154-191; Gause F.III, “Balancing What? Threat Perception and Alliance Choice in the Gulf,” Security Studies, Vol.13, No.2, 2003, pp.273-305;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11 页;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高阳:《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 期,第104-130 页;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当代亚太》2021年第4 期,第28-66 页。威胁既是一种动态的行为,也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损及行为体利益的要素。国家安全威胁则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生存能力的风险性因素。
鉴于国家实力、治理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差异,威胁识别的优先程度与衡量标准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差异显著。在对外战略实践中,美国是强调对本国安全威胁进行界定的典型国家,将威胁识别置于国家战略思维的支柱地位。②韩召颖、李圣达:《美国政治信念与对外政策——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操作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 期,第23-47 页;邢悦、陆晨:《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文本分析》,《国际论坛》2019年第5 期,第3-23 页。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展示出“威胁范式”的特征,通过界定对本国安全产生威胁的行为体,来认知和调整本国的安全状态。③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 期,第151-158 页。
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识别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威胁来源的主体判定。领导人需要从本体上确定威胁来源的性质,安全威胁究竟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是人为因素还是非人为因素等,这一判定影响着后续针对风险采取战略选项的议程。第二,安全威胁的识别标准。领导人在将相关行为体确定为安全威胁时,通常会根据对方挑战本国安全现状的倾向认知和敌对意图判定作为准绳:当被视为安全威胁的行为体挑战程度越强时,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可能就越大;当该行为体的敌对意图上升时,其威胁程度也可能越大。④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 页;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 期,第71-99页;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No.1, 1978, pp.93-107。第三,竞争行为体的威胁方式。领导人需要判断该行为体如何对本国安全产生了威胁:对方是直接采用军事手段给国家造成直接的安全风险,还是采用政治、经济、价值观等非军事手段给国家造成非直接的安全隐患?对于不同类别战略手段及其具体政策的判定,为本国的后续战略应对奠定了基础。
3.安全目标设定
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认知,是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维度之三。安全目标是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的具体理想规划,尽管目标常与现实存在鸿沟,但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基于本国安全现实,另一方面也引导着该国未来的安全战略方向。领导人的国家安全目标设置具有国际和国内来源。国家的安全目标既要体现出世界政治动态变化的时效性,也需作为国内政治意愿的映射。另外,领导人对安全目标的设定具有浓重的个人色彩,目标往往会体现决策者的政治人格、执政风格、从政经历等等。在形成安全目标观念后,领导人会在言辞或政策中有意地向国际和国内其他行为体传递这些目标,进而产生决策者所偏好的战略手段。①Adam Hodges, “The Generic US Presidential War Narrative,” in Adam Hodges, ed., Discourse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47-68; Zhengqing Yuan and Qiang Fu,“Narrative Fram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 Construction of Rival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3, 2020, pp.419-453.
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设定涉及不同的议题与区域,本文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建立起国家安全目标的分析框架。议题方面,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目标的界定不仅包括传统上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价值观安全,也会关注包括非传统的技术安全、环境安全与信息安全等议题。②Sharon L.Caudl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Security from What, for Whom, and by What Means,”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Vol.6, No.1, 2009, pp.1-26.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安全的衰落,传统安全在当下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作为国家安全关切的核心。区域方面,基于其战略规划,领导人对各个国际区域进行战略布局。从范围上看,决策者的战略规划会受到其战略认知的影响:扩张型的领导人将会扩大战略布局区划,扩张国家安全范围的地理范畴;收缩型的国家决策者则会缩小战略区划,缩减国家安全范围的地理范畴。③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 期,第93-119 页。从数量变动上看,领导人既可以明确地将某一区域纳入安全范围,将该地区的利益视为攸关本国安全;也可以将其排除出本国的战略设计。因此,国家安全目标产生于决策者对本国安全的背景认知与未来期望,是经过理性分析后的多维认知结果。领导人对安全目标的考量,是其安全理念中的一项核心要素。这些政治考量与国内外政治现实共同影响着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二)领导人的安全决策偏好与战略动员
上文从外部环境、风险来源和安全目标三方面阐述了领导人安全观的本质,同时领导人也需能动地采取手段维护战略安全以及进行战略资源的汲取与调配。决策信念与战略动员是领导人安全信念发挥现实政治影响的两个环节。
1.领导人决策信念对政治的影响
关于安全策略手段的特定信念,是领导人基于安全观而产生策略倾向的观念延伸,也是探讨其政策实践效应的逻辑起点。战略手段指实现国家安全的政治纲领及其具体举措,决策者有策略议题、策略烈度、策略时机和参与主体四个维度的安全策略选项。而不同领导人的决策偏好存在区别,这是导致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策略议题上,领导人需要确定采取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文化手段等不同领域的策略达成安全目标。领导人通常基于各自议题领域手段的收益分析与个体决策偏好,进而决定采取哪一议题内的安全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互动并不局限于同一议题领域。除了相同议题上的对抗与合作,也存在“议题联系”(issue linkages)的路径,进而导向了跨议题层次的战略博弈,从而实现讨价还价中的收益交换。①T.Clifton Morgan, “Issue Linkag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Bargai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4, No.2, 1990, pp.311-333.议题维度上的领导人个体偏好、本国国内政治与行为体能力分配,都影响着决策者是否决定采取跨议题策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针对不同议题的联系。对策略议题的选择,是决策者能动地采取特定战略手段的具体表现,这一维度上的表现差异将不同领导人的战略偏好区分开来。
在策略烈度上,领导人既可以选择烈度较高的冲突对抗方式维护安全,也可以采取烈度较低的让步合作方式实现安全目标。烈度是安全冲突激烈程度的变动范围,其本质是单位时间内采取特定冲突策略的收益结果变动。决策者感知中的安全威胁程度,常常是他们产生不同烈度策略偏好的来源。面对较高安全风险,决策者会更倾向于采取高烈度策略;反之则更偏好低烈度安全手段。领导人会在战略规划中预先操纵烈度,实现资源投入与收益结果的均衡,从而产生与决策者预期相接近的安全结果。例如,低烈度战争既可作为一种战略选项,对其应用也塑造了特定的战争形态。①Avi Kober, “Low-intensity Conflicts: Why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Defense &Security Analysis, Vol.18, No.1, 2002, pp.15-38; 毛维准、朱晨歌:《印度“短期高烈度战争”方针:政策框架与行为动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3 期,第127-153 页;左希迎:《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 期,第78-101 页。因此,策略烈度是对领导人战略选项及其偏好的分析中不可缺失的维度。
在策略时机上,领导人既可以选择先发制人式的战略手段,也可以选择后发制人式的战略手段。对于战略时机的判断,是影响决策者对于采取特定策略行为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②刘旻玮:《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 期,第38-73 页。领导人会根据与对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安全威胁态势决定确保安全的策略机会窗口,进而生成如何选择特定策略选项的偏好。当决策者意识到自身在实力对比中处于较优态势时,或是认定当前安全威胁较为严重时,会较为积极地推动对外安全战略;反之,其积极性则会较低。“时间”是战略决策中的一项关键要素,加入领导人对于特定策略运用时间的考量,可以扩展国际安全研究的纵深,增强个体层面决策对于政治结果的解释力。
在参与主体上,领导人既可以选择多边合作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单边行动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一般来说,采取多边主义的战略路径可以通过分摊来降低本国的冲突成本,有助于以更低代价达成战略目标;同时,这一偏好也会增加本国需要承担的制度成本,例如对于合作制度中成员的协调成本、被卷入其他成员战略互动付出的成本等。③Todd Sandler, “Alliance Formation, Alliance Expansion, and the Cor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1999, pp.727-747.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影响着领导人对策略中参与主体多样程度的偏好,其偏好程度差异也是不同领导人决策风格的区别之一。
2.战略动员对领导人发挥政治信念的影响
战略动员同样是国家安全战略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战略动员是决策者在面临国家安全威胁时的一种战略反应,通过资源征集、能力分配、外部环境优化等路径提升国家安全水平。④时殷弘、陈潇:《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史概观和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 期,第32-39 页;刘博文:《战败国为何发起复仇战争?》,《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89-127 页。
领导人在产生国家安全信念并生成政策偏好后,就需要获得国内外资源保障战略的落实。尽管领导人往往拥有最高国家安全权力,但其权责受到国内或国际政治结构的限制。以美国为例,宪法规定权力分立原则,领导人的安全动议往往受到其他政治部门的制约。①Bert A.Rockman, “Mobilizing Political Support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Armed Forces &Society, Vol.14, No.1, 1987, pp.17-41.通过运用利益和观念要素,他们可以提升国内外行为体对特定倾向政策的支持程度,并实现战略资源的汲取与重新配置。战略动员不仅为领导人提供战略资源,而且有助于更加可信地展示战略意图。②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78-202 页。
战略动员是一个决策者能动地变动战略环境、减轻自身理念推行时所受阻碍的过程。领导人会采取措施加速动员进程,强化动员成果。决策者及其团队可以基于理念、制度两种方式动员大众等政治资源。首先,领导人可以将自身理念传播至决策圈层、国内民众与国际盟友或对手等行为体,其核心逻辑是增加自身理念的外部接受程度。其次,可以通过制度路径将决策者的安全理念确立下来,进而实现稳固的战略资源征集与配置。通过上述方式,国家权力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战略动员。
(三)领导人安全观的政策实践效应
领导人在能动地调整战略环境时也会受到外部结构的限制。因此,要探讨领导人如何影响本国安全战略制定及其对外战略实践,就需关注决策者在将其观念转变为政策实践时,在何种条件下影响政策结果。综合考量国家安全战略生成的国内单元与政治过程,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两类影响机制:结构性约束程度与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
1.结构性约束程度
领导人在政治结构中越居于中心位置,其理念对于政策的影响力就越大。结构性约束表现为对于领导人自主设置战略议程的限制。如果领导人是较为积极的战略议程设置者,就会选择尚未受到广泛关注的、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安全议题;如果领导人较为消极,则倾向于顺从外部给定的主流战略议程,或是承袭前任领导人遗留的安全议题。这一要素的衡量指标是,领导人是否提出新的战略议程,以及在特定议题上的观念是否与前领导人观念存在显著差异。领导人在战略议程形塑动力上的表现差异,代表着其对于主导地位的不同取向,进而影响他们对事实采取不同形式的框定方式,③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86 页。最终影响了他们对本国安全战略的塑造能力。
结构性约束也体现为领导人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位置。政策团队是强化领导人政治主导权的政策制定与权力协调结构,①孙成昊、肖河:《白宫掌权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2019)》,时事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271 页;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众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 页。他们不仅负责将领导人的个体观念系统化、精细化与理论化,并将其转变为正式文本,还承担着向领导人提供决策信息、调整其战略偏好的角色。因此,决策者对于安全战略的主导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配安全政策团队。一方面,领导人对于安全政策团队具有人事决策权,直接决定团队成员的任职或去职;另一方面,领导人向团队进行安全理念的输出,从而实现个体观念向政策生成的转型。对于安全决策团队的掌控能力,是影响领导人理念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主导程度的另一项因素。
2.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
领导人所处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其安全理念的政策影响力就越强。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之一是本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环境复杂性与偏好自主性呈正相关关系。②弗雷德·I.格林斯坦:《人格与政治》,景晓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48 页。一方面,当国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战略安全环境中时,领导人对政治现实的理解也更为丰富多元,③Brian C.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1, No.3, 2007,pp.533-557.进而其战略选项也更为复杂,在国家安全议题上问题呈现(problem presentation)的变动为其采取个性化决策留出了空间;另一方面,复杂化的外部环境改变了战略安全选项的收益结构,降低了决策者沿袭传统安全策略的倾向。因此,当国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时,例如出现国际结构变动与重大冲突爆发等情况时,领导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塑造国家安全政策。
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之二是国内安全理念的分裂程度。战略安全问题上的观念一致性对领导人角色的影响,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阶段。在领导人的战略偏好生成阶段,国内关于特定议题的意见一致性越强,领导人则更难生成稳定且相异的个体偏好。在国家安全政策决策阶段,高度共识性的决策观念会对领导人施加较强压力,但如果是“小集团思维”则会强化领导人的安全信念自主。④欧文·L.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张清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而在战略动员阶段,高度分裂的国内社会为领导人通过言辞和行动传播自身理念、汲取战略资源提供潜在机会。因此,国内安全观念一致性越弱,领导人与之相异的理念对安全政策的影响就越强。
(四)领导人安全观及其政策效应的分析框架
前文从内容、偏好与动员三个维度论述了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思维,并辨析了个体安全思维如何影响国家安全战略形成和对外战略实施,论述了其在界定本国战略意图、驱动安全战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内容维度上,领导人的安全观为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提供了意图内核。一方面,领导人的安全思维是塑造安全决策的核心要素之一,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与对其他行为体的认识,有助于解释重大政策的形成;①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7 页。另一方面,领导人的安全思维作为本国意图的最权威阐述,可能影响决策者对其他国家行为的解读方式,进而改变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②Daniel L.Byman and Kenneth M.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2001, pp.107-146.领导人相对稳定、系统的安全战略思维,可以界定该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安全意图,并作为进一步战略实践与战略分析的依据。
在过程维度上,领导人的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战略出台过程的驱动力。由朴素的安全观念转变为系统、精准的政策内容,需要一个逐步深入细化的转变过程。领导人在安全议题上形成稳定偏好,则是国家安全战略出台的前提条件,也是驱动官僚组织生成政策、动员国内政治的一项动力因素。而领导人基于决策信息产生的偏好变动,同样影响了安全战略政治过程的调整与适配。个体安全战略思维参与和塑造着国内安全战略形成及其实施的动态平衡。在国家安全战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各个因素侧重于在不同阶段中发挥作用,而这一系统的原初动力则是领导人安全战略思维的形成与调整(参见图1)。

图1 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思维及其战略塑造能力分析框架
本小节给出了一个领导人安全观及其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环境、威胁来源识别和国家安全目标三个维度的理解,构成了其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结构;基于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与现实政策选项,领导人产生特定战略手段偏好,并对国内政治资源进行动员;领导人在安全议题上受到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则影响着其安全观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支配程度。
二 拜登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政治影响过程
本节将依托上述分析工具,研究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及其政治影响过程,包括拜登的国家安全理念、政策手段选项与政治动员方式。
(一)拜登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要素构成
拜登在军事、经贸与价值观安全领域有重塑美国霸权的安全目标。他对于美国当前安全环境现状及其趋势的认识较为悲观,这一负向认知源于他将中俄等大国视为美国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来源”,这些因素使其产生了修复美国受损的安全现状的动力。
1.对美国安全环境的理解
拜登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现状一直持有负向认知,并意图扭转美国的安全颓势。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目前正处于恶化的状态,表现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美国国际地位降低:前者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国家的政策执行力,后者则降低了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信誉。在他看来,这一现状的国内原因主要是特朗普政府对本国民主环境带来的破坏,国际原因则是部分非民主国家崛起带来的秩序变动。①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在拜登的信念中,这些破坏可能是美国霸权长期衰落的先兆;如果美国对安全环境恶化的趋势不加重视,就可能失去现有战略优势。
拜登评判美国安全环境的标准包括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两个维度:①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1,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一方面,美国实力是否在国际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民主价值观是否为世界政治中的绝对主流。作为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者与践行者,拜登认为“领导世界”是美国的天定命运,要保持这一状况,既要维持美国国力增长的态势,也要引导其他国家践行西式民主政治。因此,重振本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巩固民主,是拜登所期望的美国的发展方向。
拜登沿袭了建制派对美国所扮演世界主导角色的定位,也表现出了对前任政府战略判断的显著差异。对于美国所处安全环境及其趋势与动因的负面定性,以及对于现有安全环境中主要行为体的类型区分,这些判断为拜登所提出的国际安全战略纲领奠定了基础。基于“与美国政治制度的相似程度”与“是否对美国安全现状提出挑战”两项维度,可以辨析出三类国家(参见表1)。②因为在政治现实与拜登认知中,并不存在挑战现状的西方民主制大国,因此本文对第一个象限采取了空缺的处理。第一类,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且被认为对美国安全现状产生强力挑战的大国,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第二类,实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且缺少挑战美国安全现状能力的国家,包括且不限于欧盟国家、英国和印度等,被视为美国应予以联合的国际盟友。③Jamie Dettmer, “Biden’s Initial Steps to Repair Global Ties Receive Praise in Europe, Asia,”VOA, April 27,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europe_bidens-initial-steps-repair-global-ties-receivepraise-europe-asia/6205122.html; Pat Cox, “Biden’s Europe Challenge: Repair Tattered Transatlantic Ties,” Poltico,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biden-europe-challenge-repairbroken-transatlantic-relationship/.第三类,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且缺少安全挑战能力的国家,以第三世界的中小国家为代表,拜登在现有的政策规划中并未较多关注这类国家,更加重视避免美国被相关区域内冲突所牵连。这三类行为体构成了拜登认知中的国际安全环境。

表1 拜登总统关于国际安全行为体的认知类型
2.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的评估
拜登关于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来自两方面:从范围上看,美国面临着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威胁;从行为体类型上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体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中的非明确主体。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被明确指出的“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行为体,其中,中俄两国还“被特意指出”对美国产生了全球性的“安全威胁”。①“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Democracy in Action, July 11, 2019, https://www.democracyinaction.us/2020/biden/bidenpolicy07111 9foreignpolicy.html.
拜登的国家安全威胁理念具有三个要素:危及美国霸权的大国竞争、渐趋显著的全球安全议题关切以及对长期敌对国家的冲突管控理念。其一,拜登认为,中俄等国经济、军事实力的提升,违背自由主义国际规范,增加了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风险,甚至对美国本国安全增加了“威胁”。②Quint Forgey and Phelim Kine, “Blinken Calls China ‘Most Serious Long-Term’ Threat to World Order,” Politico, May 26,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5/26/blinken-biden-chinapolicy-speech-00035385.其二,拜登将全球安全议题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这些议题缺少明确的行为主体,需要政府间合作的介入,这为美国联合其他盟友留出了议题领域空间。对于这些安全议题的认知和表述,回应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关切,是落实选举承诺的表现。③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the Build Back Better Framework,” October 28,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8/president-biden-announcesthe-build-back-better-framework/.其三,对于美国的传统敌对行为体,包括朝鲜、伊朗以及极端组织等,拜登试图采取比前任领导人更柔性的方式,摆脱它们带来的战略威胁。这些传统上对美国产生重大“安全威胁”的行为体,当前则“成为拜登解决更严重战略威胁的障碍”,④Ben Rhodes, “After 20 years, Biden’s Afghanistan Withdrawal Has Finally Ended the 9/11 Era,”The Guardian, September 10,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sep/ 10/20-years-biden-afghanistan-withdrawal-ended-9-11-era.而非直接撼动美国的国家安全。
由上可知,拜登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是基于对行为体挑战美国现状能力与意图的认知而得出的。在他看来,前者表现为军事实力与经济、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是否削弱了美国领导地位,后者则是基于目标国是否实行西式民主政体的简单判断。因此,在被判定为正在挑战美国安全现状且政治体制与美式民主差距越大的行为体,越会被拜登断定为重大国家安全威胁。重点关注军事或经济安全之外的政治价值观影响力变动,是拜登国家安全威胁观念的一项主要特点。

表2 拜登总统对美国安全威胁来源的界定
3.军事、经济与价值安全目标设定
美国是二战后西方世界体系的主要领导国,对于其安全目标的理解,离不开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战略布局规划的认识,拜登称之为“安全同时意味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①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ing the Fiscal Year 2023 Budget,”March 2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28/remarks- bypresident-biden-announcing-the-fiscal-year-2023-budget/.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表现出了对“硬”安全之外多元安全议题的关切。美国领导人的安全目标在地理范围上可以分为本土安全与全球安全,在议题领域上则可以分为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与政治价值观安全。而拜登视阈中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是推进本国的“安全、繁荣与价值观”。②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拜登在这三个维度上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认知是,将实现并维持美国在物质与价值层次的超越性地位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参见表3)。

表3 拜登总统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认知
在军事安全领域,拜登重视维持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目标,并强调中俄等国为美国带来的安全挑战。一方面,拜登沿袭了以往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点,即维持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确保美国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准备最好、训练最好、装备最好的军队”;①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ing the Fiscal Year 2023 Budget,”March 2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28/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nouncing-the-fiscal-year-2023-budget/.另一方面,拜登在全球安全目标的认知上有了显著变动,他将来自中俄等大国的竞争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风险,并明确指出美国要克服潜在战略对抗的风险。
在经贸技术领域,拜登判定本国所处安全状态的标准是,美国是否维持了世界最强经济实力与经贸信誉。拜登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应确保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国内经济复苏紧密结合起来。②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他强调“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创造共同繁荣的关键源于国内”,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和重塑产业链入手。③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utlin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October, 202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 speeches-andremarks/2021/october/remarks-prepared-delivery-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在国际制度参与方面,拜登希望修复特朗普时期频繁“退群”对美国经贸信誉带来的损害,而更倾向于提升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领导力,借以对冲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更新我们自己的民主和联盟”。④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在政治价值观领域,拜登的国家安全目标是实现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完全胜利。拜登将“民主”的具体目标界定为“支持自由、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促进民主技术与捍卫自由、公平的选举政治”。①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Announcing the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Dec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 09/factsheet-announcing-the-presidential-initiative-for-democratic-renewal/.拜登是典型的建制派精英,坚信美国传统主流政治价值观,西方式民主观念系统地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中。拜登一直以“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思维框架认知世界政治,确保美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优先性,针对民主衰退的现状则竭力使其恢复到理想状态,这是拜登对于国家安全目标的价值观式阐释。
(二)拜登安全信念中的策略手段偏好
在面对特定的战略选项时,领导人对于策略手段的偏好既是对国家安全本质认知的结果,也是对外政策输出的重要前提。基于前述对于拜登认知中的国家安全环境、安全威胁来源与国家安全目标的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将采取何种手段以及为何选取特定手段来达成既定的安全目标。
本文认为,拜登偏好于在低安全议题上通过外交路径采取积极的安全战略,但当涉及核心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时,则不惜采用对抗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在涉及国际冲突时,拜登会优先采用后发制人的军事手段,并且更倾向于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处理安全问题。其安全策略倾向可以总结为“跨议题、强价值、后发式、多主体”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安全程度存在高低差异的手段选项,拜登的战略偏好聚焦于政治价值观等低安全议题。拜登摒弃直接对抗性质的战略安全竞争方式,并展示出持续推行西式民主价值的意愿,以及在这一议题上联合西方国家的倾向。对于不符合西式民主标准的“威胁性”国家,拜登直斥其为美国政治价值观的敌人。②Daniel Fried and Rose Jackson, “How to Get Biden’s Democracy Summit Right,”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9,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o-get-bidensdemocracy-summit-right/.将大国战略竞争限定在价值之战、言辞之战的维度,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是拜登处理战略竞争的一项策略偏好。
其次,拜登侧重运用价值观要素塑造战略竞争的外交路径。其个人政治经历塑造了他通过外交路径达成战略目标的偏好。拜登长期从政,与国内外政治精英建立起深厚的个人联系,在华盛顿享有“战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的声誉。①Michael Crowley, “‘Strategic Empathy’: How Biden’s Informal Diplomacy Shaped Foreign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5/us/politics/joebiden-foreign-policy.html.但当安全议题与拜登民主价值观背离时,他则倾向于采取激烈的言辞或行动传递意图。尽管拜登偏好外交沟通的战略路径,但在涉及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议题领域,他倾向于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与目标国家进行竞争对抗,达成本国在价值观维度的安全目标。
再次,拜登认为军事行动应作为国家安全目标的最后手段。拜登对高烈度军事行动的战略收益抱有怀疑态度:“困在无法取胜的冲突中,只会消耗我们在其他待关注问题上的领导能力。”②“The Power of America’s Example: The Biden Plan for Leading the Democratic Worl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Joe Biden, https://joebiden.com/americanleadership/.在他看来,采取军事手段只能用来“回应”而非“发起”攻势,而且必须是在本国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刻才能加以运用。2021年拜登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具体阐明了美国使用武力的标准:只有在本国遭受“持续不断的攻击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之时。③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6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降低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手段在外交决策中的首位度,延迟采取武力手段的战略时机,是拜登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
最后,拜登强调要联合多边主体以实现战略安全目标。其价值观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威尔逊主义的政治传统,即国际主义与道德主义。他多次指出,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联合才能解决安全问题,正如他所宣称的,“美国的联盟是我们最大的资产”。④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拜登进而倾向于通过国际制度合作的形式应对国际安全议题。具体来说,这些举措既包括重返国际合作制度,修复美国与国际组织在特朗普时期受损的关系,也包括在核心战略区域加强与传统盟友、周边国家的联合。拜登摒弃了前任总统的单边行动倾向,在国际合作制度、区域盟友合作与联盟共同防御方面,拜登表现出了强烈的多元主体联合倾向。
(三)拜登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战略动员
拜登就任总统以来,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主要基于言辞与行动进行理念式动员,以及通过强化安全制度进行稳定的战略资源汲取,试图为推行其安全动议增强国内和国际凝聚力。拜登在政治动员中的策略具有政治形象塑造、安全威胁建构与战略动力整合三个维度。
其一,拜登着意塑造自身富有领导力的政治形象,为有效的战略动员提供符号动力。拜登试图将本人塑造成一个重振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符号。他在白宫官方网站的个人主页开篇即阐明“作为总统,他将恢复美国的领导力”,并将这一点作为本届政府的“当务之急”(priorities)。①The White House, “Joe Biden,” https://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president-biden/;The White House,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mmediate Priorities,” https://www.whitehouse.gov/priorities/.这一辞令体现了其本人对自身国家安全职能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安全环境目标的理解。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他将当前的战略转折时刻,与美国内战、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九一一事件等重大安全挫折相类比。②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拜登试图在美国国内与传统西方国家联盟中,扮演一个恶化安全环境中的“警醒者”形象,他曾明确表明本届美国总统要承担“收拾残局”(picking up the pieces)的职责,③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以此展示改善美国所处安全环境的核心意图。④The White House,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3, p.53,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3/budget_fy2023.pdf; U.S.Department of Defense,“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Dr.Kathleen Hicks Remarks on President Biden’s Fiscal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980638/deputysecretary-of-defense-dr-kathleen-hicks-remarks-on-president-bidens-fisca/.
保证本人在每一项重大决策中的显著性与存在感,是拜登从政以来的一项标志性风格。在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拜登就力求让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副总统之一”,⑤Steven Levingston, “Joe Biden: Life Before the Presidency,” Miller Center, https://millercenter.org/joe-biden-life-presidency; Mark Halperin, “Halperin on Biden: Pros and Cons,” Time, August 23,2008,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835480,00.html.他在包括参与重大战略问题决策、外交沟通与领导人会晤和对重大立法提出意见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同样保持在各个重大议题中的较高曝光度,承担重要安全决策的指导者身份。在拜登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就公共卫生、经济政策、移民问题和气候合作等核心议题签署了十几份法案。①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elect Biden’s Day One Executive Actions Deliver Relief for Families Across America Amid Converging Crises,”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0/fact-sheet-president-elect-bidens-day-oneexecutive-actions-deliver-relief-for-families-across-america-amid-converging-crises/; Alice Ollstein, Arjun Kakkar and Beatrice Jin, “The 17 Things Joe Biden Did on Day One,” Politico, January 22, 2021,https://www.politico.com/interactives/2021/interactive_biden-first-day-executive-orders/.拜登试图通过这类具有鲜明表演色彩的举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积极有为的领导人形象,从而提升其政治动员的效力。
其二,拜登通过向外界渲染其认知中的对美安全威胁,提升其对外战略的合法性。拜登通过加速其对于美国安全威胁认知的传播,并在敏感议题上采取标志性的对抗,以表明本人具有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意愿与能力。例如,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面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态势,拜登在2022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国的“21 世纪是经济竞争的世纪,尤其是与中国”,而美国必须要获取胜利。②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March 2,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02/remarks-by-president- bidenin-state-of-the-union-address/.拜登将矛头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这类举动表现出明显的“道德主义”色彩,实际上是基于现实考量,意在向国内、国际民众传递符合领导人预期的战略形象。
俄罗斯是拜登认知中的另一个安全威胁来源。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拜登号召为格鲁吉亚募集1 亿美元资金,并在政界抵制俄罗斯的“入侵”行为。③Lori Maguire, “‘A Weapon of Mass Disruption’: Joe Biden on Russia,” Academia Letters, July,2021, pp.1-5.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迅速将俄罗斯视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最激烈对抗者,将这次战争称为“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④Robin Wright, “Does Biden’s Presidency Hang on the Crisis with Russia?” The New Yorker,January 27, 2022,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bidens-presidency-may-hang- onthe-crisis-with-russia.并强调俄罗斯“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稳定……试图分裂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⑤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ing Actions to Continue to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March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11/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nouncing-actions-to-continue-to-hold-russia-accountable/.另外,由俄罗斯总统主导的政治体制长期为西方所诟病,美国政府以“独裁”“寡头”来描述普京政府,且这一语言对抗烈度仍在持续升级。
其三,拜登积极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以凝聚国内外政治力量,实现政治动员。西式民主之所以成为拜登战略动员的抓手,是由于其所谓的价值特性。一方面,各个政治文明、主权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对民主的界定参差百态,一言以蔽之的“民主”缺少具体的操作指标与判定标准,在政治叙事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为美国对世界政治中各项事务均冠以“民主”之名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西式民主是欧美国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中的核心逻辑,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原则,采取这一价值观策略意在联动美国国内与国际:既有助于在实现美国国内战略观念一致性的前提下实施安全决策,也有助于使西方国家间深化合作“师出有名”。①朱锋、倪桂桦:《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 期,第1-18 页。
早在竞选总统时期,拜登就宣称重振美国的“天定命运”,“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盏明灯”。②“Joe Biden’s 2020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Speech,” ABC News, August 21, 2 021,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full-text-joe-bidens-2020-democratic-national-convention/story?i d=72513129.而在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他又提出要让美式民主价值观居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地位:“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与我们的外交领导力结合起来。”③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 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对于在特朗普时期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等国际制度,拜登频频向其释放积极信号。这些有意的信号释放,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黏合政治力量,使物质、人力与观念资源为拜登所用,增强其战略塑造能力的动员路径。
三 拜登国家安全思维的政策实践
在分析梳理了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后,需要进一步明晰这些安全观念对国家对外安全战略及其实践的影响。本文对于拜登何以影响美国安全政策输出作出了推论:拜登在安全议题上所受结构性约束较弱,同时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战略环境,这使他能够依据自身安全观有效地塑造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拜登政府的对俄、对华政策实践验证了上述推论。
(一)拜登安全理念的政策效应
根据对拜登战略思维特质与前述分析框架的匹配,本文认为在安全议题上,由于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较弱,且处于较为复杂的战略环境中,因此拜登的个体政治信念得以明显地体现在国家安全政策中。
第一,拜登总统在安全议题上受到的外部结构限制较弱,因而具有较强的国家安全政策形塑能力。拜登依据个体偏好积极地设置战略议程。领导人个体政策偏好与国内政治的匹配程度高,可以降低战略决策的推行阻力,①尹继武:《领导人、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沟通(2016—2018)》,《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 期,第91-118 页。因此,尽管性格特质有较大的敏感性和压力屈从性,但拜登自上任以来表现出了对外部政治约束的高度适应。②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 期,第11-21 页。在议程创新上,拜登主导下的美国安全战略新方向包括重塑国内民主制度、积极加入多边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气候与反腐败合作等议题。③Katrina Mulligan, Alexandra Schmitt and Siena Cicarelli, “The First 100 Days: Analyz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Success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xt Year,” American Progress, May 6, 2021,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irst-100-days-analyzing-bidenadministrations-foreign-policy-successes-opportunities-next-year/.这些议题在之前的美国政府中涉及较少,而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直接成为其执政方向。在议程重塑上,传统安全议题包括中美关系、美朝关系、联盟管理和贸易政策等,④“Where Biden and Trump Stand on Key Issues,” Reuters, July 8, 2020, https://graphics.reuters.com/USA-ELECTION/POLICY/ygdpzwarjvw/.拜登仍然将这些主流议题置于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但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试图展现出与前任总统的显著区别,更加倾向于采取多边的、宏观的战略手段,表现出了针对前任领导人的较大扭转。拜登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设置议程,与其在美国政府的长期从政经历有关,他在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构建了复杂的政治人际网络,并乐于在此基础上达成政治目标。⑤Robin Wright, “The Seven Pillars of Biden’s Foreign Policy,”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1,2020,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columnists/the-seven-pillars-of-bidens-foreign-policy.在既定约束内积极创新战略议程,是拜登得以突破既定约束的表现之一。
拜登在安全决策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表现为拜登对于外交安全政策团队的人事管控有力,以及对于安全政策团队保持着有效的政治信念输出。人事关系紧密确保了拜登在团队管理上的有效性:安全政策团队较为忠诚地接受和贯彻其安全理念,团队人员的对外表态明显具有协调性,体现出较高的理念相似度。拜登就任以来,其安全政策团队成员尚未发生明显变动,也没有重要成员离任的预兆。①据统计,拜登带领的安全政策团队在第一年的离职率,是最近六任总统班底中最低的。参见Kathryn Dunn Tenpas, “‘A-Team’ Turnover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 Return to Normalcy,”Brookings, January 20,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22/01/18/a-team-turnover- inthe-biden-administration-a-return-to-normalcy/。另外,领导人的信息偏好将会塑造政策团队的信息反馈方式。②Margaret G.Hermann and Thomas Preston, “Presidents, Adviser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 of Leadership Style on Executive Arrange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5, No.1, 1994, pp.75-96.安全政策团队与拜登的政治关系网络、党派政策倾向与舆论信息管理较为接近,也进一步强化了拜登及其团队的立场一致性。上述因素使得拜登能够向政策团队深度输出他的安全战略理念。
第二,美国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内外战略环境中,因而拜登总统个体理念对安全政策的影响更加显著。拜登认知美国面临着源自多元主体、多重领域的全球战略竞争风险。这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国际秩序变动与战略资产震荡。首先,美国精英及大众的威胁认知与安全偏好,重新设置了美国的外部安全结构,即在中美权力结构变动与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上延续了美国国内共识。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共同信念生成,为拜登施展自身安全理念提供了决策环境,同时降低了安全战略出台的阻力,迎合和强化了拜登的价值观安全化建构与盟友间合作。③左希迎:《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及其根源》,《外交评论》2022年第3 期,第21-47 页。其次,从前任总统特朗普开始,美国经历了剧烈的对外政策理念震荡。特朗普积极地推行单边外交与“退群”主义,不仅重塑了基于国际秩序的交往规则,也使得二战以来美国长期经营的自由主义霸权遭到削弱。④周方银、何佩珊:《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当代亚太》2020年第2 期,第4-39 页;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 期,第84-115 页。因此,拜登具有更强的动力修复美国受损的战略信誉,在践行国际主义、道德主义政策上更具能动性。可见,国际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了拜登践行安全观的潜力。
国内政治撕裂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直接冲击。目前,美国政治极化明显,具体表现包括党派斗争剧烈、党内派系分散以及民众观念割裂。⑤周琪:《政治极化正在溶蚀美国的民主》,《美国研究》2022年第2 期,第9-34 页。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拜登总统竞选成功后,美国国会大厦遭受严重的暴力事件,冲击者们试图推翻选举结果。⑥“Capitol Riot: Biden to Blame Trump for ‘Carnage’ One Year on,” BBC, January 6, 2022,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9889760.这类事件标志着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内的黏合作用面临失效的风险。在这种稳定性不足的政治结构中,拜登不必因循长期以来的领导人战略倾向,而是可以较强地发挥其政治灵活性。尤其是对“中国威胁论”与俄罗斯军事行动加以能动的威胁性认知及宣传,以此重塑美国的政治安全观,这也是拜登提升国内支持度、增加政治收益的一项重要抓手。
(二)拜登的安全政策塑造:基于拜登政府对俄、对华政策的分析
俄罗斯和中国是拜登认知的“对美最大安全威胁”,在其国家安全信念中,两国不仅给美国军事安全带来了风险,也引发了针对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军事霸权的挑战。通过对比分析拜登个体认知与拜登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具体实践,可以辨析上述关于拜登安全思维发挥战略效应是否成立,以及决策者塑造美国安全战略能力的程度高低。
1.拜登对俄信念与安全政策生成
在拜登的安全思维中,俄罗斯一直被视作美国的安全威胁。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拜登一直认定,俄罗斯作为非传统西方政体的军事大国可能会在安全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他认为当前的美俄关系是美苏冷战的延续,尽管美国获得了冷战的胜利,两国仍然保持着高度安全与价值观的竞争关系。①Dmitri Trenin, “Joe Biden’s Foreign Policy and Rus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19, 2020,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3270.除了军事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与价值观渗透也是拜登视阈中的对美重要威胁。俄罗斯被怀疑以影响投票结果的方式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②Julian E.Barnes and Charlie Savage, “8 Takeaways from the Senate Committee Report on Russian Interferen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20, https://cn.nytimes.com/usa/20200819/trump-russia-senate/.因此,2019年,拜登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到,他将在政治选举领域“反击俄罗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攻击”。③“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Democracy in Action, July 11, 2019, https://www.democracyinaction.us/2020/biden/bidenpolicy071 119foreignpolicy.html.
2022年俄乌冲突的发生又加剧了拜登这一威胁认知。俄罗斯因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与价值冲突,成为拜登安全观中主要的威胁来源之一,具体体现为拜登政府在对全球安全的区域规划中,重点关注以中东欧为核心的欧洲地区。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拜登迅速联合西方国家开启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拜登更是开启了高成本支持乌克兰的战略动员。2022年3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Ukraine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Act, 2022),寻求向乌克兰提供136 亿美元的全方位协助。①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Signing of H.R.2471,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2’,” March 1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signing-of-h-r-2471-consolidated-appropriationsact-2022/.在他看来,当前的乌克兰是俄罗斯与北约地缘争夺的重镇,俄乌冲突是西方民主政体与“专制”的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支持乌克兰事关美国对西方社会的安全承诺。
为了应对俄罗斯这一战略竞争对手,首先,拜登明确要避免两国在军事安全上爆发直接冲突。较之前一届政府,拜登更为积极地推动两国军备管控和冲突管理议题。②Pranay Vaddi, “How Biden Can Advance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Stability with Russ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77, No.1, 2021, pp.18-20.2021年,美俄分别达成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Treaty)与《美俄战略稳定联合声明》(U.S.-Russia Presidential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Stability)。其次,拜登在对俄政策上延续了“低武力偏好”这一长期决策倾向。例如,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只提出“为乌克兰提供最低限度的协助”。③U.S.Congress, “Ukraine Supplemental Summary,” https://appropriations.house.gov/sites/democrats.appropriations.house.gov/files/Ukraine%20Supplemental%20Summary.pdf.再次,拜登在对俄问题上涉及民主价值观的问题时,采取了激烈的回应。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拜登在演讲中即兴地表示“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引发了国内外的轩然大波,以至于政府成员出面澄清美国并无这一意图。④Lauren Gambino, “‘I Make No Apologies’: Biden Stands by ‘Putin Cannot Remain in Power’Remark,”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mar/28/bidenvladimir-putin-power-russia-ukraine.最后,拜登在对俄问题上偏好采取多边主义的行为,如他所称,“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坚守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⑤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President Joe Biden on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Call with President Zelenskyy of Ukraine,” June 1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15/statement-by-president-joe-biden-on-support-for-ukraine-and-call-withpresident-zelenskyy-of-ukraine/.为此,他积极推动安全同盟和周边伙伴的参与,而非单边介入,这一点也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偏好的一项重要特质。
拜登就其对俄安全政策进行积极的战略动员。首先,拜登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维护西式民主的英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拜登在这一议题上采取了高强度、高频次的发声,也将此作为增强国内政治支持的一项策略手段。2022年2月至7月,白宫官方网站上直接与乌克兰局势相关的总统演讲与政策声明约有四十份;拜登本人也宣称,他每周会与乌克兰总统进行“大约四次通话”。①Emily Goodin, “Biden Says He WON’T Visit Ukraine during His Trip to Europe aft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Went to Kyiv for the Second Time,” Daily Mail, June 20, 2022,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935155/Biden-says-wont-visit-Ukraine-trip-Europe.html.其次,拜登极力渲染俄罗斯对美国及其伙伴国的安全威胁,并以民主价值观为核心议题,试图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友的联系。在2022年的北约峰会演讲中,拜登称:“我们团结了我们的联盟,以应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中国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构成的系统性挑战”。②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June 30,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6/30/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madrid-spain/.通过对俄罗斯的威胁渲染,拜登塑造个人政治形象,汲取国内外政治资源,这是他将对俄安全政策作为战略动员的一项重要语境。
拜登政府提升了对俄战略对抗政策的优先性。其一是政策目标调整。拜登政府一改上任初期竞合手段相结合的态势,调整为限制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降低俄罗斯对乌“侵略”的军事能力,乃至改变俄罗斯的国内政治结构。③孙成昊:《俄乌冲突重塑拜登对俄政策》,中美聚焦,2022年4月19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20419/42570.html。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公开表示,美国希望俄罗斯“被削弱到无法发起对乌冲突的程度”。④Kylie Atwood and Jennifer Hansler, “Austin Says US Wants to Se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akened,” CNN, April 25,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4/25/politics/blinkenaustin-kyiv-ukraine-zelensky-meeting/index.html.其二是政策手段变更。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是对俄极限施压、让俄方承受高度损失,以期改变俄罗斯决策者对乌军事行动的收益结构。美国政府对俄罗斯进行了高烈度遏制,具体表现为俄乌冲突前的对俄威慑行为与冲突期间的对俄强制行动。⑤Frank Hoffman, “America Needs a Comprehensive Compellence Strategy Against Russia,”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28, 2022,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2/04/america-needsa-comprehensive-compellence-strategy-against-russia/;左希迎:《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5 期,第1-8 页。这些手段包括强化出口管控、增加对俄关税、中止能源合作和直接制裁俄国内精英等,以实现对俄“重大且即刻”的制裁。⑥《简报:美国、七国集团和欧盟对俄罗斯施加重大且即刻代价》,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2022年4月7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fact-sheet-united-states-g7-and-euimpose- severe-and-immediate-costs-on-russia/。另外,美国也中止了美俄两国在军备议题上的有限合作,以双方战略竞争风险同时增加的方式,更为清晰地释放战略决心。其三是政策主体扩展,拜登政府动员一切国内外资源对俄进行非直接对抗的战略竞争。在避免美俄直接冲突的前提下,以武器运输、情报共享和经济援助等较为间接的介入方式对抗俄罗斯;另外增加共同战略遏制俄罗斯的行为体,并以此增加拜登政府的国内凝聚力,将俄罗斯塑造成彻底的敌对目标,实现美俄“全球范围内的对抗”。①Michael Hirsh, “Biden’s Dangerous New Ukraine Endgame: No Endgame,” Foreign Policy,April 29,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4/29/russia-ukraine-war-biden-endgame/.拜登政府对俄政策的目标、手段和主体呈愈发激烈的敌对趋势。
由拜登自身固有的对俄威胁认知,到美国政府战略对抗增强的政策生成,个体理念与政策结果具有高度重合的表现。拜登积极创立对俄安全对抗的战略议程,且在本届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另外,俄乌冲突让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战略目标陷入模糊,进而导致了国内安全观念分裂,国际盟友与国内民众对拜登政府的战略期望出现严重差异。因此,拜登的安全理念在对俄政策中从目标设定、手段变更与主题扩展三个维度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拜登政府也具有针对本国领导人的纠错功能,由于拜登本人采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理念表达,从而导致俄罗斯进行了高烈度回应,因此安全政策团队对此进行了澄清,其个人理念没有进入美国政府的战略议程。
2.拜登对华信念与安全政策生成
拜登把中国视为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严峻风险,将中国表述为当前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其本质是对中国战略意图与实力增长的高度质疑。其一,拜登将矛头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他看来,中国所走的不同于欧美民主的政治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导致了世界对于西式民主政体能力的信任溃败;中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限制了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发挥,进而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其二,拜登认为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实力提升可能给美国带来安全风险。他多次宣称,中国在军用技术发展上产生了对美国的直接挑战,如空间技术、网络能力和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发展。②“Biden Concerned over Chinese Hypersonic Missiles,” Reuters, October 2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biden-says-hes-concerned-about-chinese-hypersonic-missiles-2021-10-20/.拜登也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表现出对华遏制的思维,屡屡在市场地位、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与高新技术发展等议题上专门提及“中国对美国的威胁”。③佟家栋、鞠欣:《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挑战与应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6 期,第102-120 页。
受到这一威胁认知的影响,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得到了拜登政府高度重视。这一区域由美国西海岸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其中包括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地区。①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p.4,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拜登认定该地区“具有高度的经济与地理战略价值”,也是美国一项“渐趋复杂的国家安全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能力,以及美国盟友、伙伴在该地区能力的“强化与现代化”。②The White House,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3, p.50, 90, 9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3/budget_fy2023.pdf; The White House,“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拜登积极地采取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手段。首先,在宏观政治上,拜登政府注重避免陷入中美直接对抗的陷阱。中美战略竞争越激烈,对于管控两国竞争烈度的动力也就越强。③阮建平、邓凯帆、王佳敏:《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危机管控》,《国际展望》2022年第4 期,第62-79 页。拜登两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会晤,他强调了美中应避免直接冲突,“管理战略冲突的风险”,保持可预测的战略意图,避免陷入军备升级的敌意螺旋。④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The White House, “U.S.-Russia Presidential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Stability,” June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6/u-s-russia-presidential-joint-statement-on-strategic-stability/.其次,在拜登的政策叙述中,为可能的对华接触政策留出了一定空间,在强调中国可能为世界带来“一系列的风险”的同时,宣布“我们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北京合作”,⑤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而非直接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敌对关系。例如,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冲突激烈的关税问题上,拜登释放出了部分对华缓和的信号。⑥《外媒:拜登称正“逐一审查”对华关税》,参考消息网,2022年7月10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20710/2485089.shtml。再次,拜登试图采取泛道德化的对抗策略,发掘传统安全议题中的价值观对抗要素。拜登及其安全政策团队屡屡触及底线,多次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其背离承诺的程度在近几届美国政府中较为突出。①Amy Mackinnon, “Biden Struggles to Stick to the Script on Taiwa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7,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11/17/biden-taiwan-china-misspoke-policy-mistake/;李义虎:《拜登对华战略中的对台政策:战略定位与战略竞争》,《台湾研究》2021年第3 期,第1-9 页。最后,拜登倾向于积极联合西方盟友遏制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在各个领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拜登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为世界“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方案”。②Joe Biden, “Joe Biden: My trip to Europe is about America Rallying the World’s Democracies,”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05/joe-bideneurope-trip-agenda/.
在对华安全政策议题上,拜登也展现出明确的动员姿态。其一,基于个人形象塑造与价值观威胁建构的国内动员。拜登顺应美国国内日渐主流的遏华认知,在对华问题上发声颇多,从而迎合国内的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增强国内凝聚力。③赵明昊:《大国竞争的内政化:以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政策为例》,《美国研究》2021年第6 期,第9-34 页。其二,基于价值观与战略安全威胁渲染的国际动员。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存在一种将中国安全“威胁”泛化到各个议题的趋势,对抗中国成了一项动员伙伴国的政策话语,例如,2022年7月,在中东之行前夕,拜登撰文提出“总统的工作是保持我国的强大和安全……让我国占据战胜中国的最佳位置”。④Joe Biden, “Why I’m Going to Saudi Arabia,”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7/09/joe-biden-saudi-arabia-israel-visit/.中美战略竞争即是这类政治动员的动因,也由这些政治行动与话语导致烈度升级。
拜登政府清晰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持久、系统战略竞争的政策取向。首先,从政策目标来看,拜登政府寻求削弱中国对美国主导下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同时明确表达了其对中方利益底线的认知。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提到,“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增长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的国家”,⑤U.S.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因此,美国要担任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保护者。与此同时,他也表示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重申不支持“台独”。这一政策目标一方面延续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政策框架,将中国视作“竞争者”;另一方面也设定了这一竞争的边界与底线。其次,从政策手段来看,拜登政府倾向于采取多边主义的对华政策,试图在其框架中将中国与当前国际秩序对立起来,联合其盟友、伙伴与中立国家,在国际体系的场域中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其政策手段包括“投资”“调整”与“竞争”,①U.S.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其政策动向包括修复美国国内经济能力,强化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涉港、涉疆等议题上与中国展开价值观对抗等。
拜登个体安全理念同样与本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高度相似。拜登将中国视为“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克服这一“威胁”是保证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领导力的必由路径。与拜登的策略信念相同,美国政府倾向于以价值观方式、联合国际盟友制约中国,并对此进行国内外战略动员。由于美国领导人在对华问题上缺少外部制约以及在其认知中强调中国对美国带来了内外部战略环境冲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与策略选择与拜登个体的安全目标、威胁认知和策略倾向基本保持一致。
本节分析了拜登安全观的战略影响效应。拜登的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其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动所进行的调整,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外实施过程。与拜登本人的性格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他作为总统在国内政治中的主导位置,以及应对美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剧烈变动的政治需求,促成了其安全观在美国安全战略制定及实施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拜登安全观与拜登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安全政策的对比分析,验证了拜登本人的国家安全观念明确地体现在本届政府对中俄两国的安全政策实践中。
结 论
本文提出了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分析框架,并对美国拜登总统进行了个案分析。拜登作为建制派政治精英,其安全观沿袭了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威尔逊主义,具有很强的道德主义与国际主义倾向。在拜登的国家安全认知中,美国的战略环境遭受“重大破坏”,本国安全状况处于衰退趋势,而这一冲击的主要“风险”来源则是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制度大国。为了维持美国在安全、经贸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持续优先地位,拜登认识到需要通过以下四类策略来达成本国的安全目标,即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后发制人式与多主体合作。
拜登在决策过程中所受的战略限制较小,以及当前美国高度复杂的战略环境,使其安全观得以深刻塑造美国的安全战略决策。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思维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动因之一,但并非对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除了拜登本人的战略思维倾向,国内与国际结构力量的干预作用,以及安全政策团队对总统理念的输入程度和输出效果,都应纳入对美国安全战略决策及其影响的思考。拜登具有反映美国主流安全理念的动力和能力,并能够有效地将个体信念传输到政策文本中。本文通过构建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拜登个人信念以及美国政府对俄、对华政策的比较研究,分析和验证了这一结论。
论文的理论价值如下。其一,本文提出了分析领导人安全战略思维的抽象框架,并设置了具体概念指标。既有文献更为关注非人格化行为体(如国家)的安全观,对于个体的安全思维缺少系统论述。本文基于这一框架对拜登安全战略信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二,本文进一步提炼出,领导人所受的外部约束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限定其战略影响力的条件变量。作为分析个案,拜登的安全理念具有深度输出到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动力。
论文对领导人安全战略观念的研判和分析,对于预测当前的中美关系具有实践意义。理解美国总统的安全观与其决策环境,意味着可以深入分析美国政府安全战略的制约因素与推进动力。通过对拜登安全思维及其战略效应机制的分析,本文得出了针对拜登总统个体决策偏好、影响美国安全战略实践、未来美国安全战略演进趋势以及未来可能的重点冲突议题与美方策略选项的推论。上述分析结果厘清了拜登政府的核心战略意图,也为思考如何更细致地处理中美战略沟通问题、管控战略竞争烈度、促进两国关系良性互动提供了依据。
在与拜登政府战略互动时,中国尤其要关注在价值观等低安全领域可能的激烈冲突,从而将战略竞争限定在特定限度内。同时,基于本文对拜登安全观的分析,可以对其固有安全信念、或是有意投射的动员性话语加以区分,进而采取具有差异性的策略回应。另外,中国应高度警惕拜登在其他议题上泛化中国带来“安全威胁”的战略思维,在拜登政府尚未出台对华政策文件的窗口期,需保持战略沟通渠道通畅,并明确释放本国利益底线与竞争限度认知,避免因“议题联系”而在非传统安全议题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