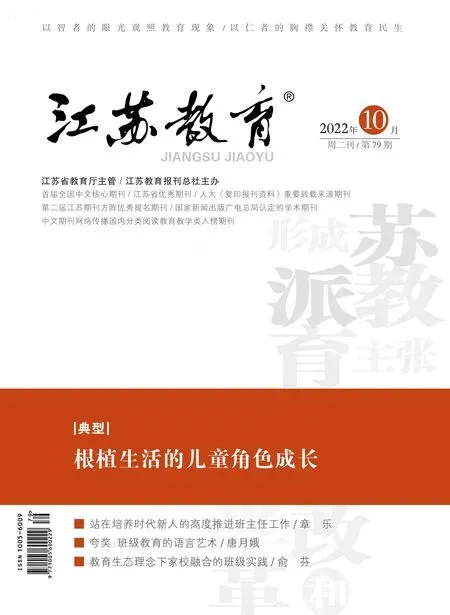相善其群:班级存续之教育性依据
张鲁川
我国“班级”这一组织形态始于1862 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在全国推广。受苏联的影响,我国于1952 年起实施“班主任制”,班主任的主要职责为学生的行为管理和指导。此后,班级作为学校基本的教育教学组织形态而存续至今,期间少有人对于班级的功能进行深入思考。2010 年,作为教育部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学校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首次提出了“行政班消失、取消班主任”的口号;2014年9月,浙江、上海从高一年级开始实施新高考改革,打破“固定班级授课制”,实行“走班制”,其他省市也渐次跟进推行。至此,班级存废与否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班级存废问题背后的更为根本的两个问题是:班级是否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如果有,这一独特价值是什么?
一、现代性文化特征及其对班级生态的影响
古代社会不存在孤立的个体,人们对个体理解都是嵌入在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与自然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并以其所处的位置来获得自我认同、行为规范、价值感和生活意义。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17~18 世纪启蒙运动将人从依附性关系中解脱出来。进入工业时代后,生产方式和物质特征也使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日益明晰,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空前的独立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代性之隐忧”,突出表现为由于伦理的失序或消解带来的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和人生意义的迷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的人不幸沦落为无实体的“个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疏离导致了他们意义感的缺失和精神的失落。泰勒认为人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他清楚地看到了“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是对古代生活的一种矫枉过正。
个人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主流思潮,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也无可避免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随处可以听到诸如“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实现自我”等标榜独特个性和自主性的“导师”忠告或自我宣言。但这种从伦理位序中的“脱嵌”在给我们带来自由感、自主感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困境。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幸福感却不如从前?为什么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我们却时常感到孤独?这种现代文化在学校、班级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缺乏责任感,越来越不会与他人共同生活……
二、班级独特育人价值的理论省思
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了21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共同生活”的提出正是基于对现代性流弊的深刻反思。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校长视点”公众号推出的《未来的教育,要有温度地育出人的器识》一文中指出,学校教育应包括三类成果:成人、成才和成群。其中,“成群”的提法很有洞见。但就目前而言,学校的“成群”教育是阙如的。“成群”教育包含着相当重要的价值观、规范、身份认同的互动与共享,其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不只成长为个体的成人,还能成长为共同体中有机的一员。如果学校在成人、成才教育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并积极实施“成群”教育,这将是学校对社会、对国家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分积极的贡献。
按照杜威“做中学”的思想,“成群”教育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群体生活。我国的学校虽然是一个大的群体,但囿于年级、班级的建制划分,且缺少像西方学校内诸如社团、俱乐部等学生组织,学生很少有真正的学校群体生活,而我国的班级恰恰是一个天然的群体生活场域。
我国的班级不同于西方“教学走班”的班级形式,而是固定的行政班级,是一群年龄相仿的学生共同学习、参与班级事务和各种活动的主要而稳定的场域。学生在校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班级中,班级不仅是学生听课、完成上级行政部门各种教育要求的场所,更是他们追逐打闹、聊天、游戏、分享秘密、合作完成项目的群体交往的地方。在这种社会性交往中,学生人际交往技能的提升、社会性情感的发展、对同伴依存感和对群体归属感的形成都有了可能,班级也就可能超越教室的物理空间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班、教学班,而成为一个能润泽学生生命的精神家园。因此,班级首先是一个“生活场域”,然后才是一个“教育教学场域”。
但毋庸讳言,受“班级授课制”和“班主任制”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班级更多是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教学班和作为“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的行政班而存在。在此定位下,这两种形态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即作为教学组织形式,是为了提升教学效率;作为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因此,班级的作用也被窄化为“应试的保镖”和“管理的工具”。尽管班主任被定位为“德育工作者”,需要承担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但班主任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使命。有学者指出:“现行学校制度中的班主任,实际上是学校行政系统中班级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所承担的往往是学校从校外承接的行政事务。在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到底有多少‘德育’或‘教育’含量,也就成为问题。”近几年,学界和实践层面逐渐认识到了班级的教育价值,并提出了“建班育人”的口号,这是对班级育人价值的回归,但仍然没有意识到“建班育人”之于其他育人路径的独特价值。笔者认为,班级作为一个群体组织和学生的共同生活场域,具有一种群性价值,是对学生进行“成群”教育的天然载体,有助于培养学生“相善其群”的公共精神,使学生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这个价值是其他育人途径难以达成的。
三、班级公共生活的开辟
班级的群性价值并不会自动显现。事实上,一个群体在一种自在状态下,更多的是冲突。霍布斯在其哲学巨著《利维坦》中早就揭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认为,一个群体在一种初始状态下,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想的是“我如何过得比别人好”,而难以成为康德所提出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那样的伦理实体。
班级要成为伦理实体,不能只是个体学生的集合并列,而必须致力于学生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唯其如此,才能使共同行动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就需要班主任开辟班级公共生活,让班级成为学生实践和习得公共精神,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最佳场所。所谓班级公共生活,即使个人进入他人,借由追求和秉持某种公共价值而让自己站到公共空间之中,从而超越自我孤立化的一种生活样态。在班级公共生活中,班级成员以班级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目标,班级公共权利为全体成员所共享,公共事务由全体成员所共治。每个成员通过积极承担共同生活的公共道德义务,在促进或增益能惠及每个成员的公共福祉的同时成就自己,养成公民人格和品德。
开辟班级公共生活,需要搭建学生参与班级公共事务的平台。冯志兰老师多年前就参与了我对开辟班级公共生活、开发班级“成群”教育价值的研究。冯志兰老师在成为上海市班主任带头人后,在她领衔的“上海市班主任带头人工作室”中开展了以构建班级公共生活为指向,以“班级会议”这一公共议事机制为核心,以班级五大公共平台为载体,培养学生个性与公共性统一的实践研究,并在上海与江苏省教育学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班主任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的苏沪两地班主任教研活动中展示了一个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召开的议题为“班级值日班长产生办法”的班级会议,与同行交流和汇报了她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理论研究者和一线班主任的高度评价。
人是社会性动物,过度强调个性和独立的个人主义只是人类在某个历史阶段的集体幻觉,共同体才是人类命中注定的归宿。个体的价值与存在意义需要在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得以确认与实现,其精神也需要在共同体中得以安顿和享受。在此意义上,班级应该致力于培养学生“相善其群”的能力,使学生从复数的“我”成为整体的“我们”,并学会“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不仅是班级存续的正当性依据,也是教育的终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