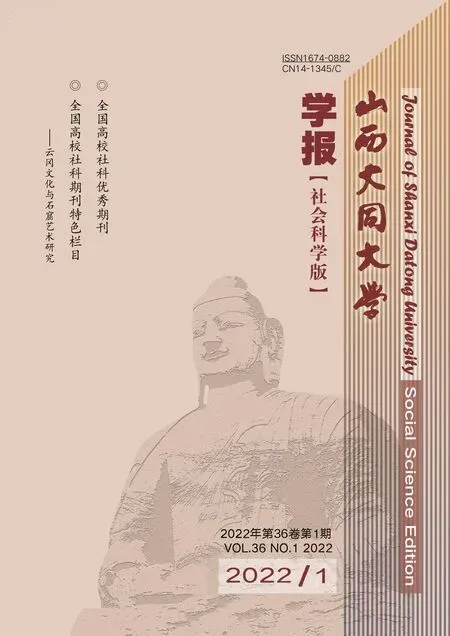北魏死刑制度立法刍议
周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中国古代遵循“慎刑”的法律原则,统治者对待死刑的态度也是极为慎重的。研究北魏死刑制度,有必要从思想指导立法的视角切入,探求这一时期对待死刑的态度。北魏建立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废墟之上,又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经营中原,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和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差异较大。本文拟就北魏政权三大发展阶段为线索,梳理死刑制度在不同时期的立法变化。
一、鲜卑代国时期非成文法:习惯至上,军刑合一
这一时期判例习惯法盛行。游牧民族相较于汉族最大的不同就是“居无定所”,人口分布相对分散不集中,缺少有效的统一辖制,这就使得成文统一法律没有施展的空间,高度依赖部俗的习惯法成为主流。习惯法内容单一明确,将几类最为常见的犯罪行为作出规定,言简意赅,对于文化水平低下、生活简单质朴的部落生活较为适用。习惯法对待犯罪行为的处理方式也简单粗暴,充斥着同态复仇的色彩。到代国建立后,经历了几次法律的整合,惩罚犯罪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明确,大体可总结为“抵物”、“抵命”两类措施。但该时期的习惯法较为明显的缺陷就是对犯罪情节的轻重区分不明显,死刑适用范围广泛。鲜卑氏族文化上的落后对法律的影响还体现在伦理层面,与汉族儒家文化“尊尊”、“亲亲”不同,鲜卑法律不优先保护长者权利,“杀父兄无罪”有违汉族社会所倡导的儒家伦理观,在鲜卑则成为普遍遵行的习惯。频繁征战的部落生存环境使得鲜卑人必须优先保证兵源和劳动力人口的充足,尊老敬长等伦理道德都要为此作出让步。
鲜卑代国时期的立法思想和法制建设深受部落部俗的影响,在没有成文法律甚至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能依据原始习惯断罪定事。常年征战的生存环境使得军法被结合到法律之中,“军刑合一”,“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1](P2873)
北魏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统治者更为重视对危害政权统治重大犯罪的打击,死刑也多存在于这一领域。大逆、亡叛等国事犯罪,就属于典型的重典惩治的罪目。在鲜卑代国时期,反逆犯罪罪犯的亲族不论性别、年龄、亲疏“皆斩”,且一概不免除连带责任。至北魏政权建立后,此种宗族连带刑罚演变成富有特色的“诛同籍”,北魏中前期频频使用该刑罚。除大逆、亡叛等罪外,还有其他比照大逆罪惩处的罪名,如“误军期”、“违大人言”等。[2](P31)频繁的征战使得军事犯罪在所有刑事犯罪中占比高、影响大,因此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贻误战机、谎报军情对作战有着重大负面影响,务必“同大逆”严处,“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1](P9)这类罪名的确立与鲜卑代国自奴隶制社会向封建集权社会过渡的趋势是分不开的,尊卑观念的树立必须有法制的保障,“违大人言者,罪致死”。此外,流刑在鲜卑代国也已经被广泛使用。流刑的出现是为弥补死刑过重而生刑过轻的畸形刑罚体系,“亡叛”罪多适用此刑,往往被作为死刑的替代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犯有重罪的贵族逃避死刑的途径。
对于严重罪行,鲜卑统治者制定了野蛮残酷的刑罚。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造成了“兵刑不分”的理念,统治者将对外征服和对内镇压相结合,产生出一系列严酷刑罚。除枭、斩等常规死刑,还伴有大量极为残忍的执行方式,轘、生脔割而食、大刃锉杀、腰斩、沉渊等异常残酷的死刑方式广为存在,这种刑罚上赤裸的暴力色彩也是鲜卑从氏族部落向国家机器过渡的必然选择。
二、神麚修律:胡汉杂糅,严刑峻法
北魏建国并定都平城后,国家从混乱渐渐走向有序。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下,统治者迅速确立了“阳儒阴法”的施政方针,籍此指导立法司法实践。道武帝初入中原,天下甫定。为了缓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巩固拓跋氏在中原的统治,道武帝采取了宽简仁厚的法律政策,
“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1](P2873)
北魏建国之初,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百姓苦不堪言,急切期盼社会稳定、生活富足、法治清明。道武帝亦能体察民间疾苦,命人修整法律,删除较为严苛的规定,“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1](P2873)官员大都能够依法办事,百姓也欢欣鼓舞,衷心拥戴。至道武帝后期,战乱和灾祸屡屡发生,为整饬纲纪,法律又趋于严酷。北魏尊曹魏为正统,故效仿汉魏明定法令,多弃晋律,之后整个北魏重刑律的传统也由此而传续。天兴元年,道武帝命三公郎中王德、吏部尚书崔玄伯等制定法律,为天兴律。崔氏为曹魏大族,志在恢复汉魏制度,其对北魏循汉魏而弃晋的法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天兴律主要内容因循汉魏律。明元帝时,继续以安定民心为主,改革官制。明元帝拓拔嗣较为熟悉并十分重视民间事务,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一同处理民间争讼,使社会基层治理恢复到有序的状态。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前期富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期间也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太武帝即位之初,患前朝刑罚之重,已不能完全适应日渐强大的北魏王朝的发展。神麚四年,命司徒、崔玄伯之子崔浩“定律令”。此次修律可见资料虽然有限,但内容涉及较为全面,涵盖了死刑刑罚、罪名、法例、司法诉讼等诸多方面。
神麚修律规定了生命刑、肉刑、劳役刑等刑罚种类。生命刑即死刑,神麚修律在继承鲜卑刑法中主要死刑方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取舍和发展,有斩、绞、腰斩、轘、沉渊等。轘即车裂,其和腰斩都是自奴隶制社会演化而来的刑罚,最为残酷,适用于大逆、灭亲等直接威胁封建统治的犯罪。针对大逆不道罪行,北魏统治者采取了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除犯罪者本人当死外,其亲族皆会受到“诛同籍”的牵连。“按汉律,不道无正法,最易比附,以不道伏诛者无虑数十百人。俱见《汉书》各记传。魏晋以来,渐革此弊,元魏定律多沿汉制,此其一端也”。[3](P369)“诛同籍”作为缘坐刑的一种,意在扩大惩治范围,起到震慑作用。神麚修律鉴取曹魏律,对被株连的犯者亲族予以区分对待,将女子和年十四以下的男童排除在死刑范围之外。女子没入官府为奴,男童处以宫刑,以此既可不留后患,又能保存劳动力,一举两得,此为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绞刑是北魏时期在成文法中新增的刑罚,陈顾远先生考得“绞之入律实自此始”。[4](P186)沉渊为北魏特有的刑罚方式,受刑人身体被捆绑以羊犬等动物,投入深水。该刑罚保留了浓厚的部落法制色彩,被用来惩治巫蛊等犯罪。
在明确规定的死刑适用刑罚的原则中,“官当”和刑事责任年龄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法律允许将量化后的官爵等级作为折抵罪行的工具,与以金赎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封建特权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神麚修律将十四岁作为减轻刑事责任的一个年龄分界线,不满十四岁的可减半量刑。已满八十岁和不满九岁的耄耋和幼童,除杀人罪之外的罪行可免于刑事处罚。但基于前文所述大逆不道罪的处罚措施,可见该原则并不是通用于所有情形。此外关于行刑时怀孕的妇女可待生产后百日再行刑以及拷讯次数限制等规定,也被后世所借鉴和发展。
神麚修律对死刑复核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当死者,部案奏闻”,因死刑涉事重大,需谨慎实行,地方直接判处死刑恐有局限和疏漏。故而“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1](P2874)地方死刑案件需先呈报中央,由皇帝亲自复审。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死刑案件判决的审慎公正,又趁机将地方的死刑终裁权收归中央,实现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
此次修律对几类重要死刑罪名也作了规制。除前文所述大逆不道罪,还有侵犯他人生命和社会秩序的蛊毒犯罪。蛊毒就是将含有剧毒的蛊虫研制成可用于人体的毒药杀人,被下蛊者极端痛苦、惨不欲生。蛊毒作为一种较为隐蔽的作案手段,广泛存在于宫廷和民间,对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冲击。因此,神麚修律中,造蛊害人者“男女皆斩,焚其家”,不仅要处死犯罪者,还要彻底销毁蛊物遗痕,免生后患。中国传统社会极重孝悌,对于杀害尊亲的残忍行为,神麚修律以轘刑处之。对大逆不道、蛊毒、害亲等直接冲击封建统治及伦常的罪行实行重点打击,可视作后世“重罪十条”的雏形。
高宗文成帝和显祖献文帝时期,北魏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不再有连年的征战,国家发展重心由外转内。太安四年,文成帝下令修律,在神麚和正平两次修律的基础上“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1](P2875)此次修律增加了较多篇幅,尤其是门房之诛和大辟的增加,使得刑律比以往更重,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大。
从道武帝至献文帝,北魏先后经过了数次修律,由部落法制过渡到封建法制,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汉魏法律传统,颇有建树。但由于这一时期汉文化的影响尚未深入,因此许多拓跋习俗也得以保留。神麚修律是北魏初期一次重要的立法活动,从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依旧保留有诸如沉渊、轘等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规定,但对死刑制度的各方面内容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死刑适用原则、重点罪名、死刑案件的审判和复核、执行方式等,总体已经基本传承了汉族封建法律的思想和规律,这与崔浩等汉族大儒担任主修是密不可分的。其后的正平修律以及文成、献文二帝的修律活动,都是在神麚修律的框架内进行的修补性工作,并未在法律封建化上形成跨越。以神麚修律为代表的北魏前期立法活动,适逢北魏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化,法律规定依然存留着大量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内容,鲜卑旧法和汉魏法律的碰撞是这一时期立法修律的主旋律。随着北魏政权的发展和稳固,封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家统治的现实需要也要求法律作出新的方向调整。
三、太和、正始修律:引礼入律,儒法结合
孝文帝元宏是北魏一朝最具作为的皇帝。其即位时,北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各方面都趋于稳定,经济基础良好,为孝文帝日后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鉴于“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1](P2877)太和三年,孝文帝下令修订旧律。“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至太和五年冬修律完成。
“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1](P2877)
孝文帝对修律一事极为重视,事必躬亲,“按魏律系孝文自下笔,此前古未有之例”。[3](P342)太和修律定为八百三十二章,较旧律条目大幅增加,律文愈加完善。死刑罪名二百三十余例,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轻刑化趋势明显。此外,还限缩了门房之诛的适用范围,除却多人共同劫掠的首谋外,最重止于枭首。
引礼入律、儒法结合是孝文帝立法的核心指导思想。礼制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孝文帝倡导“营国之本,礼教为先”,并将其贯彻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孝文帝亲自对臣民宣扬孝道,播及服制之道,违服制服丧即为犯罪。朝廷也多次表彰民间孝德行为,孝文帝更是为祖母大行丧礼,以表天下。孝文帝通过一系列举措,将鲜卑风俗转化到儒家“尊尊”、“亲亲”的伦理中来。引礼入律的最终目的是儒法结合,“若不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寇贼莫可由息,百姓无以得静”。[1](P1139)
改造缘坐刑是孝文帝死刑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的缘坐刑分为五族、三族、门诛、房诛等层级,其中门房之诛作为北魏特色的族刑,株连范围广,社会影响大,被用作打击异己、政治斗争的工具,残酷至极。孝文帝为巩固统治,稳定民心,同时也不忍无辜的人受到牵连,“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1](P140)孝文帝下诏缩小连坐范围,“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1](P150)族刑排除大量无服制相连的远亲或隔代久远的血亲,当判门诛的更是止于本人一房,父母兄弟等亲属得以豁免。延兴四年诏:“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1](P140)太和十一年诏:“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定,删除繁酷”。[1](P2878)自孝文帝之后,缘坐刑基本就限于反逆、谋叛、巫蛊、谤政、恶逆、杀人等犯罪,除有限极为恶劣罪行外,普通罪行基本排除适用。缘坐死刑的范围也得到限缩。按前律,谋逆罪处连坐,十四岁以上男性亲属无论情节皆斩,外姓养子也包含其中,孝文帝改革取消了养子随生家的连坐责任。在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下,缘坐刑的适用罪名和株连范围都得以限缩,罪行设置更为合理,反映了北魏刑法由严苛向轻简转变的历史趋势。
旧律处刑严苛,犯罪者尤其死刑者甚广,而如前文所述,自汉文帝肉刑改革以来,“死刑既重,生刑又轻”,生死刑之间过大的刑差导致司法实践中死刑泛滥。至北魏,法定枭首、斩、绞三种死刑之下,便是最高五岁的徒刑,加之北魏前期轻罪重罚的司法传统,罪不致死而判死者比比皆是。文成帝时,源贺上书建议改死从流,因北魏边境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边禁松弛,边防空虚,若以内地居民充实边关则势必“无人应命”,将犯人判处流刑旨在戍边卫国。在将流刑定为法定刑并广为实施后,其成效可谓立竿见影,“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1](P921)孝文帝时又将大量无需判死的罪名法定刑改为流刑徙边,既减少了死刑的适用,又充实了边地兵卒人丁,以至“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1](P2877)
在一系列死刑制度改革中,孝文帝还特别注意将法律与儒家经义相结合,前述废黜门房之诛便是之一。鉴于旧时死刑犯皆需赤裸上身行刑,是极大的人身侮辱,孝文帝下诏“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孝文帝还对刑具进行改革,“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5](P2883)从人道主义出发,使受刑者免受重枷之苦。孝文帝严禁司法官吏法外用刑,对违制滥刑的官吏严厉处置。古人重孝,崇尚汉族文化的孝文帝更是如此,“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相较前朝,孝文帝对于不孝罪加重处罚,并且不孝罪的范围也有所扩大。相对于严惩不孝,孝文帝也顾及到死刑犯的赡养问题,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1](P2878)此即存留养亲制度的源起,一直沿用后世不改。
在“礼教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基于北魏中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孝文帝一改前代刑法过于严苛之势,宣扬以仁义治天下,德刑相辅,法制建设日臻完备。太和修律精简了死刑罪名数量,限制了死刑连坐范围,并且针对司法实践中的虐囚现象进行修整。太和修律体系已较为完善,具备了完整律典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说北魏律已基本形成。太和法制改革奠定了北魏法制发展的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隆礼义、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不仅是对北魏百年建国的法制经验的总结,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2](P87)
世宗宣武帝元恪即位后,着手继续完善太和修律,于正始元年冬下诏:
“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1](P2878)
此次修律由宣武帝发起,太师、彭城王元勰主持,旨在修补太和修律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的瑕疵,使法律更加具有实用性。修律团队中,除元勰等皇室成员,也不乏刘芳、常景等汉族大儒。这些官员皆为太和修律的参与者或影响者,对此可谓十分熟悉,同时刘芳、常景等人重诸礼,在“引礼入律”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始修律以太和修律为基础,加之宣武帝时期颁布的诏令而成,最终被后世视为北魏律的定本。正始修律集北魏历代制律修律之大成,推陈出新,将法律儒家化推向了又一个高度。
此次修律继续在审判环节进行改制。鉴于前朝刑枷“大小违制”,永平元年,宣武帝欲改司法制度。“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1](P2879)司法实践中滥用重枷现象比比皆是,进而衍生出非法刑讯屡禁不止。宣武帝重新明定枷杖规制,将适用范围限于大逆外叛罪行,“诸台、寺、州、郡大枷,悉焚之”,“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1](P2879)但之后朝局不稳,“狱官肆虐”,此等规定并未实行太久便成一纸空文。
正始修律是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完善和补充,使北魏律发展至最完备的状态。官当制度在正始修律中得以正式确立,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宣武帝时期,北魏律基本定型,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也基本完成。
结语
北魏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分裂时期,也是各项法律制度的大发展时期。北魏继承了自秦汉以来法律宽简平和的发展趋势,在死刑制度立法上亦是稳步创新。北魏政权在百余年间完成了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跨越,并进行了彻底的汉化改革,对死刑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立法思想受时代背景和统治者的影响极大,在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中,社会思潮动荡不定,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在不断的徘徊之中。从早期的严刑峻法到中期的多管齐下,再到最终的儒法结合,死刑制度在一次次的法律修订中得以完善和发展,使北魏死刑制度最终成为后世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