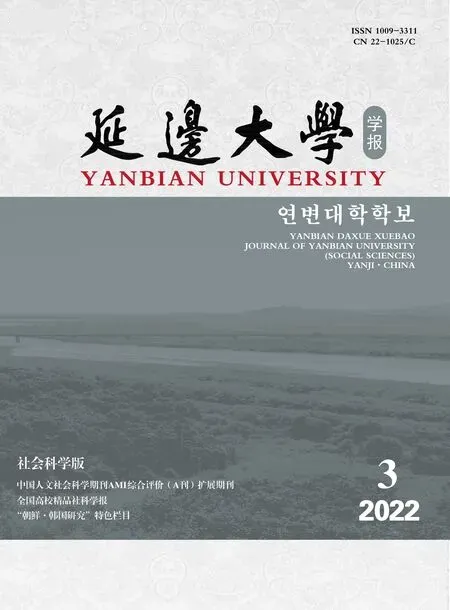论国内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资料库”理论
权绘锦 刘竺岩
网络文学的出现既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载体,也让作品本身产生了形态转变。无论对网络文学抱有何种态度,当这种新兴文学样态逐渐在大众的阅读行为中趋于主流时,以恰当的理论对其进行批评,成为诸多评论者所要直面的问题。早在网络文学批评尚未形成独立话语的2011年,邵燕君就基于学者的警醒,指出批评中的问题倾向,认为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简单套用,以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惯性继承,成为揭示网络文学深层内涵的壁垒。(1)邵燕君:《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第12-18页。因此,在后现代文化场域之下,以及去中心化的媒介传播之中,寻找一种恰切的、适应网络时代的理论工具,以应对类型化的文学生产、游戏化的叙事模式,以及超长篇幅与碎片化文本的融合,势成必然。
基于此,以“资料库”理论(又译为“数据库”理论)名世的日本后现代论者东浩纪进入国内网络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本文首先概述“资料库”理论的内涵与特征,进而探究该理论在国内网络文学批评中的三重意义,最后探讨它在批评实践中的内涵变异与误读问题。本文依东浩纪著作的两种中译本,使用“资料库”译名,如引用的他人论著使用“数据库”译名,则遵从相关论著原文,不再一一标注。
一、东浩纪的“资料库”理论概说
东浩纪(1971—),东京大学博士,有《存在论式,邮件式》(『存在論的,郵便的』)、《邮件式的不安》(『郵便的不安たち』)、《后现代再考》(『ポストモダン再考』)等著作行世,善于以后现代理论观照大众文化现象。其“资料库”理论在两部御宅族文化研究著作《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和《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ゲーム的リアリズムの誕生: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2』)中形成体系。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中,东浩纪以“资料库”理论探究御宅族的文化消费模式。东浩纪认为,御宅族系文化的兴起,契合利奥塔所言之“大叙事的凋零”,亦即在后现代状态下,与启蒙理性相关的现代性叙事已然崩解,人们遂从亚文化中捏造“神”与“社会”。(2)[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49页。因此,文本不再与现实直接相关,每一个文本都具有独立性,可以被任意编辑、随意拼接,最终组合成不关涉现实、亦不含深度的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二次创作”的意义更为突出,原作与戏仿具有同等价值,因而拟像在二次创作中不断增殖,并被多次消费。东浩纪将这样的创作模式称为“资料库”,它改变了大叙事的树状图模式,甚至较之德勒兹的“根茎”(3)[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卷2),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页。更去中心化。故而叙事不再是中心,“设定”或角色成为故事的前提。于是,从现代到后现代,御宅族经历了从故事消费到“资料库”消费的转变。论著《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只是纲领,意义在于提出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御宅族,虽然以诸多动漫作品为例,但并不深入文本,亦未提供一种作为范例的批评模式。
续作《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则重点关注轻小说,将之定义为以“角色的属性资料库”(4)[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黄锦容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年,第33页。为创作环境的小说。此著作透过轻小说的“资料库”特质,揭示其写作原理,即依据“脱类型性”或“后设类型性”的属性资料库来撰写小说,“读者若要求奇幻就给予奇幻;需要科幻就给予科幻;需要青春小说就给予青春小说”。(5)[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黄锦容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年,第36页。东浩纪以樱阪洋的AllYouNeedisKill和舞城王太郎的《九十九十九》为例,指出作品试图将电子游戏的经验小说化,亦详尽分析了作品的“二次创作”手法。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让“资料库”理论不只局限于后现代论与御宅族论,更成为一种文学论。
在理论向度上,“资料库”理论不关注文学审美,归属于文化研究范畴。在东浩纪的御宅族研究中,无论是“资料库”,还是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动物化”,都不研究作品本身,而是把作品文本化,侧重于其背后的情感结构。这样的理论致力于从文化现象观照社会的变迁,通过后现代文本研究人的生活状态,试图探讨此种生活状态怎样在文本中体现,无关乎文学审美。因此,它为大众文化现象做出了解释,而与作品本身的优劣无关。
此外,“资料库”理论也直接面向网络时代。虽然它提出于网络普及尚未完备的2001年,但仍准确论述了“资料库”消费与互联网结构的高度相似性,同时,也指出了互联网时代书刊的发展方向,即“书本或杂志今后虽然也会继续出版,但是内容和结构与文体想必会越来越接近网页;电影今后也将持续上映,不过表演与剪辑也将越来越往电玩游戏及影音短片靠近”。(6)[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59页。无疑与当下大众文学的特征相一致。
因此,“资料库”理论一进入国内批评者的视野,就介入了文学的前沿争论。首先,它被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引入国内学界。2009年,倪湛舸在《小说界》发表《轻小说、宅文化与后现代动物》,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东浩纪的御宅族研究。此文作者的落脚点在于轻小说,关注读者阅读方式的变更,她以“轻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为例,认为这类小说中历史脉络的虚无、“萌要素”的彰显与拟像的泛滥,证明了“资料库”理论的合理性。(7)倪湛舸:《轻小说、宅文化与后现代动物》,《小说界》2009年第5期,第193-198页。其次,无论是轻小说,还是网络小说,都与东浩纪作为例证的动漫一致,同属大众文化文本。最后,东浩纪本人也是“资料库”理论的实践者,如前文所述,他以此理论在轻小说批评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二、“资料库”理论在国内网络文学批评中的意义
作为大众文化文本,网络文学的文本形态更适合文化研究,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文学审美批评力有不逮,这也是“资料库”理论在国内受到重视的一大原因。自2011年至今,国内以“资料库”理论介入网络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批评对象涵盖了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因此,以国内网络文学批评文本为例,检视此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意义,有其必要性。
(一)为辨析界定网络文学“抄袭”问题提供了新见解
欧阳友权等指出20余年网络文学批评的“沟通失效”问题:“习惯于把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评价尺度简单地套用到网络文学上”,(8)欧阳友权、张伟颀:《中国网络文学批评20年》,《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第98-107页。从而产生“隔靴搔痒”之弊。对网络文学“抄袭”问题的争议,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新”“旧”之争的典型案例,也表征着媒介的逐渐去中心化。质言之,媒介形态的变化,让纸媒时代的“抄袭”共识逐渐失效,而在跨越身份的批评主体中,新的共识尚未达成。在此状况下,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生产模式的“资料库”为“抄袭”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以“资料库”理论介入网络文学“抄袭”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资料库”理论初入国内之际,张岩雨的《轻阅读时代的郭敬明现象》就以此解释郭敬明的“抄袭”争议。尽管郭敬明的作品并非网络文学,更宜划入轻小说范畴,但无论文本形态还是传播模式,都已进入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间的过渡状态,且成为一种现象性景观。作者从“粉丝文化”介入郭敬明作品的接受,试图阐释“独一代”群体竭力为“抄袭”事件辩护的内因。“独一代”抵触充满“阴谋”的成人世界,郭敬明作品的“孩子视角”为之完成了“不想长大”的自我想象。因此,是否“抄袭”无足轻重,能够填补偶像失落带来的空虚,才是作品的最大意义。文章对“独一代”群体的理解,明显综合了东浩纪所言“大叙事凋零”后的两个世代:一方面,大叙事凋零后的虚无感,令“独一代”以虚构作为填补;另一方面,单纯对片段、图画、设定等进行的“资料库消费”也初见端倪。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所谈的“资料库”是被加以改造的。作者将“独一代”的知识体系视为一种“资料库”,包括经典文本、武侠玄幻与动漫及它们的衍生品。郭敬明的小说从这样的“资料库”中抽取要素进行“仿拼”,以个人化的语言风格,让小说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在“独一代”看来,这并非抄袭。(9)张岩雨:《轻阅读时代的郭敬明现象》,《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第99-102页。在东浩纪那里,“资料库”的基础单位是角色,一切被抽取并加以仿拼的要素都基于此,与张文所言的“知识体系”并不相同。但总的来看,张文的理论改造是成功的,不仅抓住了“独一代”群体的后现代特征,也揭示了后现代文本原创与拟像界限逐渐消失的过渡性。
如果说郭敬明的作品尚处于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交界处,张文对“抄袭”的体认,尚未摆脱纸质媒介,那么肖映萱的《数据库时代的网络写作:如何重新定义“抄袭”?》则立足网络时代,从“资料库”理论出发,通过对网络文学“作者”“作品”“文字”“情节”“设定”等诸多概念的辨析,重新定义了网络文学中的“抄袭”。因为在拟像的世界中,人们很难认定某一情节、设定纯然是原创的,作品价值实质上在于“萌要素”的个性化聚合。因此,肖映萱认为,受到公认的情节与人物属性、设定不能被垄断,它们是“资料库”中被抽取的要素,在不同的聚合中形成了互文关系,再由此不断丰富“资料库”。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抄袭”已不能适应网络文学时代,作者(写手)的著作权利应被保护,“超文本”也应被更加宽容地对待。(10)肖映萱:《数据库时代的网络写作:如何重新定义“抄袭”?》,《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第134-142页。从整体看,肖文针对网络文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以“资料库”理论对“抄袭”行为进行了重新界定。对“抄袭”问题的再定义需要多学科、多层面地探讨,但从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本质入手,无疑切中肯綮。
(二)为讨论网络文学“真实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资料库”理论对网络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见解。李强的《从“超文本”到“数据库”:重新想象网络文学的先锋性》(11)李强:《从“超文本”到“数据库”:重新想象网络文学的先锋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第143-149页。似乎是对肖映萱文章的“续说”,旨在由“抄袭”现象观照“资料库消费”时代文学的真实性。在早期网络文学批评中,诸多论者以“超文本”预测网络文学文本从单一走向复杂的可能性。但这样的预测是精英的,超文本的网络文学实验被模式化的大众文化文本淹没。引起争议的“抄袭”正为网络文学的先锋性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在李强的文章看来,网络文学的“抄袭”实际上抄的是细节,是来自于“资料库”中的既有设定。这些细节的聚合,构成了“二次创作”中的人物、情节与世界观设定。但读者未必对细节的聚合感兴趣,其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制造一种代入感,对部分读者而言是“拟宏大叙事”,对多数读者而言则无足轻重。
因此,部分网络文学作者求助于写作软件,以形成模式化的细节聚合体,来回应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细节真实的关注。对细节真实的背离,让“真实”需要被重新定义。李文以同人创作的极端现象为例,指出在网络文学中,由细节构成的人物、情节、世界观设定仅仅是背景。因而,网络文学的“真实”正从“细节真实”过渡到读者“想看的真实”,这是“资料库”统摄文学生产与消费背景下先锋性的一种可能。文章的关注点,是“资料库”消费与大叙事消费的冲突,是对网络文学批评中现代/前现代话语的一种反拨。尽管其中部分观点在“资料库”理论语境下,仍有商榷之必要,诸如:作为“情节”的“梗”,是否与“细节”二元对立?“融梗”显然是“资料库”的产物,但它何以区别于“细节”的复制,从而达到“想看的真实”?但从总体看,关注这个问题仍极具现实意义,它从一个角度解释了网络文学为何能在同质化背景下不断为读者所接受,并不断因类型的变革而产生新的趣缘群体。
李强的观点,显然涉及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与网络文学怎样理解“真实性”的巨大差异。要坐实“真实性”的更新,需要从根本上阐释这种差异,因此重新定义“真实性”只能是一种设想,未必得到公认。但“资料库”理论确实促使学者们进入对网络文学“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当有论者指出“工业党”穿越小说中的世界可能“比现实的世界更具真实性”,(12)林凌:《工业党的穿越之梦及其文学追求——以齐橙小说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2期,第54-66页。并自居“现实主义”时,罗岗以“资料库”理论指出网络穿越小说不可与传统现实主义等量齐观,它只能是“资料库”消费基础上的“小叙事”。(13)罗岗:《“当代文学”的“极限”与“边界”》,《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第44-56页。可见在罗岗看来,“真实”与现实主义直接相关,网络文学不能经由“真实”的桥梁跻身现实主义。因此,“真实性”不必被重新定义,应当采取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套阐释体系来认识穿越小说。
雷雯等以“人设”为例,用“资料库”理论论证了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差异,这些观点与罗岗观点相似但更为直白。文章以《盗墓笔记》等作品为例,指出人物是否“真实”是评价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它提供了“真实感”。但网络文学中的“人设”蕴含着“假设性”,“显露出了‘虚拟性’‘可能性’与‘想象性’”。(14)雷雯、张洪铭:《“人设”:进入网络文学现场的窗口——兼论网络文学人物构建的困局》,《艺术评论》2021年第11期,第113-127页。这指出了“设定”与“塑造”的根本差异,即“设定”是外界赋予的,源自“产销一体”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本质上是提取“资料库”属性后再进行创造性叠加的产物;“塑造”的人物则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加以艺术化模仿的结果。因此,以“人设”为标签的网络文学,面向市场化的需求,异于传统的“真实”。
(三)为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新依据
在文化研究以外,“资料库”理论也为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建构做出了贡献。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早已走出趣缘群体中的自娱自乐。随着典范性、超越性作品的出现,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势成必然。既然要对网络文学进行经典化建构,对20年来的网络文学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断代与梳理就不可或缺。在此过程中,“资料库”理论成为区分网络文学“新”“旧”断代的工具。
在网络文学界,将网文区分为“传统网文”与“二次元网文”是读者的自发行为,受到普遍认同。邵燕君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试图以网络文学读者世代的变迁,概括网文的“新”“旧”变革。在《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一文中,她化用东浩纪关于御宅族世代的变迁,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第一世代”,即“70后”“80后”,在价值模式上仍带有启蒙文化的遗存,因此,他们对网络文学的消费是“拟宏大叙事”的。尽管文学生产已经逐渐逼近“资料库”,但他们消费的仍是故事,只不过“以升级模式代替了深度模式,以成功模式代替了成长模式”。而以“90后”为主体的世代登场后,他们尽管与日本“90年代御宅族”稍有区别,未完全“不需要大叙事”,但知识结构的差异让他们与宏大叙事产生区隔,宏大叙事与“拟宏大叙事”都成为“资料库”中可资移用、抽取的元素。因此“传统网文”以故事为主导,2015年以来的“二次元网文”以“资料库写作”为特征,是以“萌要素”“玩梗”为中心的类型小说。但文章同时指出,从“传统网文”到“二次元网文”,二者在“网络性”意义上不是断裂的。(15)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第1-18页。
在邵燕君看来,逐渐“资料库”化是网络文学由“旧”到“新”的渐进性过程。但在卢冶看来,“资料库”标示着“文学性”与“网络性”的分野,其特征是2013-2014年出现的“属性化”倾向。在《网络文学的“界碑”与“症候”》一文中,卢冶认为,媒介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网络文学的新旧之别。早期的网络小说与现当代通俗文学享有同一套认识准则,因此可以被纳入同一套评价谱系。对于早期网络文学来说,网络仅仅是一种载体,媒介虽然变更,但对网络功能的认知尚未彰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延续着“文学性”思维。“属性化”后,网络作为媒介的能动性被作品内化,“资料库”得以“主宰文本的内容以及作者与用户彼此交流、指认身份的内在规则”。在这样的体系下,“资料库”已不再解构关于国族与人类的大叙事,“而是将它们与各种新生事物平等地保存在无限的资讯空间中”。因此,以“资料库”的抬头为分野,网络性彻底重塑了经典文学、纯文学甚至包括“旧”网络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的叙事机制,也表征着网络文学产生了主体性。(16)卢冶:《网络文学的“界碑”与“症候”》,《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206-214页。
以同一理论阐释相近的文学现象,却得出相异结论,展示了“资料库”的强大阐释力。针对网络文学“新”“旧”的分野,邵燕君化用东浩纪对日本御宅族世代的划分,认为中国的“70后”“80后”与日本第二代御宅族(拟宏大叙事)类似,而“90后”“00后”则与第三代御宅族——“不需要大叙事的世代”相近。但也意识到,中国的“90后”“00后”未必真的不需要大叙事,仅是一种欠缺或不确定。卢冶的文章则不同,其着眼点是媒介环境的变革,因此无需考虑中国网络文学生产者、消费者与日本御宅族的可比性。换言之,卢文认为无需关注人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异化,只需考虑网络性对文学叙事机制的重构。而东浩纪的“资料库”理论,正足以阐释“网络性”覆盖下网络文学成熟的后现代状态。
三、变异与误读:理论发展中的“资料库”
理论在不同空间或语境中,其内涵会发生改变,甚至被解构、重组,在失去原有含义的同时,也增加新的含义。“资料库”理论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后,在中国本土进行有效发挥时,也是如此。
在接受东浩纪时,中国学者强调“资料库”,淡化了其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动物化”。何谓“动物化”?在东浩纪的御宅族研究中,“动物化”是与“资料库”并驾齐驱的关键词。它借用自科耶夫,意指在“战后的美国被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所包围,或者随着媒体起舞改变行为模式”(17)[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03页。的姿态。这些人服从于本能的欲望,因而被称为“动物”。与之相对的则是日本式的“清高主义”,亦即在不否定身处环境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形式上的对立”,如切腹。(18)[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04页。御宅族群体就综合了“动物化”与“清高主义”的特征,他们深知动漫设定、情节的同质化,但仍为之感动。
为什么中国的网络文学评论者淡化了“动物化”?因为中日两国社会的后现代进程有所区别,在文学层面依然如此。
其一,依照卢冶的观点,2013年以前的网络文学,与上溯至晚清的文学作品享有同一套认识准则。读者将故事与现实直接对应,故事的作用是反映现实。直到2013—2014年,才产生了“属性化”倾向。而东浩纪认为,早在日本御宅族产生时期,“大叙事的凋零”已然起步,作为替代品的虚构悄然兴起,“现实是由其他的虚构故事所组成”。(19)[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58页。到了新世纪,纯文学反映现实的作用也开始崩解。对纯文学阅读者来说,他们“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了解社会”,换言之,日本已进入了“为了解现实而阅读纯文学的时代”。(20)[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黄锦容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年,第65-66页。而中国网络文学的“属性化”仍方兴未艾,不足十年的“资料库”式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让“动物化”无从谈起。
其二,在东浩纪那里,“动物化”和“清高主义”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清高主义”本身又与宏大叙事无关,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对立,受到自命清高者的喜爱与享受,“不管有多少人为此牺牲,也绝对成不了革命的原动力”。(21)[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04页。但在中国的网络文学中,关于国族的宏大叙事一直在场。徐小的《“动物化”的两种路径——中日两国御宅族比较》指出,由于中日两国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中国御宅族时至今日也没有失去对大叙事的需求,因此东浩纪及此前的研究者,以“三个世代”描述日本御宅族的动物化路径,并不能被完全套用至中国语境。(22)徐小:《“动物化”的两种路径——中日两国御宅族比较》,《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第66-80页。从网络文学角度看,以《苗疆蛊事》为代表的大量玄幻作品,在类现实世界中展开故事,展现的是整体化的现实图景,贯穿其中的“政治国家”大叙事,以及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都极其鲜明。因此,尽管不能否认消费主义覆盖下“动物化”的端倪,但宏大叙事的在场和清高主义的缺失,都让东浩纪意义上的“(人类从)政治的动物转变成数据库的动物”(23)[日]东浩纪:《不是政治动物,而是资料库动物 朝向一个政治的半透明界面》,卢睿洋译,《新美术》2017年第6期,第50-55页。难以实现。因此,尽管偶有论者以“动物化”概括中国御宅族的生活状态,但往往落入削足适履的窠臼。而“资料库”理论则不然,它阐释了中国网络文学中的大量独特现象,诸如对“抄袭”问题的重新解读、对网络文学“真实”的再讨论,以及网络文学的断代等,展现了巨大的阐释力。也正因对“动物化”的淡化,中国的批评者更侧重于网络文学本身,不同于东浩纪那种强烈的社会面向。
不仅“动物化”如此,“资料库”理论中描述的“大叙事凋零”亦有与国内网络文学实践的错位之处。无论是邵燕君所理解的诸种因素“平等地保存”,(24)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第1-18页。还是作品中实际存在的爱国主义因素,都昭示着大叙事仍在国内网络文学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应加以提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东浩纪关于“大叙事凋零”的论述已然失效?高翔在《现代性的双面书写——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中认为,网络文学一方面在背离现代性,但另一方面又“以消弭历史屈辱的民族主义叙事、展现发展逻辑的工业党叙事以及想象未来的文明叙事”(25)高翔:《现代性的双面书写——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中州学刊》2021年第11期,第154-161页。重构现代性,延续并更新了宏大叙事谱系。东浩纪的论述仅与前者相对应,表现为网络文学中的“欲望化”“虚拟化”“奇观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是需要警惕的。将东浩纪对于文学发展方向的概括,缩小为当前中国网络文学的一种趋向,无疑属于理论的变异,但同时也证明,东浩纪的理论仍可用于阐释国内网络文学中的现象。可以看出,无论是淡化“动物化”还是缩小“宏大叙事凋零”的适用范围,都基于网络文学发展的中国语境。
当然,在“资料库”理论的批评实践中,也产生了误读。如《新媒体文学中“萌宠”形象生成探源——以网络原创小说为切入点》一文中认为,萌宠形象深受御宅族“萌”文化影响,并引用东浩纪关于萌要素的论证,指出萌要素“被锁定在了角色的动物化上”。(26)冯勤:《新媒体文学中“萌宠”形象生成探源——以网络原创小说为切入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期,第66-77页。这是对“资料库”与“动物化”概念的混淆。如前所述,“动物化”化用自科耶夫,是人在消费主义环境下的生活状态,在御宅族那里,就是“追求更有效率便能达到情感满足的萌要素方程式”。(27)[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北: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35页。而无论是“娇萌少女”还是“萌宠”,他们都是角色,与身份是“人类”或“动物”无关。因此,集中于“萌宠”身上的,只能是角色(拟像)与萌要素(资料库)的双层构造。拟像不断增殖,萌要素不断聚合,在“二次创作”中产生新的“萌点”,成为“萌宠”在网络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但这样的误读无足轻重,它并未改变“萌”文化影响“萌宠”形象的结论。
统观之,国内网络文学批评对“资料库”理论的应用,都聚焦于网络文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面对同一理论时,学者们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识:即中日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区别,以及网络时代高速发展与理论滞后的矛盾,甚至是研究对象的差异决定了“资料库”的内涵不能一成不变。因此,在批评实践中,“资料库”理论在被丰富的同时,侧重点亦有所区别。即使严格依照东浩纪的阐释体系,中日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仍要被考虑在内。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网络文学批评者立足国情,对外国理论的合理借鉴与扩充,同时也是理论发展的一个生动案例。
由此亦可看出,“资料库”理论根植于日本的历史文化语境,就中国网络文学批评而言,不是万能的。恰如千野拓政所言,“(中国学者)更喜欢从抽象角度去理解东浩纪,……我感觉应该把理论落实在具体作品和情境中,不能笼统用‘后现代’理论讨论网络文学,要关注如何把‘后现代’的具体面貌展现出来”。(28)刘成才、[日]千野拓政:《青年亚文化与东亚现代文学的转折》,《长江学术》2019年第3期,第18-25页。因此,一方面需要走出“资料库”理论对网络文学的笼统阐释,尝试发掘本土理论话语,深入网络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另一方面,它的言说边界也需要被拓展,无论是东浩纪本人,还是中国的网络文学批评者,以此触及文学批评时,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小说。灵焚在《浅谈散文诗与现代性》中以东浩纪意义上的“动物化”来理解1990年代以降诗坛的“下半身写作”,(29)灵焚:《浅谈散文诗与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第100-111页。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那么,“资料库”理论能否在文学范围内跳出小说批评的局限,进行面向其他文类的批评,也是当下学者所要思考的另一个层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后现代特质与网络时代面向,“资料库”理论在国内网络文学批评实践中介入了诸多前沿论争。该理论在国内网络文学批评中产生了三重意义:一是为辨析界定网络文学“抄袭”问题提供了新见解;二是为讨论网络文学“真实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三是为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新依据。因为相异的文化语境以及中日大众文化发展的差异,中国学者淡化了东浩纪所强调的“动物化”与“大叙事凋零”,同时也产生了理论误读。无论是内涵的变异还是误读,都是新理论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正因如此,“资料库”理论才能不断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实用价值,并被日渐丰富的中国网络文学批评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