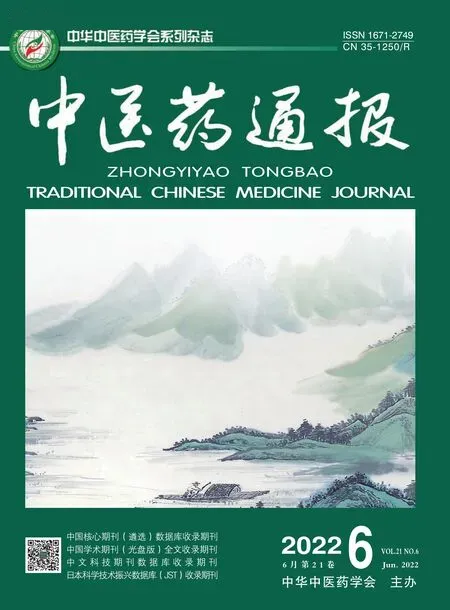论张子和“饮当去水,温补转剧”之治饮思想
陈 榆 莫迪麟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五十岁左右作为随军军医经历军旅生活,后曾短暂入召太医院,晚年在友人麻知几及门人协助下完成《儒门事亲》一书。《儒门事亲》成书于金大正年间(1224—1232年),共十五卷。从《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得见,张子和认为“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1],当有邪气时,应速去邪气,使气血恢复通畅。攻邪可根据病邪位置,灵活运用汗、吐、下三法。若需补益,则应确保病邪已祛除,才可考虑以补剂助其元气恢复。同篇末段又曰:“使用药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1]指出攻邪与补益等法虽然名目各异,但“邪去正安”之核心思想始终一致。从《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一篇中,可见张子和提倡补益选用平和之品或日常饮食,反对盲目温补。张子和擅长医治各种疾病,对痰饮病尤有心得,故于《儒门事亲·卷三》中立《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一篇以抒己见。
1 张子和对“饮”的认识
在《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的开首,张子和已开宗明义,指出“留饮,止证也,不过蓄水而已”[1]。从此句可知,“留饮”是储蓄在体内的不正常水液,其特点在于不随气化、停止于一处,亦因其静止的特性,会阻碍正常的气机运动。张子和亦引述“王氏《脉经》中派之为四:痰饮、悬饮、支饮、溢饮”及“《千金方》又派之为五饮。皆观病之形状而定名也”,指出不论是“痰饮、悬饮、支饮、溢饮”或是其他名字,总归是饮。此篇所讨论的“饮”为广义的“饮”,即不当有而有之水,下文统称为“留饮”。
班固的《白虎通德论》提及:“故水者,阴也,卑,故下。”张子和亦引用此概念,指出水的本质属阴,本应为人体一部分,但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邪气。《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提到“入肾则为涌水,濯濯如囊浆,上下无所之”,指出水无属于自己的居所,会因哪里有空隙而流溢至该处,故水在不同人身上停留,就会衍生不同名称之饮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张子和把水在身体滞留日久的影响总结为两大方面,正如《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所言之“在阳不去者,久则化气,在阴不去者,久则成形”,留饮一方面会耗损阳气,另一方面会成为有形之实邪。
2 反对“饮为寒积”的理解
张子和认为:“今之用方者,例言饮为寒积,皆用温热之剂以补之燥之。”[1]本句之“例言”一词可见认为“饮为寒积”的医者极多,而张子和却不同意此观点。其提及水饮其来有五,“有愤郁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虑而得之者,有痛饮而得之者,有热时伤冷而得之者,饮证虽多,无出于此”[1]。张子和根据以上病因,解释留饮形成的五个机理,曰:“夫愤郁而不得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化,故为留饮。肝主虑,久虑而不决,则饮气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则脾结,故亦为留饮。人因劳役远来,乘困饮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于脉,亦为留饮。人饮酒过多,肠胃已满,又复增之,脬经不及渗泄,久久如斯,亦为留饮。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饮寒水,本欲止渴,乘快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1]由此可见,水饮不单纯是寒引起的问题,也可因五行生克、情志、起居、脏腑特性等不同因素而诱发。即使是最接近“寒积”的“原因五”,亦有“隆暑津液焦涸”的先决条件,亦即暑热邪气伤津耗气后,过饮生冷成留饮,阴液本因暑气受损,假如温补岂不是更伤阴气?总括而言,张子和认为众医所持有的“饮为寒积”的观点流于表面,既未追溯水饮病的由来,亦未能全面反映水饮病的病机,并为下文作铺垫。
3 指出“温补转剧”的机理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抨击当时之医家以“温补治饮”作为主要治饮之法的做法。上述已说明留饮不一定皆为寒积,此段张子和更提出,即使真的是有“寒饮在中”,亦不应投温热药。张子和指出当寒饮在中焦,“以热药从上投之”虽看似合理,但反而会“为寒所拒”。这是因为病邪所在和药力所到之间存有差异,故出现“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焦寒栗”[1]之弊。病痰饮者,阳气受寒邪压抑不利行散,怫结于内,本有病热的倾向,当温热药的药气欲经上焦到中焦时,便难免引动上焦心火,旧病未去之余造成新病。同时,因水“上下无所”,自然会流向低处、虚处,故上部有实火时水邪则下注,造成上热下寒的情况。张子和在下文中甚至提出“留饮下无补法”,因为留饮为有形实邪,气已经受隔塞,再补气则令气壅塞的情况加剧。而张子和所谓的“补”亦不限于药补,而是包括“燔针艾火”在内的一切温热之法。
4 张子和处理水饮的方法
4.1 治病核心在于气机治水饮当首先确保气机通畅。张子和在文中引用《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之说,强调气的出入升降如常最为重要。虽然说人之气向来贵在通畅,任何疾病均与气机息息相关,但治水饮时气机通畅尤其关键。因为《素问·经脉别论》有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水作为有形之物,荡漾于六腑中,化则为津液,不化不通则为留饮,其害更甚于气滞。又《难经‧三十一难》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当留饮堵塞于胃肠时,其实也阻碍了三焦在全身气血的流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藏府肌肉之纹理也。”《灵枢‧本藏》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因为三焦和腠理的联系,留饮的影响亦不限于里,而往往影响肌表。换言之,留饮虽只在一处,其害却远播。但治疗上因留饮有形,相较于无形的气,更可以被明确地攻逐出人体。而攻逐留饮后,要评价气机通畅与否,可从饮食得知,因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儒门事亲》多处皆以“思食”“食进”为邪去正安的证明。
4.2 “留者攻之”及用药的时机、位置与药性正如上文所述,张子和并不认为留饮是单纯的寒积,水固为寒,但留饮的侧重点在于其留结于内,故并不能以温补阳气之法祛除。《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留者攻之。”指出当病邪留滞不去,应以泻下、涤饮、攻瘀等法“攻之”。张子和在《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中曰:“况乎留饮下无补法。气方隔塞,补则转增。岂知《内经》所谓留者攻之,何后人不师古之什也!”[1]值得注意的是,“留者攻之”并不只限于攻逐留饮,而能推广至祛除一切有碍气血通流的因素,继而协助五脏六腑气机恢复正常升降。《儒门事亲‧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曾提到:“《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去而肠胃洁,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1]可见,在攻的过程中,其实亦有补益之意。假如医者成功攻逐留饮,却因此败坏脾胃,这便有违“留者攻之”之意。因此,张子和从时机与药性两方面考虑,举例说明医者该如何“留者攻之”,具体如下。
治疗留饮时机方面,张子和认为邪未祛除时不宜补,新病宜峻药速攻,久病宜缓攻。《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曰:“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矣。”[1]可见,张子和认为有邪气积聚时不能急于补益,否则正气未曾得助,邪气便已受补药刺激而“横鹜而不可制”,并指出“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中张子和以刘河间三花神佑丸为例,指出“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能使“气流饮去”。同篇又引河内某人病饮一案为例,说明即使药不变,随时日而改变服法,亦有“补泻不同”。散较峻而丸较缓,散丸交替使用,先以前者涤荡肠胃水饮,十余剂后,丸剂则可在前者的基础上健脾化湿,如此重复交替,直到“肠胃宽润,惟思粥食少许,日渐愈”。《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续曰:“夫黄连、黄柏,可以清上、燥湿,黄芪、茯苓,可以补下、渗湿。二者可以收后,不可以先驱。”[1]可以看出,张子和并未完全反对治饮时运用温补药物,但要认清先后次序,邪去则可补。若尚有留饮未尽去,则需重复运用“苦葶苈、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药”,待“伏水皆去”,则可温补。
药性方面,张子和非常重视寒热。即使同为攻下药,性不同则功效有别。《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曰:“前人处五饮丸三十余味,其间有矾石、巴豆、附子、乌头,虽是下攻,终同燥热,虽亦有寒药相参,力孤无援。”[1]批评了当时之人攻下之方过于杂乱,寒热同用,最终使攻下之力大减。因此张子和主张攻下之方需药性专一,方能中病,故在《儒门事亲·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一篇则提到,“水肿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可以“泽泻、羊蹄苗根、牛胆、兰叶汁、苦瓠子”[1]等一派苦寒药分利水湿。可见,张子和认为即使药物的功效和发挥作用的位置恰当,寒热仍然非常关键,寒热错配,则攻邪之力大减,或失治病之最佳时机。
4.3 从病案看“留者攻之”的具体应用上文已提及张子和对“留者攻之”的理解和运用此法时该考虑的因素,接下来则会透过讨论《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所载的医案,来理解该如何把握“寓补于攻”的尺度。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载:“昔有病此者,数十年不愈,予诊之,左手脉,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脉,三部皆滑而大。微小为寒,滑大为燥。”[1]病人病数十年不愈,张子和认为左脉三部俱寒而右脉三部俱燥可见病人病势遍及上、中、下焦,水饮积聚而津液未能布散,更有可能是先前曾用温补,加剧病情。因而此病为久病留饮,形气俱伤。
张子和认为第一阶段的治疗应先涌寒痰数升,攻逐在脏腑的水邪,大汗出能外泄在皮毛、腠理的水,再引导水液到腑中润其燥垢而使之能从下出,曰“余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数升,汗出如沃,次以导水禹功,去肠胃中燥垢亦数升,其人半愈”[1]。就如河水泛滥,一方面可先把多余的河水直接抽走,另一方面,可以导引河水,借用水本身的特性,滋润堵塞于河道中的干泥,从而使水得以抵达下游,而中上游的水亦不再泛滥。因为水之成邪不仅仅是水液过多的问题,同时也是分布不均的问题。
张子和认为第二阶段的治疗可以用淡渗之品。经过先前大刀阔斧地攻逐水饮和处理燥热,气机已经大致恢复通畅,“然后以淡剂,流其余蕴,以降火之剂,开其胃口,不逾月而痊”[1]。因为想要淡渗利湿的话,首先要确保水有可以离开的通道,如若仍像一开始般邪实寒热壅塞三焦,则用再多的利水药也是徒劳,反而有机会更伤其枯燥之阴。连、柏降火,使胃阴得复而胃口开。上文提到气机通畅的证明视乎脾胃,因为脾胃位处中焦,是一身气机升降的枢纽,胃口复可见气机已通畅。
最后一个治疗阶段,若邪未尽去,仍可攻邪,但强调中病即止,不要攻邪太过,曰:“复未尽者,可以苦葶苈、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药,伏水皆去矣。”[1]。因伏水深伏,有时饮邪未能尽祛,但攻邪之法终能伤及正气,故攻逐时必须留意中病即止,以防伤害脾胃之气。
总结以上三个治疗阶段可知,张子和的攻邪和补益并非互不相干。第一阶段祛邪同时透过输布津液而补益阴津;第二阶段透过清热利水药补脾胃,恢复脾胃受纳运化而验明全身气机通畅;第三阶段则提醒攻邪方法应该灵活,时刻注意药力,以免过犹不及。由此病案可知张子和如何攻中带补、寓补于攻,阐析了“留者攻之”的深度。
5 与仲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治饮法的联系
张仲景(150—219年),名机,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曾为长沙太守,被后人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古往今来,学医之人皆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为经典,其中《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就曾详细讨论了痰饮病的证治,并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法。
人饮水入胃,但脾胃阳虚运化无力,水液不布而为痰饮。痰饮属阴邪,能阻碍气机,继而再伤阳。仲景所说的“痰饮”,即张子和所说的“留饮”。此病从病性看,当属正虚邪实。正气虚,故应用温药以温运脾胃;邪气盛,故应用温药以温散寒饮。用药的目的在于调和虚实,损有余而补不足。
5.1 “温药和之”不同于“温药补之”温药,一般指药性温,助阳气之品。和,指调和缓解。魏荔彤在《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中说:“言和之,则不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亦概其例义于温药之中,方谓之和之,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2]魏荔彤指出,温药的含意并非温性药物之意,只要以和之方法祛除水邪亦可视之为温药,本句更注重“和”一字。而又从《伤寒论》中“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一条,可看出“和之”不一定要用温药。况且“热则寒之”,仲景治疗饮热互结之证,亦会用到寒药,《金匮要略》就载有“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的条文,方中防己、葶苈子、大黄皆为寒药。
由以上可见,张仲景“温药和之”不同于一般医者“温药补之”,虽然一般医者医治痰饮病时亦多用白术、桂枝等温性药物,但背后运用之理法有异。换言之,仲景和张子和的观点并非相互对立。
5.2 时代不同故所关心的亦不同上一部分已厘清了“温药和之”和“温补”的差别,仲景和张子和二人,实际上都以使气机通畅为目的,但这样并不代表两人治痰饮的方法一样。
张仲景“温药和之”的代表方为苓桂术甘汤,方能温阳化饮,健脾利水。方能使水邪从小便去,亦符合张子和对“攻邪”的理解,如直接引用仲景此方来论述“饮当去水”的观点原是更直接。只是,自宋以来医师普遍喜用辛温香燥之品,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仲景“温药和之”思想的影响,以为饮就是寒,只能用温药以治之,而没有其他方法。故此,张子和反而引用“今代刘河间依仲景十枣汤,制三花神佑丸,而加大黄、牵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气流饮去”的例子去阐述“去水”之法。从《儒门事亲》书中多次引用仲景条文可知张子和熟读仲景医书,其明知苓桂术甘汤为治痰饮的第一方,却不用以此方解释此病,可能别有深意。三花神佑丸加了大黄、牵牛,泻下逐水之力更强,可以推断张子和更加重视邪气对气机壅室损伤的一方面。
上文提到,饮为阴邪。仲景的时代,死于伤寒者不计其数,而伤寒病是以伤阳气为主要发病倾向的,或而令仲景更关心的是阴邪阻碍气机,会进一步损伤虚弱的阳气。反之,张子和的年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人们滥用香燥之药,伤于热的人很多,故其更担心阴邪阻碍气机,会使气郁化火,进一步伤害阴气。张仲景重视饮为寒邪,易伤阳气,阳气伤则阳虚气机不通;张子和则重视留饮为停留之邪,留而化热成实,阻碍气机。两者虽重点不同,但最终都以气机通畅为治病依归。张子和虽然不同意“饮为寒积”,却从未反对“饮为阴邪”,而“温补转剧”之剧更有可能是针对“气机阻塞”转剧,是针对留饮成实而言,而非寒邪直接恶化。对张子和来说,温药本身便离不开温运、温散之品,按“温补转剧”的机理来看,即使用温热药的目的不在补,亦有“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之风险。故张子和更希望以神佑丸为例子,说明甘遂、大戟、大黄、牵牛等寒凉之药亦能逐水助气机恢复运化,非定要以温运、温散之品,才能帮助脾胃。神佑丸又来自十枣汤,继承仲景逐水不忘顾护脾胃之意,又比十枣汤更为寒凉,以针对时弊,更能体现张子和能融会前人之言,而变通于今日之病。
6 小结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论述了张子和对留饮的认识。首先,从何谓“饮”讨论张子和为何反对“饮为寒积”的观点,再说明“温补转剧”的机理。然后,提出张子和处理水饮最在乎气机通畅,“留者攻之”是恢复气机畅通的方法,并以病案说明“留者攻之”有不同阶段和层次,恰当使用能寓补于攻。透过比较张子和之“温补转剧”与张仲景之“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痰饮思想,可知张子和提出之治法不但没有与仲景相违,而且继承了“温药和之”的治法,对饮邪久留这一方面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