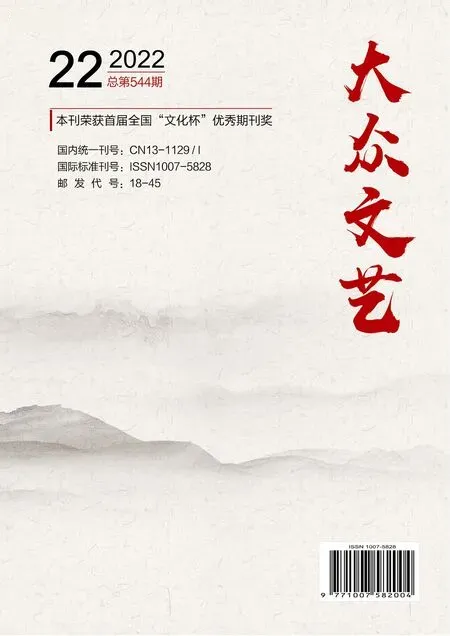多民族文化融合下的云冈飞天造像风格探究
——以云冈石窟第二期为例
李湘颖
(北京时代美术馆,北京 100036)
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的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石窟群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千米。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由北魏皇室倾一朝之力营建而成的佛教艺术宝库。其形成的石窟造像艺术将印度及西域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汉地文化融会贯通,对中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飞天”作为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经典形象,在云冈石窟中更是承前启后,样式丰富且神韵非凡,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据统计,云冈石窟目前尚存“飞天”雕刻2400余身,堪称中国石窟艺术作品中的精品。笔者以佛教艺术中国化高潮阶段的云冈第二期的“飞天”为研究对象,结合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的政治、文化、民族等因素,并着重从身形体态,衣冠服饰,道具纹饰等方面探讨“飞天”造像的风格演变。
一、云冈石窟开凿的时代背景与第二期佛教造像的改革创新
北魏是一个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于5世纪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随着鲜卑族不断南迁,日益深入中原腹地后,同汉族的交流也不断加强。此外,当时的佛教领袖法果开创性的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的主张[1]。帝神合一的思想迎合了北魏统治阶级的需要,为了巩固政权与缓和民族矛盾,佛教便顺利成章在平城发扬光大。而云冈石窟的开凿也借此拉开了序幕。
471年,对北魏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继位。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加速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由此也迎来了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于470至493年雕凿的云冈石窟第二期工程便处在这一时期,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时的佛教造像通过改革创新,在吸收早期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精华之上,融入了更多鲜卑族和汉民族文化因素,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其中,太和十年(486年)的服制改革,将前朝来自印度式的佛衣改为褒衣博带的汉式风格,这也成为云冈第二期“飞天”造像风格研究的关键。
二、中国化“飞天”的溯源
“飞天”在众多佛教造像题材中以其多变的形式,活泼生动的形象[2],深得大众喜爱。与其他受限于宗教教义约束的佛教造像相比,“飞天”的形象可塑性强且不受限于空间。他们穿梭飞翔在各窟的佛龛之中,向世人展现着佛国世界的美妙盛景。
当今学界,关于“飞天”的形象溯源一直有不同的讨论。其中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飞天”艺术源于古印度。根据佛经记载其原型来自佛教中“天龙八部”护法神中的“乾达婆”和“紧那罗”二神。“乾达婆”因其全身散发香气、善表演音乐,有“香音神”的美称;“紧那罗”因能歌善舞被称为“天乐神”[3]。他们常环绕穿梭于佛陀的左右,或持乐器散花演奏,或托圣物以供差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飞天”来自犍陀罗艺术中天使的形象[4]。在这一时期因亚历山大东征有大量希腊移民前往此地,带来希腊文明,而古希腊神话中许多天神和天使的形象便逐渐流行于后世。事实上,在佛经中多有关于“天人”“诸天”的记载,却甚少出现“飞天”一词。传自印度的“天人”沿着丝绸之路途径西域进入中原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中道教神仙思想的“羽人飞仙”相结合[5],在中外文化交流融汇下,诞生了中国化“飞天”的形象。他们不长翅膀、羽毛,主要凭借衣裙飘带凌空飞舞,以浪漫和超脱的形象,给现实中的人们传递美好和希望。
三、多民族融合下的云冈第二期“飞天”造像特点及风格演变
云冈石窟的“飞天”形象,与我国诸多石窟寺“飞天”相比较,以中西杂糅、刚柔并济的特征引人注目。云冈石窟第一期的“飞天”最具外来样式。他们多雕刻于佛和胁侍菩萨的头光、背光或龛楣处,面相浑圆,高鼻深目,体态大多丰腴,上裸下裙或着贴身大裙,裸露双足,身体线条充满力量感,飞翔动态并不明显。第二期的“飞天”处于佛教艺术本土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组窟中的“飞天”无处不在,大量出现在明窗、藻井、门楣、塔柱等各处。此时的“飞天” 在身形体态,衣冠服饰,道具纹饰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形象丰满与轻盈并存,姿态多样,既有胡汉文化交融的体现,也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由于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开凿数量多且时间跨度长,其造像风格样式差异明显,所以普遍又将第二期按石窟开凿时间划分为3个阶段:即以第7、8窟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以第9、10窟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以第5、6窟为代表的第三阶段。
第二期最先开凿的是第7、8窟(第一阶段)。该窟分前后两室,是继云冈早期昙曜五窟之后向中期过度时的代表性洞窟[6],完成于孝文帝执政早期。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记载有:“云冈壁面上下分栏的龛像布局和窟顶雕出斗四结构的平棋宝盖,都首先出现在七八窟中;许多新的造像题材和装饰、供具等形象也最早见于七八窟,前者如交脚佛像、具狮子座的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和佛传龛、摩醯首罗天等,后者如盝顶帷幕龛楣、鸟兽形龛尾、多层塔、六角摩尼、博山炉等等。”[7]位于第7窟后室窟顶雕刻的“飞天”(图1),在利用窟顶平棋藻井、梁枋等仿建筑空间的基础上,为突显出其装饰构图的整齐划一,每格的中间作团莲装饰,“飞天”环绕于中央两侧。他们头梳高宽发髻,耳带环饰,两两相随,有的共捧摩尼宝珠,有的合托莲花宝盒,有的做双手合十状。其造型主要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未离开地面以站姿或舞姿出现,飞行动感较弱,继承了印度佛教中飞天形象;另一种受本民族文化影响,“飞天”由早期较为笔直的身体形态转换为U型,增强了轻盈飘逸的飞行之势。第8窟后室窟顶中部支条双“飞天”与第7窟造型风格相近。他们项有背光,头挽高髻,由早期圆润的面相逐渐呈现出游牧民族丰满方圆的特征,服装尚留存有上身袒裸下身丝质贴体长裙的西域样式,胳膊和腿部肌肉线条尽显,呈后扬的飞行姿态,动作略显笨拙,从中能窥探云冈第一期的风格特征。

图1 云冈第7窟平棋藻井飞天
第9窟、10窟是一组典型的佛殿窟(第二阶段)。其开凿与完成年代稍晚于第7、8窟。此时正处于文化更新、继往开来的阶段,一方面外来之风不断,胡风胡韵依然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汉族文化逐渐抬头,汉式建筑、服饰、审美情趣均展现了佛教艺术进入中原后中国化的进程。此双窟最具特点的是“飞天”多位于窟顶明窗与拱门之上。第9窟的明窗顶部堪称云冈石窟最美“屋顶”,其窟门拱顶部雕刻有四身“飞天”(图2)共捧摩尼宝珠,他们面相方宽,深目高鼻,头梳平纹逆发,袒上身鼓腹露脐,飘带自左肩膀斜披至腋下向后飘起,大臂及手腕浅刻三条细纹代替印度犍陀罗风格繁复的配饰,下身着短裤或半裙,小腿和足部均裸露,体态健硕豪放。与之相对,位于10窟门拱顶部的四身“飞天”(图3)则呈另态。她们头梳高发髻,表情柔和,面露微笑,身形相较逐渐修长,细腰肥臀,以薄衣裹身的服装示人,斜披络掖,手托博山炉对称飞舞在四周。若仔细观察,这一阶段的“飞天”从男性化或中性化逐渐向女性化过渡;从体态、服饰以及所持宝器上,都逐渐融入鲜卑族和汉族文化因素。另外从这两窟“飞天”形象对比可见,即使是开凿于同一阶段的石窟,其飞天造型风格也存在差异。

图2 云冈第9窟门拱顶部飞天

图3 云冈第10窟门拱顶部飞天
值得关注的是,道具和装饰纹样的多样性使得“飞天”形态更为丰富多变。在云冈石窟第二期飞天造像中,有大量的莲花纹饰出现。莲,作为佛诞生、转世的象征物,不仅代表着“西方弥陀净土”,在中国它自古也被视为圣洁之物。雕刻于云冈第9、10窟明窗莲花“飞天”尤为经典。两重大莲花绽开,各八身发型各异的“飞天”相间环绕团莲飞行。第9窟中逆发飞天形体较大,体态健硕有力,一手叉腰一手托莲,腿部呈倒踢姿势,像极了北方少数民族男性劲舞;而身形较小的束发飞天,轻柔窈窕,态势飘逸灵动,好似汉族女性软舞,尽显胡风汉韵杂糅之美。对比来看,第10窟的这组“飞天”托莲像中(图4),八身飞天造型自由奔放,四身高发髻,四身逆发,他们有的张臂起舞,有的单臂托莲,有的吸腿跳跃,姿态十分舒展的绕莲飞行。“飞天”极具动感的舞蹈造型无一不展现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8]。伎乐成分的越发浓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乐舞的生活场景,而团莲“飞天”所呈现的画面正是北魏平城时代各民族乐舞艺术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图4 云冈第10窟明窗顶部团莲飞天
第5、6窟开凿于太和十三年(489年)之后。与同时期的7-10窟相比,云冈第三阶段石窟中雕刻的“飞天”形象变化明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到第6窟时,早期沿袭自古印度的 “双飞天”模式逐渐淡化,变为成排飞天群。在云冈石窟最为繁华富丽的第6窟中,窟内雕造有巨大中心塔柱,塔柱分两层,四面各开大佛龛,在佛龛、龛楣、龛柱上雕刻有“飞天”群组,她们凌空飞舞构成了华丽的佛国天宫画面。第三阶段的“飞天”造型轻盈,面相清秀,腹部前挺,曲线优美且灵动。其二,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推行服制改革,这一举措在佛教艺术界中具体表现为服饰和造型方面的变化。前期佛与菩萨装仍为印度、中亚的旧式,后期改为汉族褒衣博带式、披锦交叉的菩萨装。位于第6窟东壁下层释迦牟尼佛传故事中的“飞天”形象,头梳高发髻,上身内着圆领衬衣,外着V领对襟宽口短袖,下穿束腰遮足长裙,肩带长而回绕与臂后,轻盈飘逸动感十足,身材比例趋于修长。另外,在飞行姿态上已出现上身直立呈L型的“飞天”形象,其长裙裹脚,于身后呈群尾飘动。身形清瘦一改早期“飞天”的健硕与沉坠之感,具有鲜明的汉民族艺术风格。
综上所述,云冈石窟的“飞天”造像风格与佛像的中国化进程基本同步。处于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的第二期“飞天”,记录了印度佛教艺术风格的鲜卑化、汉化转变轨迹,并开启了世俗化的序幕。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第二期雕刻的“飞天”由印度装饰华丽的半裸式菩萨装逐渐过渡为汉族样式的对襟宽口长裙,早期露足后为长裙遮蔽。在身形体态上也由男性或中性、面相浑圆、体格壮硕、裸露较多的印度及西域“飞天”形象,到北方少数民族丰满方圆、质朴刚健的形象,更向着中原汉民族身形清瘦的女性化形象转变。“飞天”所持道具法器也从早期的摩尼宝珠、西域乐器变为博山炉、莲花和中国乐器。整体来说,云冈第二期“飞天”造像风格呈现出同一时期多种样式并存,总体趋于汉化的特征。其造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对后世石窟造像艺术影响深远,更对研究佛教艺术中国化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