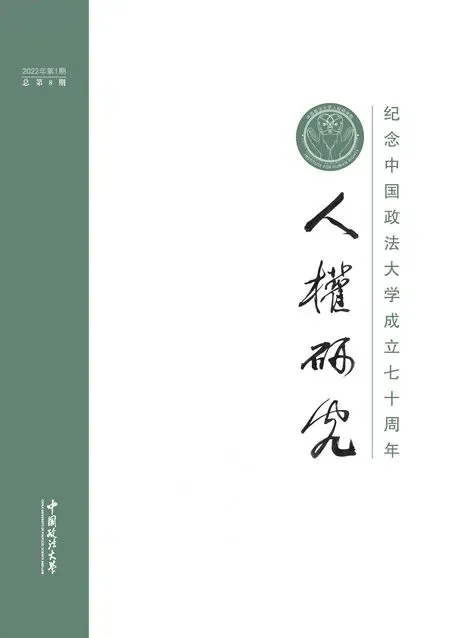“迁徙自由”传统边界的消失
——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的形成为中心
邢益波
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在当下诸多国家的宪法以及国际法层面已然成为一项基本权利,概括地说,其所指的是人行与止的自由。1在宪法层面,“迁徙自由”的定义通常为“公民自由选择生活地点和居住处所的权利”;在国际法层面,“迁徙自由”通常是“由个人移动相关的特定权利和自由组成,其中既包括个人根据意愿在一国之内自由流动和定居的权利,也包括个人离开一国和重返本国的自由”。参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 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Eckart Klein,Movement, Freedom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in Rüdiger Wolfrum ed.,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V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95-403.在历史上,迁徙自由作为某种“权利”出现,可以追溯到屋大维统治后期。在公元6年,由于罗马帝国出现了严重饥荒,屋大维特别准许元老可以自行离去。1Siehe Cassius Dio, Römische Geschichte, Band IV, Bücher 51-60, Übersetzt von Otto Veh, 2007, S.233.不过,此时的迁徙自由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一种特权。而迁徙自由的相关内容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英王约翰在这其中分别授予了商人(第41条)和忠君者(第42条)一定的出入和逗留英格兰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有着严格且有限的对象、范围以及程度。这种状况直到法国1791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791)的出现才得到短暂的松动。2See J.C.Holt, Magna Cart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89;《法兰西宪法典全译》,周威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另外,1791年宪法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之下,深受近代自然法的影响,而被视为自然法基本组成的迁徙自由“在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观念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具体可参见[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修订第二版),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0页。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Division of Human Rights)的梳理,共有27个国家将迁徙自由相关的条款写进了本国宪法之中,不过各国几乎都对这一自由施加了各种限定。3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Documented Outline, E/CN.4/AC.1/3/Add.1 (1947), p.68-72.在国际法层面,尽管近代诸多自然法大家都主张保护迁徙自由,但是对其加以限制还是在19世纪末成为主流,这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关系密切。4See Richard Plend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Revised Secon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2;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故而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际层面,迁徙自由都有着诸多限制,这些限制也逐步在其适用对象、范围和程度方面形成了传统的边界。
然而,当各国代表在二战之后聚到一起,重新检视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时,这些迁徙自由的传统边界遭到了挑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无反对票的结果正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下简称《宣言》),其中载明了30条具体条款,以涵盖个人作为个体以及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勒内·卡森(René Cassin)曾将其比作“希腊神殿”,以彰显《宣言》体系的完备与严密,而其中作为“神殿第二根立柱”一部分的第13条明确了“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同时“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5参见[美]玛丽·安·葛兰顿:《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刘轶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在这其中,长期以来针对这一权利适用对象的限定消失了,其适用的范围也未再囿于一国以内,尽管其行使仍要受到出于对他人权利尊重和民主社会正当需要所确定的法律限制(第29条第2款),但是长期以来束缚其适用程度的国家法律之限并未出现在最终的文本之中。随着这些传统边界的消失以及《宣言》作为一种国际共识的达成与传播,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以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承认。
在此之前,学界对于涉及迁徙自由的《宣言》第13条的形成并没有过多重视,关于迁徙自由本身的研究则多囿于国家范围和宪制功能,故而对于这一条款的形成过程尚有一定研究空间。1参见孙平华:《〈世界人权宣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化国宇:《〈世界人权宣言〉中儿童权利条款的来源与形成——关于起草史的回顾》,载《人权研究》2021年第1期,第62—75页;毛俊响、盛喜:《〈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1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及其当代意义》,载《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3期,第43—61页;赵小鸣:《迁徙自由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王理万:《迁徙自由的规范结构与宪法保障》,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4期,第77—87页。与此同时,在后疫情时代,迁徙自由问题重新回到了大众和学术的视野之中,故而对在迁徙自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第13条进行进一步研究亦有其现实意义。2See Jaya Ramji-Nogales & Iris Goldner Lang, Freedom of Movement, Migration, and Borders, 19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593, 593-602 (2020); Charles Heller, De-Confining Borders: Towards a Politics of Freedom of Movement in the Time of the Pandemic, 16 Mobilities 113, 113-133 (2021);孙世彦:《疫情防控措施对人权的限制——基于国际人权标准的认识》,载《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25—38页。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在其名篇《为权利而斗争》中提到:“世上一切法权是经由斗争而获得的,每一项既存的法律规则(Rechtssatz)必定只是从对抗它的人手中夺取的。”3[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页。而在这场打破迁徙自由传统边界的“论争”当中,各国之间有着怎样的“博弈”,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最后又达成了怎样的“妥协”,便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本文拟以《宣言》诞生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人权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记录和报告为核心材料,首先对与迁徙自由相关的第13条条款的嬗变进行梳理,接着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着重研究历次会议中各国代表围绕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范围和程度所进行的国家博弈,以解答迁徙自由的传统边界是如何消失的这一核心问题。
一、“迁徙自由”条款的嬗变
1947年1月27日,第一届人权委员会在纽约成功湖正式召开。在会议的第一天,与会代表以全票通过的结果选定了人权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美国代表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担任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担任副主席,黎巴嫩代表查尔斯·哈比卜·马立克(Charles Habib Malik)担任报告员。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rst Meeting, E/CN.4/SR.1 (1947), p.4.接着,在四天之后的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威廉·罗伊·霍奇逊(William Roy Hodgson)提议由联合国秘书处牵头完成“国际权利法案”初稿的撰写工作。随后各方就霍奇逊的提议展开了一定讨论,最终在两天后通过了一项决议,由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准备法案的初稿,并在第二届人权委员会上提交审议。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enth Meeting, E/CN.4/SR.10 (1947), p.3-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Twelfth Meeting, E/CN.4/SR.12 (1947), p.5.另外,《宣言》的名称在历次会议中的表述不少于四种,例如“国际权利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国际人权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国际人权宣言”(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最终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
起草成员一经确定,罗斯福夫人便将张彭春、马立克以及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司长约翰·P.汉弗莱(John P.Humphrey)请到了寓所。在这次非正式会面中,由于张彭春与马立克的理念大相径庭,他们最终一致决定由汉弗莱完成初稿的撰写。3See Eleanor Roosevelt, On My Ow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8, p.77; 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29.之后,汉弗莱与其人权司的同僚一道开始了“国际权利法案”草案(以下简称“汉弗莱草案”)的准备与撰写。对于这一草案,汉弗莱在多年后回忆道:“草案并没有基于任何特定的哲学;它所涵盖的是被许多国家的宪法以及许多针对国际权利法案给出的建议所承认的权利。”4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39.在此期间,基于现实和政治的考量,罗斯福夫人主动致信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国扩充为澳大利亚、中国、智利、法国、黎巴嫩、美国、英国和苏联。5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383 (1947), p.2;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29-30.新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于1947年6月召开了首次会议,汉弗莱在会上正式提交了共计48条的“汉弗莱草案”,其中关于迁徙自由的第9条表述如下:
第9条
在符合基于国家利益或安全考量而采取的任何一般性法律的情况下,在一国境内应有迁徙自由(liberty of movement)以及居住地点选择自由。6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Draft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E/CN.4/AC.1/3 (1947), p.4.
在这其中,我们能看出迁徙自由的范围被严格限定在了国家境内,一般性法律也成为了迁徙自由的前置条件。除此之外,汉弗莱还在第2条中对草案所载权利进行了一般性限制,即“在行使其权利时,任何人都要受限于他人的权利以及国家与联合国的正当需要”1Ibid., p.2.。与此同时,汉弗莱关于迁徙的自由所选用的词是“liberty”,而非当时在各国宪法以及代表发言中更为普遍所用的“freedom”。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Documented Outline, E/CN.4/AC.1/3/Add.1 (1947), p.67-72.尽管这两个词在中文语境中都被译为了自由,但二者在英文语境中或有一定区别,比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便认为“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liberty)观念只能是消极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freedom)的渴望等而视之”3[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liberty”“freedom”两词为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后加。。
在审议“汉弗莱草案”期间,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工作小组,由卡森、马立克、罗斯福夫人以及英国代表杰弗里·威尔逊(Geoffrey Wilson)组成,以重新组织和起草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提交的草案。这一工作最后由卡森具体进行。在之后卡森提交的“国际人权宣言”草案(以下简称“卡森草案”)中,迁徙自由条款的表述被修改如下:
第14条
在符合基于安全和公益而采取的任何一般性法律措施的情况下,在一国境内应有迁徙自由和居住地点的选择自由;个人也可以自由移民或放弃国籍。4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First Session—Repor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CN.4/21 (1947), p.56.
在这其中,我们能看到迁徙自由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卡森在增添的最后一句中明确将自由移民或放弃国籍,即跨越国境的迁徙,也纳入了迁徙自由的范围之内,这使得迁徙自由适用范围的边界得到拓宽。另外,“汉弗莱草案”第2条中的“国家与联合国的正当需要”也被卡森删去,只剩下了“任何人的权利都受限于他人的权利”。5Ibid., p.52.
不过,之后起草委员会针对“卡森草案”进行了一系列论争,从而确定了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建议案,其中迁徙自由条款表述如下:
第13条
在一国境内应有迁徙自由和居住地点选择自由。这一自由可能要受到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任何一般性法律的约束。
个人可以自由迁移出境或是放弃国籍。
(委员会认为,这一条款应当交由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进一步商榷。)1Ibid., p.75-76.
总体来说,尽管文本变化不大,但是起草委员会还是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是语序发生了转变,即第一句话从“限制”变为了“权利”。这一修改来源于张彭春的建议。1947年6月20日,在起草委员会的第13次会议上,张彭春提到这一条款的开头不应当是“在符合……的情况下”(Subject to…),而应改为“应有……的自由”(There shall be liberty...)。2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hirteenth Meeting, E/CN.4/AC.1/SE.13 (1947),p.8.其次,这一版在条款末尾增添了一个说明,其内容表现出起草委员会成员认为该条款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所涉之领域关系密切,这也触及了迁徙自由适用对象的问题。
之后,经过小组委员会的商榷以及人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充分讨论,“国际人权宣言”草案得以形成,其中与迁徙自由相关的第10条表述如下:
第10条
1.在符合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且基于特定安全理由或公益的任何一般性法律的情况下,在一国内应有迁徙自由和居住地点选择自由。
2.个人应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同时如有意愿,他们也可以获得任何国家的国籍,只要该国同意授予其国籍。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Third Year: Sixth Session, Supplement No.1,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600 (SUPP) (1948), p.16.
与之前几版相比,此处对于迁徙自由的限定明显有所增多,在一般性法律的约束中特别增添了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限定,这与之前草案修改中所呈现的边界逐步被打破的趋势截然相反。此外,这一条款也针对跨境迁徙施加了限制,即将相应接收国同意授予国籍设为前置条件。这一处变动是由英国代表查尔斯·杜克斯(Charles Dukes)在人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之后在霍奇逊更改后以12票支持、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予以通过。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con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irty-Seventh Meeting, E/CN.4/SR.37 (1947), p.7, 8.与此同时,之前在“卡森草案”中删去的国家限制则在这一版草案中通过在“国家”之前增添“民主”这一限定的方式而被重新纳入进来。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Third Year: Sixth Session, Supplement No.1,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600 (SUPP) (1948), p.15.在该版“国际人权宣言”草案第2条使用了“democratic State”的表述。
在此之后的起草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各国代表针对这份草案有着一系列的争鸣,最后在确定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审议的草案中,迁徙自由的传统边界再次呈现出逐步消弭之势:
第10条
1.人人被赋予在一国境内的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和居住自由。
2.人人都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Second Session—Repor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CN.4/95 (1948), p.7.
在这一版草案中,除了将上一版草案中的诸多限制统统去除外,还有两个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是明确了权利的适用对象,即“人人”拥有迁徙自由,对这一适用对象也没有再施加任何限定。其次是针对迁徙的“自由”所选用的词从“liberty”改为了“freedom”,与这一用词同时发生改变的则是之前附加在该条款中的一系列限定的删除。
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各国代表调整了该条款的位置以及个别表达,不过其主体内容没有再发生太大变化。与此同时,在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中,此前的“民主国家”被修改为了措辞更为中性的“民主社会”,其所在位置也被移到了《宣言》的倒数第二条。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800 (1948), p.11, 13.这一位置的移动主要来自张彭春的提议。在1948年5月27日的第50次会议上,张彭春建议将此项对个人权利进行一般性限制的条款放到《宣言》的最后,“因为在言明权利之前先宣称限制并不合逻辑”2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ieth Meeting, E/CN.4/SR.50 (1948), p.17.。至此,关于迁徙自由的条款在人权委员会层面的嬗变告一段落。在之后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七届会议上,各成员国并未就该条款展开过讨论,故其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48年8月26日通过第151(VII)号决议正式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递交的“国际人权宣言”草案一样,在内容上并未发生变化。3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of 26 August 1948, E/RES/151(VII) (1948).
不过,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各国代表召开了多达一百多次会议,逐条辩论了《宣言》中的条款,其中各国代表在第120次会议上用了几乎所有时间来争论迁徙自由这一条款。最终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个成员国支持、8个成员国弃权的结果正式通过了《宣言》,而其中迁徙自由所在的第13条条款表述如下:
第13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在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增添了“有权返回他的国家”的表述。从文本上来说,这似乎有些冗余,而这一条款的修改则源于黎巴嫩代表提交的修正案。4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raft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Recapitulation of Amendments to Article 11 of the Draft Declaration (E/800), A/C.3/284/Rev.1 (1948), p.1.
至此,《宣言》的第13条条款正式确定了下来,这一确定也打破了原先围绕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范围和程度所设定的传统边界。与此同时,尽管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仍有不少代表主张恢复针对《宣言》权利一般性限制中的“民主国家”表述,但是“民主社会”还是在《宣言》最终文本的第29条第2款中保留了下来。从文本的嬗变中,我们能够看到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逐步从未明确主语的状态转变成了“人人”;适用范围则从一国境内转变为将出入国家的权利也包含在内;适用程度则从受到各种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一般性法律所辖制转变为不在迁徙自由条款中提及限制,而针对《宣言》所载权利一般性限定中的“民主国家”也被措辞更为中性的“民主社会”所取代,迁徙自由自此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这些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各国围绕这三大传统边界在历次会议上有着怎样具体的论争、博弈、考量和妥协,则是下面三个部分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二、适用对象:特定群体之限的消失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权利,自其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屋大维时期的元老,还是《大宪章》中的商人与忠君者,抑或是后来各国在宪法中施加了特别限定的臣民、国民、公民或市民等等,始终是与特定群体相伴而行的,这也成为各国代表在二战之后针对《宣言》中这一权利的适用对象进行商榷的具体语境。通过梳理历次会议的记录与报告,笔者认为各国代表关于适用对象的论争主要围绕三大群体展开:经济迁移者、罪犯和其他少数群体。
第一类群体是经济迁移者,即出于经济动因进行迁徙或会对目的地经济产生影响的人。对于这一群体的限制,最早是由英国代表杜克斯在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他认为“迁徙自由自然受到接收国吸收能力的限制,而这些接收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其本国国民的就业问题”1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eenth Meeting, E/CN.4/SR.14 (1947), p.2.。这一表述所针对的迁徙对象便是经济迁移者,而其所受的限制则是当地就业的满足情况。这一时期的英国由工党主政,故而民生问题成为其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杜克斯的这一提议与当时世界正在经历的民族解放运动关系很大,作为殖民大国的英国不得不担心潜在的大规模人口涌入的风险。这一时期同样深受民族解放运动影响的还有法国,其在二战结束之后直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这无疑成为这一时期困扰法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故而在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卡森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卡森指出,迁徙可能会引起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工厂并不会建在一个工人想要生活的地方”2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h Meeting, E/CN.4/AC.1/SR.4 (1947), p.4.。在之后的会议上,卡森重申了迁徙自由与经济迁移者的关系,他认为“有时候政府因为可能的经济原因,必须要预防大规模人口迁徙”1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hirteenth Meeting, E/CN.4/AC.1/SR.13 (1947), p.10.。某种程度上来说,卡森与杜克斯一样,都希望将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限缩在不影响当地或目的国经济的人群中间,故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将经济迁移者排除在迁徙自由的条款之外。
在1948年11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第120次会议上,罗斯福夫人同样提出,“出于一国经济的考虑已经使得一些特定国家采取法律措施来限制移民了,而其措施也已经广为人知并在整体上被接受”。沙特代表贾米勒·M.巴鲁迪(Jamil M.Baroody)则认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国家危机的高发期,而在国家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出现危机时,政府应当有权限制其领地内的自由迁徙。针对这种对于经济迁移者进行限制的提议,作为智利代表的左翼人士埃尔南·圣克鲁斯(Hernán Santa Cruz)率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提及了拉丁美洲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的历史,以论证没有任何权威能够使得“将个人视为国家经济元素来对待具备正当性”。波兰代表弗里德里卡·卡利诺夫斯卡(Fryderyka Kalinowska)则提到了法国最近驱逐外籍罢工者的事件,她指出“这些人中有许多在法国已经居住超过20年了”。与此同时,她表示自己担心的不仅是波兰被驱逐者的命运,还有其他陷入同样困境的工人。2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17, 319-321,324.尽管从国家力量来说,支持对经济迁移者进行限制的多为实力较强的国家,而反对者相较而言并不如前者,不过由于与会多国战后经济重建的需要,最终在是否对经济迁移者进行限制的问题上,并没有依国家实力而定。一年之后,最初提出对经济迁移者施加限制的英国也通过了《1948年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从而让每一位英联邦公民在英国定居和工作的权利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3See Peter Gatrell, The Unsettling of Europe: How Migration Reshaped a Continent, Basic Books, 2019, p.164.另外,关于该国籍法出台的动因可参见周小粒:《试析〈1948年英国国籍法〉》,载《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第49页。
第二类群体是罪犯,这一群体同样是一些国家希望排除在迁徙自由权利的适用对象之外的。在1946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英国代表杜克斯提出迁徙自由问题要被极其谨慎地对待,在这其中一定要保留一个国家引渡其罪犯的权利。4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eenth Meeting, E/CN.4/SR.14 (1947), p.2.在四个月后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此时的英国代表威尔逊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他认为各国政府未必会批准这样一条限制其将人驱逐的条款。卡森则强调了迁徙自由权利执行的困难性,他认为“迁移出境权并不等于就有权进入另一个国家”。在这种联系中,“国家拘留罪犯的权利也应当被考虑到”。针对于此,张彭春表示他同样认为迁徙自由是基本权利,然而其执行不得不依具体国家情况而定。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h Meeting, E/CN.4/AC.1/SR.4 (1947), p.4-5.不过,在迁徙自由条款中对罪犯进行专门限定的提议并未获得通过,最后各国妥协的结果是在《宣言》最终的文本中,一方面在第11条中规定“无罪推定”的相应内容,另一方面在免于迫害和寻求庇护的条款(第14条)中增加了“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的限定。
第三类群体是其他少数群体,这其中包括受歧视者、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与前两类群体不同,这一类群体是一些国家希望在迁徙自由条款中特别强调的对象。在起草委员会1947年6月12日的会议上,威尔逊指出迁徙自由条款“主要处理的应当是非歧视问题,故而它应属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职责范围”2Ibid., p.4.。而在八天之后的会议上,威尔逊再次表示这一条款应当交由该小组委员会商榷,“因为该条款的主要内涵便是防止人们由于种族、肤色、可能的居所和迁移方式遭受歧视”,其他国家的代表则对威尔逊的主张未置可否。3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hirteenth Meeting, E/CN.4/AC.1/SR.13 (1947),p.8.故而在同年7月1日人权委员会审议的建议案中,该条款被特别添加了“交由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进一步商榷”4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First Session—Repor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CN.4/21 (1947), p.76.的说明。由于对这些少数群体进行特别强调无疑会有缺漏,故而基于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各方最终妥协的结果是不施加特别限定。这样的结果也反映出了当时在联合国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即“如果所有人都能被等同视之,便无需对少数群体施加特别保护”5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20.。
最终,无论是可能会影响目的地经济的经济迁移者,还是有可能会利用迁徙自由逃离本国的罪犯,抑或是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的受歧视者、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都没有被写入迁徙自由的条款当中,留在最终文本中的适用对象只有两个字,即“人人”。与此同时,在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条款即第29条第2款中,其适用对象同样是“人人”。关于这一表述,海地代表欧内斯特·G.肖韦(Ernest G.Chauvet)曾在会议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这个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将所有人写进宣言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做的首要目的在于教育大众,其原则不应当是政治性的,而是教育的、社会的和人道的。”1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18.
三、适用范围:此疆尔界之限的消失
关于迁徙自由的适用范围,最初在“汉弗莱草案”中提出的“一国境内”在之后该条款的嬗变中基本没有改变,历次会议中也未曾有国家代表对此提出质疑,故而这也成为各国代表商榷迁徙自由适用范围的基础。不过,当这一适用范围甫一跨过国界,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通过梳理,笔者认为各国代表对于跨越“此疆尔界”的争议主要聚焦于是否对以下两种自由施加限制:出入境的自由和变更国籍的自由。
首先是出入境的自由。在1947年1月31日召开的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第8次会议上,乌拉圭代表若泽·安东尼奥·莫拉·奥特罗(José Antonio Mora Otero)率先提及了迁徙自由的议题,这也是历届历次会议中首次有代表提及这一权利,而其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迁徙自由在地理空间上的适用范围。当时莫拉在强调《宣言》的国际性时指出:“迁徙自由应当包含在个人的基本自由之中。每一个人都应当自由地在一国迁徙,也可以离开这个国家,而只受到其他国家移民法律之限制。”2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Eighth Meeting, E/CN.4/SR.8 (1947), p.3.然而,这一提议在此次会议上如泥牛入海,并没有任何代表予以回应。四天之后,当莫拉再次提及此前无人问津的迁徙自由问题时,罗斯福夫人率先作出了回应。罗斯福夫人认为“迁徙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项权利”,故而它也应当被理解为“自由离开一国的能力”,不过这一权利同时“应当受到接收国移民法的限制”。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eenth Meeting, E/CN.4/SR.14 (1947), p.2.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国代表并不反对迁徙自由适用范围的延伸,他们只是希望对其中的入境自由施加一定限制。这两次会议都发生在“汉弗莱草案”形成之前,不过汉弗莱在其草案中选择暂时搁置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
然而这种搁置并没有打消其他国家对此的争论。在起草委员会1947年6月12日的会议上,关于出入境的迁徙自由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而针对搁置了这一争议的“汉弗莱草案”,首先提出意见的是圣克鲁斯,他提议分别研究“在一国之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和移民他国的权利”。接着,澳大利亚代表拉尔夫·L.哈里(Ralph L.Harry)也基本赞同了圣克鲁斯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有三个概念值得思考:(1)在一国境内符合一般性法律的迁徙自由;(2)离开一国的权利;(3)为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提供便利”。除了各国代表的提议外,非政府代表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意见,当时出席会议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托尼·森德(Toni Sender)便认为需要将出境和入境分别对待。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h Meeting, E/CN.4/AC.1/SR.4 (1947), p.4-5.森德作为曾在二战期间流亡、后入籍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对于迁徙自由的适用范围有着极大关注。也正是在这几个国家以及非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卡森新修订的草案中增添了“个人也可以自由移民”的表述。在此之后,经过历次会议的博弈,出境的自由在这一条款中得到了承认,不过入境的自由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最终在1948年11月2日的会议上,黎巴嫩代表卡里姆·阿兹库勒(Karim Azkoul)提出:“根据这一条款,任何人都有权离开包括他自己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这所表达的理想是任何人都能够进入他所选择的国家,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所以最低程度的要求应当是任何人都能够返回他自己的国家。”这种对于实际情况的妥协也得到了与会多数国家的支持,会议以33票支持、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2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16, 325.
其次是变更国籍的自由。这一问题同样由莫拉率先提出,他在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第14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迁徙自由也应当包括改变国籍的自由”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Summary Record of the Fourteenth Meeting, E/CN.4/SR.14 (1947), p.2.。而在1947年6月20日的会议上,马立克同样提出迁徙自由条款的目的不仅是保护一国境内的迁徙自由,它也应当包括“迁徙出境和改变国籍”的自由。在对用词进行商榷的过程中,罗斯福夫人提出美国希望保留“放弃国籍的权利”这一表述。英国代表威尔逊则进一步补充说相比于“放弃国籍”,他更倾向于“抛弃国籍”的表述。4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First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hirteenth Meeting, E/CN.4/AC.1/SR.13 (1947),p.8-10.
不过,苏联代表弗拉基米尔·科列斯基(Vladimir Koretsky)提到“美国人口的基础便在于改变国籍,而当前条款并没有将诸如此类的历史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内”1Ibid., p.10.。之后在人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中,乌克兰代表克列科夫金(M.Klekovkin)针对迁徙出境和变更国籍的自由再次发难。在1947年12月13日的第37次会议上,克列科夫金提出了一项动议,即删除之前起草委员会针对“卡森草案”作出修改后的迁徙自由条款中的第二段(“个人可以自由迁徙出境或是放弃国籍”),因为他认为这会鼓励迁徙出境。霍奇逊紧接着表达了希望只删去该段后半句,“因为获得国籍的权利并不能被保证”。杜克斯则认为加上一句“只要该国同意授予他们国籍”,即可解决霍奇逊的疑虑。另外,杜克斯还认为“应当尽可能为获得一国国籍提供便利,因为当前世界上仍存在大量流离失所者”,故而他提出了对乌克兰动议的反对。最终乌克兰动议以11票反对、4票支持以及3票弃权的结果被驳回。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con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irty-Seventh Meeting, E/CN.4/SR.37 (1947), p.7-8.从各国代表的上述争论中不难看出,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保障放弃一国国籍的自由,而是在于如何保障获得他国国籍的自由,这在本质上与前述的入境自由属于同一个问题。
在此之后,尽管仍有代表在讨论针对《宣言》所载权利一般性限制时会提及迁徙自由适用范围的扩大对国家利益的潜在侵害,比如苏联代表阿列克谢·P.巴甫洛夫(Alexei P.Pavlov)在1948年5月4日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便提到“宣言对任何人离开其国家和改变其国籍的准许并没有考虑到其祖国的更高利益”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Second Session Twenty-First Meeting, E/CN.4/AC.1/SR.21 (1948), p.3.,但是这些言论并未再引发针对迁徙自由这一条款本身的变更动议。而针对国籍变更的自由转而在《宣言》第15条第2款中进一步明确,即“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最终,《宣言》第13条第1款明确了一国境内的迁徙自由,这种明确也因普遍的共识成为第13条的核心与关键;而第13条第2款则将迁徙自由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宽,将离开国家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也包含在内。尽管这种拓宽仍有局限,也存在对现实情况的妥协,但是这仍使得迁徙自由突破了传统的此疆尔界之限。在1948年访英时的一次演讲中,罗斯福夫人将迁徙自由与其先生罗斯福总统所提出的“四大自由”等而视之,并且认为迁徙自由可以使“全世界的人不受繁文缛节的约束而行走,去相互见面和增进理解”1Eleanor Roosevelt, Address by Eleanor Roosevelt at the Pilgrim Society Dinner, 12 April 1948 (London), in Allida Black ed., The Eleanor Roosevelt Papers: The Human Rights Years, 1945-1948, Vol.1,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7, p.791.,而这或许正是迁徙自由突破此疆尔界的意义所在。
四、适用程度:国家法律之限的消失
正如前述,经过各国代表在起草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这三个层级的上百次会议中的论争、博弈与妥协,在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方面,无论是对经济迁移者和罪犯施加限制,还是对受歧视者、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突出强调,都没有在迁徙自由条款(第13条)以及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条款(第29条第2款)的最终文本中出现,取而代之的适用对象是“人人”。而在适用范围方面,原本在“汉弗莱草案”中囿于一国境内的迁徙自由权利也因出入境自由和变更国籍的自由所引起的论争而最终突破了此疆尔界之限。然而,无论是适用对象之争,还是适用范围之辩,笔者认为各国论争的真正焦点都是具有普世属性的《宣言》中的迁徙自由是否应当受到国家法律这一传统边界的辖制,或者说国家权力是否有权干涉人人得享且跨越国界的迁徙自由,这在本质上考验的是迁徙自由的适用程度。通过梳理,笔者认为各国对于这一焦点的博弈主要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法律限制是否应当出于国家之需要,二是迁徙自由本身是否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行使。
首先是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法律限制是否应当出于国家之需要。正如前述,汉弗莱在其草案的第2条中对各项权利作出了一般性限定,在这其中,国家法律之限是通过“出于国家的正当需要”表达出来的。这一限制最早在由巴拿马代表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的声明中提出,该声明提议在《宣言》中增添“在行使其权利时,任何人都要受限于他人的权利和民主国家的正当需要”的表述,以防止个人权利的滥用。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Statement of Essential Human Rights Presented by the Delegation of Panama, E/HR/3 (1946), p.16;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Documented Outline, E/CN.4/AC.1/3/Add.1 (1947), p.12.之后汉弗莱在其草案中大致沿用了这一说法,不过删去了国家前的“民主”限定。在多年后,汉弗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因为他认为该词存在着歧义,比如“‘民主’在伦敦与莫斯科便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解读”3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66.。对于“汉弗莱草案”,美国代表强调“国家是由人们为增进其福利和保护他们的共同权利而建立的”1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o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First Session—Repor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E/CN.4/21 (1947), p.41.,故而人们行使其权利只应当以他人权利的行使为限。美国代表的这一建议无疑被卡森所采纳,其在提交的草案中删去了汉弗莱提及的国家限制。不过,在人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期间,由于巴拿马和菲律宾代表的提案,本已删去的“民主国家的正当需要”还是被写进了工作小组关于人权宣言的报告之中。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cond Session—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E/CN.4/57 (1947), p.5.针对报告中的这一说法,杜克斯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可能会造成差别和困难”,不过他的意见在第34次会议上以7票反对、5票支持以及4票弃权的结果被予以驳回。3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con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irty-Fourth Meeting, E/CN.4/SR.34 (1947), p.6, 8.
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英国联合印度再次对“民主国家的正当需要”提出了删去的修正意见。4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Ind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E/CN.4/99 (1948), p.1.而这一修正意见在1948年5月27日的第50次会议上引发了讨论。罗斯福夫人率先表达了对于该修正意见的支持,卡森则表示希望将“正当需要”修改为“正当法律”,不过此时他转而对“民主国家”这一提法表达了认可。而在圣克鲁斯看来,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正当需要”还是“正当法律”,都难以被准确定义。5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ieth Meeting, E/CN.4/SR.50 (1948), p.16.在第二日的会议上,圣克鲁斯进一步解释道:“不同国家对于‘民主国家的正当需要’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马克思主义便旨在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其中,国家是不再存在的。”之后印度代表汉萨·吉夫拉杰·梅赫塔(Hansa Jivraj Mehta)、莫拉和阿兹库勒等人都表达了对删去国家相关表述的认可,梅赫塔还进一步提出无需在《宣言》中提及人对于社会的义务,因为他们在起草的是一份“权利宣言”,而非“义务宣言”。不过,巴甫洛夫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巴甫洛夫看来,战争期间签署的文件中已明确包含了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概念,这些在之前未产生歧义的概念同样应适应于今天。与此同时,巴甫洛夫认为国家虽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保护集体利益和抵御外敌阶段,国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故而苏联希望对诸如迁徙自由施加限制,无疑只是苏联人民的自卫反应。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y-First Meeting, E/CN.4/SR.51 (1948), p.2-8.
在第52次会议上,巴甫洛夫再次提议加上“民主国家”的相关表述,不过这一提议最终以9票反对、4票支持以及3票弃权的结果被驳回,最后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民主国家”被更为中性的“民主社会”所替代。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y-Second Meeting, E/CN.4/SR.52 (1948), p.2;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eport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of 26 August 1948, E/RES/151(VII)(1948).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第三届会议中,各国代表召开了多达一百多次会议,逐条辩论了《宣言》中的条款,这也是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10日正式通过《宣言》前最为重要的阶段,其中各国代表围绕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也有着各种论争与博弈,不过最终《宣言》的第29条第2款只承认了出于对他人权利尊重和民主社会正当需要所确定的法律限制,而未将“国家之需要”纳入其中。3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raft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Recapitulation of Amendments to Article 27 of the Draft Declaration (E/800), A/C.3/304/Rev.2 (1948).
其次是迁徙自由本身是否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行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第120次会议上,各国代表用了几乎所有时间来争论迁徙自由的适用程度问题。这场争论的起因便是苏联代表团于正式会议前所提交的修正案。苏方在其中提出了两条修正意见:(1)在“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后加上“依据一国的法律”;(2)在“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后加上“依据一国法律规定之程序”。4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raft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Recapitulation of Amendments to Article 11 of the Draft Declaration (E/800), A/C.3/284/Rev.1 (1948), p.1.之后在1948年11月2日的会议当天,巴甫洛夫先是引用了一段苏俄民法典的内容,以论证“任何居住在苏联的人都有权自由地去迁徙、去定居、去拥有一份工作、去买卖自己的财产”,故而迁徙自由在其国家是得到承认的。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所有的迁徙,无论是在一国以内,还是跨越国境,都必须基于该国的法律,所以其所提交的修正案“与现实情况是一致的”,并没有违反迁徙自由条款所“普遍建立和适用的任何原则”。5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15-316.这一言论也反映出了巴甫洛夫在与会期间一以贯之的观点,即迁徙自由应当受制于国家法律。1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Second Session Twenty-First Meeting, E/CN.4/AC.1/SR.21 (1948), p.3;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y-First Meeting, E/CN.4/SR.51 (1948),p.7-9; John 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84, p.58.毋庸置疑,苏方的修正案以及巴甫洛夫的发言将此前一直围绕着迁徙自由适用对象和范围不断进行论争、博弈和妥协的真正焦点揭示了出来。
不过,苏方的修正案遭到了美国、印度、菲律宾、希腊以及智利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圣克鲁斯最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苏联代表提出的修正已经被起草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探讨许久并最终予以否决了。2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Drafting Committee Secon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Thirty-Sixth Meeting, E/CN.4/AC.1/SR.36, p.7-11;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ird Session—Summary Record of the Fifty-Fifth Meeting, E/CN.4/SR.55 (1948), p.5-12.他说:“如果依据苏联代表的意见修改,这将会是一份绝对权利宣言,而非人权宣言。”随后,他举了彼得大帝统治时期通过赎买变相剥夺臣民迁徙自由的例子,试图以此说明苏联修正案所暗藏的巨大危险。在其他几国相继表达了反对意见后,作为美国代表的罗斯福夫人总结性地指出:“声明迁徙自由只有依据各国法律行使才能得到保障,便等于是在限制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增强国家的权力。”3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16-319.针对近乎一边倒的反对声音,率先进行反驳的并非苏联,而是波兰。卡利诺夫斯卡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法律来限制迁徙自由和离开一国之自由,问题在于避免任意限制,所以苏联的修正案完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将已存在之事态纳入了考虑范围之内。”接着卡利诺夫斯卡援引了波兰通讯社领导和纽约艾萨克森(Isaacson)的事例,以说明美国对于出入境的限制。然而对于这些事例,黎巴嫩代表阿兹库勒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恰恰表明“依据一国的法律”不应该被加上,这一条款所阐明的原则不应被任何保留弱化,而且他认为恰恰相反,国家应当预防通过法律来任意限定迁徙与居住自由。4Ibid., p.320-321.另外,此处艾萨克森应指的是美国工党代表、犹太裔美国人列奥·艾萨克森(Leo Isaacson),在1948年4月30日的《国立犹太邮报》(The National Jewish Post)中的一则短讯提及了艾萨克森获得了巴勒斯坦护照的相关情况。See Isaacson Gets Palestine Passport, The National Jewish Post, 30 April 1948, p.24.
为了防止会议进入无休止的论争之中,会议主席适时发起了投票。此时巴甫洛夫特别要求通过唱票(roll-call)来进行表决,而苏联的两条修正意见都以24个国家反对的结果被驳回。1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 A/C.3/SR.120 (1948), p.324-325.随着苏联代表修正案的驳回,关于迁徙自由适用程度之争彻底告一段落。最终,经过上述各国代表在历次会议上的反复论争、博弈与妥协,《宣言》所载各项权利虽仍需受出于对他人权利尊重和民主社会正当需要所确定的法律限制(第29条第2款),但却未再将出于“国家之需要”纳入其中。与此同时,迁徙自由条款(第13条)本身亦未再附加“依据国家法律”的限制。这些内容共同促使《宣言》中的迁徙自由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法律之限。
五、结论
总的来说,《宣言》中的迁徙自由条款经过历次嬗变,就其文本本身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突出变化:首先是语序的调整,即从先阐明限制转变为先强调权利;其次是“自由”用词的转变,即从“liberty”转变为“freedom”;最后是额外的增补,即在该条款的最后特别增加了有权返回自己国家的表述。与此同时,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也从受限于他人、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正当需要逐步转变为仅受他人和民主社会正当需要的限制。另一方面,就其权利边界而言,《宣言》中迁徙自由的适用对象从未明确主语逐步转变为“人人”,适用范围则从一国境内逐步发展到将离开任何国家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也包含在内,适用程度上也逐步去除了符合安全、公益或《联合国宪章》等要求的一般性法律限制抑或出于国家需要的法律限制。正是由于上述这些转变,《宣言》中迁徙自由的传统边界逐步得到了消解。
然而,这些转变以及迁徙自由传统边界的消解并非自然产生的,而是各国代表在起草委员会、人权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中不断博弈的结果。具体来说,在适用对象方面,各国围绕经济迁移者、罪犯以及其他少数群体展开了一系列论争,才最终得以不对可能会影响目的国经济的经济迁移者、可能会利用这一权利逃离的罪犯以及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的受歧视者、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施加特别的限定,从而突破了特定群体之限;在适用范围方面,各国围绕出入境自由和改变国籍的自由展开了一系列争鸣,才最终得以在第13条第2款中将离开任何国家和返回自己国家的迁徙自由包含在内,从而突破了此疆尔界之限;在适用程度方面,各国更是围绕《宣言》所载权利的法律限制是否应当出于国家之需要以及迁徙自由本身是否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行使展开了论战,才最终得以在针对《宣言》所载权利的一般性限制中剔除掉“国家之需要”,在第13条中不再附加“依据国家法律”的限制,从而突破了国家法律之限。
在笔者看来,这些国家的博弈以及权利边界的突破有着以下三点特性:首先是动因的复杂性。在围绕迁徙自由三大传统边界的博弈过程中,各国代表有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有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对于二战记忆的反思,亦有对“普世价值”的追求,等等,故而在此期间,时而能够看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时而也能看到不同阵营的“和鸣”。与此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基于不同的宗旨与原则产生着作用。另外,这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自身的认识与经历也同样发挥着影响。这些共同组成了这场围绕迁徙自由博弈的复杂动因。其次是权利的普适性。概括地说,权利大致有过神授、天赋以及法定这三种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在解释权利来源与内容的过程中,也框定着权利的边界。不过正是由于前述的复杂动因,《宣言》中的迁徙自由得以未依附于特定的理论框架,这也使得这一权利具有了普适性。最后是不足的明显性。在《宣言》第13条的最终文本中,有一句看似冗余的增补,即“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正如前述,这一增补来自黎巴嫩代表的修正案,其出发点是对最低程度的迁徙自由给予保障,这也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一种妥协。不过,正是这种妥协,使得“有权进入其他国家”的缺位在该条款中显露无遗,这一缺位也因此成为该条款明显的不足之处。
尽管《宣言》中的迁徙自由仍有不足与未竟之处,其历经不断博弈与妥协后所打破的传统边界也在此后的不同层面遭受着挑战,但是瑕不掩瑜,随着这些传统边界的消失以及《宣言》作为一种国际共识的达成与传播,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已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承认:在国家层面,在1949年到1975年间颁行的110部宪法之中,共有68部载明了迁徙自由权利,这占到了该时期宪法总数的61.8%,相比于《宣言》之前的35.7%有了极大提升。1参见[荷]亨克·范·马尔塞文、[荷]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24页。在区域层面,《欧洲人权公约》的第四和第七议定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都相继载明了迁徙自由的相关内容。2See ETS 46—Human Rights (Protocol No.4), 16.IX.1963; ETS 117—Human Rights (Protocol No.7), 22.XI.1984;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 Vol.1144, I-17955, p.150-151; 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 Vol.1520, I-26363,p.248.在国际层面,迁徙自由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在一些旨在消除歧视的公约中都逐步有了明确的规定,1966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样载明了迁徙自由权利。1参见白桂梅主编:《人权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美]爱德华·劳森编:《人权百科全书》,汪㳽、董云虎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9页;联合国大会:《大会决议案[据第三委员会报告书(A/6546)通过者]》,A/RES/2200(XXI),1967年,第37—38页。在这些法律与公约中,我们并不难发现《宣言》的印记。而在未来,前述的不足与未竟之处在持续的论争、博弈与妥协中得以修正与补足同样是可期的,正如我们在迁徙自由传统边界的消失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