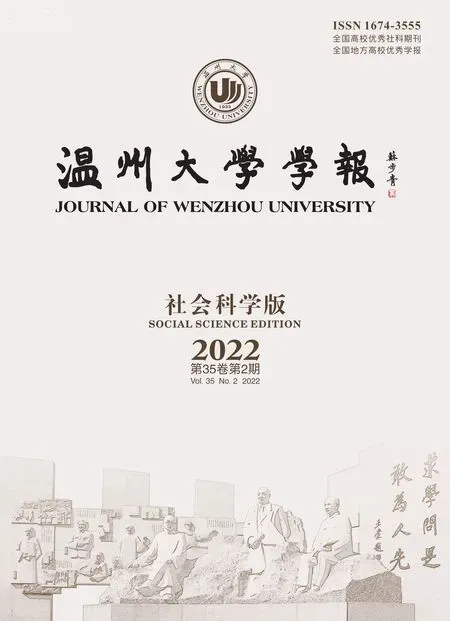龚自珍的春秋公羊学与政治改革思维
——兼论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系
孙邦金,王燕霞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1841年8月,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还没来得及目睹这个国家此后一连串的失败,生命就在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戛然而止。不过学界说起近代史的开端大概都绕不开“龚魏”(龚自珍和魏源),恰好印证了龚自珍“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1]134的自我历史定位。龚自珍在诗文、学术、政治思想等多个领域的过人才华,为其赢得了“开风气之先”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定评,使其成为揭开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的人物[2]。仅从政治思想层面上看,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强烈政治改革诉求和系列主张,使得“定庵化身”[3]成为近代赞扬改革者的常用标签。梁启超当年即曾用“若受电然”[4]四字来描述自己阅读龚自珍诗文作品时的强烈感受,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跨越时代的历史影响力,以此可想见。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多是从《易经》和春秋公羊学中化出来的,有着深厚的儒家经学渊源。他的“治平之虑”、变易历史观、历史三世说以及“劲改革”与“自改革”主张,体现出高度自觉的历史辩证思维和深刻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尤其是其“改革”与“革命”话语,业已成为现代中国流播甚广、至为熟悉的名词,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这两种历史进步模式蔚为壮观的分流、对峙与汇流历程,而且蕴含了通过持续深入的自我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易姓革命来实现中国全方位、根本性变革的社会革命理念。下拟从龚自珍变易哲学与春秋公羊学角度分析其改革思维的理论渊源与内在理据,以彰显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之前中国近代改革与 革命文化自身内在的源头活水。
一、龚自珍的春秋公羊学及其历史哲学基础
孔子所编撰的《春秋》,共一万五千余字,“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5],是一本历史书,更是一本儒家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专著。正如梁启超所说:“《春秋》者,孔子所立宪法案也。”[6]孔子所作《春秋》,微言大义,特别是其“刺讥”“褒讳”“挹损”之春秋义例与笔法,构成了儒家历史书写的基本原则,成为历代士人讽谏现实政治的重要依据。《春秋公羊传》经过历代儒家学者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等人的阐发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科九旨”为纲领、以“大一统”与“三世说”为主干的公羊学理论体系,为儒家学者诠释经典、创立新说、指陈现实奠定了理论基础。清代的春秋公羊学要以庄存与和孔广森为开端,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继其后,不断“大张其军”,渐入高潮,引起了学界普遍重视,带动培养了一批学术后劲,进而取得了匹敌清代古文经学势力的学术地位。在这场经学转型运动之中,“常州之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7],龚自珍以其大胆的政治议论被公认为常州今文经学的殿军,成为近代中国改革思潮的嚆矢。
1819年,龚自珍在28岁时回到北京,大约从此时开始正式师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后著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对此段经学研究经历,龚自珍有诗记载:“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1]76诗中高度肯定了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春秋公羊学研究,并表达了要“敬承”(自觉继承)常州今文经学研究学脉及其经世致用的学风。龚自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一步摆脱了乾嘉考据学烦琐支离和远离实际的学风,将经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凭借经义以讥弹时政”[8],表现出紧贴现实抒发议论的特点。陈其泰曾就此认为,正是“公羊学的变易观、进化观,及公羊学派把发挥经义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的学术特点,使龚自珍上升到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9]。在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公羊学研究以及汉代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以经义缘饰吏治”[10]、宋代王安石和清代顾炎武等人“经术正所以经世务”[11]等经学研究范式的共同影响下,龚自珍的经学研究并没有囿于当时纯粹的文字训诂、史实考证等“微言”限制,而是自觉地将经学研究提升到了发挥“大义”的义理研究层面。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说:“《春秋》之指,儒者以为数千而犹未止,然而《春秋》易明也,易学也。”[12]63解读《春秋》文本的“微言”无数,然不离“大义”宗旨,只有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考察《春秋》,进而从历史智慧中找寻医治现实政治问题的药石,才是《春秋》经学研究的精义之所在。正是《春秋》大义使得龚自珍有了一个新兴而有力的历史哲学支撑,这对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的孕育成熟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龚自珍对公羊学义理的发挥虽然开启了晚清经世致用和勇于议政的学风,但与晚清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学家们经常“讬于微言大义,穿凿附会”[13]之举不可同日而语。龚自珍并没有脱离经典文本和史实依据,也没有援引谶纬、灾异等异议可怪之说来神化自己的理论,而是充分继承了乾嘉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断的征实学气,这体现出十分可贵的理性精神。
二、龚自珍的春秋三世说与历史进步思维
其实早在师从刘逢禄之前,学染百家的龚自珍已经受到了公羊三世说的影响。在25岁时写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1815―1816)中,龚自珍已经使用三世说这一理论武器来把握传统封建王朝政治的发展规律了。龚自珍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12]6这里所说的“深于《春秋》者”,是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三世说”理论。在此基础上,龚自珍将其概括为“治世”“衰世”“乱世”的三世说,这为他洞察时代走势并提出相应改革方案提供了带有方向性的历史坐标系。
龚自珍认为“三世,非徒《春秋》法也”[12]46,“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蓓亦用之”[12]48。这就是说,三世说不只是用来解释春秋时代的特殊原理,还可以用来解释自然进化过程以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是可以通用于多个领域的普遍规律。在壬癸之际(1822―1823)的系列政论文章中,龚自珍指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2]16。万事万物都可以分成初生、强盛和衰败三个前后继起、不断循环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家天下”的封建政治亦不例外。在《尊隐》一文中,龚自珍用一岁里的“发时”“怒时”“威时”和一天里的“早时”“午时”“昏时”三个时段来比喻王朝政治的三个发展阶段[12]87。在《平均篇》中,龚自珍则采用了“安天下”“与天下安”和“食天下”来阐述一个朝代“治世―衰世―乱世”的阶段性变化过程[12]78。很显然,龚自珍入京之后获得的系统的公羊学训练,只是其早前业已成型的历史思维模式的自然延伸和深化。
不仅如此,龚自珍还进一步根据儒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理论来概括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只不过,王朝政治摆脱不了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而人类历史则体现出不断向前进步的总体趋势。结合《礼记·礼运》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龚自珍指出,“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12]46,治世手段和方法的变化就是人类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阶段性进步的一个侧面。在原始社会,人类食货相争,以力治世,是为“据乱世”之政治;后来国家以及礼法制度相继建立,人类社会有了规则意识,师官(司徒、司空、司寇)以兵、刑治世,是为“升平世”之政治;到了圣人(以孔子、箕子为代表)以文化治世的时代,人类社会才达到没有威迫、人人皆能够自由发展的“太平世”之政治。
在龚自珍这里,公羊三世说显然已经上升为一种普遍抽象的历史方法论,用于察往知来,观照现实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盛衰趋势。正是由于龚自珍很善于“以小见大”,很善于将现实时势放在历史规律中检视,很善于将个别琐碎的微观历史事件置于“盛―衰―乱”这一宏观历史线索中看待,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前进性与一个朝代的衰败可能性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复杂性之中,他仍旧能够保持精准的历史判断力和深邃的历史预见性。《己亥杂诗》第十九首曰:“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垒到十枚时。”[1]19这里的“理”就是抽象的历史规律,而“势”则指举目可见的社会现实及其整体趋势;“观理自难观势易”就是一种势中见理、理势相依的历史思维方法。1839年,龚自珍在辞官南归途经淮扬一带时即运用了借势见理的思维方法,敏锐地指出当时江南盛地依旧“嘉庆中故态”只是表面现象,其“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12]185寥寥数语,就使人真切地感知到清代社会的繁荣盛景已经风光难再。由于龚自珍准确判断出清朝由盛转衰的乱世时间已经悄然到来,老大帝国内忧外患已然重病缠身,他才提出了“为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宾宾”“尊隐”等多项有远见的自我改革建议。《己亥杂诗》第七十六首云:“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1]102果不其然,五十年后鼎革的历史不幸被龚自珍言中,中国的衰败终于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暴露无遗。
面对清代社会的衰败,龚自珍又从《易经》和公羊学理论中寻找到了变易进步的历史哲学作为其强烈“改革”“变法”诉求的动力依据。龚自珍在38岁时所写的《上大学士书》中说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2]319他还说:“忧无故例,患无故例,仇无故例,恨无故门,言无故家。”[12]17在他看来,运动与变化是事物的普遍特性,包括君主权力在内的几乎一切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不能事事讲求天条和先例,将事在人为的进步可能性扼杀在宿命性的历史循环论之中。可以说,“变易说”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三世论”提供了历史变革的阶段性方向,两者一道构成了龚自珍政治改革思维的两大哲学基础。有学者指出:“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类由于认识到人类在不断地增强能力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狄德罗常常说自然是人类的永恒敌人),因而产生了对进步的信念。”[14]如果说突破传统历史循环思维、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是近代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的重要标志,那么龚自珍等人主张摆脱天意和自然束缚的历史主体性意识和主动追求进步的思维,与现代性之间是有内在契合之处的。随着西方社会进化论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并逐渐深入人心,由《春秋》“张三世说”抽绎出来的自然与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尤其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历史哲学与维新变法主张,很难说没有受到龚自珍历史进步思维的启发[15]。
三、“劲改革”与“自改革”的历史辩证思维
除了具有历史进步思维之外,在“追求历史进步”的手段和路径选择上,龚自珍亦有着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他的“劲改革”与“自改革”的提法,基本上预见了近代中国变法图强过程中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深刻分歧。
(一)“革命”“维新”与“改革”
在近代中国大变动以前,中国自身传统内部已经孕育出了一套政治改革思维及其话语。它们可以用极具变法意味的三个政治术语——“革命”“维新”和“改革”来代表。虽然这三个词都强调了适时改变现存政治状况的现实必要性,然而它们在社会变革的规模、深度、速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革命”一词源于《周易·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16]这里的“革命”是指更替代表着政治合法正当性的“天命”。虽然古代的“天命”是人类意志的一种回应,但究其本身,它还是代表着超越人类的神秘力量。跟这种终极者的意志相比,晚清时期“革命”概念之内涵的宗教神秘性已经大多隐退,“天命”已经转换为代表民众集体意志的“民命”(或说“民心”“民意”)。这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革命”虽然依旧是指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更替的政治运动,但是“革命”的对象却已经换成了大多数民众所认可的政权合法性,而非带有君权神授性质的“天命”。
所谓“维新”有两个主要出处:《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尚书·胤征》中的“歼厥渠魁,协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17]。两处“维新”分别与“旧邦”“旧俗”相对,有除旧布新、新陈代谢的进步意味。
至于“改革”一词的由来,学界一般都认为是龚自珍从距其约八百年的王安石“改易更革”四字浓缩而来,之后该词成为可以与“维新”“变法”互换的近义词[18]。这个被近代中国广泛使用的概念,首见于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这篇政论之中:
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有亿万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天之议,听其自,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2]5
“自改革”与我们今天的“改良”“改革”基本同义,而“劲改革”则接近于今天所说的“革命”。龚自珍在这里不仅清晰地指出了“主动而温和的自我改革”和“被动而激烈的暴力革命”这两种基本的历史前进方式,而且还提出了“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历史辩证法,着实非泛泛而谈。
(二)“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的自改革思维
由于内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改革时机不断错失,近代中国愈变愈乱,愈乱愈急,最终从温和的改良轨道走向了激进的革命道路。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中国并不存在顽固不变派,只有温和小变的改革派和激烈大变的革命派。这从反面印证了龚自珍的不主动进行自我改革或者改革不成功皆会被革命的历史判断。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龚自珍认为自我改革仍是社会进步的最优路径选择,暴力革命只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个观点看似平常,实际上其中深意是颇耐人寻味的。
龚自珍的“自改革”主张是其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三十年就已经提出的呼吁。类似的改革吁求,在十八世纪末便已出现,在整个十九世纪的文献中反复道及,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龚自珍公开直接的“自改革”主张是引领时代风潮之先的。较之于当时昏然不觉大变将至或者主张消极维持现状的人,龚自珍无疑是十分清醒和相当进步的。龚自珍之所以没有选择足够大胆和激进的革命路径,倒不是因为他思想不够先进,而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革命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
更主要的原因是,龚自珍认为社会积弊和矛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改变它也应有一个过程,不宜操之过急,理应优先选择务实、渐进和可控的改革手段。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一》中用“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的道理来说明社会危机是长期郁积而成的机理[12]1;在《平均篇》中则直接指出,“浮不足”乃“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12]79,即均富水平是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可是事实上每个封建王朝都重复上演着“小不相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2]78的历史悲喜剧。“子亦知物极将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12]1社会终至暴力相向的最根本原因是统治者不能发挥历史主体意识而放任矛盾激化,统治者可谓咎由自取。统治者若想避免被革命,就只能从自已身上找原因。正确的做法是“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谨持其源而善导之气”[12]1。龚自珍在《平均篇》中曰:
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谆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12]79
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要去颠覆政权合法性,君主自己就已经意识到政权随时可能被颠覆的危险进而主动采取改革行动,维持天下太平。龚自珍寄希望于“有天下者”能迫于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而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不要等到下层民众“知贸迁”“相有无”时采取暴力革命去推翻政权。受历史局限,“徒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自觉而未能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相关制度设计”的自我改革办法尚未脱离儒家民本-君主政治的基调,新意不多。尤其到了社会变化纷乱多端、社会运动多且激进的清末民初,革命热情日渐高涨,大多数国人深感非彻底更弦更张不可,龚自珍这种渐进的社会改良理论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冷遇甚至抛弃。当然,与一揽子整体改革方案和通过革命推倒一切重来的抱负相比,寄希望于统治者自我革命固然多数时候是一厢情愿,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办法即便是在不断革命的近代中国也具有逐步改善的价值。
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场“自改革”和社会革命
由于龚自珍公开倡言“自改革”,因此他被后人看作是政治改良派的先驱代表,受到政治改良派的吹捧。由于龚自珍没有优先选择“劲改革”,他又不免饱受后来政治革命派的批评,政治革命派认为他属于保守派,政治改革思想过于软弱,不够彻底。其实,这些毁誉包含了太多历史后来者的“后见之明”,人们只有回到当时历史情境中才能准确评判龚自珍改革话语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从历史长时段来看,龚自珍的改革话语难能可贵地蕴含了一种可以通过积极主动性不断深化改革来实现中国社会根本性变革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追求中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这个意义上,从历史长时段来重新审视龚自珍对历史进步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思考十分必要。这对今日之社会毕其功于一役的急于求成、过于乐观的想法或者认为改革遥遥无期、治标不治本的悲观论调都是有针砭时弊之功的。
近代思想史家张灏曾将近代世界的革命分为两种:一种是被称为“小革命”的“政治革命”,另一种是被称为“大革命”的“社会革命”[19]。社会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其深度和广度皆非易姓之政治革命可比。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考察中国历史的革命循环时也指出宋元明清的易姓革命是“政权争斗的革命,是王朝的交替而非社会革命”[20]。1919年,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就已经指出,不仅中国的社会革命未发生,而且中国已发生的政治革命亦不成功[21]。如果说革命是指一种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劲改革”的结果就是,社会价值观念、民众日常生活、法律制度等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种“劲改革”也难以纳入社会革命的范畴。依此来看,龚自珍心目中的“劲改革”形同后人所说的“起义”和“造反”,指向一种政权更迭的“易姓革命”,而非社会革命。从龚自珍坚持“自改革”、怀疑“劲改革”效果的立场来看,他所主张的“自改革”反而比其所主张的“劲改革”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之意涵。在近代中国,改革通常是在革命之后方才能进行,而且似乎比革命更为漫长,更为曲折,可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革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龚自珍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他始终对暴力革命的“根本解决”方案未抱梦想。处于十九世纪前半叶的龚自珍,已经隐约看到暴力革命也具有不彻底性,看到不断循环的易姓革命与社会基本面的真正改善是两回事情。龚自珍的“自改革”主张其实不只是为“一姓劝豫”,为统治者分忧,更是在追问有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使中国历史从唯有通过“劲改革”手段实现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和“血酬定律”中彻底摆脱出来。龚自珍不仅意识到革命手段不应该成为和平时期国家治理的常用手段,更意识到中国根本性的变革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唯有坚持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精神,久久为功,通过持续深入的改革手段方能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今天,每当回顾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政治命题,就愈觉得“自改革”思维的建设性,就愈觉得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根本性社会革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