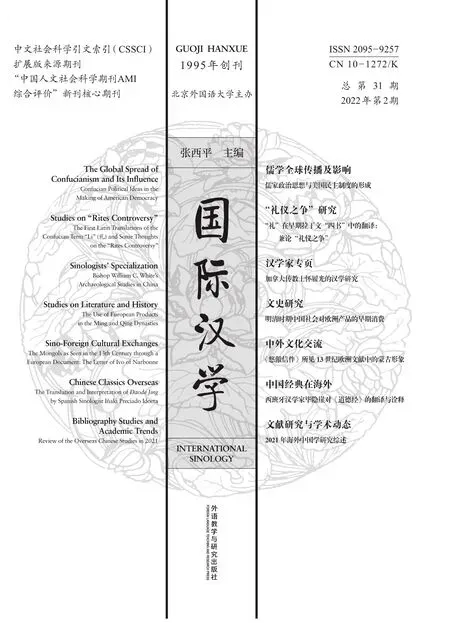以中国为镜: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
□ 张 恒
作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在哲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对中国人而言,莱布尼茨的重要性还要追加一条,那就是他对中国怀有极大兴趣并将中国思想与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论题,这在事实上构成了17—18世纪“中学西渐”进程的重要一环。
就哲学而言,莱布尼茨确曾在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上下过一番工夫,并形成了目前可见的几个文本,但是莱布尼茨哲学与理学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学界对此一直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莱布尼茨哲学深受理学影响,其许多重要理论是在理学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古典哲学曾经帮助莱布尼茨创立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尔后传到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又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吸收,一直影响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这种观点不仅在中国有一定市场,在西方也为不少学者所主张。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莱布尼茨并没有受到理学影响,将其“单子论”“二进制”等成果归于理学的启发属于言过其实。①以上两种观点参见陈乐民:《莱布尼茨与中国——兼及“儒学”与欧洲启蒙时期》,《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第13—17页。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影响是间接的,二者关系不能遽言有无。②参见许苏民:《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9—57页。
上述争议的解决,既有赖于对莱布尼茨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也有赖于对莱氏文化背景的观照,还有赖于对其理学观与其固有哲学体系的比较。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揭示莱氏理学研究的真实面向及其范式选择,进而一窥17—18世纪“中学西渐”进程之全貌。
一、“理”即“上帝”:莱布尼茨对龙华民之驳
莱布尼茨对理学的了解主要来自耶稣会在华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6③据李天纲考证,学界对龙华民出生年有不同说法,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认为龙华民诞生于1559年,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布鲁克尔(Joseph Brucker,1845—1926)神父说法为1556年9月10日,布鲁克尔历史研究著作《中国与远东》(1885)出版晚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875),应当是订正了后者的错误,故本文采纳布说。参见李天纲:《龙华民对中国宗教本质的论述及其影响》,《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第165页。—1654),确切地说,来自他写于17世纪20年代、出版于1701年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1701)①此书有多种中译名,“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译法参见龙华民:《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节选),杨紫烟译,《国际汉学》2015年第2期,第150页。原文出自Niccolò Longobardi,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Paris: L. Guérin, 1701.。龙华民写这部书的初衷,是批评、反思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前任会长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华传教的“适应政策”,亦即适应中国礼俗的传教策略。出于批评的需要,龙华民在书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理解。莱布尼茨晚年看到龙华民以及利安当(Antoine de Sat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等人的作品后,应约写下长篇评论,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1716)②此文题目有多种译法,本文取莱布尼茨1716年1月27日和3月27日致信德雷蒙(Nicolas de Remond)时的说法以及由秦家懿根据法文原文翻译的译法。参见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秦家懿译,载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该文法文版最初刊登于1768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莱布尼茨文集第四卷。该文英文版参见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Chicago: О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庞景仁根据英文版的中译文参见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4期与1982年第1期。,它是目前所见莱布尼茨关于理学的主要作品。
根据龙华民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对利玛窦时期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予以批评和反思,是因为他发现中国哲学与天主教教义不能融通,而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无神论,他曾尖锐批评说:“中国学者陷入了最严重的邪恶即无神论之中。”③龙华民:《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节选),第156页。在论证中国哲学属于无神论的过程中,龙华民对理学着墨颇多,或说他主要是以理学为中心展开论证的。而莱布尼茨的理学观念,正是在批驳龙华民等人的基础上确立的。总的来说,双方的分歧涉及“理的本质”“理气关系”“太极的本质及其与理、气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理学的核心问题。
“理”的本质无疑是理学的头等问题,莱布尼茨在评论前首先引述龙华民对“理”的理解:
我认为有人可能相信理即是我们的至高神,因为人们归于它的特征与善处都是只属于至高神的。不过,你们该小心,不要给这些名称迷住,因为底下却有隐着的毒素。若是追根究底的话,你们会发现这“理”即是我们的原始物质(primematter)。这句话的证据,是他们一方面将众善都归于理,另方面又以许多过失也归于它,就如我们的哲学家们谈到原始物质时一般。④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77页。
龙华民的意思非常明确,“理”既是众善之源又是众恶之源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天主教的“至高神”,而只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原始物质”,这实际上是以“理”的物质性来证成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无神论特质。对此,莱布尼茨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他针锋相对又不失幽默地指出:“我记下龙华民神父自己的话,以便小心检讨一切,因为我认为他完全错了。”⑤同上。莱布尼茨也的确这样做了,他一一列举龙华民对“理”作物质性理解的五条理由,并逐一检讨、批评。根据莱布尼茨的总结归纳,龙华民的五条理由如下:第一,“理”不能自存,而必须靠“元气”存在;第二,“理”本身并无活力,并无生命,并无沟通能力,又无知力;第三,“理”的所为,不发自意志或判断,而是偶然性的,元气自然地、偶然地出自“理”,受激动的气也一般自然地、偶然地产生热,而天与地的受造也是不需判断和计划而发生的;第四,“理”是所有产生和腐化的主体,对于各种特点和偶然形式采用或取或舍的形态;第五,凭中国人的话,世上的万物都必然是物质性的,而没有真的精神体。⑥同上,第82—86页。
理由一认为“理”不可自足,需要依托“元气”,但莱布尼茨认为,理学的相关论述并不是在说“理”的非自足性,而是在说其非自动性,亦即“理”凭借事物而动的特性,就像它凭借原始物质(元气)产生事物一样,龙华民的理由恰恰说明“理”与“气”实为二物,“理”不是物质。针对理由二,莱布尼茨提出,如果中国古典作者说过关于“理”无生命、无知识、无力量诸如此类的话,他们的意思是说“理”不具有具体的、体现于万物身上的那种生命、知识和力量,实际上,由于中国哲学赋予“理”至善至美的特点,它便已经具有最为崇高的美性,它比所有具体的生命、知识和力量都要高级,后者只是它的“影子”。理由三可简单概括为“理无意志”,莱布尼茨认为这一条也不能成立,因为“理”正是凭借其自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了最妥善的一种,产生了“气”(或物质),进而产生了万物,这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仍是“理”的意志的体现,“理”的这一特点正符合“至高神”的特点。理由四实际上是将“理”视为万物生成与发展变化的经验性本原,亦即认为“理”有形体、形制,莱布尼茨认为龙华民所引文献中并未将“理”说成是“产生和腐化的主体”,相关表述说的是元气或物质,“理”并不直接产生万物,而是通过元气或物质创造出原初的隐德来希(Entelechie),亦即“单子”(Monas),进而构成万物。对于理由五,莱布尼茨指出龙华民所引文献不足以提供支持,他认为中国人承认精神体的存在,那就是可以产生物质的“理”,除此之外,中国人不承认任何非物质性的实体。
可以看出,龙华民试图以“非自足”“无生命”“无意志”“有形制”“非精神”等特征来证成“理”的物质性,进而证明其无法与天主教所信奉的精神性的“至高神”相融通。而莱布尼茨却从龙华民所引文献中看出了截然相反的意思,即“理”是中国哲学中唯一的精神性实体,它至善至美,具有最为崇高的生命、知识和力量,它自然地、必然地创造了元气或物质,并借此创造了万物。既然如此,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的“理”就是他们拜为至高神的至上实体。
至于“理气关系”问题,上文已有所涉及。尽管龙华民认为“理”是物质性的而莱布尼茨认为“理”是精神性的,但二者在“理气先后”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气”出于“理”,“气”是“理”的产物。二者的分歧在于,莱布尼茨不同意龙华民“理本身并无所为,产生元气之后开始有所为”的观点,这实际上仍是上述“理的本质”问题的延伸,即“理”究竟有没有意志和活力。莱布尼茨认为,龙华民的观点内部存在抵牾,因为既然说“理”产生了“气”,便不能说“理”无所作为,“理”显然是有所作为的,是有意志与活力的。在莱布尼茨看来,理学的“理生气”观念正可以理解为至高神通过纯动而产生了原始物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比较古希腊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的神学”①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90页。,因为后者认为物质与至高神同等,即不是由至高神造的,而只是由它赋予形式。
与此同时,莱布尼茨还重点探讨了“太极”问题,这也是理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莱布尼茨引述龙华民关于“太极”的观点以展开批评,但是他的引述有些支离破碎乃至模糊不清,好在这些内容可以从龙华民的原文中找到相对完整的表述:
“理”“气”形成他们称为“太极”的无穷大球体,“太极”的意思是完美与完满的终极程度;在太极尚未产生万物之前,中国人也称之为浑天。从混沌经过五次挥发产生出来的“气”,从物质层面来说是不灭的,也是与“理”同质的,不过物质性更强,在浓缩、稀释、运动、静止,热与冷的作用下更容易变化。②龙华民:《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节选),第157—158页。
龙华民一方面认为“太极”包含“理”与“气”,是“理”与“气”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太极”是“理”(至善至美)或者是“气”(产生万物),此间的矛盾便被莱布尼茨敏锐地捕捉到了。莱布尼茨认为龙华民混淆了“太极”与“理”“气”的关系,在他看来,“太极”与“理”实则是一回事,只是言说角度不同,“太极”是在“气”上有所作为的“理”。至于龙华民所说的“太极”包含“理”“气”,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包含”绝非经验性的、组成式的“包含”,而是逻辑地“包含”,就像“结论”早就存在于“信念”之中那般“包含”。总而言之,在莱布尼茨看来,“太极”不可能是物质性的“气”,而只能是精神性的“理”。
除此之外,莱布尼茨还对“鬼神”“灵魂”“万物一体”等概念或命题做了探讨,试图从多个角度证成“理”是中国哲学中唯一的精神实体,是中国人信仰中的“至高神”,而龙华民关于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判断是错误的,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是确确实实的有神论。
二、正解、误解与曲解:莱布尼茨理学观辨析
莱布尼茨在对龙华民等人的批驳中建立起了关于理学的观念体系,他相信理学之“理”是中国人的“至高神”,理学是一种有神论的哲学体系。这种理解是否符合理学的实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结合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做一番考察。
考察之前须先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所依据的文本,亦即龙华民等人在论述、评析理学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龙华民固然也引述了《论语》《尚书》《礼记》等中国早期文献,但他对理学的阐释主要还是基于《性理大全》。①孟德卫亦注意到这一点,参见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性理大全》是由明代胡广等人奉敕编撰的一部类书,全书70卷共收录120位宋儒的著作、言论等,其中前25卷收录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等名家名篇,后45卷按照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等主题分门别类地汇编各家的言论,可谓一部宋代理学百科全书。该书作为理学“入门书”的确在全面性上有其价值,但问题也在于此,即其所涉百余位学者前后跨越二三百年,不仅所属学派不一,即便同一学派内部观点也不见得完全一致,想从中抽绎“理”“气”“太极”等理学概念与命题的一致性,对龙华民、莱布尼茨等人来说无疑是一巨大挑战。这一问题导致了他们对理学的误解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
首先来看龙华民与莱布尼茨对“理”的理解。二者第一个分歧在于“理”是否能够自存,龙华民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理”必须依靠“元气”而存在,莱布尼茨则认为“理”可以自存,只是不能自动,必须依靠“气”而动。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理的本质”,也深度涉及“理气关系”,可以说是理学最为核心的问题。对理学史做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尽管“理”字早有,但真正将其作为超越性的哲学概念来使用实始自二程兄弟。二程既承认现实世界是气化感通的产物,又为现实世界找到了“理”这一超越性依据,他们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二。言开阖,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阖者道,开阖便是阴阳。”②(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0页。又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③同上,第162页。
在二程以及朱熹那里,“道”即是“理”,二者不作分别,其创见在于将早期“一阴一阳之谓道”观念作了“所以阴阳者道”的理解。早期“一阴一阳之谓道”观念以阴阳二气相交相感化生万物为“道”,有将“道”气化的倾向,更多体现出生成论的意味;程朱则将“道”“理”理解为阴阳二气相交相感化生万物的原因或根据亦即“所以然”,这便不单是生成论,而且有了存在论的意味。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是“气”的原因与根据,“气”是“理”的载体和呈现,二者不即但也不离,这种解释框架背后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体用”思维范式,即“理”是“气”之体,“气”是“理”之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④同上,第689页。。当然,在朱熹那里,“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足性,所谓“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但朱熹也强调“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②同上,第2页。,因此说朱熹主张理气相依也并无不可。在这个意义上,龙华民和莱布尼茨的理解都是对的,“理”既不能自存,也不能自动,它须依“气”而存在、显现。
接下来的问题是,“理”是否具有活力、生命、沟通能力和知力呢?龙华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莱布尼茨则提出了一种值得玩味的理解,即“理”虽然不具有具体的生命、知识和力量,却比天地万物之中任何一种具体的生命、知识和力量都更高级,因为它是至善至美的,堪比“至高神”。显而易见,莱布尼茨对“理”采取了一种“超越”的理解方式,亦即将“理”视作一种超越于经验世界的至善至美的存在。就此而言,莱布尼茨的理解比龙华民的理解要准确、到位。
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超越性的、至善至美的“理”是否具有意志或判断呢?龙华民认为没有,即“理”的所为皆是出于偶然;莱布尼茨的理解恰好相反,他认为所谓的“偶然”是“理”凭借自身的完美而从众多可能性中选择的最为妥善的一种,因此实际上也是出自“理”的意志或判断之“必然”。从宋代理学家的观念来看,“理”显然并没有神学意义上的意志或判断,对此朱熹说得非常明确:“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③同上,第3页。但需注意的是,“理”的所作所为却也并非全凭偶然。二程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老子之言,窃弄阖辟者也。”④《二程集》,第121页。众所周知,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其“自然”之论没有道德价值取向,全凭“偶然”。二程反对老子的观点,认为既然“理”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至善至美,由理而发便无所不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是理学家普遍强调的“德性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的确敏锐地把握到了“理”的必然性,但他认为“理”有意志或判断则属于牵强附会。
基于以上分析,莱布尼茨与龙华民分歧中的第四点与第五点就很容易解决了。龙华民认为“理”有形制亦即是所有产生和腐化之主体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理学家们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理”作为超越存在是无形无象的,有形有象的只可能是“气”,对此莱布尼茨的理解更加准确。由此,龙华民关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万物皆属物质性的观念也是错误的,“理”显然就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如果不考虑“理”有意志或判断等牵强附会的解释,莱布尼茨对“理”的理解要比龙华民到位。
再来看莱布尼茨与龙华民对“太极”的理解。莱布尼茨认为龙华民的“太极”观念是混乱的,即他有时称“太极”包含“理”“气”,有时又称“太极”是“理”或是“气”。在莱布尼茨看来,“太极”绝不可能是“气”,而是在“气”上有所作为的“理”,也就是“至高神”。究竟谁的理解更准确呢?历史地看,“太极”一词较早出自《庄子·大宗师》,是一个表征空间的概念。《周易》经传中关于“太极”的表述对后世影响颇大,其更多承续了道家的宇宙论追求,亦即“太极”是作为宇宙生成本原而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点又被汉唐学者的“气论”诠释路径所强化。⑤郑玄曾说:“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孔颖达说得更加清楚:“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参见(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成玄英亦言:“太极,五气也。”参见(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7页。在隋唐五代学者尤其是道教人士中间,“以气解易”“以气论丹”等是极为普遍的观念和实践。当邵雍、周敦颐等早期理学家从道教徒陈抟那里几经转手而得到《先天图》或《太极图》时,其哲学体系便很自然地沾染了宇宙生成论的色彩。邵雍和周敦颐都有将“太极”视作“气”的思想倾向,但深入其哲学内部又可发现,“释极为气”并不是他们的创见与旨归。邵雍说“心为太极……道为太极”①(宋)邵雍:《邵雍全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4页。,“万化万事,生乎心也”②同上,第1228页。,“太极”不仅仅是“气”,而具有了一定的“理”的特点。周敦颐说太极“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③(宋)周敦颐:《通书》,载《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太极”固然有“物”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神”的一面,这一面具有“是万为一, 一实万分”④同上,第32页。的超越性。邵、周等人从宇宙论跃向存在论的努力在程朱那里“修成正果”,朱熹在诠释周敦颐哲学时说:“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二气之实,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⑤(宋)朱熹:《通书解》,载《周敦颐集》,第32页。在朱熹看来,“太极”就是“理”,而且是“总天地万物之理”,是“统体一理”。
可见,龙华民的确知悉“太极”的话语演变与不同形态,但他并没有理清这些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此做出恰切的解释,这种“混乱”被莱布尼茨敏锐地捕捉到了。尽管莱布尼茨不了解“太极”的话语演变与形态演变,但他从逻辑与语言的角度做出的判断确有道理,因为“太极”的确不可能同时是“理”和“气”,而只能是其中之一,莱布尼茨将“太极”理解为“理”,这与朱熹所见略同。而且,莱布尼茨关于“太极”逻辑地“包含”“理”和“气”的观点也准确反映了朱熹对“太极”“理”“气”之关系的理解。
总之,莱布尼茨对理学的理解有正解也有误解,甚至有“刻意的”曲解,其典型之处即是将“理”与西方的“至高神”画上等号,将理学与有神论画上等号。这种曲解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文化背景与哲理基础的。
三、镜鉴与确证: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范式
美国学者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曾指出:“考察莱布尼茨对中国及文化交流兴趣的挑战在于,我们要揭示出这一兴趣不是偶然的东西,揭示出莱布尼茨对交流的推进不是与他的哲学体系无关的而正是出自他的哲学本身。”⑥方岚生:《互照:莱布尼茨与中国》,曾小五译,王蓉蓉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这一问题意识极具启发意义,对莱布尼茨理学观的研究亦应作如是观,即“比较”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其理学观的文化背景、哲理基础及其作为跨文化研究范式的特点。
莱布尼茨最主要的理学研究文本《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完成于其晚年的1716年,此时距离利玛窦去世已超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天主教内部针对在华传教策略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这场论争的焦点,一言以蔽之,即是否应继续执行利玛窦时期采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尤其是允许教徒祭孔、祭祖以及摆放牌位等礼仪方面的策略。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是这一策略的反对者,他通过对理学的分析发现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实为无神论,这与天主教无法融通,其作为莱布尼茨“靶子”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即是在“中国礼仪之争”的“蛰伏阶段”⑦林金水将“中国礼仪之争”划分为四个阶段:蛰伏阶段(1610—1628)、爆发阶段(1632—1692)、高潮阶段(1693—1722)、余波阶段(1722—1742)。参见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0—25页。写成的。
1693年3月26日,耶稣会强硬派代表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发布告示,严禁其代牧区教徒祭孔、祭祖,引起清廷反感,并逐渐将“中国礼仪之争”推向高潮,耶稣会内部反对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对中国发生兴趣亦即频繁与在华传教士通信并据此编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就是说,莱布尼茨对中国、理学等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处于论争的思想氛围之中,尽管他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开篇声称无意卷入论争,但他还是清晰表明了立场:“龙华民神父——中国传教区首创者利玛窦神父的接班人——为反驳[利玛窦]的‘适应文化’性的解释而提出的最强理由已失去效力。”①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69页。在莱布尼茨看来,利玛窦的“适应文化”传教策略是一种正确路径,应该继续执行。莱布尼茨实际上与龙华民等人一样,是带着神学“眼镜”来看待中国、中国人及中国哲学的,也是以“纠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为其最终目的的,只不过在路径选择上与龙华民等人发生了分歧。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莱布尼茨的路径选择是与其哲学体系密切相关的。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莱布尼茨的核心任务是阐明“理”是中国哲学中唯一的精神实体,他说:
总之将灵魂说成它可能是发自至高神的实体,使至高神似是有部份的,是不对的。灵魂只能来自无。所以若是某些中国哲学家说事物发自“理”,我们不可以立刻说他将“理”变成事物的“物质因”(material cause)。②同上,第80页。
莱布尼茨似乎已意识到,中国哲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些学派需要被“谴责”,而另一些则可以予以认可,标准即在于将“理”视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而这一问题在当时的西方哲学中是能找到与之呼应的问题的,莱布尼茨正是相关问题的深度参与者。具体而言,莱布尼茨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提出的,而斯宾诺莎哲学又在事实上是为解决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哲学的困境而建构起来的。笛卡尔从“怀疑”出发,得出“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彰显人类理性的结论,亦即只有“我思”才是唯一可以确证的存在,它是非物质性的精神实体。从逻辑上讲,“我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实体”,它不可确证;另一类便是可以确证的,它只可能是“上帝”。由此,笛卡尔一方面“确证”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也陷入了“思”与“物”二元对立的困境之中。对此,斯宾诺莎的解决方案是只承认“上帝”这一“实体”,将“思”与“物”视为“上帝”的属性,这也就是莱布尼茨对斯宾诺莎的批评——“受造物只是至高神的各种变化”。在莱布尼茨看来,斯宾诺莎并未彻底解决笛卡尔的问题,因为如果“思”与“物”是上帝的属性、变化,那就意味着上帝有这样或那样的部分,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至高神并非是由各种部份组成的”,它只能是“一”:“只有上帝才是原始的统一(I’Unité primitive)或最初的单纯实体,一切受造的或派生的单子都是它的产品。”③莱布尼茨:《单子论》,段德智、陈修斋译,载段德智编《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89页。上帝是“大一”,是“原始的统一”,是“最初的单纯实体”,是最高级的“单子”,除此之外一切“单子”都是上帝造的。每一个“单子”都完满自足、有知有力、不可分割、不可交通(“没有窗户”),尽管如此,“单子”间以及由其组成的事物间也不会陷入混乱,因为其存在状态是早已被“至高神”所预先设定好的前定和谐(I’harmonie preétablie)状态。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与“前定和谐论”。
莱布尼茨上述哲学思想大概形成于1686年底以前,④许苏民:《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第49—57页。当后来较多接触中国哲学时,他立即从理学那里找到了共鸣。陈乐民认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与莱布尼茨早些时候写成的《单子论》(La monadolagie,1840)实为“姊妹篇”,两文可以相互参比,因为前者中通篇可见后者的影子。⑤参见陈乐民:《莱布尼茨和“儒学”》,《读书》1996年第7期,第108—115页。这一观察是敏锐的。下文试举两例以作说明:
其一,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一部分“中国人对至高神的看法”的结尾,莱布尼茨这样总结:“我们可能说,我们实在不可将‘理’与我们(西方)哲学家的原始物质一般看待;但是我们仍可将它当作第一形式(first form)即是世界的灵魂……第一形式或纯行动并无其部份,所以第二级形式不出自第一级,而是它造的。”⑥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88—89页。莱布尼茨强调“第一形式”不可分、纯行动的特点,这显然是指“单子”而言。“第二级形式不出自第一级,而是它造的”是指作为最高级单子的上帝创造了原初的单子亦即原始物质,原始物质继而变化生成宇宙万物。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单子是可以找到的“最后的”本原。莱布尼茨以这样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理学,鬼神自然都是实有的,虽然它们是“理”创造的,但与“理”一样本质上都是“单子”。在莱布尼茨看来,从“单子论”出发,“理气二元”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其二,莱布尼茨对龙华民“理无意志或判断”相关观点进行了批驳,莱布尼茨反驳之后这样说道:“我相信我们不用违背中国人古代的学说,即可说‘理’凭着本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妥善的一种,因而产生‘气’或物质,但[气]因备有其本能,而使其他的[万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习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实在值得受人称扬。”①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第85—86页。莱布尼茨极为赞赏的“事物因自然习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观念,实际上是理学的“德性自然”观念,也就是“顺应天理、自然中礼”的观念。这一观念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异曲同工,都强调宇宙万物先验地具有和谐的“种子”的状态,在莱布尼茨那里,这种“前定和谐”得自“至高神”,在理学那里,“前定和谐”得自“理”,莱布尼茨将“理”解释为“至高神”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理学体系的诸多特点让莱布尼茨看到了它与“单子论”“前定和谐论”等理论的相通之处,而“理”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其至善至美更是让莱布尼茨看到了它与“至高神”的相似之处,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它好得不能更好:这句话说出一切。”②同上,第77页。以此为诠释框架,莱布尼茨不得不一次次地向龙华民发问:“为什么不能也说中国人的‘理’即是我们拜为至高神的至上实体呢?”③同上。
可见,莱布尼茨对理学的诠释是基于自身的信仰与哲学的,他对理学的认可实际上是从理学那里发现了可与自身信仰与哲学相呼应的元素。他固然有一些对理学的正解,但在终极之处却是对理学的曲解。至于“理”是否真的如“至高神”那样有意志和判断,是否真的如“至高神”那样有知有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属于一种“镜鉴 - 确证”范式,也就是“以中国为镜”“以理学为镜”,他的确对“镜子”充满了兴趣,但更让他兴奋的是从“镜子”中照见了自身并确证了自身,更具体而言,确证了至高神的存在,确证了其理论体系和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
四、结 语
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相遇”发生在17—18世纪西方近代启蒙时期与“中国礼仪之争”的思想背景中,他基于自身业已形成的“单子论”“前定和谐论”等思想理论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做了“有神论”理解,驳斥了龙华民等人的“理学无神论”观念。莱布尼茨对“理”的确有独到见解,但他将“理”视作与“上帝”一般的精神性实体并进而将理学视为有神论,这却是对理学的曲解。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实则采取的是“以中国为镜”,并从中照见自身、确证自身的范式。尽管如此,相比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莱布尼茨的跨文化研究范式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在17—18世纪“中学西渐”进程中,莱布尼茨对东方的兴趣远超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回顾并梳理其研究范式,有助于对莱布尼茨哲学及其与中国哲学关系的准确理解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