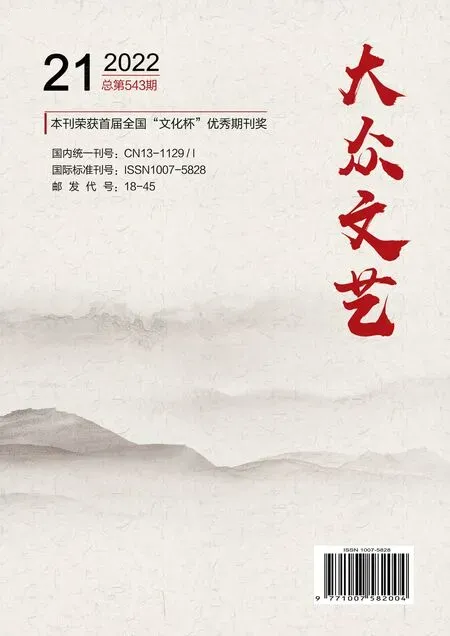从“虚实相生”看秦可卿形象的“不写之写”
刘 军
(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北京市 100071)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名著的《红楼梦》,其历史文化地位自不必说。小说的艺术特色一直被学者们研究讨论,尤其是叙事上的特殊笔法。脂评言道:“《石头记》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种种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1]除此之外,“不写之写”也是全书极为重要的叙事笔法,其所引发的艺术空白点效应,不但与全书的思想主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达到了某种内在契合,并且在阐释与解读的过程中,容易营造出一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意蕴。尤其是在塑造秦可卿这一人物形象时,这种笔法的运用显得格外精彩与典型。那么,如果我们要对“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及由此产生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意蕴作一文化精神与美学精神溯源的话,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虚实相生。
一、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虚实相生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于宇宙的思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重视区分,把混沌与秩序截然划分开,并且将有规律可循的秩序作为宇宙最终的本质。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西方文化一直试图从混沌中找出秩序。然而,中国文化始终将混沌与秩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既要看到有迹可循的秩序,又要体悟秩序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强调的不是“实”的秩序与“虚”的混沌之间的对立,而是主张、重视二者的统一与和谐,即中国人的宇宙观强调的是“虚实相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具有人文特点的居室中。《老子·第十一章》讲:“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是说,房屋之所以能够成为房屋,一方面在于“室”这个事物本身,另一方面,更在于户(门)以及牖(窗)的存在,它们以空无的状态弥合了房屋的虚实相生结构。除了房屋之外,还有房屋里住的人。《黄帝内经》讲人体的筋骨肉(实)与精气神(虚)的统一,显示的也是一种天然的虚实相生结构。最后,我们再来看天地之间所构成的虚实结构:天上的风云雾霭,地下的山河动植……,中国的宇宙及万事万物始终呈现着虚实相生的结构。[2]
诚然,中国文化的特质——虚实相生——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淀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中。从绘画中的“无画处皆成妙境”到书法中的“计白当黑”,从园林中的“借景”“隔景”到戏曲中的“一桌二椅”,中国各门艺术的创作都离不开对虚实的运用。“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3]甚至于中国古代的理论体系著作—《诗品》,其言说方式都在强调“虚”与“实”的统一。比如什么是“雄浑”呢?“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什么又是“冲淡”呢?“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司空图语)事实上,“雄浑”也好,“冲淡”也罢,每一品,都是通过具体的场景和景象让你自己去感受。中国美学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从来不会让你去理解一个定义或分析一个概念,而是通过“实”的景象让你由象入境,直接在境中体悟和感受“虚”的意蕴。你说它说了,其实什么也没说,如果真的没有说,怎么又能让你领会其深层的底蕴呢?从这一层面来说,《红楼梦》叙事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借助“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使文章多处呈现出“空白点”,即脂评所谓“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以此丰富作品的内在意蕴。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视野,从情节结构设置的“空白”点以及人物描写设置的“空白”点两个方面着手,以秦可卿的“不写之写”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期挖掘秦氏内在的、丰厚的审美意蕴。
二、情节结构“空白”
情节结构“空白”是《红楼梦》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情节结构“空白”,指的是作者在情节结构的编织中刻意留下空白,以此调动读者的想象,使读者一起参与到文本的二次创作中,从而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秦可卿作为《红楼梦》中的一位特殊人物,正当妙龄却意外夭逝,并且在她出现的寥寥数回中,作者所用的笔墨也是相当的有限。但是她的地位,她的人物形象意蕴并没有因此衰减。相反,在《红楼梦》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恰是在秦氏的有关情节中所运用的“不写之写”叙事笔法,使得其与黛玉、宝钗、凤姐等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秦氏“速死”的情节中。
首先,在刚出场没多久,她就患病卧床不起。作者叙述她的病十分蹊跷,在医治的过程中也因各个大夫的不同看法,使得其病源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及至她的暴死,更是让所有人“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4](第十三回)脂批明确指出此处:“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5]当张太医将秦氏的病因归结为“思虑太过”时,读者不免会想到加重秦氏病情的导火索:他的弟弟秦钟与宝玉在私塾中和金荣产生了冲突,金荣对他说了些难听的话,他将这些话转告给姐姐,秦氏听到后又恼又气。这是因为,秦钟与香怜的缠绵之事被他人所议论,直接触动了秦氏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众所周知,原来小说第九回的回目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在“爬灰”“养小叔子”“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宁府”以及秦可卿的判词等蛛丝马迹中,我们对贾珍与秦可卿之间的乱伦之事已有了初步的判断。
其次,对秦可卿室内摆设的叙述同样运用了“不写之写”的笔法:“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第五回)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等在中国野史中,皆与风流韵事相关,从这些摆件中,透露出种种暧昧的气息,这里仅以“宝镜”为例进行简要说明。《资治通鉴》曾有记载:“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遽令剔去”[6],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则天室内造了镜殿,以供男女嬉戏之须。后来,镜室也因此成为淫乱的代言词。当武则天镜室中的宝镜出现在这里时,一方面固然是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间接暗示,另一方面,更是对秦可卿风流之事的直接指认。
最后,直至秦氏葬礼上丈夫贾蓉与婆婆尤氏的“缺席”,整个过程都是由作为公公的贾珍忙里忙外,这一切似乎都能从“写”出的内容体悟到“不写”的韵味。先看贾蓉,小说将秦氏之丧涉及的各行辈分亲友,罗列出二十八位之多,唯独不见贾蓉。贾蓉的唯一一次出场,是贾珍为贾蓉捐官后他的出场:“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第十三回)贾珍父子的种种行为,犹如二者角色发生了“错位”,“即公公做的,恰是丈夫分内的事。公公对儿媳的感情,恰是丈夫应对妻子的感情。而丈夫的表现,恰是公公碍于礼法处处回避儿媳所当为者。”[7]再看尤氏,“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第十三回)平日里,那么疼爱儿媳妇的她怎么突然在此时就碰巧地胃疼了呢?要知道,小说中写道凤姐、黛玉、宝钗等生病时,多少都会提及请医问药之事,唯独尤氏没有。即使没有请医问药,至少也应该有人来探问看望,难道是作者创作上的疏忽?又难道是阖府上下都在为秦氏的丧事忙碌奔波,故无暇来问?或许,尤氏的病根本就不需要人来医,也不需要人来慰问,她的病只有自己才能疗愈,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心病”。再来反观贾珍,当得知秦氏夭逝,从哭得“泪人一样”到表明自己对丧事的态度:“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以上种种,在许多学者看来,无疑是为了表现封建社会的淫乱生活。也因此,“不写之写”的内容具有了相对清晰的指向。然而,可卿的“速死”,以及由“不写之写”所引发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意蕴是否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呢?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除了上述指涉的淫乱之事,作者处理秦氏的“速死”,一方面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借她的死,借着丧事的操办,以此渲染贾府的富贵荣华,贾府盛极时的光景。另一方面,也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写秦氏之死,无非是为了表现凤姐的精明能干,从协理宁国府到弄权铁槛寺,凤姐多方面的才能与见识在处理秦氏丧葬这事件中不断显现出来。[8]
当然,作者通过“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借秦可卿的“速死”,并由此所引发的种种阐释,对于我们理解秦氏形象的特殊性多少产生了一些启发性。不过,要充分把握秦氏之于整本书的存在意义,更加全面合理地阐释与解读秦氏形象的内在意蕴,还应当将作者对她生前的相关描写结合起来综合考量与把握。
三、人物描写空白
如果说,由秦可卿的“死”所营造的情节结构“空白”是通过省略情节或者淡化情节的设置,以此实现“不写之写”的话,那么,她的“生”所构成的人物描写“空白”,则是通过他人之口的评价以及点睛之笔的渲染来完成的“不写之写”。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性人物,比如宝玉、黛玉、凤姐等;另一类是虚体化人物,比如甄士隐、贾雨村、一僧一道等,秦可卿就是后一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书中关于她的描写,一方面是通过他人的评价来完成的:第五回,她的第一次登场,作者并没有直接对其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贾母的视角展开的:“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此外,作为婆婆的尤氏更是坦言道:“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第十三回)实际上,从他人对秦氏的评判中,我们对其人物形象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内容。然而,恰是在这些看似重复、累赘并且极为有限的叙述中,可卿人物形象的模糊性、朦胧性,可卿人物形象的“空白”点由此获得了足够多的阐释空间。
除了他人的评价外,运用“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对秦氏形象塑造的另一条路径,是通过点睛之笔的渲染来实现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她的出生、婚配以及“梦中人”的形象基质上。作者交代,她原是其父亲从养身堂里抱养的孤儿,长大后“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第八回)我们想想看,这样的身世究竟是怎样与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匹配成亲的?对这门亲事的判断与评价,我们自然不能用常规的情理去衡量。
在出生与婚配之外,秦氏作为“梦中人”的形象同样运用了“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来完成的。秦氏出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宝玉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午休,尽管有学者认为她与宝玉也有过淫乱关系。[9]且不论这种看法有无事实依据,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秦氏在这里是作为宝玉梦中的引路人出现的,其身份也在这一过程发生了裂变:其一是警幻仙子,另一则是乳名兼美字可卿者。宝玉在警幻仙子的带领下,窥得“薄命司”中的十二钗判词、画册以及曲词等,并在警幻仙子的主持下,将兼美许配给了自己。于是,秦可卿作为“梦中人”形象的内在意蕴得以顺利体现出来:一方面预示了宝玉往后以恋爱为重心的情感生活,另一方面,对红楼女儿们的思想性格、悲剧命运作出总揽式暗示。[10]
如果说,秦氏入梦于宝玉是从“情”的立场出发,通过“不写之写”的笔法对宝玉的情感生活及大观园众女孩的悲剧宿命所进行的勾勒的话,那么当她入梦于凤姐,则是从“政”的立场出发,同样是通过“不写之写”的笔法对贾府盛极转衰的发展趋势做了充分警示。从“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到“登高必跌重”;从“乐极生悲”到“树倒猢狲散”,在一个个俗语、成语的累积堆砌下,秦氏“将一个大家族的盛衰之理、危机无可更改的自古而然的必然性予以了充分的强调。”[11]因此,当她入梦于凤姐,并针对贾府的现状给出具体的筹划措施时,其作为“梦中人”形象之于《红楼梦》的特殊意义也同时凸显出来:一方面,她对贾府未来的衰败之势作出充分警示,另一方面,也将凤姐作为治理家政的中心人物予以暗示说明。至此,无论是作为“情梦”的引路人,还是作为“政梦”的引路人,秦氏之于《红楼梦》中的“情”与“政”的最终悲剧,都具有了一种“警幻”意义。[10]于“情”而言,大观园众女儿们“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第五回);于“政”而言,最后只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他人对秦氏的评判以及她的出生与婚配乃至其作为“梦中人”的形象,都是经由“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为揭示秦氏形象的内在意蕴,为说明其之于《红楼梦》的特殊意义所做的一种特殊叙事策略。
结语
诚然,由“不写之写”的叙事笔法所构成的情节结构“空白”与人物描写“空白”,将秦可卿模糊性与朦胧性的形象基质予以了双重指认。由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通过表面上外在的“实”的叙述,进入到人物本质上内在的“虚”的把握。也就是说,有了情节结构与人物描写的“空白”,有了“虚”,秦氏人物形象的生命意蕴才会饱满,才会充实。所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其实都是在强调“空白”和“虚”所内嵌的审美底蕴与精神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