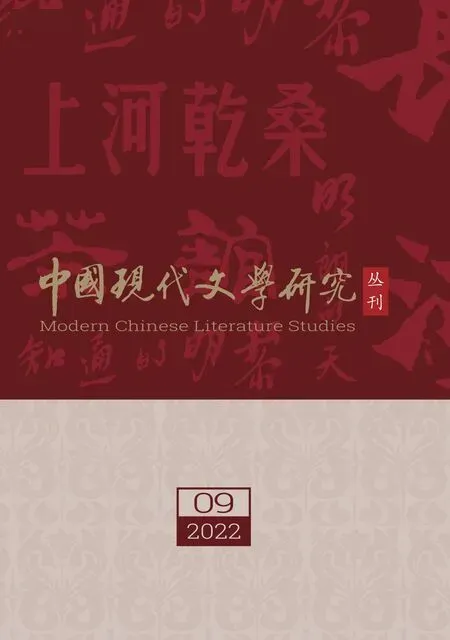诗歌翻译理论的新发展※
——王家新的翻译诗学
方 舟
内容提要:王家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外国诗歌的中译工作,同时思考、探索诗歌翻译理论,其翻译诗学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以翻译辨认生命,主张诗人通过翻译,在辨认生命过程中建构自我精神家园;二是认为译诗是追求“更高的忠实”,即以忠实为准则,同时要具有创造性;三是将译诗视为对语言的刷新,主张通过翻译丰富自身语汇体系,形成新的语言意识。王家新的翻译诗学体现了20世纪后期中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初,伴随着外国诗歌的译介,中国开始建构自己的现代翻译诗学。长期以来关于外国诗歌翻译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于音译、意译以及“信达雅”等问题,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新诗诗意创造相吻合的翻译诗学。20世纪后期,王家新、西川等一批诗人,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向国外,翻译了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策兰、茨维塔耶娃等一批外国诗人的作品,他们进一步思考外国诗歌翻译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诗歌翻译观。王家新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版了《保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选》《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等译诗集,他称“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使我真正抵达一个诗人的‘在场’”①王家新:《辨认的诗学——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及其翻译》,收入王家新,《翻译的辨认》,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248页。。抵达“在场”就是抵达诗中的生命所在,通过翻译联结生命与创作,诗歌翻译也成为其个人精神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家新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国诗歌翻译观,推进了中国诗歌翻译理论的发展。
一 翻译是对生命的辨认
王家新曾提到:“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②王家新:《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收入王家新,《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辨认的诗学”源于曼德尔施塔姆,王家新认为:“创作和翻译都是一种‘辨认’。诗人的一生就是一种辨认。”③王家新:《辨认的诗学——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及其翻译》,《翻译的辨认》,第250页。辨认生命的意识使王家新选择了曼德尔施塔姆、策兰、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勒内·夏尔等作为翻译对象。在他的观念中,“译了策兰,就不能不去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甚至不能不去译勒内·夏尔”④王家新:《为语言服务,为爱服务》,《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第138页。,这种“不能不去译”包含着王家新对域外诗人生命的深刻辨认。王家新在翻译中辨认这些诗人生命的脉络,联结与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谱系”。
在这个生命的精神谱系中,保罗·策兰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王家新进入翻译领域便是从翻译策兰开始的,三十余年来,他在不断地翻译、扩充策兰诗作的过程中,审视、辨认策兰的生命。策兰的作品中,语气断裂是生命艰难的象征,而那些不可译的部分则暗示着生命本身的不可言说,王家新努力辨认策兰诗作“去人类化”的特点,在翻译时“全身心进入并蒙受诗人所创造的黑暗”⑤王家新:《保罗·策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以生命进行品读,因此他译出的策兰总是笼罩在荒谬、怪戾的气氛中。策兰之痛是生命之痛,其母亲死于喉咙的枪伤,因此他的诗里常常出现“喉咙”“咽喉”等字眼。王家新抓住了策兰生命中最残忍的秘密,他的翻译是从爆裂的喉咙里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是“在死亡中自己绽开的词语之花”⑥王家新:《“喉头爆破音”——英美诗人对策兰的翻译》,《翻译的辨认》,第375页。。在《你,这从嘴唇采来的……》中有“你,这从咽喉撕出的/词结,以一种/光,被针和头发穿过,/在行进,行进”。此处的“撕出”带有一种撕扯的痛感,凸显出整个过程的艰难,这是对策兰生命本质的辨认,亦是在翻译中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在翻译《安息日》时,王家新感叹道:“这首诗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我似的。”①王家新:《越界的诗歌与灵魂的在场——答美国汉学家江克平》,收入王家新《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页。《安息日》也是一首言说死亡的作品,王家新翻译时用“纺着”“绕着”等字眼制造一种窒息感,最后以“在屈身之中”作结,王家新解释:“我们只有‘在屈身之中’,才能进入到策兰所说的‘我们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中。”②王家新:《越界的诗歌与灵魂的在场——答美国汉学家江克平》,收入王家新《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页。显然,王家新是以自身的痛感来感受策兰,用生命来辨认生命。
沿着策兰,王家新辨认出另一个独特的生命——曼德尔施塔姆。策兰在《下午,和马戏团及城堡在一起》中直呼“曼德尔施塔姆,我看见你”,作为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德语译者,策兰与曼氏有着相似的经历,策兰将曼德尔施塔姆视作精神同类,王家新捕捉到了两人之间的联系,由策兰而发现了曼德尔施塔姆。他在翻译曼氏的《曾经,眼睛……》时有这样的表达,“现在,在充满的光流量中,它勉力辨认着一道黑暗、孤单的星系”,“勉力辨认”与其说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话语,不如说是王家新的独白,是他对曼氏“辨认的诗学”的致敬与跨文化的认同。在《我多么爱这重压之下的人民》中,王家新译道“我多么爱这重压之下的人民,/他们睡眠,叫喊,生儿育女,/被牢牢钉进这片土地,/并把每一年当作一个世纪。”“睡眠”“叫喊”“生儿育女”三个词的并置,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重压下的生活状态,尤其是“生儿育女”一词的运用,显现出人们顽强抗争,只为活下去的努力;而“钉进”一词既有被外力摧残的意味,又暗示着人民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虽被恐怖笼罩,但人们早已根植在这片土地,世代繁衍,无法分割,如同被“钉”进去一样。这是对生的渴望,也是对暴力的无声抵抗,王家新在翻译时将自己完全放进这片土地,用自身的感受来体会“爱”和“重压”。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时,开头处的译文是“我又回到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泪,/我的脉搏,/我童年时肿胀的腮腺炎”。原文并没有“肿胀”的描述,因为腮腺炎的疼痛唤醒了他儿时留在身体里的记忆,他以自身的疼痛辨认出诗行间的生命细节,才有了“肿胀”这个与生命体验相关的词。
就像策兰呼唤曼德尔施塔姆一般,曼德尔施塔姆也以诗歌呼唤阿赫玛托娃,他在《致安娜·阿赫玛托娃》里写道,“你像个小矮人一样想要受气,/但是你的春天突然到来。/没有人会走出加农炮的射程之外/除非他手中拿着一首诗”。王家新翻译这首诗,某种意义上是借曼德尔施塔姆的声音向阿赫玛托娃致敬。王家新将阿赫玛托娃的一首作品译为《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其他诗人多半译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对此王家新指出,他愿意将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创作都置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读解”①王家新:《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洪子诚曾评价王家新:“血管里流动的可能有更多19世纪‘遗产’,一种混合古典精神和启蒙意识的浪漫、理想激情。”②洪子诚:《读〈塔可夫斯基的树〉》,《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这样的评价似乎从侧面解释了王家新为何在“没有英雄”与“没有主人公”之间选择了前者,与阿赫玛托娃诗作的气质不谋而合,她曾写下“所有未安葬的——我来埋葬,/我为所有的你们哀悼,但是谁来哀悼我?”(《所有未安葬的……》,王家新译)王家新被她“对苦难历史的承担、在地狱中的冒胆穿行及其反讽品质所深深吸引”③3 王家新:《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
阿赫玛托娃在晚年写下《科马罗沃速写》,诗的开头如此呼唤茨维塔耶娃——“啊,哀哭的缪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结尾处的“有一枝新鲜、黑暗的接骨木探出/那是——来自玛丽娜的信!”再一次强调了这种联系。王家新参观阿赫玛托娃旧居时,不断地吟道“哀泣的缪斯”④王家新:《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上海文化》2017年第7期。,在那个时刻,一股来自诗歌内部的力量把王家新推向这两位诗人。在王家新看来,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哀婉的、有耐心的女性的缪斯”,茨维塔耶娃的缪斯是“更勇猛、更有力量的男性化的缪斯”⑤王家新:《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茨维塔耶娃的诗》,《上海文化》2014年第7期。,他多次提到当年与茨维塔耶娃的“相遇”——泰晤士河桥头路灯下,一首《约会》让他“经受着读诗多年还未经受过的颤栗……”⑥王家新:《“披上你的光辉”:翻译茨维塔耶娃》,《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6期。茨维塔耶娃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诗歌,这种让王家新颤栗的力量拉近了二人精神上的联系。她的诗作《书桌》几乎凝聚了其生命的全部意义,王家新译为“三十年在一起——比爱情更清澈”,此处的“清澈”,把诗人与书桌之间纯粹的感情体现出来,这与后文的“钱,账单,情书,账单”以及“绝不接受账单和残羹剩饭”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茨维塔耶娃将生命奉献给诗歌的决绝。这种“献身”不仅是茨维塔耶娃的献身,也是王家新本人对诗歌的献身,他在翻译中辨认原诗的生命,辨认原诗所表达的精神理念与生命价值观,构造属于自己的诗歌精神谱系,“辨认生命”是其翻译诗学的重要内容。
二 译诗追求“更高的忠实”
王家新曾经直言“我的翻译观的前提仍是‘忠实’”①王家新:《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第185页。,但他也提出:“如果不能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赋予原作以生命,这样的‘忠实’很可能就是平庸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②王家新:《“创造性翻译”理论和教学实践初探》,《写作》2018年第6期。王家新所信奉的忠实,并非逐字逐句进行语言间的转换,而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原语文本面貌的前提下,抵达原作的精神和诗质。他认为评判一首译诗“是要看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前提下,能否在汉语中创造出无愧于原作的‘对等物’”③王家新:《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诗潮》2015年第4期。。在王家新的翻译观中,“忠实”与“创造性”并不矛盾,翻译需以忠实为基础,同时赋予诗作更多的灵魂,达到“更高的忠实”。
王家新的翻译不少属于依据英译本进行的转译,如何做到在转译时“忠实”于原作?历史上不乏优秀的译作由不通晓原作语言的译者翻译而来的例子,埃兹拉·庞德不懂中文,他根据中间语言将中国古典诗歌转译为英语诗歌,虽然某些细节难免变形、丢失,但从整体上来看,他的翻译把握了中国古典诗的精髓。要达到此种境界,不仅需要掌握恰当的方法,更需要对翻译对象有透彻的理解。叶维廉称庞德“能够领会原作者的核心思想”,拥有“过人的洞察力”④Wai—LimYip: Ezra Pound’s ‘Catha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p.88.。王家新持守诗歌翻译是“诗”的授权的观念,在他看来,“如果一个译者不能与原作达成更深的默契,不具备一颗敏感的诗心和与原作者相称的语言技艺,那就无法胜任这种‘授权’”⑤王家新:《翻译的授权:对阿米亥诗歌的翻译》,《翻译的辨认》,第286页。。王家新以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力为基础,充分领悟原作的精髓,与原作者心灵相通,获得诗歌的授权,进入更深层次的翻译,达到“更高的忠实”。
王家新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环形的海湾敞开》时,将最后几句译为“你——深喉音的乌拉尔,多肌肉的伏尔加……而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来呼吸你们”。他知道“深喉音的乌拉尔”“多肌肉的伏尔加”等与原文有所出入,但他坚持“只有以这样的‘再创造’,才配得上曼德尔施塔姆在语言上惊人的创造力,也只有这样来译,才能给我们自己的诗歌带来一种灼热的语言上的冲击”①王家新:《辨认的诗学——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及其翻译》,《翻译的辨认》,第272页。。在他看来,翻译要以具有张力的语言表现原作内在的生命与诗意,通过“再创造”使译作具有诗性力量。在翻译洛尔迦的《黑暗爱情秘密》时,他“冒昧替洛尔迦在汉语中写起诗来”②王家新:《“绿啊我多么希望你绿”——洛尔迦诗歌及其翻译》,《翻译的辨认》,第328页。,将最后的意象大胆地翻译为“炸裂的荆棘”,他认为是“诗”赋予了这种创造性表达以权利,这无疑抓住了译诗的诗性诉求与本质。王家新曾说:“我想任何翻译都伴随着‘抵达之谜’,这个‘抵达之谜’就和‘忠实’相关联。我们看到过那种亦步亦趋的、表面的忠实,也看到过一种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③王家新:《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第185页。王家新追求的是“更高的忠实”,探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诗歌从形式到精神层面的声音,他的翻译是在贴合原作的内在灵魂,赋予译文独立的诗性和生命力。
在翻译保罗·策兰的作品时,王家新将这种诗人间的交流上升到互相信任的程度。他翻译的《死亡赋格》中有诗句“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我们在早上喝在正午喝我们在傍晚喝/我们喝呀我们喝”,语气词“呀”是根据对全诗语感的把握加进去的,他认为这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原诗的语感。”④王家新:《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与北岛商榷》,《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这种大胆的尝试,是充分体会到策兰灌注在整首诗中的悲怆之情后所做的更契合原诗内在声音、语调及节奏的“再创作”。《死亡赋格》在中国存在数个版本的译文,王家新的版本用极强的张力和高度的紧张感制造出悲怆气氛。例如“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躺在那里不拥挤”中的“不拥挤”所带来的空间上的窒息感;又如“他瞄得很准”一句中的“瞄”,拉近了与死亡的距离。曾朴曾经提出:“我们译诗,先要了解诗人个性的总和,然后再把所译的诗细细体会,不要把它的神韵走了丝毫的样,那才能算得了神韵。”①曾朴:《读张凤用各体诗译外国诗的实验(节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王家新翻译的《死亡赋格》便是在反复揣摩作者心性后准确把握住了原作的神韵。
在分析王佐良翻译的奥登诗作《蒙田》时,王家新评价:“王佐良的译诗体现了对忠实的追求与创造性翻译之间的辩证关系。”②王家新:《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关于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对杜甫《对雪》一诗的翻译,他直呼:“这种‘大胆’的、出人意外的翻译,可以说创造出了另一首诗,却又正好与杜诗的精神相通!”③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在王家新看来,“更高的忠实”是真正“抵达”原语诗的途径,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对于穆旦的翻译,王家新指出:“他通过他的翻译所期望的,正是一种‘真正的诗’的回归。”此处的重点是“真正的诗”,即诗歌翻译的核心诉求是“诗”,也就是在“诗”的意义上看待诗歌翻译问题。王家新认为穆旦的翻译体现的是其“对那些具有永恒价值、贯通古今的诗歌精神的确立和把握”,这里的“诗歌精神”就是诗之为诗的精神,即诗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体现了他对诗与现实、诗与诗人、诗人职责以及诗的功能的思考。也可以说,他把这首诗的翻译,作为一种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④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翻译的辨认》,第87、89、90页。与其说王家新是在谈论穆旦,不如说他是借穆旦来阐述自己的诗歌翻译思想,即诗歌翻译是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是通往更高的忠实的路径,是诗性的再创造。
三 诗歌翻译是对语言的刷新
作为一名诗人译者,王家新对翻译与语言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新诗史上一些优秀的诗人译者,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乃是为了语言的拓展、变革和新生。”⑤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诗歌翻译可以借助域外语言以质疑、破除母语中那些抑制表现力的惯用语,重组语词,丰富语汇系统,简言之,就是刷新既有的语言系统。翻译是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桥梁,译者的重要使命是通过翻译引进异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为了母语的成长,促使语言的更新。
王家新在语词的使用上追求陌生化效果。他在翻译叶芝、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作品时,都用到了“死床”,如“死床的混乱结束”“死床不再可怕”“躺在我的死床上”等。“死床”不是汉语通用词汇,而王家新认为没有其他词汇比这两个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诗含义,他对翻译的要求是“宁愿‘自造生词’也不套用现成成语的”①王家新:《奥登及其翻译》,《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第166、166页。。陌生化语词考验着译者的语言创造力,属于有难度的翻译,在他看来“我们可以在翻译时调动汉语言的资源,但目标应是对语言的激活和刷新”②2 王家新:《奥登及其翻译》,《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第166、166页。。一种语言服务的对象是另一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应当建立起必要的联动性,实现语言的革新。他认为现代汉语“要求的只是不断的拓展、吸收、转化和创造”③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收入王家新《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这里的“拓展”、“吸收”、“转化”以及“创造”是建立在对不同文化内涵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语言表象的一种处理,最终目的是为语言注入生机和活力。
王家新曾提到诗人帕斯的一句话:“翻译与创作是孪生的行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的交往,一种持续的互相孕育。”④[墨] 奥克塔维奥·帕斯:《论诗歌的翻译》,赵振江译,《诗刊》2014年2月号上半月刊。在他看来,翻译反过来影响着译者自身的语言表达习惯,使其创作中的语言无形中发生改变,融入新的元素,促使创作实现突围,所以在翻译的同时,他没有停止寻找自己诗歌艺术的突破口。在从事诗歌翻译之前,王家新的作品更多描写的是古老中国的山水意境,如《河西走廊》《中国画》《空谷》等;从事诗歌翻译后,他认识到自己应对“语言的创造、语言的‘自我更新’作出贡献”⑤王家新:《辨认的诗学——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及其翻译》,《翻译的辨认》,第271页。。例如他创作于1993—1994年的作品《纪念》,其中的部分章节从词语的选择到语气的停顿与转换,再到书写对象,都与前一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诗人的视线也从古老的中国大地转向西方世界。诗中出现了“众神的土地”“凯撒大帝”“帝国的意志”等非传统的新词,其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中还出现了希腊神话中的语言元素——“抵抗着塞壬诱惑的奥德修斯”(《伦敦随笔》),而《欧罗巴的秋天》《斯卡堡》《临海孤独的房子》《布拉格》等诗歌仅从诗题便可发现其异域特征。王家新曾经说:“我们需要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读到几首好诗,在根本上正如本雅明所说,乃是为了‘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自己的语言’。”①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坐矮板凳的天使》,第103页。王家新个人诗歌风格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西方诗歌的钻研和翻译,翻译带来的不仅仅是语词、语法及句法上的变化,还有诗歌深处“纯语言”的更新,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都不可能只在自身单一、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它需要在‘求异’中拓展、激活、变革和刷新自身”②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王家新的语词系统与表意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柏桦认为:“王家新正是从《日瓦戈医生》这部‘巨型词典’(罗兰·巴特语)中抽出了一套文本进行改写和重组,并在改写和重组中连接了自己的生命经验。”③柏桦:《心灵与背景:共同主题的影响下——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影响》,《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罗振亚认为:“王家新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互文,不过是在《帕斯捷尔纳克》中把后者被翻译的诗《二月》之句‘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改写成‘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④罗振亚:《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这些都是中肯之论,但也应当认识到,王家新所做的并不是对原文进行简单的拼接或者摘取。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⑤[法]罗兰·巴特:《本文理论》,转引自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可以认为王家新是在用“互文”的形式与西方诗歌发生联系与交流,更新着自己的语词和诗歌意识。王家新认为:“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一直在起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比创作本身更重要的作用:它已在暗中构成了这种写作史的一个‘潜文本’。”⑥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坐矮板凳的天使》,第 102页。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从诞生之初,评论者在提及它们时都无法忽视其与《日瓦戈医生》之间的联系,某种角度来看,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在这种反复争论、不断研读的过程中,二者已经演变成了《日瓦戈医生》的潜文本。
语词系统的更新最终带来了诗歌风格的转变。在《最后的营地》中,既有“生,还是死”这样不朽的莎士比亚之问;又有“一,或众多”这种让人联想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王家新一方面吸收西方诗歌的语词、语法及句法等特点,另一方面保留中国诗歌的血脉,因此西方诗歌的思辨性、逻辑性和中国诗歌的韵味得以融合。他的诗片断系列《反向》便有这样的特点。当一个人来到远方时,他的内心被质朴的北方大地所召唤,先是“为了让你看它最后一眼”,在与这片广袤的土地互相凝视之后,诗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的家园在哪里?”这首诗原本是对现实中家园、故土以及归属感的追问,而诗人是没有“家”的,他在语言中漂泊,他的泪水,不仅是为家园所流,更是一种对语言的奉献。王家新用思维逻辑的递进串联起整首诗,同时灌注以原始的情感,将理性与感性相融合,这便是他所说的“当语言的封闭性被打开,当另一些语言文化参照系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无论在他们的创作中还是在翻译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语言意识”①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王家新使得自身语言具有一种“放射性”与“收缩性”——前者是翻译之功,后者则是回望传统的结果,在融合中形成一种全新的语言意识,完成诗风的转变。
王家新所建立的关于翻译的诗学理论,体现出他对诗歌翻译的重视。王家新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受了磨难和洗礼,燃烧自我的“牺牲”精神,使其译作在语言之外仿佛都有一个灵魂,翻译联结了王家新的生命与创作,他的翻译诗学是其生命与诗创作意识的体现。